第2章 15分钟,36分钟,还是36小时
转化模型
安迪·沃霍尔说:“在未来,每个人都有成名15分钟的机会。”然而,一只无形的手在放慢人类行动的进程,在今天这个信息饥渴的时代,一条新闻在多长时间之内才算新?我们真的能度量转瞬即逝的成名吗?
当电视和电脑的屏幕变得可以互相转化且多样化,使得新闻和娱乐更具自主性的时候;当思想理念、凡人凡事从忘却的记忆中重现,曝光在聚光灯下受人仰慕、厌恶或大展魅力,而最终又被人遗忘的时候,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名言:“在未来,每个人都有成名15分钟的机会”,现在看来比他在1968年初次说出时要更加接近现实。
《时代》杂志在2006年将“你”评选为“年度人物”,承认了这一趋势。的确,是“你”通过YouTube、聚友网、维基百科、facebook以及《美国偶像》,将以前那个只有像爱因斯坦或沃霍尔这样的头号天才才会受人敬仰的社会,变成了只需15分钟的曝光机会、普通人也能闻名世界的社会。Fame(出名)已经让位于Fameiness(我出名)[1]——这是《洛杉矶时报》一个专栏创造的词汇,用以形容这种转瞬即逝的“以我为中心”的出名方式。
未来还无法检索。我们紧绷神经游走在它的边缘,努力吸收徘徊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各种信息。人们如饥似渴地期待下一个头条,所以现在的头条总免不了被遗忘。一个故事可能会引起新闻界的广泛关注,不过一旦新的情况出现,老故事就会很快,且不可避免地失去新闻价值。
当然,这只是公众和媒体之间社会契约的一部分。正如雪花一接触温暖的手指就会融化,新闻也只是在你接触它的第一时间才显得重要。新闻就应该是新的,要不断更新以满足人们定期追踪的欲望和需求,要让昨天的报纸变得毫无价值。你必须快速阅读,因为这一章可能马上会变得无关紧要。
爆发洞察
沃霍尔说对了吗?真的只需要15分钟吗?还是必须要花上半天时间?或许更短,只需要5分钟?在如今这个信息饥渴的时代,一条新闻在多长时间之内才算新?我们真的能度量转瞬即逝的成名吗?或许你会觉得这些问题很傻,但它们绝对不是微不足道的。一旦我们将它们放在科学和魔法下审视,它们就会揭示出人类行为的奇妙与不可思议。
一条新闻的半衰期
在盖瑞·卡尼斯标记钞票的第二年,我利用年假离开了美国,前往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Collegium Budapest)。
这个研究所位于布达城堡中心处一座16世纪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的壮丽建筑中。这里原是布达城的市政厅。当1873年位于多瑙河两岸的布达和佩斯合并,更名为布达佩斯之后,这座建筑的原主人就不存在了。1992年,这里成了新成立的供进修深造之用的研究所。它是一个精英聚集的研究所,每年都会吸引世界各地的学者到访。
研究所有个著名的罗马尼亚设计师,他参与设计了无数正统教堂建筑,他告诉我,过去的教堂总是建造在神圣的地方。山顶或高地是首选,因为它们能让会众更加接近上帝。其他的吉祥地还包括四通八达的道路交叉口、十字路口以及市中心。
根据这样的原则,加之这座建筑自1265年起就坐落在了匈牙利最高峰的顶端,那么据此判断,如今的这座研究所过去肯定是一座教堂。厚厚的墙壁加上幽深的窗户,让很多大厅都散发出一丝修道院的气息,也让研究所显得异常壮观。置身这样的深墙大院,总是让人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不敢有一丝妄念。
我的上一本书《链接》的匈牙利文版恰好在年假期间出版。翻译事宜由脱离前匈牙利国有电话公司的网络公司赞助。公司总裁乔治·西蒙(György Simó)是一位社会学家,大学毕业后就参与经营匈牙利首个地下社区广播电台。1997年,他进入国有电话公司,创立了Origo.hu,并很快使其变成匈牙利最大的门户网站。2003年春天,我跟西蒙以及他的另外两个朋友共进晚餐,并聊起了《链接》以及联络的话题。
那个时候我对网络科技的另外一个大问题颇感兴趣:网络是如何被利用的?一个网站何时会访问万维网?人们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相互影响?遗憾的是,这些重要数据都由一些大型公司掌握,而他们通常将这当做商业机密小心保管不会泄露给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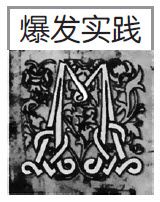
像谷歌和雅虎这样的网络供应商和搜索引擎,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将人们在何时做过什么事记录下来。但是,这些数据飞速地商业化使得那些乐于研究人类基本行为的科学家们无从下手。如今,谷歌是这一趋势的标兵,它那著名的“不作恶”理念就是一个巨大的智力黑洞。谷歌不惜挥金数十亿网罗业内顶级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然后将他们藏在位于圣克拉拉的谷歌总部中,让他们签署严格的保密协议,确保他们不会对外发表自己的研究发现。
2003年那个春天的夜晚,曾经身兼学院派与地下文学作家双重身份的西蒙细心地倾听了我的问题,并为我提供了帮助。第二天,他介绍了安德拉斯·卢卡奇(András Lukács)给我认识。卢卡奇是一位数学家,负责将访问Origo.hu的人们的网页浏览模型归档。他并不知道这些用户是谁,但每次只要有人登上网页,他都知道对方在浏览哪篇文章,以及在点击别的链接之前在这篇文章上停留了多久。Origo.hu每天的访问量非常之大,所以根本无法及时追踪某个用户。但数月之后,数据库会模糊再现一下百万人的点击状况。卢卡奇和他的搭档会从一个月的记录中,将能够识别出身份的个人信息从数据库中删除。一个月的点击率通常是650万,相当于整个匈牙利网页点击量的40%。利用他们提供的信息,我们差不多有机会了解匈牙利全国人民的网页浏览习惯。
利用卢卡奇提供的浏览记录,我在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团队中的研究生研究员佐尔坦·德若(Zoltán Dezsó)和博士后助理艾文德·阿尔马斯(Eivind Almass)试图解答下面这个问题:
在一定时间内,Origo.hu上某条新闻的受访时长是多少?换句话说,每个15分钟曝光时长的新闻实际能坚持多久?为了找到答案,他们决定先统计出每小时浏览某篇文章的人数。结果毫不令人吃惊,一条新闻在网上发表后,在最初的24小时内的访问量占总访问量的28%。第二天,点击量会明显下降,总共只占总访问量的7%。
这肯定是有道理的:如果你对一条新闻感兴趣,在浏览网站时肯定会先读它。到了第三天或第四天,所有对这条新闻感兴趣的人,应该都读过了,就不再有人读了。问题是,事实并非如此。大部分新闻在发布很久之后,仍然会被阅读很多次。
这似乎令人难以理解。首先,这些文章很久之前就已经被撤下首页,那么人们是怎么找到它们的呢?其次,为什么会有人对旧新闻感兴趣?
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一些文章会在热门论坛上重获新生,有些网站也会进行转载。但第二个问题就不那么容易回答了:为什么有人会定期查看一周甚至是一个月之前的旧新闻?
神选之子与贤者之石
土星上藏身着不死灵魂。用它的枷锁禁止它去看,因为之后那上面就会出现一颗善良的东方明珠。土星和火星用爱的纽带连接起来。它耗尽了强大的力量用灵魂劈开了土星的身体。从它们的连体之躯形成那不可思议的明亮之水,有太阳落入其中。金星是被火星拥抱的最明亮闪耀的一颗星。它们的力量应该结合起来,因为她是太阳和我们真正的亮银之间唯一的纽带,利用她可以将两者永远地结合起来。
这个文章片段写于1670年,作者“神选之子”(Jehova Sanctus Unus)试图说明行星在亲属关系以及爱情中所起的作用。这是占星家们今天仍然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然而,文章的实际意思并非字面上表达的那样。文中提到的“土星”不是指一个星球,也不是指罗马之神,而是指代“辉锑矿”,其主要成分为化学元素“锑”。“不死灵魂”也不是指某位神,而是指代“锑”本身——一种一经加热就会挥发的不稳定元素。“金星”代表“铜”,“火星”代表“铁”,土星吞没火星是指借助铁将辉锑矿还原为锑。最后,“那不可思议的明亮之水,有太阳落入其中”并不是描绘海上日落壮丽景观的诗语,而是指金子溶解于水银中的景象。
这个如谜般难解的片段说的不是占星学方面的事,而是在说它的近亲——炼金术。它用一种密码般的语言道出了将普通金属转化成“贤者之石”的秘密公式。整个中世纪,炼金术士们都坚信这种石头能够去除任何金属中所含的杂质,使其变成永不褪色的不朽黄金。同时,“贤者之石”也能治愈人类的疾病,所以它是人类超越自然力量的最终象征。
虽然“神选之子”如今并不为人所熟知,但在他生活的时代他却是举世无双的天才。他解开了自然的密码;他的盛名让爱因斯坦都甘愿称他为“值得我们膜拜的天才发明家”。究竟谁是“神选之子”?究意谁是本始智慧,谁是从摩西以及包括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在内的世代贤哲们手中传下来的神秘智慧的拥有者?
1936年,久负盛名的苏富比拍卖行拍卖了329份手稿,其中三份详细记录了尝试制造“贤者之石”的实验过程。这些手稿的作者在1727年去世前,在手稿上面明确标注了“不宜出版”的字样。保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这份文件揭露了“神选之子”的真正身份,而这个人一生都在尝试将普通金属变成黄金。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伊萨克·牛顿爵士。
众所周知,牛顿从未成功地将锑、铅以及其他金属变成黄金。即便如此,这一时期的他却相当高产。在进行炼金实验的间隙,他写出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一部解开万有引力以及行星运动之谜的见解深刻的数学专著。然而,他终其一生研究的炼金术却没有成功,这个谜在两个世纪后才被破解。
1901年,当弗雷德里克·索迪(Frederick Soddy)目睹了放射性钍自动转化成镭之后,兴奋地冲着他的同事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喊道:“卢瑟福,这就是转化(炼金术术语)!”卢瑟福并没有跟他的朋友一样因这个发现而感到兴奋,他冷淡地说道:“索迪,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把这叫做转化好吗?他们会像杀掉炼金术士那样砍掉我们的脑袋的!”最终,他们凭这个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彻底证明了不借助人类的力量,一种元素确实能够转化成另一种元素。
尽管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和亨利(Henri)早索迪、卢瑟福一步观察到了镭变成铀的过程,但因为卢瑟福成功地量化了他的发现,列出了转化定律,所以他赢得了诺贝尔奖。他的观点很简单:所有镭原子都是相同而无法分辨的,因此它们随时都有均等的机会转化成钍。也就是说,一个镭原子受某种“不可救药的自杀式狂热”的驱使而转变成钍的时间在本质上是随机的。卢瑟福根据他的实验数据推导出,镭原子的数量迟早会按指数律减少。
36分钟,还是36小时
现在,让我们回到匈牙利以及门户网站Origo.hu上来。想象一下,如果每个登录网站但并未阅读某条新闻的网民都是一个尚未分解的镭原子的话,出于某种致命的好奇,他们会打开这条新闻的链接。而对并不知道这些访问者的计划和动机的我们来说,他们阅读这条新闻的时间就是随意的。一路下来,他们就构成了一种类似镭原子随意分解的模型。因此,根据卢瑟福的理论,我们就能推导出一个数学关系,以此计算出那些尚未浏览自己感兴趣的新闻的网民的数量。计算结果表明,潜在读者的数量在快速减少,实际上,正如卢瑟福的转化定律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数量是按指数律减少的。
这个理论的迷人之处在于它很简单:你只需一个参数——一个用户每天点击链接数的平均值,就能推导出每条新闻的访问历史。这个参数很容易得到,因为数据显示一个用户每天将在网站上点击26次。有了这个条件,将卢瑟福的理论用在网站上就会得出一个非常特殊的结论:一条新闻在发布36分钟后,超过半数想阅读它的访问者就已经点击访问了。也就是说,一条新闻的半衰期大约为36分钟。
36分钟和15分钟并非天壤之别。事实上,这已经相当接近了。所以,经过严密的计算和推理,我们最终证实了安迪·沃霍尔关于出名的观点的正确性。虽然沃霍尔说的是人出名,而我们关注的是新闻“出镜”问题,但其实无论是刚出道的女明星本身,还是她所制造的言论,沃霍尔的看法都一样。然而,沃霍尔是如何在1968年就看到今天人们的行为模式的呢?仅仅是个巧合,还是他的先见背后藏着某种更深层次的真相?
但是,最终,我们的推导并没有站住脚。实际上,我们很快就意识到不依靠理论和模型也能直接测量出每条发布在网上的新闻的半衰期。结果是令人沮丧的:我们的测量非但没有证实沃霍尔的15分钟理论,而且连我们的36分钟理论都推翻了。实际上,半数用户点击某条特定新闻需要的时间是2100分钟,也就是将近36个小时。因此,我们的推测以及沃霍尔的观点都与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
你可能会问又有谁在乎这些呢?也许你是对的——无法精确地定位帕丽斯·希尔顿闯祸新闻的持续时间可能还算幸事一件。有哪位自重的科学家会把精力放在这种蠢事上呢?
爆发洞察
坦白来讲,我们关心的是帕丽斯·希尔顿还是安迪·沃霍尔,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也并非为此困扰。我关心这些事并不是因为我真的需要知道Origo.hu上一条新闻的半衰期,况且直接的测量已经表明这一数值是36小时。其实,真正困扰我的是,为何我们的预测和实际测量之间存在那么大的差异,这意味着我们对网站访问过程的理解存在问题,而且存在着很大问题。转而来想,这同样意味着我们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也严重受限。
放慢人类进程的手
卢瑟福有句傲慢的口头禅:“自然科学指的就是物理学,其他学科都是集邮一般的小儿科。”诚然,物理学的终极追求就是探究基本原理和理论,而这正是现如今取得的很多重大进步——从晶体管到太空旅行的基础。然而,其他科学分支也同样在探究这些问题。生物学家需要面对复杂无比的细胞,脑科学家要应付不可思议的神经系统,而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大家不断质疑迷宫般的社会和经济进程(像经济泡沫和经济危机等)根本不存在基本原理之前,还处于困惑不已的状态中。相比而言,也有很多人会批评物理学家对探究普遍原理的坚持,认为他们不仅是误导而已,更糟糕的是他们终会走向失败。
鉴于本书目前提到的两次失败的研究方案——德克·布洛克曼关于人类旅行原理的发现以及我们对追踪网页访问现象的努力,那些怀疑论者将更加坚持他们的观点。的确,这两项实验证实了将物理学方法应用于人类行为研究上存在局限性。虽然卢瑟福的指数原理精确地说明了转化问题,但它却不能解释网页访问量的减少问题。同样,爱因斯坦的扩散理论很好地捕捉到了原子的不规则运动,但却不能正确地预测出钞票的流通规律。
同样令人困惑的是,这两次失败存在着某种相似之处。在这两个案例中,我们预测出的周期值都太短。实际上,美元的流通速度比用爱因斯坦的扩散理论推出的结果要慢很多,而实际的网页访问半衰期也要比利用卢瑟福的模型推测出的时间长很多。也就是说,这两项实验都暗示了有只无形的手在放慢人类行动的进程。预期与实际的差异确实令人沮丧,但它也提出了一个更加惹人深思的问题:究竟我们能否像描述物质世界那样精确地描述人类行为?
如果新闻节目可以播报未来
现在,你只需花上24999美元就能请伊利诺伊的一家公司将你的亲人的骨灰变成一颗1.5克拉的钻石。尽管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愿意看到自己的祖母变成一枚钻石戒指,但我不得不佩服市场针对这些高科技做出的大胆尝试。严格来讲,这并不是炼金术语中的转化,因为骨灰和钻石都是由碳元素构成的。不过,他们做得不错,不是吗?1980年,继欧内斯特·卢瑟福之后,格伦·西博格(Glenn Seaborg)再次成功地从铋元素中分离出黄金。这一壮举无疑会让牛顿感到骄傲。但是西博格发现这一过程消耗了太多的能量,几乎没什么经济价值。
爆发洞察
不过,西博格的成功确实能够说明,定量法适用于一些科学家们长期怀疑,甚至是幻想的命题。
那是不是可以说,如果我们完善科学方法,总有一天能够在研究人类行为上取得一样的成就?我们能不能把它转化成一项精确又可预测的科学?我们能不能通过定位病毒的走向,精确地告知人们哪个街区明天要做好防御准备,以达到避免下一次大瘟疫扩散的目的?我们的晚间新闻会不会不再需要播放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可以像天气预报那样播报未来几天的人间世事?
但另一方面,这些问题远远超出了现有的学术能力,以至于大部分科学家都选择绕道而行。现在,我们甚至都不清楚到底哪门学科最适合解决这个问题,也不知道它能不能胜任。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还是某一门社会科学?不管怎么样,现在看来,预知人类行为的重任是落在了商业顾问以及算命师的肩上。
虽然他们的预测可能是瞎编乱造,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正是那些不受世间金钱琐事叨扰的算命师和预言者,决定了一个王国、整个十字军,还有离我们更近的,一个商业帝国或整个经济体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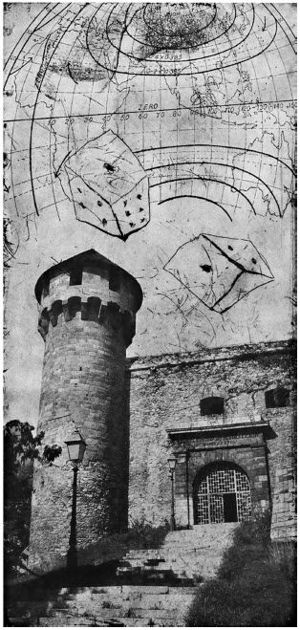
血腥预言
地点:布达城的皇宫
时间:1514年3月24日,乔治·塞克勒与伊派瑞斯的艾利决斗3周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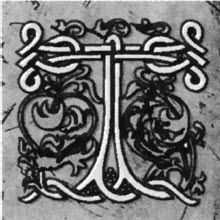
“如果将教皇的意愿传达给民众,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积极应召。”伊斯特凡·泰勒格迪若有所思地说道。[2]他毕恭毕敬地转向匈牙利国王乌拉兹洛,但却小心翼翼地将话锋指向周围的贵族。阴冷黑暗、修缮不周的宝殿里仍旧回响着巴科兹主教的声音,他刚刚向宫廷宣布了教皇的旨意。
两年前,正是在这座宝殿里,乌拉兹洛王及其心腹聚集在一起,与即将赴罗马竞选教皇的巴科兹主教告别。大家为他提供了中肯的建议、坚定的支持,并为他祈祷,还以重金相赠,送别这位匈牙利准教皇。但今天,离大家得知教皇宝座落入乔凡尼·德·梅第奇手中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匈牙利宫廷还是感到困惑:为何红衣主教团会抛弃精于外交的阴谋大师巴科兹,转而投票给一个乳臭未干、娇生惯养的奉承者?
巴科兹主教最近一直烦闷难耐,毕竟他曾那么接近教皇宝座。他曾跟人说起过当意识到自己已然击败对手的那一瞬间的美妙,不过最后竟意外发现自己出局了。巴科兹有所不知的是,他早已成了新故教皇的眼中钉。
教皇朱利斯二世临终前将自己的遗愿托付给了他的心腹:选谁也不能选匈牙利人。所以,为了防止巴科兹主教登上圣彼得宝座,卡斯特里西主教只能折中选择与宿敌乔凡尼·德·梅第奇为盟。在红衣主教团中,巴科兹已经获得了足够多的选票,但如若票数超不过2/3,他仍然无法当上教皇。年轻的主教们则希望他们中的一个人当选——一个年轻但不能在位太久的意大利人,这样一来他们仍有机会在罗马一展宏图。
手术新愈坐在轿子里的梅第奇成了最后的赢家。不过他的任期应该长不了。就这样,那天早上卡斯特里西主教投出自己的一票后,梅第奇就成为了新教皇。当一团团白色烟云升上罗马的蓝天,那些主教们才注意到他们疏忽了一件事:尽管梅第奇在30年前就已经戴上了主教的宽边红帽,但他从未真正承接圣职。不过,补救的办法很简单:第二天他将被授以圣职,第三天就为他举行主教授职礼。最后,在1513年3月19日,乔凡尼·德·梅第奇正式被加冕为教皇利奥十世。
“既然上帝给了我们神权,那我们就该好好享用。”利奥十世如是说,他也是这么做的。
但是现在,新教皇的旨意却在匈牙利宫廷中引起了一阵骚动。泰勒格迪继续谈论着那些可能对教皇的号召做出反应的人。“但什么样的人会应召呢?那些死刑犯,或是因犯罪而被驱逐出境的人?”他转向巴科兹主教继续说道,“那些背负耻辱、四处流亡,而且了无生趣,只有继续堕落和作恶的亡命之徒、债台高筑者、皮条客和暴民?”
然而,作为国王最信任的外交官,泰勒格迪并未意识到主教回到布达并非出自他自己的意愿,更不是他自己的主意。教皇竞选惨败后,作为梵蒂冈最有影响力的主教,巴科兹辞去了主教之职,打算在罗马度过余生。但是,在自我流放数月后,巴科兹又被授予了一项重要使命,或许这是那个世纪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攻克君士坦丁堡。
利奥十世希望将这颗50年前被抢走的东方基督明珠从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夺回来,所以必须成立一支新的十字军。谁能担此重任呢?当然是这位来自数世纪来不断阻截奥斯曼土耳其人进犯欧洲的国家的主教了。
所以,巴科兹回到了布达。他是以宗座代表的身份回来的。他手中拿着教皇敕令,被任命为“匈牙利、波西米亚、波利尼亚、底特律、塞尔维亚、普路萨姆、俄国、利沃尼亚、 立陶宛、瓦拉奇、斯利姆、摩拉维亚、卢萨蒂亚、特兰西瓦尼亚、斯洛文尼亚、大麦町、克罗地亚和莫斯科”,也就是大部分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国家的代表。根据敕令,他可以为这场战役招募军队、征收税款,还会得到所有捍卫基督教精神的人们的宽容和祝福。正常情况下,只有教皇本人才享有这样的特权。但正如匈牙利国王以及他在朝中的心腹认为的那样,当下的情况再正常不过了。
虽然巴科兹主教被授予了空前的权利,但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有待解决:他需要佣兵百万才能攻克君士坦丁堡。但是这些兵力从何而来?环顾这座简陋的宝殿,我们就知道国王不可能筹到那么多军资。别看现在这么破败,这座曾经美轮美奂的布达城堡可是伟大的约翰·匈雅提之子马提亚王千里迢迢从意大利请建筑师来设计建造的。马提亚王发起建造了这座宫殿,但还没等建完他就西去了。现在,这座宫殿已变得如废墟一般。就算是在宫殿内部摆着国家最高权力宝座的地方,也处处显出破败之象。庭院里那座华丽的雕刻喷泉已经干涸,基座断裂的石缝中杂草丛生;破碎的窗户鲜有修缮,碎片沿墙跌落,在墙角堆成了一座灰尘满布的小山;阴森、凌乱的弃堡中到处都能勾起人们对过去辉煌成就的回忆。
那招募新军的资金怎么办呢?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乌拉兹洛绝对不会从自己的金库中拿钱出来。教皇敕令赋予的无上权利更多的是一种象征,周边的国家不可能去遵守。虽然已经向威尼斯以及其他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威胁的国家发出了支持请求,但巴科兹至少要花上好几个星期才能等来他们的答复。这儿有个问题:既然这位主教十分清楚形势不容乐观,他为什么还会同意在没有充足的兵力和资源的情况下组建十字军呢?那是因为他自有计划。
1456年,约翰·匈雅提挡住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铁骑,使基督教世界免遭蹂躏的一幕仍然让人们记忆犹新。他率领那支人数众多但缺乏训练的农民军,在贝尔格莱德击败了强大的穆罕默德二世。巴科兹主教只需重演这一幕即可——以教皇和神圣的十字军的名义招募农民从军,教他们打仗,让他们把君士坦丁堡抢回来。
泰勒格迪,这位富有的地主毫不掩示地说出了自己的顾虑。“我相信很多农民都会积极应召,”他说,“但是他们会不会只是想逃避辛苦的耕作、报复平时受到的不公,或是逃脱惩罚和严刑拷问呢?”
公元14世纪至15世纪,匈牙利人口激增,居民数量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了好几番,已经达到了大约35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受雇于农庄的奴隶和农民。由于贵族需要服兵役,所以他们的税收可免,但奴隶必须承担苛捐杂税。很多人都试图逃往城里,因为那里的税轻一些,但这却引来了贵族更加严格的看管。泰勒格迪的农庄里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在劳作,他非常清楚他们的处境有多艰难。虽然这位国王的亲信说得有理,但主教却确信减轻农民重负的最好办法就是带他们去遥远的战场,远离眼前的艰辛。而且,泰勒格迪并不是朝中唯一一个需要说服的人。
巴科兹主教的突然归来打乱了乌拉兹洛宫廷悉心维持的权利均衡。在这位主教离开匈牙利的两年里,他的权利已经由年轻的约翰·萨普雅王子接手。马提亚王驾崩后,只有3岁的约翰就被后来担任维也纳首领的父亲抱出了摇篮。这位父亲满怀信心地声称:“你将来一定会成为国王。”如今,年仅24岁的约翰·萨普雅已经是匈牙利势力最大的地主,而且作为特兰西瓦尼亚的总督,他统治着匈牙利大部分领土。
之前,主教在宗教和世俗规则面前都显得游刃有余,使得这位年轻的总督难以接近权力中心。但两年时间对政治运作来说好比永恒,那些效忠于萨普雅的朝中大臣早已爬上了布达城堡的权利顶峰。国王本人并没怎么参与宫廷权利纷争,他一直把精力放在对至爱亡妻的哀悼,以及对两个年幼继承者的教养上面。他对国家事务漠不关心,一遇到正事总是显出一副犹豫不安的模样。于是,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多勃雷”,即波兰语中“好”的意思,因为每次需要他签署文件的时候,他都这么说。
由于国王的懦弱,宫廷中的决策者由以前的巴科兹主教变成了现在的萨普雅。这位年轻的总督无疑会反对成立新的十字军。他对奥斯曼土耳其人并没有什么好感——事实上,正当巴科兹、泰勒格迪以及朝中众臣就教皇的敕令展开争论的时候,萨普雅正在前线跟奥斯曼土耳其人打仗。而他之所以反对十字军,是因为十字军会帮助主教恢复势力,这是他和他的支持者们不愿看到的。
在萨普雅不在的时候,他就只能指望这些追随者们约束主教的夺权行为。即便如此,萨普雅的阻挠运作还是非常顺利,因为泰勒格迪也算是他的自己人,而泰勒格迪似乎也对主教的计划感到困扰。
“如果贵族们抱怨土地杂草丛生,农民日常劳作的役租地荒废不堪怎么办?如果贵族因十字军带来的破坏和损失指责我们怎么办?如果他们监禁农民以阻止他们去从军,或者将应召归来的奴隶视为逃亡者,抑或是监禁从军者的家人朋友又怎么办?这是经常发生的事,而且我们将无法忘记自己的罪行,并最终因自己的贪婪尝尽苦果。另外,如果战争结束了,你还能让这群乌合之众继续听你调遣吗?”泰勒格迪咆哮道。然后,他又以一种灾难性的预示做了总结:“这些手拿武器的农民会不会反过来攻击贵族,以从现在的悲惨遭遇中解脱?那些配发给他们作为上阵杀敌之用的刀剑会不会反过来对准我们?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妻儿和手足都将被侮辱和蹂躏!”
泰勒格迪停了下来。主教谨慎地环顾四周,掂量了一下这篇黑色演说的威力。泰勒格迪太富有了,要收买他没可能,而且他对整个王国的命运的真诚担忧让很多人肃然起敬。他话语中流露出的无私公正,更加重了这番说辞的分量。他积极地说出了在场的每个人心中的困惑和不安。
“他能说服大家吗?”巴科兹主教在心里盘算着,“他会不会把十字军扼杀在摇篮里?”在他73岁高龄时,他的教皇梦破碎了,所以他没多少选择,他必须将宝押在一件事上:不惜一切代价率领十字军取得胜利,然后以英雄身份荣归罗马,使自己有机会再争教皇宝座。
[1] Luther,公元15世纪至16世纪抗议罗马天主教会的传教士。——编者注
[2] 钞票当然是经常在我们的钱夹外四处晃悠——它们偶尔会从商人手中回到银行,然后又转移到另一家银行或另一个商人手中。但比起我们带着它们四处旅行所走过的距离,这样的距离我们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作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