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谁掌控着我们的未来
第11章 爆发来到大数据时代
数据,是一把双刃剑
虽然我们的过去由安全防火墙和隐私法保护着,但通过精密系统的预测,我们的未来却极易被人掌握。未来比过去更具价值,那么谁掌握着我们未来行为的信息?谁又会从中获利?
处于测试状态的LifeLinear网的页面上没有任何图标、商标或标志语,只是在黑色背景上设置了一个简洁的白色搜索框,不禁让人联想到谷歌那干净的界面或是AC/DC乐队的专辑《回到黑暗》(Back In Black)的简洁封面。我将自己的姓“巴拉巴西”打进了搜索框中,按了回车键,电脑屏幕上就出现了一组名单,上面只有两个名字:
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布鲁克林,马萨诸塞州
丹尼尔·莱文德·巴拉巴西,瓦屏九瀑布市,纽约
我点击了自己的名字,页面上出现了一张熟悉的照片——是我穿着一件蓝色衬衫的照片,旁边配有我的基本履历资料,一眼就能看出是从维基百科上复制下来的。剩下的基本都是一些数据和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地名链接。
我点开了一个最近更新的链接,地址是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大街。接着,屏幕上出现了一则视频,上面显示的是涌入哈因斯地铁站的人潮消失在地铁入口处的黑色大门后的情景。两秒钟后,我在视频中看到自己推开了地铁站那厚重的大门,然后左转去了马萨诸塞大街。我并没有注意到摄像头,而是直接走出了它的监视范围。
另外一个链接上的时间显示是10秒钟后,点开后上面出现了一张一群年轻人站在马萨诸塞州收费高速公路的铁架桥上开怀大笑的照片。我的第一反应是那上面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但随后我马上意识到这张照片出现在我的条目下面并不是因为那些年轻人,而是因为背景中一个模糊的身影正是我,是我离开地铁站后被偶然捕捉到的。
然后,我又点开了一个链接,上面还是在马萨诸塞大街被捕捉到的一个小片段。这一次我从左侧进入镜头,经过柏克莱音乐学院,不一会儿就在醒目的基督科学会世界总部旁边从镜头中消失了。
每次看到自己出现在视频中,我总是会觉得浑身不自在。但现在可好,我的一举一动已经被LifeLinear网的系统给记录了下来。我接着往下点,一路跟着镜头中的自己进了我在东北大学复杂网络研究中心的办公室。目瞪口呆的我又点开了其他一些链接。最终,我意识到,不管我在哪儿,LifeLinear网上都有我的影像记录。通过整合陌生人、朋友或认识的人所拍的视频和照片,以及网页和博客的链接,我在私人住处以外的大部分生活都被分类保存在数据库中。
从数千人中找出某个人在前几年还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计算机任务。这项任务对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蓄着长长的白胡须的拉多万·卡拉季奇无疑是塞尔维亚最臭名昭著的战犯,但面部特征如此明显的他竟然公开在贝尔格莱德生活了好几年,期间跟他有日常接触的几百人都没能认出他来。事实上,LifeLinear的成功并非得益于面部图像识别系统这项发明的出现,他们所用的设备也并不比其他监控企业的好多少。他们之所以能够追踪到大部分美国人的生活片段得力于一颗执著的心: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跟丢任何人。
LifeLinear的前身是一家合资监视设备公司。他们在全美各地安装了几百万台无线摄像机,然后将反馈数据连接到了一个单条检索数据库中,并指示他们的计算机追踪所有运动中的人。他们的技术是在两个原理的基础上建立的。
●第一个原理就是LifeLinear编程师口中所说的“守恒定律”(Conservation Law):没有人会凭空出现或消失。换句话说,不管你是进了一座大厦、坐上了一列火车,还是乘上了一架飞机,你迟早都会从里面出来。
●第二个原理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根深蒂固的规律性生活导致了我们的可预测性。基于此,LifeLinear为每个人都建立了一个行为模型,然后仔细分析我们平时的方位,再预测我们将来的行踪。
比方说,他们的系统分析出我通常在中午12点和下午1点之间离开家。所以,当他们的街头摄像机在某天中午12点半的时候在我家门前捕捉到我的影像后,他们就不需要在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照片中寻找我的照片了——他们的软件已经知道在那个时间点出现在那个地方的人一定是我。
一旦我坐上市区列车,在接下来的20分钟内LifeLinear根本不需要费心找我。只有当列车差不多到达哈因斯车站的时候,摄像机才再次开始反馈我的信息,并意识到这好像是我最常到达的目的地。当我步行去办公室的时候,系统会用一台接着一台的摄像头追踪我的位置,并将记录下来的片段上传到我的LifeLinear页面上去。如果他们在哈因斯车站找不到我的踪影,也没什么大不了——他们的系统知道朗伍德站是我第二常去的站,因为如果我在哈佛媒体学院有课的话,我就会在那儿下。只有当我偶尔打破常规,打车上班或乘飞机旅行的时候,他们才会投入实时资源来追踪我。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LifeLinear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巨型机器”的化身。它也是臭名昭著的整体情报识别计划(TIA,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 program)[1]的公开版。
这个计划是由海军上将波因德克斯特(Admiral Poindexter)发起的,是一个以反对战争或打击恐怖主义为托词建立的,能够搜索大量有关商业、交通、金融、通信以及法律等方面数据的项目。但LifeLinear与TIA和“巨型机器”有本质不同:现实世界的TIA和虚拟世界的“巨型机器”是用来彻底搜寻个人和政府数据的,包括银行、电子邮件、电话以及联邦调查局记录。但LifeLinear搜集的是每个人都已公开的数据,比方说当我走在街上时被捕捉到的影像以及从一些网站上获得的我的个人信息。
这三个项目都侵犯了个人的隐私,而且很多人都认为应该将它们直接定为违法行为。但是美国法院一贯都规定公民在公共场所,比方说公园或街道上没有隐私权。所以,LifeLinear的创立者坚信他们的行为有坚实的法律依据。
归根结底,对大部分人来说,LifeLinear、“巨型机器”和TIA没什么本质区别,而且他们引发的另一个问题也同样令人不安:不管我们本人是否同意,就对每个人进行实时追踪真的可行吗?又有谁敢操作这个项目呢?在一个充斥着功能强大的LifeLinear、TIA或“巨型机器”的世界里,人们是不是就没有隐私可言了?
然而,人们为什么会有隐私期待呢?
越是相互依赖,隐私期待就越少
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村子里,婚礼前两三天,一群老妇人会聚集在新娘的屋子里清点佩内(perne)——嫁妆。这是一个由商业交易演变而来的仪式,佩内女和新娘家人之间的这种贵重物品交易是这里的一个古老风俗。清点完毕后,这些贵重物品将由一个佩内女通宵把守,直到第二天三辆马车来到为止。第一辆马车装亚麻织品,第二辆装家具,第三辆装剩下的其他东西。
热气腾腾、美味可口的肉汤在大锅里慢慢炖着,辛辣可口的辣粉肠和培根摆在盘子里,一个个玻璃杯倒满了果子白兰地,每个人都觉得温暖而幸福。新娘的父亲按照礼仪感谢那些帮忙往马车上装嫁妆的人,还不忘打趣着提醒他们:“你们要保证别把东西退回来!”一连串双关语、谚语以及诗歌,听起来好像是随口说出的俏皮话,但实际上都严格遵循着礼仪,而且是所有新娘在婚礼当天都必经的礼数。
当亲朋好友吃吃喝喝并往车上搬贵重物品时,旁边的一位妇女会仔细清点并做记录。她的职责就是保证床单、毛巾、床罩、枕头,甚至是新娘儿时的玩具都正确地摆放到马车上去。她不必将注意力放在整齐度上——她的职责只是保证每件东西都清楚易见。
装车完毕后,身着色彩鲜艳传统服饰的佩内女和她们的丈夫会唱起欢乐的歌儿跟着马车在村子里巡游一番,他们的歌声嘹亮清脆。村里的女人都走出厨房,男人都放下牲口,专心看着热闹的游行。吵闹的孩子和不知谁家的小狗一路跟在游行队伍的后面,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有热闹事儿就有好吃的东西。这个壮观而持久的仪式只有一个目的:让村里的每个人都能看到嫁妆。
塞克勒人在出生、订婚、结婚以及死去时都会举行各种仪式,因为他们坚信这样的大事不应该偷偷摸摸地举行。实际上,只有让部落里的人都看见才能证明这件事有效。
若孩子出生时没有办洗礼仪式,大家会说他“像狗一样取了名”;男女在订婚、结婚时没办典礼则会被认为是“像狗一样生活在一起”;而人死时没办葬礼则会被说成“像狗一样被埋掉”。
“为了上帝的荣耀和人民的快乐。”[2]塞克勒祈祷着。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一样会得到上帝和同乡的支持。自从乔治·多热·塞克勒开始了人生的冒险之后,家乡的人们仍然没有丢掉所有事情都要让周围的人知道的惯例和习俗。每个人的生活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爱情、偷窃、患病、困苦、友谊或憎恶,所以什么事都不可能瞒很久。知道邻居所有的事并不让人感到羞耻。那是维持部落团结安康的一种责任和必要因素。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小村庄里,大家对美国人所期待的那种高度隐私几乎闻所未闻。
当然,这是没得选择的,大家必须这么做。住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挨着天寒地冻的冬天,挤在喀尔巴阡山的大片松林旁,这里的居民必须学会互助互惠、互通有无。为了生存,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遭受战乱时,他们都必须互相帮助。如果不融入这种丰年时互通有无,荒年时互救互助的生活方式中,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被排挤到了边缘。
爆发洞察
观察这些塞克勒人的习惯能让我们一窥掌管我们隐私的一个基本方程:
一个社区里的人越是相互依赖,对隐私的期待就越少。人们越是需要家人和朋友,就越难以对某件事守口如瓶。只有在信赖金钱化的北美和西欧,人们才会要求独处的权利。
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幸福和健康的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朋友的数量和质量。所以,谁说我们做的就一定对?我们的隐私是不是拿幸福换来的呢?
无处不在的数据信息系统
2008年1月8日,我将这一章的草稿发给了艾妮可·扬科(Enikö Jankó)。她是一位专门帮我将手写稿打出来并备份的朋友。之后,我收到了她丈夫波尔迪萨的一条短信:
“LifeLinear的网址是什么?”他问,然后又说,“好像在谷歌上搜不到啊。”
我笑了笑给他回复道:“这很重要吗?”
“我可以用它查查我生日聚会那天大家是怎么胡闹的。怎么了?难道是保密的吗?”4分钟后他这样回复道。
我很高兴能抓到机会戏弄他一下,于是回复道:“没错。”不一会儿我又收到了一条回复:“你就告诉我吧!”
被我拒绝后,他开始瞎想,然后又马上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一开始他觉得我会拒绝向自己的好朋友透露这一信息,是因为我疯了。那后来的想法呢?“LifeLinear根本不存在。”他说。
他的第一个理由可能是对的,但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说的重点。有一件事无可否认:LifeLinear到目前为止只是我想象出来的。然而,波尔迪萨没有马上意识到它是虚拟的这一点,可以表明它不是那么令人难以置信。
爆发洞察
我从不怀疑现在的科技有能力造出LifeLinear这样的系统。我也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会生活在一个有TIA、LifeLinear和“巨型机器”的结合体出现的世界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主张或容忍这种监视系统。相反,基于我和我的团队针对人类行为所做的一些研究,以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一想到这种系统的潜在能力我就觉得毛骨悚然。
我想说的只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已经使造出像LifeLinear这样的系统成为了可能。而且,如果某项技术存在隐患,不管我们有多么不安,它的某些好处总能迅速诱使人们接受它。
“巨型机器”或TIA之类的系统必定要不断搜集我们的信息,就跟天气预报要依靠现在和过去的大气情况才能做判断一样。而如今这样的信息简直遍地都是:
●手机运营商掌握着我们的实时通信信息和行踪;
●我们的花销和旅行习惯对银行来说已不是秘密;
●我们的社会关系和个人爱好都被电子邮件供应商归了档;
●监视器会经常录下我们和身边人的一举一动。
虽然这些记录到处都是,但我们仍然对隐私保持着期待和幻想。我们总是自欺欺人,认为那些搜集来的信息都分散存储于不同的专门数据库中,要想跨越那么多障碍获得并将它们联系起来是不可能的。
然而事实上,“9·11”之后世界各地的情报机构已经投入了上百亿美元资金试图将平时搜集来的数不清的电子记录联系起来。哈桑·伊拉希在多年相安无事后因“形迹可疑”被扣留这件事,恰好证明了国土安全部正致力于将个人和政府的数据融合起来。虽然这些系统的预测能力不见得比得上虚拟的LifeLinear和“巨型机器”,但它们肯定就是以此为目标设计的。除非明令禁止,否则它们总有一天会实现那个目标。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我们能不能造出一个像LifeLinear这样的完美预测系统,而是谁敢去造,是政府还是私人呢?
没有隐私的未来?
在美国,我们经常会向公司透露我们的个人信息。作为交换,我们能获得一些真正的或认知上的利益,比如产品或服务的打折。然而,如果我们意识到政府正在搜集我们的个人信息,我们又会齐声抗议。欧洲干脆就顺着人们:法律明文禁止企业之间分享客户的个人信息,但欧洲联盟法规定所有通信公司都必须将客户的信息(包括个人的行踪和通信记录)保存6个月到两年时间,并与政府分享。
结果,美国人普遍认为企业是好的,但政府是坏的。欧洲人却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政府是好的,私企则是大反派。隐私到底有没有一个普遍的界定?如果有,谁会强制大家遵守?如果缺少强制性,又有谁会去造“巨型机器”?在欧洲,严格的隐私法限制了私营企业,所以政府赞助的TIA或“巨型机器”似乎更有可能出现。但基于美国制度与文化的禁忌和敏感度,如果真的出现一种无处不在的监视设备,那很可能是一种由私企开发的类似LifeLinear的机器。
有一家公司已经具备了将LifeLinear变成现实的技术和资源。它的名字叫谷歌。我相信你肯定听说过。
大数据时代的隐私保护
在过去几年里,我曾好几次打算放弃对人类行为的研究。科技已经远远超出我们能够合理运用的能力,而且我也不能保证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会被一些类似于“巨型机器”的不法企业利用。
我们的论文发表后,大篇大篇的新闻报道让人们注意到自己的很多信息都已经被记录了。一些人读到我们的论文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杀死那些提供这些信息的人,并将我们视为独裁者。不断的失眠促使我问自己,研究者的责任究竟是什么呢?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颖的问题了。它是萦绕在一代又一代科学家脑中的问题,而且涉及从核能到基因的各个领域。跟人类动力学一样,这些研究能带来巨大的利益,如新型药物的研究以及清洁能源的发现等。
现在,所有研究人类动力学的人都陷入了同样的两难境地:我们怎样才能避免为监视国家或大型联合企业的建立做贡献,让世界进入奥威尔在《1984》那本书中所描述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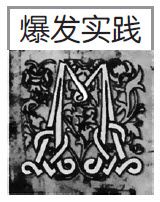
哈桑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
“所有情报机构,不管是哪里的,都是一个经营信息的企业。”他注意到。“它们的信息之所以有价值,”他补充道,“是因为没有人有权使用它。”
那他的解决办法又是什么呢?只要放弃了,它们就没价值了。“信息的保密性使它具有价值。”他如是说。于是,他就学塞克勒人那样将自己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自己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都上传到网页上。
但他真的放弃自己的隐私了吗?如果你打开他用于追踪自己的那个网站,你马上就会发现哈桑本人从未在他上传的几万张照片中出现过。没错,他就在镜头的另一边。他的相册里也没有经常出现的面孔。不管你花多久去浏览他的照片,你心里都会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他没有同伴,没有家庭,也没有朋友。你越研究他的网站,你就越想问:这些都是什么啊?我为什么要来看这个家伙用过的厕所和吃过的饭?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给你们看了所有东西的同时又什么都没给你们看。”他曾这样告诉我,“在那成堆成堆的数据中,我虽然公开了我的生活,给出了该给的信息,但实际上我的私生活相当保密。你可能知道我的财务细节,知道我住在哪儿,也知道我的房子是什么样儿的——你可能知道我所有的一切,但对我的私人生活你还是一无所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虽有悖于常理,但通过完全放弃我反而保护了我的私生活。当所有事情都摆在眼前的时候,反而没有人会在意了。”
遗憾的是,在涉及研究和隐私的内在冲突时,我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放弃学术研究只会让人类动力学的研究落入秘密政府实验室以及口风很紧的私人企业手中,他们绝对不会向公众透露半点信息。事实上,现在私企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远远超过学院派。谷歌的摇钱树广告联盟计划就是针对人类行为的一个大型实验,目标就是增大广告理论创造最大季度收益。
那我们还有必要进行学术研究吗?除了急于找出答案,我觉得自己更有责任将这门新兴技术的前景和不足之处公之于众。我杜撰LifeLinear主要也是出于这个考虑,我想阐述一下这一研究可能出现的结果。如果我们真的不想生活在一个处处受到监视的世界中,我们还是可以利用很多方法(法律和科技手段)来避免这一情况出现。
“准隐私”模型
在我们思考人类动力学研究的命运时,还有一个看似荒谬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的未来掌握在谁手中?现在,我们有数不清的隐私条款、规章制度以及实践经验保护每个人的数据。另外,我们心中抱有的一丝恐惧和小心也在更大程度上保护了我们的信息:从电子邮件供应商到手机服务商,大多数公司都太功利了,以至于他们不敢随便处理个人信息,激怒消费者。所以我们可以说,虽然那些数据存在很多潜在风险,但相对来说,我们的过去还是被保护得很好。
爆发洞察
未来又会怎样呢?我们的未来又受到了多少保护呢?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预测个体的行为已经变得非常容易了。未来比过去更具价值,因为我们的旅行和购物计划可能是商业圈中最有影响力的商品。虽然我们的过去由安全防火墙和隐私法保护着,但通过精密系统的预测,我们的未来却极易被人掌握。基于此,我想出了一个新的模型并称之为“准隐私”。简单地说就是:谁掌握着我们未来行为的信息?谁又会从中获利?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视角,我们需要借助历史来理解。虽然迄今为止我们遇到的所有事情都在遥远的过去发生过,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了它们的结果,但那些结果离我们还是很遥远。那些促使我们得出结论的战势也开始变得明朗了起来:在风扫落叶般占领了大半个匈牙利之后,乔治·塞克勒率军来到了泰密斯瓦,想在那里建立一个永久的根据地。无畏的副官洛林茨教友也迫使繁荣的科罗日瓦为他打开了城门。接着,那只沉睡的雄狮觉醒了。既然起义军都打到家门口了,特兰西瓦尼亚的总督萨普雅伯爵不会也不能再沉寂下去了。面对两场棘手的战事,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自己的军队分成两部分,分别赶赴两个战场。
所有事情都已就绪,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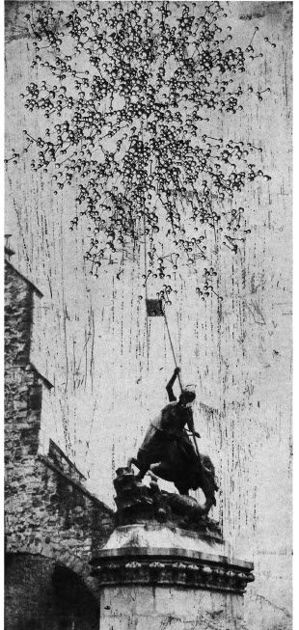
塞克勒人VS.塞克勒人
时间:1514年7月15日,大屠杀后不到两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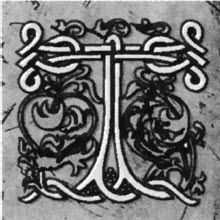
“现在轮到你们去惩罚那些可憎的敌人了!”乔治·多热·塞克勒用全军都能听见的声音大声喊道。他看着眼前这群两个月前追随他攻打内格雷克的士兵,包括商贩、铁匠、织工、裁缝以及几乎消失在大群亡命之徒和农民之中的市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然而,这里不是内格雷克,而是泰密斯瓦堡垒附近那广阔的尤里克斯田野。两个月的变化都刻在战士们那一双双透着经验之光的眼睛上:经历了多场胜利后,战士们那肮脏不堪的紧身上衣外都套上了盔甲。大部分人都扔掉了斧子和镰刀,换上了长矛和利剑。
战争对大家都造成了伤害,而这场战役将更粗暴、更残酷。他们不再是一群无知的惊兽,盲目地进攻之后看到快速冲来的骑兵又一齐逃跑。战争和苦难已经将这个队伍彻底净化了——弱者都已倒下,而那些失去勇气或信心动摇的人都已逃跑了。尝到并且已经习惯轻而易举就取得胜利的那群自以为无敌的幸存者,组成了一个非常奇妙的、纪律严明的队伍。
“为亲人的自由而战的时刻到了!”乔治·塞克勒用惯常的自信口吻说道。他深刻地意识到今天,特别是今天,他必须激发出战士们的所有潜能和士气。因为在他们面前那一座座连绵起伏的山里,身穿彩衣盔甲的萨普雅伯爵正在集合他的军队。那是一个可怕的劲敌,乔治·塞克勒非常清楚这一点。当他还是边疆一名普通的雇佣兵时,这个人的威名就已经响彻军营。
萨普雅的一线部队是一群可怕的撒克逊火枪手。他们个个头戴德式头盔,腰别火绳枪,肩挂子弹夹。他们身后是几千名手持长剑和长矛的乱成一团的农民军。虽然他们人数众多,但乔治·塞克勒并不把他们看在眼里。他知道自己的农民军比起这群被萨普雅强行拖上战场的可怜人更有经验、更坚强。
一排加农炮将步兵和后排分成左右两大边路的骑兵分开了。他们是重骑兵和骠骑兵的组合,骑手全是20~40岁的壮年男子。刺绣短上衣和醒目的队旗使他们成了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在马背上摇晃着身子,兴奋和激动不言而喻。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打气,兴奋地迎接这场即将打响的战役。就是他们让乔治·塞克勒感觉颇为棘手。他知道战场上制胜的关键就是快速机动的骑兵,而他那支以步兵居多的十字军根本不是这些特兰西瓦尼亚骑兵的对手。
“向那些毁了我们祖国的人复仇!打倒这群残暴的敌人!”乔治·塞克勒最后总结道。当战士们欢呼喝彩的时候,乔治·塞克勒的思绪仍然停留在特兰西瓦尼亚步兵身后那群人数虽少,却威猛无敌的骑兵身上。他和他们流着同样的血,因为他们都是塞克勒人。看着马背上的他们,他一眼就能认出来。然而,他们的队形和人数倒是令乔治·塞克勒感到很惊讶。按照以往的传统,在战场上打头阵是塞克勒人的责任。但总督这次却将他们和雇佣兵以及自己的宫廷卫队一起放在了主力部队后面,很明显是不想让这支强队在这场恶战中受到伤害。或者他是不是害怕塞克勒人会倒戈,听从自己的同族而不是他自己的命令呢?到最后,这就是一个优先权的问题。
但最让乔治·塞克勒感到困惑的还不是他们的队形,而是骑兵的人数。剩下那些人去哪儿了呢?一旦战事爆发,塞克勒人能够集结3万兵力,所以很容易派出1万人跟随总督上战场。但这支塞克勒骑兵队的人数却出奇地少,可能一共也就1000人。“剩下的兵力被总督部属到哪儿了呢?”乔治·多热·塞克勒心想。
虽然萨普雅的军队明显很有实力,但乔治·塞克勒一眼就能看出弱点——不仅塞克勒人不多,勇猛的撒克逊人以及罗马尼亚人也不见了。他们的缺席应该就是总督将经验不足的农民军编入队伍中的原因。所以十字军在人数和经验上的优势,让乔治·塞克勒觉得即使没有强大的骑兵,他们也有希望赢得这场战役。
与此同时,在离泰密斯瓦300公里外的科罗日瓦城内,穷人们已经当家做了主人。仗着十字军的统领已经在城里的客栈安了身,城里的贫民明目张胆地打劫了来城内避难的贵族。城外的情形也再令人激动不过了——十字军宰杀了城里人的牛,并将周围所有能找到的东西洗劫一空。不断扩大的危机让城内的大臣们方寸大乱,因为他们现在才意识到自己不仅管不了洛林茨教友和他在城外的部下,甚至连城内的局面都控制不了。
然而,城里的气氛很快就由欢呼雀跃变成了恐慌和困惑。食物的短缺,管理的缺失,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使贫民对十字军的热情降了下来。所以当士师突然变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放下闸门,将那群目无法纪的农民军关在城外的时候,城内的贫民竟然袖手旁观。城内,士师来了个瓮中捉鳖,将十字军的军官都逮了起来。
洛林茨教友在那个关键时刻应该不在城内,因为我们知道他逃过了这一劫。士师的突然倒戈应该不是一时冲动,他肯定已经听说救援部队就在路上。事实上,正当大家因十字军军官被捕乱成一团时,副总督巴拉巴西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兵靠近了城外十字军的营地。这支救援部队正是由缺席萨普雅在泰密斯瓦对阵乔治·塞克勒的那场战役的塞克勒人、撒克逊人以及罗马比亚人组成的。
7月中旬,所有战线都已准备就绪。在泰密斯瓦,乔治·塞克勒的十字军遇上了人数虽少但却更有经验,而且是由特兰西瓦尼亚的总督亲自领导的部队。在科罗日瓦,一支由副总督带领的由塞克勒人、撒克逊人以及罗马尼亚人组成的军队,正准备突袭洛林茨教友那支已经乱成一团的十字军。
两个战场,两场战役,每场的结果都不确定。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十字军打赢了总督的队伍,那整个匈牙利或者特兰西瓦尼亚都没人能阻止十字军的前进了。
[1] TIA的全称是整体情报识别计划(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它是一个政府项目,是由海军上将波因德克斯特发起的,是一个以反对战争或打击恐怖主义为托词建立的能够搜索大量有关商业、交通、金融、通信以及法律等方面数据的项目。——作者注
[2] 原文为匈牙利语:Isten Dicsöségére,emberek tetszésére。——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