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上帝从不掷骰子
泊松分布
只要遇到无法理解的事情,我们就会说那是偶然,似乎这种表面上的偶然行为推动了历史的演进,而事情发展之迂回曲折似乎如掷骰子一般。但这种偶然真正意味着什么?
1991年5月31日,正准备去后院泳池的莫莉听到了敲门声。当时还不到11点,她刚度过一个繁忙的早晨,她去学校取了成绩单,这学期也就算结束了。听到敲门声时,她正一个人待在位于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枫叶岭郊区富裕的家中。由于自己没有钥匙,这个聪明的11岁姑娘建议来访者跟她在后门碰面。
陌生人告诉莫莉,他是来整理院子的。这个人一副休闲打扮,小个子,很瘦,留着一头亮红色短发,脸上刮得很干净,但长了一脸痘痘。
莫莉很有礼貌地解释说父母不在家。她想快点结束这次谈话,然后去泳池游泳。
他似乎理解了。
不过,在离开之前他问了一下时间。
莫莉不知道几点了,但是她身后就有一个钟。
她转过身去看时间。
突然,门开了,还没等她回过神来,那个陌生人就用结实的手臂抱住了她。
案发时蒂姆在哪里
在南边320公里外的得克萨斯,蒂姆·德拉姆看着父亲的背影消失在达拉斯射击俱乐部的门后。听到门锁的咔哒声后,他收起了父亲的护目镜、耳塞,还有一把点410来复枪和一包点28口径的子弹。他拿着这堆东西上了一辆黑色林肯大陆。
富有的詹姆斯·德拉姆在塔尔萨经营着一家电器商店,同时他还是个双向飞碟射击迷,他的儿子蒂姆也是。他们一同驱车去达拉斯参加全美双向飞碟射击大赛,顺便拜访家族好友杰西和詹姆斯·斯普兹夫妇,并与他们共度周末。
老德拉姆参加了比赛,而小个子、红头发、满脸络腮胡的蒂姆被禁止用枪,所以就去当了裁判。
第二天就是蒂姆29岁的生日,他很期待斯普兹家的女儿们为他准备的生日派对。
过去这些年,他可没少触犯法律——在公共场合酗酒、酒后驾车、偷东西,还擅自用朋友父亲的信用卡刷了70美元。虽然都是些小偷小摸的轻罪,但也令人担忧。更糟糕的是,他最近又在一家当铺里卖了一把枪,这违犯了假释条例。他这种人是不能携带枪支弹药的,更别说去商店卖了。因为这次过失,他可能马上就会被关进监狱。
其实,现在他收拾起父亲的武器也算违法。不过,他人在得克萨斯,而不是俄克拉何马,所以当他跟着父亲进入俱乐部的时候,他很自信地认为警察追到这儿的概率太渺茫,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因而,当莫莉在塔尔萨打电话报警的时候,蒂姆和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俱乐部,驱车去斯普兹家吃午饭。
杰西·斯普兹帮蒂姆热了热前一天晚上在橄榄园餐厅打包的饭菜。在跟蒂姆的妈妈一起去做美容之前,她看到这对饿坏了的射击选手正狼吞虎咽地吃着意大利家常菜。
中午时分,杰西和詹姆斯的女儿辛西娅顺便回家吃了盘意大利面。此时,沿着75号高速公路驱车向北4个小时的地方,塔尔萨警方的警笛声打破了枫树岭社区的平静。
陪审员越多,错判概率越小
我们相信没有人能总是做出正确的决定,尤其是那些会影响到我们自由的人。哈桑回想起跟联邦调查局之间的经历时说道:“当你面对一个掌握着你的生死大权的人时,你就会变得不理性。”于是我们引入了陪审员,因为大家相信与一个人单独在审讯室相比,12个人一起更能看到事实的真相。
事实上,就算我们假设一名陪审员有80%的时候能看到真相,但他还是有20%的出错机会。所以,你肯定不想把自己的自由押在一个陪审员的手上。但如果有12个陪审员,虽然每个人出错的概率仍是20%,但你被冤枉的可能性只有(0.2)12,也就是0.0000004的概率。这就意味着12名陪审员参加5亿次审判才有一次冤枉被告的可能。这对蒂姆·德拉姆来说是个再好不过的消息了。
“谁也没想过这样的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太愤怒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做这样的事。”莫莉的妈妈在7月15日的时候对一个记者说道。
此时,距离她11岁的女儿遭到陌生人野蛮强暴已经过去6个星期了,她绝对有理由感到绝望。调查全无头绪,使得住在俄克拉何马州这个高档社区里的人们,不得不开腔对这件悬而未决的案子表示愤怒。
但不久之后,警方有了意外突破。塔尔萨一名警探的妻子(她在缓刑部门工作)告诉她的丈夫,她知道有个人符合莫莉对疑犯的描述。那个矮个子、红头发的人很像处于缓刑期的蒂姆·德拉姆。
警方将蒂姆的照片和其他人的照片一起拿给莫莉看,但她并不确定。他们又试了一次,这次她似乎觉得这张照片上的人有些熟悉了。“看上去像他。”莫莉指着蒂姆的照片说道。基于此,警方在1992年1月逮捕了蒂姆·德拉姆。蒂姆很吃惊,他坚称自己无罪,因为有十多个人都说曾在达拉斯的双向飞碟射击大赛上见过他,其中不乏受人尊敬的商人和老教徒。
在法庭上,被告的辩护律师安排了11位证人。这些目击者都坚称,当那个红头发的男子在俄克拉何马强奸那位11岁的女孩时,被告跟他们一起在得克萨斯。他们还告诉陪审团,袭击发生时蒂姆·德拉姆已经留了一年多胡子,所以不可能是莫莉口中那个脸刮得很干净的男子。
然后,原告开始提起诉讼。检察官助理出示了取证人员的证词。取证人员仔细地将犯罪现场发现的红发跟蒂姆的头发做了比对。另一位DNA专家检测出,莫莉泳衣中残留的精液在某种程度上与蒂姆的基因相符。只有5%的人与他们取证时用的标记基因相同,这足以证明蒂姆当时在犯罪现场。检察官又质疑了蒂姆不在场的证明,声称11位目击者都是老年人,不能,或者是根本不愿意准确地回忆起案发当天的事情。最后,莫莉站上了证人席,指证剃掉胡须的蒂姆就是侵犯她的人。
“受害者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陪审团主席在闭庭后对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说道,“她的态度非常肯定。”
所以,1993年3月13日,蒂姆·德拉姆因强奸一位11岁的女孩被陪审团定罪并判以3220年监禁。这是塔尔萨法庭历史上对非谋杀案件判罚最严厉的一次。裁定结束后,蒂姆的妈妈,一位优雅的、满头白发而且笃信上帝的女士,把自己的圣经扔到了墙上。
“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再也不会相信什么体制了,绝对不信。”她说。陪审团可能会弄错,但她不会。案发的时候,她正和她的儿子一起在达拉斯。那天之后,她再也没有去过教堂。
必然,还是偶然?
虽然偶尔会出错,或者说因为会出错,我们的司法体系才能暴露出很多有关人类决策及其弱点的信息。然而,正如那些在陪审团任过职的人所知,陪审员都是私下进行讨论的。只有在他们达成一致意见之后才能做出裁定,这使得人们几乎不可能知道每个人的决定。不过,芝加哥陪审团项目却不这么认为。
根据对大量担任过陪审员的人、辩护律师以及法官的调查,他们指出裁定结果往往偏向于第一轮投票结束后大多数陪审员的意见,而且在91%的案件中,陪审员都是在尚未进行讨论之前就达成了共识。要推测出裁定结果,就必然要着重考虑大多数人的意见。这样一来推算结果就变了,现在12个陪审员冤枉被告的可能性就从原来的0.0000004变成了0.4%。这一变化是显著的,也就是说在1000个案件中就有4个被告可能被冤枉。
可能有人会说,这一数据只能说明错误判决不常见。这话虽然没错,但对蒂姆·德拉姆来说可不算什么好消息。
虽然蒂姆的遭遇已经无法挽回,但我们发现了这种方法的不足。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陪审团在80%的情况下是正确的。但实际上他们的准确率是不是要更高,或者蒂姆这样的案例其实没预想中的那么多?从某个角度上看,我们是否能够断定陪审员在一般情况下都能做出正确的裁定?
由于没人能确定到底谁有罪、谁没罪,所以我们找到答案的概率很渺茫。但是,正如我们从19世纪一位法国数学家身上学到的,一些问题并没有它们最初出现时那么难。
西莫恩·德尼·泊松曾回忆自己初学走路时,有一次父亲发现他被绳子吊起来的经历。罪魁祸首是个女仆。她坚称那么做是为了防止孩子被地上的蚊虫叮咬,但实际上她是想把孩子关起来,然后做自己的事。
虽然年幼的泊松还在犹豫自己要不要去学数学,但他的家人坚持把他送到枫丹白露学医。但第一个病人的死吓到了他,所以他毅然退学回了家。
赋闲在家期间,泊松的父亲当上了皮蒂维耶的市长。身为市长,他的父亲要订阅很多有名的杂志,其中包括《综合工业学院学报》(Journal of the Polytechnical)。在乡间百无聊赖的泊松开始翻阅这些杂志,不想却因此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之后他便开始一一破解杂志上的难题。他的家人重新讨论了他的未来,然后决定把这位无所事事的青年送到枫丹白露学数学。这次他没有再退学(毕竟方程式是杀不了人的),反而进了巴黎的综合工业学院。他成为那里的教授,并在7年后成功破解了傅里叶级数。
如今,以泊松命名的科学发现不计其数——如泊松积分、位势理论上的泊松方程、弹性学上的泊松比,以及电学上的泊松常数。人们将他的名字刻在了埃菲尔铁塔以及月亮正面南部高地的一个被严重侵蚀的火山口上。这个火山位于以阿里辛西斯(Aliacensis)命名的火山口的东面,以杰马·弗里西斯(Gemma Frisius)命名的火山口的西北部。泊松一生发表了350多篇论文,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算是硕果累累了,更何况当时还没有文字处理器。
他最知名的成果,是发表于1873年(也就是他去世前3年)的《关于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审判概率的研究》(Researches on the Probability of Criminal and Civil Verdicts)。现在的数学家们对这篇论文的研究主题——创建一个完善的司法体系,没有丝毫兴趣。然而,这篇论文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它建立了基本的统计学理论。这一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现今大部分研究领域中。
在这篇颇具创意的论文中,泊松指出陪审员犯错的概率是可以计算的。我们只需要知道某个特定年份的案件总量以及被定罪的案件数量就够了。法国司法部会定期统计这些信息。
统计结果表明,1852年有6652人被指控犯罪,其中只有60%的被告被定罪。利用这些数据和他推导出的公式,泊松计算出每个陪审团做出正确裁定的概率只有75%。令人称奇的不是他计算出的这一结果,而是他那种潜入每个审判员的脑中,发掘他们做出正确决断的概率的能力。
利用芝加哥陪审团研究中心(Chicago Jury Study)的统计数据,艾伦·伊恩·吉尔方德(Alan E.Gelfand)和赫伯特·所罗门(Herbert Solomon)发现美国的陪审团的表现稍微好一点:他们做出正确裁定的概率为90%。与19世纪的法国前辈们相比,他们对待这项工作显然更严肃,也更用心。
但是,我们对于现在司法体系的那些疑问真的能够消除吗?虽然蒂姆·德拉姆不这么认为,但是对我们其他人来说,事情确实有所好转。事实上,如果陪审团做出正确裁决的概率是90%,那么被告被冤枉的概率只有0.005%。这比陪审团出错概率为20%的情况要好上几百倍。1990年被定罪的案件有1993880起,其中包括谋杀、过失杀人、强奸、侵犯人身罪、抢劫、偷盗以及纵火罪。那么,根据上面的方法推算,只有40个罪犯是被冤枉的。如果你不是这倒霉的40人中的一个的话,这个数据听起来也不算多。
泊松的悖论
泊松的计算在哲学层面上存在一个深层假说:他荷载取值,假设人类行为是随机的,将事情简化了。不管你是最聪明的智者,还是最愚笨的傻瓜;不管你是法官,还是犯人;不管你是怀疑论者,还是迷信的信徒,一旦坐上陪审席,我们知道的只是你做出正确裁决的概率只有90%。这也就是说,泊松将不可预测性和偶然性等同而语了。他接着指出,一旦我们承认人类行为是最随机的,它突然之间就可以被预测了。
爆发洞察
这似乎是个悖论:如果不可预测性是指偶然性,那么偶然性又怎么能预测呢?答案很简单:泊松所谓的预测跟我们日常生活中追求的有所不同。跟伊斯特凡·泰勒格迪对教皇十字军的未来所做的预言不同,他的手法更像爱因斯坦推导原子运动规律。爱因斯坦知道推测出单个原子的运动轨迹是不可能的,所以转而假设原子的运动是随机的,然后推导出原子离释放点的距离遵循扩散理论。
同样,泊松根本没去想陪审员是否做出了正确裁定,而是假设每个陪审员都像掷骰子那样投票: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对的,但偶尔会出错,而且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是对的,什么时候是错的。在这一假设的前提下,泊松利用定罪率的统计数据推导出了整个陪审系统的可靠性。
为了更好地理解泊松的推导过程,我们先说说我的电话记录。
我平均每天打12通电话,也就是说差不多每两个小时就会打一次。不过,根据这些你并不能推导出我将在何时打电话。但是,如果假设我打电话的模型是随机的,你就会对我的通讯问题有所了解。利用泊松的公式,你可以推算出我下个小时不打电话的可能性(这个概率是60%——也就是可能性很大),或者我连续打5通电话的可能性(概率是0.02%——不太可能)。利用他的公式,你也能推导出我一天之内不打电话的概率(0.001%——可能性极小)。
尽管这种推测跟神谕完全不同,但也极具价值。

假设一家电话集团的某个工程师负责测定在你所居住的小区安装的移动电话信号塔的容量。如果他设定的容量过低,很多电话就会掉线,用户和老板都会很不高兴;如果设定的容量过大,就会浪费公司的资源,不用说肯定也会惹恼老板。但如果这位工程师精确地知道你所在社区中每个人计划使用电话的时间,他就能预测出何时是高峰期,也就能计算出信号塔的容量最大值。
但工程师不可能知道你将来的通话情况。不过,他知道每个用户平均每天要打3通电话。同时,他假设所有人的通话模型都是随意的,那么利用泊松的公式,他就能推测出任何时间点计划使用电话的人数。然后,他就可以设定足够大的容量,使得100部电话同时使用时掉线的电话不超过3部,以确保公司达到“无瑕疵”的移动服务的基准。
如今,只要遇到无法理解的事情,我们就会说那是偶然。我们会看到,这种表面上的偶然行为推动了历史的演进,而事情发展之迂回曲折似乎如掷骰子一般。但这种偶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为了找出答案,我们不妨掷骰子试试。每当点数是6时,你就在纸上画条竖线,而掷到其他点数——不管是1、2、3、4,还是5,你就画个点。我自己试着掷了400次,结果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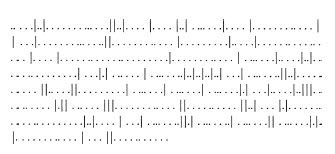
虽然每次掷的点数无法预测,但整体是有规律可循的。也就是,大约每掷5到7次就会出现一次6,而掷100次都不出现6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样两条竖线之间的距离将非常长。事实上,正如泊松公式指出的,你掷上1亿次才有可能出现一次这种情况。同样,我们需要掷上一亿次,才会出现每行有10条竖线的情况,也就是说幸运地掷到10次6。
爆发洞察
虽然下次掷的点数是个谜,但在这种偶然性中还是存在某种神奇的规律。尽管存在明显的规律,但泊松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再随意不过的过程了,因为它就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累计。因而,偏离泊松预测常常代表某种隐藏的秩序,它们揭示了一种有待发现的更深层次的规律或模型。
诚然,我们观察到的很多现象都绝非偶然,比如行星运动、亘古不变的日夜交替等。但另外一些现象,比如天气,看起来似乎纯粹是偶然。不过,正如理查森极力指出的,大气受制于一系列规律和方程式。现在,各地的气象学家都能通过计算成功预测天气情况。此前,人们认为很多现象,如日食、洪灾、旱灾都是受神秘的造物主支配。但现在这些现象都能够被人类预测。这告诉我们,偏离了随机性通常意味着某种基本规律有待人类发现。
人类行为不是随机的
蒂姆·德拉姆的家人说服了巴里·谢克为他辩护。谢克是一名DNA专家,他所在的律师团曾在1995年帮助O·J·辛普森免罪。他专门利用DNA相关技术,为含冤者洗脱罪名。一项在蒂姆的案件第一次接受审理时尚未得到认可的DNA新技术,明确排除了蒂姆的嫌疑。
蒂姆被释放的时候已经在监狱里待了5年。监狱中存在一种所谓的等级制,少年强奸犯处于最下层。蒂姆因强奸莫莉被定罪入狱后,遭到了狱友的暴打,甚至一度断了肋骨。出狱后,他了解到在莫莉被袭一个月前,她所在街区的另外一位女孩也遭到了相似的侵犯。两个女孩对嫌疑人的描述惊人的相似。蒂姆还听说在自己1992年被捕前,一个名叫杰斯·加里森的男子失踪了。这名男子身高大约1.5米,头发为红褐色。加里森在1991年12月18日——即蒂姆被定罪的两年前,上吊自杀了。他的DNA从未被检测过。
我希望能跟大家说,泊松的努力使得创造一种完善的陪审制度成为了可能,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陪审制度仍然多受法律和政治论据左右,而鲜有科学支持。不过,泊松的努力回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完美的陪审制存在吗?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
但我们能否提高裁定的准确率?泊松的研究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建设性意见:陪审员的人数越多,集体犯错的可能性就越小。这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陪审团最多由6人组成时,大家感到吃惊的原因。
支持者提出,缩小陪审团规模能够节省资源,因为去法院的人会相应减少。而且陪审团的规模越小,意见分歧就越少,审议时间也越短,因为6个人比12个人更容易达成共识。关塔那摩监狱第一个被控战争罪的本·拉丹的司机兼保镖萨利姆·哈姆丹(Salim Hamdan)就是在只有6个军官做陪审员的法庭上被定了罪。坦白讲,他绝不是无辜的,但6个陪审员决断的出错率要比12个人的高25倍。
尽管泊松的研究没能改善陪审制度,但它仍具影响力。诚然,对于那些不认识我们的人来说,我们的行为显得无序无规。他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发下封电子邮件,什么时候打下一个电话,什么时候得流感。但这些行为最终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电话集团、医院、连锁酒店、客服中心以及证券经纪公司等。一旦无法弄清我们的行为方式,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就会求助于泊松理论。
爆发洞察
1915年,人们发现,意外的发生遵循泊松规律,泊松理论自此便成了保险业的基本理论。如今,在假设受随意浏览和通信模型影响的网络通信量遵循泊松过程的条件下,人们设计了路由器。泊松公式还被用来计算因传染病死亡的人数,以及预测每个家庭得伤寒的人数。
与此同时,科学家们仍默然接受人类行为科学的基本范式:我们的行为实际上是随意的、不可预测的、偶然的、无法确定的、不可预知的,以及无规无序的。
这一假定的唯一问题在于,它完全错了。

一场始料不及的大屠杀
地点:奥帕特村
时间:1515年5月23日早晨,发起十字军东征的弥撒仪式举行一个月后

十字军东征期间,那些仍敢外出旅行的人肯定已经算到,穆列什河沿岸任意一个两千人的集军都是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军队。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1514年5月23日这天,在奥帕特村的浅滩上,迎接他们的竟然是那么一幅令人震憾的场景。
忘了白帐篷,高旗杆,五色旗帜随风飘扬,地平线上凸显中世纪军营剪影的迪士尼式画面吧!真正的营地充斥着肮脏破烂的草席和帆布垫子,泥泞的地上插着一根绑着破布的旗杆。
忘了那些身穿闪耀华丽、色彩斑斓战衣的骑士们吧!想象一下,一支由衣衫褴褛,在篝火前散发着恶臭的农民、土匪、羊倌、铁匠和商人组成的队伍。
如果你暂时忽略那些打着补丁的军服、豁口的钝斧,看着这两千个闲聊、打盹、在篝火旁狼吞虎咽的人,你很容易有置身集市的感觉。
只有个别人背上绣的十字符号才表露了他们的使命:他们是十字军。没错,这帮糟糕的家伙就是响应主教号召的志愿军。他们刚刚穿过穆列什河,但并不想在这儿久留,因为穿过前方的森林很快就能到达贝尔格莱德——信仰基督教的欧洲的最后一道关卡。关卡之外,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去往君士坦丁堡的路上已经设下了重重堡垒。
在被主教委以重任后,乔治·塞克勒就越过多瑙河,到了佩斯城附近一个名叫雷克斯的安静村庄。过去几天,志愿军都已聚集到了这里。不过,他的到达丝毫没有统率千军攻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架势。在那里等他的那群不足300人的乌合之众连攻克一个小山寨都费力。
最令人失望的是,他们的武器装备根本不值一提。有的人得意扬扬地举着一头被削尖的长棍充当长矛,还有的人拿着长柄的砍柴斧充当锤矛和战斧。不过,大部分人拿的是镰刀。这些镰刀都是前几天刚磨好,准备拿去割麦子用的,但现在不得不充当打仗的武器。只有少数几个神色疲惫的雇佣军穿着古怪的盔甲。这种打扮让乔治·塞克勒觉得似曾相识,因为那正是他过去的模样。
乔治简直不敢相信这群乌合之众敢称自己为十字军。但既然主教已经许诺会有更多的志愿军、食物和装备,所以这位统帅并不气馁。他一心扑在了队伍训练中,教那些农民基本的作战方式,比如如何使用火铳、剑、斧和矛上阵杀敌。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他的身影,看他指挥那群由马匪组成的骑兵跟新组成的步兵进行演习,看他教大家怎样用长戟对抗长矛。
与此同时,主教也信守诺言,要求各地的圣方济会修士传播征用十字军的消息,因为5年前匈雅提征军的时候,他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全国各地都有修道院,而且修士们大都来自当地的村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十字军的最佳特使。他们证明了自己那令人吃惊的影响力:布达城不足300人的军队一下子激增到了1.5万人,而且听说还有4万人正从各地赶来。
由于征兵进行得异常顺利,在弥撒仪式结束仅两周后,乔治·塞克勒就命令队伍开始行动。5月10日,他率大军开始东进,直驱特兰西瓦尼亚。当这条鱼龙混杂的巨蟒穿越匈牙利低地时,它的长度又增加了。周边地区的大批骑士和农民陆续加入队伍。至5月中旬,当塞克勒抵达奥帕特村东北部80公里开外的久洛(Gyula)时,他手下已经有3万兵力了。
中世纪的战役往往是在仲夏期间开始准备,因为那时庄稼已经收割完毕。但主教可没耐心等那么久,所以他在4月就发布了征兵启事,这比往常要早很多。他拿出金币让十字军购买食物和装备,还打开自家的大谷仓、捐出牛羊给军队作为食物。这些军资满足几千个雇佣兵没有丝毫问题,但对4万多饿狼般的志愿军来说,这些资源就少得可怜了。
由于存在潜在的粮食危机,乔治·塞克勒下令所有偷抢百姓东西的士兵都将受到严惩。但是纪律不能当饭吃,所以士兵不得不四处搜寻食物。本来这也不算什么稀奇事儿——当地居民为中世纪军队提供食物是常事,而且在必要情况下他们往往被迫给养军队。但这次情况不同:过去,在由骑士和贵族组成的军队中,农民会负责所有后勤工作;但这批乌合之众二话不说就去抢劫地主的农庄,一旦遇到反抗,他们不惜举刀杀人。
除了食物短缺外,还有一个大问题:全国各地的地主发现夏收迫在眉睫,但农民都不在了。由于人手紧缺,一些地主干脆把农民监禁起来,甚至处死那些半路被抓回来的人。对那些即将参军的人的家属实施监禁并严刑拷打的流言在整个军营散播开来,愤懑的农民不再将贵族视为同盟者,而将之视为敌人。
当地主和十字军之间发生冲突的消息传到宫廷后,主教被迫收拾残局。最后,他终于做出让步,在5月14日给了乔治·塞克勒一纸公文,命令他回绝所有还想加入志愿军的人,但成千上万的农民仍然继续涌入军营。
乔治·塞克勒推断信上的内容并非主教的本意,而是朝中反对十字军的压力迫使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别把我当成三岁毛孩或是傻子来戏弄,”《塞雷米史记》(Chronicle of Szerémi)这样记载塞克勒对主教来信的反应,“我以上帝和圣十字架的名义警告你们!”接着,他命令牧师们继续征集志愿军。
不过,这封信确实起了一定作用:乔治·塞克勒突然改变了行军路线,放弃了去特兰西瓦尼亚的计划——因为这只会证明他仍在招兵,他转而掉转马头,抄近道前往贝尔格莱德。要到达那里,他必须依靠奥帕特村的渡船穿过宽阔的穆列什河。他组织了一个2000人的前哨部队,让他们先过河,以迎接大部队的到来。
由于离最近的奥斯曼土耳其壁垒只剩两周行程,前哨部队中的每个人都希望结束长途跋涉,好好地睡上一觉,所以军营中充斥着一种倦怠感。
由于缺乏警惕,当一阵沉闷但逐步逼近的嘈杂声打破午休的宁静时,大多数士兵的反应是吃惊多于恐惧。毫无疑问,这是一组骑兵疾驰而来的声音。虽然只闻其声,但马蹄哒哒,已经震醒了整个军营。一些士兵本能地拿起了武器,但更多人只是好奇地走到营地边,以便能最先看清来的是什么人。
不一会儿,数百名身披亮甲的骑士就出现在了附近的森林中。人文作家陶里努斯(Taurinus)在四年后所写的史诗著作中形象地描绘了这队骑兵的统领:
他戴着亮闪闪的头盔,护胫、护腕,还有镀金臂鞘,腰间别着两把篮型护手、象牙柄的金剑。
熟悉这身红白相间战衣的人,很快就认出来人是腾斯法要塞的统领、匈牙利东南部的军事指挥官伊斯特凡·巴赛瑞。他身边的那位是附近乔纳德(Csanád)教区的主教,数月前曾在布达城训斥过乔治·塞克勒的米克洛什·萨基。他们身后跟着一众贵族骑士,因为依据法律和惯例,他们必须响应国家的应召上阵杀敌。这队骑兵以惊人的速度和致命的攻击力驰骋沙场,是以步兵为主的十字军望尘莫及的。
对于军营中缺少骑兵这件事,乔治·塞克勒并没有太过担心,因为农民军只是攻打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三支前锋的中锋而已。事实上,虽然泰勒格迪极力反对,但国王的顾问班子不仅支持主教的计划,而且还积极动员常规军参战。塞尔维亚军阀彼得·拜里斯洛(Péter Beriszló)已经招募新的雇佣兵,以扩充自己的队伍。尽管特兰西瓦尼亚总督萨普雅极力反对组建新十字军,但跟奥斯曼土耳其人大战怎么少得了他。所以,他也表示要出动特兰西瓦尼亚的骑兵助战。因而,当塞克勒的这一小撮前哨部队看到疾驰而来的骑兵时,他们还以为是巴赛瑞的南部兵力已经集结完毕,准备加入直捣君士坦丁堡的大军呢。
金戈铁马千里奔袭,战马所到之处尘土滚滚,骑士们豪气冲天,场面骇人。那一刻,很多农民才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真正的战争。然而,当骑兵逐步逼近,十字军才惊恐地发现他们面甲紧锁,长矛高举,大剑直挥。他们没有呐喊,没有助威,只是快马加鞭,挥汗如雨地加速冲向十字军的军营。
困惑而恐惧的农民军本能地凑到一起,拼命回想几周前接受的训练。但装备精良的骑兵疾驰而来,两军交锋的结果没有丝毫悬念。还没等十字军集合完毕,骑兵就长驱直入,所到之处哀鸿遍野,死伤无数。
面对这令人意想不到的场面,这些大都没见过战场的农民竟然意外地击退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然而,他们的胜利是短暂的,因为沉着冷静的骑兵调转马头,调整阵形,开始了第二轮进攻。夹在精兵铁骑和穆列什河之间的农民军惊慌失措地撤到了流速较慢的河流中。但那是一个糟糕的避难所。一些人被盔甲拖累,陷入泥泞的河床中窒息而死;剩下的残兵被骑士和雇佣兵残忍地砍了头。
这是怎么回事?你可能会问,那些逃命的农民肯定也会问。我们只知道,农民和骑士是同盟。他们都报名从军,共同克敌,而且都宣誓效忠皇室。那为何贵族又反戈杀死他们的同盟军呢?这些骑士卑鄙地绕开乔治·塞克勒的3万武装,转而偷袭这支毫无准备的前哨部队,是为了证明什么呢?
不管怎么想,这都没有道理。表面上看它就像一个对现代人来说动机不明的历史偶然。但这真的是偶然吗?在致命的战争问题上,我们该怎么区分是偶然,还是故意所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