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是接受绝望,还是追随希望
量子力学
如果真有透视未来的千里眼,历史真的不会重演,人类的动机和欲望也不会重复吗:我们总是想要更好、更多、更不一样的东西?正如我们以揭开次原子世界的真相为目标进行的物理研究一样,是不是说人类就会变得完全或部分可预测?
战场上,取你性命的那一声爆炸声你是听不到的。所以,每听到一声爆炸声都会让人松一口气,庆幸被炸的不是自己。不过,教授似乎对时不时震得房子乱晃的爆炸并不在意,他平静地继续尝试预测下午的天气。
他的进展很慢,因为总是要去战场抬伤员。虽然他不需要出去战斗,但他的工作也不是没有危险。几天前,当他们冲进森林救助一个受伤的炮兵时,一颗炸弹刚好落在他们的救护车上。虽然没有一个人受伤,但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还是让大家心惊胆战。
但当教授认真分析早上7点的天气预报,并努力预测6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的天气状况时,昨日的恐惧早已被他抛诸脑后。然而,一个小细节让他的努力看起来近乎可笑:他正尝试预测的是1910年5月20日那个平静下午的天气情况,但日历上明明白白地标着那一年是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把外面的世界搅得一团糟,所以那些在法国前线的战士们只会摇头心想:“谁在乎什么天气啊?”
刘易斯·弗赖伊·理查森(Lewis Fry Richardson)是一个高个子,为人和善,反对一切暴力的贵格教徒。
理查森的天气预报
1913年,他加入了英国气象服务站(British Meteorological Service),随后在同事的帮助下很快掌握了天气预测技巧。对他们来说,这一技巧更像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那里的天气预测员每天都会监测当天的天气情况,然后找到与这天的天气情况相似的过去某天的天气记录。“天气预测是在假设以前的气候状况会重复的基础上进行的。”理查森解释道。
作为一名物理学家,理查森很久以前就发现还有一种更好的预测方法。1913年,流体运动方程已经公之于世。所以,如果知道当下的天气状况,原则上你就能推测出随后的大气变化。这就意味着,利用物理和数学知识,他就能预测第二天的天气情况。
理查森在前一年完成的书稿中已经介绍了这一新方法。但在将书稿送去出版之前,他想对此做一下验证。所以,在仔细考察了1910年5月20日早上7点的天气情况后,他就开始系统地预测6个小时后,也就是当天下午1点的天气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虽然他信仰和平宗教而不愿参军,但他还是参加了贵格教徒组织的朋友救护小组(Friend’s Ambulance Unit),负责将伤员从战场上拉回来。在驾驶救护车驰骋西部前线的间隙,理查森还是顽强地继续着他的天气预测研究。
通常情况下,要想预测6个小时后的天气情况,理查森需要6个星期左右的准备时间。但事实是,只有一天24小时不眠不休,他才能在6个星期内得出结果。最后,由于他每天都被多次打断,在法国前线的两年时间里,这项计算工程花去了他大部分精力。虽然花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但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当他预测某个地方的气压变化是145毫巴时,实际的变化却只有1毫巴。鉴于当时英国有记录的最大气压变化值都不足130毫巴,所以他的预测简直大错特错了。甚至可以说,这跟预测温暖的八月会飘雪差不多。
然而,计算结果的准确性不高并不是唯一令人头疼的事,计算过程中需要的资源才更让人抓狂。在计算机还没问世之前,理查森在大脑中想象出这样一个预报作坊——在一个铺着世界地图的大厅中,人工“计算器”坐了满满一屋子。这些精通数学的人们埋头苦算各自桌子覆盖区域的天气情况。
理查森估计,要想跟上变化无常的天气,他的预报作坊必须雇上64000人。事后证明,这一预测跟他的其他预测一样不准,起码少算了136000人。难怪没人愿意将他的作坊付诸实践。鉴于人们对这一想法的冷淡态度,理查森想将天气预测变成一门精确科学的梦想也就不了了之了。
透视未来的千里眼
尽管伊斯特凡·泰勒格迪在匈牙利宫廷的朗朗演说有点儿拐弯抹角,但他的意思很明确:如果你召集农民并交给他们武器,他们就会倒戈。他们的敌人不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而是本国的贵族,是那些贪得无厌的地主。如果你现在为不能攻打君士坦丁堡感到惋惜,明天就得小心自己的性命。
泰勒格迪难道有能透视未来的千里眼?还是只是一个怕分裂、怕改变的多事老头儿?
爆发洞察
之前,我们曾经遇到了另外两个性质不同的预测案例。德克·布洛克曼预测在纽约花出去的钞票将在68天内漫游各地,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寻到它们的轨迹;还有就是我们预测一条新闻的生命大约为36分钟。
这些都不是预言,而是跟理查森的天气预报一样,是通过数学公式推导出来的。但实际上,这些预测都失败了。钞票的运动速度比扩散理论预示的要慢,而新闻的生命周期是36小时,而不是36分钟。所以,泰勒格迪的预测、布洛克曼的估计、理查森的预报,还有我们的研究,其中三项都错了,现在只剩泰勒格迪的预言……嗯,你会看到结果的。
对于预测,我们既不是迷信之人,也不是怀疑论者。迷信之人会完全信任那些预言家、读心者以及商业顾问的说辞,并不惜重金购买16世纪预言家诺斯特拉德马斯(Nostradamus),这位谜一般预测出人类文明中所有大事件的人的所有专著。而怀疑论者则认为诺斯特拉德马斯的含糊说辞并没有显出真正的预测能力,然后又指责一些专家的预测失误连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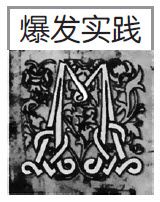
举例来说,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经济学家们提醒我们,平均房价“自1968年来一直保持着不降价的良好记录”,而且还预测2006年内房价会上升6.1%。然而,那一年房价跌了3.5%,预示着美国房地产泡沫即将破裂。你可能会想,这些预言家碍于上次失误的尴尬,可能会改变一下策略。但实际上,他们仍然遵循着那种奇怪的逻辑,在2007年12月9日的新闻上乐观预测:“2008年现有房屋销售量将攀升!”事实再一次不合作,房屋销售量在2008年12月23日跌了11%,是大萧条以来下跌最厉害的一次。
鉴于这些预测的失误,让我们再次问一问怀疑论者:为何像泰勒格迪这样一个深谙当时社会和政治现实的人不能预测出十字军的结局?毕竟,人类就是靠开动脑筋精确预测某些事情来进化受益的。在打网球的时候,我会根据对球打过来的时间、位置以及速度的即时预测,在球场上跑动,以将球打回给对方。同样,看到一辆疾驰而来的汽车,我很容易就能预见如果我慢慢走过街道的话肯定会被撞到。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反驳他人之前先相信一些预测。我们找到了内在规律,所以能对那些遵循自然规律的事件做出精确预测——比如网球的飞行轨迹,以及疾驰汽车的运动轨迹。但要预测由数以万计的农民参加,并且受到一群国王、主教、奥斯曼土耳其王以及总督们左右的战役的结果就非常困难了。虽然仅凭人类的意愿,这样的事情是很难预测的,但是难并不代表不可能。所以,既然我们要探究人类行为的科学性,那么就该问自己一个重要的问题:原则上讲,我们能不能预知未来呢?
我们能预测革命吗
这个颇具批判性的问题的提出者不是别人,正是20世纪科学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他将社会科学将做出历史预言的期望称为“历史主义”,并指出这些观念是“人类最古老的梦想之一 ——预言的梦想,即我们能知道将来我们会遭遇些什么,我们能据此调整我们的政策并从这种知识中获益”。在他1959年发表的《预测和预言》(Prediction and Prophecy)这篇标题贴切的文章中,波普尔说:“我们能够高度精确,并且远在发生之前就预测到日食。为什么我们不能预测革命呢?”
波普尔的观点丝毫不留歧义,并为将来数十年的社会科学研究确立了议程:一旦涉及人,预测就会变得不可能,所以大家也无须困扰。他的观点简单却令人信服:
我们的太阳系是一个稳定而周而复始的系统,而日食的预言只有建立在季节规则性上……才可能成真;这还因为一个偶然因素,即太阳系由于拥有浩瀚的空间,脱离了其他力学体系的影响,所以相对地摆脱了外界的干扰。和人们普遍的认识相反,对这种周而复始的体系的分析在自然科学中并不具有典型性。这些周而复始的体系仅仅是些特例,虽然其中的科学预测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但仅此而已。
历史不会重演,人类的动机和欲望也不会重复:我们总是想要更好、更多、更不一样的东西。所以,鉴于波普尔的权威,在人们还没真正展开讨论之前,这篇论文的出版事宜就定了。一旦涉及历史或社会科学问题,你就无法进行预测。泰勒格迪的观点无疑是可笑的,而且在这一问题上任何尝试预测的行为都将以失败告终。
量子力学的局限
现在,我们的全球天气预报系统在过去五年里对未来3天的天气预测的准确度已经达到了95%。令人吃惊的是,这一取得巨大成功的系统正是利用了理查森书中的方法。我们不禁会想,为什么他自己的预测错得那么离谱呢?
问题不在于他的方法,而在于他掌握的数据。现在的气象系统依靠的是精密的雷达和卫星地图,地面和高空的温度也会在世界各地的气象站即时更新,而不再需要像理查森那样到处收集参差不齐的大气情况数据。另外,高速计算机已经取代了他要求的二十万左右的人工计算者,而且还规避了那些妨碍计算的不稳定因素。这是不是说明人类预知未来的能力只是受到了数据质量以及计算机速度的限制?还是不管我们掌握多少数据,无论我们的处理器变得多快,只要涉及人类行为的问题,我们就注定无法进行预测?
这是一个典型的爱因斯坦式两难推理。爱因斯坦在给康拉德·赫博瑞奇的信中提到的第一篇论文,也就是后来帮他赢得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中介绍了量子力学的雏形。现在,量子力学无疑可算做将人类的预知能力发挥到极致的科学理论。
比方说,根据量子力学,我们精确地推导出了电子的磁偶极矩,并将误差锁定在了1/1010内。这可算做科学史上最精确的推测了。另外,据估计美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的30%来自于那些通过量子革命出现的科技,如手机、iPod等。
尽管如此,量子力学在本质上还是不能准确无误地预知未来。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能提供某个特定事件的发生概率。事实上,对于像这本书这样的大目标来说,它在你阅读过程中突然消失的可能性为零。但对于组成这本书的其中一个电子来说,事情就不一定了;它很可能从这里消失,然后又在世界的另一边出现。你可能注意不到,但它绝对是在量子宇宙的可能范围之内。
这种概率架构让爱因斯坦感到烦恼不堪,以至于后来他干脆拒绝研究量子力学。直到去世,他都在寻找一种更加接近现实的理论,一种不牵扯概率的理论。他那句“上帝从不掷骰子”的名言是他新知识运动的核心论点。他幻想能发现一种跟牛顿力学一样,能够精确预测未来的完全确定的理论。
这只是一个顽固不化的科学巨人的不切实际的追求吗,就和巴科兹主教坚持率军征战君士坦丁堡一样?难道人类的预知能力真的存在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即使理论再强大、资料再充分、电脑再快也无济于事?
现在,我们知道爱因斯坦错了。根据量子力学的推断,宇宙是存在概率的,而混沌理论的出现又给预知能力的实现一记重击。比如说,掌管明天天气情况的大气现象,如果我们对当下的现象有一丝不确定,那么不确定因素就会快速扩大,使得长期天气预报变成徒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人们还是难以预测两周以后的天气情况。
爆发洞察
科技进步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难题:我们能否为未来行为中的不可预知的因素提供数学验证?鉴于我们身体中的每个原子和分子都是遵守量子力学规律的,是不是说我们人类从内部就无法预知?
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发现人类预知能力上存在的严格限制,是不是就意味着人类行为实际上是可以预测的,而且还存在着揭开人类未来行为秘密的概率构架?如果我们投资研究揭示人类行为的规律,正如我们以揭开次原子世界的真相为目标进行的物理研究一样,是不是说人类就会变得完全或部分可预测?我们是接受波普尔的绝望,还是追随泰勒格迪的希望?
寻找未解之谜的答案
到目前为止,本书只是列举了一系列有趣的未解之谜和问题。德克·布洛克曼发现爱因斯坦的扩散理论无法解释美元的流通轨迹,于是推测有种无形的力量放慢了钞票的速度,我们也发现转化模型无法预测网络访问量。
而我们讲述的中世纪故事也一样令人困惑[1]。我们看到巴科兹主教未能如愿当上教皇,而一年之后又被乔治·塞克勒将奥斯曼土耳其大将大卸八块的骇人一幕吓到。主教带着一支耀眼的新十字军重回布达城堡——这是藏在他法衣袖子里的王牌,然而我们却听到了泰勒格迪为反对十字军计划而给出的可怕警告。这些山重水复、曲折离奇的情节就跟杂乱无章的天气一样让人难以捉摸。到了该把这些情节串一串的时候了。
●这一个个中世纪的人物,塞克勒、主教,还有大预言家泰勒格迪是怎么联系起来的?
●我们为什么连反映人类行为特点的最简单的模型都无法推导出来?
●为什么旅行方案失败了,网络浏览器实验也没有成功,更别提跟经济相关的预测了?
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会看到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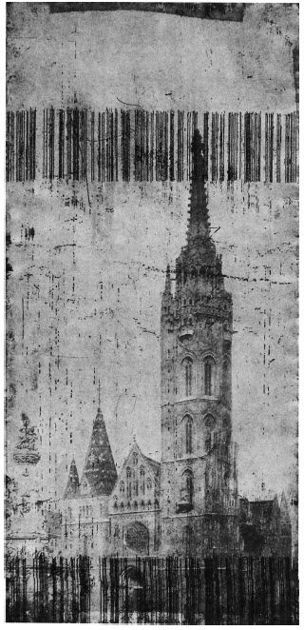
圣战奇兵
地点:马提亚教堂,布达
时间:1514年4月24日,圣乔治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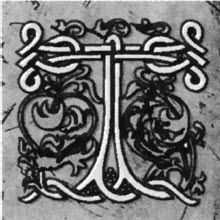
马提亚教堂并不位于布达城堡的中心位置,但它的确已成为其精神核心。这座教堂是整个国家的圣殿,是城堡区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它坐落在高级研究所旁边,离伊斯特凡·泰勒格迪数百年前进行激情演说的匈牙利宫廷大殿只有数步之遥。每次重大战役之前,全军统帅都会在此参加大弥撒仪式,以示祝福。如果军队胜利凯旋,大家就会高唱圣歌迎接他们。当他们面对天国唱响圣歌的时候,失败者的旗帜就将被悬挂在教堂内壁上。
1444年,约翰·匈雅提站在这座教堂里,看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旗帜,那是他在那年冬天那场漂亮仗中收获的。十年后,乔凡尼·达·卡皮斯特拉诺同样站在了这里。这位有着三寸不烂之舌的年长圣方济会修士,曾帮助匈雅提招募参加贝尔格莱德之战的军队。如果你乐意沿着渔夫堡那宽阔的台阶爬上121级,就正好能看到匈雅提的铜像。他手扶一柄长剑,目光越过宽阔的多瑙河,仿佛仍在凝视着遥远的贝尔格莱德。
现在,一排排的长椅几乎摆满了整个教堂,不过这是最近新添的。1514年的时候这座教堂里没什么东西,很像一个挤满了欢呼雀跃的三教九流的集市。1514年4月24日这天,骑士、贵族以及富商都聚集在这里寒暄闲聊、互相祝福,那的确不是一般的嘈杂。
当6个身穿白色亚麻圣衣的辅祭手捧长长的烛台,从教堂前厅进来的时候,嘈杂声才渐渐消失。紧随辅祭的是身着仪式长袍的执事和神父。当列队靠近圣坛时,辅祭们就走到一旁给红衣主教让路。主教虽然年事已高,但还是以这类场合必需的那种华丽而自信的态度结束了整个游行。
从容而庄重的主教将左手放在圣坛之上,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然后用能让所有人听见的洪亮声音开始了弥撒仪式。他高声吟道:“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
众礼拜者大呼“阿门”,然后主教继续说道:“我要走向上主的圣坛。”
礼拜者们聆听着熟悉的经文,目送主教鞠着躬走向圣坛。主教右手握拳击打胸膛三次,并吟唱道:“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尽管这种拉丁仪式在此前被无数次地重复过,但这次的弥撒绝对非同一般。如果你抬眼看看雕刻精美的空王座,你定会感触良多。王座旁边站立着十几个战士,其中有骑士也有雇佣兵。骑士都是地主,而雇佣兵是按日取酬。如果他们开始相敬如宾,那就表示可能要打仗了。
一名披坚执锐、全副武装的骑士在列队中显得尤为耀眼。不过,如果你注意看从那身红色制服刺绣精致、金丝镶边的袖口露出来的粗糙双手,或是留意到他那浓密胡须遮掩下的脸上的风伤泛红的皮肤,就会怀疑这不是他惯常的着装。身着这身昂贵制服的正是乔治·塞克勒,我们已经将他抛之脑后两个月之久了,当时他正忙着砍断伊派瑞斯的艾利的手臂。他原来那身嘎吱作响的盔甲、锈迹斑斑的盾牌以及褪色的头盔,已经被胸前的金链和锋利闪亮的鱼尾金柄长剑取代。这身装备可值不少钱。如果你还是怀疑这个表情严肃的人不是他,那跟他站在一起的弟弟格瑞格里应该能让你确定那个人就是他了——格瑞格里没有佩带华丽的装备,只是擦亮了原来的盔甲。
杀死艾利对乔治·塞克勒来说既是铤而走险,又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他给艾利的那致命一击让前线的骑兵如沐清泉,骄傲地欢呼起来。随后爆发的欢呼声让他吃了一惊。突然之间,他就成了众人皆知的一招将伊派瑞斯的艾利致死的大英雄。
乔治·塞克勒本想缴获艾利的战马,但那匹马由于感受不到熟悉的主人的双手而惊慌落跑了。这匹骏马随后被匈牙利的马术师抓住,给乔治的胜利留下了瑕疵。最后,乔治放弃了这匹战马,以300块金币的价格卖掉了它。大家喋喋不休的闲话坚定了他离开决战场的决心。既然他已经拥有足够多的钱可以买到想要的坐骑,那现在的问题就只剩下该去哪儿了。对于这个问题,他和他的弟弟格瑞格里心有灵犀——回家乡是不二之选。
但就在乔治·塞克勒盘算下一步的计划时,有消息来报说主教正从罗马赶回来。传言称主教这次身负十字架归来,这就意味着彻底击败奥斯曼土耳其的大战即将展开。塞克勒认为他在与艾利的决战中的优秀表现可能会对新战役有帮助,所以就调转马头,带着满袋的金币,朝着布达城堡的方向进发。他在前线另外一个要塞腾斯法停留了数日。当他流连于市井各大酒馆,将钱散尽之后,他还不知道这趟征途的起点也将成为终点。
布达城里熙熙攘攘,街道上到处都是骑士、雇佣兵和商人。信使快马加鞭地进城,每天都有很多人涌入城内。时值春天,万物复苏,城里的居民很乐意从过冬的发霉窑洞和小屋中走出来。乔治·塞克勒在那些雇佣兵经常厮混的地方吃惊地发现,他击败艾利的事迹已经在宫里传开了,而且大家还添油加醋地将他夸了个天花乱坠。说他是男性荷尔蒙爆发也好,疯子般的勇敢也好,他在贝尔格莱德的功绩已经被大家当做众人追求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史诗广为传颂。多亏了这种夸张的传言,塞克勒发现那一扇扇自己原本不可能叩响的大门,现在都为他敞开了。
他并没有对传言多做解释,而且很快就得以觐见国王,并得到了国王的赞扬。但他的殊荣绝对不是靠几句空话装点的:国王赐他靴刺和宝剑,封他为骑士,并把腾斯法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一处拥有40户居民的土地和庄园赏赐给他。国王还赏赐给他一件绣有带血断臂的战衣,以传颂他在贝尔格莱德的胜利。此外,还有双倍俸禄、一条纯金项链、一件他正骄傲地穿在身上的绣金猩红战袍,同时,国王承诺从国库中拿出400块金币赐予他,以保证乔治·塞克勒和他的弟弟后半生都能安乐度日。
尽管得到了很多礼物,也受封了爵位,但乔治·塞克勒似乎并没有适应他的新身份。他的快速晋升使得他看起来像个不懂装懂的假内行。当他去取国王允诺的400块金币的时候,高贵的伊斯特凡·泰勒格迪让人将金币扔了出去,这更加剧了他的不安。另外,乔治·塞克勒的新庄园所在教区的主教米克洛什·萨基竟当面指责起他过去的不端行为。到目前为止,他在布达的经历就如同坐了一趟过山车——今天还受到国王的赏识,明天就遭到了傲慢的泰勒格迪和萨基的羞辱。
弥撒仪式结束后,红衣主教巴科兹终于站起身,开始了大家静候已久的演讲。
“在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领了50年后,君士坦丁堡是该回归了。”主教这样说着,他同时还强调回归基督教精神是神的旨意。他表示自己授命率领十字军东征实在是诚惶诚恐,并声情并茂地要大家做好随时为这场圣战牺牲的打算。然后,他以教皇的名义为那些勇于抛头颅、洒热血的子民祈祷,并请出教皇的公证人、帕维亚地区的主教伯纳德伯爵上前宣读教皇利奥十世的诏书。在一位圣方济会修士简单地将诏书内容翻译成匈牙利文后,主教又补充说,父子中的任何一方阻止另一方参加圣战都是公然触怒上帝的行为。
然后,主教做了个手势,邀请乔治·塞克勒走向圣坛。这位骑士恭敬地走了上去,他的贴身长矛击打着教堂的石阶,砰砰作响。主教递给他一面绣有红色天鹅绒十字标志的白色大旗。这面大旗是严格按照圣战骑士进入圣地时所举的旗帜制造的。得到教皇的祝福后,旗帜就直指君士坦丁堡了。乔治·塞克勒接过大旗跪了下来,主教的裁缝敏捷地在他的战袍上绣上了同样的十字标。
每个人都清楚这一刻所代表的意义。通过这个简单的动作,主教正式封这位此前鲜为人知的前线战士、这位来自偏远喀尔巴阡山脉的塞克勒人,为十字军最高统领。
1514年4月24日是圣乔治日,也是乔治·塞克勒的命名日,而且如果他的父母是遵守传统,在他受洗时用他出生那天的圣人的名字为他命名的话,那一天实际上也是他的生日。还有比这更神圣的生日礼物吗?如果这不是上帝的旨意,那么上帝肯定从不干预人类的生活。十年来,乔治·塞克勒一直效忠国王,为他而战,俯首称臣。现在,他被主教赋予了更高的权利,他身上那块红色的十字补丁使他成为了基督的战士。
乔治·塞克勒不知道主教为什么会对他这个微不足道的人委以重任。但在这一刻,他什么都不在乎了。教皇下诏许诺每个参加奥斯曼土耳其之战的战士,不论成功或失败都能升上天堂,更何况他并不打算吃败仗。他命中注定要举起教皇的白色大旗,直捣土耳其帝国的中心,并胜利凯旋,将君士坦丁堡的旗帜挂在教堂内壁上,聆听胜利的颂歌。
但这位皮肤黝黑的前线战士并不是唯一一个应该庆贺的人。主教也很高兴,因为他最终在宫廷之上说服位高权重的怀疑论者泰勒格迪,并得到了国王的支持。他成功地为十字军选择了一位统领,使得他的游说最终得以成功。
这个国家从来不缺能够担纲重任的经验丰富的骑士,比如,特兰西瓦尼亚的总督萨普雅。从他之前对抗奥斯曼土耳其的一系列战役中俘获的战利品和俘虏上,我们就能看出他的英武。但是主教绝对不会傻到将十字军交给自己的政敌。
还有跛脚的腾斯法首领伊斯特凡·巴赛瑞(István Báthory)。他来自军事世家:1457年另外一位伊斯特凡·巴赛瑞(后来当上了特兰西瓦尼亚的总督)攻破了奥斯曼土耳其的盟国瓦拉几亚公国(Walachian)的博雅堡垒(Boyars),将弗拉德公爵(Vald the Impaler)囚禁在了南罗马尼亚的皇宫中。这位后来广为人知的德拉古拉伯爵作为宫廷的俘虏和客人,在被囚禁在布达城堡的14年中逐渐赢得了总督的信任。还有一位伊斯特凡·巴赛瑞,他是不朽的波兰王,是唯一一个击败王国的宿敌俄国的人。所以伊斯特凡·巴赛瑞应该是领导圣君的最佳人选。不过可惜,这位身经百战的贵族对领导一支农民十字军没有丝毫兴趣。
就在主教一筹莫展之时,乔治·塞克勒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尽管他能否成为大军统领还有待考验,但他也算久经沙场,而且农民军和雇佣兵都很尊重他。没打任何小算盘的他可谓白纸一张,而且势必会对主教忠心耿耿。因为每个人都很清楚,如果没有主教撑腰,他谁也不是,只不过是个剑术高明的雇佣兵,一把耐用的剑而已。
[1] 由fame变成fameiness,其中的“i”可以看成是英语单词“我”(I)的小写,“-ness”是抽象名词的后缀,这个“iness”就变成了“i-ness”(“小我”)。——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