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伯伦书信摘录
这是纪伯伦写给《侨民报》主编艾敏·欧莱伊的书信摘录。艾敏的胞弟、画家海里勒·欧莱伊将之摘录在自己的日记中,其中一部分曾发表在已故历史学家优素福·易卜拉欣·耶兹拜克主编的《黎巴嫩文稿》杂志上。
黎巴嫩、叙利亚和埃及的部分报刊转载纪伯伦在《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时,既不署纪伯伦的名字,也不提文章来源,致使艾敏·欧莱伊十分生气,并以中断文稿交流威胁这些报刊。《实况喉舌》主编哈利勒·赛尔基斯只得写信给艾敏表示歉意。就这个问题,纪伯伦写信给艾敏·欧莱伊,信中说:
……假若《实况喉舌》、《艺术之果》和《灯塔》杂志再偷我的《泪与笑》,请你手挥利刃,斩断它们的魔爪,一来教育他们,二来警告他人,让它们从《侨民报》转摘东西时,记住那是从《侨民报》上偷窃的。因为那是我的当然权力。
《埃及联合报》写信给其主编奈吉布·葛尔高尔,盛赞《侨民报》上发表的纪伯伦的散文,并提及《埃及联合报》曾转载过其中一篇。纪伯伦写信给艾敏,信中说:
我看过《埃及联合报》及其他报刊所载文章,你们愿意说我什么,就请说吧!你们乐意转载我的什么文章,就请转载吧!但是,你们不能够改变我的自我信仰,我深信纪伯伦这位在黑暗世界中蹒跚行走的柔弱老翁,一心想借朱庇特 392 的闪电、雅典火炬之光、阿施塔特 393 的光荣之美、阿波罗 394 琴弦之歌,直到应该得到你们给的评价,至少让我知道自己距目的地还有多远?
纪伯伦在《侨民报》上发表了一篇谈侨民诗人的文章,从而引发了纪伯伦与艾斯阿德·鲁斯图姆之间的口角,但艾敏·欧莱伊能够使二人重归于好。纪伯伦读过艾斯阿德·鲁斯图姆发表在《侨民报》上的一首题为《将军与大军》长诗新作之后,写了一封信给艾敏,信中引了长诗中的几行诗:
其时将军像只鸟,
遭俘翻腾欲飞逃;
不期大风伤双翅,
脊梁几乎断碎了。
纪伯伦评说道:
这真是好诗。这是我近来谈到的鲁斯图姆的精辟创造性比喻。请代我谢谢他,并转达我对他的最美好问候。衷心祝福他获得成功。
《胡达报》主编奈欧姆·姆凯尔泽勒鼓励纪伯伦在他办的报上发表文章。艾敏便写了一封信给纪伯伦,信末尾说:“亲爱的物质的新朋友,我不对你说‘告别’,而是对你说‘再见’。”这句话使纪伯伦感到痛苦,他回信说:
你的纪伯伦不是物质的新朋友,也不会成为新物质的人,而是旧精神的人,尽管他在物质上是弱者,尚需要吃和穿,以便防饥御寒,免受大自然因素侵袭。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心中至爱和保留生命。
纪伯伦致贾米勒·马鲁夫
贾米勒·马鲁夫(1879—1951),生于泽哈莱。在故乡接受初等教育,后入贝鲁特希克玛学院。
1897年移居纽约,主编《天天报》;该报原由贾米勒的叔父努阿曼·马鲁夫发行。后由纽约迁居巴西圣保罗,继而迁至巴黎和矮斯塔那,然后返回黎巴嫩。贾米勒·马鲁夫留下大量政治、历史著作,其中有:《新土耳其》、《人权》、《民族如何振兴》、《拿破伦·波拿巴的统治》、《女人国》和《黎巴嫩问题》等。
1906年11月2日
亲爱的贾米勒:
你现在在太阳运行的另一个方向,而我仍在这里;我想念着你,而你已距我遥远。但是,这遥远的距离却不能将我们分开,因为巨大的心灵中有无数晕环,就像石子击破静静的湖面荡起的层层波环。
……我们这里是秋天。万木瑟瑟抖动,将剩余的黄色泪滴飘飘洒洒地抛洒在枯草地上,空气中波涌着冬翁的气息。不几天之后,田野和草原就要披上银装。你们那里是春天,生活在苏醒,欢快地唱着歌儿行进。莫非你离去时带走了春天,还是无论春天走到哪里,大自然便美上加美,一片生机?
我依如积习,忙于写作和绘画。时而遨游太空,追逐着被太阳染着金色的云朵。时而沉入大海深处,聆听波涛的呼唤声。我时而跌入黑暗的山谷里,这里充满可怖的幻影,时而又登上松柏密布的山顶,倾听回声的乐曲,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命运降临到我的头上。
这种思想折磨着我的心,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找到值得留存的东西。不过,我应该发奋图强到明天,明天将为我进行裁决,它的裁决是公正的。但是,我想在走之前听一听裁决。
……我亲爱的,爱情是爱情的镜子。爱好是爱好的猜想。真正的爱情不会居于一颗心中,而要居于两颗心中。这使我想起我们曾经谈到的那种火焰,上帝亲自将之分为两半,一半是男人,另一半是女人。
……你在最近写给我的那封信中说,你多么希望有一颗充满爱的心和一个饱含恋情的魂。亲爱的,我可不希望如此。我宁可因爱而死,因恋而亡,也不要远离爱与恋。我宁愿被圣火吞食,也不愿意身被冰包雪裹。我此生中的最大欢乐便是感到魂饥心渴;不饥之魂不会遨游梦想太空,不渴之心也不会翻飞在美之源泉四周。就请你保持原状吧!千万莫求孤独,因为孤独中存在着令人死亡的厌烦。
……
纪伯伦
1908年 波士顿
贾米勒兄:
读到你的来信,我只觉得有一颗神奇的灵魂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游动。那是一颗美丽而令人痛苦的灵魂,它以它的波涛将我分离开来,于是我看到你成了一位具有两种不同圣象的人:一种圣象展开巨大翅膀飞翔在人类的上空,那翅膀就像约翰看见的站在七个尖塔旁的宝座面前的六翼天使的巨大翅膀;另一种圣象则是被坚固的锁链锁在巨石之间,就像将第一只火把从天上降入人间的布鲁米斯,神灵们甚为生气,于是将其躯体捆绑在海岸边的一块巨石上。一种圣象令我心神欢快,因为它伴随着太阳的灿烂光辉和拂晓的惠风波动起伏;另一种圣象使我情感痛苦,令我心与肋饱受压迫,因为它是夜神的俘虏。你过去和将来仍然能够从天上取来火焰,并能将之交给人类,为他们照亮前进道路,可是,世间有哪一条法律,有哪一种力量能将你置于圣保罗,又将你的躯体禁锢在那些生来就已死亡,只是尚未被埋葬的人当中呢?难道希腊女神仍有力量束缚这几代人吗?
我听说你想回巴黎居住。我也想去巴黎,我们能在艺术之都会面吗?我们能在世界中心见面和同住吗?在那里,我们夜里同去听赏戏剧,去法兰西游乐场,然后回来谈论拉辛 395 、高乃依 396 、莫里哀 397 和雨果的作品。我们相聚在这里,漫步走到巴士底狱,然后回到住处,仔细体会卢梭和伏尔泰 398 的精神,然后再写作,写作。我们写关于自由和专制的文字,以便帮助人们摧毁东方每一个地方的巴士底狱。或者,我们去卢浮宫,站在拉斐尔、达·芬奇和柯罗 399 的绘画前留意欣赏,之后,我们返回住处,写作,写作。我们写关于爱和美的文章,写二者对人心的影响。我们这样安排,你说好吗?啊,我的兄弟,我感到饥饿难忍,迫切需要接近艰巨伟大的工作;我感到思念难耐,曲线向往那种壮丽不朽的话语;我觉得这种饥饿和思念是深藏在我心底里的那种巨大力量的结果。那是一种想以不能估计的速度宣布自己存在的巨大力量,只是因为时间尚未到来——因为生时就已死亡的那些人成了活人行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我的健康情况,正如你所知,是一把握在不善弹奏者手中的吉他,使你听到的只能是不令人喜欢的乐曲。我的情感如同有潮有汐的大海。我的神魂如同鸟,双翅已被折断,只有藏在树枝之间痛苦不堪,因为看到群鸟展翅翻飞,而它却不能与它们长空比翼;但是,它像鸟儿一样,喜欢夜的寂静,喜欢晨曦的来临,喜欢太阳的光芒,喜欢山谷的壮美。我时而绘画,时而写作;在绘画和写作之间,我就像一只小船,漂泊在身不知底的大海与蓝天之间;那蓝天便是离奇的梦幻、崇高的意愿、伟大的希望和断断续续的思想。在这些梦幻、意愿、希望和思想当中有一种东西,人们将之称作绝望,而我却将之称作火狱。
我昨天寄给你一本小册子,名叫《草原新娘》,由三个短篇小说组成。第一篇名为《世代灰烬与永恒世界》,那是我们关于真实一半的谈话的结果。我是在它那美的灵魂用它那饰带边沿触摸我的情感和你的声音回荡在我的耳际中时,写成那篇故事的。第二篇题为《玛尔塔·芭妮娅》,那是一位烟花女子的痛苦所洒出的一滴燃烧着的眼泪。那女子还未听到一男子心灵的呼唤声,而且她的灵魂,也没有感受到遇到真正一半所激发起的天赐爱的冲动时,她便依附了那个男子。第三篇题为《痴癫约翰》,讲的是一个在黑暗舞台上的令人悲伤的故事,那是一个鲜活的故事,记录了一个盲目屈服者的生平及害人的专制制度。我观察过,认为过去作家们与牧师的专制进行斗争和反对屈服所采用的手段本身就有害于那些作家们的原则,而有利于敌人。那些作家们把蔑视宗教传统作为打倒那些坚持传统的神父的办法,那是错误的。因为宗教情绪是人的一种自然情感,而通过宗教说教实行的专制制度则相反,根本不是一种自然情感。因此,我使约翰热爱耶稣,信从《圣经》,忠实地服从宗教教育。
……你沉湎于香烟和咖啡,使我对这两种东西更加喜欢。我本以为更加喜欢香烟和咖啡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正像你所知道的那样,我的生活已离不开咖啡和香烟。我想起了一个小故事,非讲一下不可,因为它与咖啡和香烟关系密切,请听我讲:
昨天有位美国太太请我去吃晚饭。这位太太是位富有创意的诗人,也是一位心灵与容貌俱佳的美女。她有一种嗜好,就是使生活美上添花。她的心神渴望得到一切美好有滋味的东西。我们坐下,同张桌上没有第三个人。我们边吃边聊,在一饱眼福和口福之余,免得剥夺耳福享受。我们吃过肉和菜,又吃甜点喝咖啡,之后我点上一支香烟。呷一口咖啡,抽一口烟。我的那位女友津津有味地注视着我,脸上挂着类似春天到来时田野泛着微微笑容。一支烟快燃尽时,又续上一支烟,并且再次将咖啡杯加满,因为周围的环境和我们之间的谈话使得香烟和咖啡有了一种神奇的味道。一阵无言的寂静过后,那位女诗人将目光转向天花板,然后平心静气地说:“纪伯伦,你可知道这是我第一次想做男人吗?”我问:“为什么?”她回答说:“因为男人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既可登上享受的顶峰,也可以潜入享受的深渊,而不必顾及人们说些什么。我们女人则不同,我们总是相互监督着,总是尖锐地批判我们做的好事或坏事。”
我用征询的目光望着她,希望她再解释一下。她说:“假若我现在是个男子,我也能和你一道享受吸烟的乐趣。因为这种土耳其型香烟的气味和点燃的方法勾起了心灵中的强烈馋欲。”我当即站起来,打开烟盒,放在她的面前,用一种意味深长的方法,暗示着许多东西,对她说:“上帝创造了我们,本来就是让我们欢悦,尽情地按我们内心深处所招待自己。来吧,我们一起抽支烟吧!我们把我们一生吞云吐雾的时光比作烟花岁月。”
我们那位女诗人拿起一支烟,夹在她那秀美白皙的指间,将烟点着,开始如饥似渴地抽起来,边吸边凝目注视着那袅袅上升的银线般的缕缕烟丝,一支烟尚未吸完,只见她的脸色已显微黄。片刻后,她用手腕撑着自己的头,双唇间含着微微笑意。我问她:“你怎么啦?”她异常平静地回答道:“我的头略觉沉重,但我心中却充满具有东方色彩的美丽幻想。”
我们离开餐桌,到了书房。在书房,我坐在两个松软的靠枕之间,和她继续交谈。一个时辰过后,她伸出她那丝绸般光滑的纤指,摁了摁自己身边的一个电钮,一个女仆应声赶到。她对女仆说:“约瑟芬,给我们煮一壶浓咖啡来!”
女仆走去,不一会儿送来一壶热咖啡。女仆正要离去时,我们的女诗人喊住她,吩咐说:“如果有客人来访问我,你就说我不在。”之后,女诗人倒了两杯咖啡,微笑着说:“纪伯伦,请给我一支烟!”我说:“你刚开始抽烟,过多对你有害。”他回答了这样一句风趣十足的话:“生活中真正甜美的东西,都是穿过痛苦之路来到我们身边的。”
亲爱的,我们就是在香烟、咖啡、诗歌及类似东西中度过那个夜晚的。第二天,她写信对我说:“给我寄一份香烟礼物吧!”我立刻让她如愿以偿,作为回礼,她给我寄来了那首关于土耳其型香烟的长诗。
……时时已指在午夜后两点钟。酣睡在翕动着人们的灵魂,窗外大雪纷飞,整个城市已换上银装。纪伯伦仍然在与你窃窃私语。黑暗与白雪将亚当的子孙送回了自己的巢穴,寂静笼罩着世间万物的灵魂,我能听到的只有狂风的痛苦啸吟。啊,多么美丽的夜,夜赐予灵魂以理想翅膀,以便让灵魂翻飞,盘桓在乌云之上和乌云之后。
纪伯伦
1912年4月23日
贾米勒兄:
……
明月啊,你怎么样?你好吗?你在巴黎欣赏其壮美,走遍它的角角落落,探访它的秘密和优点,感到高兴吗?巴黎——巴黎——巴黎,那是艺术和思想的舞台,那是幻想和美梦的落脚之地。在巴黎,我获得了再生,我想在那里度过我的余生。但是,我希望我的尸骨葬在黎巴嫩。假若天命助我实现至今盘飞在我头上空的部分梦想,我将返回巴黎,让我那饥饿的心饱餐一顿,让我那干渴的灵魂一番痛饮,我们一起共餐那里的高级面包,一道合饮那里的神奇琼浆。
我在纽约的生活就像被无形之手日夜转动着的车轮。我的工作多不胜数,我的梦想联翩新奇,我的欲望令人生畏,它时而带着我升上云天至高处,时而又将我抛至火狱的最低层。只有站在生活的最神圣之地的人们,才懂得幸福的完全意义和绝对不幸的深层内涵;也只有他们才能在生的杯盏中饮到死的苦酒和从死的杯盏中饮到生的甜酿;我便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纪伯伦
致奈赫莱·纪伯伦
奈赫莱·纪伯伦是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的堂弟。二人也是在故乡贝什里时的童年伴侣。然而移民将二人分开了,纪伯伦迁往美国,而奈赫莱则移居巴西,在那里经商。不过,兄弟友情和对故乡土地的思恋将二人紧紧结合在一起。
1908年3月15日
亲爱的奈赫莱兄弟:
我是多么想念你们,多想把你抱在我的怀里。我在这时收到你的来信,一方面感到心中高兴,同时也觉得心中难过,因为它使我回想起梦幻一样闪过去的时光画面。那些日子一闪而过,留下来的只有随日光而来、伴黑夜而去的忧伤幻影。奈赫莱,那些日子是怎样过去的呢?布特鲁斯 400 活在世上时的那些夜晚到哪儿去了呢?充满布特鲁斯的甜润歌喉和他那英俊容颜的时辰是怎样闪逝过去的呢?那些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就像花儿一样,当黎明从灰暗天空降临时,连续不断地飞逝而去。你知道你深深铭记着那些时日,每想起它便激动不已。我从你这封信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你的情感的影像,仿佛它来自巴西,以便将贝什里周围的山谷、废墟和小溪的回声传到我的心中。亲爱的,生命有些像一年的四季:欢快的夏天过去,紧接着而来的便是悲凉的秋季;随悲凉秋季而来的便是愤怒的冬天;美丽的春天随着可怕的冬季的消失而显现。我们生命的第二个春天还会再来吗?到那时,我们与万木共欢同乐,与百花一道微笑,跟着小溪流水奔跑,和着鸟雀啼鸣歌唱,就像布特鲁斯活着时我们在贝什里那样玩耍嬉戏……这样的春天会到来吗?风暴还会回来,就像将我们分开那样,再将我们聚集在一起吗?我们能够回到故乡再一起坐在玛丽·赛尔基斯修道院旁,坐在奈巴特河边,坐在玛丽·吉尔吉斯山的巨岩之间吗?这些,我全不知道,但我觉得生命是一种债务与偿还;它今天借给我们,明天则要我们偿还;然后又借给我们,再要我们偿还,直到我们在借贷,归还中疲惫不堪,由苏醒变为因疲惫而转入睡眠。
奈赫莱,你知道,纪伯伦把自己的生命的大部分都用在了写作上,他发现给他最喜欢的人写信,有一种神奇的乐趣。奈赫莱,你知道纪伯伦小时候最喜欢奈赫莱,而在长大成人之后也未曾忘记过奈赫莱。童年所喜欢的东西,深深印在心中,直至老年都不会忘记。奈赫莱,在这一生中最美好的东西,便是我们的灵魂盘飞在我们曾经享受某种乐趣的地方上空。我就是对事情永远保持记忆的人之一,无论那些时期多么遥远,多么细微,也决不会让它的幻影随雾霭而消逝,我对以往岁月的幻影记忆得那么清楚,也许因为我在某些时候的忧伤与苦闷过甚;但是,若容我自由选择,我决不会用心中的悲伤去换取世界上的所有欢乐。
现在,请允许我为过去的容貌罩上一层面纱,容我把我的现在和未来告诉你。因为我知道你想了解你过去喜欢的那个少年的情况。请听好,我现在就给你讲纪伯伦故事中的一节:我是一个体弱者,而我的健康状况总是好好的,因为我不去想它,也没有时间顾及它的特点和情况。我喜欢喝咖啡,喜欢抽香烟。奈赫莱,假若你现在来了,进到这个房间,便会发现我被散发着希贾兹咖啡浓香的香烟云雾所遮罩。
奈赫莱,我喜欢工作,不让每一分钟空过。对于我来说,我的灵魂沉睡、我的思想懒惰的那些日子,则苦过西瓜汁,难过的如同身落狼口。我在写作和绘画中度过;我在这两种艺术中所体验到的快乐胜过一切。这柄滋养我的情感的火炬,想以墨水和纸作为衣裳,我不知道阿拉伯世界是否仍像近三年那样还是朋友,或者变成了可怕的敌人;我之所以这样说,叙利亚人将我称为叛教徒,埃及的文学家们则批评我说:“这是公正法则、家庭关系、古老传统的敌人。”奈赫莱,这些作家说的是真理,也是事实,因为我一番自问之后,发现我的灵魂厌恶人类为人类制定的法律,憎恨祖辈留给孙子们的陈旧传统。这种憎恶是我深爱神圣精神情感的果实;这种神圣精神感理当成为大地上每一种法律的起点,因为它是人间的上帝的影子。我知道,我为我的作品所确定的原则,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居民的响应。因为对精神上独立的向往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如同心脏在体躯中的地位……难道我的学说在阿拉伯世界没有丝毫分量,或者像树影一样隐翳消逝了吗?
纪伯伦能把人从骷髅和荆刺变成光明和真理吗?或者纪伯伦像许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一样,身后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人们提及的东西,便回到永恒世界去?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在我的脑海和内心深处有一种力量,它一直想迸发出来;如蒙天意,它定会与岁月一道冲出来。
我有一个不乏重要性的消息,那就是我将于七月初赴巴黎加入绘画委员会,而且将在那里停留一整年,然后返回这个国家。这次远行必将充满艰辛、困苦、学习与探索,但它同时也是新生活的开端。
奈赫莱,当你们聚会时,当全家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时,我希望你常提及我,并说有一位名叫纪伯伦的亲戚,他对家中的每位成员都怀着深情厚意。
我妹妹玛尔雅娜与我一道向你们所有人问好。我已向她读过你的来信,她非常高兴。当读到某些段落时,她禁不住淌出激动的泪水。
祝你健康,永远做你兄弟喜欢的人!
纪伯伦
1909年12月14日 巴黎
亲爱的奈赫莱兄弟:
奈赫莱,敏感心灵会记住每一句有意思的话,每一个高尚的工作隔阂每一项美好的活动,直至生命的尽头。在这个世界上,最令敏感心灵感到痛苦的则是误会。
现在让我来向你谈谈你最感兴趣的事情。我的健康状况很好,我的工作正像我所理想的那样进行着。如蒙上帝默助,我将于来年春天在国家的展览馆里展出我的部分画作。奈赫莱,我已看到未来正在向着我微笑,我不应该像偶像一样面无表情,而应该用工作、学习和探索面对未来的微笑。
我的朋友艾敏·雷哈尼先生将到巴黎来。如蒙天意,你将听到令你快慰的消息。因为我们将进行一项极好的工作,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艾敏·雷哈尼是叙利亚少有的人才;面对伟大工作,他是不会退缩的。
纪伯伦
1910年3月7日 巴黎
亲爱的奈赫莱兄弟:
这些天来,我颇似被工作转动的轮子,想停都没有办法停下来。但是,你知道,没有工作的生活就像死亡一样。两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忙于准备送往即将在下周开幕的法兰西美术展览会的部分画作。在我准备送展的作品中有一幅巨制,被我命名为《历代行列》;至于我在这幅画中倾注了多少心血,则只有上帝知道。因为这幅画所涉及的题目,需要进行大量研究,要花费许多时间苦心思考,还要有深层次的感悟。我真不知道自己把工作做好没有,只知道自己在那幅画中投入了上帝赋予我的一切和人的能力能够完成的一切。不久的将来,我会将结果告诉你。
奈赫莱,我们能在黎巴嫩见面吗?到那时,我们将分骑两匹宝马,去巴勒贝克废墟一游。我们将穿越阿绥,从那里前往霍姆斯,再去宽广的平原。我们在阿拉伯人中间过夜,听他们唱歌,让我们的胸中充满美妙的“迈瓦利亚”情歌 401 。这是遥远的美梦——随夜幕垂降而至,复伴晨光而去的美梦——人们醒时将之视作幻梦,很快便在眼前消失,就像山谷中雾霭画面,顷刻消散,影迹不见。
……
纪伯伦
1910年5月7日 巴黎
亲爱的奈赫莱兄弟:
几天之前,法兰西全国美展开幕了。这画展的重要性,当然你是知道的,它是现代文明展,其地位相当于阿拉伯蒙昧时期的“欧卡兹集市” 402 。奈赫莱,我真希望你能来巴黎,一览法兰西共和国的壮美外观,亲眼看一看用绘画和雕塑表现出来的艺术之美,颇似《一千零一夜》作者所谈及的奇珍异宝。在法兰西共和国建造的代表着他的国力和财富的宏伟建筑中,排列着当代最杰出的画家和雕塑家们的绘画与雕塑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一幅生长在可迪河谷梁上的黎巴嫩青年的画作。奈赫莱,我不曾梦想评判委员会将接受我的这幅作品,以便将之悬挂在艺术大师们的传世佳作旁边。但是,我却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学习,以期获得为实现理想未来的这种精神积淀,继而将我的目光转向太阳。上述画作所表现的是《秋》,画面中站着一个半裸女人。瑟瑟秋风戏动着她的秀发和面纱,她以她的站姿、色彩向四周环境诉说着自来夏日欢乐和冬季痛苦之间的忧伤。法国报纸以大量篇幅谈这个展览,而且有文章提及我的名字,文章末尾用了一些很有味道的形容词,以赞美的词句评说这幅画。评判委员会还给我发来一封信,信中有许多鼓励的话语;我将把这封信保存到生命的终点,以便使我记起在巴黎度过的勤苦岁月。
我还有一个消息,其重要意义可与上述消息相提并论:法国一家大杂志已经向巴黎学院阿拉伯教授米沙勒·拜伊塔尔先生约稿,要他把《玛尔塔·芭妮娅》译成法文。这位教授已经译完,不几周之后,这篇小说将登载在那家杂志上,并附有我的生平简介。也许《玛尔塔·芭妮娅》将是第一篇译成法文的阿拉伯短篇小说。不过,我希望《沃尔黛·哈妮》也能译成法文,因为我更喜欢这篇东西,更倾向它的思想和情感。你在我已故母亲的衣箱里发现的那些东西,虽然本身没有多大价值,也不是什么贵重之物,但我打心眼里想得到它,因为那是我母亲的遗物,我理当敬重母亲留下的东西。因此,奈赫莱,我希望你把那些东西送给贝什里的穷苦人家。
上面提到的那些东西,应该归穷苦人所有,而不属于那些讨饭的乞丐。你可以把那些东西悄悄地送给故乡穷苦人,只要提一提我已故母亲的名字就行了。
纪伯伦
1910年9月27日 巴黎
亲爱的奈赫莱兄弟:
你还记得冬天大雪纷飞、寒风在住宅周围呼啸时,我们围在火炉旁聆听的那些有趣的故事吗?你还记得那个关于花木茂盛、风景秀美、果实香甜的花园的故事吗?你还记得那个故事的结尾,那些中了魔的树木怎样变成了大人和小孩儿,天命又如何将他们带进花园里的吗?当然,你记得这一切,但你不知道纪伯伦就像那些中了魔法的青少年,身上缠着无形的锁链,受着看不见的东西制约着。
奈赫莱,我是一棵中了魔法的树,直到现在阿拉丁 403 也没有从七海回来为我解开桎梏,从我的身上将魔套解除,使我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自由人。两天前,我买了一张去往纽约的票,下月十四日我就将告别巴黎和这里的一切。现在,我正忙于安排我的工作。上帝知道我像轮子一样,日夜围绕着我的工作转个不停。苍天就是这样与我的生命做游戏,命运就像这样让我围着一个已知点转动,使我不能偏离它。
我今晨收到了你的来信,自打那时起,我一直在想呀想,但不知道该干什么。奈赫莱,你能用你的思想和情感给我以帮助吗?难道你不能朝我的内心深处看一看,以便看一下上帝置于那里的不幸和辛酸?我所要求你的,就是让你与我一道感受一下,相信我已经变成了现实条件的俘虏。奈赫莱,我并不抱怨我的命运,而且也不想用另一种情况替代我现在的处境。因为我已经选择了文学生活,完全知道这种生活面临的痛苦。
奈赫莱,只要你稍稍观察一下纪伯伦的生活,便会发现那是一种奋斗和挣扎,简直是由艰难和困苦组成的锁链,一环扣一环。我虽然这样说,但我坚强地忍耐着,而且为生活中充满艰难困苦感到高兴,因为我满怀希望克服它,战胜它;如果没有艰难困苦,也便没有奋斗与工作;倘若没有奋斗与工作,生活会变得冷酷、荒凉、寂寞和令人生厌。
纪伯伦
1911年6月17日 波士顿
亲爱的奈赫莱兄弟:
近些天来,因为我在一次文学聚会上发表了一次演说,阿拉伯世界天翻地覆,对我议论纷纷。我在演说中说,叙利亚人不应该依靠自己的国家,而应该依靠自己。因此,埃及、叙利亚的报纸对我进行了严厉、尖锐的批评。
奈赫莱,我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我要沉默了,人们愿意说我什么,就让他们说吧!我应该忠实地说真理,不管人们满意还是发怒。
纪伯伦
1918年9月26日 纽约
亲爱的奈赫莱兄弟:
上帝向你的美好灵魂和宽广心胸致安。今天早晨收到你6月21日的来信。看来北美洲的监察部门很像南美洲的监察部门。那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协约国认为应该检查每一封信,以便弄明黑白,知道是德国人还是非德国人。
东方运动中的志愿活动在这个国家里依然开展得热火朝天,叙利亚和黎巴嫩解放委员会在此间成立,很重视在派往叙利亚的志愿者问题上与法兰西政府合作。但是,叙利亚人至今还没有学会如何真切地显示热情。虽然在美国军队中有一万五千名叙利亚裔士兵,与我们发起志愿活动的种种原因相比,至今派往东方的人太少太少了。但是,不管叙利亚人能否尽自己的义务,前程已在向叙利亚微笑。在过去的一周里,我们国家挣脱奥斯曼统治和奥斯曼压迫的疑问已经消失了。
纪伯伦
纪伯伦致赛里姆·赛尔基斯
赛里姆·赛尔基斯(1869—1927),年生于贝鲁特。先就学于艾尼·泽哈莱塔学校,后入布特鲁斯·布斯塔尼 404 先生创办的国民学校。自幼与其叔父哈利勒在《实况喉舌》报工作。
1892年赴法国,在那里与艾敏·伊尔斯兰等文学家、思想家共同办《揭面纱报》。
由巴黎迁往伦敦,在那里发行《回声报》。没过多久,即离开伦敦,于1894年赴亚历山大。在那里创办周刊《指导者》,因此被奥斯曼帝国宣判死刑。随即迁往开罗,然后赴美国。他到哪里,就将报办到哪里。他最后在埃及创办的杂志《赛尔基斯杂志》是他于1905年从美国带到埃及的。
他留下大量著作,其最有名者《稻米》、《美国的团结之心》、《角落隐秘》、《纺织潮露》、《1920年的鲁图福拉家族》等。
1912年10月6日 405 纽约
亲爱的赛尔基斯先生:
现将精灵新娘默示的一篇故事寄给你,以表示对哈利勒·穆特朗 406 先生敬重之情。正如你所看到的,这篇故事与伟大的埃米尔的尊严及伟大诗人相比,显得太短;而在喜欢言简意赅的作家和诗人看来,又嫌过长,尤其是在表彰性质的大会上。不过,这是新娘的默示,其中必有些许原因,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谨对您邀请我参加表彰一位伟大诗人的盛会表示衷心感谢。这位诗人将他的精神作为玉液琼浆全部注入了现代阿拉伯复兴杯盏之中,将他的心作为香焚烧在两国圣坛之前,从而使友好关系更加密切。
请接受我充满敬佩之意的问候。
纪伯伦
纪伯伦致艾敏·穆什里格
诗人艾敏·穆什里格(1894—1928),生于朱拜勒省的艾尔祖兹。在乡间小学接受初等教育,后入的黎波里的美国学校。
1914年离开黎巴嫩赴美。在纽约结识纪伯伦及其文学界同事,后由纽约去厄瓜多尔经商。
1932年回到黎巴嫩成婚。之后返回定居地瓜亚基尔 407 。1938年死于车祸。
1982年朱拜勒省文化委员会将他的诗作和散文收集成册出版作为对他的永久纪念。
1919年11月23日 纽约
亲爱的艾敏兄弟:
上帝为你祝福。收到了你的亲切来信,感谢你那罕有的文学激情及你留心在你的朋伴和相识中间传播《行列之歌》 408 一书。那是一种持久的力量,我也是以默示你在这方面发奋图强的那种情感领受这种力量的;我的意思是说只有精神上的联系才会产生的那种情感。按照你的旨意,今天我给你寄去了五十本《行列之歌》和一本《疯人》 409 ,但愿你从这两本书中将发现使你感到高兴和快乐的东西。我将这些书打成十八包邮寄,期望你能顺利收到。
当然,《艺术》停刊,我和那些与你同感遗憾的人一样感到惋惜。我已试图与部分朋友一道努力,帮助奈西卜·阿里达复活这个杂志,但没有成功,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印刷、出版材料价格昂贵,使该计划的投资者失去了信心。不过,我们仍然怀着希望,也许一世难办的事情一时便告办成。
请接受我的问候、祝福和友情。上帝保佑你平安。
忠实的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
又及:
寄给你的书所写地址如下:
Ms.Amine Muchrck Coayaquil Ecuador
1930年7月7日
亲爱的艾敏兄弟:
向你的美好慷慨精神问安致意。我在波士顿城收到了你寄来的礼物,当着一些好友的面打开外封皮,取出礼物,一种奇异美妙的情景令在场者惊喜不已,更使他们发笑的是那王冠的拙朴,如同美术博物馆的藏品。你干得好啊!我知道你是怎样地使我感到自豪,让我高昂着头,几乎摩云接天……我感到豪迈无比。我仅仅看一看这件古董,便觉得白日的温度已开始下降,甚至连神仙都会感到舒适的程度,于是我的心灵随即歌唱起来,感赞上帝。
只要我还活着,我一直将你的恩情顶在我的头上。愿上帝让你永做我亲爱的兄弟。
纪伯伦
纪伯伦致布特里斯·哈纳·塔希尔
1924年2月12日 纽约
亲爱的朋友:
谨向你的美好灵魂致敬。今天我见到了美国的茂顿太太,她将那封甘美的来信交给了我,之后她又絮絮叨叨地讲你对她和阿卜杜·巴哈·阿巴斯 410 的两个女儿所表现出的慷慨品格及种种善举。听到这位贵夫人的絮语,我感到非常高兴。接着,我向她提出一千零一个问题,详细询问你和你的家庭情况,还问到故乡贝什里。她的回答使我心中充满对你们及故乡的想念之情。
近来我收到许多访问过黎巴嫩北方的美国人写给我的信。他们每个人都说了关于我们祖国及其人民的许多好话。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十分希望黎巴嫩人尤其是黎巴嫩北方人为旅游者提供更多舒适的条件。若把他们的这种想法告诉我们的乡亲,乡亲们定会留心这不但能给他人提供方便,也将给他们自己带来好处。
请多多把你的情况告诉我,也希望把你的乡亲和我的乡亲的情况告诉我。请不要忘记以我的名义向你的双亲问安。求上帝保佑平安。
忠实的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
致菲里克斯·法里斯
菲里克斯·法里斯(1882—1939),生于黎巴嫩山脉迈特尼省的赛里马。在拜阿白达小学接受初等教育,毕业于1898年。跟其父亲学会阿拉伯语,随其法国裔母亲学得了法语。
1909年创建《统一语言报》。两年之后停办,以便去阿勒颇教授法语。他在阿勒颇一直逗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21年,奥鲁将军派他去美国到黎巴嫩、叙利亚侨民中间执行一种特殊任务。在此行期间,他与侨民文学家和诗人的关系得到加强。
他回黎巴嫩之后,开始了律师生涯。
菲里克斯·法里斯以善演说而著称,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同时也以文学创作为职业,致力于民族的复兴与觉醒。他的主要著作有《阿拉伯东方讲坛的使命》、《与叙利亚妇女私语》;小说《纯真的爱情》、《爱慕与狂恋》;剧本《桎梏》、《雅典革命》;学术著作《德国近二十五年来的进步》;诗集《吉他》(未曾出版)等。
他最著名的译作是《琐罗亚斯德对德国哲学家尼采如是说》、法国杰出诗人缪塞的《世纪儿忏悔录》 411 。
菲里克斯·法里斯致纪伯伦
菲里克斯·法里斯写信给纪伯伦,信中说:
……纪伯伦,我看你的病比我的病还要重,来吧,我们到体躯的故乡去问候它一番吧!躯体热恋故乡的土,就像灵魂当痛苦风暴刮起之时对自身精髓的向往。
兄弟,来吧,让我们抛开那些垂头丧气的人,把身心健全的人带到安静的地方去吧!我的心灵中充满对你的思念之情;这种思念类似于思念把我自己的心放置的那个地方。站在贝鲁特港,我的双目仰望着我的雪杉乐园及我的祖国田园。纪伯伦,站在你的身边,我的心灵遥望祖国大地上的永恒雪杉,仿佛祖国居于宇宙的真正边沿。来吧,让我们争取爱国者,医治两种疾病吧!这种使你疲惫不堪多年的文明已经远离我数月。来吧,让我们把由此而产生的痛苦放在雪杉和雪松树荫中;到那时,我们将最贴近大地,最接近苍天。
……我的双眼思观大地沃土及隐秘世界在其中的显灵。纪伯伦,请相信,自打你我家乡东方大地的壮景消失在我的视野之内那一刻起,我再也没有看见过一朵鲜花,没有嗅到过任何芬芳气味,没有听见过燕子鸣叫一声,没有沐浴过一丝惠风。
来吧,让我们唤醒沉静的痛苦!来吧,让你那晴朗的天空听一听你那饱饮忠诚的歌声,让你的画笔画出现在你心中的幻想印象。
菲里克斯·法里斯
纪伯伦致菲里克斯·法里斯
1930年
亲爱的菲里克斯:
……某暴君同时向我们射出一只箭,射伤了你的一个翅膀和我的一个翅膀,这是不足为奇的。兄弟,这没有什么关系。痛苦本是一只无形的手,它可以打碎核的外壳,使核仁开始生长发育。我仍然是专科医生手下的人质,他们不停地为我称量,直至我的躯体背弃他们,或者我的灵魂抛弃我肉体而去。这种背弃也许以顺服的形式而来,或顺服以背弃的形式而去。不过,不管我背弃与否,我一定要返回黎巴嫩,一定吸收这种靠轮子行走的文明,一定要拥抱那种关于阳光的文明。但我认为,我不应该离开这个国家,直至借之斩断捆在我身上的绳索和铁链;君必知,那绳索和铁链是何其的多啊!
我想去黎巴嫩,意愿不移。
纪伯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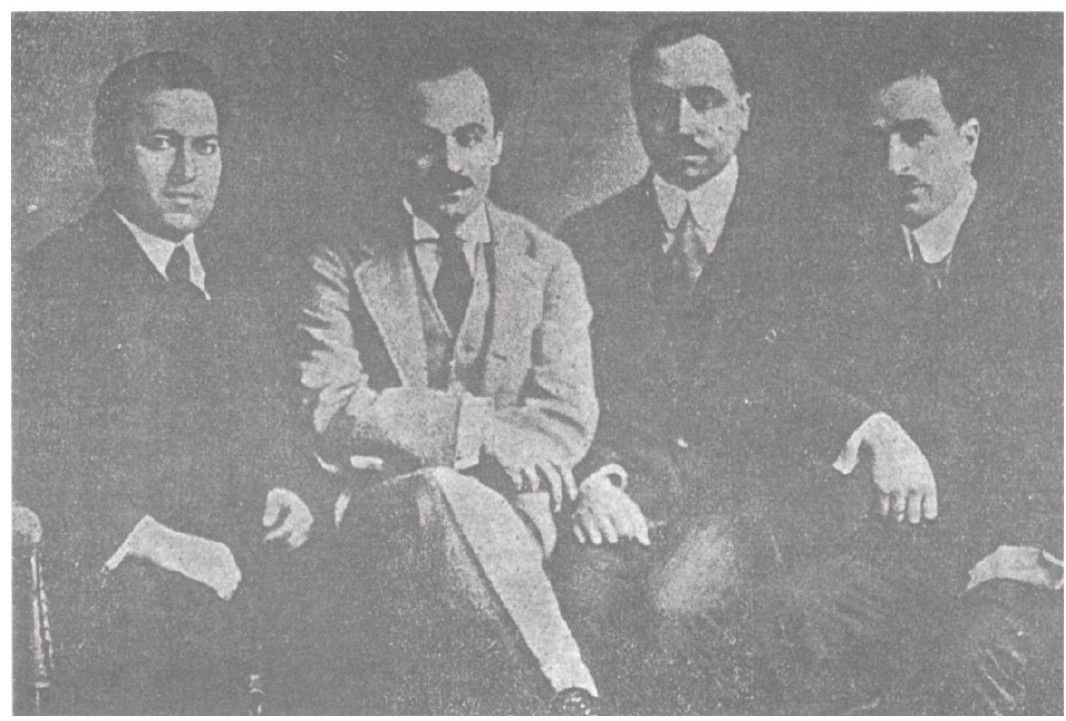
纪伯伦(左二)和笔会主要成员阿里达(左一)、哈达德(右二)努埃曼(右一)合影(摄于19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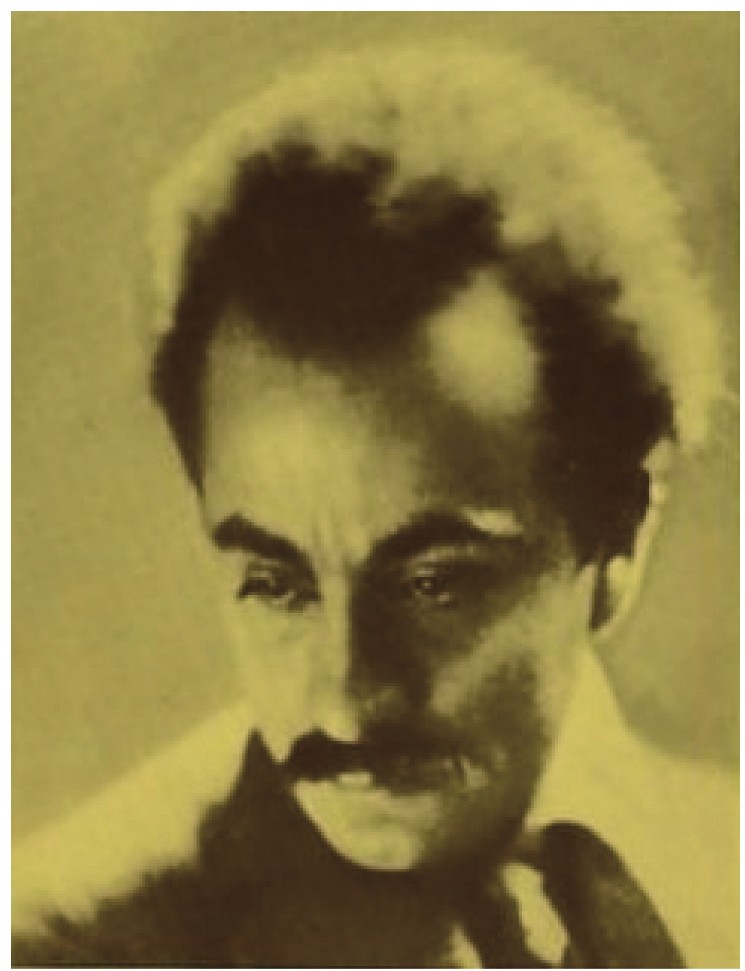
中年纪伯伦
致艾德蒙·沃赫拜
艾德蒙·沃赫拜20世纪初生于阿里亚县的赛勒法亚。
1925年,艾德蒙·沃赫拜访问纽约期间,在晚宴上与纪伯伦相识。
他在法国驻东方代表团工作,之后担任法国公使翻译。自1940年至1965年逝世前,一直在法国驻黎巴嫩新闻处任职。
他发表过许多政治、社会方面的著作。
1919年3月12日 412 纽约
亲爱的文学家兄弟阁下:
你好,我收到了你的来信。信中洋溢着你的文学天赋、灵魂美和你对艺术及艺术之子们的热情,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我真希望自己不愧你的信中对我的称赞,但我期望有一天实现你对我的美好祝愿。
我怀着敬佩的心情读了你选定并译成法文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413 ,不过,你所谈到的黎巴嫩、叙利亚青年一代的心理状态及他们热衷于外国语的倾向,不免是我感到遗憾。正是这一点激起了你的爱国热情,于是将用祖辈语言写给青年一代的小品译成外文。
你对笔会 414 及其成员所取得的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热情,证明你倾向于革新、进步和发展的决心和愿望。在此,我谨代表笔会的兄弟同仁们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请接受我的敬意与友好之情。上帝保佑你。
忠诚的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
又及:
劳驾代我向优秀的文学家菲里克斯·法里斯兄弟问好致意。
约1925年
亲爱的兄弟:
向你的美好心灵致意。我今天收到了你的有滋有味的上乘礼物。我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词语感谢你对我的关心和重视。
那礼物何其多啊!它令我们赏心悦目,但不超越我们的目光,那礼物又是多么少啊!它却触摸和弥漫了我们的心,因为它是充满恩惠与欢乐的巨大之心的外在表征。
你的善举令我感动得无以复加。我衷心为你祝福。若有机缘,我真想向你倾吐我的所有感触。
但求上帝让你的两掌中充满生活的甘甜和馨香。愿上帝保佑你。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