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象比类:想象力“恶之花”
蜘蛛网治健忘/表象与意象/五色与五脏/“失眠第一汤”与甘澜水

中医学是人类历史文明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绵延千年,是中华历史文明的继承者,体现了中国人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欲望,也凸显出中华文化的奥妙。
现代西方医学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发展迅速,中医则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时光慢慢踱步前进,现代科技会让中医学的发展向左还是向右,不禁让人好奇不已。
虽然屠呦呦院士从中药中提取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让不少人开始重新审视中医药的存在意义,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人们对中医学的态度依旧褒贬不一:有人为它摇旗呐喊,积极背书;也有人对它不屑一顾,冷嘲热讽;其他人则处在一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尴尬境地:不知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对中医学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一拨人,也是有自己的论据来佐证其观点的,比如中医学的“取象比类”治疗法,这大概是导致一些人有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过于想当然的治病逻辑
我们不妨先来看古代医书中的几个奇特“妙方”:
翻开明朝的陈嘉谟撰写的《本草蒙筌》,有一种治病的药方很是奇妙,这个妙方可以称为“蜘蛛网治健忘方”。
怎么个奇妙法呢?蜘蛛网“七夕取食,方获奇效”,即七夕这天取来的蜘蛛网,可以拿来治疗健忘,而且疗效十分好。
再来看清朝张璐撰写的《千金方衍义》,这本书里面也有奇妙的药方。比如“蝉皮方”:取两个蝉皮,弄成粉末,三指撮,就温酒服用。
这个方子是治什么的呢?治疗“逆生”或“横生不出”,就是女性分娩时孩子的脚先出来(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头先出来),或者干脆生不出来。
再比如“蛤蟆兔屎方”:“蛤蟆兔屎,上二味等分为末,取敷疮上。”
这又是治什么病的方子呢?——阴蚀,又叫阴疮,就是生殖器部位长了肿块或者出现溃烂,成了疮。按照这个方子敷药即可!

因蝉“善脱”,古人就用蝉皮治难产,希望女人分娩能像蝉蜕皮一样顺利。
古人为什么要用这么奇葩的药方呢?
先说“蜘蛛网治健忘方”。为什么选蜘蛛网治健忘?还要选七夕这天去取?我国传统的七夕节在古代也叫乞巧节。神话中的织女非常心灵手巧,所以,女孩子在七月初七晚上诚心祈求、许愿的话,就会变得聪明、灵巧,可以很快掌握女孩子需要具备的各种生活技能,比如织布、绣花之类。
蜘蛛网又是怎么一回事?它源自蜘蛛网“卜巧”的意思。在七夕这天,捉到蜘蛛后放在一个盒子里藏起来,第二天看蜘蛛结网结得怎么样。如果蜘蛛结网很密,说明“巧”多,捉到蜘蛛的人以后就会心灵手巧;如果结网疏松,“巧”就少,说明这个人容易大意,办事不周。
而且,这种“听天由蛛”的习俗从汉代起就已经开始了。
再来说说用蝉皮治难产。古人认为,蝉“善脱”。女人生孩子犹如过鬼门关,人们希望女人分娩能像蝉蜕皮一样顺利,能很容易把孩子生下来——所谓“金蝉脱壳”也。
如此一说,蛇也能蜕皮,那么用蛇皮也行吗?答案是肯定的。蛇也是“善脱”的动物,所以也能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记载的就是用蛇蜕的皮来治疗。
选蛤蟆和兔屎来治疗“阴蚀”,则跟古代的特殊信仰有关。在古代的传说中,兔子原是月亮上的生物(可追溯到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等神话),而月亮属“阴”,与太阳所属的“阳”相对,那么属于月宫的兔子的屎就可以治“阴”蚀。至于蛤蟆一说,据说是一只三只脚的、像蛤蟆的妖怪,为了吸收月亮的光,把月亮吞了,所以才出现了“月食”,所以蛤蟆也是可以克“阴”的。
除此之外,人们还用蝙蝠治疗视力不好——蝙蝠在夜间飞行;用猫屎治疗老鼠咬伤——动物相克;用小麦苗汁治疗黄疸——小麦苗在春天生长,所以能通达肝气……对于这样的解释,如今看来未免太过儿戏。要说蝙蝠在夜间飞行,那猫头鹰也是夜行动物;猫捉老鼠,老鹰也能捉;不只小麦苗在春天生长,那么多植物都是春天开始复苏……如果用这样的逻辑就能想出办法治病,想来人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独门秘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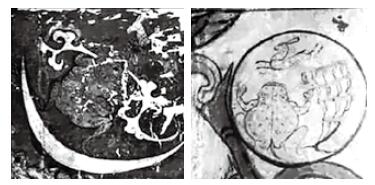
马王堆西汉墓出土帛画中的月亮和磁涧西汉墓壁画中的月亮,可清楚地看到里面有蟾蜍和兔子的形象。
吃啥补啥
前面提到的古人治病方法,其实可以归结为“取象比类”治疗法。古人选取治病的药材,并不是按照药材所含成分是否治病这一标准,而是一厢情愿地根据药材与人类“相似”的“特性”来做选择,这种选择药材的方法可以称之为“取象比类”。
那究竟什么是“取象比类”呢?想要一探究竟的话,我国古代大文学家苏轼可以给大家答疑解惑。他的文章《荔枝似江瑶柱说》中有这样一段话:
仆尝问:“荔枝何所似?”或曰:“似龙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实无所似也。仆曰:“荔枝似江瑶柱。”应者皆怃然,仆亦不辨。昨日见毕仲游,仆问:“杜甫似何人?”仲游云:“似司马迁。”仆喜而不答,盖与曩言会也。
在这个故事中,认为“荔枝似龙眼”是直观感受,只是看到了两者的表象——都是圆的、甜的,并没有指出它们之间本质的区别,所以客人都笑了。
后又说“荔枝似江瑶柱”,“江瑶柱”是用江瑶贝的闭壳肌制成的一种名贵的海味小吃。这一类比已经超越了形体的表象类比,而是通过这种名贵的小吃来夸赞荔枝的高贵品性(苏轼很爱吃荔枝),这种非直观逻辑的类比相较之前的“龙眼”更进一步。但这种类比的问题是有很大的个人主观性,无论从形态还是从质地,两者好像都不相干,也没有相似之处,只是苏轼自己给荔枝赋予的一种类比关系。对这个类比,人们拍掌而笑,但苏轼却认为自己的类比很准。
后来,苏轼遇见了好朋友毕仲游,就问他:“杜甫像什么人?”朋友说:“像司马迁。”苏轼听后,“喜而不答”,欣然默许。为什么?毕仲游用司马迁比杜甫,当然是从两人的学识、才华、内在品性和对历史的影响力上来说的,而跟他有同样学识的苏轼,认为他的这种类比极有道理。
苏轼和他的朋友正是通过直觉思维,用取象比类的方法,表达了不同事物内在的相同本质和规律,他们两个的认同感是建立在对杜甫和司马迁有同样认知的基础上的。如果换成问仆人,这一类比恐怕就不成立了。这是古代关于取象比类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简而言之,取象比类是将符合同一规律的事物归于一类来研究的思维方式,它在物象的基础上,靠想象直接进行推论。比如看到A,通过想象挪用到有类似特点或情景的B上,而不管它们是不是真的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取象比类是中医学常见的一种思维模式,中医学也因此学说而被很多人质疑和否定。
“天人合一”的思想根源
取象比类的起源可追溯到6000多年以前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一切人事都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西医治病要求明确的定性、定量、定位,必须有直接的效果;而中医就稍有不同,它还包含了中国特有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及气化学说,还有《易经》中所表达的“万事万物都处于变动中”等哲学思想。所以,如果说西医治病的理念是静态的,那么中医的理念则是动态的。
“取象比类”中的“象”有三种不同的含义。第一种是最简单的,即单纯表象和体征,就是外表看起来像;第二种是“意象”,这一种逻辑稍微高深(或者无理)一点,把主观的意念附加于某种符合意念的事物之上;第三种是将事物归类,总结它们的共同规律。如果不同事物存在某种相似性,可以将其归为一类;甚至可以设定某种标准,把不同种类的物象联系起来——即便它们没有关系,也可以“撮合”到一起。
从季节上看,树木花草和人处于夏天的时候,就同处于同一“火象”,因为天气炎热,跟处于着火的状态很像;同时,人的脏器中的心脏跳动力很强,如同火苗一样,使人有了体温,所以也属火;从地理位置上看,南方比较热,热得如同下火了一样,所以南方也属火;等等。此种类比之象处处可见。
与之相对应的,春天万物复苏,则是“木象”;秋天累累硕果,处处一片金色,是“金象”;冬天冰雪覆盖,是“水象”……
再比如,所有事物上部都具“阳象”,下部则是“阴象”;奇数为阳象,偶数为阴象……不胜枚举。
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古人治病也不会像西医那样,研究化学成分、化学元素、DNA、细胞等,反而把精力放在研究万物的生长习性、气机变化上。
红色的食材在古人看来属“火象”,而人体心脏也属“火象”,所以红色食材补心,对心脏有益,心脏不舒服可多吃红色食物,如红枣、红豆。
绿色食材属“木象”,而人体的肝脏也属“木象”,所以绿色蔬菜对肝脏有好处,肝不好就多吃点菠菜、青菜、黄瓜等。
以此类推,白色食材对肺有好处,黑色食材对肾好,黄色食材能补脾——这就是中医很有名的“五色对应五脏”学说。
再介绍另一个很有意思的药方,《黄帝内经》中的“失眠第一汤”——半夏秫米汤,对这个药方的治病机制,现代人听完之后肯定要“拍掌而笑”了。
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其滓,饮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为度,故其病新发者,复杯则卧,汗出则已矣。久者,三饮而已也。
将盆内的水用瓢扬起来、倒下去,重复多次,直到看到水面上有数不清的水珠滚来滚去。这时候的水被称为“甘澜水”。然后取部分清水,烧芦苇煮沸,然后加粟米、半夏,慢慢烧到一定程度,去掉渣滓。每次喝一小杯,每天三次。新发病的人喝两杯后躺下,出汗后,失眠就可痊愈;至于久受失眠困扰的人,则需要喝三杯。
普通的清水被搅了几次就变得不一样,就有了神效?在古人看来,一个人阴阳之气不通达——“阳不入阴”,就会失眠。这个药方中,把水扬起来又倒下去,重复多次,这样一来,水就富有了“流动”的气力。至于芦苇,它则代表“空心通达”,粟米代表“黏滑”,半夏代表“潜阳入阴”——这些事物结合起来做成汤药,就能让病人阴阳通达,阳也能入阴,就能治疗失眠。

水扬千遍,静止的水有了“流动”的气力,可通达阴阳,用此水熬药,其效甚显。
取象之辨
作为一种唯象理论,取象原是我国古人通过眼睛直观得来,再用一些特殊方式(类比、象征等)来认识这个大千世界的奇妙方式。它的观察方式可以由表及里、由外到内,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虽说不失为一种探索事物的研究方法,有助于了解某种属性,但它也给中医治疗带来了表象性、模糊性、不确定性,这在治病中存在相当大的风险和禁忌,容易酿成悲剧。
要知道,不同事物、不同的人,除了拥有相似性,更多的是差异性,况且,相似的属性之间也不一定有必然联系。只谈相似性而忽略差异性,难免存在很大弊端。
因此古人取象比类的思考模式就显得轻率,不利于人们进行深入思考,对药物和疾病的本质认识也更容易出现偏差和谬误。
取象比类完全没有效果吗?也不是,有时会有效果,所以经常出现有时有效、有时无效,甚至加重病情的现象。很多冒这种风险以身试法的人,多是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当然,想想古代人知识贫乏,很多人也是任由命运摆布而已。
所以,对取象比类治病的思维,应该客观地认识,纵然不能一概否定,但也不能盲目相信。对于根据明显不合理的联系而得出的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我们更应该果断舍弃。
方剂名称里的取象思维
取象比类所包含的内容很广,譬如古代医学典籍中的“大方”和“小方”,“缓方”和“急方”,“奇方”“偶方”和“复方”,“汤剂”“丸剂”和“散剂”,也有类似的意思在里面。
大方就是药物种类多、药量大、药力猛的药,主要用来治疗重病或下焦病;小方治疗较轻的疾病或者上焦病,药量轻,或药物种类少。
缓方是让疾病慢慢消失,而不用迅速达到药效,主要用来治疗慢性虚弱症状;急方就是治疗急病重病的药方,通常用汤剂,药性强,气味雄厚。
奇方的“奇”是奇偶数的奇,所用的中药数量是单数的,主要用来治疗病因单纯的疾病;偶方所用的中药数量是双数的,用来治疗病因复杂的疾病;而复方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药方组成的药方,在原处方基础上加药也属于复方。
汤剂,“汤”通“荡”,用来治疗重病;丸剂,“丸”通“缓”,主要治疗慢性病;散剂,主要治疗急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