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 古城
今天谈论梁思成保卫北京古城,谈得最多的是故都的牌楼和城墙。其实,牌楼、城墙的保卫,不过是那场“大战役”中的“小战斗”,或者说是“大战役”失败后对“小战场”无奈的坚守。这场保卫古城的“战役”,林徽因健康很差,往往由梁思成挺身,阵地上从来都不是梁思成一个人的身影,始终有林徽因并肩。而一旦林徽因到场,她的鲜明态度,加之犀利言辞,比丈夫更显锋芒,总给人以难忘印象——可惜她病得难出家门,出现战役一线场合的时候有限。
有人把城市比作容器,那么不能什么都往里乱塞。欧洲便有过太多乱塞的教训。十九世纪初期,工业无序发展,古老城堡里掺杂进众多工厂,街道两旁商业大楼林立,极具价值的历史古迹被割得支离破碎。工厂、商厦的急剧增多,又造成人口密集、区域紊乱、交通困难的弊端。于是,伦敦不得不用五十年的时间和难以数计的人力、物力来纠正犯下的错误。
梁思成、林徽因非常担心中国重蹈欧洲覆辙。北京古城的建设,历朝历代都有规划,内含理念和审美,是整体保存下来的,布局妥当的有机的古迹群体,雄伟、壮丽。一旦破坏它的格局,造成的将是有甚伦敦的难以弥补的损失。林徽因和梁思成合作撰写了《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新观察》杂志发表此文仅署名梁思成一人)详尽地说明了古都的非凡:
大略的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的布局中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这全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和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对立的大街,到达珠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着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百余公尺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过了此点,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民国初年已拆除)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大胆的空间处理,衬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这个当时曾经为封建帝王据为己有的禁地,今天是多么恰当的回到人民手里,成为人民自己的广场!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峋峙,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削,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的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群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地,也恰到好处地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
如此精心布局的古都,其价值当然远非欧洲任何一座古城所能攀比,梁思成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得十分动情:“那么单纯壮丽,饱含我民族在技术及艺术上的特质,只要明白这点,绝没有一个人舍得或敢去剧烈地改变它原来的面目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然而,书生的梁思成哪里想到,对于“那么单纯壮丽,饱含我民族在技术及艺术上的特质”的建筑,就是有人舍得,也有胆量,更有足够的力量去损害它!而且不久,这损害即成为铁的事实!
随意乱盖还只是局部问题,不惜整体改变古都的人是中央政府请来的苏联专家团,专家团提出一份《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一位专家说:“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苏联专家想按照莫斯科红场的模式,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改建北京,建设一个中国版的莫斯科。这位苏联专家倒不像梁思成那么“书生气”,不会对古都有那么天然的感情。他依仗“老大哥”的特殊身份,斩钉截铁地断言,他们的建议,“这是任何计划家没有理由来变更也不会变更的。”(巴兰尼克夫:《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转见窦忠如:《梁思成传》,本节多参考此著)梁思成竟然当场反对。年轻而学术前景大可期待的陈占祥,态度鲜明地支持梁思成意见。
梁思成、陈占祥与苏联专家分歧的焦点之一在于,中央行政中心设计在城内还是迁往西郊。会后,梁、林夫妇和陈占祥充分准备了数月,写了两万五千言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于一九五〇年二月上呈党中央。这份建议由梁思成和陈占祥联合署名,即俗称的“梁陈方案”。“方案”构划了一个以行政中心外迁、建设与旧城相连的新市区的“大北京市”理想。梁思成自费印制一百多份,分头报送各部门相关首长。他真诚地希望,中国的当政要员能够“从谏”,尽管不可能那么“如流”。然而,任凭他振振有辞:“我们这一代对于祖先和子孙都负有保护文物建筑之本身及其环境的责任,不容躲避。”要员们却置若罔闻。两个月后,梁思成再以个人名义上书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希望赶快定下方针。他要求和总理面谈:“不忖冒昧,作此请求,如蒙召谈,请指定时间,当即趋谒。”信尾特附明家里电话号码。梁思成所以如此急切,看到不少单位已经随意在各处建房建楼,北京古城面貌显现出凌乱的端倪。林徽因急得说:“现在这样没秩序地盖楼房,捂都捂不住!将来麻烦就大了!要赶紧规划!”(见杨秋华《怀念林徽因先生》)而另一方面,严守规章的单位请示建房地址,迟迟不见批复下来,许多单位部门的工作大受影响。
总理没有召见梁思成。“梁陈方案”遭到一些人的指责,最厉害者给梁思成扣上政治帽子,说他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当别人将技术性的分歧意见上纲上线到政治层面,梁思成还全然蒙在鼓里,正埋头于规划天安门周边的方案。他考虑,万一(不存在的万一)“建议”不被接纳,作为专家干部,他应该服从领导,但应该及时拿出一道后备方案。
梁思成慢慢才意识到,他已经丧失了参与故都规划、设计的资格,纵然他是权威的建筑学家,并且是政府任命的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这位技术领导被架空了,政府已先行指定别人规划了两个方案,苏联专家作方案顾问,另行成立了规划小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中提及:“为了在讨论与研究过程中避免引起一些无谓的争论,我们又指定了几个老干部,抽调少数党员青年技术干部,在党内研究这个问题。”梁思成不属党内。同样不在共产党内的陈占祥比他惨烈得多,一九五七年被打为“右派”列入另册。
苏联专家、老干部、党员青年技术干部一起研究出来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其务虚的文字,在泛泛肯定古都价值后着重指出:故都原来的建设,“反映了封建时代低下的生产力和封建的社会制度的局限性。它是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当初建设的方针完全是服务于封建统治者的意旨的。它的重要建筑物是皇宫和寺庙,而以皇宫为中心,外加上一层层的城墙,这充分表现了封建帝王唯我独尊和维护封建统治、防御农民‘造反’的思想。”二三十年前宾夕法尼亚的大学生林徽因,声讨西方建筑模式对中国民族建筑的破坏:“我们悲伤地看到,我们的土生土长的特有的本色的艺术正在被那种‘与世界同步’的粗暴狂热所剥夺。”(见王贵祥《林徽因先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现在,剥夺它的是曾引以为荣的炎黄子孙,是学习不算西方的西方苏联老大哥。
这份《要点》还说:这些遗迹,“对它们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显然是不对的;同时对古建筑采取一概保留,甚至使古建筑束缚我们的发展的观点和做法也是极其错误的”。前者仅“不对”而已,后者则是“极其错误”,孰轻孰重,判若分明。唯恐分明得不够,“要点”再追加上一句,“目前的主要倾向是后者”。(上引均转见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行程纪略》)
《要点》上报了中央,北京市委在附属的报告中透露,《要点》形成过程中,“批判了‘废弃旧城基础,另在西郊建设新北京’以及‘北京不能盖高楼’等错误思想”。显然指批判了梁思成一流专家的思想,梁、林的一场故都保卫战以夫妇彻底失败告终。林徽因只知道失败,并很不清楚批判内情,她痴痴地长长地长叹一声:“我们的党太不懂建筑!”她哪里明白,这岂止是建筑问题。确定的规划宗旨非常明确:“在制定首都发展的计划时,必须首先考虑发展工业的计划,并从城市建设方面给工业的建设提供各项便利条件。”(《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为了工业发展,牺牲不能发展的古城,拆除城墙、牌楼,乃势所必然。另一面,梁思成等人,退守保卫城墙、牌楼,同样是必然的。如果说建议开拓新城区、保卫故都还有点主动出击的意思,那么保卫城墙、牌楼,完全败退下来的悲壮守卫。
早在一九五〇年,梁思成已经发表过城墙不可拆毁的意见,并写成文章《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刊《新建设》杂志第二卷第六期)。爱护城墙绝非梁思成等少数建筑史专家嗜古成癖,在一次北京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已有一些代表注意到,城墙上面积宽敞,可以布置栽种花草,设置鱼池,安放椅座,或远或近的地方还可建些凉亭。人们伫立城头,近可俯视护城河,碧水粼粼,远可眺望郊外平畴和尽头的西山。这正是梁思成赞叹的:“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公园之一——一个全长达三十九点七五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
决策者不许别人再讨论,某位负责人在会上狠狠地警告大家:“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员就开除他的党籍!”梁思成此时尚未入党,无籍可除,但是他还能说什么呢?要说只能说给林徽因听:“拆掉一座城楼就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就像剥去我一层皮。”你的肉和皮,在伟大的工业化进军面前算得了什么!仅仅为了利用城墙这一带之地,开动了一两个野战军人数,排山倒海似的上阵,放炮,挖砖,肩挑,车推。红旗飘扬,灰雾蔽天。梁思成、林徽因没住在皇城根下的北总布胡同,没有目睹城墙毁灭。然而,即使他俩远住郊外的清华园,有泪不肯轻弹的男子,依然禁不住潸然泪下。
实在忍无可忍,夫妇二人也有挺身而出的时候。某负责人说,天安门前两侧的东三座门、西三座门影响了节日游行检阅——军旗过门不得不“低头”;眼巴巴想瞻仰人民领袖的人民,卡在门外不能早一刻如愿;还说,三座门还有解放前的罪恶。一个小型讨论会上,梁思成、林徽因据理力争,会议上午开到下午,下午开到晚上,梁思成三次发言,舌战二三十位反对者,林徽因嘤嘤啜泣。市长过来安慰,你们爱护文物爱护建筑艺术的精神值得钦佩。上级主意早已内定,东西三座门非拆不可。拆除工程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一个会议程序。北京各界人民代表公议那天,林徽因凛然出场,她代表梁思成参加。会场设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没有固定椅座,临时拖来的椅子,排座时让开一条过道。机敏的林徽因,一上台就抓住眼前这过道做文章:椅子为什么让开过道来摆?还不是为了交通方便!如果说北京从明代遗留下的城墙妨碍交通,多开几个城门不就解决了?与会人员并不弱智,听了林徽因声辩,原本准备举手同意拆除的代表,情绪起了波动,不免犹豫是否还举手附和。此刻,林徽因哪里是个抱病的柔弱女子,她是英雄!市长见势,立即召集会场里的党员代表临时急召党员会,规定他们服从市委决定。党员占了代表中的多数,拆除三座门就这样通过了,林徽因又做了失败的英雄。失败而悲壮,这位英雄隐隐感到,从此声势浩大的古都建筑撤除风暴将席卷而来。
将有更多的失败等着她和梁思成,这对夫妇屡战屡败之后仍屡败屡战。北京拆过城墙准备再拆牌楼,主张并主持拆牌楼的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这位市长精通明史,牌楼的文物价值他比一般文化人应该明白得多。然而吴副市长拆牌楼态度异常坚决,尽管保护牌楼的队伍里有他的老师并顶着国家文物局长“乌纱”的郑振铎先生。北京数百座牌楼,遍布于全城各处,拆起来动静不小,反对的呼声也高,郑振铎、张奚若、翦伯赞都是著名的反对派。市政府一连开了几次座谈会,双方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无果而散。拆牌楼的理由依旧是妨碍交通,策略依旧是借群众压专家。他们甚至找来人力车夫,用车祸诉说牌楼之害,声泪俱下。吴晗满口官腔说:“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以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
梁思成再次上书中央领导人。上书中央是他常用却屡不见效的一柄纸剑,可是除此,他还能有什么武器?信中列举有些颇具文物价值的牌楼,“所在的一段大街,既不拐弯,也不抹角,中间一间净宽六点二米,足够两辆大卡车相对以市区内一般的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通过,不必互相躲闪,绝对不需要减低速度;若在路面上画一条白线,则更保绝对安全。两旁的两间各净宽五点一五米,给慢行车通过是没有问题的”。周恩来终于出面找梁思成做思想工作,不知内里情由的梁思成,颇动情感地对总理赞叹,夕阳余晖照射在帝王庙牌楼时,有一种极富民族文化传统的古诗般的意境。总理无奈地答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林徽因情绪比丈夫更为激烈,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招待建筑专家吃饭,她指着临席的吴晗斥责:“你们把真古董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不久在吴晗主持的座谈会上,林徽因又作了一次长篇发言,就文物保护与建设的关系、文物建筑保护不只限于宫殿庙宇、古建筑文物的整体性和它的环境保护等等问题,多方面阐释自己的看法。她说得很全、很透、很动感情。
挽救牌坊的努力毫不见效,梁思成痛心疾首。毛泽东听说梁思成为城墙、牌楼落泪,斥之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他见到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依旧坚持己见:“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果然预言得到历史验证。然而,一个事后太久才明白的对与错,于历史补救的作用是微乎其微了。今天来评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若不以成败论英雄,其护卫古城失败的光辉远在成功的国徽、纪念碑设计之上。
拆城之风兴起,妨碍交通的古亭古塔及其他古建筑均在扫荡之列。堪与紫禁城角楼媲美的大高殿习礼亭拆了,西长安街金代庆寿寺双塔也拆了,后来团城也将在劫难逃。团城是国家文物局办公用地,以保护文物为己责的局长郑振铎,无力保护自己身处其地的文物古迹,不能不说是莫大的讽刺。倒是局长的秘书罗哲文,他是梁思成从李庄带出来的徒弟,急急来找老师商量对策。梁思成已然心有余力不足了,仍病急乱投医,倒去求助苏联专家,两次拖着“老大哥”到团城来看看,希望他们支持,结果不用说的。最后的指望在总理——梁思成再去中南海求见,力陈利弊。周恩来两上团城实地勘察,最后决定中南海围墙南移,修筑的马路稍稍拐弯,让过了古迹。这几乎是他唯一的成功。
梁思成、林徽因还曾经有古城四周不宜建造高楼的主张。梁、林护卫古城是鉴于西方城市的教训,他们护城的无畏值得大书特书,而深受西方教育的这对夫妇,却不是唯西方是从,亦步亦趋。这份精神遗产殊为可贵。

1950年,林徽因与郑孝燮、周卜颐、王君莲、李宗津等在清华营建系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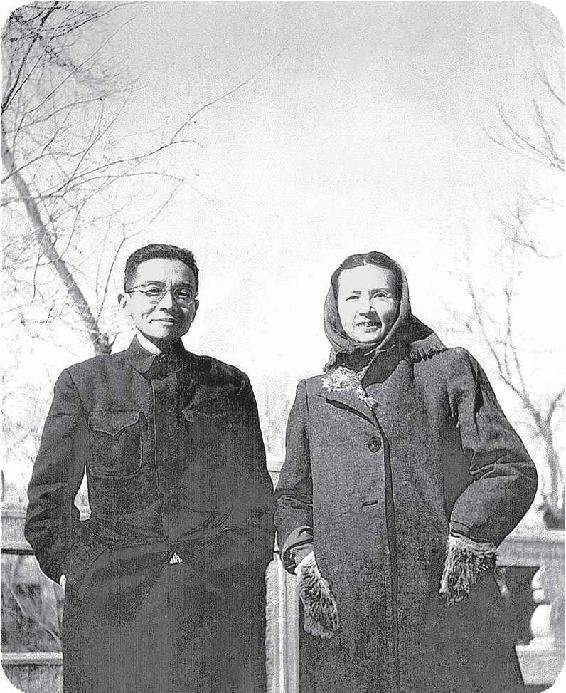
1950年代初,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清华大学新林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