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白的画布
随着年龄日渐增大,塞尚的绘画作品越来越爱留白。他有一幅这样的作品叫《非限定形式》(nonfinito),这是一幅看上去未经完成的画作,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作品显然没有完成,怎么能算得上是艺术品呢?可是塞尚在面对人们的评论时却表现得泰然自若。他知道自己的作品只是表面上留有空白罢了。[6]不完整性其实只是对视觉过程的一个隐喻。在这一未完成的画布上,塞尚为观赏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设法为之找到了可以用大脑完善艺术作品的方法。于是,他的模糊性变得尤为慎重,含糊也是基于精准性的。如果塞尚想让我们填补他艺术作品中的空白,那么必须要让这些留白恰如其分。
让我们来看看塞尚《圣维克多山》(Mont Sainte-Victoire)这幅作品。在晚年,塞尚每天清晨都要散步到雷罗威小镇(Les Lauves)的山顶。在那里,普罗旺斯平原广阔的景色会在他的眼前铺展开来。他会在一棵酸橙树的阴凉下作画。塞尚说,从那里他能看到大地隐藏的图式,看到河流与葡萄园交叠地排布在一起。背景永远是群山,嶙峋而等边形的岩石似乎将干旱的土地与无限的天空连在了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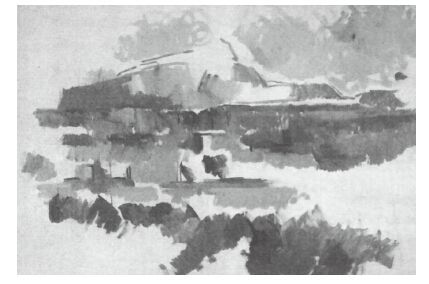
塞尚在雷罗威小镇望到的圣维克多山,作于1904—1905年
当然,塞尚的醉翁之意并不在于对风景的如实描摹。在他对山谷的描绘中,想要画的只是最基本的元素,即支撑形象所必要的骨骼。所以,他将河流简化为了一道婉转的蓝色;栗树丛成了几抹短促的亚绿色,偶尔还被巧妙地加进一笔琥珀黄。然后便是群山了,塞尚总是将冷峻的圣维克多山浓缩成几笔淡色的线条,在辽阔的天空中一扫而过。这条细细的灰线——山峰的剪影,完全被周围的空间所环绕。它是广阔无垠虚空中的一道脆弱的痕迹。
然而群山并没有消失,它就在那里,是一种坚定而固执的显现。观赏者的大脑可以轻而易举地创造出由颜料轻描淡写出的形象。尽管山峰从表面上几乎看不见——塞尚只是暗示了它的存在,可它隐约的重量却为整幅画找到了支点。我们不能确定画家的画笔停在了哪里,而我们又该从哪里开始。
塞尚对空白画布的欣然接受——他决意让留白展示一切,是他最关键的创造。学院派风格推崇画作的清晰感和细致的纹理;而塞尚后现代派绘画则注重描绘对象的含糊性。在对事物有与无的精心混淆下,塞尚《非限定形式》这幅作品质疑了形式的本质。他那不完整的风景画是一个证明。它证实了,即使没有感受——画布是空白的,但我们还是能够看得见。群山也还在那里。
在塞尚开始对空白画布做研究时,科学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画作会比它们实际的样子更显充实。塞尚《非限定形式》这幅作品的存在——大脑能够在一片空白中找到意义的这个事实,似乎提出的都是反证。这些反证让任何将视觉简化成光像素的心智理论都显得站不住脚。
形式的幻觉是塞尚早已驾轻就熟的问题,但20世纪早期的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家们却是面临这一问题的首批科学家。格式塔的字面意思是“形式”,这也正是格式塔心理学家们所感兴趣的问题。卡尔·斯顿夫(Carl Stumpf)、库尔特·考夫卡(Kurt Koffka)、沃尔夫冈·柯勒(Wolfgang Kohler)、马科斯·韦特墨(Max Wertheimer)在20世纪初建立了德国形式主义,反对当时的简化主义心理学是这场运动的起点。简化主义心理学当时还崇拜着威廉·冯特和追随他的心理学家的理论。冯特曾辩论说,视觉最终可以被简化成几样最基本的感觉。就像镜子一样,大脑也能够反射光。
然而,大脑并不是镜子。格式塔主义者试图证明视觉过程会改变我们所观察到的世界。就像他们的哲学先驱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所认为的,“许多我们本以为会存在于那里——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感觉,实际上都来自这里,从大脑内部中来”。(康德写道:“想象是感知能力本身必要的原材料之一。”)格式塔主义者把对光的幻觉用作了感知理论的证据。这些幻觉从电影中明显的动态(电影实际上是一组每秒钟翻动24次的静态照片),到在两种不同形象间转换的图画(经典案例就是可以被看成两边是人脸剪影的花瓶)不等。按照格式塔主义者的说法,这些日常的幻觉就足以证明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一场幻觉。关于形象的指令是自上而下下达的,冯特的追随者们总是从感觉的碎片处着眼,而格式塔主义者们则与之不尽相同,他们的大前提是把我们实际感觉到的经历作为现实。
关于视觉皮层的现代神经学研究确认了塞尚和格式塔主义者的直觉判断——视觉经历是超越视觉感受的。塞尚的群山能够从空白的画布上平地而起是因为大脑执着地要从这幅绘画作品中探个究竟,从而填补画作的细节。这是一个必要的本能。如果大脑没有对眼睛施加严格的控制,那么视觉就会漏洞百出。举个例子,因为没有将感光神经连接到视网膜的感光视锥细胞,我们每个人的视野中心事实上都有一个真正的盲点。虽然我们对这一盲点视若无睹,但大脑也还是能够记录这个天衣无缝的世界。
这种整合我们不完整感觉的能力是人类大脑皮质构造的产物。视觉皮层被划分为几大块区域,从1至5整齐划分。V1脑区是视网膜信息第一次作为线条集合显现的地方,如果从V1脑区到V5脑区一直寻找光的回波,你就能够看到视觉场景是如何获得无意识创造力的。在主观性吞噬掉那些不完整画面的原始感受之前,现实总是在不断地被雕琢完善。
在视觉皮层中,神经细胞对幻觉和实际感觉这两种意象作出反应的第一块区域就是V2脑区。在这里,大脑开始改变视觉过程。于是,当仅有一条细细的黑线时,我们也能够看见群山。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不能够把自己精神上的造物与真正存在的事物分离开来。在我们实际看到一座山和想象一座山时,是相同的神经细胞在参与着反应。所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完美的视角。
在视觉皮层的其他区域快速处理完数据后,色彩和动态便被整合到了画面中。数据流入了内侧颞叶(medial temporal lobe,也被称为V5脑区),这是大脑中产生意识观念的区域。在靠近头部后侧的这个区域里,小的脑细胞的子集会最先回应复杂的刺激,比如塞尚的一幅画着山峰的作品或一座真正的山峰。当这些特定的神经细胞亮起来时,所有的视觉处理过程就都已经结束了。此刻,意识所需要的感知也都备齐了。
因为颞叶皮层中的神经细胞在再现形象时都非常特定,所以一丁点儿脑损伤都会擦除形象的整个体系,这种综合征叫作“视觉物体失认症”(visual-object agnosia)。某些患有这种综合征的患者可能会识别不了苹果、人脸或后现代派绘画。即使患者还能够意识到物体所具有的各种元素,但还是不能将这些碎片连成一个完整而有序的实物影像。关键是,形象世界只存在于神经反应过程的后期,存在于远离外部世界光照的头部内的大脑沟回的褶皱中。
另外,对意识神经的补充本身就会受到意识的影响。一旦前额皮层觉得它看到了一座山,就会开始调整自己的输入信息,直到在空白的画布上想象出一个形象为止。这也解释了保罗·西蒙(Paul Simon)的一句话,“一个人会看见他想要看的东西,而置其他于不顾”。事实上,在外侧膝状体(lateral geniculate nucleus,LGN)中,粗神经将眼球与大脑连接起来,从皮层投射到眼部的神经纤维要比从眼部投射到皮层的多10倍。这就是我们让自己的眼睛说谎的原因。正如威廉·詹姆斯在《实用主义》(Pragmatism)中所写的,“‘感觉’更像是一位把自己的案子交给律师的客户,然后只能在法庭上被动地聆听律师为他所提供的权宜之计”。
所有这些分析的意义是什么呢?大脑不是照相机。正如塞尚所理解的,观察就是想象的过程。可是问题是,根本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量化我们觉得自己看到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被锁在自己特定的视野中了。如果我们把自我意识从世界中移除,如果我们的眼球以一种公正的态度去审视的话,那么我们只能看到闪现在无形空间中的几点光,不会有群山,画布也会空空如也。
塞尚引领的后印象派运动是把我们不诚实的主观性作为艺术主题的第一风格。他的画是对绘画作品的批评——这些画的非现实性会引发人们的注意和深思。从塞尚的画中可以看出,风景是由空白空间所构成的,水果拼盘是笔触的集合。为了迎合画布,一切都经过了调整:三维被压缩成了二维,光线被换成了颜料,整个情景都是虚构的。塞尚提醒我们:艺术四周布满了诡计和欺骗。
让人震惊的事实是,视觉本身就像艺术。我们看见的并不是真的。经过改造后的景致只是符合了我们“画布”的要求——大脑的要求。当睁开双眼时,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幻觉的世界,这是一个被视网膜打破而又经过皮层重新组合的世界。正如画家阐释画面一般,我们同样阐释着自己的感觉。但是无论我们神经的地图变得多么精细,也永远解释不了我们真正看到了什么,因为每个人看到的景致都不同。视觉经验会超越视网膜的成像以及视觉皮层中破碎的线条。
我们通过艺术途径表达自己内心的所见之物,而不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如此看来,离现实最近的便是绘画了。绘画会让我们最贴近所经历过的事物。当盯着塞尚的苹果时,我们其实就在他的大脑中。通过设法再现自己的精神图景,塞尚展示了艺术是如何超越现实主义艺术的神话的。正如赖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所写的,“塞尚让水果变得如此真实,以至于它们都没法吃了。它们变得如此物体化、真实化,倔强地存在于那里,不容销毁”。苹果的形象就这样永恒了—— 一幅由大脑创造出的绘画作品,一幅抽象得绝对真实了的图景。
[1] 伍尔夫在这里同时也暗指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同年发表了《数学哲学导论》。罗素的这部“逻辑史诗”激起了一场唇枪舌战,对现实是否能够被拆分成逻辑基础问题,人们各执己见。详见安妮·班菲尔德(Anne Banfield)所著的《幽灵的席位》(The Phantom Table)一书。
[2] 印象派画家在风格上的创新同时也仰仗了当时颜料制作技术的新发展。例如,莫奈常用于画海洋和天空的钴紫色仅是在他创作绘画的几年前被工业化学家发明出来的。莫奈很快就意识到,这种新型颜料具有描绘光影效果的巨大潜力。莫奈称:“我终于发现大气的颜色原来是紫罗兰色了。”
[3] 对我们视觉皮层前期部分的刺激来自与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的绘画极为相似的视觉输入。蒙德里安是受塞尚影响极为深远的一位画家,他花了一生的时间寻找被称为“关于形态的永恒真理”的东西。他最终让艺术的本质扎根于直线上。至少从V1脑区的角度来看,他是正确的。
[4] 波西米亚式生活,追求自由的波西米亚人在浪迹天涯的旅途中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哲学。这种生活方式崇尚自由,豪放不羁,十分颓废。在法国人的眼中,波西米亚人会让他们联想到四处漂泊的吉普赛人,他们独立于传统,还十分不讲卫生。——编者注
[5] 迭哥·委拉斯贵兹,17世纪西班牙最具影响力的现实主义画家。——编者注
[6] 正如格特鲁德·斯泰因对塞尚的一幅风景画的评论:“完成的或是未完成的,看上去总是蕴含着油画的精魂,因为一切尽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