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的分裂思绪
伍尔夫的写作风格深深扎根于她对自己大脑的亲身感受中——她不幸患上了精神疾病。伍尔夫一生都在忍受周期性的神经崩溃,那些可怕的情绪低落的时刻,几乎让她窒息。于是,伍尔夫是处在对自己大脑的恐惧中度日的,对自己激烈的大脑“振动”极为敏感。内省是她唯一的解药。“我对自己的心理很感兴趣,”她在日记中写道,“我致力于将自己跌宕起伏情绪的隐私全部记载下来。这样它们就被对象化了,也立刻减弱了它们带来的疼痛与羞愧。”当其他一切东西都失效时,她会用充满讥讽的幽默来麻痹痛苦:“我觉得我的大脑,就像一个梨子,要看它有没有成熟;9月会是最妙的时节。”一方面,她向福斯特(E.M. Foster)和其他人抱怨她的医生和他们开的糖浆,抱怨被迫躺在床上的痛苦和昏迷的感觉;而另一方面,她又承认这个病带给了她奇特的便利。她无法医治的狂乱——这“回旋着无数翅膀的大脑”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又奇异地给她带来了超验的感受。她说:“从疯狂和所有其他感觉中,我并不是片叶不沾身、与它们毫无瓜葛。其实,我怀疑它们在我身上起到了与某种宗教体验相似的作用。”[1]
伍尔夫从未从病痛中恢复过来。她持久反省的状态,对低落情绪再次来袭迹象的警觉让她的文字充满了惊恐。“神经”是她最喜欢的词语。这个词语在医学术语上的那些变式——神经症、神经衰弱、神经崩溃、神经衰弱官能症等一直都倾注在她的文章中,它们尖锐的科学意义上的痛苦与她所具有流畅灵活的内心独白相矛盾。在日记中,伍尔夫对近况的记载总是与对头痛的评论交织在一起。
但是疾病也给予了她的实验性小说一种目的,给了她“将经历寄存到适合它的形式中”的一种方式。在每一个消沉阶段之后,她都会在日记中填满对自己“晦涩难懂的神经系统”的一些新见解,会分外强烈地感觉到一阵创造力的喷涌。当医生们强制她卧床养病的时候,她会盯着天花板,思考关于自己大脑的问题来度过这些时光。她决定让自己不仅仅活在“单纯的一种状态中”。她发现:“生病真的很古怪,一个人会忽然分裂成好几个不同的人。”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瞬间里,她都是既疯狂又透彻、既疯癫又精辟的混合体。
伍尔夫从她所患的疾病中了解大脑,了解它的变幻莫测、它的多重性以及它“将格格不入的事物古怪地聚集起来”的能力。她把这些收获都转化成了一种文学技巧。她的小说写的是了解人是多么困难的,写的是“下定论说他们是这样或那样的”是多么困难的。“下关于人的结论是没有用的。”她在《雅各布的房间》(Jacob’s Room)中这样写道。尽管自我仿佛已经很确定,但伍尔夫的文字却揭露了一个事实,我们实际上是由不断变化的印象所书写而成的,凝聚这些印象的正是名为“身份”的那一单薄的外衣。正如在《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一书高潮段落中自杀的那个先知般的疯子赛普蒂默斯(Septimus)一样,我们活在一种分崩离析的危险之中。我们为什么能够在这危险中存活下来的奥秘才是她的艺术张力如此活跃的根源。
1922年,伍尔夫在日记中写道:“40岁时,我开始了解大脑的运转机制。”同一年,伍尔夫开始创作《达洛维夫人》这部小说,这是她针对《尤利西斯》一书在文学上的回应。同乔伊斯一样,她将这部小说的场景设置在了熙熙攘攘城市的一个周末。小说的主人公克拉丽莎·达洛维(Clarissa Dalloway)既不是什么英雄人物也不是什么悲剧人物,而仅仅是“那些必须被记录下来的无名生命”之一。伍尔夫喜欢提醒自己说:“我们不要自以为是地认为,比起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微小的事物,生命总是更多地存在于人们觉得更为重大的事件中。”
小说以达洛维夫人亲自去买花开篇。6月的时节里总会充盈着诸多此类差事,可是伍尔夫却总能够让日常事件展露出其深层的含义。“这就是我们活过的生活,”她说,“我们的领悟离不开日常琐事,写下的诗篇与平凡生活交织在了一起。经过精妙的描绘,就算是单纯的一天都有可能成为投射我们心理的一扇灵性之窗。”
伍尔夫用《达洛维夫人》展示了大脑的脆弱。赛普蒂默斯·史密斯(Septimus Smith)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后来成了一位患有极度精神异常的诗人。伍尔夫将克拉丽莎的派对与塞普蒂默斯·史密斯的自杀编织在了一起。暗中作恶的医生布拉德肖(Bradshaw)试图通过强制运用“均衡”养生法治疗他的疯癫,结果这药却把一切搞得更糟。布拉德肖坚持认为赛普蒂默斯的疾病是“器质性的,纯粹器质性的”,这导致了诗人的自杀。他的自我崩溃了,再也无法重新凝聚起来。
在派对上,听说了赛普蒂默斯自杀消息的克拉丽莎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尽管她从来没有见过赛普蒂默斯,但克拉丽莎却觉得“自己的感觉和他很相似”。与赛普蒂默斯一样,她知道自我不稳定得可怕,并缺少“模糊状态中的某种向心力”。当布拉德肖医生出现在她的派对上时,她怀疑他“犯下了一桩无法用语言描绘的暴行——逼迫你的灵魂,就是这样”。
但是他们平行的生活就是从这里结束的。不像赛普蒂默斯那样,克拉丽莎在零星的存在中也能够得到些许安慰。克拉丽莎是一位持有怀疑主义的无神论者。尽管她并不相信会有什么不朽的灵魂,但还是为“我们生命中无形的那部分”总结出了一套“超验理论”。像布拉德肖那样的医生会否定自我,但是克拉丽莎不会。她知道,自己的大脑包含着一个“看不见的中心”。随着小说的铺展,这个中心开始逐渐显现:“那就是她的自我。”凝视着镜中的自己,克拉丽莎想道。“脸儿尖尖、像只飞镖、清楚明确。那就是她自己——当某种努力、某种要求她做自己的召唤把她的各个部分聚拢在一起时,只有她自己才知道这完整是有多么不同,多么不协调。她只是为了外部世界才这样把自己组合成了一个中心、一颗钻石、一位坐在客厅里的女人……”关键是,达洛维夫人的确让自己完整起来了。是她让自己真实起来,创造了一个“无论走到何处都属于自己的世界”。这就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们拾起思绪的片段和断断续续的感受,将它们捆绑成某种坚实之物。可见,是自我创造了它自身。小说的最后一句话证实了达洛维夫人单薄的身影是毋庸置疑地存在着的——“她就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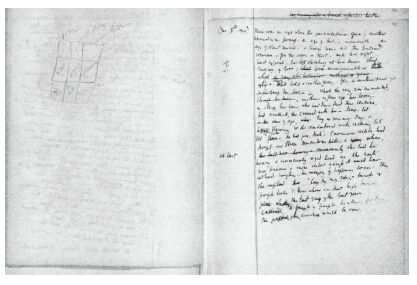
伍尔夫在写《达洛维夫人》时所记的日记(1925年)
伍尔夫接下来的一本小说《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是挺进动荡大脑更深处的冒险。伍尔夫曾说,写这本书是她与精神分析最为亲密的一次接触。历经了疾病缠身的长长夏日,文字仿若慷慨激昂的告白,从她的胸中漫溢而出。小说本身并没有包含多少情节。到灯塔去的计划本来马上就可以实现,可是在经过了晚饭后的又一段时间后,去往灯塔的旅行才成了现实。接下来,画家莉莉(Lily)画完了她的作品。尽管小说中的事件看起来很贫乏,但它却好似暴风骤雨,到处都充溢着川流不息的浓烈思绪。叙述一直被思绪打断,被对思绪的反思打断,被关于现实的思考打断。有些人说出了一个事实(在大脑中或大声说出),之后又马上出现了矛盾。同一个大脑常常在自相矛盾着。
据伍尔夫说,这种精神紊乱是对我们精神现实极其精确的描述。自我是从意识的混沌中产生的,是用“颤抖的碎片拼成的整体”。她的文章《现代小说》(Modern Fiction)是对自己现代主义理想最有力的陈述。在这篇文章中,伍尔夫用心理学术语定义了自己新的文学风格。伍尔夫写道:“大脑会接受千千万万个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就好像沐浴在无数原子无休止流淌的瀑布之下;当它们落下时,自然地堆砌成了星期一、星期二等诸如此类的生活。让我们(现代主义小说家)按照这些原子落在大脑中的顺序将它们记录下来,让我们追踪那些隐现的式样——不管表面上看上去是多么不相干,也要让每一个画面、每一个事件都进入意识之中。”
《到灯塔去》充满了这种会无休止出现的思绪。小说中的人物对周边世界怀揣着转瞬即逝的印象和不完整的感觉,全书重点描写的那位母亲拉姆齐夫人(Mrs. Ramsay)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当她想到丈夫时,那位正在写哲学《百科全书》的哲学家正瞪着字母“Q”的位置犯着难呢,他的思绪四处游移着。拉姆齐先生以“气压表陡降,西风吹得紧”为理由,刚刚拒绝了儿子詹姆斯(James)到灯塔去的要求,而拉姆齐夫人却觉得她丈夫太不讲理了:“在追求所谓真理时一点儿都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如此放肆粗鲁地扯下了文明的外衣,而这类举止是对人类体面的一种可怕的亵渎。”但是后来,在紧接着的下一句话中,拉姆齐夫人的感觉却截然相反了:“没有人能比她更崇拜自己的丈夫了……她只不过是一只充满了人类情感的海绵。她连当他的鞋带儿都不够格。”
对于伍尔夫来说,拉姆齐夫人缺乏连贯性的思绪正是对现实的忠实反映。通过把我们与小说人物纷杂多变的大脑相融合的这一途径,伍尔夫显现出了人类自我的脆弱。自我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我们的意识流就流动在其中。在任何特定的时刻,我们都不免处于心血来潮之中,而且搞不清为何自己会处于这不可抗拒的感受之中。拉姆齐先生认为:“想法就像琴键……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而拉姆齐夫人却知道,大脑总是“连接、流动、生成”,就像赫布里底群岛(Herbrides)的天气一样,变化才是常态。
伍尔夫的文字从来不会让我们忘记自身存在于风雨飘摇状态中的事实。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这本书中好奇地问道:“当一个人说‘思想的统一’时,是什么意思呢?……它(大脑)似乎从来不会在一种单一的状态中运行。”她想让读者意识到“大脑中的隔离和对立”以及意识会“突然出现分歧”的状态。伍尔夫写道,至少人们必须意识到“人类无限困窘的境况”。尽管自我在感觉上似乎是连续的——“如同永恒那般坚不可摧”,但其实它只会存在一瞬间。我们“就像波浪上的云朵一样”穿行在这无穷尽的思绪之中。
想象出这种易变的大脑以及一种与自身分裂开来的自我是现代主义的核心信条之一。“我的推测就是主观的多重性。”尼采曾对自己的哲学这样概括道。“‘我’只是又一个人罢了。”阿尔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不久后也写道。在《心理学原理》一书中,威廉·詹姆斯将涉及自我的那一章节的大部分笔墨都用在了写“自我的突变”上,那是我们意识到自己“同时存在的另一种意识”的时刻。弗洛伊德同意这种观点,他将大脑看成了一张有着矛盾张力的网络。T.S.艾略特将这种观念转化成了一种文学理论,断绝了自我与“灵魂实际上是统一体这一形而上学理论”的关系。他相信现代诗人必须要抛弃表达“和谐统一的灵魂”的这一想法,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灵魂。“诗人并不具有一个可供表达的‘人格’,”艾略特写道,“他具有的只是一种媒介,仅仅是媒介——而不是人格。”像许多现代主义者一样,艾略特想要刺破我们的幻觉,展现给我们实际的样子,而不是我们想要的样子,或者说只是存在的瓦砾和一些随意的感觉碎片。伍尔夫呼应了艾略特的观念,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只是“裂片和马赛克”,并不像它们曾经那样,是完美无瑕、坚如磐石、完整如一的整体。
虽然这一观念看上去很超现实,但现代主义者对大脑的见解却是正确的。一项又一项的实验表明,任何经历都能在短期记忆中留存10秒钟。之后,大脑便用光了“现在时”的容量,意识就必须要重新从一个新的流动开始了。正如现代主义者期待的那样,看上去持久不变的自我实际上是以散乱瞬间为单位的一场无穷尽的游行。
大脑中若是缺少了任何一个单个元素的位置,就会使人产生困惑,比如说缺少了像“笛卡儿剧院”这类元素的位置,我们就不可能在激奋时刻里舒缓自我的节奏了。(格特鲁德·斯泰因对奥克兰这个城市所做的评论同样适用于大脑皮质:“那里并没有任何东西。”)相反,大脑聚集了疲于吵闹的细胞议会组织,将无休止地处于争论状态中的那些感觉和思绪转化成了意识。这些神经细胞分布于整个大脑,随着时间的流逝生生灭灭。这意味着大脑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位置,而是一个存在的过程。正如影响颇广的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所写的,我们的大脑由“多重渠道组成,在其中,特殊的回路群情沸腾,设法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运行的同时生成多重草稿”。因此,那些被我们称为现实的东西也只不过是终稿而已。(当然,下一个瞬间就需要勾勒出一个完整的新草稿了。)
可以证明思维拥有这种散播性质的直接证据源于大脑的形状。尽管被头盖骨包裹着,但大脑其实是由两个独立的区块(左右半球)构成的,它们生来就不同意彼此的想法。《到灯塔去》中的画家主人公莉莉对自己的剖析是极为正确的:“这就是事物的复杂性……同时强烈地感觉到两种相反的东西:就像是我的感觉是这样,而你的感觉是那样,然后两种想法彼此争斗,就像现在这样。”就像莉莉观察到的,每一个大脑都充斥着至少两种不同的想法。
当1962年神经学家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和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第一次陈述这种观念时,迎来的只是人们劈头盖脸的嘲弄和怀疑。[2]对于脑损伤患者的研究让他们下结论说,大脑的左半球是有意识的那部分——它才是我们灵魂的宝座,是集结起一切的地方。而大脑的另一半,也就是右半球,仅仅被认为是某种附属物。在1981年的诺贝尔演讲中,斯佩里做了大概的陈述:右半球不只是“寂静一片、没有图像,而且患有阅读障碍症和失用症、对词语一窍不通,一贯缺乏更高的认知能力”。这来源于他刚刚从事此类研究时所形成的一系列观念,这在当时是大脑右半球方面很盛行的理论。
斯佩里和加扎尼加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检验了受到胼胝体损伤的割裂脑(split-brain)患者(胼胝体是连接左右脑稀薄神经组织的桥梁)。神经学家们以前研究过这些患者,并且发现他们在本质上是正常的。(这些发现的结果是,通过手术切分大脑成了治疗严重癫痫症的常用方法。)这证实了神经学家们的怀疑,那就是意识只需要左半脑参与其中。
但是斯佩里和加扎尼加决定做更进一步的观察。他们研究割裂脑患者的第一步就是检验隔离状态下右脑的能力如何。让他们惊奇的是,右半球既不沉默也不愚蠢,相反,它在“抽象、概括、精神联想等方面”似乎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与所处时代的普遍信条不同,他们认为大脑的一个半球既不会主导也不会压倒另一个半球。事实上,这些患者证实了相反的情况才是正确的——每个半球都是独特的,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欲望、才能和感受。斯佩里写道:“我们迄今看到的一切都表明,手术留给了这些人两个独立的大脑,也就是说,意识属于两个孤立的半球。”
胼胝体让我们每个人都相信它是单数形式的,可是每一个“我”其实又都是复数形式的。割裂脑患者是我们具有不同大脑的鲜活例子。当胼胝体被割裂时,多重人格一下子就被释放了出来。大脑不会再压抑其内在的不一致性。一位用左脑读书的患者发现它目不识丁的右脑对书页上的文字极其厌倦,右脑也会命令他的左手将书扔出去。另一位患者用左手穿衣服,右手却不由自主地忙着把衣服脱掉。还有一位患者的左手对他的妻子很粗鲁,而右手却在左脑的指挥下对她充满了爱意。
但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感觉不到这种大脑皮质的矛盾呢?为什么自我在破碎的状态下,我们的感觉却是完整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斯佩里和加扎尼加狡猾地让不同图片组在割裂脑患者的左眼和右眼前交替闪过。例如,他们会在患者的右眼前闪过一张照有鸡爪的图片,在左眼前闪过冰雪覆盖的车道的图片。之后,他们会向患者展示更多图片,请他们选出与刚才看见的最相近的图片。这种犹疑以一种悲喜交加的方式呈现出来,割裂脑患者的两只手会指向两个不同的物体:右手会指向小鸡(与左半球看到的鸡爪相对应),而左手则会指向铲子(右脑想要把雪铲走)。当科学家们要患者解释他矛盾的反应时,患者会立刻讲出一个貌似那么回事的故事出来。“哦,鸡爪与鸡有关,你又需要一个铲子来收拾鸡粪。”他不会承认自己的大脑已经完全被迷惑了,而是将这种疑惑编造成了一个自圆其说的叙述。
斯佩里和加扎尼加对割裂脑的发现以及我们本能地将这种分裂解释通的做法对脑神经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科学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一个观念——意识从整个大脑的低语声浪中浮现出来,而不只是来自无数局部的某一处。
根据斯佩里的说法,我们对统一的感觉是一种“精神交谈”;为了忽视我们的内在矛盾,我们发明了自我。正如伍尔夫在她的文章《逛街》(Street Haunting)中产生的疑问:“我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或者真正的自我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而是某种多变而游移的东西,只有在我们顺应它的愿望,让它畅行无阻的时候,我们才会是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