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智术师及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
[286]智术师运动对人类历史发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索福克勒斯的时代见证了这场运动的开端。我们在导论中就提到了这场运动:它是 ,即教育,或者毋宁是狭义上的文化。“paideia”一词,它首次出现时的意思是“幼儿的养育”, [1] 公元前四世纪时的希腊人和罗马帝国时代的人不断地扩充这个词的含义,现在该词第一次与人可能的最高德性有了关联:它被用来表示身心两方面理想的完美状态的总和,亦即完全的kalokagathia[美善],一个现在被有意识地用来概括真正的智识和精神文化的概念。这一文化理想的综合概念,到伊索克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即教育,或者毋宁是狭义上的文化。“paideia”一词,它首次出现时的意思是“幼儿的养育”, [1] 公元前四世纪时的希腊人和罗马帝国时代的人不断地扩充这个词的含义,现在该词第一次与人可能的最高德性有了关联:它被用来表示身心两方面理想的完美状态的总和,亦即完全的kalokagathia[美善],一个现在被有意识地用来概括真正的智识和精神文化的概念。这一文化理想的综合概念,到伊索克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从一开始,德性就与教育紧密相连。 [2] 不过,随着社会的变迁,德性的理想以及达到此种理想的途径也有了变化。因此,全希腊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一个问题上:何种类型的教育通向德性? 如果没有这个问题,希腊文化的独特理想就永远不可能产生;尽管其基本方向是明确的,但要以之前的各种发展为前提——从最古老的贵族阶层的德性观念,到民主法治国家中新的公民理想的各种变化。贵族阶层不可避免地认为,德性应该以不同于赫西俄德的农夫或城邦公民的方式得到保存和传承——就后者有履行此项职能的任何特定方法而言;因为,除了斯巴达(从提尔泰奥斯时代以来,斯巴达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公民教育体系,即agogé,一种在希腊地区独步天下的教育体系),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官方形式的教育,[287]可与《奥德赛》、《神谱》和品达的诗歌所见证的旧式贵族教育相提并论;而创建一套教育体系的私人尝试进展得十分缓慢,有待时日。
实际上,与旧的贵族统治相比,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国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尽管它拥有一套自己的关于人和公民的新理想, [3] 并且相信这种理想远远好于贵族阶层的旧理想,但它没有一套正规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培养年轻人达到这种理想的方法。如果孩子子承父业,跟随父亲从事某种贸易和其他职业,父亲自然会给孩子一种职业技能和行业规则的训练;但是,这种职业和技能训练不能代替整个人的身心教育,比如贵族阶层实施的 [美善]教育,以及以一种理想——它结合了身体和灵魂两方面的最高品质——为范型的教育。 [4] 但是,城邦的公民必须尽快着手寻找一种新的教育方法,以便按照新的公民理想来教育他们的孩子。与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城市国家不得不模仿其前辈。贵族教育通过高贵的血统传承德性,新的德性自然也基于同样的原则;例如,雅典使每一个本土自由民都认为自己是阿提卡社会共同体的一员,且有资格为其效劳;这种做法只是血缘关系观念的一种延伸,只不过现在的共同体是由一个城市的成员共同组成的共同体,而不是由几个贵族家庭的成员组成的共同体。这是城市国家唯一可能的基础。尽管有一种新的对个体人格的强调,但那时,教育除了建立在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的基础之上,任何其他想法都是难以想象的。实际上,这[把教育建立在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的基础之上]是一切文化教育的最高公理,其真理性的最大证明莫过于希腊教化(paideia)的起源。希腊教化的目标是超越贵族阶层特权教育的原则;除非一个人生来就有从神圣祖先继承而来的高贵德性,贵族教育的血统原则堵塞了任何人通向德性的道路。通过运用逻辑推理,似乎很容易超越贵族阶层的血统原则,逻辑推理这种新工具的力量在不断地增强。要达到这一目标只有一种方法,即把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教育体系施加于人的心灵。应该指出的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人们对心灵的力量具有一种无限的信念,而不受品达对“学而知之者”的傲慢嘲笑的影响。 [5] [288]除非国家权力延伸到人民大众(这是不可避免的)的道路被堵塞,政治德性对高贵血统的依赖是不能被允许的;而如果新的城邦共同体用体育训练制度接管了贵族身体方面的德性,为什么就不能用一种精心建构的教育体系同样产生一种无可置疑的智识优势呢?
[美善]教育,以及以一种理想——它结合了身体和灵魂两方面的最高品质——为范型的教育。 [4] 但是,城邦的公民必须尽快着手寻找一种新的教育方法,以便按照新的公民理想来教育他们的孩子。与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城市国家不得不模仿其前辈。贵族教育通过高贵的血统传承德性,新的德性自然也基于同样的原则;例如,雅典使每一个本土自由民都认为自己是阿提卡社会共同体的一员,且有资格为其效劳;这种做法只是血缘关系观念的一种延伸,只不过现在的共同体是由一个城市的成员共同组成的共同体,而不是由几个贵族家庭的成员组成的共同体。这是城市国家唯一可能的基础。尽管有一种新的对个体人格的强调,但那时,教育除了建立在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的基础之上,任何其他想法都是难以想象的。实际上,这[把教育建立在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的基础之上]是一切文化教育的最高公理,其真理性的最大证明莫过于希腊教化(paideia)的起源。希腊教化的目标是超越贵族阶层特权教育的原则;除非一个人生来就有从神圣祖先继承而来的高贵德性,贵族教育的血统原则堵塞了任何人通向德性的道路。通过运用逻辑推理,似乎很容易超越贵族阶层的血统原则,逻辑推理这种新工具的力量在不断地增强。要达到这一目标只有一种方法,即把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教育体系施加于人的心灵。应该指出的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人们对心灵的力量具有一种无限的信念,而不受品达对“学而知之者”的傲慢嘲笑的影响。 [5] [288]除非国家权力延伸到人民大众(这是不可避免的)的道路被堵塞,政治德性对高贵血统的依赖是不能被允许的;而如果新的城邦共同体用体育训练制度接管了贵族身体方面的德性,为什么就不能用一种精心建构的教育体系同样产生一种无可置疑的智识优势呢?
因此,这场伟大的教育运动不可避免地要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而且是在前五世纪的城市开始,它使前五和前四世纪的希腊卓然独立,它还是欧洲文化观念的源头。正如希腊人自己对这场教育运动的理解那样,它完全致力于公民的政治教育,训练公民为城邦服务。城邦共同体的本质需要产生了这种教育理想——它承认并运用知识的力量,亦即一种新的伟大精神力量,来塑造人的品格。至于我们是否认同导致这些问题的雅典民主政治原则,与我们这里的讨论无关。无论如何,除非全体成员积极参与政府管理(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是民主政治的显著标志之一),否则对希腊人来说,要想提出并回答那些永恒的问题必定是不可能的——在那个历史时期,他们曾经为这些问题深深困扰,并将这些问题留给后世子孙,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来回答;在我们现代社会也一样,相同的发展再次提出了相同的亟待回答的问题。只有在这样的精神发展阶段,诸如自由与权威、公民教育和领袖教育等等问题,才能得到思考和回答;也只有在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些问题作为人类命运的铸造者,才获致其全部的迫切性。这些问题不可能在原始的社会共同体中产生,不可能在游牧共同体或家族共同体中产生,因为在那里,对个体心灵的力量是没有概念的。因此,尽管这些问题最先是从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民主制中得到孕育的,但它们的重要性不限于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它们是国家本身与生俱来的问题。这一断言的明证就是,那些伟大的希腊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们,从民主政治的教育实践开始,很快就达到了大胆的结论,这些结论远远越过了既存政制类型的边界,对后世任何类似的处境都具有无比珍贵的指导意义。
[289]我们现在正在分析的这场教育运动,从古老的贵族文化发端,然后,在沿着一条广阔的曲线运动之后,在柏拉图、伊索克拉底和色诺芬那里,又回到了原初的贵族传统和贵族的德性观念,从而,贵族的德性观念在一种新的理性化基础上得到了重建。当然,在公元前五世纪的第一阶段,它离最终的回归仍非常遥远。因此,教育家们的首要目标是要冲破旧观念的束缚,即传统对高贵血统的钦羡;血统和世系只有在其作为 [智慧]和
[智慧]和 [公正]体现在理智的和道德的力量中时,才能确证其正当性。塞诺芬尼表明了,“心智的力量”和公民身份之间的联系在德性理想中即使在一开始时也是多么紧密,这种理想又是如何建立在正确的国家秩序和共同体的繁荣安宁之上的。 [6] 而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尽管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说的,他说,法律应该建立在产生它的“知识”之上;而这种神一样的知识的尘世拥有者,要求在城邦中的一种特殊地位,否则就会与城邦发生直接的冲突。 [7] 这些伟大人物的文字第一次表明了城邦与智识的关系问题的迫切性,新问题的迫切需要直接催生了智术师运动;同时也表明了,当智识的贵族统治取代种族的贵族统治之后,一种新的冲突马上就在老地方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伟大的智识人格(intellectual personality)和他所生活的城邦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无休止地困扰着哲学家们,直到希腊城市国家寿终正寝。在伯利克里那里,这个问题找到了一个对城邦共同体和个人都幸运而短暂的解决办法。
[公正]体现在理智的和道德的力量中时,才能确证其正当性。塞诺芬尼表明了,“心智的力量”和公民身份之间的联系在德性理想中即使在一开始时也是多么紧密,这种理想又是如何建立在正确的国家秩序和共同体的繁荣安宁之上的。 [6] 而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尽管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说的,他说,法律应该建立在产生它的“知识”之上;而这种神一样的知识的尘世拥有者,要求在城邦中的一种特殊地位,否则就会与城邦发生直接的冲突。 [7] 这些伟大人物的文字第一次表明了城邦与智识的关系问题的迫切性,新问题的迫切需要直接催生了智术师运动;同时也表明了,当智识的贵族统治取代种族的贵族统治之后,一种新的冲突马上就在老地方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伟大的智识人格(intellectual personality)和他所生活的城邦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无休止地困扰着哲学家们,直到希腊城市国家寿终正寝。在伯利克里那里,这个问题找到了一个对城邦共同体和个人都幸运而短暂的解决办法。
智术师运动第一次使“德性应该建立在智识之上”的主张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如果城邦共同体本身未曾感觉到城邦普通个人的视野应该由智识教育来打开的话,也许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教育运动,就不会以伟大的个体思想家的出现和他们的个体人格与城邦共同体的冲突而肇始。希波战争之后,当雅典在经济、商贸和政治各方面都步入国际舞台时,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雅典将其得救归功于一个才智杰出的强人,但在胜利不久之后,就又将他驱逐出境,因为他的权力无法与古风时代的均平(isonomia)理想相调和——这种行为看起来像一种隐蔽的专制暴行。 [8] [290]尽管如此,历史的逻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民主国家想要维持其自身的存在,就必须有适当类型的人作为其领导者。实际上,这就是民主政治首要的、唯一 的问题,因为一旦民主国家试图超越核准其代议人士之决定的一整套严格管理体系,民主原则就注定要朝着荒谬的 (ad absurdum)方向发展,从而实际上成为多数人的统治和暴政。
因此,这场由智术师所领导的教育运动,从其一出现开始,其目标就不是教化城邦的民众,而是造就城邦的领袖。说到底,这场运动只不过是贵族政制在新形势下的一个老问题。诚然,即使雅典没有一个由国家主导的教育体系,也没有任何别的地方能像雅典那样,让最普通的公民也有许多获得基础教育的机会。智术师们总是忙着向一些挑选出来的特定听众讲话,并且只对他们讲话。他们的学生都是些希望成为政治家、并最终成为国家领袖的人。抱有此种目标的人,不可能像亚里斯泰迪(Aristides)那样,仅仅通过实现旧的正义理想——即尽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一般义务——来满足他那个时代的需要;他不仅要遵守城邦的法律,而且还要制定法律来引导和治理城邦:职是之故,除了需要只有通过长期的政治实践才能获得的必要经验外,他还需要一种对人类生活的真正本性的普遍洞察。一个政治家的主要素质不可能从外部获得。沉着镇定和深谋远虑(这是修昔底德赞扬第米斯托克利的首要品质 [9] )是与生俱来的;但说话坚定有力、让人信服的才能则可以通过训练获得。那种口若悬河的辩才,即使在荷马时代组成政务会的贵族长老们中间,也是领导才能的显著标志;这一点在后来的世纪中一直保存下来。赫西俄德认为,这是缪斯女神赠与国王的一项权力,凭借这一权力,国王可以用温和的强制主导每一次会议;实际上,赫西俄德将其与诗人的灵感相提并论。 [10] 毫无疑问,他主要是将其作为一种法庭审判时的表达能力——确立真相并作出裁决——来讲述的。在民主国家,全体民众因为政治目的聚集在一起,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在那里自由发言,演说才能成为每个政治家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291]它是政治家手中[掌控城邦这艘航船]的方向舵。在古典希腊,政治家被径称为rhétor,即演说者。这个词在当时还没有获得它在后世所具有的那种纯粹形式的意义,它也指演说家讲话的内容:那个时代的每一次公开讲话都会涉及国家及其事务,这是显而易见且自然而然的。
因此,要将一个人培养成政治家,雄辩的口才是任何此类尝试的必然起点。政治教育合乎逻辑地变成了修辞学[演说术]教育——尽管作为教学目标的语言(logos )可能包含形式和内容(二者的比例各不相同)两个方面的传授。理解了这一点之后,就很容易明白雅典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教师阶层了,他们公开宣称,只要有钱,就可以传授你“美德(virtue)”。 [11] “美德”是“德性 (areté)”一词的翻译,但用这样一个词来翻译德性,是一种错误的现代化,它很容易让我们把智术师是“知识的教师”的主张当作愚蠢的自大而不屑一顾——先是他们的同时代人以“知识的教师”称呼他们,很快他们自己也这样称呼自己。一旦我们将这里的“德性”解释为意指政治德性,以及政治德性在古典希腊自然而然的重要意义,且它首先意味着理智的力量和雄辩的口才——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新形势下,这注定是城邦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这种愚蠢的误解马上就会消失。我们不可避免地会用柏拉图怀疑的眼光来回顾智术师,柏拉图认为一切哲学知识的开端是苏格拉底的疑问,即“美德是否可教”。不过,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错误,它使我们不能理解文化史上的这个重要的新时代,并将后来的哲学思想发展阶段上的问题强加在了智术师身上。在人类精神发展史上,智术师和苏格拉底或柏拉图一样,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实际上,如果没有智术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从来就不可能存在。
智术师传授政治德性的尝试,是城邦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一种深层次变化的直接反映。修昔底德以其天才的洞察力,看到并描述了城邦的社会结构在雅典步入希腊的政治舞台时所经历的巨大变迁。当它从传统的静态的城市国家向动态的伯利克里的帝国形态转化时,它的全部能量被激发为暴力行为和激烈竞争,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292]政治教育的理性化,仅仅只是雅典内部全部生活的理性化的一种特殊情况;现在,生活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变成了成功和成就。这种变化注定要给评判人物的标准带来影响。人的道德品格现在退居幕后,聪明才智得到空前强调。几乎不到五十年前,塞诺芬尼曾经是新的人格理想的唯一捍卫者;但他对知识和理性的羡慕现在已蔚然成风,尤其是在商业和政治生活中。德性理想吸收了后来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在理智德性( )的标题下集合的一切价值,德性理想还试图与伦理价值相融合,以便构成一个更高的统一体。 [12] 当然,智术师的时代还没有看到这些问题。因此,人的理智方面第一次被放到显著的位置,从而产生了智术师们努力实现的教育使命。这是他们宣称自己可以传授德性的信念的唯一可能的解释。因此,智术师及其教育预设,在某种意义上与苏格拉底及其根本疑问同样是正确的:因为苏格拉底和智术师思考的实际上是不同的事情。
)的标题下集合的一切价值,德性理想还试图与伦理价值相融合,以便构成一个更高的统一体。 [12] 当然,智术师的时代还没有看到这些问题。因此,人的理智方面第一次被放到显著的位置,从而产生了智术师们努力实现的教育使命。这是他们宣称自己可以传授德性的信念的唯一可能的解释。因此,智术师及其教育预设,在某种意义上与苏格拉底及其根本疑问同样是正确的:因为苏格拉底和智术师思考的实际上是不同的事情。
尽管他们说自己的教育目的是心灵(mind)的教育,但他们用各种意想不到的不同方法来达到这种教育目的。然而,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的心灵可以出现在多少个方面,那么就可以尝试从一个单一的智力目标中得出该变化的所有方面;从一个角度来说,心灵是人把握对象世界的一个器官——它与外在事物紧密相连。但是,如果我们采取智术师的态度,将心灵从对象的内容中解放出来,那它就不再是一个空虚的接收器,而是有一个真实的内在结构,第一次被揭示出来的内在结构。这就是被视为一种形式原则的心灵。与这两个心灵本质的概念相对应,在智术师中间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教育方法。一种就是把千变万化的事实 ,即各种知识材料输入心灵,另一种就是对心灵进行各种类型的形式 训练。 [13] 显然,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只有在超越性的智力文化观念中才能得到统一。它们二者都传承至今,尽管通常是以一种折中的方式,而不是以彻底肯定其中一种反对另一种的方式。[293]在很大程度上,智术师时代的情况与此类似。不过,尽管不同的智术师将这两种方法以不同的方式混合在一起,我们切不可忽略这一事实,即它是对[如何进行]心灵教育这个相同问题的两种根本不同的回答。与纯粹形式的教育方法一样,智术师们有时也实践一种更高类型的形式教育,这种教育不是致力于解释理性和语言的内在结构,而是致力于培养灵魂的各种能力。这种方法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除了文法、修辞和辩证法之外,主要是利用诗歌和音乐来塑造人的灵魂。这第三类智术教育(sophistical education)的原因,是基于政治和伦理的考虑。 [14] 它与前述形式训练和内容灌输二者不同,不是把人当作抽象的、作为孤立的个体来对待,而是作为城邦共同体的一员来看待,因而给了人在价值世界中的一个稳固地位,从而使智识文化成为德性整体的一个部分。这种教育方法也是智识教育,不管怎样,这种方法把心灵既不当作形式的,也不当作事实的东西来处理,而是当作受社会秩序调节的事物来处理。
有人认为, [15] 智术师运动新颖独到之处、同时也是所有成员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的修辞学[演说术](rhetoric)教育理想,即 [辩才无碍],因为他们都培训演说术(oratory),但他们在其他任何事情上又意见相左;也有一些智术师是单纯的修辞学教师(rhetors),不教任何别的东西,如高尔吉亚。不过,这显然是一种肤浅之见。实际上,他们所有成员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教授政治德性, [16] 而且都希望通过训练增强理智的力量,从而逐步培养其政治德性——无论他们接受的训练是什么。对于智术师们提供给世界的、新颖而永久的宝贵财富,我们只能感到惊讶。他们是智力文化和教育艺术的发明者。与此同时,很显然,每当他们的新文化越出形式教育或内容教育的界限,每当他们的政治训练抨击伦理道德和城邦的深层次问题时,这种新文化就陷入了传授半真半假的知识的危险——除非它能够植根于真正的、彻底的政治思想之中,因政治本身之故寻找政治的真理。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后来抨击整个智术文化体系,并动摇了其根基。
[辩才无碍],因为他们都培训演说术(oratory),但他们在其他任何事情上又意见相左;也有一些智术师是单纯的修辞学教师(rhetors),不教任何别的东西,如高尔吉亚。不过,这显然是一种肤浅之见。实际上,他们所有成员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教授政治德性, [16] 而且都希望通过训练增强理智的力量,从而逐步培养其政治德性——无论他们接受的训练是什么。对于智术师们提供给世界的、新颖而永久的宝贵财富,我们只能感到惊讶。他们是智力文化和教育艺术的发明者。与此同时,很显然,每当他们的新文化越出形式教育或内容教育的界限,每当他们的政治训练抨击伦理道德和城邦的深层次问题时,这种新文化就陷入了传授半真半假的知识的危险——除非它能够植根于真正的、彻底的政治思想之中,因政治本身之故寻找政治的真理。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后来抨击整个智术文化体系,并动摇了其根基。
[294]我们现在必须探究智术师在希腊哲学和科学的历史上究竟居于何种地位。实际上,尽管我们毫不犹豫地接受在绝大多数希腊哲学史中出现的传统观点,认为他们是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有机部分,但智术师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一直不明不白。我们决不可依赖柏拉图对他们的叙述:因为柏拉图与智术师们一直意见不合的关键,不在于他们的知识,而在于他们传授德性的主张,在于他们与生活和行为之间的联系。只有唯一的一次例外——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对普罗泰戈拉的知识理论的批评; [17] 在那篇文章中,智术师运动确实是被看作哲学的一部分,但也仅仅是就普罗泰戈拉所代表的而言。这就是智术和哲学之间的一点微小联系。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哲学史叙述,将智术师排除在外。有关这一主题的现代历史将智术师看作哲学上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奠基者。不过,普罗泰戈拉勾勒出了一种哲学理论的轮廓的事实,不足以为我们提供充足的理由来概括所有的智术师,从历史的角度看,将传授德性的教师与诸如阿那克西曼德、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这样的大思想家相提并论,是一种失误。
历史(Historia ),根据伊奥尼亚人的实践,纯粹是一种客观公正的研究,它无关乎人的生活和人的实际教育目的——正如米利都人的宇宙学理论所充分显示的那样。从他们开始,我们已经表明了,随着人的存在问题越来越成为人的兴趣焦点,对整个宇宙的探究是如何逐步集中到对人的探究上来的。 [18] 塞诺芬尼将人的德性建立在对神和宇宙的理性知识之上的大胆尝试,实际上已经在宇宙学和教育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联系。有那么一段时间,被转化成诗歌的自然哲学似乎将要在整个国家的生活和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塞诺芬尼后继无人,尽管当人的本性、价值和得救之路这些问题被提出来之后,追随他的那些哲学家并没有抛弃这些问题;只有赫拉克利特这个伟大的思想者,足以在一个单一原则的基础上,建构一种逻各斯治下的宇宙论,这种宇宙论将人作为一个本质性的部分包含在内。 [19] 应该指出的是,与米利都学派不同,赫拉克利特不是一个自然哲学家。[295]米利都宇宙学家在公元前五世纪的继承者,把对自然的探究越来越看作是科学的一个特殊部门,他们要么将人完全排除在其理论之外,要么根据他们特殊的哲学思维能力,各自发明一套他们自己的解决方法。在克拉佐曼纳的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 of Clazomenae)那里,宇宙演化学说第一次受到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宣称存在的根基是心灵 这种安排和主导的力量;但除了这一原理之外,他对自然的解释完全是机械论的,他从未成功地表明自然和心灵是如何相互渗透的。 [20] 阿克拉加斯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 of Acragas)可以说是一个哲学上的半人马怪物(centaur),是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和俄耳甫斯宗教的一种奇妙结合。他教导说,人,这个自然之永恒生成和消逝手中被遗弃的玩物,可以沿着一条神秘的道路前行,跳出他命中注定的自然力进程的悲惨循环,进入灵魂的那种纯洁的、原初的、神圣的生活。 [21] 如此这般,每一个思想者都以不同的方式支持人的精神生活的独立性来对抗宇宙自然力的权力。即使德谟克利特也不能从他严格的宇宙论逻辑中,将人的问题和人的道德世界排除出去。不过,他避开了他的前辈们已经提供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之中有些是非常奇怪的——他选择将自然哲学从伦理学分离出来:他以一种陈旧的教谕(parainesis)形式,即道德劝诫的形式,而不是作为理论知识的一门学科的形式,来阐释他的伦理教导。正如他所推进的那样,它是传统的道德格言和当代哲学的科学理性主义精神的一种奇妙混合。 [22] 所有这一切试图融合两个世界(即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努力,都是人性和人生这一新哲学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增长的清晰征兆。尽管如此,他们都没有创造出智术师们的教育理论。 [23]
哲学日益聚焦于人的问题,是智术师的存在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另一明证;不过,他们的出现是对实际生活需要的一种响应,而非对理论和哲学需要的一种响应。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雅典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而伊奥尼亚的自然科学家却不能在那里生根发芽的基本原因。[296]实际情况是,智术师们不理解与生活相分离的哲学。他们是诗人 的教育传统的传人;他们是荷马和赫西俄德、梭伦和泰奥格尼斯、西蒙尼德斯和品达的后继者。在把他们作为诗歌传统的继承人,给予他们在希腊文化教育史上的应有位置之前,我们不可能把握他们的历史地位。 [24] 西蒙尼德斯、泰奥格尼斯和品达早就已经用诗歌讨论过德性是否可教的问题,尽管在他们之前,诗人们只是简单地呈现和赞扬他们自己特殊的人性理想,还没有展开讨论;诗歌随着他们成了教育理论家们的争论阵地;例如,正如柏拉图自己所言,西蒙尼德斯骨子里就是一个典型的智术师。 [25] 智术师们只不过是沿着既有的道路跨出了最后一步。他们把各种形式的劝诫诗及其显著的教育目的转化成了运用自如的艺术散文,从而开始了他们与诗歌的公开竞争,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方面。 [26] 与此同时,教育理论从诗歌转移到散文这一事实,是其终于完全理性化了的一个信号。智术师继承了诗人对诗歌教育功能的所作所为,他们也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诗歌的性质和目的的讨论。他们是首批为大诗人们的作品给出有条不紊的讲解的人,通常会根据自己的讨论内容选取诗歌中的段落。他们当然不是按照我们所理解的“阐释” 一词来阐释诗歌。他们视诗人为即时而永恒的存在,对他们进行天真无忌的讨论,仿佛他们书写的就是当代人的生活。 [27] 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冷静的目的性,在智术师“诗歌意味着教诲”的信念中是最明显的,也是最不恰当的。智术师们将荷马看作人类一切知识的百科全书,从战车的制造到战略的运用,将他看作为人处事的审慎智慧的宝藏。 [28] 史诗和肃剧,这两种通过表现英雄的行为来达到教育目的的诗歌,现在从一种公开的实用主义的角度得到了阐释。
然而,智术师们不只是借用诗歌的教育传统:他们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他们的著作和讲演讨论形形色色的新问题;他们是如此深刻地既受流行的理性主义伦理学和政治学理论的影响,[297]又受到自然哲学家们的科学学说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创造了一种综合文化的氛围,甚至远比庇西特拉图时代的文化还要生动活泼、激励人心、意味深长。他们对知识的力量的骄傲和自信让人想起塞诺芬尼:柏拉图不知疲倦地以各种形式对此进行模仿和嘲弄,从矫揉造作的自尊到细枝末节的自负。无论是在智力的自负上,还是在自身的独立性、在他们倜傥不羁的世界主义上,他们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学士(literati)极其相似。埃利斯的希庇阿斯(Hippias of Elis),他通晓知识的各个分支,学习过各种商业贸易,从未穿戴不是自己亲手制作的服饰,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通才 (uomo universale)。 [29] 另外还有两个人,他们如此巧妙而又令人目眩地将学者和演说家、将教师和文学家的职能结合在了一起,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将他们归于任何一个传统的职业范围之下。智术师们所到之处,因为他们的学说和教导,还有他们的才智和精神魅力,让他们成为各个城市富贵之家蓬荜生辉的座上宾。也正因为这一点,他们是我们在公元前六世纪僭主的宫廷和豪门中看到的巡回诗人的真正继承者。 [30] 与“智术师”的字义一致,他们以其才智为生。由于不断地从一个城市漫游到另一个城市,因而他们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国籍。一个人以这样一种彻底的独立性生活于那个时期的希腊是完全可能的,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根本的个人主义文化类型即将形成的最不容置疑、最独特的征兆——因为智术师都是个人主义者,不管他们嘴上如何说教育要服务于城邦共同体、要培育一个好公民的德性。整个时代正在朝着个人主义大步前进,他们站在这一运动的前列:因此,他们的同时代人把他们看作时代精神的真正代表是正确的。那个时代的另一个征兆,是智术师都以[贩卖]文化为生;柏拉图说, [31] 文化[知识]就像市场上的商品一样贩进来、卖出去。在柏拉图这个带有敌意的比喻中,存在着几分真理,尽管我们决不可把它看作柏拉图对智术师及其生活方式的一种道德批判,而是一种理性诊断。他们提供了一个几乎未经开发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社会学”的宝藏。
[298]千言万语一句话,他们是文化史上具有第一等重要性的一种现象。通过他们,教化(paideia)——文化的理想和理论,这种被有意识地塑造和追求的理想和理论——逐步生成,并被建立在一种理性的基础之上。因此,他们标志着人文主义发展的一个巨大进步,纵然其最高明最真实的形式,只有在随之而来的柏拉图对他们的理想的讨伐中才得到实现。 [32] 智术师身上存在着某种非永久的不彻底的东西。他们并不代表一种哲学的或者科学的运动,他们只代表哲学和科学(伊奥尼亚传统的自然科学和历史学[historia])领域被其他兴趣和问题侵入了,尤其是被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变化所造成的教育和社会问题侵入了。因此,他们的工作的直接后果就是取代科学和哲学,就像他们不久以前被教育学、社会学和新闻学取代一样。尽管如此,通过将旧的主要包含在诗歌中的教育传统,转化为他们自己理性主义时代的语言和思想体系,通过建立文化的理论和目标,他们将伊奥尼亚科学的影响扩展到了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并将其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哲学、可以与自然哲学相提并论且超越自然哲学的一种哲学。 [33] 他们的形式革新比他们工作的其余部分具有一种更为持久的影响。但是,当科学和哲学逐渐从修辞学[演说术]独立出来时,他们的伟大发明即修辞学[演说术]即将在科学和哲学领域遭到强有力的挑战和竞争。因此,即使在其多样性上,智术师的文化也包含着伟大的文化冲突——哲学和修辞学[演说术]之间的冲突——的第一个征兆,这种文化冲突将贯穿接下来的所有世纪。
教育理论的起源和文化的理想
智术师被说成是教育科学的奠基者。他们确实创立了教学法,即使今天的智识文化很大程度上都是在遵循他们指明的道路。 [34] 不过,教学法是一门科学,还是一种技艺,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们自己也把他们的教育艺术和理论叫作“techné”,即技艺,而不是科学。在柏拉图那里,[299]我们可以看到普罗泰戈拉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的一个详细叙述;因为,尽管柏拉图对这位大智术师的言行的报导有些滑稽和夸张,但它在本质上必定是真实的。普罗泰戈拉把自己的职业叫作“政治的技艺”,因为其目标是教授政治德性。 [35] 教育是一种专门的技艺这一信念,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大趋势的又一例证,当时的大趋势是将生活本身划分为许多特定的行为领域,各个领域有各自的目标,各自建立的理论,各自涉及一个特定的可以经由教育来传授的知识部门。在数学的不同分支以及医学、体育、音乐理论、戏剧技巧等诸如此类的学科中,希腊当时有许多专家和专业出版物;甚至像波利克里托斯(Polyclitus)这样的雕刻艺术家们,也开始写作他们专业的理论著作。
当然,智术师们相信他们自己的技艺是所有其他一切技艺的皇冠。在柏拉图借普罗泰戈拉之口说出的关于文明起源的神秘叙述中——作为普罗泰戈拉对自身技艺的性质和地位的一种解释——智术师区分了人类发展的两个阶段。(显然,普罗泰戈拉不是将其设想为历史中两个不同的时间阶段,而是为了强调智术师所代表的高级教育的重要性和必然性才将其区分开来。)第一个阶段是技术文明的时代。遵循埃斯库罗斯的说法,普罗泰戈拉将其叫作普罗米修斯的礼物,是人类随着火的使用而获得的文明阶段。他说,尽管那时的人拥有了火和各种技艺,但如果宙斯没有赠送给他们“正义”的礼物,使他们建邦立国并生活于社会共同体之中,他们仍然会因为毒蛇猛兽而孤独无助地悲惨死去。普罗泰戈拉的这一观念是同样借自埃斯库罗斯(借自《普罗米修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还是借自赫西俄德,这一点还不清楚;赫西俄德第一个将正义作为宙斯送给人类的礼物来赞美,这礼物使人类与相互吞噬的动物相区别。 [36] 不管怎样,普罗泰戈拉对这一主题的论述完全是他自己的看法。他说,普罗米修斯的技术性知识的礼物只派送给少数专家,而宙斯却将正义感和法律观念发送给了所有人,因为如果没有它,城邦共同体就不可能存在。但是,还有一种更高类型的对城邦及其正义原则的洞见,这种洞见是由智术师们的政治技艺来教导的。他相信这就是真正的文化,[300]是将整个人类社会的结构和文明整合在一起的理性纽带。
并非所有的智术师对自身的职业都具有一种如此高贵的构想——毫无疑问,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只满足于向公众贩卖知识。不过,要想理解和鉴别整个智术师运动,我们就必须研究这一运动的那些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的断言——文化教育是人类一切生活的核心——表明他的教育目的不加掩饰地指向人文主义 。他暗示,通过将我们现在称之为文明的东西——亦即技术能力——从属于文化,在技术的知识和能力与真正的文化之间做出的清晰而根本的区分,是人文主义的真正基础。也许,我们应该避免将希腊的专业知识与现代的职业观念( )相等同,后者从起源上说属于基督教,它比希腊的技艺观念含义广泛。 [37] 在我们看来,一个政治家的工作——这是普罗泰戈拉想要教育人们去实践的——也是一种职业;但在希腊,将政治也叫作技艺那是极其大胆的,这么做的唯一正当理由,是希腊语中没有另一个词可以表达政治家通过训练和实践获得的那种知识和能力。很清楚,普罗泰戈拉急于将其自身的政治技艺与狭义的技术性职业相区别,并将其作为某种综合与普遍的东西呈现出来。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严格地将他的“普遍”文化的观念与其他智术师提供的教育区分开来,后者是一种纯粹的事实性课程与教学。根据他的说法,他们是在“毁灭青年”;尽管他们的学生为了逃避一个工匠获得的那种技术性教学来向他们求教,但他们忽略了学生的愿望,而向学生传授另一种类型的技术性课程。 [38] 在普罗泰戈拉看来,唯一真正的“普遍”文化是政治 文化。
)相等同,后者从起源上说属于基督教,它比希腊的技艺观念含义广泛。 [37] 在我们看来,一个政治家的工作——这是普罗泰戈拉想要教育人们去实践的——也是一种职业;但在希腊,将政治也叫作技艺那是极其大胆的,这么做的唯一正当理由,是希腊语中没有另一个词可以表达政治家通过训练和实践获得的那种知识和能力。很清楚,普罗泰戈拉急于将其自身的政治技艺与狭义的技术性职业相区别,并将其作为某种综合与普遍的东西呈现出来。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严格地将他的“普遍”文化的观念与其他智术师提供的教育区分开来,后者是一种纯粹的事实性课程与教学。根据他的说法,他们是在“毁灭青年”;尽管他们的学生为了逃避一个工匠获得的那种技术性教学来向他们求教,但他们忽略了学生的愿望,而向学生传授另一种类型的技术性课程。 [38] 在普罗泰戈拉看来,唯一真正的“普遍”文化是政治 文化。
这一关于“普遍”文化的本质的观点概括了希腊教育的全部历史:伦理和政治相结合是真正的教化的基本品格之一。 [39] 直到后来,一种新的审美理想才被叠加于、甚至干脆取代了旧的人文主义观念,因为城邦在人的生活中失去了主导地位。但是,高级教育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仍然是古典希腊的一个本质性特征。在此,[301]我们并不是将“人文主义” 一词作为一种早期现象的历史相似物含糊其辞地来使用的,相反,我们是在根本的意义上,深思熟虑地用它来指那种在希腊人的精神中长期孕育之后最终在智术师的教育中一朝分娩的文化理想。如今,与其同源词“人性(humanities)”一样,它与我们的文化和古典时期的关系有关。然而,这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普遍”文化的理想起源于希腊罗马的文明而已。因此,在此意义上,人文主义本质上是希腊人的一种创造。现代教育本质性地且无可避免地建基于对古典时代的研究之上,正是因为古代希腊实现的人文主义对人的精神具有一种永久的重要地位。 [40]
此外,我们在这里必须看到,尽管人文主义的本质一以贯之,但它是一种活的、不断发展的思想:普罗泰戈拉的定义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最终定义。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伊索克拉底,都接收了智术师的文化观念,而且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对它进行了损益。 [41] 这种变化的一个最显著的证据就是普罗泰戈拉的那句有足够理由闻名遐迩的格言——这句格言在许多方面都标志着普罗泰戈拉的人文主义的本质特征——被柏拉图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和最后一部著作中所接受,并将其由“人是万物的尺度”改为“神是万物的尺度”。 [42] 在这一点上,我们最好记住普罗泰戈拉的话:“关于神,我既不能断言他存在,也不能断言他不存在。” [43] 鉴于柏拉图对智术师的教育原则的批评,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宗教怀疑主义和无动于衷,以及道德和形而上学的“相对主义”——这些柏拉图如此愤愤不平地反对、又使他成为智术师的激烈批判者和毕生反对者的东西——是人文主义的本质性因素吗? [44] 这个问题不能由任何个人意见或者个人喜好来回答:它必须由历史来做出一个客观的回答。本书会时不时返回到这一点,并描述宗教与哲学的文化之战——当基督宗教最终为希腊罗马世界所接受时,这场战斗也在人类历史上达到了高潮。 [45]
我们至少可以先这么说,在智术师运动之前,在古代希腊教育中不存在任何文化与宗教之间的现代区分:古代希腊教育深深地植根于宗教信仰之中。[302]二者之间的裂隙首先是从智术师时代开始的,这个时代刚好也是文化理想首次得到自觉建构的时期。普罗泰戈拉对一切传统价值之相对性的断言,对一切宗教奥秘不可解性的顺从接受,毫无疑问,都与他的高级文化理想密切相关。或许,除非到了原有的标准——这一标准一度对希腊教育极其重要——开始受到质疑的那一刻,否则,伟大的希腊教育传统不可能产生自觉的人文主义理想。实际上,智术师的教育清楚地表明了对一种人类生活本身的有限基础的回归。教育永远需要一种标准;当此之时,在传统的教育标准分崩离析且渐行渐远之际,它便选择人的[而非神的]的形式 (form)作为它的标准,从而也就成了形式的 (formal)教育。 [46] 此情此景在历史的各个不同时期反复出现,而人文主义的出现也总是与这样的情境紧密相连。不过,这确实是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这种教育在哪个时候都是一种形式的教育,但它总是越过自身前瞻后顾——后顾历史传统中丰富的宗教和道德力量,将其作为真正的“精神”,而抽象到空空如也的理性主义智识观念,必须从中提取其具体而生动的内容;前瞻一种生活理念的宗教和哲学[基础]问题——这种生活理念包围和保护着人类,就像保护一颗幼嫩的根苗,同时也把它归还给它所生长的肥沃土壤。这就是所有教育的基本问题:我们对它的回答将决定我们对智术师的重要性的判断;用一种历史的语言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智术师的人文主义,这个世界第一次见到的人文主义,是被柏拉图摧毁的,还是由柏拉图来完成的。我们对此历史问题给出的任何回答都将是一种信仰的告白。然后,从单纯历史事实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似乎早已尘埃落定:智术师提出的人类文化的理想在其自身内包含着伟大未来的胚芽,但其自身并非一种成熟和完美的作品。 [47] 由于牢牢把握住了教育中的形式要素,即使在今天,这一理想仍然对教育实践具有无可估量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它所主张的理想如此高远,所以它还需要一种更深的宗教和哲学上的根基。从根本上说,柏拉图哲学是早期希腊教育——从荷马到肃剧作家——的宗教精神的转世重生:[303]通过进一步斟酌智术师的文化理想,他超越了智术师的理想。 [48]
智术师与众不同的是:他们是构想自觉的文化理想的开山鼻祖。从荷马时代到雅典的崛起,如果我们纵览希腊精神的漫长发展进程,就会认识到,这一观念并非一个令人吃惊的新起点,而是一个必要的续集,是整个历史进程的顶点。因为它是所有希腊诗人和思想者寻找并表达人性的持久努力的结果。这种努力本质上是一种教育活动,尤其是在像希腊这样一个如此哲学化的民族中,它为更高层次的文化观念——作为一种被理解和遵循的理想——奠定了基础。因此,智术师将早期希腊的所有艺术和哲学都看作其文化理想的组成部分,看作其文化理想的必然内容,是非常自然的。希腊人总是清楚地意识到诗歌的教育力量。因此,当教育( )的含义超出儿童训练(
)的含义超出儿童训练( )的范围之外,尤其是扩大到青年的教育,以至于教育可以延伸到人类生活全部领域的信念也得到鼓励之际,希腊人最终将诗歌作为文化教育的材料来接受就是不可避免之事了。希腊人突然意识到成年人也可以有教化(paideia)。教化的概念起初只应用在教育过程上,现在其意义变成包括其客观方面(即教化的内容)在内了——就像我们的“文化 (culture)”或拉丁语的“cultura ”一词,曾经意指教育的过程 ,变成指被教育的状态 ,然后是教育的内容 ,最终是教育所呈现的智识和精神的世界 ——任何个人根据其国别或社会地位之不同,均出生于此种理智和精神的世界 之中。当文化的理想得到自觉的筹划和建构之时,建造文化世界的历史进程也就达到了顶点。相应地,在公元前四世纪或之后,当教化的概念最终成形,希腊人用“教化” (在英语中,是“文化” )一词来描述一切艺术形式及其种族的智识和审美成就——实际上就是他们的整个传统 ——也就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的范围之外,尤其是扩大到青年的教育,以至于教育可以延伸到人类生活全部领域的信念也得到鼓励之际,希腊人最终将诗歌作为文化教育的材料来接受就是不可避免之事了。希腊人突然意识到成年人也可以有教化(paideia)。教化的概念起初只应用在教育过程上,现在其意义变成包括其客观方面(即教化的内容)在内了——就像我们的“文化 (culture)”或拉丁语的“cultura ”一词,曾经意指教育的过程 ,变成指被教育的状态 ,然后是教育的内容 ,最终是教育所呈现的智识和精神的世界 ——任何个人根据其国别或社会地位之不同,均出生于此种理智和精神的世界 之中。当文化的理想得到自觉的筹划和建构之时,建造文化世界的历史进程也就达到了顶点。相应地,在公元前四世纪或之后,当教化的概念最终成形,希腊人用“教化” (在英语中,是“文化” )一词来描述一切艺术形式及其种族的智识和审美成就——实际上就是他们的整个传统 ——也就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从这个角度看,智术师站立在希腊历史的核心地带。他们使希腊自觉到她自己的文化;[304]而希腊精神则在此文化自觉中抵达了它的终点 ( telos ),实现了它自己的形式和发展目标。他们促进了希腊人理解文化的真正意义这一事实,远比他们没有给出这种文化的最终形式这一事实重要。 [49] 在传统的价值标准土崩瓦解之际,他们认识到了,而且也使希腊人认识到,这种文化是降临在他们全民族之上的伟大职责;因此,他们找到了整个种族发展的最终目标,以及各种有组织的生活的基础。这种领悟是一次伟大的如日中天;不过,(正如在每个民族那里一样)它只是一次秋季的如日中天,而不是一次夏季的如日中天。当然,这是智术师的工作的另一个方面。尽管无需证明从智术师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一时期,希腊精神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并达到了更伟大的高度,但(如黑格尔所言)密涅瓦(Minerva)的猫头鹰要到黄昏降临才起飞也是真实的。希腊精神将要赢得的主导地位——智术师首先宣告了这种主导地位——是希腊以其青春为代价获得的。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尼采和巴霍芬(Bachofen)会觉得希腊的夏天是在ratio( 即自觉的理性)出现之前的那个时期——也即神话时代、荷马或伟大的肃剧家们的时代。但是,我们想要接受早期希腊的那种单纯的浪漫主义观点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民族的精神,与一个人的精神一样,是根据一种内在的必然规律而发展的,它留给后世的印象必然是复杂的,不可能是简单的。一方面,我们觉得在一个民族那里,这种精神的成长和发展意味着一种无可避免的损失,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仍然不能放任自己牺牲这种发展所取得的力量。我们知道,只是由于这种力量,我们才有能力如此自由、如此充分地羡慕早期希腊的非理性阶段。这当然是我们今天的立场:我们的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晚的阶段,在许多方面,直到智术师的兴起,我们才开始在希腊有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智术师比品达和埃斯库罗斯与我们更亲近,正因如此,我们更需要品达和埃斯库罗斯。经由智术师,我们认识到了,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早期阶段确实仍然存活在它之内;因为除非我们同时也羡慕和理解早期的发展阶段,否则就不能接受后来的发展阶段。
[305]我们对智术师所知甚少,即使对他们之中最伟大者的学说和目的,我们也不能给出一个详尽的个别的叙述。正如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中对智术师所做的比较性描述所表明的,他们自己也特别强调彼此之间的差别;但他们又并非自己所想的那样截然不同。我们对他们几无所知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写过任何能够长久流传的著作。普罗泰戈拉在文学以及其他教育活动中享有最高地位,但他只留下了几篇零星的古代晚期仍能读到的随笔,但即使是这样的文章,也差不多被那个时代全部忘记了。 [50] 少量由不同智术师撰写的哲学性和科学性比较强的论文流传了几十年,但一般来说,这些作者并不是学者,他们想要影响的是他们自己时代的人。用修昔底德的话说,他们的展示(epideixis) [51] 不是一种永恒的财产,而是一种炫人耳目的时兴表演。因而,即使他们最严肃的教育著作,自然也是为眼前的活人写的,而不是为未来的读者所作。苏格拉底远胜彼等,因为他不著一字。对智术师的教育技艺没有真正的了解是一种无可弥补的损失。这种损失无法以我们对他们的生活和见解所知的少数细节来抵消,因为这些细节归根结底是无足轻重的。我们只需考察那些能够说明其理论的材料就可以了。从我们的角度看,研究他们在把握文化理想的同时,他们理解文化教育过程的诸阶段,是第一要紧之事。他们对教育的理解证明他们了解教育的基本事实,尤其是他们能够分析人性。他们的心理学很简单:与现代心理学相比,他们的心理学几乎像伊奥尼亚哲学家的宇宙基本结构理论与现代化学相比那么简单,但是,现代心理学家对人的真正本性的了解,并不比智术师多,而化学家对世界本性的了解并不比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西美尼强。因此,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可以接受并赞赏智术师们开创的新教育理论。
大约一个世纪之前,贵族教育和民主理想的冲突已经爆发——泰奥格尼斯和品达证明了这种冲突。 [52] 现在,智术师们追索这一冲突提出的问题,[306]探究一切教育的基础——自然 [天性]与有意识的教育影响在品格塑造中的关系。我们没有必要在当代文献中大段引用此类讨论的重复论调,它们无非是表明智术师已经使全希腊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尽管表达的方式不同,但结论总是大致相同——自然 ( )是一切教育得以建立的基础;完成那种教育的过程叫学习 (
)是一切教育得以建立的基础;完成那种教育的过程叫学习 ( )——有时也叫教学 (
)——有时也叫教学 ( )——和练习 (
)——和练习 ( ),这一过程使学进去的东西成为第二自然 。 [53] 鉴于贵族教育和理性主义之间的传统对立,智术师的这个结论是综合二者的一种尝试:它抛弃了品格和德性可以凭血统继承,而不是经后天习得的贵族观念。
),这一过程使学进去的东西成为第二自然 。 [53] 鉴于贵族教育和理性主义之间的传统对立,智术师的这个结论是综合二者的一种尝试:它抛弃了品格和德性可以凭血统继承,而不是经后天习得的贵族观念。
现在,神圣血统的伦理权力被人的自然 (human nature)的普遍观念——连同其个体的偶然性和模糊性,当然还以一种更广阔的范围——所取代。这当然是一种最重大的偏离,如果没有医学进步的帮助是不可能完成的。长久以来,医学一直是一种原始的急救措施,其中夹杂着大量流行的迷信行为,以各种咒语和巫术感应来治病,直到伊奥尼亚关于自然进程的新知识以及一套常规的经验性技术的建立将其提升为一门技艺,并教导医生对人的身体及其变化过程进行科学的观察。我们在智术师及其同时代人那里经常见到的人的自然 的观念,首先是从开明的医生和医学研究者中间产生的。 [54] 自然 ( )的观念从整个宇宙转移到了其中一个部分——人类身上;而且在那里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人受他自己的 自然所规定的特定法则的制约,如果他想要健康地生活并从疾病中适宜地康复的话,就必须了解他自己的 那个自然 。这是对这一事实的首次承认:即人的自然是一个符合自然法则的有机体,它有一个有待认识的特定结构,需要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治疗。从这一医学的自然观念出发,希腊人很快就有了“
)的观念从整个宇宙转移到了其中一个部分——人类身上;而且在那里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人受他自己的 自然所规定的特定法则的制约,如果他想要健康地生活并从疾病中适宜地康复的话,就必须了解他自己的 那个自然 。这是对这一事实的首次承认:即人的自然是一个符合自然法则的有机体,它有一个有待认识的特定结构,需要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治疗。从这一医学的自然观念出发,希腊人很快就有了“ ”这个词的广泛应用,它是智术师的教育理论的基础:现在变成指由身体和灵魂一起构成的整个人,尤其是指人的精神本性(spiritual nature)。与此同时,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也正在使用人性(human nature )的概念,[307]只不过是根据他的学科做了改变,来指示人的社会和道德本性。现在,首次得到确切规定的人性观念,不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或自然而然的观念了:它是希腊精神的一个伟大的基础性发现。只有在它被发现之后,才有可能建构一种真正的文化理论。 [55]
”这个词的广泛应用,它是智术师的教育理论的基础:现在变成指由身体和灵魂一起构成的整个人,尤其是指人的精神本性(spiritual nature)。与此同时,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也正在使用人性(human nature )的概念,[307]只不过是根据他的学科做了改变,来指示人的社会和道德本性。现在,首次得到确切规定的人性观念,不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或自然而然的观念了:它是希腊精神的一个伟大的基础性发现。只有在它被发现之后,才有可能建构一种真正的文化理论。 [55]
智术师并未解决隐含在“自然” 一词之中的深层宗教问题。他们以一种乐观主义的信念——人的自然[本性]通常可教,而且能够向善——开始;他们相信,不幸的人或者性情邪恶的人只是例外。当然,在这一点上,人文主义经常遭受基督徒的抨击。毫无疑问,智术师的教育乐观主义并非希腊人对此问题给出的最终答案;然而,倘若希腊人从人皆生而有罪的信念,而不是从人皆可使向善的思想出发,那么他们就永远不可能创造出他们自己的教育技艺和文化理想。要想知道希腊人是如何经常深刻地意识到教育的问题,我们只需要记住《伊利亚特》中菲尼克斯教导阿喀琉斯的那一幕、品达的颂歌以及柏拉图的对话就可以了。贵族政治论者尤其怀疑教育是否能够普遍化。品达和柏拉图从未陷入过这样的幻想:即理性可以像物质材料一样以一种机械的方式进行分配;苏格拉底这个平民重新发现了传统希腊对人的无条件的可教育性的怀疑。请记住柏拉图第七封信中的那种极度无奈,在那里,柏拉图悲伤地谈到知识对人这个种类发生影响所受的局限,谈到促使他只对少数听众说话,而不愿向大庭广众讲道的原因。 [56] 不过,也请记住,尽管他们有种种怀疑,但构建并确切表述民族的一切高级文化理想的正是希腊的智识贵族;你也会认识到,希腊精神永恒的伟大和丰饶正是由教化天下的意志和对一种机械教育之可能性的怀疑之间的冲突所造就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基督教的罪感及其悲观主义文化观,和智术师的教育乐观主义二者都有容身之地。如果想要对他们的工作公正相待,我们就必须努力理解产生和制约其乐观主义的历史处境。即使当我们对它赞赏有加时,我们也不可能避免对它有所批评,[308]因为智术师的目标和成就在现代生活中仍然起着一种不可或缺的作用。
没有人比智术师的伟大批判者柏拉图更好地理解和描述了支配智术师视角的政治环境。他的《普罗泰戈拉》是我们必须常常回归的源头,因为它将智术师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技巧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了正面考察,且以无可争议的真实揭示了他们全部的社会和政治预设。当教育达到智术师开始从事教育活动的那种特定程度时,这些预设的前提总是不断地出现。对于一个智术师与另一个智术师所使用的教学方法之间的个体差异,柏拉图仅仅将其作为笑料来看待。他让三大智术师同台表现——阿布德拉的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 of Abdera)、埃利斯的希庇阿斯、开俄斯的普罗迪科(Prodicus of Ceos):他们都是雅典富翁卡利阿斯(Callias)家中的座上客,卡利阿斯将自己的家变成了名流学士的雅集之地。 [57] 通过这一策略,柏拉图得以表明,尽管智术师们性格各异各有千秋,但他们所有人都有一种显著的家族相似性。
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普罗泰戈拉。他承担着向一个出生良好的雅典青年传授政治德性的任务——这位名叫希波克拉底的青年恳求苏格拉底把他引荐给普罗泰戈拉;面对苏格拉底坦诚的怀疑态度,普罗泰戈拉解释了他为什么相信人在其社会性上是可教的。 [58] 他从公认的社会状态开始。没有人耻于承认他对任何一项需要特殊技能的技艺[如建筑、造船、航海]一无所知,但也没有人会公开承认自己犯了违法乱纪之罪,而是至少保持遵纪守法的样子。如果一个人想要摘下面具,公然承认自己是一个不法之徒和不义之人,人们就会认为他是发疯而非坦诚。因为我们都假定,人人都分有正义和常识。现在,政治德性可以习得的事实是从现行制裁制度得出的,现行的制裁制度惩恶扬善。我们不会谴责他人天生的缺陷,因为这不是他的奖罚之所在。社会用奖罚来激励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努力习得的良好品行。因此,法律惩罚的罪行必定可以通过教育来避免,[309]除非整个社会体系即将崩溃。普罗泰戈拉从惩罚的目的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拒绝传统希腊关于惩罚的因果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受]惩罚作为必须支付的报偿是因为 一个人犯了罪;他提出了一种显然是新的惩罚终结论,即惩罚是为了改善和威慑——它改善作恶者,而劝阻其他人。 [59] 这种关于惩罚的教育学解释依赖于人是可教的前提假设。公民德性是城邦的基础:没有它,就没有一个城邦共同体能够存在。任何不具备公民德性的人必须受教育、受谴责、受惩罚,直到他改过向善;如果他无可救药,那么就必须把他逐出城邦,或者干脆处死。所以,根据普罗泰戈拉的看法,不仅城邦的正义,而且整个城邦本身,就是一种整体的教育力量。更确切地说,以这种教育理论的严格逻辑说话,并通过这种理论来寻求自身合理性的,是当代城市国家(与他自己举的例子雅典一样)连同它对法律和正义的依赖。
执法意味着教育,此种作为国家职责的教育观念,似乎认为国家在对其公民的教育施加一种系统性的影响。但是,如前所述,除了斯巴达之外,没有一个希腊城邦实施过这种影响。但智术师显然从未提出过需要国家监管的一种教育,尽管从普罗泰戈拉的立场出发,他们应该很有可能这样做。通过给数量众多的个人提供教育,他们自己填补了国家教育的空白。普罗泰戈拉指出,每个公民从出生起,终其一生都在接受教育引导的影响:保姆、父母、教师,一言一行,都在教他和展示给他这个对、那个不对,这个好、那个不好,在塑造孩子的性格方面,一个胜似一个。就像整治一根扭曲变形的枝条,他们试图以威吓和惩罚使人的灵魂重回正轨。然后,他就可以去学校学习如何行为端正,阅读和写作,演奏竖琴。
当他度过这个阶段之后,老师就让他诵读优秀诗人们的诗篇并用心背诵。 [60] 这些作品包含许多道德训诫和颂扬好男儿们的故事,他们的榜样会感动孩子去模仿。音乐课程也会训练他节制,远离不良行为。接下来就要学习抒情诗人的诗作,他们的作品要配上音乐吟唱。[310]这些可以使孩子们的灵魂熟悉节律与和谐,让他们更温雅,因为人的一生都需要良好的节律与适当的和谐。实际上,节律与和谐必须由一个真正受过教育的人用全部言行来表达。 [61] 除此之外,还要送孩子去体育学校,教练员(paidotribés )会训练他的身体以便为健全的精神效力,这样他就不会因软弱而胆怯。普罗泰戈拉强调,富家子弟的学习时间远比穷人家的孩子要长,他们的孩子入学早而离校晚,由此他使自己的演说适合于出类拔萃的听众。 [62] 他想让大家明白,每个人都尽可能仔细地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因此,整个世界的一致意见(communis opinio )都认为人是可教的,而在实际生活中,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几乎从不吝啬、从不迟疑。
普罗泰戈拉并不认为当孩子离开学校时教育就结束了,这一点告诉我们新文化观的许多消息。在某种意义上,他认为此时教育才真正开始。当普罗泰戈拉断言在政治德性上教育人的是法律时,他的理论再次反映了关于城市国家性质的流行观念。一个公民真正的文化教育,是在离开学校进入积极主动的社会生活之后,城市国家强制他学习法律,并依照典范和榜样来生活( )。 [63] 这显然是将旧式贵族教育转化为新的公民教育的一个例子。自荷马以来,遵循高贵典范的观念一直支配着贵族阶层的教育。一个伟大的人物是学生必须遵循的规范和准则的物质载体,学生对这一人物的理想品格的钦羡自然会敦促他模仿先贤。当法律为人提供典范时,模仿(
)。 [63] 这显然是将旧式贵族教育转化为新的公民教育的一个例子。自荷马以来,遵循高贵典范的观念一直支配着贵族阶层的教育。一个伟大的人物是学生必须遵循的规范和准则的物质载体,学生对这一人物的理想品格的钦羡自然会敦促他模仿先贤。当法律为人提供典范时,模仿( )中的这种个人因素就消失了。在普罗泰戈拉所描述的毕业离校后的教育体系中,这种模仿并没有完全消失,只不过被转移到了一个较低的层次:它现在成了诗教中基础教学的一部分,只致力于内容的解释,强调它所体现的道德准则和历史范例,而不是强调发展精神上的节律与和谐的形式。但是,在法律所提供的范例中,规范性因素得到了保留,甚至加强,法律是每个公民最高级别的教育者;因为法律是现行道德标准最普遍和最后的表达。[311]普罗泰戈拉将依照法律而生活与孩子写字的初级课程相比较——孩子在学习写字时必须把字写在老师划定的界线之内。法律本身就是公民生活不可逾越的界线:古代伟大的立法者们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发明法律的。普罗泰戈拉已经把教育的过程比作修直一根长歪的枝条;现在,使一个逾越界线的人回归正道的惩罚,用法律的语言来说就叫euthyné,即矫直;智术师相信,法律的教育功能也在这里一目了然了。 [64]
)中的这种个人因素就消失了。在普罗泰戈拉所描述的毕业离校后的教育体系中,这种模仿并没有完全消失,只不过被转移到了一个较低的层次:它现在成了诗教中基础教学的一部分,只致力于内容的解释,强调它所体现的道德准则和历史范例,而不是强调发展精神上的节律与和谐的形式。但是,在法律所提供的范例中,规范性因素得到了保留,甚至加强,法律是每个公民最高级别的教育者;因为法律是现行道德标准最普遍和最后的表达。[311]普罗泰戈拉将依照法律而生活与孩子写字的初级课程相比较——孩子在学习写字时必须把字写在老师划定的界线之内。法律本身就是公民生活不可逾越的界线:古代伟大的立法者们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发明法律的。普罗泰戈拉已经把教育的过程比作修直一根长歪的枝条;现在,使一个逾越界线的人回归正道的惩罚,用法律的语言来说就叫euthyné,即矫直;智术师相信,法律的教育功能也在这里一目了然了。 [64]
在雅典,(如品达在一句当时经常被引用的诗中所言 [65] )法律不仅是国家的“君王”,而且是雅典的公民学校。我们现在不以这种方式来看待法律,也不相信法律是往昔伟大立法者的发现:它们是转瞬即逝之事,就像它们在雅典将要成为的那样,即使是法律专家,也不能全部了然于胸。我们几乎不能想象,这一切如何可能:当苏格拉底在狱中面临死亡,别人为他提供一个安全逃亡、重获自由的机会时,法律竟以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建议他在法庭审判时仍然忠于法律,因为它们教育和保护了他一辈子,是他全部生存的基础;普罗泰戈拉对法律作为教育者的描述使我们想起了柏拉图《克力同》中的场景。 [66] 他只是在构想他那个时代的法治国家的理想;即使他没有频繁地提到雅典,并解释说其教育理论的全部结构奠基于那种生活观念之上,我们本来也应该注意到,他的教育理论与雅典文化理想之间的亲缘关系。到底是智术师自己确实感觉到了这种亲缘关系,还是只是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中以生花妙笔自由模仿他的演说从而将其归之于他,要想断定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柏拉图本人总是觉得,智术师的教育体系直接来源于当时的实际政治环境。
普罗泰戈拉的所有言辞都旨在证明人在德性上是可教的。但是,智术师提出的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城邦与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假设,涉及到政治与道德常识,而且还涉及到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人的自然(human nature)的可教性问题,只是另一个问题——自然 与通常所谓的技艺 的关系问题——的一种特殊情况而已。[312]普鲁塔克在其《论儿童的教育》(On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中曾经对教育理论的这个方面有过启人深思的讨论。这篇作品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中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一次又一次地再版,其中的观念被现代教育者们接受并到处推销。在导论 [67] 中,普鲁塔克明确陈述了一个事实:他了解并利用了关于这一主题的早期文献。他利用这些文献并不局限于教育问题的特定一点,而是整个下一章的内容,在该章中,他讨论了教育的三个基本要素:自然[天赋]、学习和练习。非常清楚,普鲁塔克的思想建立在早期教育学理论的基础之上。
最为幸运的是,普鲁塔克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教育的三位一体”——它原本属于智术师, [68] 而且提供了对此问题的连续不断的讨论——它说明了智术师的文化理想的持久影响力。普鲁塔克的资料来源以农艺(agriculture)为例,说明了教育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农艺是为一特定目的,以人为的技艺培育自然[天赋]的主要事例。成功的农艺需要:首先是适宜的土壤,其次是技艺娴熟的农夫,最后是良好的种子。在教育中,土壤就是人的自然,教师对应于农夫,种子就是由言辞传授的教诲和劝告。当这三个条件都全部实现时,产品肯定非同一般的好。不过,即使一个资质略欠的自然[天赋]得到恰当的照料、教诲和练习,其缺陷和不足也能得到部分弥补;而另一方面,即使一个禀赋极高的自然如果疏于照料不加教导,也会被糟蹋掉。这就是使教育技艺不可或缺的事实。历经艰辛之后从自然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要强于自然本身。如果不加耕作,良好的土壤也会颗粒无收——实际上,自然禀赋越好,它会越加糟糕。不那么肥沃的土地,如果耕作适当,持之以恒,最终会产出珍贵的作物。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农夫的另一半工作,即树艺(arboriculture)。身体训练和动物驯养都是自然可以被教化的良好事例。重要的是,在正确的时机,最可培育的时机,开始工作——在人类身上就是孩提时期,那时人的自然还是柔韧易塑的,无论学什么都很容易,而且经久不忘,都会被心灵吸收。
[313]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在普鲁塔克的论证中区分开早期的因素和晚期的因素。他显然是将智术师的一些观点与智术师之后的哲学家们的学说混在了一起。因此,关于年轻人灵魂的可塑性( )的思想可能来自柏拉图; [69] 技艺可以弥补自然缺陷的这一想法出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70] 不过,这二者很可能首先是智术师们的想法。教育与农艺的鲜明对比看上去与教育的三位一体说联系如此紧密,它必定是智术师教育理论的组成部分。 [71] 这种比较在普鲁塔克之前就已经在使用了,因此必定可以追溯到一个更早的源头。它被译成拉丁文之后,进入欧洲思想并催生了“cultura animi [灵魂的培育]”这个新隐喻——正如土壤的培育是农艺,人类的培育是精神的培育。现代社会的“文化” 一词显然是原来那个隐喻的清晰回响。这些思想在后来的人文主义理论中复活,并促使文明国家或“文化”(cultured)国家从此之后高度重视智育(intellectual culture)理想。
)的思想可能来自柏拉图; [69] 技艺可以弥补自然缺陷的这一想法出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70] 不过,这二者很可能首先是智术师们的想法。教育与农艺的鲜明对比看上去与教育的三位一体说联系如此紧密,它必定是智术师教育理论的组成部分。 [71] 这种比较在普鲁塔克之前就已经在使用了,因此必定可以追溯到一个更早的源头。它被译成拉丁文之后,进入欧洲思想并催生了“cultura animi [灵魂的培育]”这个新隐喻——正如土壤的培育是农艺,人类的培育是精神的培育。现代社会的“文化” 一词显然是原来那个隐喻的清晰回响。这些思想在后来的人文主义理论中复活,并促使文明国家或“文化”(cultured)国家从此之后高度重视智育(intellectual culture)理想。
我们将智术师作为历史上首批人文主义者来描述,这种描述与他们创造了文化 的观念这一事实相一致,尽管他们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们的隐喻会远远超出单纯的教育思想,成为文明的最高象征。不过,这一文化观念的巨大成就有充分的理由:教学与农艺二者富于联想的比较表达了希腊文化一种新的普遍基础——通过人的意志和理性改进自然禀赋的一般规律的最高应用。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教育学和关于一种文明的哲学之间的联系——它归功于所有的智术师,但主要是普罗泰戈拉——是内在的和必然的。他们认为,在最广泛、最普遍的意义上,文化的理想是一个文明的顶峰,它包括从人把自己的意志加于原初自然的首次简单尝试,到人类精神最高级别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塑造的一切。通过将教育建立在如此广阔而深刻的基础之上,智术师再次揭示了希腊精神的真正本性:全神贯注于普遍的东西,即生活的整体 。如果他们未曾这么做,[314]文明的观念和文化教育的观念就不可能以一种如此可塑和富饶的形式而存在。
然而,无论为教育奠定一个深刻的哲学基础有多么重要,但将教育过程与农艺相比较本身仍没有多大价值。通过学习的方式渗透进灵魂的知识与种子和土壤的关系不是同一种关系。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自动生长的过程——教师可以根据他自己的意志引导和鼓励这个过程。我们曾经提到过教育的另一个相似物,即通过体操训练塑造身体的过程,这一塑造过程古老而规范,它为新的塑造灵魂的过程提供了一个显著的比较。正如希腊人在思考雕塑时认为,身体的训练如雕刻家雕琢他的石头,都是塑造身体的行为,现在普罗泰戈拉也将教育看作塑造灵魂 (shaping the soul)的行为,而且把实现它的手段看作一种构成性力量。 [72] 我们不能确然无疑地说,智术师是否将构造或塑造这样的特定概念运用于教育过程:原则上,他们的教育观念会非常认可这样的想法。因此,柏拉图是否是首个使用“陶冶 (mould, 即 )”一词来描述教育行为的人无关紧要。 [73] 诗歌与音乐的和谐与节律必须烙印在灵魂上,以便灵魂富于节律与和谐,塑造灵魂的观念内在于普罗泰戈拉的这一明确主张之中。 [74] 在那段文章中,普罗泰戈拉正在描述的不是他自己提出的教育,而是每个雅典人或多或少都在享受的教育,是雅典现有的私人学校提供的教育。我们可以认为,智术师的教学就是对这种教育的精心筹划,尤其是在教育体系核心的正式科目中。在他们之前,我们从未听说过文法、修辞和论辩术这些科目:因而肯定是他们的发明。新技艺显然是塑造智力的原则的系统表达,因为它以语言的形式、演说术的形式及思想的形式开始授课。 [75] 这种教育技艺是人的意识曾经做出的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直到意识探索这三项教育活动,意识才领悟到其自身结构的隐蔽规律。
)”一词来描述教育行为的人无关紧要。 [73] 诗歌与音乐的和谐与节律必须烙印在灵魂上,以便灵魂富于节律与和谐,塑造灵魂的观念内在于普罗泰戈拉的这一明确主张之中。 [74] 在那段文章中,普罗泰戈拉正在描述的不是他自己提出的教育,而是每个雅典人或多或少都在享受的教育,是雅典现有的私人学校提供的教育。我们可以认为,智术师的教学就是对这种教育的精心筹划,尤其是在教育体系核心的正式科目中。在他们之前,我们从未听说过文法、修辞和论辩术这些科目:因而肯定是他们的发明。新技艺显然是塑造智力的原则的系统表达,因为它以语言的形式、演说术的形式及思想的形式开始授课。 [75] 这种教育技艺是人的意识曾经做出的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直到意识探索这三项教育活动,意识才领悟到其自身结构的隐蔽规律。
[315]不幸的是,我们对智术师在这些科目中的伟大工作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文法方面的论文已经轶失了,尽管后来的文法学家们(逍遥学派和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曾将这些论文作为他们自己的著作的基础来使用。柏拉图的滑稽模仿告诉了我们普罗迪科对语义学的许多研究,而普罗泰戈拉对不同类型的词语的划分,以及希庇阿斯关于字母和音节的意义理论,我们也略有所知。 [76] 智术师的修辞学著作也都散失殆尽了:它们都是教学手册,无意于出版。阿那克西美尼的《修辞学》(Rhetoric)不足称道,靠从比它好的著作那里继承的观念取胜,但也透露了那些著作的一些内容。关于他们的论辩术,我们知道得多一点。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即普罗泰戈拉的《论相反论证》(Antilogies),已经轶失。不过,在一本名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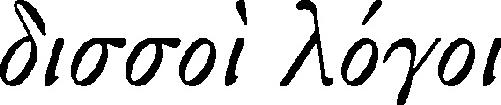 (即《两边都说》[Double Speeches ])的书中 [77] ——该书是公元前五世纪晚期一个不知名的智术师用多利安方言写就的——我们还可以管窥他们的“从两边说”的著名论辩技巧:也就是说,先批驳一个命题,然后再捍卫同一个命题。逻辑学是在柏拉图的学园中首次教学的;一些严肃的哲学家曾经批评过许多二流智术师变戏法似的争论术,认为它们毫无意义,柏拉图在《欧绪德谟》(Euthydemus )中对它们进行了滑稽模仿和讽刺,但它们证明了这种新的论辩技术起初主要是被看作演说家军火库中的一种武器。
(即《两边都说》[Double Speeches ])的书中 [77] ——该书是公元前五世纪晚期一个不知名的智术师用多利安方言写就的——我们还可以管窥他们的“从两边说”的著名论辩技巧:也就是说,先批驳一个命题,然后再捍卫同一个命题。逻辑学是在柏拉图的学园中首次教学的;一些严肃的哲学家曾经批评过许多二流智术师变戏法似的争论术,认为它们毫无意义,柏拉图在《欧绪德谟》(Euthydemus )中对它们进行了滑稽模仿和讽刺,但它们证明了这种新的论辩技术起初主要是被看作演说家军火库中的一种武器。
智术师所传授的正规教学科目的所有直接资料几乎完全缺失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主要根据这些资料对时人以及后世的直接影响来对其作出评判。其同时代人在演说中的无与伦比的技巧,在演说的结构处理上的胸有成竹,在证明过程中的论证和说服,在演说中阐述思想所使用的每一个方法——从对事实的简练叙述到最激动人心的情感铺陈,希腊的演说家们以那种大师的沉着自信所运用的全部手段——都应该归功于智术师。演说术,正如智术师所教导的,是“智力的体操”——在我们同时代人的演说和著作中难得发现的一门艺术。在阅读那个时期的阿提卡演说家的作品时,我们真正感觉到论证(logos)就是拳击场上赤膊上阵的搏击者。一个精心设计的证明,紧凑整齐而又灵活柔顺,就像一个训练良好的运动员的身体,结实强健而又伸缩自如。希腊人把一场诉讼或审判叫作搏斗 (agon),因为他们总是觉得这是两个对手之间以一种合法的形式进行的一场战斗。[316]现代学者已经表明,在智术师时代,希腊的辩护律师逐渐抛弃了传统的那种通过目击证人、刑讯拷问和赌咒发誓这样的证明方法,代之以逻辑论证这种新的修辞学证明方法。 [78] 即使修昔底德这样的史家,真理的最迫切的寻求者,在其演说技巧、句子结构、乃至遣词造句(即“正确措词[orthoepeia]”)上,都显然深受智术师的形式技艺的影响。 [79] 在古典时代晚期,修辞学是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它与希腊人对形式的强烈爱好如此相称,以至于它实际上就像一种爬行植物那样过度生长,覆盖了其他所有生物,从而毁灭了这个民族。不过,这一事实决不能影响我们对新发现的教育价值的判断。与文法和论辩术一起,修辞学成了整个欧洲的形式教育的基础。这三者在古代晚期叫“三学科(Trivium)”,与四学科(Quadrivium)一起构成“自由七艺”,从而正式组成了一个教育体系,它们比古代文化和古代艺术的其他一切优美与辉煌都经久不衰。时至今日,法国学校的上层阶级仍然有这些“学科”的名字,它们由依附于中世纪修道院的学校继承而来,因而象征着智术师文化连绵不断的传统。 [80]
智术师自己没有将这三门形式技艺与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相结合,构成后来的“自由七艺”体系。在这个教育体系中,“七”这个数字其实最无关紧要;将希腊人称之为数学 (mathemata)者(它从毕达哥拉斯时代起就包含和声学与天文学在内)包括在高级文化体系之内——它实际上是将三学科与四学科相加的关键环节——其实是智术师的工作。 [81] 在智术师之前,正如毕达哥拉斯对流行教育体系的叙述所表明的,音乐中只有实践教学的课程:它是由职业的里拉琴演奏者传授的。 [82] 智术师将毕达哥拉斯关于和声理论的学说加了上去;他们也通过将数学课程引入音乐教学改变了世界历史。在毕达哥拉斯学派中,数学一直是科学研究的一个主题。智术师希庇阿斯首先确认了数学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的无可替代的价值;其他智术师,如安提丰,还有他之后的布莱森(Bryson),[317]都教授和研究数学问题;自此之后,数学就从未丧失其在高级教育中的地位。
时至今日,作为由智术师创立的希腊高级教育体系,支配着整个文明世界。它被每一个国家所接受,尤其是因为它可以在没有一种关于希腊的知识的情况下被透彻理解和消化吸收。我们永远不可忘记,是希腊人不仅创造和阐述了普适的伦理和政治文化(我们在其中追溯到了我们自己的人文文化的源头), [83] 而且创造和阐述了人们称之为实践教育的东西(它有时是人文文化的竞争者,有时是人文文化的反对者)。我们在狭义上叫作人文主义的教育类型(它在缺乏一种关于希腊和拉丁的知识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只能在一种文明中出现——它本身不是希腊的,而是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一种文明,也即罗马文明。希腊与拉丁一起的现代教育体系,是由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首次完全实现的。我们以后还要研究它在古代晚期文明中的初步发展。
我们不知道智术师开出的数学课程的旨趣如何。对它的主要反对之一是数学在实际生活中一文不值。作为一种对哲学学习的准备,柏拉图自然将数学整合进了自己的教育体系。 [84] 这当然不可能是智术师教授数学的目的。然而,相信智术师认为数学只是对才智的一种形式训练,我们也不可能是正确的:尽管伊索克拉底——他本人就是智术师的修辞学的一个研究者——在反对了多年之后终于承认,在有限的程度上,数学对学习哲学还是有用的。 [85] 在他们的教育体系中,数学是实体因素,而文法、修辞、论辩术则是形式要素。后来的“自由七艺”划分为三学科与四学科,也提示智术师所教的课程分为两组互补的科目;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两组课程各自履行不同的教育功能。那些努力将它们结合起来的人是试图达到一种和谐的理想,或者,像希庇阿斯本人那样, [86] 达到一种普遍性的理想:不是简单地将一个与另一个相加产生一个统一体。即从表面上判断,包含天文学(那时它还不是一种严格的数学研究)在内的数学,仅仅只是作为一种对大脑的形式训练来传授,也是不可能的。[318]智术师好像没有承认数学在那个时代的实际生活中的无用是对其教育价值的一种决定性的反对意见。他们肯定羡慕数学和天文学作为一种纯粹理论的思维锻炼的价值。尽管其他人很少是富有成效的学者,但对希庇阿斯而言,肯定如此。因此,这是第一次对一种纯粹理论学科在才智培养中的价值的认可。这些理论学科与那种技术性的和实践性的学科在发展人的能力方面相当不同,文法、修辞和论辩术旨在促进人的实践能力的发展。学生由于数学知识的获得而加强了建构和分析能力,或者概括地说,是加强了纯粹思维的能力。智术师从未获得过产生这种效果的理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首次完全实现纯粹科学的教育意义的人。但是,我们必须因智术师准确无误的洞见而赞赏他们,这种洞见使他们为此目标选择了正确的学科训练,这种洞见也为后世的教育家所认可和推崇。
当理论科学一旦作为一种教育科目被引进,就有必要决定要学习它到何种程度。这个问题出现在那个时期的每一次有关科学教育的讨论中,出现在修昔底德、柏拉图、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这不是一个只由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我们到处都可以听到对这些奇怪的新学科的普遍反对声,为了这种远离日常生活的兴趣的纯粹智力学习,人们需要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在那之前,这种精神态度只出现在少数行为古怪的学者身上:他们对日常生活的兴趣的令人吃惊的缺乏、他们的独创性、既荒唐可笑又才华横溢,一直被待之以宽容、友好,甚至尊敬。 [87] 不过,现在不同了。理论科学声称自己是真正的、最高类型的文化,而且要取代或支配现行的教育科目。
主要的反对者不在劳动人民之中,他们自然不会对理论科学有任何兴趣——它是“无用的”、昂贵的,它意味着上层阶级。批判它的只能是统治阶级,他们一向拥有一种高级的教育和一整套固定的衡量标准,他们的美善(kalokagathia)理想、彬彬有礼的性格,即使在民主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中仍然存在。[319]对追求理论知识兴致勃勃的榜样,是由像伯利克里这样的大政治家和像卡利阿斯(Callias)这样的社会领导者——雅典最富有的人——树立的;许多声名卓著受人尊敬的家族打发他们的孩子去听智术师的演说。不过,要想对 [理论知识]威胁到了贵族阶层的理想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的。父亲们并不想让他们的孩子被教育成智术师。一些天资聪颖的学生跟随智术师,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旨在凭他们从智术师那里学到的东西谋得一官半职;但是,同样参加智术师讲座的雅典青年贵族,并不觉得他们的理想是值得追随的榜样:相反,它使他们认识到了自己与智术师之间的社会鸿沟(所有智术师都来自于中产阶级家庭),也使他们感觉到了智术师可能施加给自己的影响的局限性。 [88] 在伯利克里的阵亡将士演说中,修昔底德阐述了雅典城邦对新文化的态度:尽管他非常重视头脑的训练和培养,但他通过
[理论知识]威胁到了贵族阶层的理想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的。父亲们并不想让他们的孩子被教育成智术师。一些天资聪颖的学生跟随智术师,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旨在凭他们从智术师那里学到的东西谋得一官半职;但是,同样参加智术师讲座的雅典青年贵族,并不觉得他们的理想是值得追随的榜样:相反,它使他们认识到了自己与智术师之间的社会鸿沟(所有智术师都来自于中产阶级家庭),也使他们感觉到了智术师可能施加给自己的影响的局限性。 [88] 在伯利克里的阵亡将士演说中,修昔底德阐述了雅典城邦对新文化的态度:尽管他非常重视头脑的训练和培养,但他通过 [不要软弱]的提醒,以限制
[不要软弱]的提醒,以限制 [爱好智慧]:理想应该是“爱好智慧,但不因此而变得柔弱”的智力文化。 [89]
[爱好智慧]:理想应该是“爱好智慧,但不因此而变得柔弱”的智力文化。 [89]
这一警句表达了对智力训练的乐趣的一种严格限制,它使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的雅典统治阶级的态度一目了然。这使人想起柏拉图《高尔吉亚》中的“苏格拉底”(在此就是柏拉图本人)与雅典贵族卡利克勒斯(Callicles)之间的争论,两人就超然的学术研究对有志于政治的贵族的教育价值发生了争论。 [90] 卡利克勒斯激烈抨击这种观念:即知识本身就可以是一种人生目的,值得人们毕生奉献。他说,为了让年轻人在未成熟之前的危险时期远离不良习惯的危险,并训练他们的推理能力,那种纯粹的理论研究是有益的。一个在人生早期未曾对理论知识发生兴趣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自由人。 [91] 但是,另一方面,任何将一辈子都花费在封闭的空气中学习的人,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而是被拘束在了其发展的一个早期阶段之中。 [92] 卡利克勒斯划定了一条界线,人们决不能越过这条界线去从事理论学习,他说人们应该“因文化之故(for the sake of culture)”而追求理论知识——也就是说,作为对人生的一种准备,在某个特定阶段有限度地学习即可。 [93] 卡利克勒斯成了他那个阶层的典型。(我们在此不必在乎柏拉图对他的态度。)[320]整个上层阶级和雅典的中产阶级,对正在吸引自己孩子的新智识崇拜,或多或少都持卡利克勒斯的那种怀疑态度,唯一的区别是这个人与那个人之间的区别。我们会在后续章节讨论阿提卡谐剧对智术师的态度,这将是我们在此事上最重要的证据之一。 [94]
正如卡利克勒斯说的每一句话所表明的,他本人就是智术师的学生。但是,在他随后作为政治家的生活中,他学会了将自己所接受的智术教育服从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他引用欧里庇得斯的话,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所有问题。在他的《安提奥普》(Antiope)中,诗人介绍了两个彼此完全对立的当代典型——敏于行动的人与天生的理论家和梦想家;前者以卡利克勒斯现在对苏格拉底说话的相同语气对他的兄弟说话。众所周知,罗马诗人埃纽斯(Ennius)曾经模仿这部戏剧,并借阿喀琉斯之子、青年英雄涅奥普托勒摩(Neoptolemus)之口说,“可以进行哲学思考,但要少(philosophari sed paucis )”。 [95] 人们一向认为,罗马人——这些彻头彻尾地注重实践和政治的人——对希腊哲学和科学的态度已经由这句话给出了一个干脆利落的表达,好像它就是一种历史规律似的。然而,这句令许多现代的希腊爱好者(Philhellenes)坐立不安的“罗马短语”,其实原来是一个希腊人说的。它只是将雅典贵族对智术师和欧里庇得斯时代的新型科学和哲学的态度翻译成了罗马短语,同时也反映了罗马人对纯粹理论所持的相同冷漠态度。伯利克里时代的文明“只因文化[教育]之故”才决心从事哲学研究, [96] 它只在获致文化的范围内才是必要的:因为这种文明完全是实践的和政治的。它建立在雅典帝国的基础之上,志在统治全希腊。即使当柏拉图在雅典帝国没落之后宣扬“哲学生活”的理想时,也解释说它在建立城邦方面具有某种实际价值,从而证明其存在的正当性。 [97] 伊索克拉底在也其文化理想中,给予纯粹知识大致相同的地位。伊奥尼亚的科学只在逍遥学派、在雅典的伟大时光已逝之后的亚历山大里亚得到重生。智术师有助于填平雅典人与其远亲伊奥尼亚人之间的沟壑。[321]他们注定要赋予雅典智识的能力——这是她为了艰巨而复杂的使命所需要的——并让伊奥尼亚的知识为阿提卡的文化服务。
教育和政治危机
正当智术师构建文化理想之际,希腊城市国家也达到了其发展的顶峰。数个世纪以来,城邦规定了其公民的生活方式,各类诗人都称扬城邦的神圣秩序 (cosmos);但是,城邦教育其成员的义务此前从未得到过如此权威和全面的规划。智术文化不只是为实现一种实际政治的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的:它有意识地将城邦作为一切教育的目标,作为理想的标准。在普罗泰戈拉的理论中,城邦似乎是一切教育力量的源泉,或者,城邦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教育机构,它给全部法律和所有社会系统都烙上了相同的精神。 [98] 伯利克里的城邦观,如修昔底德在葬礼演说中所展示的那样,也在他的宣告中达到了高潮:城邦是伟大的教育力量,雅典的公共生活是城邦的文化使命的完全实现,是他人学习的榜样。 [99] 如此这般,智术师的思想穿透了实际政治领域:他们征服了整个城邦。没有任何一种对事实的其他解释是可能的。在其他方面,伯利克里和修昔底德表明他们都深受智术师见解的影响;因此,他们二人也必定是这种思想的借鉴者,而非创造者。当修昔底德将智术师关于城邦的教育观念与另一个新观念——新兴国家必为其本性所驱使去追求强权 ——相结合时,智术师的教育观获得了一种额外的重要性。古典时代的城市国家存在于权力和教育这两极之间的持久张力中, [100] 因为它们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尽管城邦教育其公民完全是为了其自身。当城邦为了其目的要求个体牺牲他自己时,它假设这些目的与共同体整体的幸福以及各个部分的幸福相一致。共同体的幸福及其各个部分的幸福必须由一种客观的标准来衡量。长期以来,希腊人一直认为这个标准就是正义,即diké。城邦的秩序,因而还有城邦的幸福,都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之上。[322]与此相应,普罗泰戈拉认为,以城邦为宗旨的教育就是正义的教育。 [101] 但是,正当人们得出这一结论之时,城邦的危机也应运而生,它也是教育最严重的危机。许多人因为这一发展结果而谴责智术师的影响,但只谴责智术师是对智术师影响的一种夸大。 [102] 智术师只不过是在教学中最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对当代的所有问题都格外敏感,因为教育总是对针对既定权威的任何攻击做出最强烈的反应。
梭伦曾以深厚的道德情感在城邦中宣扬正义的理想,这种道德情感在伯利克里时代余波犹存。城邦最大的骄傲是成为世间正义的捍卫者和遭受不公正压迫之人的保卫者。但是,即使在采用民主制度之后,超越法律和宪法的古老权力斗争仍然四处肆虐:现在,这种斗争在武器装备更新换代之后继续进行,而且远比质朴诚实的先辈能够想象的更野蛮、更不敬、更具毁灭性。确实存在着一种核心的观念,这种观念从希波战争起获得力量,直到占据主导地位:这就是民主政治的理想,数量上的多数拥有一切权力和决策权。这种理想以长期面临爆发内战的危险为代价,在激烈的冲突中赢得了胜利;伯利克里的家族是雅典的名门望族之一,但即使是伯利克里的长期的几乎未遭异议的领导权,也只是以民众权力的大规模扩大为代价才成为可能的。不过,在雅典民主制度的表层之下,在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贵族或者寡头们(正如他们的敌人称呼他们的)中间,仍然暗暗燃烧着难以扑灭的反叛火种。 [103]
实行民主制度的雅典,其对外政策在大政治家们的指引下,在伯利克里的最高指挥下,赢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贵族们仍然忠心耿耿,要不然就佯装忠诚,把为民众服务挂在嘴边,敷衍塞责,他们对这一套新技艺很快驾轻就熟,成为令人吃惊的行家里手——这套东西有时就变成了荒诞不经和滑稽可笑的伪善。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将雅典稳步上升的权力置于致命的终极考验之中,它动摇了政府的权威,继而是国家本身的权威,伯利克里逝世之后,争夺政治控制权的斗争剧烈恶化,最终到了闻所未闻、无所不用其极的激烈程度。[323]双方在党派斗争中都用上了智术师论辩和论证的全部武器;我们不能确切地断定,智术师依其政治信念注定会支持民主派,还是贵族派。即使普罗泰戈拉相信,现存的民主制度就是其全部教育努力之目标的“国家”,也会有民主制度的反对者——他们拥有并使用他们从智术师提供的训练中获得的武器。智术师当初锻造这些武器,本意并非用来对抗国家,但它们确实是危险的武器。比智术师的雄辩技艺更危险的,是他们关于法律和正义的本质的一般理论。这些理论使一向属于党派斗争的东西演变成一种理想信念的冲突,这种冲突威胁到社会和国家建立于其上的根本原则。
雅典的先辈们一直将法治国家作为一种惊人的成就来看待。狄刻是一位强大的女神,没有人可以攻击其统治的神圣根基而不受惩罚。地上的正义植根于天上的正义。这是全希腊的共识。当旧的威权政体变成新的建立在理性和法律基础之上的法治国家时,它也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内容,神圣的约束力仍然存在。实际上是正义女神接受了理性和正义的人类属性。但是,新法律的权威与旧的一样,依赖于它与神圣秩序的一致——或者,如新哲学家们所表述的那样,依赖于它与自然的和谐一致。自然已经成为一切神圣之物的总和。人尊之为最高道德标准的同一种法律和正义在自然之内施行统治。这就是有序整体 (cosmos)观念的起源。 [104] 然而,这种自然概念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演变过程中再次改变了。即使是赫拉克利特,也将有序整体看作对立面之间无休止的冲突:“战争乃万物之父”。世事流转,舆论变迁,秩序渐行渐远,唯冲突和斗争长存世间。现在,在各种机械力量的相互作用中,宇宙被设想为盲目冲动和优势权力的偶然产物。
到底是先有这种自然观,然后被运用到人类世界之中,还是人将新的“自然主义”人生观普遍化,再将其作为一种永恒的法则投射到了自然之上?乍一看来,要想断定这一点殊为不易。在智术师时代,新旧观念紧密交织。在《腓尼基妇女》(The Phoenician Women)中,欧里庇得斯将民主制度的基础(即平等)[324]描述为自然中天日昭彰的法则,法网恢恢,无人可逃。 [105] 然而,与此同时,也有人攻击被民主派人士接受的平等理论,认为自然从来就未曾被机械的均平 (isonomia)所支配,而是由弱肉强食的法则所支配。无论哪种情况,显然都是从人的视角来看宇宙及其结构,都是根据一套特定的假设来阐释宇宙及其结构的:它们实际上是一种贵族的自然观和一种民主的自然观。贵族的新观念表明,有一种人的数量在不断增长:他们不羡慕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几何学上的平等,而是突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天然不平等,而且让这一不平等的事实成为他们全部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基础。与其先辈一样,他们向世界的神圣治理诉求权力,而且以有了最新的哲学和科学理论的支持而自命不凡。
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中,在不可磨灭的人物形象卡利克勒斯身上,新原则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106] 他是智术师的一名虔诚的学生:他的观点来源于智术师的教导,正如《王制》第一卷所表明的,强者的权利得到了智术师和修辞学教师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的支持。 [107] 一概而论会歪曲历史的真相;我们很容易举出一个不同类型的智术师:他的哲学与柏拉图与之搏斗的自然主义理论截然相反——他是传统道德体系的宣扬者,只是将格言诗形式的道德准则译成了散文。但是,卡利克勒斯类型的人更加有趣,正如柏拉图所描述的,也远为强大。在雅典的贵族阶层中必然有许多像卡利克勒斯那样的强人:柏拉图从年轻时起就对他们了如指掌。克里提亚是主张寡头政治的保守派的肆无忌惮的领导者,后来成为“僭主”,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柏拉图可能从他那里借鉴了一些性格特征或者一种相似的志趣,用在虚构的人物卡利克勒斯身上。 [108] 尽管柏拉图从根本上来说反对卡利克勒斯的观点,但他仍以一种安之若素和意气相投的态度将它们陈述出来,就像一个人已经在他自身内压制住了它们,或者就要压制住它们那样。在柏拉图的第七封信中,他说他本人就被克里提亚的追随者们认为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战友和党羽,[325]这显然不仅仅是由于他与政治寡头们的私人关系;他说他一度对他们的政策持同情态度。 [109]
普罗泰戈拉意义上的教育——也即本着传统的正义理想的教育——遭到了卡利克勒斯慷慨激昂的诚挚批评,这批评使人深刻地认识到他重估一切价值的全部力量。雅典国家及其公民视之为最高正义者,于他而言,乃是不义的深渊。 [110] 他喊道:
我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在我们中间锻造出最优秀、最强大的人,趁他们还年幼时,把他们像狮子一样抓来,用符咒迷惑和奴役他们,告诉他们每个人都必有平等的权利,而这就是高贵和正义的含义。不过,在我看来,如果有人生来就真正强大,他肯定会冲破牢笼,打碎枷锁,摆脱一切控制,践踏我们的文字和咒语,以及一切非自然的法律和习俗,他会站起来成为我们的主人,而以前他是我们的奴隶;然后闪耀出自然正义的光辉!
由此看来,我们的法律和习俗是一种人为的枷锁,是组织起来的弱者约定俗成的规矩,以压制他们天然的主人(即强者),并迫使其按照他们的意志来行动。自然的法则与人为的正义正好相反。按照自然法的标准,平等主义的国家称之为法律和正义者,恰恰是肆意妄为的专制强权,纯之又纯,彻头彻尾。在卡利克勒斯眼里,那种人为的法律是否应该被遵从,端赖一个人反抗法律的力量有多大。无论如何,他在被设想为等同于现存法律的正义观念中看不到任何内在的道德权威。这就是来自一位雅典贵族的革命口号。实际上,公元前403年雅典战败后的武装政变(coup d’etat )就是受到卡利克勒斯精神的启发。
我们必须了解卡利克勒斯的这些话见证的知识革命的全副景象。要想从我们自己的时代出发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是不可能的,因为尽管那种看待国家的特定态度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必然会导致国家权威的瓦解,但是,在政治生活中强者应该统治的信念,在今天,并不就是在私人生活中的道德无序状态的宣言。且不论是非对错,我们现在都相信,政治和道德是两个独立的领域,不必由同一套行为准则来治理。没有任何一种试图填平二者之鸿沟的理论尝试可以改变以下历史事实,即我们的道德观可以追溯至基督宗教,而我们的政治观则可以追溯至希腊-罗马的国家观念,因此,它们来自不同的道德源泉。[326]这种两分的忠诚为两千年来的习俗所检验,是现代哲学家们试图将其转化为一种优秀品德的必然需要;但是希腊人从未如此。我们总是把政治道德看作个人道德的一种尖锐对比:实际上,我们许多人宁愿将其写成带引号的政治“道德”。不过,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实际上是整个城邦文明时期的希腊人——都认为政治道德和私人道德事实上完全是同一回事:因为城市国家是一切道德标准独一无二的源泉,而且,除了国家的行为准则——个体生活于其中且只有在其中才有其存在的城邦共同体的法律——之外,要想看到其他道德准则的存在是很困难的。一种纯粹私人的道德准则,一种无关乎城市国家的道德准则,对希腊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在此必须忘却自己的那种观念,即各个个体的行为是由其自身的良知主导的。希腊人也这样想,不过是在后来,在一个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时期。 [111] 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国家的法律是人的生活的最高准则,它与宇宙的神圣治理相一致,在此情况下,人是城邦的一个公民,不多,也不少;要么,国家的准则与自然或神的既定法则相冲突,因而人不能接受它,在此情况下,他就不再是政治共同体的一员,而他的生命的根基也就坍塌了,除非他能够在自然的永恒秩序中找到某种确定性。
当这样的鸿沟出现在宇宙的法律和城邦的法律之间时,希腊思想已经离希腊化时期的世界主义不远了。实际上,已经有一些智术师从他们对城邦法律(nomos)的批判中推论出唯一有效的法律是宇宙的法律;他们是最早的世界主义者;从各方面看,他们与普罗泰戈拉属于不同类型的智术师。柏拉图在他和普遍主义者埃利斯的希庇阿斯之间进行了鲜明的对比。他让希庇阿斯说:“先生们,根据自然,而非根据法律,我认为你们都是亲人、朋友和伙伴。因为根据自然,同类相联,但是法律这一人的专制统治者却强迫许多事物彻底与自然背道而驰。” [112] 这就是卡利克勒斯在《高尔吉亚》中使用的法律与自然(即nomos和physis)之间的对比,不过,卡利克勒斯和希庇阿斯两人,尽管都批评人为的法律,[327]但从不同的要点开始,且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无论如何,两人都从攻击现行的平等观念开始——平等观念是传统正义观的实质——但卡利克勒斯针对民主制度的平等理想反对实际现实,认为人凭自然就是不平等的, [113] 而智术师和哲学家希庇阿斯则觉得,民主制度的平等太过局限,因为它只对自由民的平等特权和一个城邦内部的相似血统有效。他但愿平等和亲情扩大到普天之下的所有人。雅典的智术师安提丰也在其理性主义论文《论真理》(Truth)中表达过相同的观点——最近在埃及发现了《论真理》的相当数量的残篇; [114] “实际上,根据自然,无论是希腊人,还是蛮族人,我们生来都是一样的”。安提丰为废除一切植根于历史的民族差异提供的理由,以其天真的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与卡利克勒斯对不平等的狂热信仰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他继续说:“自然给予一切人以应有的补偿,这是人人都看得到的;所有的人也都有能力获得这种补偿。在这些方面不可能像区分希腊人和蛮族人那样作出区分;我们大家都用嘴和鼻子呼吸,都用手拿吃的东西。”这种国际间的平等确实离希腊民主政治的理想非常遥远,同时与卡利克勒斯对他们的抨击形成极端的对比。安提丰不仅以无情的逻辑废除了国家间的差别,而且也取消了社会差别,“我们尊重那些出身高贵的家族并给他们荣誉,但对那些出身低贱的人却既不尊重,也不给予荣誉,我们这里是这样,我们的邻人蛮族人也是这样”。
就实际政治而言,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论对现存政权和政治体制算不上什么危险,尤其是这些理论创造者既不在大量民众中寻求支持,也没有在民众中发现支持,他们只在一个开明听众的小圈子里自说自话,这些听众的信念多数是卡利克勒斯式的。然而,现存政体受到这种哲学坦诚的自然主义论调的间接威胁,它通过将这种哲学的标准严格地运用到所有人类生活之中,正在削弱现有道德规范的权威。早在荷马的史诗中,我们就可以找到自然主义的蛛丝马迹,这种自然主义思想总是能够与希腊的心灵产生共鸣。希腊人具有一种天生的将事物作为整体来看待的能力:这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328]因为不同的人都可以看这同一个整体而且对其做不同的阐释。有人将世界看作英雄壮举的舞台,召唤高贵者施展其最高权力;有人将世界看作一个川流不息的“自然”进程。有人英雄豪迈,视死如归,人在盾在,盾亡人亡;有人苟且偷生,丢盔弃甲,盾牌丢了再买一个,因为他珍惜生命胜过皮革。当世国家对其公民的行为准则和自我牺牲精神提出了巨大要求,而这种要求的正当性是由城邦的神圣性来核准的。但是,那个时代对人类行为的分析导致了一种纯粹偶然的和自然主义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强调人们天生喜欢的事物与不喜欢的事物之间,以及城邦法律命令人们喜欢的事物和不喜欢的事物之间的无休止的冲突。安提丰写到,“绝大多数法律的指令与自然为敌”,他又称法律是“自然的锁链”。这种看法对城邦的正义观、对传统的法治国家是严重的威胁。“所谓正义,就是不要违反你身为其中一分子的城邦的法律。” [115] 即使是表述法律的措辞方式的变化,也被认为是法定的标准从来就不是绝对不变的证据。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一套不同的法律。如果你想生活在一个国家,就必须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但法律并没有绝对的打动人心的力量。因此,法律被设想为一种外在的任何人都不得违反的强制规范,而非从人心中自发生长出来的一种道德和社会准则。但是,如果法律缺乏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精神动力,那么正义就只是外在的合法性,只是对违法乱纪所招致的惩罚的逃避,倘无证人在场,人们就懒得劳心费力去遵纪守法,没有必要顾全面子。实际上,在安提丰看来,这正是法律标准与自然标准本质上各不相同的地方。即使没有证人在场,人们也不能违背自然的法律而不受惩罚。在对待自然法则时,人们必须不仅顾全“面子”,还要尊重“真理”,智术师安提丰的说法明显是对其著作标题的暗示。因此,他的目的就是表明人为的法律标准的相对性,证明自然法则才是唯一真正的法律。
这一时期,希腊民主制度越来越受到用法律来解决人类生活全部事务的激情的支配。当一部新的法律产生时,现存的法律就被不断地改变或废除;[329]后来,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这种情况做了概括, [116] 他裁断说,对国家而言,拥有长期稳定的次等法律,也比朝令夕改好,即使新法是良法。批量制造的法律以及它们产生的党派纷争,连同因此发生的一切罪恶与愚蠢,给思想者们留下了极为痛苦的印象,这使他们很容易接受相对主义。安提丰对法律法规的反感与厌恶,与当时的公众意见不谋而合,也与整个时期的普遍倾向完全一致——我们只需要想一想阿里斯托芬笔下的人物就可以了,他来贩卖议事会的最新法令,却在一片响亮的喝彩声中被饱揍了一顿。 [117] 最彻底的民主派人士的理想,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你想怎么活,就可以怎么活”。在对雅典政制的描述中,伯利克里本人也本着同样的精神说,在雅典,对法律的普遍尊敬不会妨碍任何人在私人生活中满足自己的突发奇想,也不用在意他人难看的脸色。 [118] 但是,这种政治生活中的严肃与私人生活中的宽容之间的微妙平衡,尽管在伯利克里的演说中如此富于人性,听起来如此真实可靠,却并不是所有人的理想。当安提丰说人类行为的自然标准是有益的、最终也是享受或快乐时,他的无限制的坦诚所表达的,可能是大多数公民同胞内心深处的隐秘情感。 [119] 这就是后来柏拉图选择攻击的要点,以便为共同体的重建奠定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当然,并非所有的智术师都如此坦率地宣扬享乐主义和自然主义,并一概接受其原则。普罗泰戈拉不可能这么做,因为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当苏格拉底试图引诱他走上薄冰时,他明确否认曾经持有这样一种理论;苏格拉底精妙的对话技巧只是让善良的老人相信,他确实给他已经拒绝的享乐主义留下了一个仍然可以悄悄混进来的漏洞。 [120]
[330]这种折中肯定是那个时代所有最精致的大脑的共同特征。安提丰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是他的自然主义具有合乎逻辑的优点。他在人们在有人见证时的所为和无人见证时的所为之间作出的区分,暴露了当时的道德观念的核心问题。发现一种新的道德行为的基础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因为只有从那里,法律才能获得它所需要的新力量。服从法律的朴素观念,在民主法治国家形成时,曾经是自由和进步的伟大理想, [121] 但现在它已经不足以表达希腊人更深层的道德情感了。与所有得到法律认可的道德准则一样,它陷入了使人的行为成为一种纯粹外在的遵守的危险,甚至是反复灌输一种精心编织的、虚伪的社会道德体系的危险。埃斯库罗斯曾经把真正聪明和正直的人叫作“那希望不是看起来像好人而是确实是好人的人”; [122] 他的听众应该想到了亚里斯泰迪。雅典人中最伟大的人必定充分理解这种危险。但是,当时流行的正义观念无非是对法律的正确遵守,遵守法律的人们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害怕会受到惩罚。法律的深层道德基础的最后一个支撑是宗教,但宗教本身也遭到了理性主义者的大胆攻击。克里提亚,这个未来的僭主,写了一部剧作《西西弗斯》(Sisyphus),其中一个人物在舞台上公开说,诸神不过是政治家们的一种聪明发明,目的是使他们的法律得到尊敬。 [123] 他宣称,为了让人们在无人注意时不违法乱纪,政治家们就告诉人们,诸神无形无像,无处不在,无所不知;通过让人害怕这种看不见的力量,他们使人臣服于自己脚下。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柏拉图在《王制》中虚构了巨吉斯(Gyges)的魔戒这一神话,这枚戒指有让带上它的人隐身的魔力。 [124] 这枚戒指能够区分因其灵魂正直而行事正义的人与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后者只是装出尊重社会规则的样子。柏拉图试图解决安提丰和克里提亚提出的问题。德谟克利特也一样,他将一种新的意义赋予希腊传统的aidos (即隐秘的羞耻)观念,并以一种人们因自己而感觉到的羞耻观念取代那种人们因为法律而感觉到的aidos 观念——这种羞耻感已经被诸如安提丰、克里提亚、克里克勒斯等智术师的批判彻底摧毁。 [125]
但是,无论是希庇阿斯和安提丰,还是卡利克勒斯,都没有任何重建当前道德规范的想法。在他们身上没有一丝要想真正解决宗教和道德的终极问题的痕迹。智术师关于人、国家和宇宙的看法,没有任何严肃性和形而上的理解——这种严肃性和形而上的理解使他们的前辈建立了雅典城邦,[331]而他们的后辈即将在哲学中重新发现它们。然而,如果我们想要在哲学和伦理学领域寻找他们的真正成就,那就错了。他们的长处在于他们建立起的杰出的形式教育体系,他们的弱点在于他们学说的智识和道德基础[的缺失],但这一特点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所共有。艺术的灿烂和国家的强盛,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对威胁那个时代的严重道德危机视而不见。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伟大时代,对教育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需求,而天才杰出的教育家们会应运而生,来满足这种需求,这是自然而然且不可避免的。然而,这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个时代会认识到,它缺乏一切教育力量中最伟大的的东西:尽管它才华横溢,但它没有最弥足珍贵、最必需的天赋,即一个引导他们的理想。
[1] 埃斯库罗斯,《七将攻忒拜》(Sept. ),第18行;亦可参看品达,残篇19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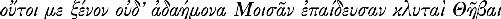 [光荣的忒拜人曾教我,不要对缪斯们陌生,也不要对缪斯们无知],这一残篇是以下事实的重要证据,即在品达和埃斯库罗斯的时代,即使在希腊中东部地区的波奥提亚(Boeotia),“
[光荣的忒拜人曾教我,不要对缪斯们陌生,也不要对缪斯们无知],这一残篇是以下事实的重要证据,即在品达和埃斯库罗斯的时代,即使在希腊中东部地区的波奥提亚(Boeotia),“ [教育]”一词就已经包含了音乐(当然还有体育)文化的意义,它构成了伯利克里时代文化的主要内容,参见本书第三卷,此处,注释[81] 。
[教育]”一词就已经包含了音乐(当然还有体育)文化的意义,它构成了伯利克里时代文化的主要内容,参见本书第三卷,此处,注释[81] 。
[2] 参见本卷“荷马时代贵族阶层的文化和教育”一章。
[3] 参见本卷“城市国家及其正义理想”一章。
[8] 译注:第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公元前525—前460年),雅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公元前493—前492年任执政官,为民主派重要人物,力主扩建海军,并着手兴建比雷埃夫斯港及其联接雅典城的“长墙”,旨在抵御波斯侵略。公元前480年,海军统帅第米斯托克利指挥希腊海军,将大约六百艘波斯军舰诱入雅典城外的萨拉米斯湾,予以一举歼灭,从而为雅典建立了之后一个世纪的海上霸权。战后,第米斯托克利的个人声望和权力达到顶峰,雅典人害怕出现一个军事强人独裁者,遂以陶片放逐法将其放逐;走投无路之际,老对手薛西斯收留了他,并赐予他小亚细亚一块封地。公元前460年,薛西斯任命第米斯托克利为舰队司令与提洛同盟舰队作战,这一任命使第米斯托克利进退两难,最终他用一杯鸩酒为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划上了句号。第米斯托克利是民主制社会杰出个人(智识人格)与城邦共同体发生冲突的典型案例。前有第米斯托克利,后有苏格拉底,所以作者在上文中说:“这个问题无休止地困扰着哲学家们,直到希腊城市国家寿终正寝。”
[9]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38.3。
[10] 赫西俄德,《神谱》,第81行及以下。
[11] 关于智术师的职业,参见本书第二卷,第三卷。
[12] 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6。
[13] 教育的百科全书式的理想,在埃利斯的希庇阿斯(Hippias of Elis)那里得到了更具体的体现。开俄斯的普罗狄科(Prodicus of Ceus)开办了文法和语言研究班,比如著名的“同义词研究”,在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339e—341e、358a中,苏格拉底对此进行了表扬,同时也对此进行了滑稽模仿。普罗狄科与普罗泰戈拉一样具有这些形式方面的兴趣。
[14]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25e以下。在318e中,柏拉图让普罗泰戈拉自己在其教育理想和埃利斯的希庇阿斯的百科全书式的教育理想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
[15] 贡珀茨(H. Gomperz),《智术与演说术:公元前五世纪与哲学关系中的雄辩教育理想》(Sophistik und Rhetorik:das Bildungsideal des  in seinem Verhaeltnis zur Philosiphie des fuenften Jahr hunderts ),Leipzig,1912。
in seinem Verhaeltnis zur Philosiphie des fuenften Jahr hunderts ),Leipzig,1912。
[16]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18e及以下;《美诺》91a及以下,以及其他各处。
[17] 柏拉图,《泰阿泰德》152a。
[18] 参见本卷“哲学的沉思”一章。
[20] 关于阿那克萨哥拉在早期自然哲学家和苏格拉底之间的地位特征,参见柏拉图,《斐多》(Phaedo )97b。
[21] 恩培多克勒本人就是一个自然哲学家,即使在《论自然》(On Nature )一诗中,他也比之前的思想家们更多地关注人的身体的结构,参见比格农(Ettore Bignone),《恩培多克勒》(Empedocle ),Torino,1916,第242页。不过,另一首诗《论净化》(Purifications )表明,这不是恩培多克勒的全部,与人的身体结构相比,他更深地专注于人的心灵问题。参见比格农,《恩培多克勒》,第113页及以下。
[22] 参见纳托尔普(Paul Natorp)的《德谟克利特的伦理学》(Die Ethika des Demokrit ,Marburg,1893)一书,以及朗根贝克(Hermann Langerbeck)上的 一文,载《新语文学研究》,耶格尔编,第十卷,Berlin,1935。
一文,载《新语文学研究》,耶格尔编,第十卷,Berlin,1935。
[23] 在这方面,只有德谟克利特是一个例外,参见朗根贝克上引论文第67页及以下,他离智术师关于人性和教化问题的理论途径最为接近。
[24] 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316d中,把普罗泰戈拉描绘成完全意识到了此种连续性的大智术师。当然,普罗泰戈拉此处只是把过去的诗人看作一群早期的智术师、看作他自己的先行者来谈论。然而,毫无疑问,这里面也反映了一些历史的真相:即智术师是诗歌这一伟大教育传统的继承者。伊索克拉底也一样,他是智术师的名副其实的学生,在其演说艺术中,将赫西俄德、福西里德斯和泰奥格尼斯称作前辈(《致尼可克勒斯》[Ad. Nic. ]43)。
[25]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39a。
[26] 参见拙文《提尔泰奥斯论真正的德性》,载《柏林科学院会议报告》,1932,第564页。
[27]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39a以下中,有一个关于这种态度的有趣事例。在《王制》331e以下中,苏格拉底举了另一个例子。
[28] 柏拉图,《王制》598d,描写了智术师对荷马的此类解释,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及注释。
[29] 柏拉图,《小希庇阿斯》(Hipp. Min. )368b。
[30] 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关于智术师及其与社会和财富的关系,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
[31]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13c。
[32] 有许多学者认为,智术师不仅是人文主义的奠基者,而且也使人文主义臻于完美,换句话说,这些学者想把他们树立为我们的典范。我们在这些事情上的意见,依赖于我们看待哲学的态度,哲学实际上是从与智术师的教育类型的冲突中生长出来的,尤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这种冲突来源于什么是最高价值的问题——根据希腊“哲学”,人的教育问题决定于价值问题。参见拙著《人文主义和神学》,第38页及以下,在该书中,本人已经区分了两种相互对立的人文主义的基本形式——智术师的人文主义和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人文主义。关于普罗泰戈拉的人文主义,参见拙著《人文主义和神学》,第300页。
[33] 柏拉图的《大希庇阿斯》(Hipp. mai. )218c清楚地表明了,智术师的实用目的与传统哲学家和圣贤的非实用倾向之间的区别。
[34] 参见巴斯(A. Busse),《教育科学的开端》(Die Anfaenge d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 ),载《新年鉴》(Neue Jahrbuecher ),xxvi,1910,第469页及以下;以及贡宁(C.P. Gunning),《论作为希腊之教师的智术师》(De sophistis Graeciae praeceptoribus ),Amsterdam,1915。
[35]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19a。
[36] 赫西俄德,《劳作与时日》,第276行。
[37] 参见侯尔(Karl Holl),《“职业”一词的历史》(Die Geschichte des Worts Beruf),载《柏林科学院会议报告》,Berlin,1924。
[38]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18d。针对埃利斯的希庇阿斯,普罗泰戈拉将算术、天文、几何、音乐(这里指音乐理论)包括在技艺(technai )的范围之内。
[40] 参见拙著《人文主义和神学》,第20页及以下(参见本卷此处,注释[33] );亦可参见拙文《古代文明和人文主义》(Antike und Humanismus)和《文化观念与希腊人》(Kulturidee und Griechentum),收录于《人文主义演说集》,第110页和第125页及以下。
[41] 参见本卷此处,注释[33] ;以及本书第二卷、第三卷,关于教化(paideia)发展进程的描述。
[42] 柏拉图,《法义》716c;参见普罗泰戈拉残篇1(第尔斯本)。
[43] 普罗泰戈拉残篇4(第尔斯本)。
[44] 参见拙著《人文主义和神学》,第36页及以下。
[45] 目前暂且参见拙著《人文主义和神学》,第58页及以下。我希望在一部独立的著作中来讨论古代晚期,古典希腊的教化理想与新的基督宗教在古代晚期融合在了一起。译注:耶格尔后来写了《早期基督教与希腊教化》(Early Christianity and Greek Paideia )一书,已有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2016,吴晓群译)。
[46] 参见拙著《人文主义和神学》,第39页及以下。译注:关于“它就选择人的形式(form)作为它的标准:它也就成了形式的(formal)教育”,参见本卷此处注释[76] 和此处 的内容。
[47] 参见拙著《人文主义和神学》,第42页及以下,第53页以下。
[48] 参见拙著《人文主义和神学》,第47—54页。
[49] 译注:耶格尔认为是柏拉图及其哲学给出了希腊文化的最终形式。
[50] 关于普罗泰戈拉论存在的论文的一个复制本,波菲利(Porphyry)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参见普罗泰戈拉残篇2(第尔斯本)。
[51] 译注:希腊语“epideixis”意为“展示”。“deixis”,即“用手指给大家看”;“apodeixis”则指哲学家要干的事,意即“说明、解释原因、证明”。
[52] 参见本卷“贵族阶层:冲突与转形”一章。
[53] 参见来自普罗泰戈拉,《大论》(Great Logos )残篇,普罗泰戈拉B3(第尔斯本)。我们可以在柏拉图、德谟克利特、伊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类似的区分。译注:此处的“自然(nature, )”和“第二自然”译为“天性[本性]”和“第二天性”较为合适,但为说明该词的原始意义,此处仍译为“自然”和“第二自然”;下文中的human nature或译为“人的自然”,或译为“人性”;智术师说的human nature字面上也可理解为“人性”,但不能把他们说的“人的自然”与修昔底德、苏格拉底、柏拉图所强调的社会道德本性相混淆。
)”和“第二自然”译为“天性[本性]”和“第二天性”较为合适,但为说明该词的原始意义,此处仍译为“自然”和“第二自然”;下文中的human nature或译为“人的自然”,或译为“人性”;智术师说的human nature字面上也可理解为“人性”,但不能把他们说的“人的自然”与修昔底德、苏格拉底、柏拉图所强调的社会道德本性相混淆。
[54] 现在迫切需要对包含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的“人的自然”的思想做一种新研究,参见本书第三卷“作为教化的希腊医学”一章。
[55] 十七、十八世纪,以人性观为中心的科学思想有了平行的发展。参见狄尔泰(W. Dilthey),《世界观与人的分析》(Zur Weltanschauung und Analyse des Menschen),收录于(《论文集》[Schriften ],第二卷。
[56] 柏拉图,《书信》7.341d。
[57] 参见本书第二卷,“《普罗泰戈拉》”一章。
[58]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23a及以下。
[59]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24a—b。
[60]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25e。
[61]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26a—b。
[62]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26c。
[63]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26c—d。
[64]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26d。
[66] 柏拉图,《克力同》(Crito )50a;参见《普罗泰戈拉》326c。
[67] 普鲁塔克,《论儿童的教育》。
[69] 柏拉图,《王制》377b。
[70] 本人从新柏拉图主义者扬布利科(Iamblichus)的《劝勉篇》(Protrepticus )中重构了亚氏已经遗失的《劝勉篇》中的这个部分——亚氏在其中发展出了艺术可以弥补自然缺陷的思想,参见拙著《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第74页及以下。
[71] 教育与农艺的比较也出现在“希波克拉底文集”的《法则论》(Law )3中。但是,由于其起源日期不可知,所以在年代确定方面对我们帮助不大。《法则论》似乎是智术师时代的产物,或者出现在智术师时代之后不久。
[74]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26a—b。
[75] 译注:grammar(语法、文法),希腊文原意是“语言的技艺”;rhetoric(修辞学),希腊文原意是“言说的技艺”,用于辩论时也叫演说术或雄辩术;dialectic(论辩术),希腊文原意是“对话”,两人反复论辩,所以也叫辩证法。关于“以语言的形式、演说术的形式和思想的形式开始授课”,可参见本卷此处,注释[46] 。
[76] 少量证据收集在《前苏格拉底残篇》(第尔斯本)中:普罗迪科A 13及以下,普罗泰戈拉A 24—28,希庇阿斯A 11—12。
[77] 《对言》(Dialexeis )8提到斯巴达对雅典及其盟邦的胜利,以及胜利对两边的后果,也就是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局。译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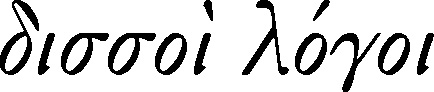 ,Double Speeches,“两边都说”“两边都论证”;智术师认为对一切事物而言都存在着两种相反(但都又讲得通)的说法,所以智术师可以同时论证两个相反的命题;这一原则后来发展为Dialexeis,即“对言”的观念。参见刘亚猛,《言说与秩序:轴心时期中西语言思想的一个重要区别及其当代意义》,载《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Double Speeches,“两边都说”“两边都论证”;智术师认为对一切事物而言都存在着两种相反(但都又讲得通)的说法,所以智术师可以同时论证两个相反的命题;这一原则后来发展为Dialexeis,即“对言”的观念。参见刘亚猛,《言说与秩序:轴心时期中西语言思想的一个重要区别及其当代意义》,载《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78] 参见索尔姆森(F. Solmsen),《安提丰研究》(Antiphonstuien),载《新语文学研究》,耶格尔编,第八卷,第7页。
[79] 芬利(J.H. Finley),《修昔底德》(Thucydides ),Mass. Cambridge,1942,第250页及以下。
[80] 古代艺术(artes )继续存在于耶稣会士的《课程计划》(ordo studiorum )中。“自由艺术”一词相当有活力,在美国用来指“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尽管其内容已经现代化了,而“博雅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则是与实用主义和专业主义的教学法相对应的一种特殊学院。
[81] 参见希庇阿斯残篇A11—12(第尔斯本)。
[82]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26a。
[84] 柏拉图,《王制》,536d。
[85] 《论财产交换》(Antid. )265;《泛雅典娜节演说辞》(Panath. )26。
[86] 柏拉图,《大希庇阿斯》285b及以下,只展现了希庇阿斯百科全书式多样性的学识,而在《小希庇阿斯》368b中,柏拉图描述的是希庇阿斯有志成为通才(to be universal)——他有成为一个通晓各种技艺和全部知识的大师的雄心。
[88]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12a,315a。
[89]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I,40,1。
[90] 柏拉图,《高尔吉亚》484c及以下。
[91] 柏拉图,《高尔吉亚》485c。
[92] 柏拉图,《高尔吉亚》485d。
[93] 柏拉图,《高尔吉亚》485a: [因文化之故]。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12b,以及后来的伊索克拉底的观点,也与此类似,参见本书第三卷,此处 。
[因文化之故]。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12b,以及后来的伊索克拉底的观点,也与此类似,参见本书第三卷,此处 。
[95] 《埃纽斯诗歌遗著》(Ennianae Poesis Reliquiae ),瓦伦(Vahlen)编,第二版,第191页:我以警句的形式引用了西塞罗给出的这句话。
[97] 参见拙文《哲学生活理想的起源与循环》(Ueber Ursprung und Kreislauf des philosophisoschen Lebensideals),载《柏林科学院会议报告》,1928,第394—397页。
[98]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21d,322b及以下,324d及以下,326c—d。
[99]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41.1。
[100] 如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说所展示的,这一点在伯利克里的民主理想中已经很明显,即城邦的两个不同方面的张力仍然保持着严格的均势,但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中则转化为了尖锐的对立,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
[101] 参见此处,注释[100] 。
[102] 柏拉图,《王制》492a—b(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正确地说明了,智术师更多地是公共意见和道德的产物,而非公共意见和道德的领导者和创造者。
[103] 关于这些贵族和寡头们的感受和批评的最有趣的文献——来自雅典城邦内部的一些贵族圈子——是我们现有的最古老的散文著作《雅典人的政制》(State of the Athenians ),它是一个无名作者的作品,以阿提卡方言写成。这部作品被保存在色诺芬的著作当中,据推测是因为该书手稿是在色诺芬的文献中间发现的。现在该书一般都以“老寡头(Old Oligarch)”的名义被引用。参见盖尔泽(Karl Gelzer)对它的透彻分析:《关于雅典国家的文章》(Die Schrift vom Staate der Athener ),《赫尔墨斯》单行本,第三辑,Berlin,1937。
[104] 参见本卷此处 。关于下文所述,参见拙文《希腊的国家伦理学》(Die griechische Staatsethik),收录于《人文主义演说集》,Berlin,1937,第93页。
[105] 欧里庇得斯,《腓尼基妇女》,第535行及以下;参见《乞援人》,第399—408行。
[106] 柏拉图,《高尔吉亚》482c及以下,尤其是483d。
[107] 柏拉图,《王制》338c。
[109] 柏拉图,《书信》7.324d。
[110] 柏拉图,《高尔吉亚》483e。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及以下。
[111] 参见祖克(F. Zucke),《道德意识-良知》(Syneidesis-Conscientia ),Jena,1928。译注: (syneidesis),“道德意识”、“是非之心” ;Conscientia,拉丁文的“良知”。“良知”一词,英文conscience,德文Gewissen,其字面意思都是“共同一起知”,与拉丁文Conscientia一样,都来源于希腊文
(syneidesis),“道德意识”、“是非之心” ;Conscientia,拉丁文的“良知”。“良知”一词,英文conscience,德文Gewissen,其字面意思都是“共同一起知”,与拉丁文Conscientia一样,都来源于希腊文 ,它由
,它由 (共同一起)和
(共同一起)和 (看见、知)组成。“个体的行为是由他自己的良知主导”那样的“良知”,形成于城邦解体之后的希腊化时期,尤其是斯多亚学派那里。
(看见、知)组成。“个体的行为是由他自己的良知主导”那样的“良知”,形成于城邦解体之后的希腊化时期,尤其是斯多亚学派那里。
[112]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37c。译注:关于physis和nomos,可参见《希腊哲学史》,第二卷,第202—206页,汪子嵩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4] 《奥克西林纸草》(Pap. Oxyrh .)1364(洪特编):现版于《前苏格拉底残篇》(第尔斯本)II,第5版,第346页及以下,残篇B44,第2栏,第10行及以下。
[115] 安提丰残篇A,第2栏,第26行,第4栏,第5行;参见第1栏,第6行。
[11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2.8.1268b26及以下。
[117] 阿里斯托芬,《鸟》,第1035行。
[11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37.2。
[119] 残篇A,第4栏,第9行及以下。
[120]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58a及以下。
[121] 参见本卷此处,注释[22] 。
[122] 埃斯库罗斯,《七将攻忒拜》,第592行。此处的读法见维拉莫维茨,《亚里士多德和雅典》I,第160页。
[123] 克里提亚残篇25(第尔斯本)。
[124] 柏拉图,《王制》359d。
[125] 德谟克利特残篇264(第尔斯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