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小型冠军企业
在中小企业中,可以发现德国工业有一个特定的创新优势。许多改进和相当多的技术突破(绝大多数在工程产品领域),可追溯到小型独立供应商。它们的根据地在德国西南部,但业务遍及全国各地。加里·赫里格尔(Gary Herrigel)的研究在理解小企业对许多德国工程产品的高质量和复杂性的重要意义中至关重要,他将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关系网络称为“一种新的混合型批量化生产战略”,其中小企业充当着“制造能力的外部来源”(Gary Herrigel,1996,第155页)。起初,小企业被认为是19世纪工业化的受害者,当时它们的命运是一个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后来小企业又被提升为德国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支柱。
赞赏小企业的成功会遇到一个理论问题,那就是,它们没有增长,因为一旦增长以后它们就不再是小企业了。但是,在那些本质上规模有限的市场中,我们在大企业中看到的那种增长不可能出现。鉴于德国小企业有着惊人的恢复力,获得了持续的成功,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当德国经济仍落后于其欧洲邻国时,对它们的兴趣重又燃起。事实证明,一些小型企业冠军(对中小企业的一种昵称)在高度专业化的利基市场上是极富创新精神的世界市场领军者。例如,占有世界鱼切片机械90%市场份额的巴德公司(Baader),以及只有20名员工却在超声刀市场占有世界36%份额的Sring公司(Simon,1996,第26页、第55页)。这些中小型高科技公司是连续创新或制造“连续新奇”(continuous novelty)的源泉,也是管理才能和创业天赋的完美结合体,“连续新奇”被菲尔·斯克兰顿(Phil Scranton,1997)用来描述较大的美国高科技公司。
4.“服务沙漠德国”
正当德国联邦政府的科技政策集中支持前沿技术的时候,市场早已转向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德国最重要的市场是原欧盟15国(EU-15),在这些国家中,前沿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就业人数,是前沿技术领域就业人数的3倍。在德国和瑞士,其第二梯队的熊彼特工业产品保持着非常强势的地位,前沿服务业的就业人数也仍然是尖端技术领域的两倍之多(Felix,2006)。在原欧盟所有15个国家中,前沿服务业的生产率均高于前沿技术领域,尽管在德国这种差距表现得不如其邻国那么明显。原因不是德国技术部门的生产率高于这些国家的平均水平,而是德国服务业的生产率低于平均水平(Gtzfried,2005,第4页)。德国创新型企业家集中在被视为德国经济据点的技术领域,这种状况已经开始变成了一种劣势。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通过创造“服务沙漠德国”(service desert Germany)这个短语,来提醒决策者和管理者严肃对待这一问题。许多年来,更有利于物质生产而不是非物质生产的机会成本已大幅提高。德国创新型企业家是否已觉知到这种变化,并开始管理小型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进而将创新活动的重点从工业转向服务业,仍有待观察。
四、德国的熊彼特式企业家
1815年以来的近两个世纪中,德国的熊彼特式企业家必须应对各种迥然不同的环境。在19世纪的绝大多时期,复制策略,即从其他地方引进适合德国自然和制度条件的发明成果,是他们顺利实现工业化的全部需要。但保护主义的复苏和法律支持的卡特尔化,为进一步的无效率埋下了种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德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独创性中获益匪浅的德国企业家已经有能力涉足全新的技术领域,如有机化学和电子工程等科学工业在德国欣欣向荣,使帝国晚期的工业在许多产品生产领域成了世界领导者。化学工业和电子工业的企业家足够敏锐,以至能从德国这种非同寻常的人力资本禀赋中获利,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从事工业研究、市场营销和外商直接投资。
这种势头在“一战”后便消失殆尽。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对商业发展比较有利的短短几年,不足以重新恢复德国工业的创新潜力。纳粹党人上台后,闭关自守和备战主导了政策议程,两者均不利于长期的工业竞争力。此外,惨绝人寰的反犹主义和在校学生数量的不断下降,将德国推向了一条史无前例的知识上的自毁之路。与此同时,大众营销和大规模零售业均备受排斥和阻挠,既抑制了潜在创新,又只允许经济中更重要的服务部门实施复制和引进策略。这种灾难性的发展一直持续至“二战”结束后。重要的制度改革,如禁止成立卡特尔组织、取消零售价格管制和废除贸易保护主义等,逐渐把德国企业文化重新引向一些更注重竞争能力和开放市场的目标。
由于战后几十年间经济重建成了时代主题,且商业环境较为有利,德国企业家在渐进式创新中表现抢眼。20世纪下半叶,当“一战”之前似乎触手可及的前沿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已不再是一个现实选择时,一种非常成功的改进和完善现有技术的文化得以形成。颇具讽刺性的是,德国灾难重重的历史反而成了一种比较优势。当生物技术和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尚未发展成为成熟产业,甚至还在挣扎着成为快速跟随者时,高度精致的汽车工业表现极佳。即使在零售业等备受政治和流行观念歧视的商业领域,在利用对自己有利的熟知策略中也获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功。德国企业家不太可能是能抓住全新机遇的先行者,他们似乎更擅长成为第一批成就斐然的追随者和实践者。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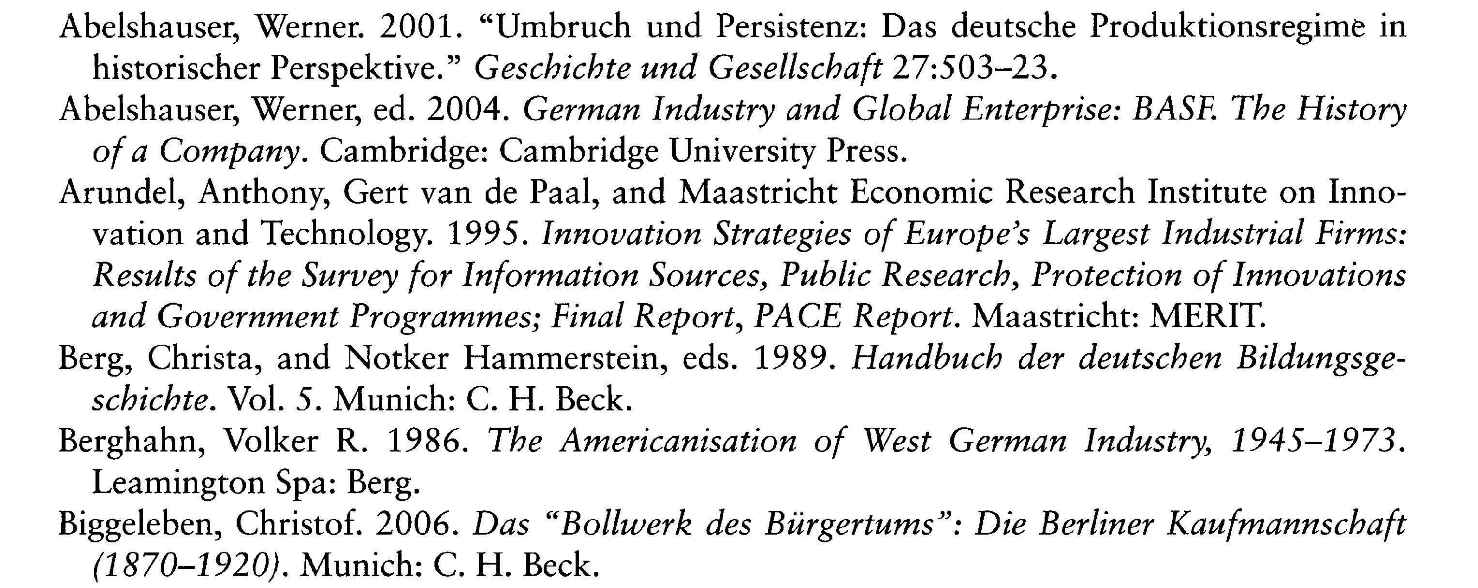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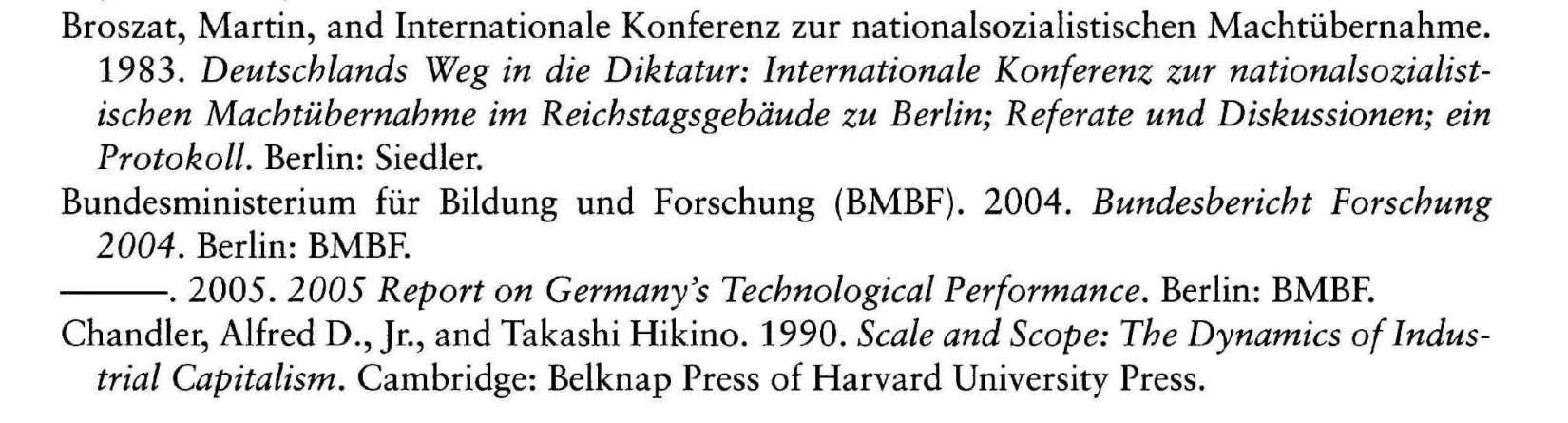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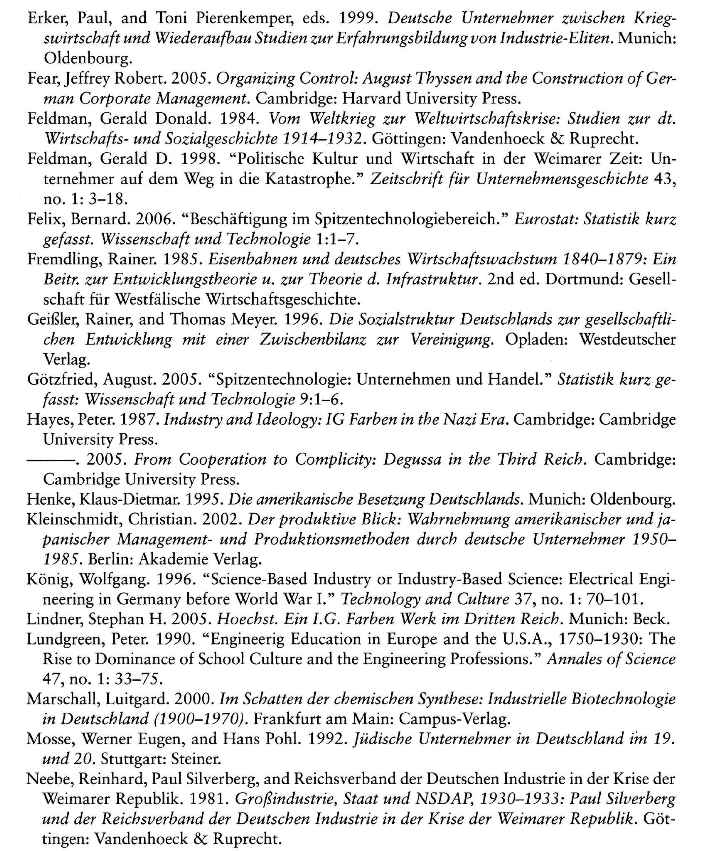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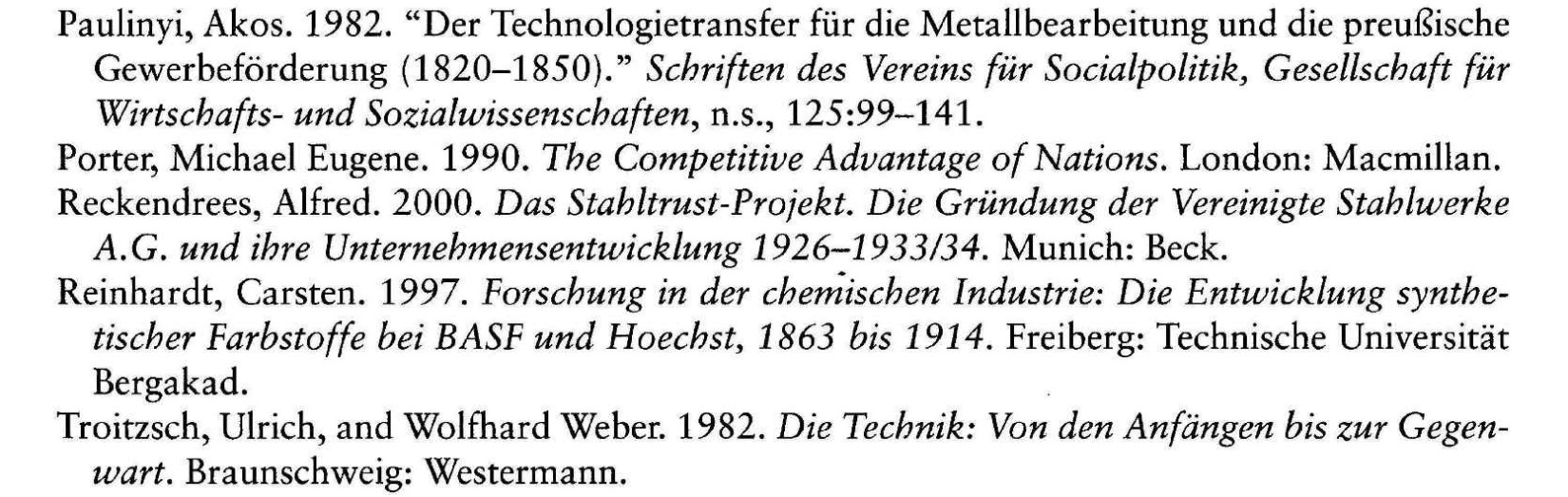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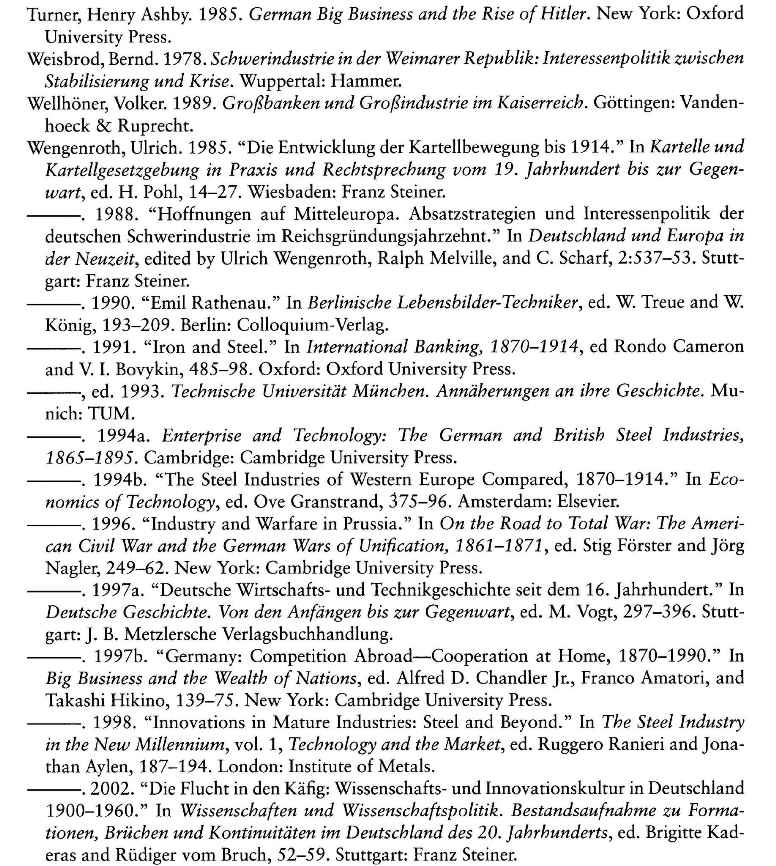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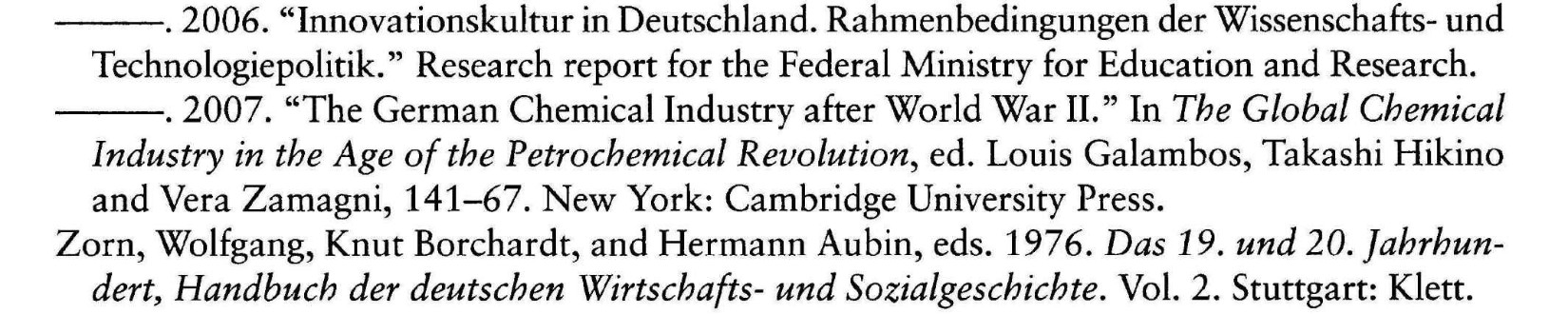
[1] 参见http://www.bmbf.de/prees/1761.php,2008年10月14日。
[2] 新姓氏为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和Thyssen-Bornemisza de Kászon。
[3] 根据作者同这两家公司的档案负责人之间的个人通信整理所得。
[4] 《通俗德国史》(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第54卷,第477—501页。
[5] 《德国商报》(Handelsblatt)电子版,2006年7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