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法国工会制度由革命分子在19世纪80年代创立,通常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劳资纠纷与其以有限度的改善为目标,还不如转向同资产阶级的重大对抗。这种观念极大地恶化了劳资关系。在港口、矿业盆地和城市郊区等工人生活密集区,劳资关系变得越来越严峻。罢工和暴力事件在1906年达到了一个高潮。但1936年的罢工给雇主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因为工人占领了各处工厂和作坊,而政府(人民阵线)却未采取任何干预措施。
左翼的反资本主义也扩散到了知识界。从19世纪90年代起,引领法国知识精英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教师们越来越敌视商人,特别是商人中的最富有者,左翼称之为“200个家族”,并指责他们削弱了法国货币,以此诋毁左翼政府。
(四)撤出本土市场
法国的第二波工业化浪潮发生在困难重重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下。由于出生率下降、本土市场萎缩和非生产性农业部门的膨胀,1860年以后增长开始放缓。“一战”之后,批量化生产又遇到了需求不足的制约。国民生活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50%,70%的人口生活在不足2万人的小城镇和小乡村(Lévy-Leboyer,1996,第18页)。
1871年后,工业也受困于阿尔萨斯的割让和该地区富有创业精神的商人的外迁。一些阿尔萨斯商人在孚日省或诺曼底重新创建工业企业,但绝大多数则流失到了德国;也有的迁往了其他国家,如凯什兰移居到了瑞士,斯伦贝谢移居到了美国。但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利,使许多出身于这些商人家庭的勇敢子弟选择踊跃参军。随着阿尔萨斯人的相继离去,法国雇主中最保守的元素重新恢复了它们的影响力。19世纪60年代的自由贸易条约遭到了各大雇主协会的质疑(Lambert-Dansette,2000,第136页)。保护主义思潮死灰复燃。但大公司依然对更大的外部世界持开放态度。工业出口商面临的最大障碍来自农业保护主义。对葡萄种植者的担忧阻碍了法国同东欧和南欧国家签署工业协议,将该市场留给了德国出口商(Poidevin,1995)。
三、国家干预的黄金时代:1940—1983年
(一)新柯尔贝尔主义的根基
自20世纪30年代起,法国工业投资开始大幅萎缩。推进现代化的能力大大减弱。与此同时,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苏维埃俄国的新独裁统治,大肆标榜其或虚或实的成就。法国“现代化促进派”公开谴责或真或假的家族资本主义路线,呼吁成立国家和大企业之间的联盟,甚至诉诸对经济资源的计划管制。1940年的战争失利给这些“现代化促进派”提供了上台掌权的机会。他们中许多人开始在维希政府担任公职,直到后来才加入了抵抗派阵营(且不论是否名副其实),以至解放政权在许多方面仍延续着维希政府任内的措施和政策。
法国人民解放政权是两大抵抗派力量——戴高乐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相互妥协的产物。为了换取一项普遍性的商业国有化政策和对主要公共部门工会的控制权,共产主义者放弃武装。而这些公共部门控制着诸多重要经济领域,如科学研究、教育、煤矿开采、新闻出版、电力输出、铁路运输、海港及邮政和电话服务等。
煤矿、电力、天然气、核能、石油、铁路和航空设备,以及巴黎的绝大多数银行和雷诺汽车公司,都被国有化。这使“现代化促进派”深感满意,他们认为只有国家才能推动现代化[Andrieu和Van-Lemesle(1987),Kuisel(1984),Picard、Beltran和Bungener(1985),Jeanneney(1959),Desjardins等(2002)]。在国有公司的领导层,政府委派了许多工程学院毕业生、新涌现出的年轻精英和社会进步的追求者。
一项四年计划(1966年后改为“五年计划”)使法国商人得以追求他们的发展目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66—1970)完成以后,由于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不断增加,法国企业开始逐渐摆脱主要关注国内需求的计划。
(二)私营企业面临的约束
1945年起,私营企业的税收负担急剧加重,税收收入主要被用于支付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成本,包括家庭津贴、事故保险、健康和养老保险、交通和住房成本补助,以及1958年后实行的失业保险和1971年后实施的员工培训补助。
现在,政府握有一系列干预经济的金融工具。价格控制始于1939年,它给商人和管理部门进行对话预留了空间。伴随着法兰西银行、其他四家法国最大存款银行和各大保险公司的国有化,信贷控制被引入。国家同时还控制着其他金融机构,包括:法国信托局(CDC),它管理着公证员和储蓄银行的存款(Aglan、Margairaz和Verheyde,2003);1919年改组后重建的国家信贷银行(Crédit National);以及法国地产信贷银行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最终,法国在1948年设立了“现代化与设备基金”(Fonds de Modernisation et d'Equipement),用于配置“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资金。该基金在1955年后获得了国家出资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Fonds de Développement Economique et Social)的注资。如此一来,作为法国行政精英核心基地的财政部,便能直接决定大量国家投资的流向(Quennoulle-Corre,2000)。铁路、电力和煤矿获得了技术最先进的大型设备。法国的火车成了世界上最快的火车之一,法国电力公司的发电站也成了世界上产能最高的发电站之一。
相比之下,私人融资要势单力薄得多。价格控制危害重重,且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股票交易萎靡不振。由于货币贬值和来自政府贷款的竞争,法国公司很少能求助于增发新股或债券。因此只剩下了银行融资这条唯一的通道。1945年后,中期(5年)信贷成了颇受欢迎的选择。法国公司在财务方面非常脆弱。
1981年的社会主义国有化将更多的资本转到了政府手上。国有部门雇用的劳动力占全部工业劳动力的份额从6%上升至19%,国家还控制了90%的银行存款。至此,法国最大20家公司中的13家已经变成国有企业。国家增加了这些公司的资本,给那些陷入困境的公司,如布尔公司(Bull)、罗纳—普朗克公司、汤姆逊公司和佩希内公司等提供补贴。1985年,国家股份在法国公司的资本中占10%,达到了其最高水平。
(三)法国的企业家精神:1940—1983年
法国的雇主们并不担心非殖民化(Marseille,2004;Eck,2003;Fridenson,1994)。但他们担心更低的关税和进口配额的解除,这会使他们陷入同德国工业企业赤裸裸的竞争中,后者只需负担相对较低的社保缴费和税收。正如在1860年,相当大部分的法国雇主,尤其是小企业主,反对降低保护。1959年,戴高乐将军在履行条约义务时,创设了货币自由兑换制度,取消了进口配额制度,并第一次降低了海关规费(customs dues),这令很多人大为恼怒。
大企业依旧受到国家政府的束缚,其高管人员(总共约有成千上万名,参见Bauer和Bertin-Mourot,1997)大多是从顶级工程院校招聘的。 [5] 他们是法国的统治阶级。众所周知,1940年法国被德国战败,旋即接受了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观点:“被击败的是我们亲爱的小镇”(Bloch,1995,第182页;Daumard,1987,第380页)。法国并未充分实现工业化,以成功应对新式德国军队。而现在正是追赶其他先进国家,补回失去的发展时间的良机。1962—1968年间的法国总理和1969—1974年间在任的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以及此后于1974—1981年间在任的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等人物,是这个由精英和野心家统治的世界中的一员,他们接受过同样的精英教育,乔治·蓬皮杜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母校分别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综合理工学院(Fridenson,1997,第219页)。人人都认为经济增长没有理由放缓。在一场圣西门主义复兴运动中,规划专员(即计划委员会主席)皮埃尔·麦斯(Pierre Massé)很乐观地预言道:“平均生活水平在20年内将翻一番,如果我们越来越多地掌握技术和经济学,提高的幅度可能会更大,速度会更快”(Massé,1965,第89页)。
“二战”期间,法国工业技术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其他国家。从1948年起,法国工程师和企业家每隔五周便会组织一次去美国学习新的生产和管理技术(Barjot,2002)。在20世纪50年代,267个这样的生产力代表团共吸纳了约2600名参与者。1960年以后,美国投资的持续流动也带动了美国经济和技术方法向法国的转移。
事实上,在蓬皮杜出任总理和总统时期(1962—1974),法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从1962年法国刚摆脱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包袱到1974年法国陷入国内第一次石油危机,年均GDP增长率为5.2%。许多人从农业转向工业:20世纪70年代,农业部门劳动力比例下降到10%以下。工程师踌躇满志地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并充满信心地期待国家帮助落实这些计划。国家和精英们决定一展宏图。在“二战”前或德国占领时期成长起来的几代人,再也不满足于前辈们的小打小闹。因此,在1969年,法国不仅创建了空客公司,实现了英法两国之间协和式超音速喷射客机的第一次飞行,而且成功研制了两辆试验性的高速列车(TGV)(Lachaume,1986)。在1971年,第一台完全数字化的电话交换机开始在佩罗斯-吉雷克的布雷顿镇(Breton town)投入使用。1973年,成功研制了欧洲航空发射火箭——亚利安(Ariane)系列运载火箭。
也是在1973年,一纸欧洲协议导致法国创建了一家民用铀浓缩反应堆工厂。随后法国迎来了一场核电站建设高潮,以至法国当时34的电力供应都来自于核能,这一比例高于其他任何国家。法国企业法玛通(后来更名为阿海珐集团)成了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这些便是法国面对石油危机时的应对之道(Beltran,1985)。
(四)创建“国家冠军企业”政策
与此同时,法国政府鼓励公司兼并,以建立欧洲(洲际)层面的大型“国家冠军企业”(national champions)。其目的是让法国企业能抵抗外国企业的渗透,结果却催生了大量多样化企业集团。在石油行业,几家国有企业兼并后成立了法国埃尔夫石油化工集团。在银行业,国民工商银行(Banque Natioanale pour le Commerce et l'Industrie)和巴黎国民贴现银行的合并,产生了巴黎国民银行(BNP);与此同时,巴黎的大银行接管了绝大多数区域性银行。在化工领域,国家氮办事处(Office National de l'Azote)同阿尔萨斯钾肥(Potasses d'Alsace)合并成了矿物与化工企业(Entreprise Miniere et Chimique)。1968年初,20来家小保险公司以同样的方式组合成了欧洲层面的三大企业集群。钢铁工业也很快聚集成两大集团,即东部的萨西洛尔钢铁集团(Sacilor)和北部的优基诺钢铁集团(Usinor)。人们不难想到电气工程领域的法国通用电气有限公司(Cie Générale d'Electricité),通信领域的阿尔卡特公司,电子工业领域的汤姆逊公司和航空工程领域的法国宇航公司(Fridenson,2006b)。但这些“国家冠军企业”主要建立在规模的基础上,它们较少关注竞争性的投资选项。
同时,组织和管理创新(租赁业务的引进、抵押贷款市场的发明和外汇管制的削弱)帮助法国金融体系补回了失去的发展时间。这些领域的创新者是1966—1968年担任法国财长的米歇尔·德勃雷(Michel Debré)。在取消存款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分野后,法国金融部门有了一个比英国以外的其他邻国都要好的基础。但是,货币市场仍然微不足道,表现为过多依赖债券发行,1970年债券发行达到了70%。整个这段时期,货币市场只提供了10%的公司融资。
这种国家控制的发展模式直到1974年前都运行良好。1974年,法国的每工时产出高于联邦德国或英国。法国精英坚持推行这些制度安排也就不足为奇了(Maddison,2006,第353页),此外他们也满足于国家控制为他们创造的精英权力和社会地位。
(五)一种独立于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兴起
这是否等于说法国这一时期不存在自发的资本主义?答案是否定的。制造业和消费品销售领域都出现了私营部门。因此,在银行的帮助下,我们看到农业和食品部门中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农业综合企业(Bonin,2005)。达能集团一开始生产法软干酪,后来依靠布苏瓦—苏雄—弗塞尔(Boussois-Souchon-Neuvesel)玻璃集团发展壮大。在建筑和公共工程、化工和美容产品领域,也可发现类似的新式企业集团。一个例子是巴黎欧莱雅集团,该公司以生产香皂起家。万能集团(Moulinex)和赛博集团(SEB)成功地在小型家用电器设备领域实现了专业化生产(Seb,2003;Gaston-Breton和Defever-Kapferer,1999;Pernod-Ricard,1999)。在汽车制造领域,标致公司回购了雪铁龙汽车,重组为标致雪铁龙集团。这些公司都有着广泛的市场营销资源。这些现象质疑了关于法国中小型公司的负面评价。
在零售贸易领域,保护小型商铺的限制性法规在1959年之后逐渐被废除。大型超市,如勒克莱尔和家乐福等,不断涌现。不久后,家乐福便建立了最庞大的商业组织形式,即超级大卖场。
随着这些新式零售巨无霸在普通合伙领域日趋衰落,它们越来越把资源转向有限责任公司。这种资本主义的活力体现在1945—1954年间小企业的繁荣发展以及1955年之后有限公司的蓬勃增长上(参见表11-1)。
表11-1 公司创建的累年平均数量

资料来源:Caron(1981,第215页)
四、回到自由主义:1983年至今
(一)国家的退出
1981年以后,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总统任内的社会主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更甚于以往,政府对新近独立的私人银行和绝大多数大型工业企业实施了国有化。但是,国有化的企业并不盈利,因此越来越需要国家的支持(Cohen,1989)。尽管有公共补贴,但法国国有铁路公司(SNCF)和供电系统(即法国电力公司)的债务仍在不断攀升。这些国有化企业只创造了较少的工作岗位,而且它们的管理经常会犯重大错误。最严重的要数里昂信贷银行,由于未能遵守美国的监管法规,该行损失了一大笔钱,不得不支付创纪录的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罚款。所有这些均在敲响着法国社会主义工业政策的丧钟。
转折点出现在1983年,尽管此时法国仍由社会主义者掌权。面对不断攀升的赤字和法郎汇率灾难性的下挫,政府放弃了积极的经济干预主义政策。尽管其效应是逐渐显现的,但法国经济现在已朝西欧自由经济体靠拢。到1984年,资金流动的自由度大大提高,工资也不再同价格挂钩。增加值中进入工资的比例在1983年达到68%的峰值水平,随后迅速降至60%以下。1984年,克勒索—卢瓦尔工业公司(Creusot-Loire)遭受了巨大损失。克勒索—卢瓦尔是当时法国优质钢冶炼和机械制造领域最大的集团公司,员工人数多达23000名。经过一番犹豫后,政府决定不插手支持,该公司被迫于1984年陷入财务破产状态。
1968年的大选使右翼重新掌握了政权。右翼政府决定完全放开价格,让国家退出13家大型金融和工业企业,其中包括1945年被国有化的所有银行。汽车制造商雷诺在1994年实行了私有化。公共金融部门现在仅限于势力仍然庞大的法国信托局和邮政部门。随着欧元在1999年1月启用,法国融入了欧洲金融大家庭。
即便如此,国家仍试图创建两大企业集团:一大企业集团由巴黎国民银行、埃尔夫集团、圣戈班、佩希内、苏伊士集团和巴黎保险联盟(Union des Assurances de Paris)组成;另一大企业集团由法国一般保险公司(Assurances Générales de France)、阿尔卡特、汉威士集团、巴黎银行(Paribas)、罗纳—普朗克、法国兴业银行和托特尔(Total)组成。但该体系建立在交叉参与的基础上,沉淀了大量资金,并导致这些企业的资本化程度不足,阻碍了它们的进一步合并和增长。20世纪90年代中期,问题开始不断显现。股东再次撤走了他们的投资。
外国投资者现在开始大举涌入。到1999年末,在那些规模最大的法国企业中,有略高于一半的法定股本由外国人所有(Morin和Rigamonti,2002)。有选择性地私有化原本旨在保护法国企业免遭外部收购,却产生了相反的效应:它削弱了企业的资本化程度,使企业陷入了困境。现如今,法国是对境外资本最开放的国家之一。2005年,巴黎国民银行、法国兴业银行、阿尔卡特、阿克斯(Axa)或维旺迪集团(Vivendi)等企业,有30%—50%的股权掌控在境外投资者手中。到2006年,法国政府根本没有任何办法阻止英裔印度商人米塔尔(Mittal)控制阿塞洛公司(Arcelor),该公司是当时欧洲最大的钢铁制造商,由来自法国、卢森堡和西班牙的多家企业合并而成。
(二)金融市场的凯旋
受益于国际经济环境,法国股票交易指数从1981—1987年涨了4倍。随之而来的是20世纪90年代指数的另一次上升。20世纪80年代,股票交易在法国经济的全部融资中只占27%,到1997年已上升至80%。对这一革命性变化,法国并未做好准备。虽然储蓄仅为GDP的15%,但国家却鼓励它们用于债务融资。这给境外机构投资者留下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同时,法国的机构投资者,如保险公司,却偏向于政府贷款。
由于更大的金融自由,法国企业得以削减债务,充实资本,并实现自我融资。大企业做出了较好的调整,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发挥一定作用。法国企业主能自由流动,实施全球化战略,在世界各地设立子公司。2005年,有40家法国跨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最著名的有:路易威登集团(LVMH,奢侈品行业)、欧莱雅集团(L'Oréal,化妆品行业)、达能集团(Danone,乳制品行业)、芬奇(Vinci,土木工程行业)、维旺迪集团(电影、音乐和出版等行业)、威立雅环境集团(Veolia,水处理行业)、法国航空公司(Air France)、阿海珐集团(Areva,核能行业)、液化空气集团(Air Liquide,工业煤气行业)和依视路集团(Essilor,眼镜行业)。法国在出版、数字处理(Marseille和Eveno,2002;Gaston-Breton,1997)、酒店旅游(Luc,1998)、奢侈品(Bergeron,1998;Marseille,1999;Ferrière,1995;Dalle,2001;Dubois,1988)、能源工程、交通运输(Barjot,1992,1993,2003)和大规模物流(Villermet,1991;Chadeau,1995;Petit、Grislain和Le Blan,1985)领域也表现不俗。美国和英国的投资基金一开先例,法国企业便迅速对金融领域的市场信号做出回应。人们可看到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型企业家群体,正积极地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一个例子是雷诺集团主席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戈恩是黎巴嫩后裔,1954年出生于巴西,曾是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学生,他在1999年成功合并了尼桑(Nissan)和雷诺,2005年正式成为兼并后的联合企业集团的主席。
企业集团主席手握大量权力,这是法国模式的特点之一,如今虽已不受政府约束,却不得不对日益增长的股东影响做出回应。短期内的金融逻辑取代了长期内的工业逻辑(Trumbull,2004;Fridenson,2006a)。
(三)家族资本主义的持久性
罢工风险和行政约束(如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35小时、《公平劳动标准法》的复杂性、企业税收和社会保险)依然抑制着法国公司的创立。法国似乎是欧洲设立公司最不易的国家。这正是如今这么多法国人生活和工作在国外的原因。比如,今天仅生活在伦敦的法国人就多达20万或以上。
近几年来,行政障碍已大大减少,行政手续被重组和精简,社会保险税也有所降低。法国公司已在向英美模式转变,私人股权越来越多。2003年,720万法国人(14的家庭)持有公司股票,比工会成员人数还多。法国西部地区(布列塔尼、旺代省、马耶讷省)正经历着经济复苏,大量中小型企业不断涌现。
五、结论
法国继承了两种传统:一种是由君主国及后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主导的管制经济传统;另一种是市场资本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在缓慢融入更广阔社会的地区(北部和东部)和宗教群体(新教徒和犹太教徒)中表现得尤为强烈。
法国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的行政和政治权力,从未完全阻止相当大一批新型企业家推动法国实现工业化和技术进步的努力。18世纪末君主制或法国大革命时期创立的国家制度,有助于各种发明在法国制造业企业中的扩散。但是,首创性几乎全都来自企业家。法国北部、东部和巴黎是企业家最具创新精神的区域或地方。城市自治传统和摆脱中央集权国家,似乎刺激了企业家精神的发展。
富于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角色至关重要。许多发明家同时也是工业家,他们开发出某项创新,并使之能供终端用户使用。例如,法国火车头的设计者使发动机耗煤量远低于英国,从而能适应法国煤炭价格高昂这一现实条件。另一个例子是卢米埃尔兄弟:他们不仅发明了电影放映机,还帮助成立了一家公司,为普通大众制作电影。
大革命结束后的19世纪初,企业家已跻身于法国社会第一等级。最富有的企业家的财富很快超过了最大的地主,且在1830年后,他们在国家最顶层中的影响力颇大。但是,他们结交权贵向上爬的做法遭到了其他精英,如旧贵族、新兴知识界和艺术界精英的批评。工业化过程本身也不受一些公众舆论的欢迎。直到“二战”前,许多法国议会议员都对大规模工业的发展和大量劳动者聚集的增长持保留态度。在法国,不利于企业家精神扩散的障碍大多来自右翼或左翼极端分子。19世纪,一些精英人士更倾向于谋求公职或军职,而非步入私营工业领域。但是,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政府高官和企业家均接受相同的精英教育,毕业于相同的工程院校,汇集成一个独特的统治阶级。这种趋势在“二战”后得到了加速,表现为,法国政府在推动新技术发展、给能源和运输部门的巨额投资提供资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和行政精英选择了国家管制经济的模式,试图发展大型国有企业。这一趋势在弗兰西斯·密特朗总统的社会主义政府掌权的早年(1981—1983)得到了强化。但1983年后,法国政府决定放弃干预主义政策,逐渐回归自由竞争规则。
如今,法国的企业家精神似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企业家掌握着大量权力。短短20年间,法国已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型为市场资本主义。战后“国家冠军企业”的政策遗产见证了法国跨国公司像外国跨国公司那样高效运转。它们的最大任务是足够快速地增长,而非继续保持小规模。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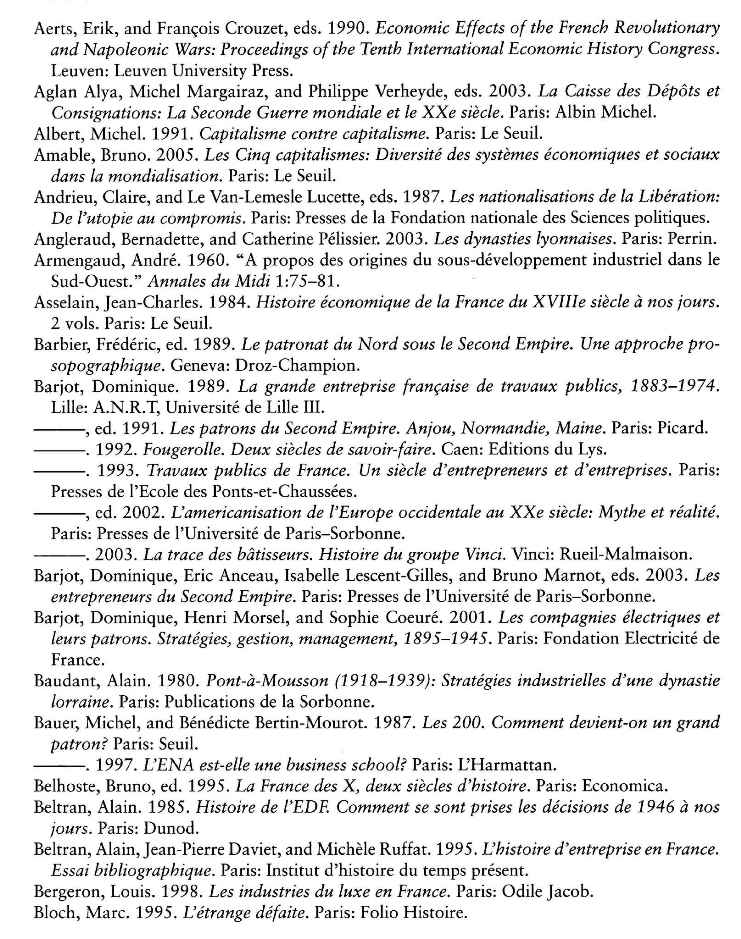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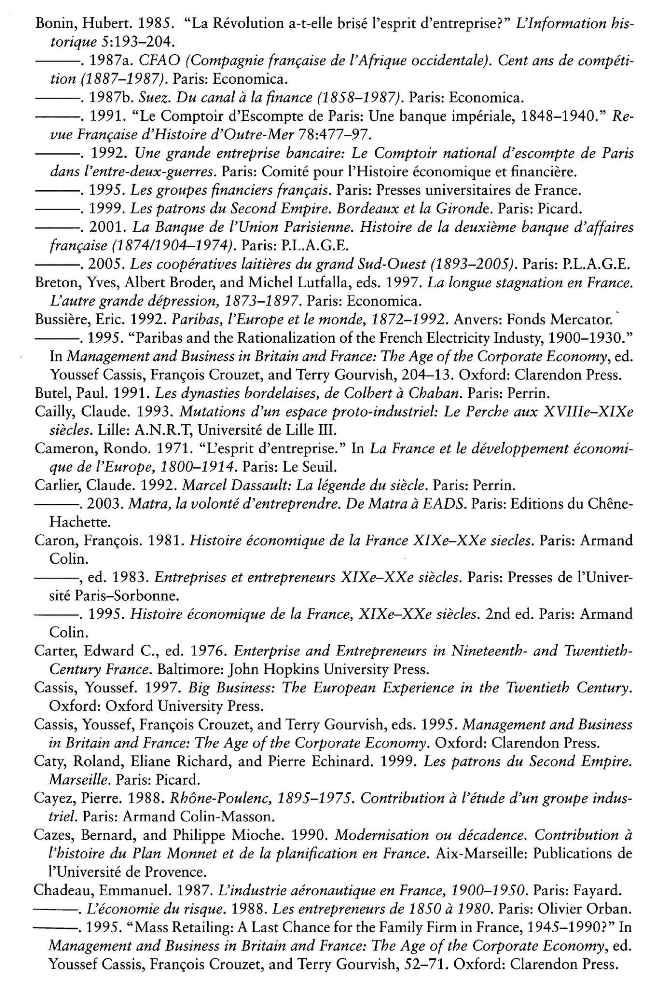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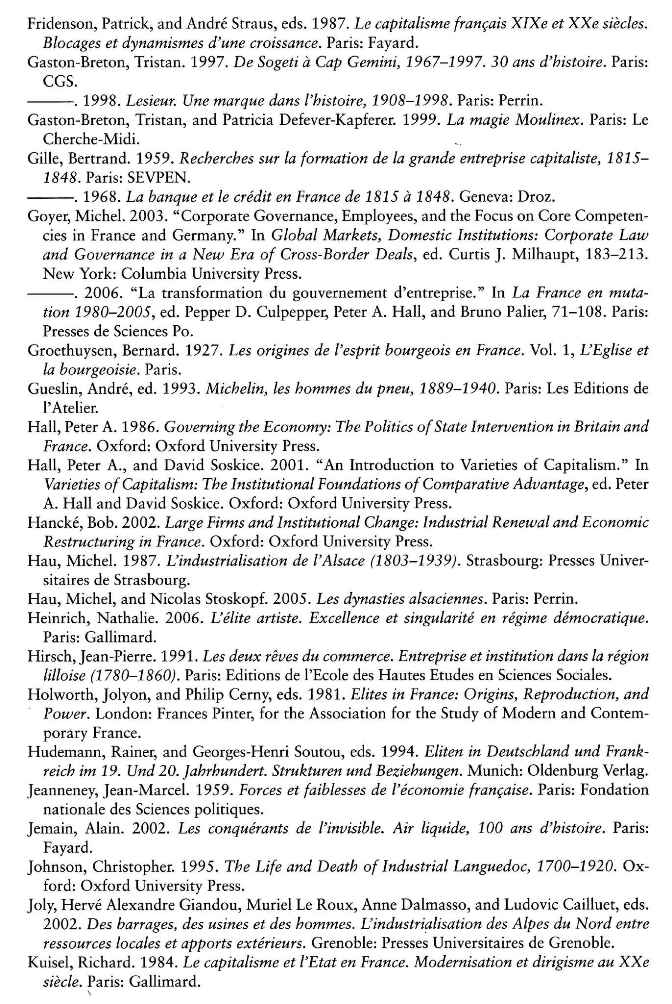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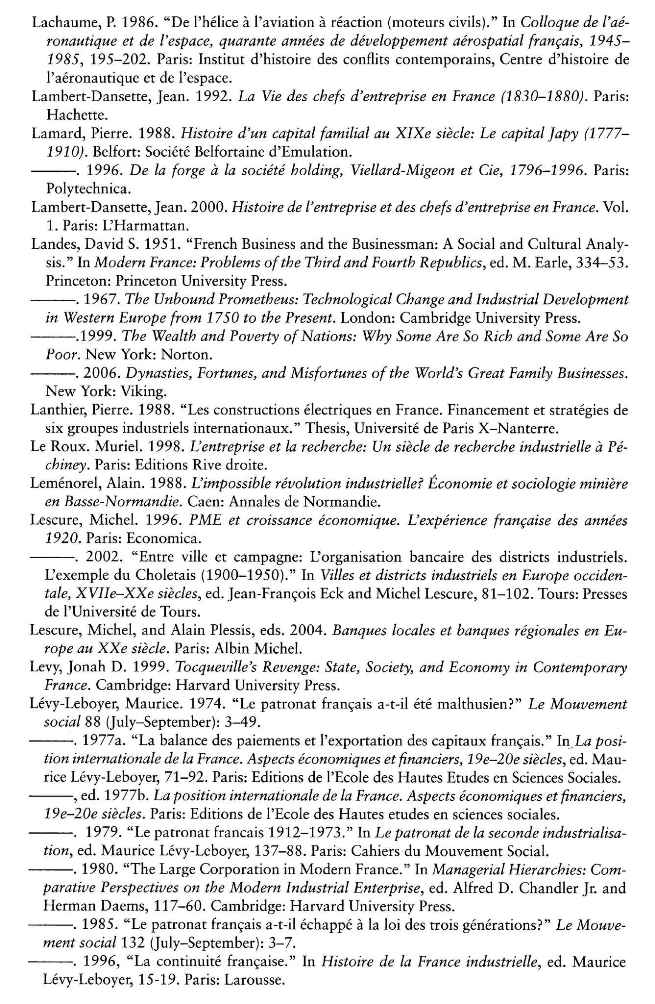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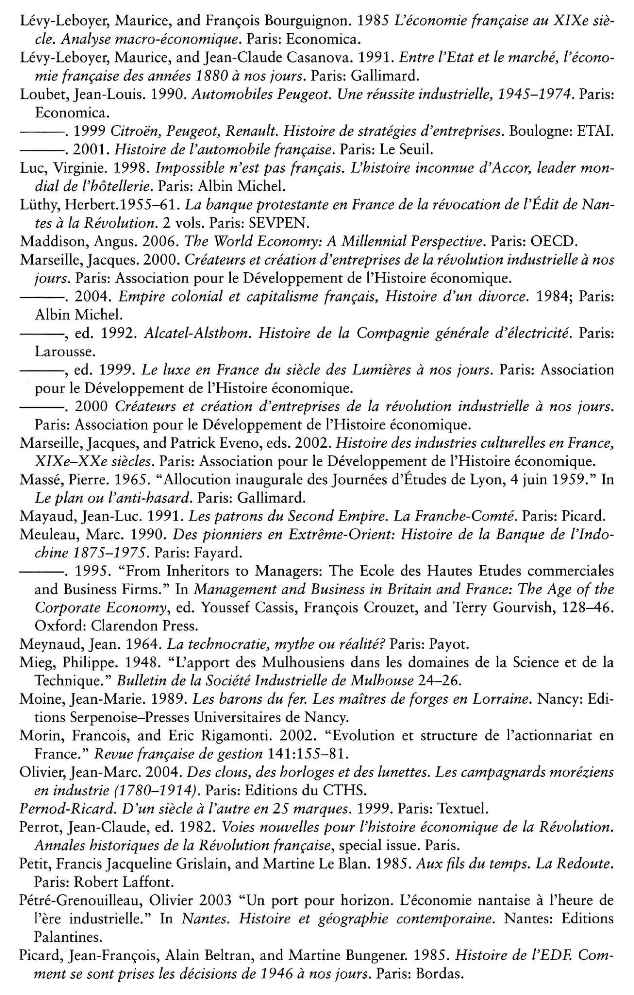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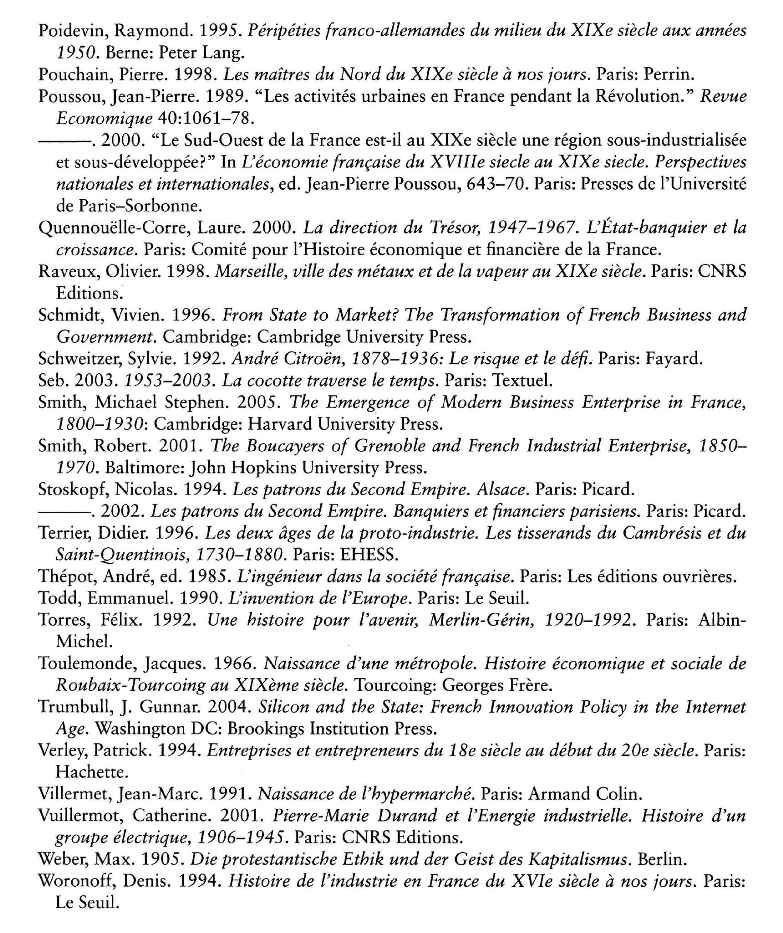
[1] Toulemonde(1966),Bar(1989),Pouchain(1998),Daumas(2004b);Hau(1987),Stoskopf(1994),Hau和Stoskopf(2005)。
[2] 参见Cailly(1993)、Barjot(1991)、Chaline(1982)、Leménorel(1998)、Armengaud(1960)、Terrier(1996)、Johnson(1995)。
[3] 巴黎联合银行(Banque de i'Union Parisienne)、瑞士—法国银行(后来更名为法国商业信贷银行)、巴黎国际银行(后来更名为法国工商银行,即Banque française pour le Commerce et d'Industrie)等。
[4] 参见Fridenson(1998)、Schweitzer(1993)、Fridenson(2001)、Moine(1989)、Baudant(1980)。
[5] Jean Meynaud估计他们的数目在5000—6000之间(1964,第1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