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美国的企业家精神:1920—2000年
玛格丽特·格雷厄姆
20世纪美国经济的“卓尔不群”,就在于大型一体化公司中的企业家对技术的充分利用。起初,这完全是私营部门的现象,随后伴随着联邦政府越来越多的干预。 [1] 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中的所有部门,不管是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营利部门还是非营利部门,无不受这一体制的影响。甚至娱乐和通信等非制造业部门,也被打上了科技进步和受管制的工业化的烙印,正是后者巩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 [2]
但是,对20世纪美国历史更仔细的研究得出了一幅比单纯的巨头公司统治复杂得多的画面。 [3] 甚至明显的创新制度化,如同一台安装在大型企业网络中的依靠互补机构提供支撑的永动机,也只是这个复杂故事的一部分。 [4] 较不明显但仍重要的是小型创业企业和个体发明家兼企业家的活动,不过他们常常和大公司携手合作。尽管被路易斯·高隆博什(Louis Galambos)称为“组织合成”(organizational synthesis),并依赖相关专业人才、管理人员、科学家和政府官僚的连锁官僚机构可能已成为20世纪绝大多数时期美国经济的主导模式,但美国体制推陈出新的推动力建立在企业家和企业(可称之为法人企业家)之间的互补关系上,前者富于创新精神,后者积极进取。 [5]
到20世纪初,大企业已纷纷涌现(如我们在第十三章所了解到的),不过,其中有许多并未实现“公司化”。如历史学家奥利弗·聪茨等人(Olivier Zunz、David Hounshell和JoAnne Yates)已详细描述的,美国的公司化采取了官僚化不断加深的形式,主要表现为标准化生产、信息流控制、非人格化资本投资和文化同质化。 [6]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生产力获得了极大解放,导致了科学管理(特别是)在大企业、大企业的供应商以及工会等机构合作者中的系统性应用。 [7] 大型工业化企业的制度化本身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经济协作形式,如研发一体化、公司间联盟以及政府管制程度的不断提高(Galambos和Pratt,1988)。这些变化共同导致了美国创新体系的部分失效,由此带来的短期结果就是技术创新的流水线化,并将之上升为国家优先事项。这个高度一体化和片段化的创新体系,并未完全激发出个体企业家的潜能,但它形成的创业环境不同于我们在前面章节所看到的开放的创新体系。该创新体系的重新开放伴随着信息技术的传播和20世纪末达到顶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而这并非巧合。
一、创新是20世纪版的企业家精神
《牛津英语词典》显然认为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于1939年最早把“创新”一词当作基本创业行为使用,因为20世纪上半叶,“企业家”这一术语已和科学创新密切相关。熊彼特式企业家的角色是,提供协调和努力,以使新工艺或新产品能达到应用和商业化,但他们不一定提供资本。对熊彼特这样一位20世纪美国经济的睿智观察家而言,企业家所做的,不管是独立行动还是从属于公司内部,远不止是在变化面前制定决策。他们创造性地对变化做出反应,试图掌控和利用变化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尽管熊彼特式企业家不一定拿自己的金钱冒险,但企业家精神天生就是一种冒险活动。从其他方面看,它是如此苦涩和残酷,充满不确定性,只有通过成功带来的金钱收益才能得到证实,有时这种收益甚至极高。
熊彼特起初在描述企业家的时候,将之限制在创造性个体上,但他后来的研究承认一体化大公司的出现改变了美国的创业环境。如果考虑科学研究,最大的不确定性所在就是技术发明。将发明和研究作为公司职能加以整合的企业,有潜力启动破坏性创新,使禀赋稍差的竞争对手处于劣势。它们也有潜力控制其所处行业的技术进步率,且常常设法防止个体企业家打断有序和有利可图的技术发展路径。 [8]
二、成功和地位
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时期对企业家的满腔赞美和崇拜,能比得上19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或电气化时代。但到“一战”时,电气化革命已进入巩固阶段。它带来的财富与权力在许多地方也和各种各样的反社会活动交织在一起。当政府和公司治理各层面的腐败问题引起公众关注时,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的联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社会和监管政策,以图抑制贪婪所带来的更多反社会后果。监管政策也有利于培育稳固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它们既能抵制社会主义又能抗衡团结一致的工会。
在这种背景下,公司采取了更注重现实的风格,更多地同公众情绪和基于科学的效率精神保持一致,并用职业经理人,即“组织人”(organization men)来取代魅力型领导人。集中化的大企业往往由工业政治家掌舵,如通用电气的董事长欧文·扬(Owen D.Young),这类企业在20世纪的商业环境中仍然相当常见,对维系上述社会阶级起着重要作用(McQuaid,1987)。工业政治家是德高望重者,往往具有大学学历,拥有广泛的社会和政治人脉,这一角色很少对企业家开放。崛起为工业政治家的一些人,如英国移民、电学先驱及20世纪20年代电气工业的领军者塞缪尔·英萨尔(Samuel Insull),因傲慢自大而身败名裂。 [9] 在20世纪剩下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企业家”一词被赋予了负面意义,指代那些极有可能破坏高度一体化组织的怪人。 [10]
新的社会景象由其他因素共同塑造,包括财政政策使社会财富分配差距不断缩小,以及更多普通人掌握了合理的技能。众所周知的“大压缩”(great compression)缩小了美国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降低了私人投资资本的集中度,同时也增强了联邦政府的财政实力。联邦所得税,最早于1913年向最高收入群体征收,帮助巩固了中产阶级群体。如所得税记录所反映的,最高收入百分比人群的收入从“一战”前占总申报收入的18%下降到“二战”初期的8%。在最富裕群体的边际税率被提高到80%,以便为战争行动提供资金支持后,收入不平等降到了20世纪的最低水平,并一直稳定地持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Piketty和Saez,2003)。收入政策的变化,如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和公司所得税,可以部分解释“20世纪中叶的收入差距下降”,不过,公司所得税也降低了应付股息总额。大工会、大公司和政府项目支持了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群体的工资水平(Fischer,1996,第202—203页)。
20世纪70年代收入差距扩大标志着新技术革命,即信息革命的出现。 [11] 对某些人而言,收入差距再次扩大可以用工薪阶层和代表他们利益的工会未能很好地掌握技术变革所需的新技能来解释;对其他人而言,则反映了个体企业家精神及其报酬的增加(Reich,1991)。收入差距的再次扩大也反映了一波波金融创新浪潮的影响,这些金融创新通过各层次投资的非人格化和自主化将信贷扩展至越来越少的受限群体。
对企业家的社会态度和收入不平等曲线的走势相一致。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到“喧嚣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通过企业家精神获得的财富或诸如娱乐等其他形式的成就,为社会名流的地位提供了支撑,但如薇拉·凯瑟(Willa Cather)和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的小说所描述的,随之而来的物质主义和道德沦丧既受到了社会的赞美也遭到了非议。 [12] 在经历“二战”的共同牺牲后,个人权力和财富开始受到质疑,大型组织——不管私营的还是公共的、民用的还是军用的——的领导者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知道如何使这些组织更具生产力(Farber,2002)。到20世纪90年代,情况发生了逆转,企业家频频出现在《时代》杂志封面上。最富裕群体再次掌控了超出11%的国家年收入。但这一次,最高纳税群体中只有相对较少的财富归功于食利者。由于包括股票期权在内的高管薪酬的惊人增加,从金融创新活动中获得报酬的人,如风险资本家、对冲基金经理和私募股本合伙人的收入大幅上升,这一次的财富增加更多地归于工作的富裕阶层,而他们通常又把自己的钱投资于创业企业。
三、企业家精神发展的环境和条件
1920—2000年的企业家精神由三段截然不同的发展时期组成。第一段是1920—1941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金融混乱时期,以生产率的下降及其对失业的影响为特征,以美国被正式卷入“二战”为结束。 [13] 对企业家精神而言,该时期非常动荡,随着许多新创公司在大萧条之前和大萧条时期的迅速崩溃,20世纪20年代发展迅猛的行业出现了大量机会。从“二战”到始于越南战争的长期通货膨胀(1941—1974)是第二段时期,该时期虽经历了持续不断的国家动员,却也实现了相对稳定的强调最优化的经济均衡。该时期创新并不是大公司的重要优先事项,或者在许多行业受到高度欢迎,但军方所需的特定“高科技”企业及能将军事技术转化为民用产品的“交叉行业”除外。1975—2000年间为第三段,以伴随全球化而来的信息革命的蓬勃发展为特征,两者共同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该阶段见证了许多不同经济部门创业机会的复苏,特别是信息技术和新消费品领域。该阶段始于以“滞涨”为特征的经济衰退,继之于一场金融制度革命,而这场革命又以一系列金融泡沫告终:如电信行业崩溃、互联网狂热以及21世纪之交发展而成的次贷危机。上述企业家精神的各个发展阶段都以其自身的独特制度发展为特征,且三段时期的企业家精神都是当时环境的一个重要而又独特的组成部分。
四、1920—1941年的第一段时期:寻求经济的自我调节
20世纪20年代,经济产出不断上升,直至1929年达到了1940年为“二战”提高产能之前未再达到过的水平。这一成就是有意识地致力于合理化和提升效率的结果。除了生产率外,重要的贡献因素还包括产生了新型消费的各种社会因素,如社会流动和郊区化、越来越多的人口拥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以及休闲时间(Bakker,2003;Melosi,2000,第206—207页)。尤其受益于这些因素的是一些大型高增长行业,这些行业在世纪之交以技术开发起家,利用战时需求和金融进步,在战后实现了规模扩张。这些行业包括:交通领域的两大新兴行业——飞机和汽车制造,以及参与这两大新兴行业的基础设施建造商、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商;电气化行业,主要由电动设备、电影业及改变了娱乐和广告业的电子消费产品等构成。推动这些行业发展(不管技术还是资金上)的企业家,如电气先驱者和大城市电力公司的公认领军者塞缪尔·英萨尔,已将他们战前活动的大量收益用于投资。在20世纪20年代的高增长行业中,标志性的增长行业是无线电,它为企业家特别是富于发明精神的企业家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机会。若19世纪发明者能得到资助的行业是电报和铁路,则20世纪发明者能得到资助的行业则是汽车、飞机制造、家用和工业电气设备及娱乐,特别是电影和无线电。它们当中,无线电及其衍生出来的电子设备是创业机会的最大来源。
(一)无线电:发明与创新
无线电技术基础被认为既有军事战略性又对日常民用颇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和“交叉”产业的结合体。出于该原因,美国政府在“一战”时期进行了干预,以确保无线电技术不被知识产权争端所“绑架”,因为在此前的时期,知识产权争端曾困扰着无线电技术和其他新兴技术。这类干预的特征是对美国马可尼(American Marconi)的接管并将之重组成通用电气的子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RCA),该公司的设立旨在管理通用电气、西屋电气、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和联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的专利池(Aitken,1976;Chandler,2001,第2章;Reich,1977)。该行业的发展得到了这一时期重大社会运动的推动。例如,前几十年的移民汇聚是一个关键增长因素,因为非英语移民群体通过无线电这种新媒介来了解新移居地的社区、娱乐及其他信息(Graham,2000,第149—150页)。
“一战”前,无线电主要作为一种点对点(即船到岸)的通信媒介,但其发展得到了成千上万业余无线电运营商的推动,后者帮助开发出了无线电艺术并在“一战”前和“一战”时贡献了许多方面的专业知识(Douglas,1987)。从1920年匹兹堡设立的KDKA无线电台开始,无线电演变成了广播。到1930年,有近1400万美国家庭安装了广播,其采用率远高于电气化和电话。广播和电影这两种技术上可行的娱乐形式,均满足了对其使用的迅速增长,尽管收音机的销售量先后在1926年和大萧条时期出现大幅下降。对企业家而言,同无线电相关联的机会包括收音机以及专供经销商和维修店、广告商、公关公司和娱乐提供商的电子元件设计与生产。尽管活跃于无线电行业的公司数量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初的行业洗牌中急剧减少,但少数新创企业幸存了下来,并成为辅助设备的大型供应商。给无线电行业的企业家精神发展造成阻碍的一个因素是前文提到的美国无线电公司对无线电相关专利的控制,它要求所有无线电生产商都必须获得“专利包”许可证,而不管这些生产商能否利用这些“专利包”。这对规模较小的企业是重大负担,对通用电气和西屋电气等电气公司对元件制造和供应的控制而言亦然(McLaurin,1949)。
(二)混乱与创新
“喧嚣的二十年代”不仅同突然增长的行业有关,疯狂的繁荣也掩盖了其他形式的经济混乱,后者反过来又促使老牌公司往往通过同创业企业建立关系来采取应对性的创新举措。虽然总产出有所增加,但是在采矿业、钢铁、制鞋、家用品和服装生产等以往较稳定的部门,就业人数出现了下降。 [14] 受战争年代机械化进展迅猛的刺激,公司利用电力来取代人力,并探索出了内燃机在交通运输和农业中的新用途。当家庭雇工和农场工人到制造业企业和政府机关就职时,家庭和农场引进了新的劳动节约型设备。由于公司试图隔离外部变化,在公司层面出现了一场新的合并运动。许多获得必要融资的企业收购了其他企业,特别是竞争对手企业和供应商。然而,即使在各类产业联合中脱颖而出的公司,也不能只凭规模获得进一步发展,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不再能依靠以往供给市场的商品维持生存。为了引进新鲜血液,许多公司积极“拥抱”社会需求,如伴随1918年流感疫情而来的清洁家庭运动,或者利用家政学等新的科学基础来更新观念。
像20世纪20年代末广为人知的那样,跟上“美国新节奏”(The New American Tempo)并非轻而易举。有学者表明,为了吸引更广泛的客户群体,为了同新房和汽车购买抢夺居民消费支出,即使最老字号的公司也不得不改变它们的产品线,并且通常以创新为手段。公司加入了新的专业知识,如设计,并同客户建立新型反馈机制。科勒公司(Kohler,现为美国第三大卫浴公司)这样的创业企业,废弃了由传统水管工和管道供应承包商主导的老式分销渠道,通过整合样品间、设计师和色彩专家来直接吸引客户(Blaszcyzk,2000)。特种玻璃公司康宁玻璃公司(Corning Glass Works)原来只向实验室出售耐热玻璃器皿,现在开始推行多样化,与不同市场建立联系,以此来销售可视烤箱器皿和餐具。连不愿以创新面目示人的福特汽车公司,也开始改造其一成不变的T型车,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 [15]
人们通常认为,此时的企业家精神有其不同的形态,在许多行业,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都是新型的共生关系。被迫创新的大公司随时都有可能退回到老路上去,但科勒和康宁这样的创业企业吸取了它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验教训,通过引进新的产品线或新业务来积极利用经济冲击和剧变。百货商场和连锁店等大型经销商采取了融资、全国性广告、消费者教育计划,以及用分销管理来应对供应全国经济带来的挑战等措施,而较小的设计和生产家庭则采取了更好地联系当地消费时尚需求的策略,同时以较低的价格更有效率地生产更高质量的商品。
尽管(或者也可能是因为)所有企业均狂热地致力于提高效率或在创新和控制之间谋求平衡,但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仍使许多人担心只靠私人部门已不能实现经济秩序。虽然新兴行业,如汽车、飞机制造、电气设备和消费电子产品等创造了新机会,但20世纪30年代工作岗位仍在大量流失。公众将这点归咎于两件事:金融体系,尤其是股市上发生的滥用公众信任;以及伴随研发制度化而来的为追求效率而无节制地利用新技术。 [16]
(三)制度转变:股市与创业基金
股市的发展既促进了高增长行业的快速崛起,又推动了购买力的后续变化。20世纪20年代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既为谨慎者也为胆大妄为者创造了大量机会。已发生的重大变化使美国证券市场能为新公司提供可靠的融资。根据玛丽·奥沙利文(Mary O'sullivan)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的新股发行量远高于美国以往任何历史时期(O'Sullivan,2007)。例如,飞机制造和无线电行业的企业不需企业家自己提供资金就能获得融资。不得不改进自身业务或同其他公司合并的企业,也能获得它们所需的资金支持,而已经合并的企业则可找到融资以收购业内其他公司。若19世纪90年代的大合并运动旨在组建市场,20世纪20年代的并购运动则旨在改变公司金融结构、发行股票或赎回股票以提高剩余股份的价值。在“一战”后的合并时期,许多行业中的大公司比小公司更易于获得资本。
除了新形式的股权融资外,债务融资也很重要,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绝大多数时期美国都维持着较低的利率,这刺激了投资者寻求收益更高的投资。瑞士“火柴大王”伊瓦·克鲁格(Ivar Kreuger)以欧洲政府的名义向试图谋求高收益的不知情的美国投资者出售战后赔款债券大发横财,且被视作慈善家,直到其自杀才披露了他不只是金融企业家,更是个大骗子。 [17] 美国小企业往往诉诸借贷来满足资金需求。只有极少数20世纪的企业家像亨利·福特那样,既不想和股市有任何关联又极其讨厌信贷市场(Zunz,1990)。尽管福特在“一战”后的经济衰退时期遭遇了严峻困境,但他并没有陷入负债,因为他的供应商和经销商都乐于帮助他。但是,豪恩谢尔(1984)认为,福特坚信,赊销(信用销售)对消费者有害,并“坚决拒绝将消费信贷看作合理的消费工具”。
成本低廉的消费信贷为购买郊区新房产和相关耐用商品提供了资金。城镇反过来发行自己的债券,以筹集资金投资于所有新社区和业主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产阶级消费者借债购置汽车和房产的行为,将其储蓄转换成投资的行为都是受到鼓励的。许多人花光了他们的低息银行存款,将储蓄投入股市。尽管20世纪初,此类消费和投资可广泛获得信贷,但到20世纪20年代末,所有形式的投资都变得成本高昂。
银行业被认为是一个不适宜合并(至少是跨州银行合并)的行业。但像其他企业一样,银行也意识到了全国性市场的发展机遇,试图采取措施获得利用规模优势所必备的规模。银行业企业家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 Eccles)后来成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的美联储主席,他最早创立了一家银行控股公司,该行在特拉华州获得特许状,收购并拥有不止一个州的多家银行,并使它们紧密地整合在一起,以获得东部地区的银行业务、规模经济和巨额资本(Hughes,1986)。
但随着高增长行业的合并不断发生,市场上能找到的绩优股(蓝筹股)数量大幅下降,已发行股票的价格因此节节攀升。当普通投资者不再买得起许多高价股时,一些创业投资公司从英国引进了投资信托,以给小投资者提供多样化持有股票的机会。绝大多数提供这种信托的资产管理公司很快就遭到了失败,但JP摩根、高盛、波士顿独立万通(Boston-based independents Mass Mutual)和先锋(Pioneer)等少数公司幸存了下来。于是,新型共同基金行业、创业管理公司和独立的金融企业家由此诞生。
(四)萧条阻碍了创业活动
如前文所示,伴随1929年股市大崩盘而来的大萧条,暴露并加剧了各种经济缺陷,如过度扩张和杠杆化企业的溃败倒闭、银行业机构的相互关联和股市信贷的唾手可得。学术界对大萧条的起因仍争论不休,但大萧条的结果之一便是需求发生了变化,以及普通民众的购买力显著下降。在1929年11月21日胡佛总统召集的一场工业巨头会议上,亨利·福特观察到,“美国产出已相当于并超过的不是美国人民的消费力,而是他们的购买力”(McElvaine,2003)。自相矛盾的是,中上阶层却获得了较他们以往相对更大的购买力(Szostak,1995)。1929年至“二战”爆发前的10年里,并非一贫如洗的普通消费者虽然继续购买商品和服务,但许多人的消费是由另一项金融创新推动的,该创新就是金融和工业巨头通用汽车公司引进的分期付款计划。经历前10年的混乱和财富毁灭后,分期付款计划提供了一种颇具吸引力且安全可靠的财政约束。
持续的战时萧条对美国经济随后的走势产生了持久影响。倡导新政的民主党承诺联邦政府将解决失业和经济动荡问题,由此入主白宫。联邦政府着手调整经济中的重要领域并提供资金,先是《国家复兴法案》时期的公共工程,随后主要是国防支出。在所谓的“第二次新政”中,罗斯福政府还转向了严厉执行反垄断立法(此前它们大多是一纸空文,并未得到很好的实施),以及改变其他监管措施。
20世纪20年代的无序增长伴随着新行业迅猛增长以及大量新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引进,为个体企业家精神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环境,20世纪30年代的条件不仅相当不利于创办新企业,且使新创企业的存活率大大下降。除了不易获得资金外,日益增加的监管负担使一家自力更生的企业更难实现最小有效规模。许多由投资企业家掌控的企业要么被大企业收购,要么被它们逐出竞争市场。企业(特别是中小规模的)破产越来越频繁,并于1933年达到顶峰,直到“二战”前仍维持在高位。大多数情况下,罗斯福新政中实施的一些试图调整经济复苏的零散努力止步不前,一开始就带来了担忧和悲观情绪(Raff,1991;Hughes,1986)。
未过度举债的大企业能更好地抵抗长期低迷,许多这样的企业开始抓住机会寻求创业机会或扶持创业企业。 [18] 对管理得当的公司而言,大萧条为它们的新型创业提供了机会,使其可以利用研究型发明而非依赖直接需求,来预测并多元化地利用长期商机。 [19] 例如,百路驰(BF Goodrich)开始试验人工橡胶,美国无线电公司力图完成可行的电视系统,美铝公司(Alcoa)研制可用于住房和大型建筑物的结构铝,康宁玻璃生产出了新的高纯度玻璃和大型望远镜镜片,杜邦公司则在尼龙和其他人造纤维领域遥遥领先。 [20] 对于这些公司和其他许多公司来说,20年代残酷的需求压力暂时得到缓解,这为它们致力于长期研发新产品和服务提供了机会。虽然有一些企业在设立研究部门不久之后,就因经济原因关停了它们,但那些在大萧条时期保留并经营研发实验室的企业,不仅积累了知识,还获得了技能,这些技能为随后几十年的新业务增长奠定了基础。 [21]
20世纪30年代初,许多观察家把大萧条归咎于利用工业研究追求效率的提高。甚至像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这样一名罗斯福新政时期的重要人物也认为,技术性失业是发明的一个必然结果(National Resources Science Committee,1937;转引自Rhodes,1999)。麻省理工学院(MIT)院长卡尔·康普顿(Karl Compton)和贝尔电话公司总裁弗兰克·朱厄特(Frank Jewett)等科学家兼政治家积极反对这种技术悲观主义,并试图说服公众不要简单地把科学、就业和繁荣混为一谈。他们认为,与公众的观点相反,资金充足和组织合理的科学创新是增长的持续推动力,远比托马斯·爱迪生等独立发明家的试错性“想象”要可靠。他们发起运动,宣称工业研究在未来经济增长中将起关键作用,试图以此来挽回科学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他们的运动也为大幅提高公司和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公共经费铺平了道路。 [22]
(五)工业研究对企业家的影响
“一战”后,工业研究已实现制度化。这里有两层含义:首先,大公司使内部研究在公司层级制中占有一席之地;其次,企业实验室与其他超越本公司边界的组织形成了一整套关系和实践网络,即所谓的美国国家创新体系。 [23] 由此导致的密切和互动关系从未完全拒斥以往时代的发明型企业家,但确实将他们放在较不重要的位置,处在大企业和研究型大学形成的更正式的知识网络扩展边界之外。
如第十三章已讨论的,“一战”前的美国,只建立了少数特殊的开拓型公司研发实验室。 [24] 根据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RC)的调查,有500多家企业在“一战”结束后的10年内成立了企业实验室。 [25] 绝大多数人认为,工业研究中的领导地位为“一战”期间的德国带来了巨大优势,特别是在先进的军事物资、武器装备和毒气上。由于内部研发需要大量投资,且在任何行业只有最大的公司才有实力支持它们,已投入研发并愿意分享或许可转让其成果的企业正为整个行业创造着知识资源。联邦政府积极鼓励私人投资于研发活动。特别是在柯立芝执政时期,公司对工业研究提供资金使美国无线电公司这样的技术型企业成为被认可的技术垄断企业(Sturchio,1985)。
若作为一种机构的大公司到20世纪20年代已变得同质化和单一化,最新流行的公司研发部则不然(Zunz,1990)。工业研究实验室会根据个人魅力及公认的科学成就从国内外招募领导者和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公司实验室已不是公司拥有的第一批实验室,也不同于已投入使用的其他实验室。在公司实验室出现前,已经出现了工程实验室、销售实验室、实验工厂、授权实验室、设计工作室和测试实验室。像一代人之前的公司形成时期一样,它们的技术员工包括了来自许多学科和职业的各色人等。早期的实验室对普通员工而言并非遥不可及,也没有神秘到成为客户、授权商和供应商(他们许多都是企业家)的禁区。但是,当公司实验室不断激增且与政府资助的研究越来越相关时,其研发功能便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即越来越远离普通员工和学院化,且不会因为与生产基地的密切关系而受到日常干扰。
20世纪20年代,公司研究实验室同其他工业实验室、大学院系、科学协会以及国家标准局(NBS)和专利局等政府部门建立了联系。 [26] 到“二战”时这些网络已得到进一步发展,但仍局限于同政府资助部门和部分研究型大学之间有重要往来,形成了一套自给自足且越来越封闭的一体化创新体系。 [27] 经验丰富的发明者和某些大中型公司之间的良好关系延续到了20世纪30年代,但是,随着业余发明者和民间匠人的产品创意颇受高增长行业公司的欢迎,这段“蜜月期”也就随之结束(Hintz,2007;Douglas,1987;Israel,1992,结论部分)。
“一战”后,公司实验室有望为大公司发挥新作用,为大公司战略目的服务,创造长期机会,并充当公司不同部门之间的仲裁者和标准制定者。许多公司实验室掌控了其所在公司的整个研发议程,它们有时会关闭或整合其他实验室,且常常改变他们的做法(Graham和Pruitt,1990)。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实验室会变成公司领导者的组织代理人,推动创新的制度化。1951年,美国无线电公司总裁大卫·萨尔诺夫(David Sarnoff)通过兼任公司研究实验室的主管,明确推进创新的制度化。
五、第二段时期:战争与创新体系
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而言,“二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子,说明联邦政府若采取干预和最优化措施则经济可以取得何等成就。通过大型公司实体可以最高效地实现政府指导和最优化,后者反过来可能又依赖甚至起源于较小的创业公司。在始于“二战”的第二段时期,成功的企业家和创业公司必须善于同政客和采购专员打交道,其老道程度令经济史学家乔纳森·休斯(Jonathan Hughes)把他们称为采购企业家。 [28] 主要充当政府供应商的大公司被称为“主承包商”,他们主要靠政府研究合约支撑自己的研究,并将较小的项目转包给其他分包商。在军方业务上,主承包商经常充当中介人和保护者,服务于不能处理政府需求的小型创业企业和那些因担心不得不在知识产权上做出妥协而不愿直接和政府打交道的大公司。
将经济导向战时模式的努力,强化了20世纪30年代末技术依赖型大企业所体现的模式。通用和福特等公司刚刚扭亏为盈,就因准备“二战”和《租借法案》(Lend Lease)而被迫改变工作重点,把产能转到军工生产上。西屋、通用电气和美国无线电公司等拥有研发实验室的大公司,为一些服务于“二战”需求的大型秘密科学项目,如麻省理工学院的雷达项目、哈佛大学的无线电项目、芝加哥大学和洛斯阿拉莫斯市的曼哈顿计划,贡献了它们的工程和研究人员及项目管理的专业知识。这些跨学科项目涉及公司研究员、大学研究员和从其他机构招募的研究员之间的合作研究。他们采用的跨学科方法及其产生的发明成了大学创业的早期形式,且为战后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机会。
“一战”时期,战时动员的主要挑战给了制服生产商、食物供应商及军需品和车辆制造商,但“二战”给许多美国制造商带来了更困难的选择。当动员时限较短时,老牌大企业较之小企业具有更明显的优势,且初创企业没有多少反应时间。新的军方采购计划需要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从海外或交战国进口的关键原材料的人工替代品,包括制鞋和轮胎用的橡胶及医疗设备和用品的关键材料。面对不可预测的需求,老牌企业可继续生产其常规产品,或者也可选择增加那些有明确军事需求的产品产量,对于后者,政府承诺了新的创新性补偿安排,即“成本加价”补偿。如在橡胶工业,百路驰选择了继续生产橡胶,固特异(Goodyear)则选择成为一家飞机制造商,以回应政府的国防计划(Blackford和Kerr,1996)。公司高管代表他们的公司频繁往返于华盛顿,部分是出于他们的爱国责任,部分是因为他们发现战时生产委员会(WPB)和其他协调机构的服务有助于获得有关当期需求和战后时期可能出现的竞争的有价值信息。但是,正如一些创业企业试图避开政府的知识产权要求一样,由私人承担转向新的军事项目产生的成本,可能意味着持续遭受项目任意中断所造成的严重损失。
备战为知名的新进入企业创造了大量机会,但很少针对小微公司。由于美国军方长期以来偏爱能以大规模和低成本提供物资的大型集中供应商,所以它很自然地会寻找已展示出必要管理和组织技能的新进入企业。钢铁巨头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朋友亨利·凯泽(Henry Kaiser)便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当政府怀疑美国铝业公司有无能力和意愿满足其各方面的需求时,凯泽被说服去执掌该公司的业务。政府已对美铝公司作为一家垄断企业提出过反垄断诉讼,在这种情况下,该公司似乎不太愿意继续扩大产能。传记作家史蒂文·亚当斯(Steven Adams),将凯泽称为一名新型政府企业家(Adams,1997)。战后和冷战时期涌现的其他类型的企业家都是乔纳森·休斯所谓的采购企业家的变体,如具备国防相关领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技术型企业家,以及根据自己的研究项目创建新企业但往往仍保留大学教职的学院型企业家。对于这些新型企业家,政府赞助不仅提供了必备资金和专门知识,而且还提供了稳定、可预测且通常无关乎成本的需求。 [29] 当然,其缺点就是由于政府机构中的官僚化以及同他们打交道的公司,逐渐形成了一种锁定效应。
(一)政府角色、均衡与民主化
相比于“二战”前或“二战”时期,“二战”后时期的企业家精神有明显不同。若20世纪30年代的逻辑主要集中于科学创新,即发明能重启经济发展的新产品;战后时期的逻辑是最大化现有工厂的产出。许多战后时期被推向市场的产品,均基于战前时期的发明和开发。为满足意料之外的需求水平和降低成本,必须完善生产工序,特别是消费品领域,产品发明已屈居工艺开发之后(Hayes和Abernathy,1980)。
民用经济中的例外是获政府项目资助的旨在提高生活水平和复员军人生产率的产品。例如联邦住房贷款,它使许多人第一次买得起房子,为住房建筑行业创造了大量创业机会,其中尤以大西洋中部地区的莱维顿镇和旧金山的戴利城最为突出,且在全国各地郊区随处可见。对于战后以全职家庭主妇为特征的核心家庭,另一个重要的增长领域是大众娱乐行业,主要是电视和流行音乐唱片。围绕电视广告、电视机制造和唱片制作及代理权和维修服务,涌现出了大量创业机会。
20年间(1950—1970),70%的美国劳动力受雇于大公司,为大众消费者提供相对可预测的服务需求。不管这些企业供应钢铁、铝、建筑设备、电视、计算机、化学制品还是电子产品,它们似乎都能维持稳定的均衡并掌控自己的命运。当现有产品面临如此大的需求时,企业为何要冒险去发明新产品呢?毕竟,这是一种被视为自我淘汰的非理性现象。但有一个经济部门的创新市场是无穷无尽的,它便是联邦政府,尤其是军方。
政府的角色:资助“大科学”
“二战”期间形成的“三方架构”(three-way establishment)——政府部门、大学和私营企业的共同演进——在和平时期被果断地纳入了军方的命令控制模式(Balogh,1991;Roland,2001)。最终服务于军方、政府机构和消费品市场的指定技术(designated technologies),通过一套后来被称为“大科学”(Big Science)的新型中介组织体系获得融资。如前文所述,公司研究实验室是该新型创新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对政府资源应如何配置、由谁配置持不同意见者展开了激烈的政治辩论,此后的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实现了众所希望的经济稳定。普通民众认为科学在赢得“二战”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科学界应继续优先服务于军事方面的优先事项。战前的工业实验室主要集中在工业和消费品行业,包括人造纤维、电话系统、照明设备及摄影和玻璃器皿。在战后时期,国家工业科研能力的一小部分面向民用目的,相当大一部分则被配置到国防应用领域,美国国防部(DOD)和军方各下属机构控制着研究议程。由于国会议员普遍认为最有望保障其选民就业的途径是军方资助,且民众普遍担忧新的国际冲突将持续带来威胁,但在决定哪些科学学科和问题领域将获得、并通过哪些渠道获得资金时,美国国防部仍有最大发言权。他们同样深信美国必须在科学上实现独立自主,并认为集中投资于基础科学知识将在各种新应用领域获得丰厚回报;政府资助被分配到严格规定且相对较狭隘的科学学科和技术领域,它们中许多同大型战时项目有关。经费从三个不同方面转到研究项目执行者手上,即研究型大学、政府实验室及那些围绕新军工产品开展研究的拥有研发实验室的大公司(Graham,1985;Mowery和Rosenberg,1989,第143页)。冷战时期的许多高科技企业家都起步于某个主导实验室。在东海岸,有林肯实验室、贝尔实验室,它们都和麻省理工学院携手;还有美国无线电公司培养的企业家,他们形成了波士顿128号公路的创新集群。在西海岸,联邦政府有一个特殊的发展目标,使许多高科技企业家从生产电子元件的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开始起家。众多公司脱颖而出,如瓦里安兄弟(Varian brothers)创立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生产微波管的硅谷公司,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以制造科学仪器起家,后来的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离开肖克利西海岸实验室,创设了仙童半导体公司(作为仙童相机公司在东海岸的一个分部),且不久后两人又离开了仙童公司,和安迪·格鲁夫一同创立了英特尔公司(Lécuyer,2006)。
通过主承包商加以协调的国防动员反过来为各式民用企业创造了环境。许多战后时期的设计技术都出现在交叉领域,如飞机和航空电子设备、计算机和控制器、电子和通信以及核能和固体材料。尽管美国的政治经济辩论认为不应由政府决定赢家和输家,但国防预算和未披露的分配到知识界的数百元万美元资金,事实上有选择性地创造了吸引和聚集绝大多数国家动态资源的技术型产业。消费电子产品利用了相同的知识库,并和军事电子产品共享了许多相同的生产工艺。甚至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都要有国防理由的支持,如国家高速公路系统、包括外语在内的各层级教育投资,所有这些都以某种方式同联邦国防优先事项相挂钩。
当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Sputnik),从而使美国政府对国防动员的资助迅猛增加时,政府的科研资助热情开始逐渐消减。艾森豪威尔总统最明确地表达了由此导致的担忧,作为美国“二战”期间最卓越的军事领袖之一,他于1961年向全国作告别演说时,提醒人们警惕“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在政府议会中不受限制的影响(Kevles,1978,第393页)。
驾驭“二战”后日益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需要类似于政府企业家精神的组织技能,以具备充当政府承包商的资格。乔纳森·休斯将成功捍卫了联邦心理健康计划的玛丽·斯威策(Mary Switzer)和重塑了美联储的马里纳·埃克尔斯等人物视作政府企业家,他们像瑟曼·阿诺德(Thurman Arnold)改变了联邦反垄断政策那样,有效改变了美国政府的发展进程。尽管他们三人都成功创立了新计划,并找到了使之有效运行的组织手段,但没有一人完全诉诸官僚机构的扩大。三人都力求推动立法,或引入行政实践程序,各个击破华盛顿之外既有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以实现他们认为的必要改革。
但是,在20世纪剩下的大多数时间里,联邦政府的非军事机构呈扩张之势,它们获得了和平时期采购企业家迫切需要的巨额投资:社会保障、国内税收及后来的美国宇航局(NASA)、医疗补助计划和联邦医疗保险等大型机构的数据处理系统。高科技公司可能不会完全集中在供应政府需求上,但对它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政府是其全部业务中相当重要和有利可图的一部分。一旦获得政府项目后,业务关系很容易保持,且在成本加价资助模式下风险相当低。在这种情况下,高科技企业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华尔街充满活力的源泉,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连续不断的防御准备和冷战时期迅猛扩张的联邦政府支出这一背景下,这种性质的政府采购使个人和公司创业比20世纪20年代更狭隘地进一步聚焦于技术。但在所有设计技术领域,即通信、电子产品、新材料和计算机技术,采购企业家都有着诱人的机会(Mowery和Rosenberg,1989;也可参见Galison和Hevly,1992;Galambos和Pratt,1988;Dyer,1998;Dyer和Dennis,1998)。特别是计算机和基于计算机的技术,后来被统称为信息技术,渗透到了各行各业(Coopey,2004)。虽然计算机的早期使用主要面向导弹开发,但不到10年时间,计算机技术便获得了更广泛和更普遍的应用,如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的数据处理中心,以及为制造工艺提供的自动化控制系统。
(二)计算机:信息技术革命的基础
尽管所有的大型科学项目都为老牌公司创造了大量创业机会,但它们绝大多数和在美国传统上受管制且被管制理论家归类为“自然垄断”的行业(如电力和通信)有关。在研究设备上,这些大型科学项目也是相当资本密集型的,在开发上,尤其需要巨额投资,如核粒子加速器、核燃料加工设备和核电站,及雷达和收音机专用的电子元件制造。对新进入企业和小型企业来说,创业机会最多的领域主要聚集在一开始以计算器而为人熟知的信息设备周围。
如坎贝尔和阿斯普雷(Aspray)所指出的,最终产生了处于信息革命核心的多层面信息技术产业的技术,建立在20世纪上半叶已形成的统称为系统化管理的技术、系统和实践的庞大网络基础上。但现代计算机本身是一种关键设备,少了它,系统的其余部分将不复存在。计算机的研发最初出于军事目的,战争期间,不同大学的若干组发明家几乎同时“发明”计算机——哈佛的艾肯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均开发出了所谓电动式计算器的类似版本,这些计算器旨在处理“二战”武器装备所需的复杂计算任务(Yates,2000;Campbell-Kelly和Aspray,1996)。
尽管都是学院型企业家,但最早参与计算机研发的发明家很少意识到除了给为此提供资金的武器系统外,这种新型高速计算器可能还有商业应用价值,有许多在计算机面世前就被淘汰。宾夕法尼亚大学摩尔学院的埃克特和莫克利(Eckert and Mauchly)团队是个例外,他们意识到这些设备不仅是数学计算机器,还将使自动化处理大量信息任务成为可能,庞大的信息处理对大公司及迅速扩张的政府部门和机构(它们对信息的要求越来越高)保持正常运行必不可少。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花费了数百万美元研发成本的设备的市场仅限于已雇用了数千名专业人士处理巨量信息的大型组织,或者有性能要求的先进武器系统,其中速度和信息容量至关重要(Yates,2005)。美国曾出现一段5年(1948—1953)的窗口机遇期,当时将计算机设备投入商业运作所需的资金数量足够小,以至于在那些能获得资金且已建立起分销网络的大型老牌企业抢得机遇和建立新产能之前,新进入企业就能站稳脚跟。另一方面,鉴于大企业的技术惯性,若不存在积极行动的新进入企业,大企业是否会如此迅速地进行投资颇值得怀疑。
三类企业很可能涉足新兴计算机产业,即电子公司、商用机器公司和创业型初创企业。第一类企业包括了8家公司(IBM和其他7家小公司)。它们当中,除了埃克特—莫克利电脑公司外,另两家初创企业是CRC和DEC(数字设备公司)。IBM是当时旨在帮助其他初创公司实现成功转型的商用机器公司,4家电子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通用电气、宝来(Burroughs)和收购了埃克特—莫克利的兰德公司——在该行业待得足够长,它们通过创建新企业帮助重塑了计算机行业(Cortada,2000;Fabrizio和Mowery,2007;Usselman,2007)。尽管三类企业的规模、经验和禀赋差别极大,但它们都是各自行业的创新者,且配得上创业企业的称谓。
埃克特和莫克利的经历表明各类企业的小企业家,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家,在战后环境下所面临的困难有多么棘手。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是确保他们的新创企业能获得融资。由于既需要大量不可预测的资金,又缺乏相信他们产品且愿意掏钱购买的买家,规模不等的早期开发者采取了一种军方合约和商业订购相结合的方式,来为他们机器的初始开发筹措资金。他们均严重低估了该项目成功所需花费的时间和投入的努力以及最大的那些挑战。埃克特和莫克利甚至在战争结束前就曾试图寻求资金赞助,但只能筹集到小额资金,这对研发所需的投入而言远远不够。他们尝试过的筹资对象(绝大多数是老牌企业)中,没有一个愿意资助他们最保守的筹款数目,更不用说他们在实际开发计算机埃尼阿克(ENIAC)中将花费的更巨额的资金。最终,埃尼阿克计算机的商业版获得了一些民用合约的融资支持,但相比于军用合约所能给予的资金,仍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最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功主导了计算机产业的是IBM公司,但IBM的胜出并非源于它是技术领导者,而是因为它为用户设计出了一套管理和技术支持系统,该系统使用户的计算机投资变得有利可图。几十年间,这套系统像垄断者一样运行,竞争对手不易模仿,且不对外部供应商开放。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当IBM同意向外部企业开放其研发部和IBM个人电脑等利润较低的产品时,法院判定(针对IBM的)反垄断诉讼告一段路。
IBM孵化了自己的分拆企业家,如曾多年担任IBM公司销售主管的罗斯·佩罗(H.Ross Perot),他于1962年离开IBM并创建了自己的公司——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DS),该公司主要为政府机构提供数据处理服务。20世纪80年代佩罗将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和通用汽车合并时,他成了亿万富翁。通用汽车公司的高管认为,在通用汽车公司内部工作的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员工的创业行为和态度带来无法容忍的破坏性影响,佩罗便完全出售了电子数据系统公司。
IBM公司出于自身需求,无意中帮助创立了创业企业,这些创业企业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追赶苹果公司的个人电脑业务,当时,IBM已经在小型计算机的竞争中不敌数字电子公司等创业企业。由于既不能做到将所有必要的内部组件和软件生产出来,又不确定这样做是否能成功地组合出小型计算机,IBM便将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外包给了一家由哈佛大学辍学生比尔·盖茨及其合伙人保罗·艾伦所经营的新创软件企业,同时将微芯片设计转让给了从仙童公司中分立出来的英特尔。当“蓝色巨人”IBM像其他许多更早期的高科技公司一样陷入收缩和重组时,这两家企业却很快实现了远高于IBM公司本身的账面价值。
(三)封闭创新体系中的制度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专利体系的批评家们就尖锐地指出,为确保给发明者公平补偿而创立的制度已被大公司所绑架(Noble,1977)。莱昂纳德·赖克(Leonard Reich)指出,以专利律师和雄厚财力为支撑,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和通用电气等公司采取了全部买下(buy up)的防御策略,并压制任何威胁其控制自身行业技术变革的专利。它们要么拒绝转让自身持有的专利,要么索要高额专利费或对专利使用附加极其苛刻的条件,以至该技术变得不再有利可图。同时,它们还会对侵犯或试图围绕其专利从事发明的人及时提出起诉。
一个类似的讽刺性现象出现在反垄断制度中,该制度试图最大化公司之间的竞争,并为消费者保持低价格;当严格执行这一制度时,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20世纪中叶,努力抵消这些相互作用的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创新和企业家精神非常重要,这事实上推动了美国创新体系的终结,因为在该体系下,获取创意和研究变得更加严格,且保密和排他性在20世纪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里颇为盛行。
专利与反垄断
如前面两章所表明的,美国早已建立起了较好的专利许可和反垄断体系(Khan,2005)。美国在建国之初就创建了专利体系以鼓励发明活动,同时,专利的有效期旨在防止它们被滥用于对贸易的技术限制或阻碍连续创新。申请专利需支付的较低费用只是为了补偿管理成本和鼓励创业活动,这种安排一直持续至20世纪90年代。反垄断立法,特别是1890年的《谢尔曼法》,适用于专利垄断和其他形式的贸易限制。美国专利体系已在没有任何规则制衡垄断的情况下,运行了一个世纪,但是,当公司而非个人成为专利持有实体后,该体系开始遭到广泛滥用(Markham,1966)。
无线电领域颇有争议的相关专利案例是这一更广泛问题的一个例证,且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是一个问题(Aitken,1976,1985;McLaurin,1949;Lécuyer,2006)。一方面,美国无线电公司对“无线电相关”专利池的统一控制,使这项重要通信技术迅速应用于军事目的和完全未预见到的无线电广播领域。但美国无线电公司控制所有无线电相关专利的能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遭到了雷神公司等大量小型电子公司的强烈抵制。像飞鸽(Philco)等电子公司利用战争期间专利许可费暂缓实行的机会,扩张自身的研究,在战后不得不给美国无线电公司支付巨额的“一揽子许可费”,因此陷入了困境。 [30]
反垄断政策及其实施的一大转变始于20世纪30年代,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只有在“二战”期间暂缓实行,当时,耶鲁大学法学教授瑟曼·阿诺德被任命为罗斯福政府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的负责人。阿诺德很快就重组并扩张了他掌管的反托拉斯局,使之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名杰出的政府企业家。尽管阿诺德公开质疑美国的反垄断法,但他很快便以推行反垄断法震撼了整个工商业界。阿诺德认为,虽然美国人不信任大公司,但恰恰不是大公司的庞大规模,而是其蓄意的行为导致消费者未能获得效率带来的好处,这是一种更大的罪恶。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阿诺德采取了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同时归档的做法,给公司高管提供服罪判决书以作为逃避个人牢狱之灾的一种手段。从1938年起,司法部发起了数百次调查,覆盖几乎所有行业,如住房和建筑、轮胎、化肥、玻璃制品、电影、电气公司及石油和运输等。由该法律维持的新活力被证明在创造不确定性和改变行业竞争格局上颇为有效,但部分由于这一时期更宏大的商业环境,其对创新的影响尚无定论。 [31]
尽管反垄断起诉在“二战”期间被延缓实行,但战后政府继续推行执法诉讼并逐渐拓宽它们的适用范围。虽然具有重要战备意义,但美国无线电公司、美铝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电气和许多科技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均遭遇了反垄断行动,从而导致成千上万专利或免许可费或以极低成本被转让。美铝公司被迫将其最新技术转让给竞争对手,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政府创立的凯泽公司(Kaiser)和雷诺兹公司(Reynolds)。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也被迫将其核心晶体管和半导体专利无偿转让给所有新进入企业。
进入20世纪6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反垄断政策可以有效刺激研发投资,因此自然也是创新的催化剂。当专利政策和反垄断政策之间存在冲突时,后者通常更占优势,但这并非因为法院禁止在专利许可协议中订立价格固定条款,并设置了更高的可专利性(patentability)标准。然而,史蒂夫·于塞尔曼(Steve Usselman)在考察IBM的案例时坚持认为,美国专利体系的优势在于它虽同监管体系的其他部分不相协调,但大型企业仍能找到适应该监管体系的方式,往往是通过损害小公司的利益和限制它们获得技术的能力(Usselman,2004)。被要求强制授权的公司,通常会选择依靠保密而非获取专利来保护其知识产权。就这点而言,它们也得益于逐渐超越了军方承包商范畴的冷战安保体系(Markham,1966)。
即使瑟曼·阿诺德以公司可分享技术的方式,强制促成了一场大变革,但对专利垄断的抑制仍给专利体系带来了意外后果。虽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被迫许可其持有的专利,但仍可以交叉许可,这相当于是一个以货易货体系,使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能够在许多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当施乐(Xerox)在静电印刷技术上的专利垄断被提前剥夺时,它转而采取了一种同日本主要竞争对手佳能大规模交换专利的做法。美国无线电公司在国内的一揽子专利许可方案被责令中断时,它只是将自己的许可制度转向日本的专利被许可方,因而帮助加速了日本消费电子产品行业的发展(Graham,1986)。
20世纪70年代,专利领域的发明数量大幅下滑,这部分是由于前文所述的变化,部分是由于专利局经费的削减。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专利体系的改革,包括延长专利有效期、指定专门法院处理专利案件,以及允许向软件发明授予专利保护,依然有利于专利持有人而非对他们发起反垄断诉讼的人。20世纪90年代,当专利申请费提高后,专利局实现了自给自足,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在美国专利体系下,大部分专利申请人已不再是美国公民或纳税人。该时期,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搜寻专利和获取专利权更加容易,且这种能力很快变得有利于专利持有人,而不管他们是否“使用”该专利。那些“专利流氓”(patent trolls)公司购买了多套专利,但并不打算使用这些专利,而是一直持有,然后起诉某家拥有相关技术的大公司有专利侵权之嫌。不论大公司实际上有没有侵权,它们通常宁愿达成和解,也不愿意走法院审理的路,这将使它们的产品上市延迟数年。这类案例中,颇有名的一起发生在20世纪末,主要同一家电子邮件设备和服务提供商,即行动研究公司(以下简称RIM,黑莓手机的加拿大制造商)有关,该公司因自己的某项专利侵犯了检索电子邮件而被专利持有公司NTP起诉。许多其他公司,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威瑞森通信(Verizon)等,均勉强接受了以巨额赔偿了事的做法,但RIM却忽视了NTP的要求,且在几年后才以近5亿美元的代价解决了该诉讼,这还不包括为应付侵权指控而层层上诉所花费的时间和法律成本。
(四)作为公司型企业家的实验室
事实上,制度化的公司研究很少能培育出大卫·萨尔诺夫等业界领袖所希望的代位创新者(surrogate innovators)。作为公司诸多部门之一,它们很少能克服同僚之间彼此相互冲突的利益。在两败俱伤的争吵中,作为一种自卫手段,或作为增加其工作可测量价值的一种方法,它们往往诉诸通过申请专利和许可专利来提高自身研究的货币价值。
对许多技术型大公司,如得州仪器和美国无线电公司,专利技术的许可收益变得同专利发明有望产生或支撑的创新一样重要,有时甚至比后者更重要(Graham,1986;Jelinek,1979)。最终,这种做法使之前的创新型公司易受更小、更具创新性和更灵活的创业企业的侵害,后者不把知识产权视作收益来源或控制手段。例如,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面临迅速增加其系统带宽的挑战时,无法同更灵活和更具创造性的康宁公司相抗衡。康宁通过20世纪70年代的光纤创新,并在1984年最先将光纤供应给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死敌微波通讯公司(MCI),迫使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提前20年就默许了这场光纤通信革命(Graham,2007)。
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创立于1970年,原本是20世纪30年代许多公司成功追求封闭的公司实验室创新模式的反周期例子,但它反而成了重启美国创新体系的意外典范。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坐落于硅谷中心,是一个肩负长期特殊任务的公司实验室,在发明型企业家普遍感到步履维艰的时期,它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孵化器”。施乐董事长彼得·麦卡洛(Peter McCullough)将设立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作为10年战略投资,计划通过它发明“未来办公室”,以替代受专利保护的施乐复印机。当时,高利率甚至高通货膨胀率导致许多公司质疑研究的价值,施乐从主要的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院系及智库,招募了一批极有天赋的研究人员,他们当中有许多是国防部国防高等研究计划(DARPA)的成员,彼此颇为熟悉。通过有意识地雇用既聪明又有实践经验的研究人员,即想把发明用于实践的人,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很快就成功获得了足够多的发明和充满创意的创业型人才,为硅谷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大贡献。Adobe、Small Talk、苹果电脑、微软甚至谷歌的兴起或至少是它们的创新成功,都可部分归功于施乐小小的西海岸实验室的技术繁殖力。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并不指望甚至没想过要从这些投资中获得早期回报,它的母公司施乐从这些创造性活动中也只获得了微乎其微的报酬。只有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成立几年以后,发明家才离开这个中心,在旧金山湾区寻找更灵活的机会。那时,如下文将讨论的,情况已发生变化,支持个人开发和销售新兴“未来办公室”的制度正在形成。施乐公司后来承认,如果它打算从该实验室的许多副产品(spin-offs)中获益,它本可以从投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中获取大得多的回报。
六、第三段时期:第三次工业革命
20世纪美国企业家精神发展的第三段时期刚开始获得历史学家们的认可,尽管其他社会科学家已提供了一些既意义深远又有启发性且常常相互矛盾的命题,但这些命题不仅需要利用总量数据来验证,还需要用分类证据(disaggregated evidence)和更多定性证据来检验。 [32]
在这段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时期,企业家精神发展的条件受信息革命和全球化这两股力量的影响,它们组成了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继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推行的自由化改革后,全球金融市场也日益自由化,美国受管制的产业开始放松管制。 [33] 历史学家认为,这使国际贸易和竞争达到了并非前所未有、但自“一战”前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水平(Osterhammel和Petersson,2005)。对美国企业家尤其是个体企业家而言,这些进展,连同反垄断政策实施的放松和一些以往受管制产业的放松管制,为个人创造了自“喧嚣的二十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大量机会。
长期的经济冲击终结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商业的运行路径。尽管该时期由一系列几乎严酷至极的挫折组成,但最严重的还是史无前例的高通货膨胀和缓慢增长,即所谓的“滞涨”。由于对这些冲击的应对远不如一些国际竞争对手,因此在那些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美国经济中流砥柱的行业中,如汽车、电子设备和消费电子产品,美国企业正面临着国际竞争。 [34] 以前对国防动员相当重要因而受到保护且颇值得尊敬的美国工业,如机床等,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完全消失不见。新国际竞争的基础不仅仅是价格,还包括质量和性能。“二战”后,欧洲和亚洲采用最新制造业技术和现代管理实践,重建了它们的制造工厂,特别是在钢铁等基础行业。美国制造商被迫陷入了一段长达10多年的“生产率困境”(productivity dilemma)时期(Abernathy,1978;Abernathy,Clark和Kantrow,1983)。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美国经历了生产率增长率的普遍下降。流行解释认为,这种下降是由一系列源于电气化革命的基础技术转向一系列信息技术所致,后者虽然获得了广泛使用,但却未带来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降低了研发支出的回报。数据也反映了美国经济基础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根本性转变。回头看,尽管这些进展被解释为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的题中之意,但它们也可能体现了几十年来对独立创业活动的抑制。如我们已看到的,若这些转变预示了许多大公司及其员工、公司以外的企业家乃至美国以外的企业家即将面临的困境,那么它们同时也开创了大量诱人且可以获得的机会。
(一)公司创业的衰退
随着冷战体系在内部离心力和外部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开始瓦解,大企业中的公司创业也成了一种例外而非一种规则,即使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技公司来说,也是如此。如斯珀吉翁(Spurgeon)和莱斯莉(Leslie)已表明的,创业发展的硅谷模式,往往被视为美国私人企业家精神的象征,深深根植于联邦政府发展西海岸国防工业的战时计划,且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旧与斯坦福大学一起同军方业务关系紧密(Spurgeon,2000;Leslie,2000)。
随着冷战步入常态化以及军事部门基于成本加价法的有保障收益,掌控着基础专利的公司坐享专利保护之果实,受管制公司积极钻监管环境的空子,投资者则开始迷恋“高科技”企业。在一个缺少激烈竞争的充满寡头垄断和成本加价合约的世界里,高科技公司似乎证明了公司创业的回报是无风险的。
但是,由于高利率环境导致维持成本过高和收益过低,大公司和政府机构开始出售或剥离它们的技术,重建、再设计、精简甚至销毁其库存,完全私人的创业机会出现得越来越频繁(Sullivan,1997)。
同时,在主承包商内部,政府资助的研究及其纷繁复杂的披露要求,导致那些将创新者和创新推到边缘的公司出现了官僚化。在冷战的顶峰时期,极少有公司实验室能容忍真正的怪才,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发展出反主流文化,破坏实验室和公司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Graham,1985)。低效、迟缓的官僚程序像蜗牛一样延缓了许多工业项目。官僚程序的负担如此之重,以至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型航空航天承包企业洛克西德(Lockheed)创设了“臭鼬工厂”,以使计划顺利进行。这一最具活力与专业精神的员工亲密组合,致力于在规定时间和预算内启动并完成一项新的开发项目。若臭鼬工厂象征着大公司内部的创造力和高效性,那么它依托政府承包商的迅速扩张则说明了在越来越紧密相连的官僚制这一背景下追求创新有多难(Arthur,1989)。
颇具讽刺性的是,公司实验室作为首要创新者的角色最终损害了许多大企业的创业能力,但使这些大企业对外部企业家的作用重新产生了需求。影响商业创新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依附于冷战时期军事研发的新安全规定,以及它们施加于科学知识传播的诸多限制。 [35]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公司结构的创新,即多部门结构或“M型”结构,它帮助确立了公司实验室作为重大创新原动力的模式。在一次以组织变革实现公司创业的著名行动中,杜邦率先把“M型”结构从武器制造推广到民用产品以促进多元化,后来又将这种组织结构用于创办新企业。“二战”后,其他许多公司竞相效仿杜邦的例子,但这种新型组织形式不仅能且往往也的确导致了不同企业部门之间在争夺资源上展开破坏性的内部竞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求每个部门不断超越自己的公司战略规划和资源配置的做法会偏离统一的行动计划,并破坏有效的公司创业精神。这种转变的结果在塑造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企业集团运动的风险规避中尤为明显。金融界要求公司更多地披露信息,并严厉对待意外事件,这使风险规避和短期技术收益最大化的趋势不断增强,最终导致许多原来的创新型大公司走向衰败。对一开始供职于公司研究部门的人而言,公司研究和多部门结构带来的组织问题并未消失。英特尔是下一代最成功的创业公司之一,事实上,它的创始人就以极不寻常的方式来组织研发活动,英特尔聘用了许多博士,却把他们分派到生产一线,并在公司的所有业务部门都设置了研究机构。
尽管“二战”后公司实验室非常有吸引力——稳定且收入高的岗位、吸引人的研究设备、优越的位置及旅游和设施资源——但许多最聪明的发明家和科学家(特别是那些有创业倾向的)仍选择了在较少安逸的环境下追求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早期技术型企业家从那些试图拓展政府业务的大公司(绝大多数位于东部地区),如兰德公司和仙童公司处获得资金。许多主导工业的研究人员——计算机科学家和材料学家——在看到母公司高管获取了绝大部分研究回报后,萌生出了自己创业的倾向,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起初,他们从朋友、家庭和其他人脉圈子里获得必要资源,后来则主要是大企业的采购合同。他们一开始就获得风险资本这种新融资渠道支持的情形微乎其微。特别是在硅谷,那里的创业气候允许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户外工作,许多车间现场成了一些知名高科技公司的起家之地。威廉·休利特(William Hewlett)和戴维·帕卡德(Dave Packard)、史蒂夫·乔布斯(Steven Jobs)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 、保罗·艾伦和比尔·盖茨,最后是迈克尔·戴尔,以及其他许多如阿泰尔(Altair)计算机成套元件(computer kit)的设计者爱德华·罗伯茨(Ed Roberts)等较不为人知的装备制造商和试验者,为车道、车库和宿舍等领域的新兴“高科技”企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的企业集团运动标志着公司行为的一个转折点,终结了20世纪中叶的大型企业创业模式。在企业集团的模式下,科技公司找到了防范风险的有利方式,金融投机和资产操纵取代辛苦创业的企业家精神,成为获取厚利的途径。因创新不确定性而饱受股价波动之苦的科技公司,(通常会在董事会上)禁不住投资银行家的循循劝诱,涉足包含不同风险特征的无关业务。规模较小的成长型公司开始包装自己,以便成为大公司的备选收购对象。收购方企业很快发现,收购有不同管理特征和资本条件的无关企业,会削弱它们稳定开展产品创新的能力,而这一能力正是更新核心业务所需要的。20世纪60年代康宁对仙童子公司西格尼蒂克(Signetics)的收购就是一桩令收购方核心业务发生重大转移的交易(Lécuyer,2006;Graham和Schuldiner,2001)。即使像北方电信公司(Northern Telecom)这样的大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收购了他们认为技术相关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小公司,在使被收购公司实现盈利上仍碰到了不少困难。其他许多受迅速获取资金和收购股份等狭隘目的所驱使的收购,则遇到了更棘手的难题。当美国无线电公司于20世纪60年代收购了几家服务业和消费品行业的公司后,股东发起了强烈抗议,他们质疑这些无关业务将削弱这家大型科技公司继续主导消费电子产品部门的能力。为证明其批评者是错的,美国无线电公司引进了作为第二代消费电子产品的视频唱片,却导致了近10年代价惨重的决策失误,且最终不得不于1984年宣告破产(Greham,1986)。
美国无线电公司并非特例。其他许多原本算得上可靠的大型创业型科技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试图引进大众市场创新产品时也遭到了失败,如伊士曼柯达公司的转盘式照相机、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电视电话,以及宝丽来对电子相机创新的屡次尝试。即使在更可预测的政府业务领域,传统的领导企业也丧失了掌控力。杜邦等待了许多年才为“凯夫拉”(Kevlar)这个品牌名找到了用场。IBM虽主导了大型计算机,却没能在小型计算机上同数字设备公司(DEC)或数据通用公司(Data General)等新进入企业成功展开竞争,它甚至放走了巨型计算机设计师西摩·克雷(Seymour Cray),后者自己创建了一家独立的巨型机公司。甚至连安培公司(Ampex)——一家包袱远不如大企业沉重且获得其创新型机构客户(美国广播公司,简称ABC)稳定承诺的小公司——在专业版便携式摄像机上也输给了索尼公司(Florida和Kenney,1990;Graham,1982;Rosenbloom和Freeze,1985)。
确实,整个苦涩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老牌公司在非军方技术领域仍扮演着创业公司的角色。明尼苏达矿业与制造业公司(即3M公司)以通过鼓励研究人员成为本公司体系内的企业家而给市场带来大量新产品著称于世。以“惠普之道”(HP Way)著称的惠普公司,通过保持较小的业务单元并将大量权力下放给上进心强的年轻经理人,来鼓励创造力和新形式的公司创业。康宁公司引进了各种各样基于玻璃配方和专利工艺相结合的颇具技术挑战性的新产品。但在大量涉及巨额研发投入和新创企业的失败经历后,创新开始变得不再风靡,且金融市场不再能给“高科技”公司提供相同程度的回报(Lazonick,即将发表)。几乎在所有的科学工业领域,当创新颇受重视时,新进入企业、分拆公司或新创企业往往能把握和保持着对较大公司而言更大的优势。
在几十年间加速为特定技术的研究提供资金后,由于其收益仍难以衡量,美国社会开始普遍偏离将大量公共支出倾注于科学和武器技术的做法。当公众和许多科学界的观点转向反对科学的军事使用后,成长于国防部(DOD)研究体系下的年轻一代研究人员,便积极寻求其研究成果的民用领域。联邦政府每年有40%—50%的研究经费未用于工业,这些研究经费本可产生的潜在商机,却主要受到了九个州少数研究型大学和一些政府实验室的压抑(Nowery等,2004;Mowery和Rosenberg,1989)。
(二)消费者运动:企业家的规模
美国消费者的反叛也给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转型打下了烙印。“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恰逢一段反对越南战争的时代,伴随着大企业对化学战剂等技术的破坏性使用和一套胡作非为的军事采购系统(Roland,2001)。在反抗日益根深蒂固的经济体系和已开始显露出缺陷的官僚形式中,“婴儿潮”一代不断抵制大公司的科层制和越来越疲弱的安全保障及其产品的千篇一律化。如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所表明的,作为应对,他们欢迎小生产商的多样化及进口产品和放松管制产业的低价格,同时还要求更大程度的社会监管:清洁饮用水和清新空气、消费者保护、产品安全和各种各样的环境监管。为了适应市场中的这些新进展,联邦政府削减军方研发经费、将政府管制重点转向能源和生活方式等问题,以及把监管体系的重点转向卫生、安全和公平就业机会。航空、通信和公用事业等领域随后的放松管制吸引了大量创业企业,在某些情况下(如微波通信公司和西南航空),它们很快便对以往的行业领导者发起了挑战,并凭自身活力把握机遇跻身于主导地位。 [36] 电信放松管制不仅催生了微波通信公司等创业企业,而且当电信设备不再由西电公司支配时产生了一大批新供应商。
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大众甲壳虫车和索尼便携式晶体管收音机的进口在美国找到数量可观的意愿购买者时,“二战”后看似稳定的受管制经济已出现轻微的裂痕。但是,直到第一批日本进口收音机和电视机及随后的进口汽车在美国市场获得大批追随者,才标志着“二战”后长期稳定的结束。1971年消费电子产品一场突如其来的衰退,揭示了美国正在逐渐失去最强大的制造业部门之一。很快,像通用电气和美国无线电公司等财力雄厚的大公司也在高增长的电子商务部门惨遭失败,不再能跟上迅猛发展的计算机行业的管理或融资需求(Coopey,2004,“引言”)。
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一代人首次质疑美国经济所立足的核心前提,即对增长和规模的双重追求。看上去不成气候的社会反叛,很快蔚为壮观,成为经济“支柱”。“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对美国的批评似乎更具乌托邦色彩,但他们在大学宿舍、车库甚至集体农场创建的企业确实“占领”了大有前途的新领域。尽管这些新生事物一开始似乎不可能成为可靠的商业实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小型商品的追求,如天然食品、中草药、天然纤维及生物质(biomass)、风能和太阳能等新能源甚至个人电脑,产生了能同大公司相竞争的大量业务。一些现存公司意识到了这些新生事物有成为未来潮流的潜力,另一些公司则适当缩小规模或转向了其他业务领域。 [37]
当计算机从机构专用品发展到消费产品时,信息革命步入了第二阶段。尽管IBM、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和施乐等大公司仍控制着办公设备和计算机硬件行业的主机和全程服务环节,但它们很快失去了对相继而来的小型设备浪潮的掌控。独立软件和外围设备、家用电脑和电脑游戏在如此不同的方向上占据了整个计算机行业,以至到20世纪末只有少数原来的公司仍在该行业中幸存下来。随着同硬件的分离,软件在几年间成了信息技术产业最容易的切入点,同时也是美国市场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创业机会的最早行业之一(Campbell-Kelly和Aspray,1996,第181—205页;Coopey,2004,第300页)。20世纪80年代后期,信息技术已开始向其他行业的产品和生产工艺而不仅是它们的生产系统渗透。机器人技术产生了人工智能,新兴机器人技术公司开始孵化,并给机床制造企业带来了挑战。
信息技术的组合趋势表现得最明显的一个领域是制药业,其中于1990年启动的获联邦政府30亿美元资助的人类基因组计划(HGP),需要只有计算机运算能力大幅提高才有可能实现的数据处理和信息储存技术。基因组学,似乎是微生物学的一个扩展,成为即将迎来创业活动的又一领域。
(三)创新体系的开放
随着国会要求政府实验室和私营企业一同分享它们的发明,基于新兴生物科技技术、新材料及高级软件和信息学等信息技术应用形式的创业机会越来越开放。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规定,大学获准为政府经费资助的发明申请专利。少数研究型大学,从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开始,很快积累了大量专利许可使用费,且当年轻一代由研究人员组成的创业者获得他们的研究专利并寻求投资者合伙创办初创公司时,研究型大学的金融股权变得更高(Mowery等,2004)。类似的,许多工业实验室采用了出售其专利技术的做法,而不是持有它们以备开发之用。
长期被隔绝在政府实验室里的技术,连同许多相关领域富有进取心的研究人员的专业知识一起,开始对私人投资者开放。当20世纪80年代冷战突然结束时,解密后的非常规武器技术,如数据库技术、动画和游戏的计算机成像、超级计算机、卫星技术和航天器,已随时可依托创业企业实现商业化运作,经验丰富的企业家由此创办了一系列初创公司,如曾被苹果公司解雇的史蒂夫·乔布斯创立新公司内克斯特(Next)和皮克斯(Pixar)。
一些行业受益于对非军方相关研究不断增加的联邦资助。这些受资助领域中最主要的是农业及依托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药物和疾病研究,农业部门通过赠地学院和学院研究站,已长期获得州政府层面的支持。在这些领域,即使冷战时期,美国创新体系也从未像特殊技术中那般严密封闭。早期最重要的一种公共资助形式是农业研究资助,在数额上远不及特殊技术,但依旧使全国各界及服务于它们的公司获益颇丰。同时,如高隆博什等人(Galambos和Sturchio,1996)所叙述的,某种程度上总是有些国际化的制药工业,依赖于一个创意与投资来源网络,这个网络不仅包括公共研究资助,还包括政府、大学院校及工业实验室的私人和公共研究人员。
网络在整个20世纪都是创新体系的一个主要部分,直到各种新的发展趋势推动美国创新体系更全面地开放之前,创业活动仍以封闭和合作为主。只有到20世纪80年代,如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和安进公司(Amgen)等生物科技初创企业成长为制药业的主要参与者,创业活动才比较常见。基因泰克和康宁集团共同成立了以股权代替投资资金的杰能科公司(Genecor),由此获得了迅猛发展(Dyer和Gross,2001)。杰能科这样的联合公司,因对技术分享的反垄断关注已过时几十年,现在又成了具备高科技专长的小型初创企业同大企业展开合作且仍保持独立的一种常见方式。对于以埃尔默公司(PEC)提供的3亿美元投资开创了赛雷拉基因公司(Celera Genomics),并同政府扶持的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相竞争的克雷格·文特尔(Graig Venter)这类学院型企业家来说,支持初创企业致力于研发的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已很到位。
特别是,受益于各种研究经费及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严厉管制的国际制药行业成为少数先进行业之一,在这些行业,即使欧洲龙头企业也选择将其总部和研发实验室设在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的附近,而非设在本国或外包给远东开发商和生产商。这意味着可以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发明,接近学院型企业家领导的初创企业,为药物与医疗设备投资创造了尤为吸引人的条件。同样,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公司擅长信息技术,特别是微处理器生产商,因此选择将先进的工业研究实验室建在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知名研究型大学附近。
随着20世纪末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越来越比固定资本重要,其他行业盛行的成功组织形式也从科层制转变为网络制,从而使科层制程度较低和开放度更高的公司受益匪浅。开放标准是大势所趋的早期信号,包括施乐公司20世纪80年代可无偿授权的以太网标准,以及IBM生成其个人电脑软件的开放代码方法,它有助于IBM获得比已被普遍认可的苹果公司个人电脑更先进的技术优势。即使在互联网为它们提供更充分的运用手段前,开放软件运动和美国在线(AOL)、苹果、亚马逊、易趣、思科及谷歌等公司的成功,都成为美国创新体系至少同19世纪以来一样开放(甚至可能更开放)的信号。
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人们普遍认为,相比于仍依靠其自身内部研发能力的公司,同小型技术公司形成战略联盟并和大学研究人员建立正式研究关系的公司,已开发出更快和更有效地获取新技能和新商机的方法。那些需要迅速转向基因组学和丰富它们药物产品线的制药公司、需要新设备和新软件的通信公司,以及许多需要能跟上新技术步伐的劳动力的公司,通过收购或共同合作(但主要是作为专利续期代理商),都寄希望于创业公司。
(四)创业欺诈
随着文化重点从国防转向扶贫和替代性生活消费方式,以及创新体系越来越少受控制和更加开放,新领域不仅对合法创业敞开大门,而且也对花样百出的欺诈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自20世纪20年代的金融投机客和20世纪中叶的军方“倒爷”以后未曾出现过此类欺诈行为。紧随卫生保健方面的新政府立法——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而来的,是提供实验室测试等各色外包服务途径的私营企业。事实证明,许多这类企业都以各种复杂手法欺诈联邦政府。其他同生活方式有关的机会把大众娱乐引向了新领域,预示着计算机自动化的不断普及有望释放出更多的休闲时间。这些进展不仅提高了磁带录像机(VCR)等新型消费电子设备的国内外销量,而且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互联网的商业化,为兜售色情照片和毒品、网络赌博等大量新兴的非法交易创造了条件。许多这类业务都遭人唾弃,大型中立组织大多不愿意触碰,从而留出一个巨大市场,更灵活且较少受社会影响的企业可通过法外经营,包括地下广播电台、集团犯罪和原住民保留区,谋取利益。
类似情况在金融界也时有发生。例如,一旦放松管制,储贷机构(S&Ls)便利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存款额达10万美元的账户进行鲁莽投资,以追逐更高收益。到1988年,500多家储贷机构已濒临破产的边缘。20世纪80年代末政府对储贷机构的紧急救助,加剧了本已规模庞大的联邦赤字,不但没有带来更多的财务廉洁(financial probity),反而造成了20世纪末对公众信任的更大伤害。除空前薄弱的政府银行监管所界定的受保护领域外,金融企业家开发出了新的金融工具和大量新的统称为“对冲基金”的投资媒介,试图继续以最低的实际风险敞口谋求可观收益。
(五)金融创业活动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些力图适应重大变化并应对该时期新的不确定性的公司看来,当时变幻不定的环境推动了大量创新活动,与此类似,20世纪美国企业家精神发展的第三段时期困难重重的金融市场也推动了金融创新的新浪潮。
如前文在讨论高科技企业和企业集团运动时已提到的,20世纪60年代以股票和账面利润所做的投资,往往导致收购方公司在近十年后丧失其自身价值。小投资者从股市大量撤出。伴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金本位制的缺位,自越南战争以来出现的通胀势头演变成两位数的通胀。资本短缺伴随着极高利率,迫使人们迫不及待地尝试各种创新方法来为新企业融资。受数百万普通投资者损失惨重的打击,股市开始关注低风险类投资。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至今仍备受争议的金融企业家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开始在华尔街登台亮相。意识到正常公司很难为它们的内部发展筹集资金,米尔肯发明了一种高收益债券的新发行市场。米尔肯的雇主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虽只是华尔街众多公司融资巨鳄中的一名“小玩家”,却颇乐意尝试一些新事物。有了米尔肯这一发明的帮助,信用评级较低且不太有希望在企业债券市场筹措资金的公司,便能发行所谓的“垃圾债券”。新的垃圾债券市场之所以能产生,部分受益于“415规则”(Rule 415)的实施,该新规则使承销商可以快速地销售垃圾债券。垃圾债券对承销商而言既有高风险,也有可观收益。
储贷机构被允许购买垃圾债券,它们迫不及待地抓住机会谋求更高的利率,却忽视了垃圾债券的高风险特征。在狂热追逐垃圾债券几年之后,米尔肯成了华尔街有史以来薪酬最高的雇员,谣传他积累的个人财富超过了30亿美元。不幸的是,垃圾债券的最初购买者在将这些债券转手给投资者并把一部分现金汇回德崇证券之前,已进一步推高了原本就较高的债券价格。1987年股市崩盘导致垃圾债券市场暂时关闭,米尔肯被判入狱,德崇证券也被迫关门,但不久后垃圾债券市场又继续运行。
杠杆收购是一项依赖于垃圾债券可得性的金融创新,它利用债务来收购公司,剥离它们的资产,实行裁员,然后将被收购公司出售给其他投资者,并由此兑现巨额收益。 [38]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私人手上积累的巨额财富反过来提供了新的资本池,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它们可被用来为新创企业提供融资。在科尔伯格(Kolberg)、克拉维特(Kravits)和罗伯茨(Roberts)等著名企业收购公司的引领下,许多收购专家兼并和分拆了那些因管理不善而死气沉沉或濒于破产或一些只是不够幸运的公司,由此导致了一波杠杆收购热潮,投资银行和私募股权公司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历史悠久、身经百战的大型官僚化公司,要么消失不见要么精简规模或进行重组,这给市场释放出了大量专业知识和其他资源,使更多从事风险投资的创业领袖能够加以利用。
将自由市场解决之道扩展至以往通过政府管制处理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成为创业活动的另一领域,且往往以试图把其理念应用于市场的学院型企业家为主导。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努力被证明非常成功。当1990年旨在提高排放成本来降低酸雨的《清洁空气法案》获得通过时,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理查德·桑德尔(Richard Sandor)创立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E),以推行“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制度,使电力公司的污染成本远高于安装洗涤器来控制二氧化硫排放的成本。美国环保署(EPA)高度评价了这一新体系在减少每年数百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及肺病和其他相关疾病中的作用(Specter,2008)。酸雨问题也得到了公认的改善。事实上,在努力解决清洁空气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方面,桑德尔这样的金融企业家已取代了政府企业家,他们为金融市场创造了大量新的投资机会。
(六)风险资本的制度化
私人银行和富有的个人,是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最高收入百分比人群,在20世纪之前较好地为初创企业提供了投资资金,但“二战”后风险资本逐渐开始大行其道。在美国东部和西部海岸,对风险资本短缺的相关担忧催生了新的融资形式。波士顿和旧金山湾区一马当先。1946年,一群由哈佛商学院教授乔治·多里奥特将军(General George Doroit, 他被誉为美国“风险投资之父”。——译者注)率领的波士顿民间领袖,创立了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R&D),这是一个将投资重点放在电气和医学电子学领域并按封闭式基金组织的非家族式风险资本(Kenney和Florida,2000;Ante,2008)。在25年的时间里,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既贷款又投资于波士顿周边的初创公司,它帮助麻省理工学院孵化的一些高科技公司发展壮大,颇有一些相当成功的案例,但到那时为止,它最赚钱的一笔投资是数字设备公司。
加利福尼亚州是冷战时期获得联邦国防资助最多的地区。在斯坦福附近的旧金山湾区,许多小公司不断涌现,但因缺乏筹资扩张的必要能力,它们不得不被出售给东海岸的大企业(O'Sullivan,2007)。为了找到其他融资渠道,真正意义上的金融突破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的瓦里安公司(Varian)和惠普公司先后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了股票。20世纪60年代,由于在核心业务增长上深受反垄断措施的约束,仙童公司和杜邦等大型高科技企业开始投资于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公司新项目,作为实现多元化经营的途径。
1958年,国会通过了《小企业法案》,随后是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的建立。该公司不仅使小企业能获得更多资金,而且允许企业家削减他们的个人负债。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包括多里奥特将军的一些学生在内的私人投资者,开始创建家族小企业投资公司,因此该时期东部大型老牌企业体系之外的高科技初创企业已能获得大量资金。随着小企业投资公司有了全职员工做专业投资者,这为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成熟风投公司奠定了组织基础。
尽管西海岸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投资基金,但使风险资本达到可实际应用规模的却是“有限合伙企业”。这种组织形式比小企业投资公司有着更大的发展潜力,且从那时起有限合伙企业便开始风靡于世。1968—1975年间,仅在硅谷就有多达30家风险投资公司创立和重组。当时恰逢半导体革命及晶体管向集成电路的过渡时期,这波投资活动浪潮为早期风险资本家提供了高额回报,导致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一片繁荣,而美国其他老工业区却在这场产业转型中深陷困境。少数重大交易的成功——如施乐为科学数据系统(SDS)、仙童和英特尔、苹果二代计算机等支付的10亿美元——对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风险资本的形成与巩固助益颇多。
尽管到20世纪80年代总共只有少量资金参与风险投资,但其投资收益率往往非常高(20%—30%)。风投行业的重要转折点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发生的两次重大事件:1978年资本利得税的显著下降,以及1979年管理养老金投资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ERISA)被重新解释为,只要高风险投资的比例不过分高,将此类投资纳入投资组合是一种“审慎”行为。这为养老基金投资于风险资本并促使风险资本融资的重点从富裕家庭转向机构投资者铺平了道路。此后,某些风险投资公司可定期融资,尽管任何给定年份它们所能筹融到的资金数额严重依赖于其近期业绩和资本利得税率,但后两者反过来又会影响风险投资可获得的机会(Gompers等,1998)。
在将近10年的不同经历之后,专业的风险投资家成了创业融资的重要来源,这不仅因为他们提供了不易获得的早期资本,还因为他们成了发明型企业家获取业务专长的重要来源之一。风险资本家在他们投资的任何一家公司的董事会均占有一席之地,并且掌控着被投资公司,一直到其能公开上市(Hambrecht,1984)。这种控制形式的结果之一是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风险资本家需要实实在在的投资业绩,也即当一项投资不尽人意时可转手的某些物证,或者能向投资者表明他们的投资安全可靠的证据,他们坚持保留专利组合的早期申请权利,因此专利和风险资本变得越来越紧密相关。
当风险资本家凭借自身实力成为专业人才后,风险资本便实现了制度化。在有些地区这一过程颇为顺利,如波士顿和西海岸地区,但在纽约、新泽西和得克萨斯等其他“高科技地区”,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他各类专业服务公司开发了各种各样的相关专业知识。这显然不可能发生在风险资本投资量多到足以支撑这类基础设施的领域,正是这个原因,风险资本到20世纪末仍集中在少数地区。
根据科图姆等人(Kortum和Lerner,2000)的研究,尽管风险资本融资只占1983—1992年间全部研发支出的3%,但它作为一种创新资本来源的效率却是纯粹研发的3倍。考虑到风险资本家越来越依赖作为投资过程一部分的专利,风险资本融资的增长对专利产生了杠杆效应。到20世纪末,老牌风投企业需审核的投资建议书远远超出了其所能提供的融资额度,不过握有专利是新创公司的投资申请要获得认真考虑所必须满足的条件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险资本开始涵盖从主要阶段资金到种子基金的整个融资领域,但颇具讽刺性的是,随着风险资本发展为一个行业后,它也采取了一种低风险的模式。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它们不太愿意提供早期融资;更通常地,这意味着风险资本公司试图通过企业联合组织来降低风险。随着第一代专业风险资本公司退役后,只有极少数实力雄厚的风险资本公司继续凭借自身力量承担全部投资,这个变化使初创企业可获得的有经验的建议出现了质量下降。到2000年时,只有少数早期风险资本公司,如红杉资本、汉布雷克特(Hambrecht)和奎斯特(Quist)等仍在运作。
随着20世纪末缺乏经验的年轻一代涌入该行业,被认为“热门”的技术领域吸引了不成比例的资金量,而更传统稳健的实体投资则被当作“旧经济”(old economy)遭到抛弃。不足为奇的是,每家终获成功的初创企业都经历过多次失败。但似乎矛盾的是,在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所谓的“非理性繁荣”后期,未接受风险资本融资的互联网公司较接受风险资本融资的公司更有望存活下来(Goldfarb、Kirsch和Miller,2007)。尽管许多公司倒闭了,但少数几家庞大的互联网公司(如亚马逊和易趣)却获得了成功,它们追求一种能为成千上万小企业家开拓以往遥不可及的市场提供支撑的商业模式。再一次地,老牌企业不得不投入它们自己的资金,以应对这一新的商业模式,一如各行各业的零售巨头增加新的分销形式以跟上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步伐那样。
到20世纪末,在历经互联网投资大起大落一段时期后,风险投资已从一种制度发展成熟为一个行业。在风险投资最密集的领域,它为新创企业提供了高达13的资本。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基于人际网络的公司(networked firm),起初为了追求更高收益的投资和更明智的建议,替代了大型官僚化公司,成为创业企业的重要支持者,至少在某些行业如此。另一方面,生物科学领域的准企业家发现越来越难以从风险资本家那里获得早期资金,且最近的初创公司也经历了一段再融资以扩大业务规模的困难时期。风险资本家为了寻求有保障的回报和更高的收益,而不愿承担过度风险。
颇具讽刺性的是,正当风投行业蒸蒸日上时,一场反对它的运动也随之出现。对所有最终满腔热情地投身于市场的研究人员、业余爱好者和非专业人士来说,有许多其他人会认为自己最初的企业目标被破坏,因而起来反对。到20世纪末,受互联网的刺激,开放软件运动展现出了新的活力,这反过来催生了维基百科等影响更大的志愿者运动(voluntarist movements)。这些运动可被视为不同形式的集体创业,即引进一种可免费广泛使用的技术,为诸如广告或服务等辅助活动筹集资金。尽管这些运动备受争议,但开放软件运动将对21世纪所有行业带来深刻的革命性影响,由此挑战了许多软件公司的基本经营模式(Lazonick,即将发表)。
七、结论
本章对20世纪美国企业家精神的概述表明了美国经济中一些重要的延续性,主要在法律、金融和通信等相关领域,这些延续性曾对鼓励创业活动至关重要,且仍将重要。《宪法》的保护,即契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和私有财产保护,继续存在,同时公司法也在普通法传统下得到了发展完善。整个20世纪,专利体系和社会普及率更高的可靠的公共教育体制仍在发挥效力,尽管两者都经历了兴衰起伏。新金融工具虽不断演变,但基本原则并未改变。新的运输和通信形式得到发展,降低了成本,并最终“解放”了绝大多数行业,尽管地点依然很重要。
技术开发的公共和私人融资渠道,如州政府、私人基金及农业、铁路和电报等受追捧行业,虽然很不协调,但依然在持续发挥作用,尽管发明重点在20世纪转向了其他受追捧的行业,如电子、汽车和飞机制造。“二战”后联邦政府进行了干预,选择并将资源配置到国防和公共福利领域最有潜力的技术上。
尽管重要制度和模式依然存在,但20世纪美国经济的一些特征却明显有别于以往时代,且这些变化对创业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随着大量创新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企业家需要受教育程度更高或至少受过更好教育的员工,并能获得更多资源。由于受管制公司的制度化和作为企业核心功能的研发的一体化,企业家精神变得更加同技术创新相关,且更多服务于公司影响力。随着反垄断法获得较好贯彻(像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期间那样)且禁止公司通过收购竞争对手或将竞争对手挤出相关行业来实现增长,公司对许多以往在企业外部实现的创业功能进行了整合。
在创新、研发和国防是国家强制性的统一目标、稳定的大组织提供的职业保障最具吸引力的时代,公司充当了创业天才的主要招募者和新业务的首要开发者。尽管这些进展并未抑制独立研究和发明,但它们确实对创业活动转向一些核心技术产生了影响。军事技术,甚至应用于民用目的的交叉技术,导致了一套封闭的创新体系,其应用和融资渠道不仅受限制、分类别,并且只适用于有限领域。
如我们已看到的,对于一些农业和医学研究等方面的关键技术,公众更容易获得,且更易受创业活动,甚至全球创业活动的影响。但在20世纪中叶,创业活动更多地和“高科技”企业相关,大多数资金来自公共研发支持和公共采购合约。大学里开展的基础研究并不受限制,但是,由于它主要受纯粹的科学价值引导而与商业开发相隔离,所以并不易于进入创业通道。
由于知识的集中、私人投资资本的缺乏以及许多有巨大机会的核心技术需要大量资本,20世纪中叶独立的发明型企业家大幅减少,尽管他们从未完全消失。即使在农业等创新渠道分布广泛且更容易进入的领域,诸如先锋杂交(Pioneer Hybrid)等高增长公司也开始整合研发活动,同一些重点大学建立更严格的合作网络,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关于20世纪70年代个人、私营部门企业家精神的复苏如何使创新体系重新开放,仍有大量问题有待研究。事实上,不管是推动了企业家精神的创新体系的开放,还是使创新体系重获开放的创业能量的爆发,都不易确定。企业家的机会随信息技术成本的持续下降及其向更小民用领域的普及而不断涌现。在基于计算机的新信息技术组合方面,也产生了许多有待企业家开发的崭新应用领域。
清洁的空气和水、生活方式改善以及消费者和产品安全保护等需求上的重要社会变化,改变了政府支出的重点,并开创了一种新型企业家精神,一开始在政府内部起作用,随后试图通过外部作用使之发生改变。政府企业家很大程度上被那些想利用自由市场机制带来改变的私营部门企业家所取代。
20世纪80年代,推动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已从信息技术扩展至微生物学、微型化及许多新兴杂化材料(hybrid materials)和工艺。全球化也开辟了新市场,并使开拓了贸易创业机会的移民模式重焕生机。软件等技术和许多新的反主流文化创新对资本的需求远低于20世纪中叶的“前辈们”,从而使高科技投资成了“非理性繁荣”的渊薮。到20世纪末,对于基因组学等有无限发展前景和创业参与热情的一些新兴技术,资本密集程度已变得更高,以至私人投资者和资本市场似乎均不能为他们提供支撑。
总之,从本章概述中得出的最重要发现与20世纪企业家和大型企业之间建立的多层面互补关系有关。 [39] 到20世纪60年代,大型企业本身往往锁定在官僚主义中,以至很难完全自我维续和自我更新。尽管大型企业在大萧条时期展示出了暂时性的自发创业能力,但战后时期朝着日益官僚化和风险规避发展的倾向,逐渐使真正的创业品质除了最富于创业精神的企业外不再受到欢迎。当创业型员工离开公司时,他们同时也带走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创新激情。意识到自己对新创意越来越大的需求,且很少会受到反垄断阻碍后,一些企业和富于创业精神的公司建立了联盟,其他的则试图收购富于创业精神的公司,但出于财务动机的零星收购之举很少能产生有成效的结果。
随着私人手上可以利用的资本越来越多和投资者寻求更高的收益,到20世纪末,新的创业企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它们通过各种网络获取知识和专门技术,且对老牌企业构成了直接挑战,有时甚至将它们挤出了该行业。但是,对那些意识到需要转型的公司来说,创业企业不仅是外包的备选对象和创新产品的来源,而且提供了可效仿的经营模式。最后,全球化改变了美国创业活动的地理分布,正如它曾改变了整个商业的地域特征一样。尽管把20世纪美国的企业家精神当作一种独特现象论述不乏合理性,但21世纪的历史学家似乎极不可能找到任何与此类似的经历。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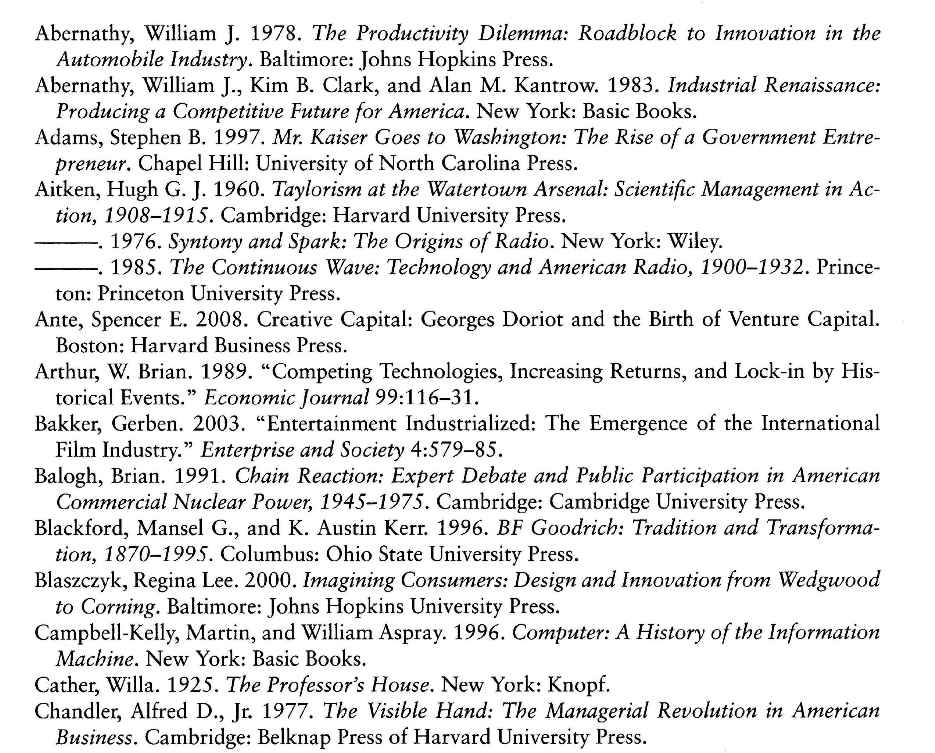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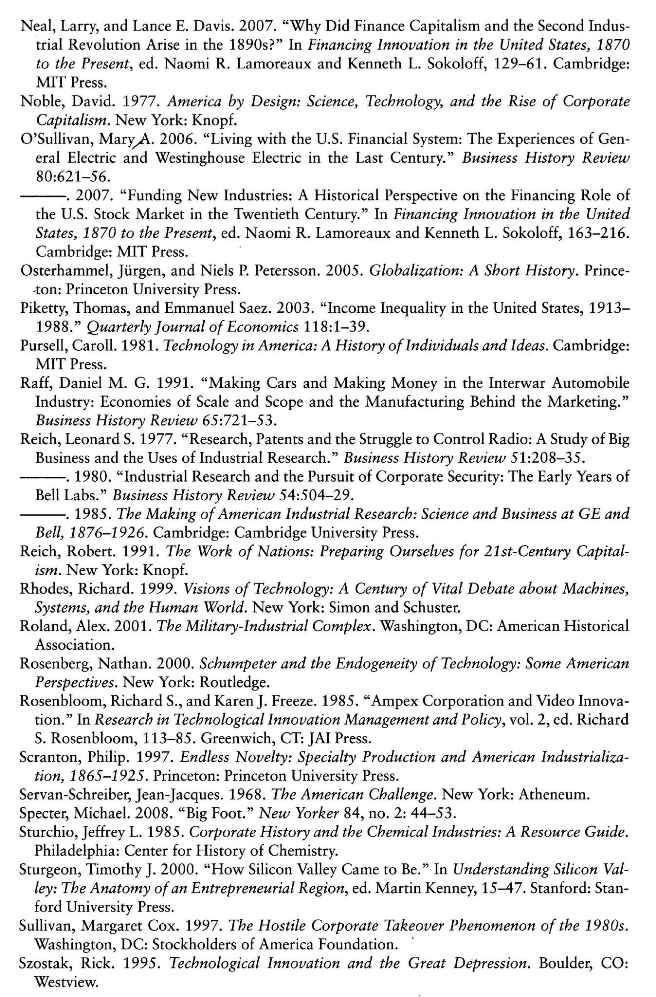

[1] Servan-Schreiner(1968)、Galbraith(1967)、Thurow(1999)、Chandler和Cortada(2000)。奇怪的是,除了作为研发资助者外,Chandler和Cortada并未重视政府的角色。
[2] Gerben Bakker(2003)指出了娱乐产业作为不受管制但仍部分受以往经济情况影响的例子。
[3] Alfred D. Chandler(1977)在《看得见的手》(The Visible Hand)中将大企业统治描述为美国工业中唯一重要的方面,这在最近受到了多方挑战:一方面是Philip Scranton(1997),另一方面是Naomi Lamoreaux、Daniel M.G. Raff和Peter Temin(2003)。
[4] Lance Davis和Larry Neal(2007)坚持认为,大企业和小企业的混合体系解释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机问题。
[5] Eric S. Hintz(2007)注意到,整个20世纪50年代,将近50%的专利仍被授予公司外部的独立发明者。
[6] Zunz(1990)、Hounshell(1984)和Yates(1989)。Olivier Zunz认为,Thorstein Veblen在《工程师与价格体系》(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1921)中指责公司金融将公司管理引向了一种受限于工程师的官僚主义做法。Veblen把工程师和企业家(他认为他们同利润动机息息相关)看成内在相对立的,并把泰勒主义(Taylorism)看作是将“技术人员”从金融首脑中解放出来的一种手段。Zunz注意到Veblen并未考虑诸如Henry Ford等我们称作发明型企业家的“多面手”。
[7] Aitken(1960,第237页)。尽管在一些早期试验后,政府兵工厂的工会组织抵制科学管理,但“一战”后,它们开始接受科学管理,并将之视为能使劳资合作大幅提高生产率的途径。参见Robert Kanigel(1997)的研究,作者表明“一战”期间泰勒主义已开始体现在美国的制造业中,且在此后以燎原之火的速度扩散。
[8] 参见McGraw(2007)。最近William Lazonick(2007)对创新型企业的理论作了扩展,以用于区分追求最优化的企业和为创新而配置资源的企业,但Nathan Rosenberg(2000)在其著作的最后一章中强调了以下关键论点,即最激进的破坏性创新是由各方的深入开发来实现的,他们均应被合理地视作创新过程的组成部分,尽管他们可能算不上企业家。也可参见Reich(1980)。
[9] 塞缪尔·英萨尔以作为托马斯·爱迪生的秘书开始其职业生涯,后来逐渐成为一名重要的电力创新者和芝加哥创业圈子的组织者,以及其所在行业的领军者;他在大萧条时期成了替罪羊,在受到证券欺诈的指控并被判无罪释放后,于穷困潦倒中死去。
[10] Yergin和Stanislaw(1998)。有效合理地管理持异见者成了创新型企业的标志,参见Graham和Shuldiner(2001)。
[11] B.M.Friedman(2007)对这一观点及其社会影响作了总结。
[12] F.S.Fitzgerald于1925年出版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中,男主角既崇拜财富和爵士时代的魅力,又对其中的物质主义和道德深感不安。类似的态度也可在同一年Willa Cather出版的小说《教授的房子》(The Professor's House)中的主角身上找到。
[13] Szostak(1995)。关于生产率提高是大萧条的成因之一,今天的经济学家不乏争议,但他们很少否认生产率进步使传统行业出现了工作净损失,当代观察家认为对效率的痴迷已导致了过度供给的状况。参见Rhodes(1999)。
[14] Galambos和Pratt(1988)引用了John Kendrick的生产率数据的传统来源。
[15] Graham和Shuldiner(2001);Hounshell(1984,第263—277页)。Hounshell指出许多T型车的车主很看重其稳定性,因而要进行较明显的修改颇为棘手。
[16] 参见Archibald MacLeish在1933年《国家报》(The Nation)上的文章,转引自Rhodes(1999,第116页)。MacLeish描述了大萧条的深层内涵,以试图在生产率论中找到新的解释。也可参见Pursell(1981)。关于最近对某金融创新者(他的东窗事发极大地刺激了深度萧条时期的银行业监管)的描述,参见《经济学人》杂志的文章“火柴大王”(The Match King),2007年12月19日,第115—117页。
[17] “The Match King.”
[18] O'Sullivan(2006)。通用电气赎回了自己的部分股份并剥离了其债务负担,西屋电气公司则屡屡过度扩张其自身。
[19] Field(2003)给出了反映这些进展成果的数据。
[20] Blackford和Kerr(1996)、Graham(1986)、Graham和Pruitt(1990)、Dyer和Gross(2001)、Hounshell和Smith(1988)。正是观察此类公司,促使熊彼特注意到创新现在主要是大公司的活动。
[21] Mowery和Rosenberg(1989)。这与Alexander J. Field(2003)的以下观点相一致,即尽管失业严峻,1929—1941年间仍是20世纪美国经济进步最快的时期。
[22] Edwin F. Mansfield(1968)概述了确保科学家实现充分就业的运动。他引用Dupree(1957)作为这些事件的原始资料来源。
[23] David C. Mowery和Nathan Rosenberg(1993)将研究执行者和制度之间的关系描述为在不同工业化国家以不同的系统性方式得以发展。
[24] Reich(1985)、Wise(1985)、Hounshell和Smith(1988)。对美国工业研究演变情况最好且最客观的总结当属Hounshell(1996)。
[25]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RC),1919年第16期、1927年第60期研究简报;Herbert Hoover(1926),转引自Rhodes(1999)。
[26] David Noble(1977)讨论了这一进展中的关系组合。也可参见Graham(2008)。
[27] David C. Mowery和David J. Teece(1996)对战后工业研究越来越内向的特性作了总结。
[28] Hughes(1986)。必须意识到这一新的现实,即“二战”后康宁公司最重要的董事之一Walter Bedell Smith将军,曾是战时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首席采购官,并在后来成了盟军机动部队公司(AMF)的董事长。
[29] Mowery和Rosenberg(1989,第123—168页)表明了依托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大学研究经费的大幅增加;1958年通过的《国防教育法案》(NDEA);以及一些针对供给方面的其他重要立法措施和针对需求方面的集中采购。
[30] Kevles(1978)。雷神公司[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在职业生涯早期曾供职于此]是近乎因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歧视性电子管分配和高许可费而被迫退出行业的诸多小企业中的一家。
[31] 当诸如收购等其他途径被迫中断时,严厉的反垄断执法事实上是否迫使越来越多的寻租活动转向狭隘的创新通道仍无定论。也可参见Miscamble(1982)、Markham(1966)和Waller(2004)。
[32] 坚持认为信息革命第一次使全球网络化成为可能的Manuel Castells同许多国际商业史学家相抵触,后者认为这一改变的质变意义远不及始于中世纪、终于20世纪早期的行为模式回归。试图对该时期进行解释和反思的历史学家包括Galambos(2005),Lamoreaux、Raff和Temin(2003)及Lazonick(2007)。
[33] 关于传统的经济解释,参见Yergin和Stanislaw(1988)。
[34] 颇具讽刺性的是,日本公司在消费电子产品领域竞争中的崛起是由美国的主要创新企业美国无线电公司所致,美国无线电公司通过将一揽子许可的实践转移到日本消费电子产品公司,成功地代替了原本来自国内一揽子许可的收益(Chandler和Cortada,2000,引言)。
[35] Mowery和Teece(1996,第113页)陈述了一个经常被忽略的观点,即许多获得政府研究经费支持的企业实验室将在分类基础上和严格的安全措施下运行,就此而言,朝偏远“大学校园”转移的趋势首先是一次事关安全的转移。
[36] Yergin和Stanishaw(1998)。航空公司的放松管制为Peoples Express和西南航空等新贵公司创造了合适条件。在电信行业,微波通讯公司(MCI)对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发起了挑战,并吸纳了与老牌西部电气公司成功展开积极竞争的供应商,如在光纤行业占据支配地位的康宁公司。
[37] 史蒂夫·乔布斯认为,这一运动的“圣经”是Stuart Brand的《整个地球的目录》(The Whole Earth Catalogue)一书。
[38] 《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关于Wolfson(公司收购的创新者)的专栏文章,2008年1月16日。
[39] 参见Jones(2007),作者指出了在大历史背景下理解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意义,他还指出,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理解不同背景所需的技能、行为和个性的不断变化这一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