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政治
人们经常说自己不关心政治,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但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无处不在。你不过问政治,政治会过问你。哪怕你是一介小民,也必须面对政治的影响。
辛亥革命前的成都茶馆,连茶馆里的顾客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地方政治之中。韩素音在其自传中写道:茶馆不再是一个闲聊的场所,而充满着政治辩论和政治活动:
你知道我们成都是一个古老的城市,那里花树成荫,有文化气氛,到处是书坊,安静平和,人们为其古老和历史自豪。……但在1911年5月底以后,它变为十分不安,公园和街头的茶馆充满躁动,这个城市正酝酿着骚乱。
这个时候,茶馆中“来碗茶”的吆喝不再像过去仅仅是社交或生意洽谈的开端:
立即吸引众多人聚集,有些人甚至站着聆听人们关于铁路国有和借外款的辩论。然后人们悄然散去,又到另一茶馆听另一场辩论。
如果说茶馆是人们公开议政的讲台,那么它也是地方政府收集情报的场所。政府派密探到茶馆偷听人们谈话,竭力发现所谓反政府的“煽动者”。
如韩素音描述的:
拥挤的茶馆召来了满清的密探。在露天茶社,在爬满藤蔓的凉亭下,在悦目的树荫和竹林中,都散布着边品茶边偷听文人谈话的密探。

1928年韩素音(左一)全家福
在这一时期,公共场所的闲聊在很大的程度上被政府干扰。例如一项规定明令:如果发现任何操外省口音者在茶馆谈论军务,看起来像一个“间谍”,店主应向警察密报;如果所报属实并协助使“间谍”就擒,可得十元奖赏。由于政府经常利用茶馆得到的“情报”打击一般民众,各个茶馆都贴出“休谈国事”的告白,以免闲聊招惹是非。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也把他们的政治引入茶馆,例如令各茶馆都必须悬挂孙中山、蒋介石画像,以及国民党的《党员守则》和《国民公约》。政府的这个强制要求也受到自由知识分子的批评,他们指出这实际上是为了钳制人们的思想以实施专制。
在军阀混战时期,成都成为滇、黔、川军争夺的战场,城市里发生巷战,这时茶馆成为地方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晴雨表,其开门营业与否成为人们衡量是否安全的标志。
吴虞在一则日记中写道,他在“闻街上茶铺已开”后,才放心出门,但他和友人在去茶馆的路上,看见“各街铺户仍未开也”。这也告诉我们,即使在战争的危险时期,成都市民仍抓紧一切机会去茶馆,追求他们的公共社会生活。

高呼“打倒孔家店”的吴虞
随着社会和地方政治的变化,大众娱乐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趋于政治化。过去地方戏剧主要表现情爱、鬼神、忠孝、贞节等传统主题,从晚清以降,此种“永恒”主题开始转变,“政治戏剧”开始进入茶馆。
1912年,悦来茶馆上演根据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川剧《黑奴义侠光复记》,该茶馆在当地报上的广告称:
本堂于戏曲改良,力求进步。现值种族竞争、优胜劣败,是以特排演《黑奴义侠光复记》一部。此剧从《黑奴吁天录》脱化而出,乃泰西名家手编,其中历叙黑奴亡国之惨状,恢复故国之光荣,尤令人可歌可泣,可欣可羡,能激发人种族思想,爱国热沈(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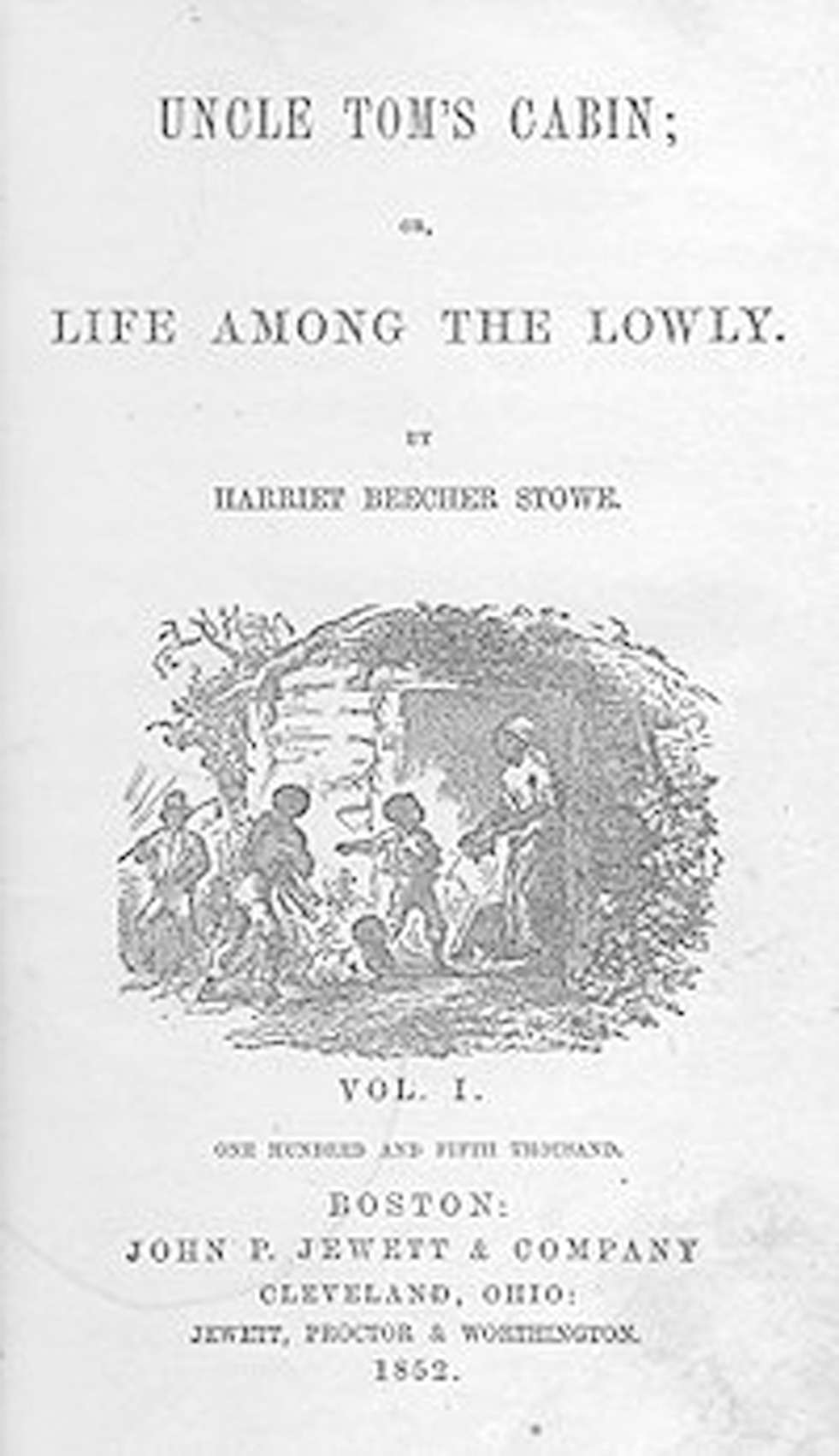
《汤姆叔叔的小屋》英文原版
显然,人们对这部美国名著的理解基于中国自己的处境。在辛亥革命之前,此书便已被翻译为中文,革命者曾用其进行反满宣传。这出剧的公演反映了在推翻清朝统治之后人们的情感和思想状况。
虽然传统的地方戏在辛亥革命后仍占统治地位,但是它们的主题从神鬼情爱转变为革命性故事。社会改良者竭力改变传统戏垄断舞台的状况。一些精英愤而指责戏院忽视道德,所演剧目是“名为教育,其实教淫”,担心中国数千年之伦理将毁于一旦。一些学校甚至禁止学生进入剧院以避免“沾染恶习”。
改良者还组织“新剧进化社”,以从事戏曲改良,其目的是教化民众、改变陋习、增进教育、宣传共和以及稳定社会。该社计划在悦来茶馆修建移动舞台,并按欧美技术进行舞台布景。
一些西方小说被改编为川戏,其大多有着明显的政治倾向,如《多情英雄》是改编自波兰的爱情故事,其揭示了爱情与政治、爱国主义与利己主义、英雄与“丑恶的”政治家的关系。改良者还建立了一个新式剧场“革新新剧院”,其由茶馆改建而成,专演那些讽世励俗、鼓吹婚姻改良的新剧。
民初话剧也被介绍走上成都舞台。新剧运动的先锋曾孝谷在民初从日本回成都后,组织了春柳剧社,与老资格的三庆会唱对台戏。三庆会是成都川剧界最有影响的班子,以其演绎精湛的传统剧目而拥有大量的观众。与其不同的是,春柳以演“时装戏”,即现代戏而吸引观众,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如《祭邹容》《成都故事》《重庆独立》《徐锡麟刺恩明》《黄兴挂帅》《闹广州》,等等。

悦来茶馆的三庆会旧址。作者摄,2003年。
这些新戏剧都是以辛亥革命中的真人真事为基础创作的,提倡革命暴力和英雄主义,与传统的鬼神、忠孝、情爱主题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大众娱乐主题的转变,亦反映了政治和社会的发展。
当然,新戏的发展并不意味这一时期传统戏被取代。对广大下层民众来说,传统戏曲仍然更具吸引力,而新剧主要以受过一定教育的青年人为观众。
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新型的“幕表剧”流行起来,参加表演者多是各校热衷于“反封建”的学生。20世纪20年代初专业话剧剧团“一九剧社”建立。除演具有革命内容的剧目之外,还上演西方名剧,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等。
1925年,通俗教育馆在少城公园开办一个剧院,由美化社和艺术研究社轮流上演话剧,每周演出两三个晚上。这些剧以四川方言上演,吸引众多观众。1926年剧协在成都成立,在其主持下一些中外名剧得以上演,包括易卜生的《玩偶之家》。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改良者还推出鼓吹婚姻自由的话剧《包办婚姻》,鞭挞那“罪恶社会”,揭露鸦片烟鬼、赌棍、流氓和妓女等“社会蛀虫”。他们称这类作品为“文明话剧”,希望以此推动“顺应世界潮流”的改革。
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展了所谓“游艺革命化”运动,修建了一个新剧场、一个影院、一个音乐厅以及一个舞厅,还支持了一个表现孙中山革命生涯的历史剧上演。显然,社会改良者和地方当局都认为,戏剧表演是教育和政治的工具,因而竭力推进具有政治性的娱乐。
革命的政治文化是由语言、形象以及人们的姿态等象征性行为组成的,在保路运动中的成都,这种象征性行为随处可见,它们焕发了人们的相互认同,促成了人们的步调一致,激起了人们同仇敌忾,从而成为革命的强有力工具。
在讨论法国革命中的政治与文化之关系时,法国史专家L.亨特(Lynn Hunt)指出,“政治实践并不仅仅是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的简单表现”,革命者通过其语言、形象和日常政治活动“来重新建构社会和社会关系”。革命者在政治和社会斗争中的经历,“迫使他们以新的方式看待世界”。
像法国大革命一样,从一定程度上讲,辛亥革命在中国城市是根植于一定的文化土壤的。这一时期,在地方政治影响之下,街头文化被纳入政治轨道。在精英主导下的传统社会共同体(或社区)演变成为社会学家R.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所描述的政治斗争中的“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即人们的社会联系和共同行为不仅仅是社区的日常生活活动,还出于共同的政治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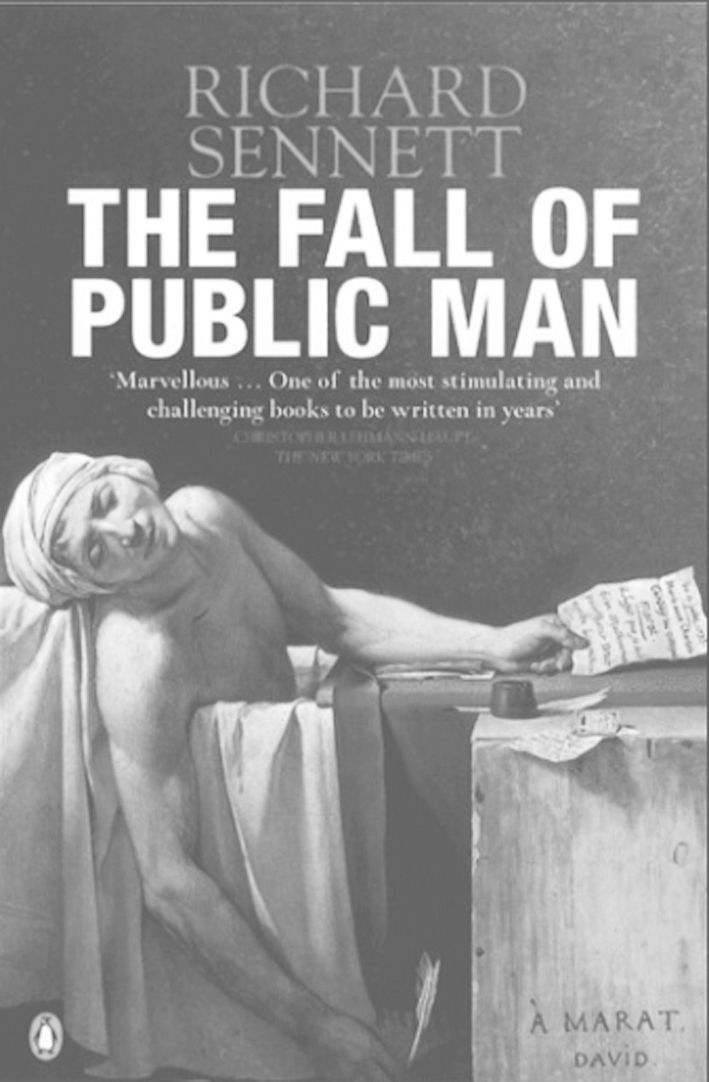
桑内特的名著《公共人的衰落》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标志着民众的政治参与,以及从街头文化到街头政治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从那时起,街头经常用于政治目的,普通民众被迫生活在无情的权力斗争的阴影之下。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街头文化和街头生活在混乱的年代幸存下来,但令人遗憾的是社会环境的恶化,街头文化和街头生活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
精英对民众公共政治参与态度的这种转化,实际上是根植于他们不同的阶级利益,他们自始至终都把民众当作与国家权力进行斗争的一种工具。当他们需要利用这种工具时,他们可以暂时容忍民众在公共场所的集体行为;然而当这种工具对他们来说不再重要时,他们便立即改变了对民众以及其公共行为的态度。
对于民众来说,无论他们是一场政治运动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他们最终都没有享受到运动的成果,无非是成了政治的工具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