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III节 罗马国家官员
在罗马共和政制的三大要素中,两个权力机构公民大会和元老院时常处于对立与竞争的状态中,而执政官作为国家最高的行政官员,则在双方的权力角逐中纵横捭阖,渔人得利。在罗马共和国,主要的国家官员由百人团大会选举产生,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公权力,包括执政官(consul)、法务官(praetor)、监察官(censor),以及在紧急状态下由元老院临时任命的独裁官(dictator)等。至于由特里布斯大会选举产生的平民保民官,虽然不属于政府官员,但是也拥有重要的政治权力,特别是有对元老院议案和执政官命令的一票否决权(Veto,即“我反对”)。这些拥有不同职权的政治角色对于共和国各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共同勾勒出共和国权力博弈的动态平衡轨迹。
执政官
公元前509年罗马人民建立了共和国,以一年一选的两位执政官取代了终身制的国王。从职能上来说,执政官就相当于国王,是国家最高的行政首脑,拥有执行权。执行权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权力,主要表现为执政官平时负责主持元老院会议和百人团大会、在打仗的时候出任军队统帅等。在罗马共和国的发展过程中,主管行政事务的执政官在相互对立的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之间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协调角色,在罗马共和政制的权力平衡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执政官的职权
与王政时期的国王相比,罗马执政官具有年度制和同僚制这两大特点,任职时间短暂并且在权力方面相互掣肘。按照罗马共和国的惯例,两名执政官每年由百人团大会选举产生,然后经过元老院批准正式就任,任期一年。罗马共和国的第一任执政官就是开国元勋布鲁图斯和科拉提努斯,他们为同僚制和年度制开创了先例。
执政官作为国家最高的行政长官,继承了王政时期国王的一些权力标志,例如“法西斯”和象牙椅等。当执政官期满卸任,“法西斯”和象牙椅就要交还元老院,表示此人已经不再掌握公权力。除了上述标志之外,执政官往往会身穿镶有紫边的袍子,因为紫色被罗马人看作最尊贵的颜色,代表着崇高的身份和地位。
执政官平时负责召集、主持元老院会议和百人团大会,参与一些重大公共事务的决策,掌管国库,发布政令等;在战争时期,执政官就会出任军队统帅,负责召集和指挥军队以及筹集军费。执政官的政令虽然不如公民大会通过的法律那样具有权威性,但是在其执政期间同样具有约束力;至于执政官在战时发布的命令和做出的裁决,更是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性。在罗马共和国的早中期,罗马军队一直保持着“将无常师,师无常帅”的传统,即将领麾下没有常规的部队,军队也没有固定的统帅。这是因为在马略进行军事改革之前,罗马一直没有职业军队,兵民一体。每当战火烽起,元老院就会按照百人团的架构征召军队,然后指派执政官出任军队的统帅。战争结束之后,执政官就不再具有军职了,士兵也就解甲归田。罗马正是因为没有职业军队,所以也就没有固定的将领,执政官只是在战时才临时充任军队统帅,平时主要是文职官员。
二、执政官与元老院、保民官的关系
由于执政官的任期只有一年,而且百人团大会选举出来的执政官必须通过元老院的批准,所以执政官的权力往往受制于人多势众且终身任职的元老院。而且共和国早中期的执政官基本出身于贵族世家,卸任后还会进入元老院继续掌控国家政务,因此与元老院关系密切,荣辱与共,执政官在元老院与公民大会的权力抵牾中往往会旗帜鲜明地站在元老院一边。但是到了共和国后期,一方面是由于执政官身世背景的变化(平民可以出任执政官了),另一方面则是鉴于平民政治势力的日益强大,一些执政官开始改变传统的立场,越来越偏向于平民一边,实际上是想利用平民的支持来压制元老院,从而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随着执政官立场的转变,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危机也就开始降临了。
执政官必须应对的另一个政治对手就是保民官,保民官是维护平民利益的官员,也是平民大会的召集人和主持人,就如同执政官是元老院和百人团大会的召集人和主持人一样。执政官拥有的是积极的执行权,保民官拥有的却是消极的否决权,二者正好是针锋相对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执政官和保民官恰好构成了两个不同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在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上,执政官长期站在贵族阶层和元老院的立场上与代表平民利益的保民官相对峙,二者之间的权力消长很好地表现了贵族与平民利益的相互制衡。到了共和国后期,执政官却开始与保民官结盟,将手中掌握的军队与保民官所控制的平民势力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元老院(从马略到恺撒都是如此),共和国的末日也就遥遥在望了。
三、执政官身世的变化
从公元前509年开始,一直到公元前367年,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全部都是贵族出身。这首先是因为罗马共和国本身就是在贵族的领导下创建的,最初的罗马公民就是指贵族和骑士(富商)这两个优越的等级或阶层。而且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贵族不仅家境优裕,而且世代公卿,家族门第长期掌握着国家权力。贵族子弟从小耳濡目染,跟随父辈在各种政治场合学习政治技能,立下了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所以成年之后很容易子承父业,跻身政坛,大展宏图。
一般而言,贵族子弟想要在政治上获得成功,需要满足几个条件:其一是高贵的身世和祖辈的荫护;其二是高尚的德行和卓越的功勋;其三是人民的拥戴和政治的机缘。在这三者之中,其一是背景根基,其二是必要条件,其三是时势命运。在共和国早中期的浓郁的权贵政治氛围中,缺乏了背景根基,其他条件很难满足,这样就注定形成了当时的执政官都是出身名门的惯例。
但是到了公元前367年,在广大平民要求政治权力的呼声之下,两位平民保民官在公民大会上通过了一条法律,这就是著名的《李锡尼-赛克斯法》。该法律中有一项条款明确规定,在每年产生的两位执政官中,有一个职位可以向平民开放,也就是说平民出身的人也可以成为执政官。果然在《李锡尼-赛克斯法》颁布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66年,罗马就出现了第一位平民出身的执政官,他就是制定这条法律的两位保民官之一的赛克斯。
然而,虽然有了法律上的规定,现实社会中的情形却是另一回事——自从赛克斯破天荒地打破了贵族垄断执政官的格局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罗马执政官仍然是由贵族出身者包揽。法律只是放宽了对平民出任执政官的限制,并没有规定两名执政官里必须有平民出身者。赛克斯本人之所以能够在《李锡尼-赛克斯法》颁布的第二年成为执政官,那是因为他本身既担任过保民官,又出生于平民中的豪门,他开辟了一条从保民官到执政官的通道。但是赛克斯之后,很少有平民再担任执政官,尽管这在法理上是被允许的。事实上,由于绝大多数罗马平民根本就不具备政治背景和政治资源,也缺乏从事政治活动的专业能力——注重法制的罗马共和政治是需要高度的专业素质的,不同于雅典民主制那样人人都可以参与——所以很难得到人民的拥戴和推举,更不可能得到元老院的认可。因此《李锡尼-赛克斯法》关于平民可以出任执政官的法律规定由于缺乏可操作的具体措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
到了公元前342年,罗马法律又进一步规定两个执政官都可以由平民出任,但是一直到公元前172年,才第一次出现了两位平民同时出任执政官的情况,这时已经接近共和国后期了。此后,越来越多的平民豪门开始跻身朝政,一些新贵家族开始染指执政官的职位,但是这些平民新贵一旦成为执政官和加入元老院,他们的政治立场很快就背离了平民,转变到贵族一边了。
四、法务官(副执政官)的设置和职权
随着《李锡尼-赛克斯法》在法律上打破了贵族阶层对执政官的垄断,贵族们也相应地向公民大会施压、令其通过了设置法务官(副执政官)的法案,并且明确规定法务官必须由贵族来担任,法务官分担了执政官的一些重要职责。因为到了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时候,罗马在对外扩张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版图已经大范围地拓展了。所以两位执政官需要治理的地域范围也日益扩大,面对越来越多的事务已经不可能事必躬亲,而法务官就是专门为执政官设立的助手。法务官最初为两名,拥有六个“法西斯”,后来随着罗马版图的不断扩大,逐渐发展为十六人。这些法务官主管司法和行省事务,并在执政官缺席的时候代行权力,他们的命令也成为罗马私法的重要来源。由于罗马地处意大利中部,经常受到周边部落结成的同盟的围攻,所以罗马军队需要在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当两位执政官分身乏术的时候,法务官也会替代执政官行使军事指挥权。
执政官是罗马最高的行政长官,大权在握,尤其是在共和国后期,更是执掌军权在罗马政坛上呼风唤雨。罗马历史上那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从马略、苏拉到克拉苏、庞培、恺撒,再到安东尼、屋大维等,都担任过罗马的执政官。
监察官
罗马共和国的另一个重要官职是监察官,监察官通常是从卸任的执政官里面选出来的,虽然从法理层面上来说,监察官的地位比执政官还要高,但是监察官实际上掌握的权力远远不能跟执政官相比。公元前435年,罗马共和国正式设立监察官,由罗马民众组成的百人团大会从卸任的执政官中选出两位监察官,任期18个月。监察官每隔四年左右要组织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人口普查。古代罗马的人口普查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罗马共和国早期最重要的社会组织是百人团,它根据财产资格把罗马公民分成六个等级。这些等级既构成了罗马人对外扩张时的基本军事单位,也构成了罗马人选举和税收的基本单元。而人口普查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调查公民的财产,包括钱财和土地,然后以此来划分等级。按照罗马法律的规定,公民在监察官进行人口调查时隐瞒财产是一种犯罪行为。当然在罗马共和国,也没有人会隐瞒自己的财产,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财产越多越好。因为财产越多,等级就越高,享有的政治权力也越大,当然需要承担的义务也更多。在罗马,财产调查就成为人口普查工作的最主要的任务,而监察官的重要职责就是负责推进这项工作。
监察官除了负责人口普查、财产登记和等级评估之外,还具有一种道德监督的职能。监察官往往都是卸任的执政官,德高望重,受人尊敬,他们也是国家最具威望的道德象征,所以公民才推选他们出来进行道德监督工作。监察官不仅可以对渎职的元老和卸任的执政官进行道德追责,还可以根据元老院的自然减员,推荐一些堪当重任、品德高尚的精英人士来补缺,成为新的元老。此外,监察官还负责公共财政与合同发包,主持赎罪节洁净仪式等宗教事务。
与执政官相比,监察官并没有执行权,他不能组织召开会议,也不能带领军队去打仗。作为国家的高级官员,他可以穿紫袍,也可以坐象牙椅,但是没有“法西斯”的仪仗。他不主管国家的内政外交事务,只是在人口普查、财产统计、等级划分和道德监督等方面发挥职能;他不掌握国家的公权力,只是国家道德的象征和维护者。
在罗马共和国中,监察官的道德评判与法庭的司法裁决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尤其是对于罗马上流社会来说,道德评判的意义丝毫不逊色于法律规范。在一个追求崇高和荣誉的强权社会,监察官的道德监督的重要性来源于罗马精英阶层自我激励的内在要求,也是出于应对广大民众的道德压力的政治需要。由于贵族构成了共和国的中流砥柱,所以身为贵族不仅意味着出身高贵,财产丰厚,还应该具有崇高的德行。因此,在道德方面对元老等统治阶层进行规范和劝勉,不断提高贵族的道德水平,就成了监察官的重要职责。
独裁官
罗马执政官、法务官、监察官以及其他较低级别的官员都是国家常设的官吏,他们的职位和权能都是相对固定的,但是在共和国的早中期,每当国家面临外敌入侵威胁或者其他重大危机,元老院就会推举出一位大权独揽、不受任何机构和个人制约的国家最高首领,这就是独裁官。
由于罗马执政官采取同僚制,而两位执政官的意见总会有所分歧,所以每当国家陷入重大危机,元老院就必须推举出一位能够力挽狂澜的领袖人物,凌驾于两位执政官的相互掣肘和元老院与公民大会的政治对立之上,总揽共和国的一切权力,乾纲独断,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独裁官一般都是德高望重之士,政治经验丰富,担任过执政官、监察官等高官,具有相当出众的领导才能,而且愿意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独裁官是一个非常设的官职,紧急情况下由两位当政的执政官之一推荐,经过元老院批准授权,任期为6个月。无论独裁官是否能够完成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赋予他的重任,都必须在任期结束时卸任。独裁官在任职期间大权独掌,不受任何权力机构的制约,元老院、公民大会、执政官、监察官都不能否定他的决断。除了代表罗马人民的保民官以外,独裁官的权力凌驾于所有高官之上(保民官也不能否决独裁官的决议,只是独裁官不得侵犯保民官的权限)。一旦独裁官接管了国家权力,执政官就处于大权旁落状态,一切唯独裁官马首是瞻。独裁官作为罗马军队的最高统帅,即“陆军统帅”(Magister Populi),他通常会任命一名与自己共同进退的副手即“骑兵长官”(Magister Equitum),协助自己来分担战场指挥和民政管理等方面的事务。
在罗马共和国的早期,由于罗马国势弱小,周边大敌林立,所以每当国家处于危急状态时,元老院就会临时将所有权力交给独裁官执掌。这些独裁官虽然在任期内独掌大权,但是都能够洁身自好,严守规则,决不贪权恋栈。这种高风亮节的执政传统,在共和国初期就已经立有典范:
公元前458年罗马遭到埃奎人的围攻,国家处于危急之中,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被元老院推举为独裁官,他就是辛辛那图斯(Cincinnatus)。辛辛那图斯曾经担任过执政官的职务,已经卸任回家务农。当罗马面临外敌入侵的危机时,元老院一致认为,能担当拯救国家重任的人非辛辛那图斯莫属,于是派人扛着“法西斯”仪仗去聘请他就任独裁官。当辛辛那图斯从农田里耕地归来时,使者向他宣读了元老院的任命,他二话不说,冲洗干净身上的泥污,穿上妻子递过来的长袍,就与使者一起离开家乡奔赴战场。结果辛辛那图斯只用了16天的时间就打败了强敌,然后立即把“法西斯”归还给元老院,再次解甲归田。在今天美国的俄亥俄州,有一个城市名叫辛辛那提(Cincinnati),它就是因辛辛那图斯而得名的,是美国人民为了纪念华盛顿不恋栈总统权力的事迹而建。在辛辛那提的市区,至今还有一座辛辛那图斯的雕像,他一手扶着铁犁,一手拿着“法西斯”。

辛辛那图斯出任罗马独裁官
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设计中有一个基本原则,即职位越高、权力越大的官员,任职时间就应该越短。两位执政官作为罗马常设的最高行政长官,任期均为一年。监察官威望虽高,但权力不大,所以可以出任18个月。而非常时期产生的独裁官不仅权力比执政官更大,而且是一人专权,相当于王政时期的国王,所以任职时间必须限制在6个月之内。在罗马,只有一个职位是终身制的,那就是主管宗教事务的大祭司长,但是他却没有什么政治权力。罗马共和国的这个制度设计是非常高明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掌握的权力太大,而且任期过长,就很容易演变为专制君主。由于罗马共和国是在推翻君主专制之后建立的,所以罗马人民对于一人专权的情况特别警惕和憎恶,在制度设计上必须要限制高级官员的任职时间。
和“法西斯”一样,“独裁官”这个名称最初在罗马并没有贬义,只是指称一种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临时官职而已。在共和国早期,尤其是公元前410年以后的50年间,由于罗马不断面临外敌的威胁,当时替代执政官掌权的6位军事指挥官又时常处于意见分歧之中,因此每到关键时刻,元老院就会推选出一位有能力、有担当的领袖人物来担任独裁官,让他合法地统揽权力,领导罗马人民来捍卫弱小的共和国。例如,著名的罗马英雄卡米卢斯就曾出任过5次独裁官,多次拯救祖国于危难之中。后来随着罗马国势日益强盛,版图逐渐扩大,罗马人从保家卫国走向了开疆拓土,也就不再需要独裁官这样的人物来应对危机了。特别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以后,罗马已经占领了大片的海外领土,国内安然无恙,威名声震四海,就更是用不着靠一位魅力型领袖来挽狂澜于既倒了。至此,独裁官制度基本上废弃不用了,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罗马政坛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独裁官。
但是到了公元前1世纪,罗马发生了内战,一个名叫苏拉的军事领袖代表贵族势力镇压了平民派。在挥师进入罗马、剿灭了与之对抗的马略党之后,大权在握的苏拉迫使元老院授予自己“无限期独裁官”的职位,以便集中权力来恢复贵族统治的古典共和体制。虽然苏拉在完成了他的共和重建计划之后急流勇退,告别了政坛,但是他所开创的“无限期独裁官”的先例却留下了无穷的隐患。
几十年后,同样通过军队干政而独揽大权的恺撒如法炮制,从积弱不振的元老院手中攫取了“无限期独裁官”的职位。恺撒不仅效法苏拉成为“无限期独裁官”,而且要做苏拉所未曾做亦未敢做之事,胁迫元老院和平民大会授予他“终身执政官”之职,实际上是要把罗马共和国变成恺撒帝国。恺撒的独裁统治激起了一批罗马贵族的极大愤慨,公元前44年,以马可·布鲁图斯为首的14名元老密谋刺杀了恺撒。
恺撒遇刺之后,在当年的执政官安东尼的倡议下,罗马元老院永久性地废除了独裁官的职位。从此以后,罗马政坛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独裁官,独裁官也就成为一个不光彩的称呼,被赋予了贬义。公元前30年屋大维在打败安东尼、完成罗马统一之后,虽然巧作安排把罗马几乎所有重要权力全都集于一身,但是他决不再像苏拉、恺撒那样使用“独裁官”的头衔,而是接受了元老院授予的一个全新称号“奥古斯都”。而从“独裁官”到“奥古斯都”的名称更迭也就意味着,冠冕堂皇的罗马皇帝从此取代了居心叵测的政治野心家。
“法西斯”内涵的演变
“法西斯”是罗马最高权力的象征,只有罗马的执政官、法务官、独裁官、骑兵长官等高官才有资格拥有,并且他们根据掌握权力的大小,分别拥有不同数量的“法西斯”,数量越多说明权力越大。例如两个执政官各拥有12个“法西斯”,法务官作为副执政官拥有6个“法西斯”,而独裁官则由于把两位执政官的权力集于一身,所以也把他们的“法西斯”全部据为己有,因此独裁官一个人拥有24个“法西斯”;他的副手“骑手长官”则拥有6个“法西斯”,和法务官一样。
“法西斯”仪仗本身具有“合众为一”、团结就是力量的含义。正因为如此,1776年在北美十三州联合的基础上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也把“法西斯”作为国家的标志之一,当时的“法西斯”一词并不具有贬义,而是“合众为一”的意思。因此,在美国参议院徽章的底部就印有两个相互交叉的“法西斯”,在缠绕着十三颗星星和红白相间的十三根竖条(均代表北美十三州)的一条飘带上,写着一句拉丁文“E PLURIBUS UNUM”,即“合众为一”的意思,表示美国参议院把各州的权力和力量集合在一起。
可见,“法西斯”原本是一个中性词,既代表罗马的最高权力,也具有团结一心、“合众为一”的意思。但是到了20世纪初,这个概念的内涵开始发生变化,流于贬义。20世纪初意大利出现了一个政治野心家墨索里尼,他在1921年建立了一个政党,取名为“国家法西斯党”(National Fascist Party),其寓意取自古罗马大权集中的“法西斯”概念。墨索里尼其人野心勃勃,狂妄至极,他不仅把自己建立的政党取名为“国家法西斯党”,而且选用了古罗马的“法西斯”仪仗作为政党的标志。通过权力运作,墨索里尼在1922年攫取了政权,他的“国家法西斯党”也就成为意大利的执政党。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墨索里尼一直控制着意大利的政权,并且利用“国家法西斯党”对内实行独裁统治,镇压人民;对外推行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与希特勒统治的法西斯德国相互勾结,成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一直到1943年“国家法西斯党”的暴戾统治才被意大利人民推翻,墨索里尼本人也在1945年被意大利游击队枪决并暴尸米兰广场。因此,“法西斯”就逐渐演变成一个贬义词了。

美国参议院徽章中的“法西斯”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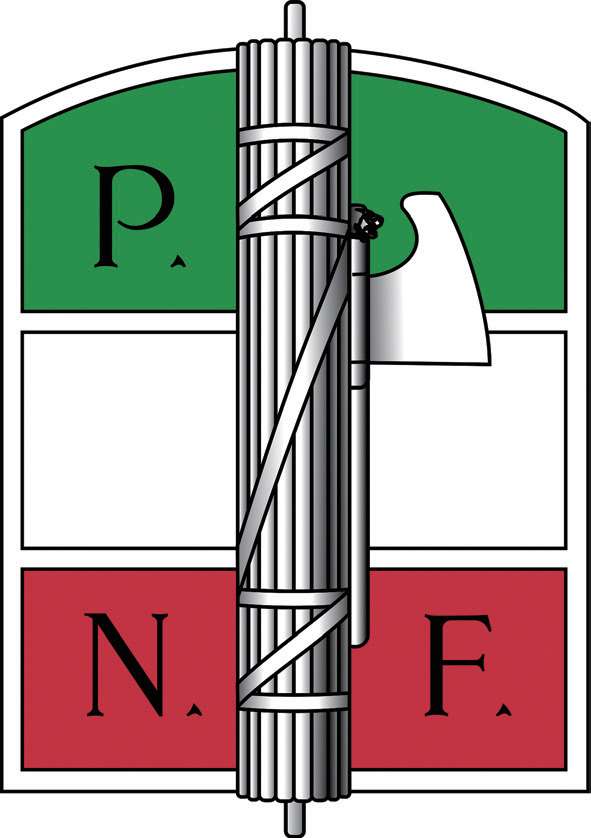
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