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谭 赴春
豖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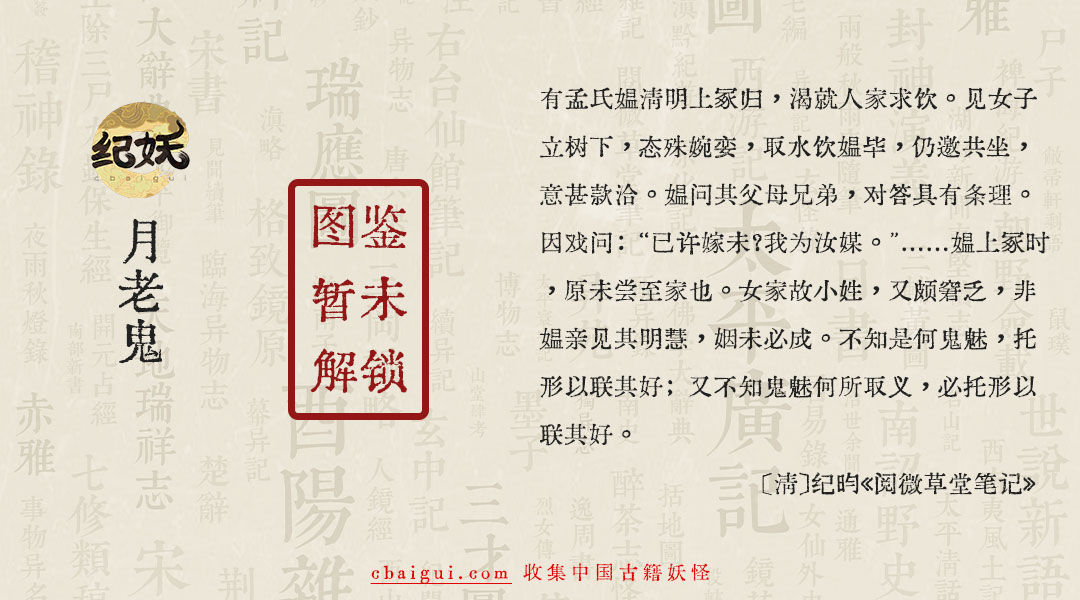
春暮,花谢檐上。
孟家今日迎新妇,到处张灯结彩,阖家上下的喜庆将这暮春恹色盖了过去。
孟家郎君可终于娶妻了。说起这孟家家事,可真是泰州城里的一大谈资。孟家历来一代单传,是泰州的书香门第,孟长屾他爹孟谨当年可是泰州最年轻的进士,可惜不好命,孟长屾才出生不久孟谨便患了痨病去世了,留下孟长屾和他娘孤儿寡母的。
孟母出身商贾之家,不懂文墨,却也是个泼辣角色,独自把孟长屾拉扯大不说,当年用自个儿从娘家带来的嫁妆起家,做胭脂布匹的生意,到如今孟氏商号已是泰州城排得上名儿的商号了。
虽说现在孟家家财万贯,但士农工商,这泰州城世代清贵的孟氏也算落俗了。
孟母原想着不打紧,还有个孟长屾,倒也不盼他能像他爹那样高中进士,只要能是个小小的举人也不算辱没门楣了。哪知她这儿子,文不成武不就不说,更是算盘都打不清,整日只知道眠花宿柳,是泰州城不折不扣的纨绔子,二十又三了,泰州城没一家姑娘敢嫁。
孟母为了他的亲事可没少操心。年年清明都把祖坟都磕遍了,这才求得这门亲事。
话说这亲事来的也是奇怪得很。
今年清明雨大,山路泥泞,孟母回程途中受困于坟山,天色暗淡之际得一喜鹊相引,来到了山脚一户人家,里头只有一个姑娘,姑娘心善收留了孟母。
二人相谈甚欢,孟母对这姑娘喜欢得紧,看这姑娘也是孤苦伶仃一人也心生怜悯,便想着提一嘴亲事,许给自己儿子,转念想到孟长屾那不成器的样子又怕委屈了人家姑娘。这思来想去又是一整夜辗转,待第二日孟母起来,见天色放晴,下定决心想要带那姑娘回泰州城时,早没了姑娘的人影儿,就连昨晚的农家小院儿都成了一间久无人居的屋子。
孟母冷汗涔涔,心道怕是遇见精怪了。可刚推门出去却见一夜之间山间桃花灼灼,回家途中一路斐然。她这前脚刚踏进府中,后脚就有媒婆拿着画像上门说媒。孟母一展画卷,怔愣半天,画上赫然是昨夜那姑娘的模样。
“这是扬州单家的女儿,单名一个宛字,生得很是灵动秀气……”
媒婆说的这门亲事远在扬州翕县,画中人是亡夫曾经同窗故友的独女,断不可能出现在泰州城郊的坟山上。媒婆一阵好说,孟母缓缓回神,管他神啊鬼啊,今日一路桃花斐然,昨晚奇遇全当结了善缘,大手一拍,敲定了这门亲事。
孟母对这门亲事满意得很,可孟长屾却不见喜色。
从定亲到成婚,竟只用了一月的时间,他也被老娘关在家里整整一月,现下心里憋闷得很,踢轿门时更是铆足了劲儿狠狠一脚,晃得轿子抖三抖,惹得围观孟长屾的狐朋狗友哄笑开来,可差点把孟母气得从高堂上蹦起胖揍孟长屾。
新娘却不恼,缓缓下了轿,莲步轻移,端庄得体,这模样倒是让孟长屾不免心生愧疚,便也收了性子,乖乖走完了流程。
“恭喜孟兄抱得美人归!”
“过几日梨园相聚孟兄可得请酒吃!”
“诶诶,孟兄如今成了亲可不知得伤了多少梨园娘子的心呢!”
见几位友人说得越来越离谱,孟长屾赶紧出言道:“再乱说话没你酒吃!”
众人又是一阵嬉笑,夜色也在觥筹交错之间悄然而至。
孟长屾喝得微醺,来到洞房门口却停住了脚步。
他孟长屾好梨园戏,甚至常宿于梨园,可梨园又不是勾栏,里头都是靠本事吃饭的人,他也从未有过逾矩之事。至于泰州城里那些风言风语,虽不尽是空穴来风,但也没那么夸张。他不过就是多了几个红颜知己,早几年年轻气盛扬鞭走马的也在城中逞过几次威风,再不然也就是没继承爹的才气也没有娘的精明,庸庸碌碌地沉溺于戏曲之中罢了。
以前他当然不屑于理会那些风言风语,但如今阿娘先斩后奏地给他娶了个新妇,倒也让他犯了难——要是再如此随性而为,他岂不是要误了姑娘终身,可他若是日后真遇见心悦之人……
孟长屾揉揉眉心,轻叹了声,推开房门。
室内稍有些闷热,孟长屾一鼓作气,径直拿起桌上的杆秤挑开了榻上新娘的盖头,盖头滑落的瞬间,孟长屾不经意一瞥,一张陌生而熟悉的脸撞入他的眼眸。
孟长屾只觉胸口一痛,心脏仿佛被攥住了,有些什么记忆的碎片在脑海飞速划过,捉不住看不明,只是眼前那双眸子灿若星河,直直看着他,这眼神仿若穿透了无尽黑夜专寻他而来。
“宛儿……”孟长屾呢喃出声,转而猛然回神,深吸了口气,赧然道,“咳,娘子……好生眼熟,还以为见过,咳咳。”
孟长屾还想再解释点儿什么,却听眼前人轻笑回应一声:“我在。”这声儿回答得娴熟,二字如玉,撞进孟长屾心间。
熄了灯,月朗星稀,院中落花和入泥土,满地旖旎。孟长屾觉得,有什么宝贝,在今夜终于失而复得。
孟母为人开明,一人拉扯大孟长屾,又是泰州排得上名号的女商贾,性格自然豪爽大气。
只是清明那日所遇实在奇异,如今逢人便说自家这天仙般的儿媳是月老牵线搭桥来的,这事儿也在泰州城传了好一阵儿。孟长屾朋友又多,每每出门儿必得被好友调笑一番,让他很是苦恼。
“我娘那嘴巴关不住,现下好了,娘子不是我娘子,反倒成了天上的神仙了。”
单宛闻言但笑不语,神仙她也没见过,她不过是个不愿过奈何桥的孤魂罢了。
孟母年年清明都得拉着孟长屾上香,今年不凑巧,孟长屾没随行倒是让她设计的“偶遇”扑了个空,还好念头转得快,造了个身份半路雇了个媒婆来说亲。不过也让二人到了暮春才见上。
思及此,单宛努努嘴,却听孟长屾哄道:“娘子何事不豫?院儿里日头辣,不如回屋里歇着?”
单宛还没接话,又听孟长屾道:“娘子莫不是嫌无聊,也是,日日在这宅子里都要憋闷死了……”说着孟长屾眨巴眼睛看着单宛,单宛听出话外音,哪是怕她闷着,分明是他想出府了。
“想去哪?带我去。”
“梨园新出了台戏,讲的是前朝戏伶宛娘和起义将军程恩的故事……”
孟长屾说起戏来就滔滔不绝,未察觉单宛收了笑容,怔愣了许久。
当朝男女设防不算严格,但孟长屾担心单宛介意他那些友人口无遮拦,便单独包了一间雅间。
今日的角儿是蕊生姑娘,也是孟长屾的知己之一,单宛眉头一挑,倒是让孟长屾在一旁解释了许久,涨红了脸。
锣声一落,满座凝神,故事在文人艺伶的润色后缓缓展开。
前朝末时,朝廷腐败,民不聊生,四方起义,程恩便是其中之一。
宛娘和程恩也算是青梅竹马,宛娘打小就长在梨园里,程恩却只是里头一个打杂的小厮。幼时宛娘落水得程恩相救,便就此相识了。宛娘是精心培养的戏伶,吃穿用度样样精致,却是笼中雀。程恩虽是下人,好歹能进出梨园,自由着些,常给宛娘带外头的点心,宛娘也会把自己学到的诗书教予程恩。
少时不知阶级恨,待宛娘及笄,开了嗓,引来京中贵胄一掷千金身份越发矜贵,常往来于各贵人府上,程恩能见她的次数越来越少。
偶有时机,二人只是隔着人海远远瞧上一眼。
后来程恩想要在将倾的时代里拼一个名利回来见宛娘,便从了军,一去数年,而后民乱四起,渐渐演变成兵乱,朝中人自顾不暇,梨园也渐渐没落。
经年之后,时局终定,李隆麾下的程恩将军率铁骑撞开了京城大门,从此天下易主。程恩封侯拜相后第一件事就是迎娶宛娘,十里红妆,万民恭贺。也是这场婚礼让李隆觉得程恩功高盖主,没两年光景,程恩入宫时离奇死于殿上还被扣了谋逆之名……
官兵围府,宛娘不签罪书,留下一曲赋春词,自刎而死……
程恩乳名春生,他一生都在寻天下春。
台上随着蕊生姑娘扮演的宛娘轰然倒地,故事便在此戛然而止。
孟长屾紧握着单宛的手,要是平日,他定会张嘴评说两句,但此时故事中的一切仿若他亲身经历的过往,让他的心绪久久难以平息。
“怪哉……”孟长屾刚想张口,却被单宛打断了。
“他从军不是为了野心名利,他生于朝廷式微之时,历经疾苦却见不得众生苦。跟随乾旭皇帝一路征战,赤子之心未泯。可乾旭帝暴政,百姓的日子不好过,饮冰十年,热血难凉,当初入宫觐见,是顾念十数年的同袍之情君臣之意,却羊入虎口,落得个死无全尸的下场。”单宛说到此处,声音微颤,眼眶微红伸手轻轻抚上了孟长屾的眉眼,“他总说众生苦,后来到了那个位置,站得高望得远,一人独醒,竟比众生还苦……”
单宛继续道:“宛娘……她原想和夫君同过奈何的,但是过了奈何来世不一定能见,若不巧又生于乱世,缘分那还是无果,他还是会走他命中该走的路,宛娘帮不到他,却只想和他做平凡夫妻。”
孟长屾急急开口:“若不过奈何不就是孤魂野鬼了吗?无论去哪都是异乡异客……”
“她等一个盛世,等他生时天下平,宛娘便可以同他做平凡夫妻了。”
孟长屾双唇微颤,他觉着有什么东西穿越生死岁月在此刻呼之欲出,良久却选择了沉默。
后来孟长屾考上了进士,在众人夸他浪子回头时他放弃仕途回泰州开了私塾,虽无高官厚禄,却也桃李天下,他想他的选择对得起盛世太平。
只是三十年岁月弹指间,又一年春至,孟长屾两鬓染霜,阖目朝身侧夫人道:“来世会是什么时候啊?”
“不知道啊,放心,你且走你的路。”
“嘿,当年娘亲还以为真是月老鬼牵线呢,没想还是你算得精明。”话落,二人眉眼皆染上笑意。
淌过这历史长河,单宛方觉混乱才是常态,盛世才是偶然。
也不知时间走了多少年。
午后阳光正好,胡同口的花店门前摆满了才打理好的花束,透过玻璃门,能看到一个少年百无聊赖地躺在躺椅上,桌上的收音机伴着“呲呲”声断断续续播放着电台。
收音机里的女声虽字正腔圆但也高亢尖锐:“封建迷信不可取,相信科学,走近科学……”
有人推开了花店门,少年半眯着眼朝里间喊道:“妈,出来做生意!”
里间“噼里啪啦”的麻将声和着女人的喊声:“兔崽子都大学生了还不帮老娘算算账!”
青年拿下扑在脸上的书本,跳下长椅却愣在了原地。
“单宛。”来人见他呆愣,便先开口。
“好,好久不见……不是,咱没见过,那个,我觉得姑娘眼熟极了,我的意思是……姑娘想买束什么花?”青年说完长舒一口气,他竟然忘记换气了!
随着单宛靠近,收音机的“呲呲”声更大了:“哗啦——有文化的青年人承担着大多数的社会责任……”
少年嫌桌上的收音机吵,伸手摁停了它。
单宛微微一笑,瞥了眼一旁的日历,1995年农历四月初九。
嗯,今生未晚,春意正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