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谭 蜉蝣梦
豖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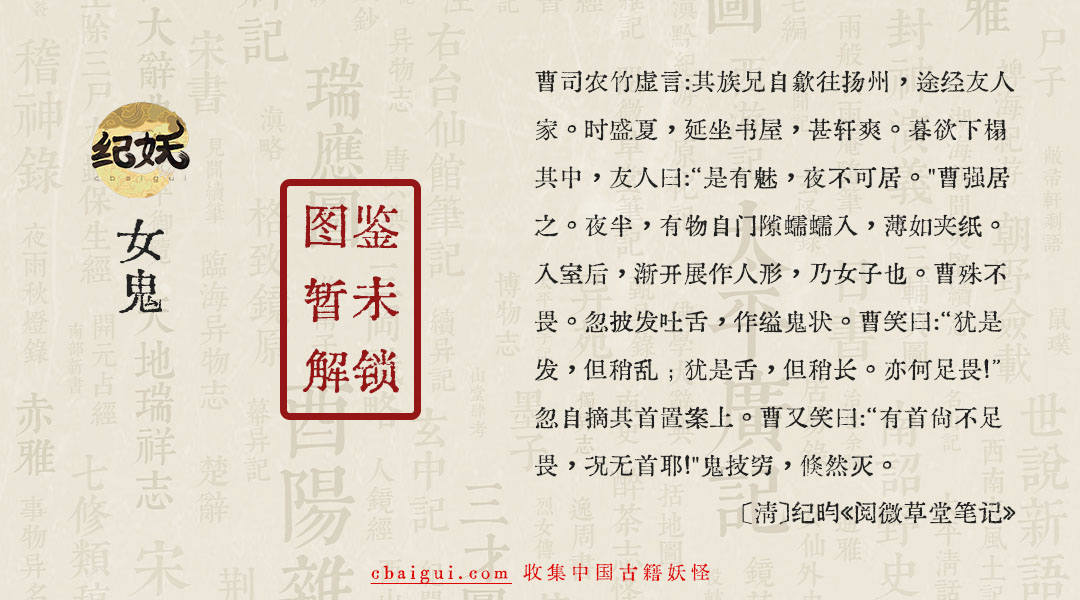
天下之富,泰半出自江南。
江南富庶,美人美酒美景样样不比京都差,世人无一不对其向往。
拨开虚妄浮糜,任你扬州再有雅韵,府衙的地牢内依旧如炼狱一般,噼啪鞭声伴着哀嚎求饶声,衙役的酒肉饭香和着血腥腐臭,此地就像扬州糜烂的脓疮,包藏着扬州所有脏污,被深藏于一片太平之下。
此时,牢狱最里间的牢房内,一个满身血污的中年男子虚弱地趴在草垛上。
萧娘没想到,再次见到曹宗旭会是这番画面,当年清风霁月的少年郎如今竟狼狈至此。
曹宗旭是一刻钟前才被府衙扔进这间牢房的,从他进来就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双目微闭,双拳紧攥,背上满是鞭痕,瘦削的背脊随着呼吸一起一伏。
萧娘也是打量了他许久才认出眼前这人的。她兴奋地蹲在曹宗旭跟前,抬手在他眼前晃了晃,问道:“喂,书呆子,你不认识我了?”
曹宗旭依旧没动静。
萧娘失落,她是个孤魂野鬼,前世不知背了什么孽不能上奈何桥,永远画地为牢在这地方打圈儿,好不容易见到故人,没想到他竟不认识自己了。
萧娘失落,重重叹息一声扶额坐下。
冷不丁地,曹宗旭开口,虚弱道:“你为何在此地?”
“呆子你可终于想起我了!”萧娘蹿起身,激动道,“你这是怎么了,怎会落得这般田地?哎呀我懂了,你不会变成你当年口中为人不齿的狗官了吧!”半句关切半句玩笑,她这吊儿郎当的样子还如二十年前一般。
可对于曹宗旭来说,二十年早已磨平少年棱角,不说他如今身陷囹圄奄奄一息,就凭他现在这把年纪怎么还和萧娘胡闹得起来?
萧娘见其沉默,自知不妥,她也是一时兴奋忘了如今境遇,便道了歉,低声解释:“都二十年啦,从前的北区舍廊改为了现在的官衙。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难行于方寸间,喏,就此地,就这间牢房,正是你当年苦读的那间破旧小屋呀,我一直困在这儿的。”
任凭此地改屋换舍,任凭人来人往物是人非……这便是她的宿命。这样一想,萧娘也难免自怜起来,却听曹宗旭突然低低地笑起来,这笑声似不甘更似自嘲。
回忆走马灯般在曹宗旭脑海里闪过。
少年须有凌云志,这是二十年前曹宗旭拍着胸脯告诉萧娘的。
那时曹宗旭不及弱冠,正准备科考,靠给人抄书写话本赚钱维持生计,在扬州城的北区舍廊租了间最便宜的小室。传言此间闹鬼,所以他才捡了个大便宜。
萧娘便是传言中那只厉鬼,在此处徘徊已有数年。
曹宗旭历来不信鬼神,可是第一晚住下他就实打实被萧娘惊了一跳。
也仅仅只是惊了一下。
萧娘从未有过恶意,只是每每见有人进了自个儿的地盘便会夜里现身吓唬吓唬,那些人不是高喊着饶命就是尿了裤子对着她倾诉恶行哭着忏悔。时日久了,在萧娘眼里,人心都是些藏污纳垢的,没一颗干净的。
她如此想着,吓唬人的行径就越来越恶劣了。
那晚见曹宗旭闭着眼摇头晃脑地背着书,她便摘了脑袋抱坐在曹宗旭的书案上。待曹宗旭背到兴处,翻来覆去仔细品着那句“少年须有凌云志,不负黄河万古流”时,陡然一睁眼,被吓得一个倒仰,和萧娘呆呆对望。
不待萧娘继续有动作,曹宗旭先开口问:“姑娘深夜造访,是……是有何冤屈?曹某人微言轻,不知如何能帮到姑娘?”
这问得萧娘一愣神,她能有什么冤屈?
“书书,书上说,人死有冤,魂凝而不散……所以……”
萧娘见他不似之前那些孙子,不过还是被吓得舌头都捋不直,便恢复了人的样貌,笑骂了一声:“呆子!”
那夜之后曹宗旭也没搬走,一是这处实在便宜,二是他察觉那女鬼没有恶意。
一人一鬼便如此相处了数月。
萧娘问过曹宗旭:“呆子,你就不怕鬼神?”
“心乱而神散,只有心中有愧之人才会惧怕。”
萧娘撇撇嘴,道:“你呢?你心里有什么?”
“西北蛮人犯境已有十年,如今战乱仍然未靖,我本想弃笔从戎,但如今新帝年幼,朝纲不稳,我要入朝为官,为我朝尽我一份绵薄之力。”话落,曹宗旭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一声。
可把萧娘逗得捧腹大笑:“啧啧,书呆子,你应该先吃饱饭!”
……
“呆子!你怎么了!”萧娘见方才狱中曹宗旭突然大笑,又突然一言不发,可把萧娘惊了一跳,他不会是神志不清了吧!
久久,曹宗旭开口:“此处原来就是当年小室。螳臂当车,蜉蝣一梦啊。可笑啊可笑。”
兜兜转转一个圈儿又绕回来了,什么少年志向,不过沧海一粟,蜉蝣之志罢了……
“这有什么可笑的?”萧娘自然不懂,想法跳跃得也快,追问,“你从前不是想为官吗,现在是什么官啦?哦对了,你还没说怎么入的牢狱呢。”
曹宗旭艰难撑起身子,坐在草垛上,就这么一个动作牵扯身上的伤口又汩汩流血,待他坐定已是气喘吁吁。
萧娘虚形一个,根本帮不上忙,只能跪坐一旁垂首相陪。
良久,才听曹宗旭缓缓道来。
“监察御史,七品小官罢了。说来,短短两年内,我已是扬州上任的第四任监察御史了,前几位不是突发恶疾就是贪墨被捕,呵,如今看来事实远非如此简单。”
曹宗旭为人刚直,年初才上任不久便发现扬州财税有问题,一查更是惊人,不止扬州,整个江南税务都有极大漏洞。
那么大一笔亏空,就算扬州池州泰州几州州府联手也消化不了啊!
曹宗旭知这张大网远不止江南,顺藤摸瓜,竟然查到了南京,一切线索直指陈王,连续五年,年年都有一大笔进账陈王府,从未听说陈王好享乐,如此一来,这些私银养一匹私兵都绰绰有余了!
曹宗旭连夜秘密修书回京,哪想到没等来京中回应自己却两眼一抹黑被绑至此。原来陈王已经嚣张至此,看来之前无故“病逝”的官员也是同他遭遇一样了。
思及此,不免又唏嘘,什么入仕为官,做什么河清海晏的荒唐梦,朝廷积弊,不过大厦将倾罢了。
“只是没想到,如此之快,如此之快便查到了我头上……”
“嘘——”曹宗旭话未说完,便被萧娘抑住,“有人来了。”
萧娘虽不能踏出这方寸,可耳目却是极灵敏的。
果不其然,一个绿袍官员带着几个狱卒,开了曹宗旭这间牢门。
萧娘一动不动跪坐在原地,这狱里的人各个戾气深重,别说看不见她,就算看见了也得压她一头。
曹宗旭见到来人,扭头闭上了眼。
“曹御史就别装死了,你可知污蔑藩王是要杀头的。”说罢,那绿袍晃了晃手上的信纸,俨然就是曹宗旭送出的那封修书。
“我劝你还是识时务些,快些把证据交出来,兴许能留你一个全尸。”
曹宗旭眼皮都没抬,任凭绿袍如何言语,他依旧不吭一声。
“哼,死鸭子嘴硬,罢了罢了,你以为凭你一个小小的监察御史,还真能掀起什么浪来不成!不就是多一个病死的官吏吗,来人,埋了吧!”说罢转身便出了牢门,几个狱卒上前,将曹宗旭拖走了。
萧娘依然跪坐原地,孤魂野鬼一个,无形无体,无知无觉的,连故人都救不了,那么些年来从未有此痛苦无力。
想来二十年前那个清朗少年,在暗里踽踽独行那么久,看皇帝昏庸,看朝廷千疮百孔,能守住本心走到现在,比她痛苦千百倍吧。
萧娘已经记不清又过了多久,许是数月,许是数年,直到某天,听外头哀嚎遍野,她惊觉自己已然没了画地为牢的禁制。
地牢里不见天日,出去才知是白昼。
怎会是白昼?她如何能见日光?
再定睛一瞧,哪还有什么扬州啊,断壁残垣,尸横遍野,几个残兵清理着昔日同伴的断头残肢,游荡的鬼比地上的人还多。
那颗太阳就高悬天上,惨白惨白的一个。
她想起曹宗旭后来讲自己少年志是蜉蝣一梦,不自量力。是不自量力吗,天下分分合合,每每再定局势必是白骨堆英将,蜉蝣虽不能千古,但他们注定埋没在大潮里的奔走呼号,会成为历史的微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