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大正九年,我们第一次远赴云冈游历,逗留了十七天,在走进并熟悉了那些石窟石佛的当时,并没有胸怀从艺术史乃至佛教艺术史的角度对那些石窟石佛进行研究的野心。我们只是陶醉于那浓郁的艺术美感中,并且全身心沉浸在了当地那铺天盖地的牧歌情调和遗迹旧城灰飞烟灭般的哀愁里。因此,我们只集中精力关注自己所喜爱的地方,也因此,关于第一窟至第六窟记述颇多,却反而疏略了对第十九窟的大露佛以下的西方各座石窟的观察。在《云冈日录》中,我只记述了当时的心绪,却缺乏客观记述以及进一步的研究,这一点恰似我的写生画——笔下所画未必与原物相像。因此,我认为这不是研究,而是一种文学,所以,才答应了座右宝出版社的请求,同意再版十八年前的旧书稿。然而,今天若欲再版发行,那么,仅凭昔日的天真烂漫或满腔好奇与热情断然不妥,云冈石佛如今已经开始以“学问”的形式被大规模地进行研究了。作为我自己,当年只要时间允许,我甚至也想把自己心中眼中的云冈发展成一门学问。然而,大正九年五月我已经定好了途经美国前往欧洲的行程了,因此,研究石佛的事业也就此完全中断了。
大正十三年,我从欧洲回来,发现我那为数不多的家产以及收藏品都已毁于东京大地震了,我那贫乏的中国学研究因而已失去了复兴的可能。因此,我开始将研究目标转向了天主教传教士文学。
当云冈石佛重新引起日本人的兴趣时,我也想起了我的《大同石佛寺》。因此,当我被鼓动着重印此书时,心想,至少可以把它当作一份对十八年前的云冈进行一种文学性追忆的材料,因此就应允了,只是想附上一份篇幅不长的《跋》使之重见天日。
匆匆忙忙中我写下了《大同石佛杂谈》,又翻阅了《魏书》(这也是跟齐藤君借的),对“北魏的造像”进行了考证。
我同时阅读了手边能够收集到的仅有的一点儿石佛研究文献。也正因此,我越发感到无法忍受将旧稿原封不动地重新印发出来。这时,《云冈日录》已经排版完毕了。时至今日,若想重新开始进行石佛研究,我既无这个精力也无那份毅力,所以,我决定至少也要补充进一部《云冈石佛文献摘编》以多少履行一下自己的责任。今年九月以来的几个月,对于我们几个人来说,是一年中最为忙碌的一段时间,就连稍稍涉猎一下那些文献的零星时间都很难抽出来。然而,对于此事,比起我来,齐藤菊太郎君更为热心,因而这部文献摘编的一半全亏他的帮助才得以制成。或许还有尚未受到瞩目的论文和考察记录等,但我们的收获的确超过了当初的预想,而且我们也管窥到“云冈石佛学”终于开始逐步巩固其兴建的基础了。作为我本人,从“杂谈”经过“造像”而跋涉到“文献摘编”的这个过程中扩大了知识面,增长了见识。以我此刻的感觉来说,《杂谈》等文章,要么应该全部改写,要么就该付之一炬。
佛教美术研究今后将更加兴盛起来,而且大有趋于完成的倾向,因此,我只希望这部增补重印的《大同石佛寺》也能成为这条道路上的一个路标,如此我将不胜欣慰。而同时,虽然都说比起龙门石窟来,云冈石窟没有什么变化,但即便如此,我们去参拜的时候与今日相比,至少感情方面的氛围已经很难说未发生巨大变化了。恐怕如果现在前往大同的话,和记述《云冈日录》的当时加以比较,必定要发出惊叹吧:从前是这个样子的吗?我想,这种文学性追忆情怀或许能对这部《云冈日录》有所裨益吧。然而,即便如此,如果没有山本明先生准许我们复制了那一百多张照片,本书的再版恐怕会失却大半依据吧。
此外,我还烦扰了东京帝国大学工学系的藤岛亥治郎教授,因而才能重新阅览到建筑学教室所保存的印度寺院和石佛的照片。借此机会,再次对藤岛、山本和齐藤三位先生表示谢意。
正如前面所述,在观看云冈石佛时,我并没有站在精确的科学观察角度上,而只凭偏爱喜好之情(在序文中已经提到)。因此,像第七窟前壁的大佛龛里的佛像(参见第六十三幅图片),铭记在我脑海里的是和那张照片印象完全不同的样子。我试图将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那座佛像用纸笔再现出来,可是,当时试过两三次都以失败告终。但我仍想把那种感觉稍微表达出来,因此,在这里插进一张当时未画完的写生画(参见第六十五幅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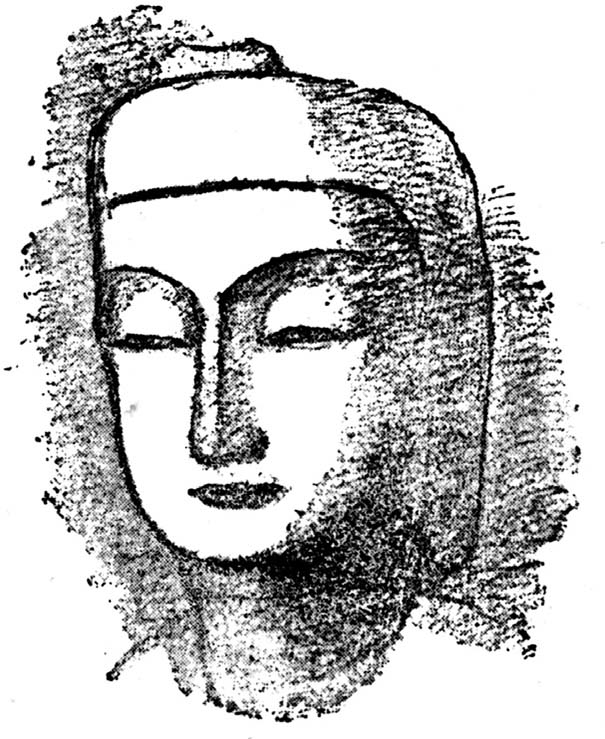
第六十五幅插图 第七窟前壁大龛里的坐像的头
这尊佛像,据关野博士的鉴定,似乎是隋朝所造的东方第三窟中的胁侍菩萨(参见第七十三幅图片),如此说来,果真是佛像雕刻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部作品了。只是由于我们当时认为佛像整体部分并不协调匀称,所以,没有给予多少关注。尽管如此,德国汉学家贝尔契斯基(Perzynski)在其著作《中国诸神》(1920年出版)中,以不同于以往的观察者的视点拍摄了这尊佛像,留下了异常优美的影像(参见第一一二幅图片)。我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的喜好也会发生变化,从这个层面上讲,在观赏从前的艺术品时,无论如何都要如此修补一下。这是因为,由人类的双手创造出来的东西往往未必能够将其所思所想完全立体化。通过作品将从前的艺术家心中的形象在我们自己的内心进行再现,就是观赏艺术性(或者宗教性)作品的途径吧。也许,《万叶集》里的和歌也是如此,对和歌的解释在创作之初与现在未必是完全一致的。然而,通过和歌来获得与作者魂魄相通的感悟,这一点则要赖于我们迥异于他人的人生经历了。在此,请允许我把多次引用过的阿纳托尔·法朗士(1)的名言再次抄录于此:
我们今天即使读到《伊利亚特》或者《神曲》里的某一行,也并没有按照它们创作之初作者所思考的意味来进行理解。所谓的生存的过程,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而能够记述我们思想的来世的生活,亦无法摆脱这个法则。
古代的艺术品也在不断地获得重生,并且,其中那些精美的艺术品还会在不断的重生中迸发出神奇的光芒与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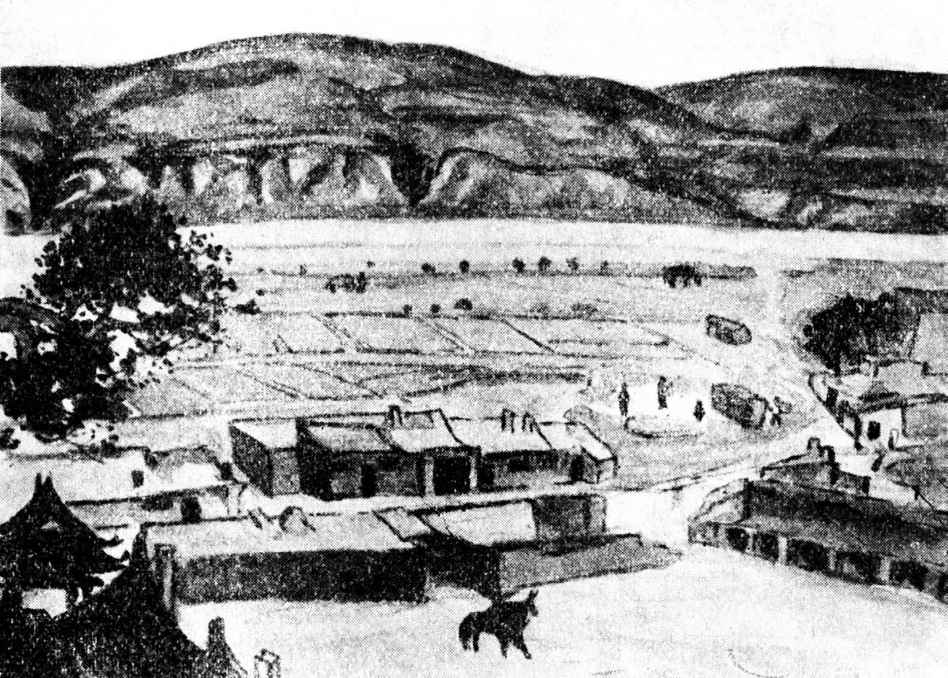
第六十六幅插图 云冈风景(由本书作者临摹)
中央第六窟和第七窟(参见第五十八幅、第五十九幅图片)等雕刻的风格起源,恐怕今后还会再次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吧。这是因为中央第一窟、第二窟等洞窟的构造形式十分奇异,同时,第十八窟、第十九窟中佛像的形态(大露佛)也迥然不同。松本文三郎博士认为,由于它们与笈多风格的雕刻相似处颇多,因而可以断定为云冈石窟初期的作品。我对此判断虽有异议,但那些佛像属于中印度型这一点却似乎不容置疑。只是由于后世的修补痕迹过重,所以,已经很难识别其原貌了。即使能够剥下其假面、清除其补色,无论是姿态还是衣服褶皱等属于中印度型这一结论恐怕也不会动摇吧。在此插进一张建筑学教室(指东京帝国大学工学系的建筑学教室。——译者注)里保管的照片(参见第一一三幅图片),把这幅照片与第五十八幅图片的下侧左方的立佛进行一下比较,一定会惊讶二者何其相似吧。
读三上次男先生的《从张家口到云冈》中的纪行文,得知在云冈一带出现了中国方面的军营和病房,而在紧邻石窟古寺的地方又建造了旧山西军的骑兵司令的别墅。说是没有变化,但同十八九年前相比还是有了很多改变,为了展示这种变化,在此插入一张笔者从中央第一窟或第二窟的楼门最上层俯瞰时所画的粗拙的风景画吧(参见第六十六幅插图)。
无论怎样写下去,我手中这支钝笔都无法溢彩生花,也罢,还是就此搁笔吧。
昭和十三年十一月六日(1938年11月6日)
在第二次地震强烈的余韵中。
(全稿完)
————————————————————
(1) 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年4月16日—1924年10月12日):二十世纪前叶法国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家、文艺评论家,曾获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