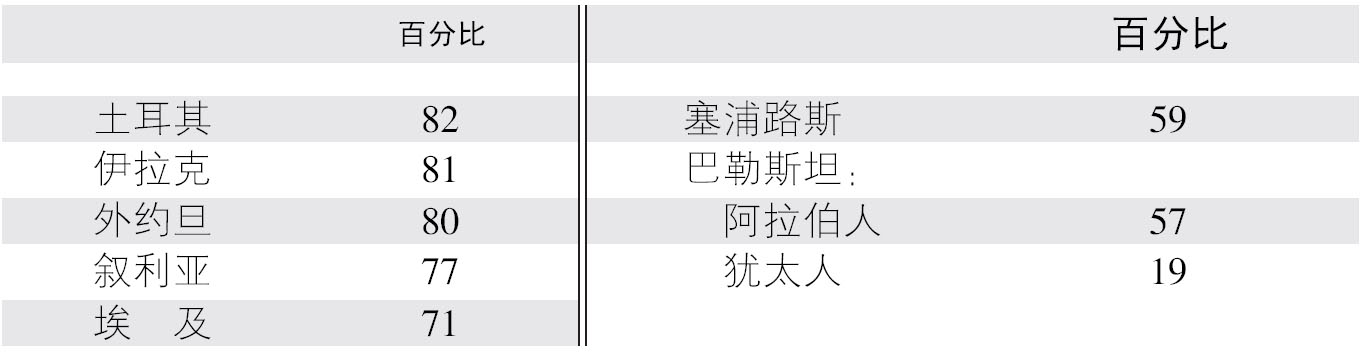
“土地所有权是建立在一个复杂而古老的制度的基础上的……社会结构类似封建制度,但是,除少数例外,那些对大面积土地拥有绝对或世袭所有权的人实际上都是一些不在故乡的地主……地主收取现金或实物地租;他甚或把收租权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这对他的佃户显然具有不幸的后果;不论出于自觉或不自觉,他实质上是土地和他的佃户的剥削者。不用说,造成这种灾难性局面的责任不在于个别地主,而在于古老的社会制度……
“但并非全部土地都为大地主占有,还有一些自耕农。1933年埃及的数字表明,虽然仅占土地所有者总人数0.6%的拥有50英亩以上的大庄园占全部耕地39%,也还有不少于2/3的土地所有者平均每人可得2/5英亩的耕地。这些小土地所有者在经济上是难以致富的……其结果是整个中东的这一阶级都落入债主的掌握。他们虽然有土地,但缺乏改良土地的手段。境遇并不比大地主的小佃户强,佃农土地的租借期限是以一年计。”〔B·A·基恩:《中东的农业发展》(B.A.Keen: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Middle East),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6年版,第13—14页〕
欲知大概,可参阅艾尔弗雷德·邦内:《中东的状态和经济学》〔(Alfred Bonné: State and Economics in the Middle East),伦敦,基根·保罗、特伦奇、特罗勃纳,1948年版〕和多琳·沃里纳:《中东的土地和贫困》〔(Doreen Warriner: Land and Poverty in the Middle East),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48年版〕。
(8) 参见H·A·R·吉布:《伊斯兰教》(H.A.R.Gibb: Mohammedanism),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144—146页。
(9) 此种“阿拉伯觉醒”在其早期几个阶段乃是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多半是基督教徒)的事业;主要是在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以后,(富有的穆斯林)上层少数派的年轻一代便抓住了此种运动的政治方面作为增强他们自己权力的工具。在这点上,1908年和1914年之间成立的那些政治团体的成员的名字是很有启发性的。参阅乔治·安东尼厄斯:《阿拉伯觉醒》(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38年版,第95页和第108—111页注。
(10) 关于埃及的这一进程的各个阶段,见《概览,1925年》,i.189—238;《概览,1928年》,第235—283页;《概览,1930年》,第188—222页;《概览,1936年》,第662—701页。关于伊拉克,见《概览,1925年》,i.466—471;《概览,1928年》,第339—342页;《概览,1930年》,第317—329页;《概览,1934年》,第109—213页。
(11) “1936年条约是在一场国际危机中缔结的,其时战争的幽灵已经出现……如果说埃及已接受了这一条约及其所意味的有关独立的种种限制,那是因为它知道这一切都是过渡性的……”(埃及致英国的照会,1945年12月20日;文本载《泰晤士报》,1946年1月31日)
(12) 一位意大利观察家客观地写道:“在这一种心理状态下,法国的政策总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希望保持那种已经过时的物质的或道义的立场而不能顺利执行。而英国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尽管对最坚定地保持它自己的利益这一点牢记不忘,但它总是懂得如何调整它的政策,使之适应每一个国家逐渐在发展的各种因素,并且明智地交替使用干涉或不干涉的手法,而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奉行的政策,虽然对普遍性问题所取的看法是宽广的和具体的,但失之于过分片面,往往忽视了细节,往往由于宗主国法国内部人物性格或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受制于意外变化。”克雷安提(笔名):“法英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政策”,《新诗集》(Cleante, pseud:“Siria e Libanonella politica franco-inglese”,Nuova Antologia),1945年8月号,第313—314页。
(13) 关于法国—叙利亚和法国—黎巴嫩的关系,见《概览,1925年》,i.346—366和386—457;《概览,1928年》,第328—332页;《概览,1930年》,第304—314页;《概览,1934年》,第284—301页;《概览,1936年》,第748—767页。
(14) 有关本节的一般情况,参阅作者的《中东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伦敦,梅休因,1948年版〕,第6章:“争取独立的斗争,1918—1939年”,第129—193页。
(15) 法国相应的战略据点是贝鲁特港和吉布提港,以及黎巴嫩的里亚克飞机场。
(16) 《联合王国的政治和战略利益》(Political and Strategic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Kingdom),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一个研究小组著,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39年版,第128页。
(17) 关于这些战略要地,见《概览,1935年》,ii.249—251。又见上文,原著第26—27页。
(18) 伊利莎白·门罗:《政治上的地中海》(Elizabeth Monroe: The Mediterranean in Politics),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8年版,第12页注①。法国从伊拉克得到的石油占其所获总供应量的40%以上(同上书,第75页)。
(19) “‘探明的蕴藏量’的依据是对留在地下的石油数量所作的科学估计,是通过实地钻探业已发现并可以用现有的经济方法复核的。这些估计数字往往因新油井的情报、新方法的应用以及价格变化而往往随之更改。”引自雷蒙德·F·米克塞尔和霍利斯·B·切纳里:《阿拉伯石油》(Raymond F.Mikesell and Hollis B.Chenery: Arabian Oil),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15页注②。
(20) 弗雷娅·斯塔克(Freya Stark)在写到这一论题的时候谈到,随着远程飞机的发展,“非洲路线就同横越阿拉伯路线一样方便了,阿拉伯的地方性骚动就不值得单单为了空运之事去进行谈判了”,接着她以素来生动的笔触写道:“石油之进入画面,犹如地质图上之奇峰突起,使整个景色顿然改观。由于石油的发现,阿拉伯国家又一次处于它们历史上曾经经历了2 000年之久的那种地位,即再度成为世界上一种最有价值的产品的中间人,而且这一产品确确实实多半埋藏在它们的领土之内。”见“阿拉伯背景”,《每季评论》(“Arab Background”,Quarterley Review),1949年1月号,第59页。
(21) 参阅A·C·爱德华兹(A.C.Edwards)关于波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陷入困境的论述:“重访波斯”(“Persia Revisited”),《国际事务》,1947年1月号,xxiii.55,57。
(22) 此种在政治上划分为“极端主义者”和“温和主义者”同汤因比所阐明的在文化上可分为“狂热的反对派”和“盲目的支持者”是截然不同的〔见《文明在考验中》(Civilization on Trial)一书的“伊斯兰教、西方以及未来”,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第187—212页〕;参阅《概览,1925年》,i.6—7。例如,“狂热的反对派”瓦哈比运动的领袖伊本·沙特自从他为自己取得了阿拉伯的君权以后就在国际政治方面变成一位“温和主义者”;同样地,塞努西首领赛义德·穆罕默德·伊德里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了一位国际上的“温和主义者”,因为他希望因此获得君权。另一方面,在“肥沃新月”各国和埃及,有不胜枚举的文化上的“盲目的支持者”变成了政治上的“极端主义者”。因为,不论是为了提高个人的地位,或为着追求他们不屈不挠地为之奋斗的某种政治原则,他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手段可以获得权力。
(23) 原文是“effendis”音译为“阿凡提”,意为“先生”、“阁下”,过去是阿拉伯人对外国人的称呼。——译者
(24) 一方面,“这样说也许不会不确切,即埃及的人口密度——相对于资源总额而言——高于联合王国8倍”;而另一方面,“埃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比联合王国高11倍”。K·A·H·默里:“中东的某些区域性经济问题”(K.A.H.Murray:“Some Regional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Middle East”),《国际事务》,1947年1月号,xxiii.13;A·S·埃班:“中东的某些社会和文化问题”(A.S.Eban:“Some Social and Cultural Problems of the Middle East”),同上,1947年7月号,xxiii.370—371。
(25) 见《概览,1934年》,第100—109页;《概览,1936年》,第720页注;《概览,1937年》,i.568—571;《概览,1938年》,i.415—416,445,458注。
(26) 例如,由学校教师哈桑·班纳领导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Ikhwānal-Muslimūn);律师艾哈迈德·侯赛因领导的青年埃及党(Misr al-Fatāh);由曾在贝鲁特美国大学任教的安通·赛阿达领导的叙利亚国民(或人民)党(Hizb as-Sūrī al-Qawmī);其领导人不断更换的叙利亚民族行动联盟(‘Usbat al-‘Amal al-Qawmī);大概是由律师兼政客奈比赫·阿扎麦领导的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俱乐部(Nādī al-‘Arabī);其主席是在柏林学习过的牙科医生赛伊德·法塔赫·伊玛目。伊拉克军训团(青年运动)是政府采取极端主义的合法产物;另一方面,由化学家皮埃尔·杰马耶勒领导的黎巴嫩长枪党则在耶稣会会士的唆使下推行黎巴嫩脱离叙利亚而依附法国的分离主义。有关叙利亚和黎巴黎的组织情况,参阅《现代东方》(Oriente Moderno),1941年3月号,第101—103页;关于伊拉克军训团的情况,参阅同上,1940年6月号,第297—302页。
(27) 贝尔纳·韦尼埃:《德国的伊斯兰政策》(Bernard Vernard: La politique Islamique de L'Allemagne),巴黎,对外政策研究中心,1939年版,第92—95页。
(28) 参阅塞思·阿塞年:“中东的战时宣传”,《中东杂志》(Seth Arsenian:“War time Propaganda in the Middle East”,Middle East Journal),1948年10月号,ii.419—421;内维尔·巴伯:“向阿拉伯世界广播”(Nevill Barbour:“Broadcasting to the Arab World”),同上,1951年冬季号,v.58—59,63。齐亚诺记录了巴里电台的阿拉伯语反英广播使他如何偶然为一位黎巴嫩主教的兄弟找到一个时事评论员的工作。加里亚佐·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Galeazzo Ciano:1937—1938 Diario),以下称为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波洛尼亚,卡佩利,1948年版,1938年1月24日日记。
(29) 见《概览,1936年》,第526—533页;《概览,1937年》,i.465—495;《概览,1938年》,i.43—69。在1938—1939年,土耳其和波斯同德国的贸易分别占它们各自的对外贸易总额的45%和31%。德国同埃及的贸易则仅次于英国而占第2位。
(30) 见《概览,1938年》,i.446。
(31) 见《概览,1925年》,i.471—531;《概览,1936年》,第767—783页;《概览,1938年》,i.479—492。
(32) 见《概览,1936年》,第793—803页。
(33) 同上书,第783—793页。
(34) 关于圆桌会议,见《概览,1938年》,i.440—458。1931年在耶路撒冷还召开过一个非官方的泛阿拉伯代表大会(见《概览,1934年》,第99—109页),1937年在(叙利亚)布卢丹也开过(见《概览,1937年》,i.552—553,又见胡拉尼:《叙利亚和黎巴嫩》,第114—115页)。在操阿拉伯语的各国人民看来,1918年以后在中东划定的各条边界线怎样说也不过是人为的,且不谈这些边界线在政治上是多么可憎。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他们从来不知道有这种障碍物。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显贵家族的成员曾一起在伊斯坦布尔或欧洲学习,其中有许多人还互相通婚。
(35) 见《概览,1936年》,第793—803页;又见弗朗西斯科·卡塔路西奥:“萨达巴德公约”,《意大利述评》(Francesco Cataluccio:“Il patto di Sa ‘dābād”,Rassegna Italiana),1940年4月号,第247页。
(36) 见《概览,1934年》,第523—530页。
(37) 见《概览,1920—1923年》,第370—373页。
(38) 阿瑟·C·米尔斯波:《美国人在波斯》(Arthur C.Millspangh:Americans in Persia),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1946年版,第3章;但参阅A·C·爱德华兹文,他于1948—1949年在波斯游览了9个月之后写道:“有趣的是发现……已故国王的声望……不仅得到了支持当前立宪政权的知识阶层的承认,甚至还提高了。因为礼萨国王的成就之显赫是有目共睹的;而他的暴政所引起的仇恨却正在被忘却。他今天在波斯被认为是自那位近乎传奇式的国王阿巴斯一世以来最伟大的国王。这位国王最近被授予尊敬的‘大帝’称号。”《今日世界》(The World Today),1949年9月号,v.393—394。
(39) 皇家国际事务学会:《英国和埃及,1914—1936年》(Great Britain and Egypt 1914—1936),情报部文件第19号(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36年版);菲利普·格雷夫斯:“埃及危机史话”,《十九世纪》(Philip Graves:“The Story of the Egyptian Crisis”,Nineteenth Century),1938年3月号,第297号。
(40) 参阅马吉德·赫杜里:《独立的伊拉克:1932年后的伊拉克政治研究》(Majid Khadduri:Independent Iraq, a Study in Iraqi Politics Since 1932),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51年版,第71—137页。
(41) 参阅H·A·R·吉布和哈罗德·鲍恩:《伊斯兰社会和西方》(H.A.R.Gibb and Harold Bowen: 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第1卷,“18世纪的伊斯兰社会”,第1编(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50年版),第258—271页,第295—296页,第307—308页。
(42) 犹太人人数从1922年的8.4万人增加到1938年年终的41.1万人。从1919年到1938年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的58.9%属波兰、俄国、罗马尼亚和立陶宛等国国籍〔英国殖民部:《关于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的管理工作报告,1938年》(Report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Palestine and Transjordan, 1938),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39年版,第231页;巴勒斯坦政府移民部:《年度报告,1938年》(Annual Report, 1938),耶路撒冷,政府印刷局,1939年版,第70页〕。
(43) 例如《自我解放》〔(Auto-Emancipation),1882年版〕的作者利昂·平斯克尔,尤其是在1896年的《德雷福斯事件》(Affair Dreyfus)的影响下写了《犹太国》(Der Judenstaat)的西奥多·赫齐尔。“犹太主义向来是民族主义、尚礼主义、弥赛亚主义和醉心上帝的特种混合物……”,对这种断言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有多少人认为是适当的,了解这一点是饶有兴趣的;见一位评论家的文章,载《犹太复国主义评论》(Zionist Review),1951年1月19日,第20页。
(44) 正如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所说,在一个文件中“一个国家给第二个国家庄严地许诺了第三个国家的国土”,《诺言和履行》(Promise and Fulfilment),伦敦,麦克米伦,1949年版,第4页。
(45) “如果没有那桩关于民族家园的荒唐事,巴勒斯坦本来会是一个易于统治而又宜于居住的国家。对犹太人来说,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救世主来临的灵感。对英国当局来说,它却只是一件糟透的讨厌东西。”同上书,第10页。
(46) 参阅同上书,第20页。
(47) 文本见钱姆·韦茨曼:《考验与错误》(Chaim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纽约,哈珀兄弟,1949年版,第203页。
(48) 凯斯特勒,前引文。
(49) 参阅韦茨曼,前引书,第280页。其中谈到寇松拒绝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提案,该提案主张前言中关于委任统治权的一段应以“承认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历史权利……”等字样开始。
(50) “犹太人……也许倾向于轻视在智力上不如自己造诣深的阿拉伯人,但他们并不憎恨阿拉伯人。如果阿拉伯人出版一些学术期刊、开办几个美术馆和组织一个交响乐团,犹太人肯定会爱上这些东西。”《犹太复国主义评论》,耶路撒冷通讯员,1947年10月10日,第5页;参阅罗纳德·斯托尔斯爵士:《方向》(Sir Ronald Storrs: Orientations),伦敦,尼科尔森和沃森,1943年版,第360—369页。
(51) 拉姆赛·麦克唐纳首相于1930年4月3日在国会的讲话(下院辩论,第5辑,第237卷,第1466栏)。犹太复国主义者拒绝了给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以同等权利这个想法,认为这是“反对全体犹太人民的”,因为“从语气的含意来看,是乘机排除了巴勒斯坦同犹太人世界之间的关系”。韦茨曼:前引书,第325页。
(52) 在1932年12月31日到1935年12月31日之间,犹太人人口据估计增加了40.8%,其中76.2%是由于移民入境,只有8.6%是由于自然增长。巴勒斯坦政府统计部:《人口动态统计表,1922—1925年》(Vital Statistics,1922—1925),耶路撒冷,政府印刷局,1947年版,第1页和第84页。
(53) 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毗连的阿拉伯国家的“干涉”提出的抗议,是同他们声称巴勒斯坦是“全体犹太人”的利害之所系的论点突出地自相矛盾的。见韦茨曼:前引文。
(54) 见《概览,1938年》,i.414—479。
(55) 1939年任商务大臣后任殖民大臣的奥利弗·斯坦利,对人们曾经怀有的希望的态度模棱两可,这种希望以为由于发表了白皮书的结果,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怒气可能会逐渐消除,和解或许会开始”;可将他在1946年7月31日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26卷,第981栏)同他在1947年2月25日的发言(同上,第433卷,第1924栏)作一对照。
(56) 1945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政治宣言,第4段(《犹太复国主义评论》,1945年8月17日,第6页);参阅韦茨曼,前引书,第403页,第410页。
两位工党议员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和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觉得对他们的命题《一次巴勒斯坦慕尼黑?》〔(A Palestine Munich?),伦敦,戈兰奇,1946年版,第26页〕来说,有必要描绘一下伊拉克1941年拉希德·阿里的亲轴心国暴动。要不是白皮书对温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起了安抚作用(据说“不具有战略意义”),那次暴动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可能会有大得多的支持;但克罗斯曼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判断完全是自相矛盾的。请对比:“在1939年,我们就非得拿出那份白皮书不可,因为阿拉伯世界可能会在战争年代加入轴心国的……这样做,很可能是出于一种地地道道的战略需要,虽然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需要”,但又说,“这是一项我曾希望每一个正派的英国人到今天都会由衷感到羞耻的英国政策。”1947年2月25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33卷,第1984栏;《新政治家和民族》(New Statesman & Nation),1951年3月10日,第274页。
(57) 参阅卡特鲁将军在不同情况下说的话:“如果盟国不愿败于地中海之役,也就是整个这场战争的话……”卡特鲁:《地中海作战的时候》(Catroux: Dans la bataille de Méditerranée),巴黎,朱利亚尔,1949年版,第116页。1941年5月丘吉尔驳斥了认为保卫新加坡比保卫埃及还要重要的意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iii.375,379。
(58) 见《概览,1938年》,i.277,306。佛朗哥举行马德里入城式是在5月19日。
(59) 加里亚佐·齐亚诺:《日记,1939年(—1943年)》,两卷集,第4版(米兰,里苏利,1947年版),1939年2月22日。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编的英译本一卷集《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于1947年出版,伦敦,海涅曼公司。以下简称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
(60) 虽然大西班牙君主国由于1702—1713年的全面战争而被瓜分,但西班牙在整个18世纪在波旁王朝的统治下仍然起着一个大国的作用。它的大国地位之丧失不妨说始于在(1793—1795年)第一次反法大同盟战争中被法兰西共和国打败和使它沦为法国卫星国的1796年圣·伊乐德丰索条约;它后来在维也纳会议上未能获准承认其为一个大国。见C·K·韦伯斯特:《维也纳会议,1814—1815年》(C.K.Webster: The Congress of Vienna, 1814—1815),伦敦,贝尔,1934年版,第61页,第75页。
(61) 安赫尔·甘尼维特:《西班牙思想体系》〔(Angel Ganivet: Idearium Español),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埃斯帕萨·卡尔佩,1943年版〕,英译本为《西班牙:一种解释》〔(Spain: an Interpretation),伦敦,艾尔和斯波蒂斯伍德,1946年版〕,第87—90页:“在欧洲所有国家中,西班牙是仅次于意大利的一个对英国海军能维持长时期优势最感兴趣的国家……毫无疑问,看来似乎是荒谬的,我们自己的利益竟同一个我们有真正理由仇视它的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但是承认和接受这种异乎寻常的现象有时在于最高的政治智慧。”参阅E·艾利森·皮尔斯:《西班牙黯然失色,1937—1943年》(E.Allison Peers: Spain in Eclipse,1937—1943),伦敦,梅休因,1943年版,第165—166页。
(62) 1938年12月31日对曼努埃尔·阿斯纳尔的谈话。《领袖言论》(Palabras del Candilo),巴塞罗那,信仰出版社,由长枪党全国代表团负责出版,1939年版,第312页。参阅卡米洛·巴西亚·特雷列斯:《西班牙国际政策要点》(Camilo Bercia Trelles: Puntos Cardinals de la Politica internacional española),巴塞罗那,信仰出版社,1939年版,第474—476页。
(63) 长枪党二十六点纲领的官方译文,转载于阿瑟·F·洛夫德:《世界大战在西班牙》(Arthur F.Loveday: World War in Spain),伦敦,默里,1939年版,附录iii,第184页。另有一种译文见艾伦·蔡斯:《长枪党:轴心国在美洲的秘密军队》(Allan Chase: Falange: the Axis Secret Army in Americas),纽约,普特南,1943年版,第14页。
(64) 见皮尔斯:《西班牙黯然失色》,第98—100页。
(65)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6月5日。佛朗哥在1940年6月给希特勒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明他的领土要求是:取得直布罗陀、法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地区,扩大里奥德奥罗和西属几内亚。见德国驻马德里大使1940年8月8日备忘录,载《西班牙政府和轴心国:文件》(The Spanish Government and the Axis: Documents),国务院出版物,第2483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6年版,第3页(该文件集以下简称《西班牙政府》)。佛朗哥就在这同一个月开始占领丹吉尔。
西班牙政府为收复直布罗陀所作的最后一次认真的努力,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进行的1779—1783年围城大战。1939年,在英国人看来,如果海上控制不能防止直布罗陀的丢失,还可以随时占领加那利群岛作为替换。从加那利群岛可以继续控制大西洋航线和地中海的西边入口。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ii.460,552,563。
(66) 这个词是一位长枪党主义的先驱、政治哲学家拉米罗·德马埃斯图在他的《捍卫西班牙文明第一主义》〔(Ramiro de Maeztu: Defensa de la Hispanidad),马德里,法克斯,1934年版〕一书中创造的。“伊比利亚—美洲”(Ibero-American)、“西班牙—美洲”(Hispano-American)和“泛西班牙”(Pan-Hispanic)这些词是多半可以互相通用的,好处就在叫你弄不清词义。“西班牙—美洲”这个词前后两半都不明确。一方面,“西班牙文明”(Hispanity)包括葡萄牙和巴西吗?按照马埃斯图的说法,它是包括的(同上书,第19—20页),而且在长枪党的宣传中常常是这么用的。“伊比利亚—美洲”就没有这种模棱两可的弊病。另一方面,“西班牙美洲”(Hispanic America)是为了方便起见把菲律宾也包括进去的标准用法(参阅特雷·列斯,前引书,第165—166页,第184—185页)。
(67) 见拉米罗·莱德斯马·拉莫斯:《对青年组织的讲话》(Ramiro Ledesma Ramos: Discurso a las javentudes de España),马德里,征服出版社,1935年版,第72页。
(68) 洛夫德:《世界大战在西班牙》,附录iii,第184页。
(69) 关于海外长枪党的情况,发表过的文章只有蔡斯的《长枪党》,但文章的可信性颇成问题。
(70)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6月5日。
(71) 见1939年7月19日齐亚诺同佛朗哥在圣塞瓦斯蒂安的谈话〔加里亚佐·齐亚诺:《欧洲面临灾难》(Galeazzo Ciano: L'europa verso la catastrofe),米兰,蒙戴多里,1948年版,第440页〕;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主编并由斯图尔特·伍德翻译成英文的《齐亚诺外交文件》(Ciano's Diplomatic Papers),伦敦,奥德姆斯出版社,1948年版,第291页。该著作及英译本以下简称“齐亚诺:《欧洲》”和“英译本”。1939年8月12日齐亚诺在上萨尔斯堡以西班牙需要恢复元气为理由,徒劳地企图劝阻希特勒不要立即发动战争。见希特勒同齐亚诺谈话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ix.49(1871—PS);译文载《文件,1939—1946年》,i.178;参阅《阴谋与侵略》,iv.515,viii.523。
(72) 齐亚诺同佛朗哥在圣塞瓦斯蒂安的谈话,1939年7月19日。齐亚诺:《欧洲》,第443页;英译本,第293页。
(73) 关于在西班牙内战结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各种情景,见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西班牙》(Salvador de Madariaga: Spain),第2版(伦敦,凯普,1942年版),第421—429页;皮尔斯:《西班牙黯然失色》,第123—137页;赫伯特·菲斯:《西班牙史话》(Herbert Feis: The Spanish Story),纽约,诺夫,1948年版,第1章。
(74) 见《概览,1937年》,ii.202。这里有着不同之处:葡萄牙有着独立于世界的光荣历史并不亚于西班牙,而苏格兰只是由于同英格兰结成联盟的结果,才对西方文明充分发挥了它的影响。
(75) 见埃德加·普雷斯蒂奇:“英葡联盟”(Edgar Prestage:“The Anglo-Portuguese Alliance”),载《皇家历史协会学报》(1934年)〔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34)〕,xvii.69以后。“葡萄牙要么必须成为伊比利亚整体中自治的一翼,要么就成为英帝国的经过乔装打扮的可是并不会有更多自治权的一翼”(马达里亚加:《西班牙》,第195页);应当注意,这是一种西班牙人的说法。
(76) 1815年维也纳会议条约第105条。爱德华·赫茨莱特爵士:《1814—1891年欧洲条约地图》〔(Sir Edward Hertslet: The Map of Europe by Treaty 1814—1891),第1—3卷,伦敦,巴特沃斯,1875年版,以及第4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891年版〕,i.268。又见H·V·利弗莫尔:《葡萄牙史》(H.V.Livermore: A History of Portugal),剑桥大学出版社,1947年版,第390—391页,第402页。
(77) 参阅格兰维尔1873年2月19日同那位西班牙部长的谈话。《英国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文件,1898—1914年》(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1898—1914),G·P·古奇和哈罗德·坦珀利编,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26—1938年版,第1卷,第69号(附件1)。以下简称古奇和坦珀利。
(78) 不妨注意下列日期:葡萄牙:1910年,推翻君主制度;1926年,军人革命建立了卡尔莫纳将军的独裁政权;1928年,萨拉查被任命为财政部长;1932年,萨拉查当上总理;1933年,制订新的宪法。西班牙:1923年,普里莫·德里维拉成为独裁者;1929年,普里莫垮台;1931年,阿方索十三世出逃,建立共和国;1933年,大选,政局向右摆;1936年,内战爆发。见《概览,1937年》,ii.10—23。
(79) 《概览,1937年》,ii.208;《概览,1938年》,i.360注②。
(80) 参阅拉莫斯:《向青年组织的讲话》,第72页。
(81) 见《概览,1934年》,第328页。
(82) 《概览,1938年》,i.360—361;皮尔斯:《西班牙黯然失色》,第144—145页。
(83) 关于法国人鉴于西班牙可能同轴心国结盟而在战略上感到的焦虑,见《概览,1937年》,ii.148—150,188—189。
(84) 齐亚诺:《欧洲》,第440页;英译本,第291页。
(85) “佛朗哥和他的顾问们知道,这个国家所处的地位还不能参战。他们同时又害怕德国,对意大利则非常友好”,1940年6月11日塞缪尔·霍尔爵士致哈利法克斯勋爵函〔坦普尔伍德勋爵:《负有特殊使命的外交官》(Lord Templewood: Ambassador on Special Mission),伦敦,科林斯,1946年版,第34页〕。
(86) 见《概览,1937年》,ii.218—221。
(87)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6月9日。
(88) 在1937年9月墨索里尼访问慕尼黑时,德国人宣称在西班牙内战上花的钱完全同意大利人一样多〔(1937年9月)墨索里尼和比洛·施万特第三次会见记录,载《德国外交部秘密文件集》(Documents Secret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Allemagne),有马德琳和米歇尔·埃里斯托夫译自俄文版的法译本,以下简称《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巴黎,保罗·杜邦,1947年版,第3卷(西班牙),第3号,第22—23页〕。一个月以后,1937年11月6日,墨索里尼在罗马同里宾特洛甫谈话时说,意大利在西班牙花了45亿里拉,而根据戈林的说法,德国花了大约35亿(齐亚诺:《欧洲》,第221页;英译本,第144页)。有关西班牙最终欠意大利和德国的战争债务的总的估计数字,见托马斯·J·汉密尔顿:《绥靖的产儿》(Thomas J.Hamilton: Appeasement's Child),纽约,诺夫,1943年版,第140页;查尔斯·福尔茨:《西班牙的化装舞会》(Charles Foltz: The Masquerade in Spain),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48年版,第140页。
(89) 1937年11月10日霍斯巴赫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411—412(386—PS);《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36—37;《文件,1939—1946年》,i.23;参阅《阴谋与侵略》,iii.303。
(90) 见《概览,1937年》,ii.193—194;菲斯:《西班牙史话》,第22页注。
(91) 德国空军总参谋部情报局1938年8月25日关于“扩大的绿色行动”的报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390(375—PS);《阴谋与侵略》,iii.287〕。1939年5月,里宾特洛甫认为,西班牙人在比利牛斯山一带牵制几个法国师是有用处的(见1939年5月6—7日齐亚诺和里宾特洛甫在米兰的谈话,载齐亚诺:《欧洲》,第430—431页;英译本,第285页;《文件,1939—1946年》,i.166)。
(92) 《概览,1938年》,i.360。
(93)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19页,第22页。该约直到1939年11月29日才获批准。《西班牙政府》中没有公布这一条约的原因不详。
(94) “关于西班牙,德国根据在西班牙内战中获得的经验,深知如不达成十分具体详细的协议,要同西班牙人办事取得进展是不可能的……总之,他(希特勒)不相信西班牙对于‘给’和‘取’有同样热烈的意愿……在经济上,德国给了西班牙好多亿。他(元首)采取的立场是,战争期间不妨把这笔债务的偿还问题搁一搁,但在佛朗哥胜利后,总还得再提出来。每当德国人要求偿还西班牙在内战期间欠下的这笔4亿债务时,西班牙人对此总说成是把经济上的考虑同理想上的考虑纠缠在一起是不明智的,所以西班牙人在德国人看来,简直就像犹太人,犹太人是想把人类最神圣的东西也拿来做买卖的。”见1940年9月28日希特勒同齐亚诺会见记录,载《西班牙政府》,第17页,第18—19页。
(95) 参阅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在向他的指挥官们讲话中谈到西班牙的部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i.339(798—PS);英译文见《文件,1939—1946年》,i.444;参阅《阴谋与侵略》,iii.582。
(96) 条约文本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3卷(西班牙),第1号;《文件,1939—1946年》,i.5—7。
(97) 1937年11月6日墨索里尼同里宾特洛甫在罗马的谈话(齐亚诺:《欧洲》,第222页;英译本,第144—145页)。但结果意大利和德国的部队于1939年5月和6月全部自西班牙领土撤走,不过意大利人留下了他们的大部分重型武器。《概览,1938年》,i.356—360。
(98)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6月14日;参阅莱昂纳多·西蒙尼(笔名):《意大利驻柏林大使馆,1939—1943年》(Leonardo Simoni, pseud: Berlino, Ambasciata d'Italia 1939—1943),罗马,米格里亚雷西,1946年版,第140页,第142页。见下文,原著第191—193页。
(99) 同上书,1939年1月8日。苏涅尔于6月访问意大利时,双方同意:“这个联盟事实上我们已在考虑中;就目前来说,签订草约还不够成熟”,同上书,1939年6月5日。
(100)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月27日和2月8日。齐亚诺考虑把他自己在1939年夏天对西班牙的访问放在戈林的访问之前进行,他认为这一点对意大利的威望来说是重要的。同上书,1939年4月21日。
(101) 同上书,1939年3月3日。
(102) 在1939年6月苏涅尔访问意大利期间,齐亚诺进行干预,缓和了苏涅尔同德国驻罗马大使的关系。同上书,1939年6月10日和14日。
(103) 同上书,1939年1月8日。从墨索里尼一再劝说佛朗哥不要恢复君主政体一事可以看到,他是想影响西班牙事务的。同上书,1939年3月5日、3月11日、6月5日;齐亚诺:《欧洲》,第442页;英译本,第292页。
(104)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月26日和2月22日。齐亚诺于1939年7月19日在圣塞瓦斯蒂安同佛朗哥会晤后意兴盎然地写道:佛朗哥完全受墨索里尼支配,盼望得到墨索里尼的指导和指示,要墨索里尼访问马德里,“由此一定能把西班牙团结过来与罗马帝国共命运”(齐亚诺:《欧洲》,第446页;英译本,第295页)。但意大利人所要的是一项条约,佛朗哥却没有给。
(105) 人们会注意到,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君主于1494年缔结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同意在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处划定为从北极到南极的分界线,无意中却同20世纪的地缘政治概念相吻合(见上文,原著第12—14页)。这条线承认南大西洋盆地是一个统一体,一个在6年以后得到了杰出证明的统一体。1500年葡萄牙人卡布拉尔在前往好望角途中偶然发现了巴西。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修改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493年5月4日的训令。教皇训令在亚速尔群岛以西100里格处沿大西洋往下划过一条分界线,那条分界线同被麦卡托投影图法歪曲了的世界地图比较一致。J·杜蒙:《世界国际法法典》(J.Dumont: Corps universal diplomatique du Droit des gens),阿姆斯特丹,1726年版,第3卷,第2编,第302—303页;路德维格·帕斯特:《教皇史》(Ludwig Pastor: The History of the Popes),F·I·安特罗伯斯编的英译本第6卷(伦敦,基根·保罗,1898年版),第160—161页。
(106) 在1939年,西班牙帝国包括行政设置上属于西班牙一部分的加那利群岛,以及沿非洲西海岸由北向南的下列领土:(1)西属北摩洛哥区; (2)西属西南摩洛哥区,或称伊夫尼; (3)里奥德奥罗和阿德阿尔(有时总称为西属撒哈拉)的殖民地、保护地和被占领的领土; (4)西属几内亚,包括大陆部分和岛屿,其首都在费尔南多波岛。西班牙的这些非洲属地,除1778年由葡萄牙割让给西班牙的费尔南多波岛和安诺本岛,以及从东边的梅利利亚(1597年被占领)沿摩洛哥海岸向西到休达的一连串各式各样的要塞外,其余都是在19世纪下半叶获得的。休达原属葡萄牙,但自葡萄牙于1668年恢复独立以后,该地为西班牙所保有。见《西班牙和意大利属地:独立国家》(Spanish and Italian Possessions:Independent States),英国外交部史料处发行的“和平手册”第20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20年版),第122—125号。根据1898年巴黎条约,美国迫使西班牙放弃对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的主权,原来的西班牙帝国终于被消灭了。目前这个羸弱的“第二西班牙帝国”在1939年的世界殖民帝国中,面积居第八位,人口居第九位。见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殖民地问题》(The Colonial Problem),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37年版,第9页,表i。
(107) 在1939年,葡萄牙帝国包括在行政设置上属于葡萄牙一部分的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岛,以及沿瓦斯科·达·伽马及其前辈和后继者所开辟的外洋航线的下列属地:(1)在南大西洋:1.佛得角群岛,2.葡属几内亚,3.几内亚湾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4.安哥拉或葡属西非; (2)在印度洋:1.莫桑比克或葡属非洲,2.葡属印度,由果阿、达曼和第乌岛的若干分散的领土组成; (3)在远印度:1.中国的澳门,位于珠江口,是香港的前驱,2.葡属帝汶,即马来群岛的帝汶岛的东部。所有这些属地都是从16世纪起取得的,但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在19世纪后半叶瓜分非洲时扩大了好多;葡萄牙帝国晚近没有损失任何领土,在印度洋,印度大陆上的塔纳、巴塞因和乔尔是在1737年和1740年之间被马拉塔人占领的,而在南大西洋,巴西的独立是在1822年。见《葡萄牙属地》(Portuguese Possessions),英国外交部史料处发行的“和平手册”第19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20年版)和《波斯湾:法国和葡萄牙属地》(Persian Gulf: French and Portuguese Possessions),同一丛书的第13卷,第79—81号。葡萄牙帝国于1939年在世界殖民帝国中,面积居第五位,人口居第七位。见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殖民地问题》,前引文。
(108) 见埃德加·普雷斯蒂奇:“英葡联盟”,载《皇家历史协会学报》(1934年),xvii.95—97。
(109) 见R·I·洛弗尔:《争夺南非的斗争,1875—1899年:对经济帝国主义的研究》(R.I.Lovell: The Struggle for South Africa, 1875—1899: A Study in Economic Imperialism),纽约,麦克米伦,1934年版,第216—218页。
(110) 古奇和坦珀利,第1卷,第90—92号。
(111) 同上书,第118号,以及编者注(第93—95页)。又见第8卷,第62章,以及哈罗德·坦珀利和莉莲·M·彭森(编):《从庇特(1792年)到索尔兹伯里(1902年)的英国政策的基础》〔Harold Temperly and Lillian M.Penson (edd.): Foundations of British Policy from Pitt (1792)to Salisbury (1902)〕,剑桥大学出版社,1938年版,第512—516页。
(112) 古奇和坦珀利,第10卷,第2编,第95章。阿瑟·尼科尔森爵士把这些谈判描写成“在我整个外交经历中所看到的最令人齿冷心疑的勾当”。哈罗德·尼科尔森:《阿瑟·尼科尔森爵士(从男爵),卡诺克勋爵(第一)》(Horold Nicolson: Sir Authur Nicolson, Bart., First Lord Carnock),伦敦,康斯特布尔,1930年版,第393页。参阅《概览,1929年》,第277—278页;《概览,1937年》,ii.203—204。
(113) 见H·W·V·坦珀利编:《巴黎和会史》(A Histo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of Paris, ed.H.W.V.Temperley),下文简称《和会史》,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20年版,ii.243—244。
(114) 见《概览,1937年》,ii.208,241—242,244—245。
(115) 葡萄牙并未漠视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的内在意义。见《概览,1935年》,ii.80,86,190。
(116) 关于英国向德国建议在刚果盆地条约规定的地区建立一新殖民地政权,见下文,原著第164—165页。
(117) 齐亚诺记苏涅尔的话:《日记(1939—1943年)》,1939年6月5日。“尽管这事可能难办,他打算朝这个方面去努力,并要求我们合作。”
(118) 《概览,1938年》,i.360注②。
(119) 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大公国。
(120) 在地理学上说,斯堪的纳维亚一词指的是丹麦、瑞典和挪威;这里也用来包括冰岛,因为冰岛通过政治纽带和丹麦联合在一起,但不包括芬兰,它将列入东欧国家。见下文,原著第206页以下。
(121) 值得政治科学家注意的是,它们都是君主立宪国家,只有瑞士是联邦共和国。丹麦和冰岛则共有一个君主。
(122) 就“大国”一词用之于论及15和16世纪的初步国际体系而言,瑞士联邦自在1474—1477年的战争中击败勃艮第起,一直到1515年的马里尼安诺之役被法国人击败,它也曾是一个扩张主义的大国。联合省(荷兰——译者)从它们于1609年结束的反对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中取得胜利之时起,一直到1702—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被它的过分强大的伙伴英国拖得筋疲力尽而黯然失色为止,也一直是一个大国,虽然在这一时期内由于1672年法国的入侵,它的力量一直在衰退。丹麦从它于1535年吕贝克大捷——这场战争摧毁了汉萨同盟的制海权,让丹麦控制了波罗的海——直到1626年卢特尔之役它败于天主教联盟,以及继而在1629年签订吕贝克和约退出了30年战争为止,也一直是一个大国。瑞典从它于1630年插手30年战争直到1699—1721年北方大战中被俄国打败为止,也曾经是一个大国。
(123) 西欧的四个小人国安道尔、摩纳哥、圣马力诺和列支敦士登是如此之小,以致它们的主权都很难说到底是有是无,通常也就不把这些国家列为国际关系的讨论题目。它们也是不健全的缓冲国,正由于这一特性,它们才得存在。安道尔共和国是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缓冲国,此时已成为它们的共同保护国。〔L·奥本海姆:《国际法》(L.Oppenheim:International Law),第6版,H·劳特帕特编(伦敦,朗曼,格林,1947年版),i.176,232〕。摩纳哥公国原先是法国、萨瓦和热那亚之间的缓冲国;自从1860年意大利把萨瓦和尼斯割让给了法国以后,它一直是法国领土之内的一块飞地,也许是因同法国紧密结盟才有独立国的地位吧(同上书,i.175注④,232)。圣马力诺共和国原先是公爵领地乌尔比诺和贵族领土里米尼之间的一个缓冲国,后来它成了一块保存下来的飞地,先是在教会国家之内,后来又在意大利王国之内,当时它是意大利的保护国〔见W·米勒:“圣马力诺的民主”,《历史》(W.Miller:“Democracy at San Marino”,History),1922年4月号,第1—16页;奥本海姆,前引书,i.176,232〕。列支敦士登公国原先是奥地利和瑞士之间的缓冲国;它也许称得上是一个有充分主权的国家,但在1921年却未获准加入国联,显然是因为它太小,1923年它同瑞士结成关税同盟,并委托瑞士在国外代表它(奥本海姆,前引书,i.232注②,169注④)。第五个同样微型的、古色古香的西欧国家是梵蒂冈城,但它起源不同,性质亦不同(见《概览,1929年》,第453—454页)。
(124) 见汤因比:《研究》,i.37—39;iii.349注②。比利时得到保证的中立和瑞士得到保证的中立,同样都会使人本能地想起它们是9世纪时称作罗退尔王国的“残余”或“复活”——很难说应该用哪一个说法好。E·A·弗里曼:《欧洲的历史地理》(E.A.Freema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J·B·伯里编的第3版(伦敦,朗曼,格林,1912年版),第304页;参阅第290—292页。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莱茵兰非军事化,便是此种欧洲政治均势持续性特征的最近表现(1939年)。
(125) 勃艮第之成为欧洲强国是通过1384年同佛兰德的王朝联盟。1419年订立的英国—勃艮第联盟使它能在百年战争的最后阶段掌握了英法之间的天平,从此一直到1476年在格兰德逊和莫拉特被瑞士打败和1477年又在南希被同瑞士结成联盟的洛林公爵打败为止,这一段时期是勃艮第国家全盛时期。瑞士国家的全盛时期是它从战胜勃艮第起一直到1515年在马里尼亚诺被法国人打败为止。
(126) 见埃德加·邦儒尔:《瑞士中立史》(Edgar Bonjour: Geschichte der Schweizerischen Neutratität),巴塞尔,黑尔宾和利希滕哈恩,1946年版;M·霍廷格节译的英文本:《瑞士的中立:它的历史和含义》(M.Hottinger: Swiss Neutrality: Its History and Meaning),伦敦,埃伦和昂温,1946年版。
(127) 韦伯斯特:《维也纳会议》(Webster: Congress of Vienna),第134页;1815年11月20日法令〔赫茨利特:《欧洲条约地图》(Hertslet: Map of Europe by Treaty),i.371—372〕。
(128) 第435条。见《概览,1925年》,ii.217。
(129) 国联盟约第7条。
(130) 阿诺德·汤因比:《和会后的世界》(A.Toynbee: The World after the Peace Conference),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25年版,第37—38页;参阅《概览,1935年》,ii.87。
(131) 瑞士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成长是和它作为一个政治单位的成长相一致的。瑞士的国家地位可以从1389年算起,那时哈布斯堡王朝被迫同瑞士联邦以平等地位签订了一项条约,放弃了对瑞士联邦每一个成员的封建宗主权;不过瑞士脱离该帝国而独立事实上是在1499年才实现的,法律上则在1648年。比利时作为一个政治单位的存在始于1579年,当时阿拉斯联盟把那些仍然忠于西班牙的尼德兰省份联合了起来,而与之对立的继续争取独立的那些省份则联合而成为乌特勒支联盟,但过了250年以后,比利时才于1831年成为一个国家。
(132) 赫茨利特:《欧洲条约地图》,ii.153和183—185,条约第7条或各该附件。见《概览,1920—1923年》,第65页。
(133) 见《概览,1920—1923年》,第65—67页;《和会史》,ii.189—190;《概览,1925年》,ii.170。
(134) 《和会史》,ii.190—191。
(135) 汤因比:《和会后的世界》,第37页。
(136) 《概览,1920—1923年》,第71页;《概览,1936年》,第353页。
(137) 洛迦诺条约第1条(见《概览,1925年》,ii.440—442);参阅同上书,第56—57页。
(138) 1441年兼并卢森堡标志着勃艮第力量达到了顶峰。先前卢森堡是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公国,在1308年和1437年之间曾经给波希米亚的一个王朝立了四个皇帝,并几乎在哈布斯堡王朝之前成为该帝国的王朝。卢森堡是在1354年由郡升为公国的。
(139) 赫茨利特:《欧洲条约地图》,iii.1801—1805。见C·R·M·F·克拉特威尔:《现代世界的和平变化史》(C.R.M.F.Cruttwell: A History of Peaceful Change in the Modern World,以下简称克拉特威尔:《和平变化》),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37年版,第188—190页。1890年,根据1783年的拿骚继承协定和维也纳会议条约第71条,把王位由统治着荷兰的拿骚家族的鄂图分支传给了以拿骚魏尔堡公爵为代表的瓦尔拉姆分支。见赫茨利特,前引书,i.253和iii.2013—2015。
(140) “到了19世纪末叶,有5条铁路和9条公路干线从首都卢森堡通向法国、德国和比利时边境的主要战略据点。在法国方面,它有摩泽尔防线的保卫,并有沿摩泽尔河顺流而进的便利。在1914年,占有卢森堡乃是德国史里芬计划的主要措置:卢森堡是德军攻防两翼之间必不可少的链环,打开通向斯特内隘口的道路就会从北方威胁整个默兹。”克拉特威尔:《和平变化》,第184—185页。参阅《和会史》,ii.188。
(141) 见《和会史》,ii.184—189。
(142) 第40条:《概览,1920—1923年》,第68—71页。关于卢森堡的特殊地位,在政治方面拥有主权而在经济方面没有主权,参阅《概览,1934年》,第404页注。
(143) 奥本海姆:《国际法》,i.224注③。
(144) 《概览,1935年》,ii.231—232。
(145) 关于保皇党运动在1936年最猖獗的情况,见《概览,1936年》,第36—37页。
(146) 见同上书,第351—360页。1920年同法国缔结的军事协定在协约国对莱茵兰的占领于1929年结束时早已废弃了。
(147) 见《概览,1937年》,i.346—368。
(148) 见《概览,1936年》,第354页注②。
(149) 《概览,1938年》,i.152;邦儒尔:《瑞士的中立》,第118页。
(150) 1939年对希特勒的计划看来并没有规定要入侵瑞士,虽然他说过瑞士会顽强地保卫它的中立,但他在谈到低地国家时也说过这种话的。见1939年8月12日希特勒同齐亚诺会谈记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ix.42(1871—PS);《阴谋与侵略》,iv.509〕;又见,希特勒于1939年8月22日对他的总司令们的讲话〔《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i.342(798—PS);《阴谋与侵略》,iii.585〕。参阅1939年8月31日关于进行战争的第1号命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v.457(126—C);《阴谋与侵略》,vi.935〕。这三个文本又见《文件,1939—1946年》,i.172,443和499。
(151) 有关同时期的对德国在这方面的利益所作的估计,见《概览,1937年》,i.350。
(152) 有关卡尔玛联合的历史意义,见汤因比:《研究》,ii.175—176。冰岛从930年到1263年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1263年斯堪的纳维亚殖民地开拓者宣誓效忠挪威国王。
(153) 见克拉特威尔:《和平变化》,第91—95页;《概览,1920—1923年》,第232—233页。
(154) 冰岛在1918年取得独立的时候发表了永久中立的宣言,因此从未参加国联;但是该项宣言是单方面发表的,在国际法上不具有法律效力(奥本海姆:《国际法》,i.218注①;克拉特威尔:《和平变化》,第184页)。在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曾保证瑞典和挪威的领土完整,1907年,英、德、法、俄曾保证新独立的挪威的领土完整(古奇和坦珀利,第8卷,第63章)。但这些保证并没有强加中立于人,而且挪威已在1922年通告废除1907年的条约(《概览,1920—1923年》,第231—232页)。
(155) 自1815年以来,这些国家卷入欧洲战争的只有一个国家:丹麦,它参加了1864年反对普奥的战争,结果丧失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但荷兰像19世纪时的英国那样,避免在欧洲进行冒险,却通过一系列殖民战争获得了补偿,其中最重要的是在1873年到1909年旷日持久的亚齐战争中征服了北苏门答腊。
(156) 《和会史》里没有谈到斯匹次卑尔根问题的解决。有关挪威人向和会陈说的理由,见戴维·亨特·米勒:《我在巴黎和会上的日记》(David Hunter Miller: My Diary at the Conference of Paris),私人印刷,1924—1926年版,xvii.479—483;参阅詹姆斯·T·肖特韦尔:《在巴黎和会上》(James T.Shotwell: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纽约,麦克米伦,1937年版,第181页注。挪威对斯匹次卑尔根的主权是通过1920年的一项条约得到承认的(见《概览,1920—1923年》,第230页;《概览,1924年》,第258页,第462页;《概览,1925年》,ii.226)。苏联在1924年承认挪威对斯匹次卑尔根的主权,并于1935年自愿加入1920年条约。见《北欧人》(Norseman),1947年3—4月号合刊,第83—90页。
(157) 见《和会史》,第2卷,第4章,第1编。
(158) 见《概览,1920—1923年》,第234—238页。
(159) 《概览,1920—1923年》,第229—230页。芬兰于1924年在外交上加入斯堪的纳维亚集团(《概览,1924年》,第461页)。进一步的情况见下文,原著第246页。
(160) 见汤因比:《和会后的世界》,第37页;《概览,1920—1923年》,第231页;《概览,1935年》,ii.79—81。
(161) 见《概览,1924年》,第73—77页;《概览,1929年》,第32页注。
(162) 见《概览,1931年》,第154页注②;《概览,1932年》,第38页。1932年芬兰加入了这6个国家的合作。
(163) 见《概览,1937年》,i.99。
(164) 见《概览,1935年》,ii.472—474。
(165) 见《概览,1937年》,i.96—99。
(166) 见《概览,1936年》,第121页,其中提供了进一步的参考。
(167) 见《概览,1937年》,i.349注。
(168) 见《概览,1938年》,i.145—146。
(169) 见《概览,1937年》,i.353。
(170) 这话是毛奇在1912年12月一个备忘录中说的;见C·R·M·F·克拉特威尔:《大战史,1914—1918年》(A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1914—1918),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34年版,第8页。
(171) 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v.744(175—C);英译文载《文件,1939—1946年》,i.13;参阅《阴谋与侵略》,vi.1011;参阅1938年6月2日德国空军计划研究报告,载《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viii.415(150—R);《阴谋与侵略》,viii.270。
(172) 德国空军总参谋部情报局1938年8月25日关于“扩大的绿色行动”的报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391(375—PS);《阴谋与侵略》,iii.287—288。
(173) 1939年5月23日会议记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vii.550(079—L);英译文载《文件,1939—1946年》,i.274;参阅《阴谋与侵略》,vii.850。希特勒在1939年8月12日同齐亚诺会谈时出于策略上的目的含蓄地否认这一点,《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ix.41—42(1871—PS);英译文载《文件,1939—1946年》,i.172—173;参阅《阴谋与侵略》,iv.508—509;以及彼得·德门德尔松:《纽伦堡文件》(Peter de Mendelssohn: The Nuremberg Documents),伦敦,埃伦和昂温,1946年版,第115页。
(174) 见《概览,1933年》,第171—173页;《概览,1936年》,第43页和注。
(175) 见《概览,1937年》,i.376。
(176) 见巴塞洛缪·兰德希尔编:《荷兰》(Bartholomew Landheer, ed.:The Netherlands),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43年版,第129—130页。米塞的运动,像德格雷尔的运动一样,在1936年其势力也盛极一时。
(177) 见1940年6月15日罗森贝格关于在挪威采取行动的政治准备情况的报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26—27(004—PS);《阴谋与侵略》,iii.20。
(178) 原文是Trondhjem,即Trondheim(特隆赫姆)的旧称。——译者
(179) 见1939年10月9日邓尼茨关于挪威基地的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v.159—161(005—C);《阴谋与侵略》,vi.815—816〕和1943年11月7日约德尔在慕尼黑的演讲〔《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vii.636(172—L);《阴谋与侵略》,vii.924—925〕。1940年希特勒之占领丹麦和挪威,同拿破仑1807年通过枫丹白露条约迫使丹麦—挪威王国加入大陆制度有着相似之处;但拿破仑的主要动机是经济的,希特勒的主要动机则是战略的。
(180) 见1939年8月12日希特勒同齐亚诺会谈记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ix.42(1871—PS);英译文见《文件,1936—1946年》,i.173;参阅《阴谋与侵略》,iv.509〕和1940年6月15日罗森贝格关于在挪威采取行动的政治准备情况的报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28—29(004—PS);《阴谋与侵略》,iii.22。希特勒在1939年12月16日和18日对吉斯林说,他宁愿斯堪的纳维亚中立〕。参阅海军作战日记摘录,1939年10月3日挪威基地调查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v.422—425(122—C);《阴谋与侵略》,vi.928〕和前一脚注提到的资料来源。
(181) 见《概览,1936年》,第533页。瑞典对德国的重要性不在于战略地位,而在于它是一个铁矿和镍矿的来源,因而保护这个来源后来便成了占领丹麦和挪威的缘由之一;见1940年3月1日“威悉演习方案”指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v,729—732(174—C);《阴谋与侵略》,vi.1003—1005〕和1943年11月7日约德尔在慕尼黑的演讲〔《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vii.366(172—L);《阴谋与侵略》,vii.924〕。
(182) 有关冰岛地位的这一剧烈变化,见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国际新闻公报》(Bulletin for International News)的两篇文章:“美国部队在冰岛”,1941年7月26日,xvii.948—951,以及“冰岛:政治和地理笔记”,1942年8月22日,xix.742—746。参阅:如果西方文明在历史上的地位被一个斯堪的纳维亚文明所取代,冰岛的假设地位就会是“在欧洲和美洲等距离的海洋中间的必然的踏脚石”(汤因比:《研究》,ii.441)。
(183) 利奥波德·冯·兰克:《拉丁和条顿民族史,1494—1514年》(Leopold von Ranke: History of the Latin and Teutonic Nations,1494—1514),G·R·丹尼斯修订的英译本,伦敦,贝尔,1909年版,第19页。
(184) 见汤因比:《研究》,ii.291—292,354—360。
(185) 瑞典在17世纪参加了西欧对北美的殖民活动:新瑞典从1638年到1655年在特拉华河两岸繁荣兴盛,1655年被新荷兰征服。在18世纪,瑞典在非洲西海岸有若干贸易站。在1939年,瑞典晚近曾有过的非欧洲领地是西印度的岛屿圣巴泰勒米。该岛于1784年由法国割让给瑞典,1877年法国又从瑞典手里买了回去。
(186) 在1939年,丹麦的海外领地包括在宪法上成为该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在丹麦议会有其代表的法罗群岛和一个殖民领地格陵兰。斯堪的纳维亚的格陵兰殖民地开拓者建立过一个共和国,直到1261年他们才宣誓效忠于挪威国王;1814年丹—挪联盟解散时,格陵兰像冰岛和法罗群岛一样没有被提及,结果为丹麦所得(关于挪威因此提出的权利要求,见《概览,1920—1923年》,第232页,以及《概览,1924年》,第461—462页)。除格陵兰外,丹麦最近有过的在欧洲以外的领地是三个西印度岛屿圣克罗伊、圣托马斯和圣约翰,这三个岛于1917年被美国买去。1939年丹麦的殖民领地在世界殖民帝国中面积占第9位,人口占第10位(见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殖民地问题》,第9页,表i)。
(187) 1939年的荷兰帝国包括:(1)荷属印度,包括爪哇岛、苏门答腊岛、西里伯斯岛、摩鹿加群岛、婆罗洲的大部分、新几内亚的一半、帝汶群岛以及一些较小的岛;(2)荷属西印度,包括南美大陆上的苏里南或即荷属圭亚那,以及库拉索岛及其附属岛屿。1939年荷兰帝国在世界殖民帝国中面积占第6位,人口占第2位(见《殖民地问题》,前引文)。
(188) 1939年比利时帝国包括:(1)比属刚果,1908年比利时国王就已兼并该地为比利时领土; (2)卢安达—乌隆迪,原是德属东非的一部分,但1920年作为委任统治地为比利时所得,行政上同刚果统一管理。1939年比利时帝国在世界殖民帝国中面积占第3位,人口占第6位(见《殖民地问题》,前引文)。
(189) 1939年挪威的海外领地包括:(1)在北极:1.斯瓦尔巴,该群岛包括斯匹次卑尔根、熊岛及其毗连岛屿,均于1920年为挪威所得(见上文,原著第158页),2.扬马延岛,兼并于1929年; (2)在南极:1.布维岛,1928年占有,在同英国发生一次外交争议后于1930年兼并,2.彼得一世岛,1931年兼并,3.位于西经20度和东经45度之间称为毛德皇后地的那一部分南极大陆,1939年1月14日兼并(见“挪威在南极的权利要求”,《北欧人》,1947年1—2月号,第1—4页)。1939年挪威的海外领地(除毛德皇后地外)在世界殖民帝国中所列的位置最低,面积和人口都居第11位(见《殖民地问题》,前引文)。
(190) 见上文,原著第24—25页。
(191) 见上文,原著第148页,第149页和注①。
(192) 这两处广大的葡萄牙非洲殖民地和比属刚果不同,它们有广阔的边境靠着海洋。安哥拉的大陆边境有一半同南非和英国的领地接壤,另一半和比属刚果接壤。莫桑比克的大陆边境全部和南非及英国的领土毗连。
(193) 参阅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Adolf Hitler: Mein Kampf),两卷集第1卷,第305—306页(慕尼黑,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38年版),第152—153页;《我的奋斗》英文版(詹姆斯·墨菲译),两卷集第1卷(伦敦,赫斯特和布莱克特,1939年版),第127页。原文本和英译本以下简称《我的奋斗》和“墨菲译本”。
(194) 参阅《概览,1937年》,i.33,326,340。
(195) “1914年的疆界对于德意志民族的未来是毫无意义的。”(《我的奋斗》,第738页;墨菲译本,第530页;分别参阅该两书的第736页和第529页)见下文,原著第335页。
(196) 见上文,原著第149—150页。
(197) 《概览,1937年》,i.368注①。参阅埃里希·科尔特:《空想与现实》(Erich Kordt: Wahn und Wirklickkeit),第2版(斯图加特,德意志联盟出版社,1948年版),第90—91页,作者把亨德森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建议说成是在1937年秋天提出的。
(198)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55以下。
(199) 同上书,第240—249页;苏联外交部:《德国外交部档案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文件和材料》(Documents and Materials relating to the Eve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48年版,第1卷,第3号(该文集以下简称《德国外交部档案文件》,苏联出版)。
(200)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242—243,246。协定上的刚果盆地是地理上的盆地的扩大,是1885年2月26日柏林总协定第1条第(2)和第(3)款规定下来的,它在大西洋一面延伸到南纬2度30分和安哥拉的洛热河河口之间,在印度洋一面延伸至北纬5度和赞比西河河口之间〔《英国与外国国家文件》(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Lxxvi.9;参阅S·E·克劳:《柏林西非会议,1884—1885年》(S.E.Crowe: The Berlin West African Conference, 1884—1885),伦敦,朗曼,格林,1942年版,第108页以下。亨德森在他同希特勒的谈话中具体提到印度洋一面的边界。协定上的刚果盆地包括比属刚果,英国属地乌干达、肯尼亚、尼亚萨兰和北罗得西亚,英国委任统治地(从前是德国的委任统治地)坦噶尼喀、半个濒临印度洋的索马里兰和半个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以及法属赤道非洲、埃塞俄比亚和葡属安哥拉的边缘部分。
(201)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247。
(202) 参阅A·J·汤因比:“英国对外政策中的问题”,《国际事务》,1938年5—6月号,xvii.321—322。
(203) 关于人口统计数据,曾使用下列著作:米歇尔·休伯等:《法国的人口》(Michel Huber and others: La population de la France),巴黎,阿歇特,1937年版;夏尔·里斯特和盖坦·皮鲁:《从战前的法国到今天的法国》(Charles Rist and Gaëtan Piron: De la France d'avant guerre à la France d'aujour'hui),巴黎,西里书店,1939年版;阿尔弗雷德·索维:《财富和人口》〔(Alfred Sauvy: Richese et Population),巴黎,帕约,1943年版〕和《幸福和人口》〔(Bein-étre et Population),巴黎,法国社会出版社,1945年版〕;罗贝尔·德勃雷和阿尔弗雷德·索维:《法国的法国人》(Robert Debréand Alfred Sauvy: Des Français pour la France),巴黎,加义马尔,1946年版。
(204) 阿瑟·L·鲍利引自W·温克勒,载《世界大战的一些经济后果》(Som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War),伦敦,桑顿-巴特沃思,1930年版,第41页。根据美国陆军部的官方档案,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伤亡数字要稍许大一些,见下文,原著第404页注④。
(205) 见《概览,1935年》,i.135—139。
(206) 在市中心,仍然有一些街区没有重建,只有兰斯的第二个教堂圣雷米教堂的中殿重新换上了屋顶。
(207) 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在青年作家的作品中,政治和社会问题才开始取代美学和个人道德问题的地位。
(208) 见上文,原著第82—83页。
(209) 在夏尔·里斯特和盖坦·皮鲁:《从战前的法国到今天的法国》一书中,工业一章的作者马克·欧居伊抱怨说,得不到关于1931年人口普查的详细资料。本书原著第168页所列的在法国的外侨数字是最权威的数字,但还有其他的数字,同该页所举的相差竟超过50万人以上。
(210) 马克·布洛赫:《奇特的失败》(Marc Bloch: L'étrange défaite),巴黎,游击队出版社,1946年版,第167页。这位伟大的中古史学者于1944年6月26日被德国人枪杀,他写的关于法国的失败及其原因的这本小书是对这方面全部问题的一篇最好的绪论。
(211) 皮埃尔-艾蒂安·弗朗丹:《1919—1940年的法国政治》(Pierre-Etienne Flandin: Politique française, 1919—1940),巴黎,新闻出版社,1947年版,第61—62页注。
(212) 关于极右翼的政治联盟,见《概览,1935年》,ii.36—38。
(213) 《概览,1935年》,ii.37注。
(214) 见《概览,1934年》,第387页;《概览,1935年》,ii.36。
(215) 这件谋杀案的罪责在12年以后仍未断定。1944年,当时意大利驻柏林大使安富索、埃马钮埃尔上校和纳瓦耳少校曾为此案受审。安富索被判处死刑,其他二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10月在佩鲁贾对此案重新审判,安富索被宣告无罪,对埃马钮埃尔和纳瓦耳的判决是“指控的罪行未经证实”。《观察家报》,1949年10月16日。
(216) 1935年5月15日,在斯大林、莫洛托夫、李维诺夫同赖伐尔为详细确定5月2日条约的含义举行会谈之后,发表了一个公报,其确切的措词是:“斯大林先生理解并完全赞同法国所采取的使其武装部队保持在安全所需要的水平上的国防政策”(《泰晤士报》,1935年5月16日;《时报》,5月17日)。
(217) 见《概览,1934年》,第550页。
(218) 关于巴尔图的东欧互助公约计划,见《概览,1934年》,第347—351页;《概览,1935年》,第1卷,第1编(iv)。
(219) 和1948年出现的同名的报纸无关。
(220) 可是乔治·博内〔博内:《从华盛顿到凯道赛》(Georges Bonnet: De Washington au Quai d'Orsay),以后简称博内:《从华盛顿》,日内瓦,布尔坎,飞马出版社,1946年版,第298页〕说,当时在议会里投票反对政府的75个议员中,73人是共产党人,两人“无所属政党”。
(221) 1939年的法兰西帝国包括以下殖民地、保护国和属地:
非洲:
1.北非(1)阿尔及利亚,1830年及其后占有,从1881年起作为法国本土三省治理,南部内地领土由军政府管辖; (2)突尼斯,自1881年起置于法国保护下,设有当地政府; (3)摩洛哥法属区(占摩洛哥苏丹国的大部分),从1907年起占领,从1912年起按当年与摩洛哥苏丹订立的条约,作为法国保护国管理。
2.法属西非,包括在总督统治下的七个殖民地组成的联邦和多哥委任统治地。联邦包括以下殖民地:塞内加尔(1736—1889年之间取得),它有自治机构,在巴黎的议会中有代表;法属几内亚(1843年取得);象牙海岸(1843年);达荷美(1893年);毛里塔尼亚(1893年);法属苏丹(1893年);尼日尔及其属地(1912年);以及达喀尔区及其附属地(根据法令于1924年从塞内加尔分离出来)。达喀尔是整个法属西非的行政中心和主要港口,又是法国的海空军基地,该港口后来在战时成为发生著名事件的场地。上沃尔特殖民地是在战后重建的,在1933年曾被划分给尼日尔、法属苏丹和象牙海岸。
多哥委任统治地占原德国殖民地的2/3,是根据凡尔赛和约归法国管理的,同西非联邦紧密相连,西非联邦的总督兼任多哥的当然高级专员,但多哥在财政和行政上仍保持独立的实体。
3.法属赤道非洲。从1841年以后取得的法属刚果在1910年分为加蓬、中央刚果和乌班吉沙里3个殖民地。1920年原来的乌班吉沙里的一块附属领土乍得成为单独的殖民地。根据1934年的法令,法属赤道非洲联邦成为一个单一的殖民地,原有的四个殖民地成为联邦的领土。法属喀麦隆委任统治地(占原德国殖民地的大部分)根据1921年和1925年的法令组成一个自治领。
1899年3月21日的英法宣言,承认法国对所有尼罗河流域以西领土的权利,实际上就是把整个撒哈拉划入法国的范围。
4.法属索马里。位于东非海岸的这块小殖民地是在1864年取得的,包括于1888年(即与英国订立划定殖民地界限的协议那一年)建立的吉布提港,通往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的铁路即以吉布提为起点站。
5.非洲东海岸外的岛屿:(1)马达加斯加,1890年宣布为保护国,1896年宣布为殖民地; (2)科摩罗群岛,从1914年起以殖民地的地位附属于马达加斯加总督管辖; (3)留尼汪岛,从1643年起成为法国领地,它有自治政府,在巴黎议会中有它的代表。
亚洲:
1.法属印度,包括5个省:本地治理(1674年由法国建立,自1814年起一直为法国占有),卡里卡尔、昌德纳戈尔、马埃和亚纳昂。设有自治政府,在巴黎议会中有代表。
2.法属印度支那(见上文,原著第82—84页)。交趾支那殖民地和安南、柬埔寨、东京和老挝保护国是在1862年至1884年之间占领的。广州湾领土是从1900年起从中国租借的。
美洲(所有殖民地均有自治政府):
1.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纽芬兰南海岸外的多岩石小岛群,1635年取得。
2.瓜德罗普岛,背风群岛之一,1634年取得,有5个由小岛组成的附属领土。
3.马提尼克,属于向风群岛,1635年取得。
4.法属圭亚那,位于南美东北海岸,1626年取得。根据1930年的法令,伊尼尼与圭亚那分离。
澳大拉西亚和太平洋(所有殖民地均有自治政府):
1.新喀里多尼亚以及由小岛群组成的几个附属领土,1854年至1888年之间取得。
2.新赫布里底群岛,自1906年起由英、法共同管理。
3.东太平洋岛屿,1841年至1881年之间取得。主要的岛群是社会群岛(包括其行政中心塔希提岛),马克萨斯群岛,土阿莫土群岛,甘比尔或曼加列瓦群岛,奥斯特拉群岛和拉帕。法国在大洋洲属地的总面积估计为1 544平方英里。
叙利亚和黎巴嫩委任统治地:
根据凡尔赛和约,由法国担任的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甲类委任统治权在法律上到1939年并未终止,因为法国并未批准1936年规定以自治政府取代委任统治制的条约(见《概览,1936年》,第748—758页,第766—767页),而且叙利亚和黎巴嫩仍在法国军事占领之下。
1939年法兰西帝国在世界上的殖民帝国之中按面积居第一位,按人口居第三位(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殖民地问题》,第9页,表i)。
(222) 阿尔及利亚的奥兰省和君士坦丁省各有3名众议员,阿尔及尔省有4名众议员,另外阿尔及利亚还有3名参议员。殖民地中,留尼汪岛,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各有两名众议员和一名参议员派往巴黎;法属印度有众议员和参议员各一名;塞内加尔、交趾支那和法属圭亚那各派一名众议员。其他设有某种自治机构的殖民地(法属索马里、马达加斯加、圣皮埃尔和密克隆、新喀里多尼亚和大洋洲法国属地)在巴黎议会中均有代表。所有法属赤道非洲的殖民地(除由总督治理并设有自治机构的塞内加尔外),以及法兰西帝国内的保护国和委任统治地,在巴黎的议会中均没有代表。
(223) 贝当也是法国最高司令部中为数不多的步兵军官之一。
(224) 规定缩短军事训练期限的法律于1928年3月31日颁布,自1930年11月1日起生效(《概览,1929年》,第31页注)。
(225) 巴黎,里德尔,1932年版,第338页。
(226) 夏尔·戴高乐:《建立职业军队》(Charles de Gaulle: Vers l'armée de métier),巴黎,贝尔热-勒弗罗,1934年版。
(227) 巴黎,贝尔热-勒弗罗,1932年版。
(228) 《奇特的失败》,第131—144页。
(229) 见《概览,1935年》,i.27—28。
(230) 保罗·雷诺:《法国拯救了欧洲》(Paul Reynaud: La France a sauvé l'Europe),巴黎,弗拉马里翁,1947年版,i.339;《概览,1936年》,第148页。
(231) 有时人们认为丘吉尔当时毫无疑问是同意关于法军实力的这些看法的〔由于他后来的言论,如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i.265)中说道:“德军在1938年或1939年是没有能力击败法国人的”〕。但应该指出,他在1936年3月说(同上书,163),“法国军队是欧洲最强大的军队”时,前面是加了修饰语的:“在今年的今天,大概在1937年的部分时间,法国军队……”等等。
(232) 巴黎,贝尔热-勒弗罗,1939年版。
(233) 雷诺:《法国拯救了欧洲》,i.339。
(234) 见“全权”,《新法国杂志》,1939年,第36页。
(235) 见《概览,1934年》,第339—343页,第387—388页;《概览,1935年》,i.58—90。
(236) 见上文,原著第174—178页。
(237) 《圣经》故事中古代犹太人存放上帝约法的圣柜。——译者
(238) 见《概览,1924年》,第2—16页。
(239) 《概览,1924年》,第16—64页;《概览,1925年》,ii.2—10。
(240) 同上书,第20—66页。
(241) 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幻想之深可从以下事例中看出:被送到德国集中营去的法国政治犯遇到波兰人和捷克人时为波兰工人的文化水平感到惊奇,尽管他们在法国为数有好几十万;他们还为斯拉夫人几乎完全不懂法语而感到惊奇。
(242) 《概览,1934年》,第386—387页;《概览,1935年》,i.60—61。
(243) 见《概览,1934年》,第207—221页。
(244) 同上书,第347—349页;《概览,1935年》,i.60—66。
(245) 见《概览,1935年》,i.72—85。
(246) 同上书,第178—193页。
(247) 同上书,第140—142页。
(248) 同上书,第156—169页。
(249) 同上书,ii.212—239,271—279。
(250) 见《概览,1937年》,ii.141—145。
(251) 见《概览,1936年》,第3编(i)。
(252) 同上书,第252—256页。
(253) 见《概览,1938年》,第1卷,第2编(ii)。
(254) 见《概览,1936年》,第283页,第287—288页,第294—295页,第297页,第299页。
(255) 见《概览,1938年》,ii.436。
(256) 见《概览,1938年》,第451页。
(257) 在写1936年至1943年的意大利对外关系史时可以使用的最重要材料是加里亚佐·齐亚诺伯爵的日记及其外交文件,他是墨索里尼的女婿和意大利的外交部长。但这些具有独得之秘性质的材料必须以批判的眼光看待。齐亚诺是一个小人物,而且他和墨索里尼的关系也不可能使他的证据完全可靠。在1938年到1943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他是一个忠诚的门徒;在他生命的末期,他深感被遗弃和被亏待之苦,而这个遗弃和亏待他的人正是他竭尽全力为之服务的。没有根据可以怀疑文件的真实性,因为其中许多陈述已从其他来源获得证实,但是也同样不能肯定齐亚诺没有修改过他的部分日记,因为他要显示自己比墨索里尼有更好的见解。
(258) 《概览,1927年》,第120—121页。
(259) 见马里奥·多诺斯蒂(笔名):《墨索里尼和欧洲》(Mario Donosti, pseud.:Mussolini e l'Europa),罗马,莱奥纳尔多,1945年版,第80页。
(260) 见《概览,1938年》,i.91—96。
(261) 见下文,原著第398页以下。
(262) 参阅雷诺:《法国拯救了欧洲》,i.439。
(263) 见“法西斯意大利的军队”,《意大利评论》,1939年,6—9月号,第1—380页,特别是陆军副部长帕里亚尼将军和空军副部长瓦莱将军题为“理论——精神”的两篇文章。
(264) 为进行比较,也许应该补充一点:甘末林也曾计划在阿尔卑斯山和北非战线上同时进攻意大利人,但他担心法国尚未准备就绪,也许只有在北非他还可以这样干。M·G·甘末林:《服役》(M.G.Gamelin: Servir),巴黎,普隆,1946年版,i.134。
(265) 见1939年5月30日墨索里尼致希特勒的“卡瓦莱罗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156—159(2818—PS);摘录译文载《文件,1939—1946年》,i.170;参阅《阴谋与侵略》,v.453—455。又见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月8日。
(266) 见《概览,1935年》,i.91—118。
(267) 见朱塞佩·博塔伊:《二十年和一天(1943年7月24日)》〔Giusseppe Bottai: Vent' anni e un giorno (24 luglio 1943)〕,米兰,加尔扎尼,1949年版,第123页,第127页。
(268) 见齐亚诺:《欧洲》,第392—394页;英译本,第258—259页;参阅《文件,1939—1946年》,i.150。
(269) 见马克斯韦尔·H·H·麦卡特尼:《孤家寡人》(Maxwell H.H.Macartney: One Man Alone),伦敦,查托和温达斯,1944年版,第10页。
(270) 《意大利日报》,1938年12月1日,1939年4月19日。
(271) 见门罗:《地中海的政治地位》,第4章。
(272) 《概览,1936年》,第17页注。
(273) 《概览,1938年》,i.137—143;协定全文见《文件,1938年》,i.141以后。
(274) 见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1938年1月3日。
(275) 见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1939年2月23日。
(276) 同上书,1939年1月4日。
(277) 雷诺的回忆录(《法国拯救了欧洲》,i.178—179)的字里行间可以隐约看出法国和意大利对争端的态度。雷诺于1936年10月访问罗马时曾警告齐亚诺说,对欧洲各处的法国敌人给予鼓励是不明智的,因为法国军队是意大利独立的保障。如果法国消失了,意大利的独立还保得住吗?齐亚诺大概为这种优越感的假说激怒了。当时他回答说,法国当然会永远存在嘛,让雷诺去推测,他是不会反对看到法国的力量有所削弱的〔关于意大利对法国人的真实或臆测的轻视态度的敏感性,见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外交家墨索里尼》(Gaetano Salvemini: Mussolini diplomate),巴黎,格拉塞,1932年版,第77—78页〕。意大利另一个动机可从一位意大利将军的答话中说明,当驻罗马的一位外交官用与雷诺相似的论据来同他打交道时,他回答说:“是啊……可是能到手的利益太逗人了!”(雷诺,前引书)
(278) 墨索里尼也想过对突尼斯实行共管〔见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1938年11月8日〕。
(279)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月8日。
(280) 见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1938年11月8日和30日;《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月8日。在11月间,墨索里尼也曾对尼斯提出要求。
(281) 见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1938年11月8日。墨索里尼在他的较长远的计划中还把吞并提契诺州也包括在内(同上书,1938年11月30日)。墨索里尼的更大的野心可以从他建议(由齐亚诺在1939年6月14日记录)的意大利—西班牙协定中看出,其中规定:在最后分配战利品时,意大利应得到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并在完全由西班牙控制的摩洛哥享有永久性的过境方便。意大利在1940年7月7日致希特勒的照会中还想取代英国和法国在地中海东岸诸国、伊拉克、埃及、苏丹、亚丁、赤道非洲和北非的地位;还要控制中东的石油供应,吞并科孚岛和北伊皮鲁斯(见西莫尼:《柏林的意大利大使馆》,第142页);参阅1940年6月19日齐亚诺与里宾特洛甫的谈话(齐亚诺:《欧洲》,第563—564页;英译本,第373—374页)。
(282) 见《概览,1927年》,第115—124页;《概览,1930年》,第16—22页。
(283) 见阿瑟·索尔特爵士著《政治上的个性》(Sir Arthur Salter: Personality in Politics)一书中关于墨索里尼的研究。伦敦,费伯,1947年版,第226—238页。
(284) 见哈罗德·尼科尔森著《外交》(Harold Nicolson: Diplomacy)一书中关于意大利的方法的描述。伦敦,桑顿·巴特沃思,1939年版,第151—153页。
(285) 见《概览,1926年》,第146页,第156页以下;《概览,1927年》,第155—160页,第166页,第172页,第298页;《概览,1928年》,第147—161页。
(286) 见《概览,1920—1923年》,第348—356页。
(287) 见《概览,1927年》,第185—201页。
(288) 见《概览,1930年》,第16页,第21页,第95页,第123页,第125页,第128—130页;《概览,1932年》,第260页。
(289) 见《概览,1933年》,第198—202页;《概览,1934年》,第328—331页。
(290) 见《概览,1931年》,第3编A。
(291) 见《概览,1934年》,第487—507页;议定书全文见《文件,1933年》,第396—398页。
(292) 见《概览,1934年》,第474页以下。
(293) 同上书,第442—448页,第454—455页,第484—487页。
(294) 见《概览,1935年》,i.156—161。
(295) 见《概览,1933年》,第206—220页,建议全文见《文件,1933年》,第240—249页。
(296) 据报道,墨索里尼在慕尼黑会议时曾对希特勒说,如果国联实行石油制裁,他在一个星期内就将被迫从埃塞俄比亚撤军。保罗·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跑龙套演员,1923—1945年》(Paul Schmidt: Statist auf diplomatischer Bühne,1923—1945),波恩,阿瑟瑙姆出版社,1949年版,第342—343页,第416页。
(297) 见《概览,1935年》,i.106,108—109,109—110注;博塔伊:《二十年》,第124—125页;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1938年12月24日;1939年3月26日《星期日快迅报》盖达的文章;索尔特:《政治上的个性》,第236—237页;马西莫·马吉斯特拉蒂:“德国和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事业”,《国际政治研究杂志》(Massimo Magistrati:“La Germania e l'impresa italiana di Etiopia”,Rivista di Studi Politici Internazionali),1950年10月至12月号,第563—606页。
(298) 见《概览,1935年》,i.178—193。
(299) 见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1938年5月11日和30日;齐亚诺:《欧洲》,第326—327页,337页;英译本,第211—212页,第217—218页。
(300) 《概览,1938年》,i.155。
(301) 同上书,i.158—163。
(302) 见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1938年11月16日。
(303) 《概览,1938年》,i.164—165。
(304) 见《概览,1936年》,第575—583页;《概览,1937年》,i.28—55,324—346;又见伊丽莎白·威斯克曼:《罗马—柏林轴心》(Elizabeth Wiskemann: The Rome-Berlin Axis),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
(305) 这份议定书的存在是齐亚诺和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在1936年10月21日谈话中透露出来的。齐亚诺:《欧洲》,第87—92页;英译本,第52—55页。
(306) 见《概览,1936年》,第582页。
(307) 据内维尔·亨德森爵士的《似水流年》〔(Sir Nevile Handerson,Water under the Bridges),伦敦,霍德和斯托顿,1945年版,第183页〕说:阿托利科常说,意大利当德国的得力的第二把手也比当有名无实的英—法—意同盟的无能的第三把手要强。
(308) 见《概览,1937年》,i.43—44,46以下,301以下,336。
(309) 在《概览,1939—1946年》的一卷中将谈到。
(310) 《概览,1937年》,i.35—36。
(311) 第二项议定书的文本,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142—146。
(312) 1945年审判时,当时曾任意大利军事情报机关首长的罗阿塔将军曾为此提供证据(见1945年1月5日意大利报纸)。
(313) 如希特勒和齐亚诺于1936年10月24日的谈话(齐亚诺:《欧洲》,第93页;英译本,第56页;参阅《文件,1939—1946年》,i.I)。
(314) 见齐亚诺:《欧洲》,第186—189页;英译本,第122—124页,关于1937年6月的提议,即由牛赖特访问伦敦的建议;另有德国驻罗马大使哈塞尔于1937年12月31日给柏林的报告,其中陈述意大利获知牛赖特访晤法国外长(在他赴东欧途经柏林时)这一消息后的反应。《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161—162和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1937年12月5日。
(315) 见齐亚诺:《欧洲》,第78页注①和第94页,英译本,第46页注①和第66页。
(316) 见墨索里尼于1936年9月23日和汉斯·弗朗克的谈话,以及于1937年1月23日和戈林的谈话(同上书,第75页,第79页,第129页和英译本,第44页,第47页,第82页)。
(317) 《我的奋斗》,第774页,墨菲译本,第544页。
(318) 同上书,第721页,墨菲译本,第519页。
(319) 同上书,第698页,第720页,第755页,墨菲译本,第505页,第518页,第541页。
(320) 见《概览,1933年》,第291—317页。
(321) 《阴谋与侵略》,v.576(2907—PS)。
(322) 慕尼黑会议后希特勒告诉阿托利科,他就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墨索里尼,所以才能坚持那么长时间的谈判。多诺斯蒂:《墨索里尼》,第132页。
(323) 这是希特勒于1939年8月22日对德军将领说的他对波兰作战的理由之一。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i.338(798—PS),译载《文件,1939—1946年》,i.443;参阅《阴谋与侵略》,iii.581。
(324) 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1937年11月16日;参阅同上书,1937年11月7日,1938年7月17日。
(325) 雷诺:《法国拯救了欧洲》,i.179。
(326) 其后不久,据报道,墨索里尼(在提议意大利应退出国际联盟时)对他的法西斯大会说过,这是德国的世纪,与德国站在一起显然要比与德国对抗强。见卡米洛·M·齐安法拉:《梵蒂冈和战争》(Camillo M.Cianfarra:The Vatican and the War),纽约,E·P·达顿,1945年版,第109—110页。此话未经齐亚诺证实,但即便不足凭信,也是非常能刻画他的性格的。据博塔伊在《二十年》一书的第112—113页说,齐亚诺前往柏林是想保持意大利所珍视的调遣自由,他失望地回来了,但仍安慰自己,希望意大利能抑制德国和德意志主义的复兴,直到意大利能领导拉丁世界进行反击德国及德意志主义的斗争。
(327) 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225—227,517—518,533,537(第315号),542,570—572(第348—350号),582—583,585,591(第373号),612。
(328) 见《概览,1936年》,第450—456页。
(329) 齐亚诺:《欧洲》,第176页;英译本,第116页;参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419。关于墨索里尼在9月这一段时期内转向不干预的情况,见同上书,第458—459页,第463—464页,和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1938年2月24日。
(330) 齐亚诺:《欧洲》,第224页;英译本,第146页;参阅《文件,1939—1946年》,i.25—26。此后不久,新任意大利驻奥地利公使吉吉被告知,他的任务就像是“一位医生,必须给垂死病人输氧气而又不能让他的继承人知道所发生的情况。在有疑难时,我们更关心的是继承人而不是垂死的病人”〔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1937年11月24日〕。
(331) 里宾特洛甫在1937年11月6日重申了这个保证。
(332) 见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1938年2月18日;马西莫·马吉斯特拉蒂:“从柏林看德奥合并”,《国际政治研究杂志》,1948年1—3月号,第77—106页。
(333) 见齐亚诺于1938年5月26日致德国驻罗马大使马肯森的声明。《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i.345—346。
(334) 见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关于希特勒访问罗马结果的1938年5月12日备忘录。同上书,i.1110 。
(335) 见1937年11月10日关于1937年11月5日总理府会议的“霍斯巴赫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402—413(386—PS);译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29—39;《文件,1939—1946》,i.16—25;参阅《阴谋与侵略》,iii.295—305。希特勒的副官施蒙德所写的关于1938年4月“元首的若干看法”的笔记说明,希特勒在去意大利以前曾想与墨索里尼达成谅解,作为德国支持意大利在非洲的要求的交换条件,但当时德国外交部起草的文件(《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1097,1104,1110),强调意大利正进入巩固时期,因此并不迫切需要轴心国的支持,结果用来作为德国善意表示的并不是非洲,而是南蒂罗尔。
(336)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436(388—PS,第11项),译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i.359;《文件,1939—1946年》,i.31;参阅《阴谋与侵略》,iii.317。
(337)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382(375—PS);《阴谋与侵略》,iii.281。
(338) 见E·L·伍德沃德和罗汉·巴特勒编:《1919—1939年英国外交政策文件》(E.L.Woodward and Rohan Butler,ed.: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第3辑(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9年版),ii.600(第1186号),以下简称《英国外交政策文件》。又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i.670,804—805,881—882,977,993,以及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1938年9月25日。
(339) 见《概览,1938年》,ii.427以下;又见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1938年9月29—30日。
(340) 见齐亚诺:《欧洲》,第373—378页,第392—394页;英译本,第242—246页,第258—259页;《文件,1939—1946年》,i.146—150,150—152。
(341) 齐亚诺:《欧洲》,第373—378页;英译本,第242—246页;《文件,1939—1946年》,i.146。
(342) 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跑龙套演员》,第382页。
(343) 门罗:《地中海的政治地位》,第239页。
(344) 本尼托·墨索里尼:《文章和演说》(Benito Mussolini: Scrittie discorsi),第11卷(米兰,赫普利,1938年版),第226页。
(345) 见菲利波·焦利:《我们是如何对待大悲剧的》,罗马,法罗出版社,1945年版,第76页。
(346) 他们于1937年11月6日的会谈;见齐亚诺:《欧洲》,第224页;《文件,1939—1946年》,i.25—26。
(347) 见《概览,1937年》,i.459—465;《概览,1938年》,i.43—69。
(348) 见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7年3月17日。罗马还怀疑德国也许会利用匈牙利人对亚得里亚海的野心〔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1938年10月3日〕,或者和斯拉夫人结成联盟来反对意大利(同上书,1938年4月21日)。
(349) 焦利,前引书,第115页。
(350) 见《概览,1934年》,第537—577页;《概览,1937年》,i.465以下。
(351) 又见《概览,1938年》,第2卷,第7章,第5节和第3卷,第1编,第5节。
(352) 见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月8日。
(353) 《日记(1937—1938年)》,1938年11月24日;又见1937年3月26日和12月6—7日、1938年6月17日和1939年1月的意南会谈。齐亚诺:《欧洲》,第158页,第233页,第330—331页,第411页;英译本,第102—103页,第152页,第214页,第271页。
(354) 见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3月9日,4月2日。
(355) 见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月8日,3月5日;齐亚诺:《欧洲》,第222页;英译本,第144—145页。
(356) 条约全文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3卷(西班牙),第1号;译载《文件,1939—1946年》,i.5—7。
(357) 朱塞佩·普雷佐利尼:《法西斯主义》(Giuseppe Prezzolini:Fascism),伦敦,梅休因,1926年版,第61—62页。又见D·A·宾奇:《法西斯意大利的教会和国家》(D.A.Binchy:Church and State in Fascist Italy),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41年版,第100页以下;墨索里尼的前合作者和后来的政敌切萨雷·罗西在1925年2月11日发表的备忘录,转引自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法西斯独裁制》(The Fascist Dictatorship),伦敦,凯普,1928年版,第412页。
(358) 关于墨索里尼的社会主义者时期,见高登斯·梅加罗:《成长中的墨索里尼》(Gaudens Megaro,Mussolini in the Making),伦敦,艾伦和昂温,1938年版。
(359) 不妨引用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描绘巴朗塔莱少爷的一句话:“谁会想到他对于坏事的这一巨大力量的感情竟然和一个对镜顾影自怜的少女的柔情如出一辙呢!”
(360) 马格里塔·萨尔法蒂:《墨索里尼其人和他的领袖才能》(Margherita Sarfatti,Mussolini,L'homme et le chef),巴黎,阿尔班·米歇尔,1927年版,第365页;梅加罗,前引书,第327页。
(361) 见《概览,1920—1923年》,第348—356页。
(362) 墨索里尼的爱好是巧言善辩和使用暴力,这是几百年来罗马尼阿人的特征;意大利人都不难了解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为何在艾米利亚如此壮大。罗马尼阿人喜欢最倾向于暴力的政党,这是非常自然的。20年来他们中有部分人是法西斯主义者,1951年他们中又有人成了共产党人。墨索里尼除酷爱使用暴力外,还有雄辩滔滔的才具,一直到他的晚年,他还在把他的辩才与他的洪亮嗓音结合在一起运用,收效颇大。他的演说听来空洞无物,大都是一些浮夸的词藻,但有动人的效果。
(363) 见墨索里尼:《文章和演说》,vi.66。
(364) 埃米尔·卢德维希:《墨索里尼和埃米尔·卢德维希的谈话》(Emile Ludwig:Mussolini's Gesprüche mit Emile Ludwig),柏林,保罗·索尔奈,1932年版,第87—88页。
(365) 见上文,原著第151—152页。
(366) 意大利的人口为4 400万人;德国在德奥合并以前有6 900万人,合并后有7 600万人,在兼并苏台德区以后有8 000万人;苏联有1.66亿人。东欧最大的国家是波兰,有3 300万人,其次是罗马尼亚,有1 800万人,捷克斯洛伐克在被分割前在1938—1939年有1 500万人,南斯拉夫的人口大致与这一数字相近。可是东欧各国的民族人数同大国的对比较之居民人数对比更为不利。大部分东欧国家的民族并不属于同一血缘,恰恰相反,在德国境外还有讲德语的少数民族。实际上只有2 200万波兰人,1 300万罗马尼亚人,1 100万南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加在一起),1 000万捷克斯洛伐克人,1 000万匈牙利人。上列数字尚未述及东欧最大的民族乌克兰人,他们共有3 60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归属苏联的。
(367) 从北到南是: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但泽自由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土耳其(只有一部分在欧洲)、希腊。
(368) 1914年东欧的小国是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土耳其、希腊。
(369) 有三个例外:克拉科夫共和国,这是波兰的遗迹,从1815年到1846年在普、奥、俄三国的隔缝中维持了中立地位;门的内哥罗公国(见下文,原著第210页注⑥,即本书第293页注⑥。——译者);爱奥尼亚群岛,英国人于1809年从法国人那里夺取过来,1815年至1864年是英国的保护地。但是东欧的历史不像西欧那样有利于像克拉科夫、门的内哥罗和但泽自由市这样一些规模非常小的国家的生存。参阅上文,原著第152页注①(即本书第211页注②。——译者)。
(370) 在普鲁士和俄罗斯历史上有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情况可以说明东欧的吸引力。1701年勃兰登堡的选侯腓特烈在他终于登上王位时,他从他的普鲁士公国取得国王称号,因为普鲁士位于帝国疆界之外,他的加冕典礼就在公国的首都哥尼斯堡举行。1703年,俄国的彼得大帝在芬兰湾创建了圣彼得堡作为新首都以取代莫斯科;莫斯科直到1918年才恢复其首都地位。
(371) 波兰从1386年弗拉迪斯拉夫二世亚盖隆王朝同立陶宛联盟以来就是一个大国,后来于1410年在坦伦堡战役中又击败了条顿骑士团,一直到1617—1629年的瑞典—波兰之战,它自己被瑞典的葛斯塔夫·阿多夫击败,从而缔结阿尔特马克休战协定结束这一战争,这又是瑞典参与30年战争在波罗的海打响的前奏曲。瑞典由于打败了波兰而成为一个大国,随后它又介入30年战争,直至在1699—1721年的北方战争中它自己又被俄国战败。参阅上文,原著第151页注⑤(即本书第211页注①。——译者)。
(372) 异教的芬兰野蛮人是在1154年被瑞典人征服的。从此芬兰是瑞典王国的一部分,直到1809年,那时才按腓特烈港条约割让给俄国。它于1917年宣布为独立共和国,在此以前它是与俄罗斯联合在一起的自治的大公国;苏俄在1918年1月正式承认它的独立地位。《和会史》,vi.287。
(373) 异教的爱沙尼亚野蛮人从1219年起就为丹麦人所征服。丹麦于1346年将这个省卖给了条顿骑士团。1561年,它自条顿骑士团被兼并于瑞典,1721年又由瑞典按尼斯塔德条约割让给俄国。它于1917年自己宣布为独立共和国;苏俄在1920年的多尔帕特条约中承认了它的独立。同上书,vi.295;《概览,1920—1923年》,第240页。
(374) 拉脱维亚大致占有相当于原来的立窝尼亚和库尔兰两省的土地,当地的蛮族居民自1158年起为条顿骑士团所征服,该地于1561年被割让给波兰。立窝尼亚于1629年由波兰按阿尔特马克条约割让给瑞典,又于1721年由瑞典按尼斯塔德条约割让给俄国,这可以说明三国之间在波罗的海的势力的消长。库尔兰从1561年到1795年是波兰宗主权监护下的一个公国,在第三次瓜分波兰时被俄国兼并,拉脱维亚在1918年宣布为独立共和国,并经苏俄于1920年的里加条约中承认。同上。
(375) 阿尔巴尼亚从7世纪到14世纪先后处于保加利亚、拜占庭、塞尔维亚帝国和拉丁君主的统治之下。从1359年至1392年曾有一段不统一的、本国人统治的时期,1392年阿尔巴尼亚被土耳其人征服。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阿尔巴尼亚宣布脱离土耳其而独立;见下文,原著第250—251页。
(376) 在20世纪以前,立陶宛是最后一个异教国家。它到1386年其大公成为波兰国王时才皈依基督教,并一直与波兰联合,直至波兰被瓜分时它才被俄国吞并。1917—1918年时,它通过与占领国德国的谈判方取得独立,苏俄在1920年的莫斯科条约中承认它的独立。《和会史》,vi.302—305;《概览,1920—1923年》,第251页。
(377) 波兰从10世纪开始就是西方基督教国家中的一员,先是一个公国,1300年起成为王国。它先后于1772年、1793年和1795年被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所瓜分。除了拿破仑建立的华沙大公国(1807—1814年)、沙皇治下名义上自治的波兰“会议”王国(1815—1831年)和克拉科夫共和国(1815—1846年)外,从1795年至1918年宣布成立独立的波兰共和国为止,就不再有波兰国家了。波兰的独立为苏俄在1921年的里加条约中所承认。《和会史》,vi.322。
(378) 波希米亚及其属地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卢萨蒂亚从9世纪开始就是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成员,从950年起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的宗主权,1198年终于成为一个王国,而且发展成为帝国的最初7个选侯之一。在1526年,由于选举了一个哈布斯堡家族的人为波希米亚国王,它终于与奥地利结成王朝的联合。1618年的波希米亚起义于1620年在白山战役中被粉碎以后,波希米亚于1621年被剥夺了作为有选举权的君主国的独立地位,其后的300年被合并为世袭的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斯洛伐克是在9世纪时被纳入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国家的,但在该世纪末它就被马扎尔人占领,此后的900年被并入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联合和独立是在1918年同时确立的。同上书,iv.105—106,112—114,261—265,270。
(379) 罗马尼亚人的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公国是在13世纪在东方基督教国家的边界上成长起来的。瓦拉几亚于1391年、摩尔达维亚于1513年被迫成为土耳其人的附庸;它们是(除俄国外)东方基督教国家中惟一没有正式并入奥斯曼帝国的部分。根据1856年的巴黎条约,它们被置于大国保护之下,土耳其只保有名义上的宗主权。1859年它们实际上已联合起来,并在1862年在法律上也联合起来组成罗马尼亚公国。它的独立得到1878年柏林条约的承认,1881年它成为一个王国。
(380) 克罗地亚公国是9世纪在西方基督教国家爱琴海边界上成长起来的,924年成为王国,1102年与匈牙利结成王朝联合,这个联合存在了800年。从9世纪开始,塞尔维亚诸公国在东方基督教国家相对应的边界上成长起来;1217年建立了一个把这些公国都统一起来的塞尔维亚王国;它在斯提芬·杜尚(1331—1355年)的领导下成为东方基督教国家中的主要强国,杜尚于1346年称帝。1389年,塞尔维亚在科索沃战役中被土耳其人征服,成为土耳其的附庸直到1459年,然后降为一个帕夏管辖区。只有门的内哥罗的亲王兼主教对土耳其人勉强维持了不稳定的独立,脆弱无力地延续了古老的塞尔维亚泽塔王国。1804—1813年的塞尔维亚独立战争导致在1812年缔结了布加勒斯特条约,于是给塞尔维亚以有限的自治。这个自治后来逐步扩大,直到1878年的柏林条约承认塞尔维亚独立,1882年它成为王国,门的内哥罗也在1910年成为王国。1918年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联合,组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门的内哥罗也参加在内。《和会史》,iv.112—114,196—204。
(381) 希腊的民族意识的基础是拜占庭帝国的传统,这个帝国是东方基督教国家最初的主要大国,它于1204年被西欧十字军摧毁,在部分恢复后又于1453年被土耳其人最后征服{见威廉·米勒文,载诺曼·H·贝恩斯和莫斯编:《拜占庭》〔Norman H.Baynes and H.St.L.B.Moss(ed.):Byzantium〕,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1948年版,第326—329页}。希腊独立战争(1821—1829年)导致由1832年的伦敦条约建立一个独立的希腊王国——这是奥斯曼帝国最早的继承国。
(382) 匈牙利在10世纪末成为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成员,在1001年成为一个王国。12世纪时,它与南方的拜占庭国家进行过斗争,15世纪时又与其继承者土耳其国家进行斗争。1526年匈牙利在莫哈哥战役中被土耳其人战败。它随之被瓜分成三部分:匈牙利的3/4被土耳其人占领和吞并;特兰西瓦尼亚成为土耳其宗主权管辖下的半独立公国;匈牙利国王的名义,以及匈牙利西北部边区于1526—1527年间归属哈布斯堡王朝,但为此须向土耳其人纳贡。在最后签订卡罗维茨条约的1683—1699年的战争中,奥地利重新征服了匈牙利,并对特兰西瓦尼亚强行实施宗主权。1687年匈牙利由选侯国转变为世袭的君主国;通过1723年的国事诏书,它被宣布为哈布斯堡王朝领地的组成部分。1849年,它在行政上与奥地利帝国合并,通过1867年的奥匈协定,奥地利帝国改组为二元制君主国,匈牙利成为与奥地利平分君主国的主权国家,通过共同王朝以及共同的外交政策、财政和军事机构与奥地利联合为一体,但在其他方面则是独立的;匈牙利给予克罗地亚以内部自治地位,但特兰西瓦尼亚则降为匈牙利的组成部分。1918年11月,哈布斯堡王室最后一个成员退位,使匈牙利自1526年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和会史》,iv.118—119,487—488。
(383) 保加利亚自9世纪起是东方基督教国家的成员,它曾在893—972年间以及1186—1258年间的两段时期内成为这些国家中的主要大国。1393年它被土耳其人征服。由于革命运动(爆发于1875年的是其高潮)和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的结果,1878年签订的柏林条约确立了保加利亚和东鲁梅利亚为附属于土耳其人的两个自治省。1885年,这两个省建立了统一的保加利亚公国。1908年,保加利亚宣布自己是完全独立的王国。
(384) 1923年洛桑条约规定的土耳其的欧洲边界,即自东色雷斯直到马里查(《和会史》,vi.108—109),实际上和土耳其自己在第三次巴尔干战争中从保加利亚赢得的并得到1913年9月29日君士坦丁堡条约确认的边界是相同的。《英国和外国政府文件》,cvii.706—721。
(385) 乌克兰民族意识的极端形式是以怀念基辅公国为其基础的,基辅在10世纪末改信东正教,成为当初的俄罗斯基督教大国。1214年它被蒙古人征服。加利西亚公国或红俄罗斯依然是此后乌克兰的惟一自治代表,直到1349年它被波兰吞并为止。立陶宛在1363年把它的边界扩展到第聂伯河口;1386年它与波兰合并,因此较大一部分的乌克兰便并入了波兰王国。16世纪哥萨克部族在第聂伯河岸兴起,成为新乌克兰民族的核心。他们发展成为一个半独立国家,通过1653年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它从效忠于天主教的波兰改宗为效忠于东正教的莫斯科沙皇。通过1667年的安德鲁索沃条约,波兰和俄罗斯沿第聂伯河瓜分乌克兰。在1773—1774年的普加乔夫起义以后,俄国政府于1775年剥夺了哥萨克人的自由,并于1781年把小俄罗斯(即左岸的乌克兰或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在行政上并入了俄罗斯帝国。1793年由于第二次瓜分波兰,俄国取得了右岸的乌克兰。1917年11月乌克兰宣布独立,1918年2月1日得到同盟国的承认,1918年2月8日通过第一个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乌克兰成为同盟国经济上的保护国。在1919年德国撤退以后的无政府状态中,一个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统一起来了,并于1923年成为苏联第二个最大和最重要的成员了。
“在1590—1700年之间曾起过作用的各种历史因素的特殊结合,在波兰王国边境产生一个共同体之前,要区别讨论‘乌克兰’民族及其起源问题是不大可能的,这个共同体由其共同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而统一起来,绝大部分成员都信仰希腊东正教,又采用俄罗斯语言形式——语言本身也在不断地改革,以适应日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环境。”W·E·D·艾伦:《乌克兰的历史》(W.E.D.Allen:The Ukraine: a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1940年版,第65页。
(386) 莱茵邦联最初的成员有16个德意志国家;26个国家最初没有在内;见阿尔贝·索雷尔:《欧洲和法国革命》(Albert Sorel:L'Europ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vii.52—53。通过1806年7月17日的莱茵邦联文书,16个签字国脱离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当即宣布他不再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的存在,8月6日法兰西斯二世放弃皇帝称号。最后所有的德意志国家,除奥地利、普鲁士、黑森-卡塞尔和不伦瑞克以外,都加入了莱茵邦联。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James Bryce:The Holy Roman Empire),新版修订本(伦敦,麦克米伦,1904年版),第409页注①。
(387) “西欧的文明是拜占庭帝国顽强维持生存的意志的副产品,这句话并不夸张。”诺曼·贝恩斯在贝恩斯和莫斯编的《拜占庭》一书中的话,第xxxi页。
(388) 《和会史》,vi.274—278,318—322。这次波兰—俄国交锋在历史上的伟大先例是毁灭了旧波兰王国的百年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伊凡雷帝发动的1558—1583年的立窝尼亚战争使他到达波罗的海海滨;于是波兰在“莫斯科动乱时期(1603—1613年)”企图征服俄罗斯,波兰于1610—1612年占领莫斯科是当时的高潮;最后俄国又再一次向西推进,根据1667年的安德鲁索沃条约首次兼并波兰领土,成为瓜分波兰的先声。
(389) “如果匈牙利在17、18和19世纪是由本族国王统治国家,它满可以像法国一样完全解决它的民族问题。”〔C·A·麦卡特尼:《匈牙利和它的继承者……1919—1937年》(C.A.Macartney:Hungary and her Successors …1919—1937)。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37年版,第35页;参阅第487页〕
(390) 1914年罗马尼亚的人口为700万人,在匈牙利的罗马尼亚人大约有350万人。
(391) 《和会史》,iv.245—248,270;麦卡特尼:《匈牙利和它的继承者》,第94—110页。
(392) 《和会史》,vi.278—279;W·F·雷德韦、J·H·彭森、O·哈勒克基、R·迪博斯基编:《剑桥波兰史》(W.F.Reddaway,J.H.Penson,O.Halecki, R.Dyboski,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第2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41年版),第522—524页;沃尔特·科拉尔茨:《东欧的神话和现实》(Walter Kolarz:Myths and Realities in Eastern Europe),伦敦,德拉蒙德,1946年版,笫108—110页。立陶宛的语言与波兰的完全不同,波兰与立陶宛结成联邦或兼并立陶宛的理由是以波兰被瓜分前的波兰—立陶宛联盟的传统为基础。
(393) 阿尔巴尼亚人口有100万不到一些,在边界外南斯拉夫的马其顿部分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接近50万人。
(394) 休·塞顿-沃森:《两次大战之间的东欧,1918—1941年》(Hugh Seton-Watson: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Wars,1918—1941),剑桥大学出版社,1945年版,第311页。参阅H·N·布雷斯福德:《马其顿》(H.N.Brailsford:Macedonia),伦敦,梅休因,1906年版,第99—103页,以及伊丽莎白·巴克:《马其顿在巴尔干强权政治中的地位》(Elizabeth Barker:Macedonia: Its Place in Balkan Power Politics),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50年版,第9—12页。
(395) 1939年初,欧洲乌克兰人的分布情况大致如下:在苏联(主要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3 100万人;在波兰,500万人;在罗马尼亚,50万人;在捷克斯洛伐克,50万人;在匈牙利(由于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次瓜分),38 000人。见《国际新闻公报》(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 News),1939年1月14日,第5页和第13页的更正,以及C·A·麦卡特尼:《民族国家和少数民族》(National States and National Minorities),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34年版,附录iii。
(396) 休·塞顿-沃森:《东欧》,第321—322页。
(397) “Ruthenus”(卢西努斯)是中世纪的俄文名称拉丁化的结果,1849年的奥国宪法对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乌克兰人正式采用这个名称。艾伦:《乌克兰》,第248页。关于卢西尼亚问题的发展,见麦卡特尼:《匈牙利和它的继承者》,第206—211页。
(398) 东欧的白俄罗斯人像乌克兰人一样,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实现民族统一的潜在对象。1939年初,在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约有550万白俄罗斯人;在波兰有150万人;在拉脱维亚有36 000人;在立陶宛有4 000人。
(399) 《和会史》,iv.272—273。
(400) 《和会史》,vi.283注。
(401) 见《概览,1920—1923年》,第255页注②,以及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新闻部编的《波罗的海国家》(The Baltic States),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38年版,第89页注③。可是立陶宛对维尔纳的要求主要还是以历史原因为依据,因为维尔纳直到1569年卢布林联盟时一直是立陶宛的首都。
(402)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以土耳其为腹地的希腊港口士麦那在数字测验上未能符合这一模式,虽然那里的希腊人除人数方面外在其他方面都比土耳其人占优势。见A·J·汤因比:《西方在希腊和土耳其的问题》(The Western Question in Greece and Turkey),伦敦,康斯特布尔,1922年版,第133—134页。这是在土耳其人于1919—1922年的安纳托利亚战争中把希腊人赶走之前的情况。
(403) 见弗朗兹·博克瑙:《奥地利及其以后》(Franz Borkenau:Austria and After),伦敦,费伯,1938年版,第93—102页。
(404) 关于阿塔图克和出生于克里特岛的奥斯曼帝国臣民维尼齐罗斯的相似之处,见《概览,1930年》,第167页。对此,有一位评论家说:“测验奥斯曼土耳其民族的是语言和文化,不是严格的种族。他们并不认为阿塔图克是‘边缘民族’,正如我们不认为劳埃德·乔治、博纳·劳和拉姆齐·麦克唐纳是‘边缘民族’一样。”
(405) H·塞顿-沃森:《东欧》,第193页。
(406) 见伊丽莎白·威斯克曼:《不宣而战》(Undeclared War),伦敦,康斯特布尔,1939年版,第22页。
(407) 见H·塞顿-沃森:《东欧》,第410页;R·W·塞顿-沃森:《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史》(R.W.Seton-Watson,A History of the Czechs and Slovaks),伦敦,哈钦森,1943年版,第334页。图卡在这一类型中不是一个主要例子,因为他大概从来没有从效忠马扎尔民族转为效忠斯洛伐克民族。关于他因叛国罪于1929年受审的相反的看法,见R·W·塞顿-沃森,前引书第335页,以及麦卡特尼:《匈牙利和它的继承者》,第132页,第140页。
(408) 见威斯克曼:《不宣而战》,第55页;《概览,1937年》,i.424。
(409) 同上书,第16页。
(410) 这是在纳粹革命之前,兴登堡对希特勒的称呼,见J·W·惠勒-贝内特:《兴登堡:木制巨人》(J.W.Wheeler-Bennet:Hindenburg: The Wooden Titan),伦敦,麦克米伦,1936年版,第407页。
(411) 参阅麦卡特尼:《民族国家和少数民族》,第10页。据说1924年在日内瓦发生的一件事很可以说明这个地区非常复杂的民族问题。国联正在讨论一个少数民族问题,有人提出,正如在希腊和阿尔巴尼亚之间一样,区分民族的真正标准是语言,即人们在自己家里所说的语言。可是当时揭露的事实是,这两国的统治者,如果按这个标准,恰好都应属于对方国家;当时阿尔巴尼亚的首相范·诺利主教据说在家里是说希腊语的,虽然他是当时在世的最伟大的阿尔巴尼亚学者;而希腊共和国的总统孔杜里俄提斯海军上将则出生于长期定居于希德拉的一个阿尔巴尼亚家族,他在自己的家庭圈子里习惯于说阿尔巴尼亚语。范德勒·鲁宾逊:《阿尔巴尼亚走向自由之路》(Vandeleur Robinson:Albania's Road to Freedom),伦敦,艾伦和昂温,1941年版,第35页。
(412) 这条分界线在东方有一些无法划定的突出部分,即东仪天主教会或希腊天主教会,这些教会又与罗马教廷重新统一,但仍保留拜占庭的礼拜仪式。它们是反基督教改革运动的胜利者。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卢西尼亚的天主教会和罗马尼亚的天主教会,前者是在1596年的布列斯特宗教会议上产生的,它是作为波兰天主教会侵入波兰东正教地区的帝国主义工具,后者是在1698年的阿尔巴尤利亚宗教会议上产生的,是为哈布斯堡王朝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同样目的服务的〔关于后者,见R·W·塞顿-沃森:《罗马尼亚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Roumanians),剑桥大学出版社,1934年版,第124—125页〕。这些教会不久便限于附属的民族,同波兰化的天主教的统治阶级或马扎尔化的卡尔文教派的统治阶级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如同东正教会自己一样,它们也真正反映了乌克兰和罗马尼亚民族的情况,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在独立实现以后,它们的作用也就相应地削弱了。在1939年3月,卢西尼亚和波兰所属的加里西亚的东仪天主教会大约有400万教徒,罗马尼亚的东仪天主教徒大约有150万。东欧其他地区的东仪天主教会的信徒人数甚少。见唐纳德·阿特沃特:《东方的天主教教会》(Donald Attwater:The Catholic Eastern Churches),修订版(威斯康星,密尔沃基,布鲁斯,1937年版),第279—282页,统计摘要。
(413) 根据人种学原则,寇松线是波兰东部最低限度的边界线,1919年12月8日和会最高会议授权波兰设立永久管理机构。见《和会史》,vi.275,322;《概览,1920—1923年》,第251页;S·科诺瓦洛夫:《俄罗斯—波兰关系》(S.Konovalov,Russo-Polish Relations),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5年版,第34页和附录3、4;L·B·纳米埃尔:《面向东方》(Facing East),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47年版,第109—113页。将近一半面积的波兰国土(15万平方英里中的64 000平方英里)和1/3的人口(3 300万人中的1 050万人)是处于寇松线和波兰最后于1921年赢得的里加条约的边界线之间。
(414) 这条分界线隐隐约约地在亚得里亚海彼岸穿过意大利继续从加尔干诺半岛延伸到加埃塔。这是从9世纪到11世纪南方的拜占庭意大利和北方的意大利王国之间的分界线(汤因比:《研究》,iv.343—344,610—611);从12世纪到19世纪,这条界线还反映了更北向的两个西西里或那不勒斯王国和教皇辖地之间的边界。这条古老的文化界线并未因意大利统一运动而消除,法西斯领袖在消除这条界线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就像当年的统一者亚历山大国王所取得的成效一样微小,后者也想消灭南斯拉夫境内的类似边界线。
(415) 这一条文化上的边界线大体上相当于被淹没的乌克兰民族的西部边沿。“乌克兰”的词义就是指边界或边缘。起初它是指俄罗斯世界(过去在波兰-立陶宛统治下)防御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的南部边境(艾伦:《乌克兰》,第64—65页)。但到了20世纪,乌克兰却变成俄罗斯世界防范西欧文明的西部边境了。
(416) 汤因比:《和会后的世界》,第70页注①。
(417) 这个区分显然是20世纪初由卡尔·伦纳在维也纳创造出来的。它同样适用于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东欧最典型的有历史的民族是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土耳其人和俄罗斯人。奥匈帝国的马扎尔人和波兰人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也可以列为有历史的民族,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丧失自己的民族传统,而且保有或取得了一种特权地位。所有其他的民族都是无历史的民族:在奥匈帝国有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尽管偶尔也承认他们的历史权利)、斯洛伐克人、卢西尼亚人、罗马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有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在俄罗斯帝国的欧洲部分有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列托人、爱沙尼亚人和芬兰人。
(418) 参阅门罗:《地中海的政治地位》,第22—23页。应该记住,虽然现代希腊民族主义利用拜占庭帝国的传统作为号召,然而拜占庭东正教世界的中心却不是希腊,而是小亚细亚;希腊一直是远离中心而靠近西方世界的边沿地区,直到732年它都是包括在罗马大主教管辖区之内的,其后它遭到法国人和威尼斯人的侵犯和占领。
(419) 坦伦堡“是斯拉夫海洋中的一个德国岛屿。可是在这个岛上却有着一块神圣的土地,那里的一个民族是以剑作为道义价值的象征的。而且这块土地是纪念德意志民族的光荣复仇的,他们湔雪了五个世纪以前条顿骑士团遭到惨败的耻辱。有人也许会想,经过了500年的时间,一切关于战败的回忆都会消失了。1914年的坦伦堡胜利说明了这种回忆只是‘休眠’而已。爱国歌曲和军队进行曲使东部边境在感情上和历史上的号召力都不会泯灭”。伊恩·F·D·莫罗:《德国—波兰边界的和平解决》(Jan F.D.Morrow:The Peace Settlement in the German-Polish Borderlands),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36年版,第217页。
(420) 参阅佐尔坦·格列维奇的文章,载《匈牙利和文明》,乔治·卢卡奇编(La Hongrie et la civilisation,edited by Georges Lukács),巴黎,复兴书局,1929年版,第66页。关于导致莫哈奇败绩的匈牙利统治阶级的骄傲自大和失策,以及处于从属地位的克罗地亚人对此的反应,见R·W·塞顿-沃森:《南方斯拉夫人问题和哈布斯堡王朝》(The Southern Slav Question and the Habsburg Monarchy),伦敦,康斯特布尔,1911年版,第19页和注⑤。和坦伦堡一样,莫哈奇的败绩也因为帝国于1687年在同一地点击溃土耳其的伟大胜利而得到湔雪。
(421) R·J·克纳:《18世纪的波希米亚》(R.J.Kerner,Bohem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纽约,麦克米伦,1932年版,第279页。
(422) 丽贝卡·韦斯特:《黑羊和灰鹰:1937年南斯拉夫之行记事》(Rebecca West: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A Record of Journey through Yugoslavia in 1937),伦敦,麦克米伦,1941年版,i.523;参阅i.157。
(423) 布雷斯福德:《马其顿》,第271—272页。参阅鲁宾逊:《阿尔巴尼亚走向自由之路》,第11—12页。
(424) 关于这种古老的民族主义的研究,见科拉尔茨:《东欧的神话和现实》。参阅塞顿-沃森:《东欧》,第8章。
(425) 1938年底的世界主要犹太少数民族的人数如下:美国470万人;波兰334.5万人;苏联318万人;罗马尼亚80万人;匈牙利48万人;德国和奥地利47.5万人;巴勒斯坦44万人;联合王国37万人;捷克斯洛伐克31.5万人。见阿瑟·鲁平:《犹太人的命运和未来》(Arthur Ruppin:The Jewish Fate and Future),E·W·迪克斯译,伦敦,麦克米伦,1940年版,第2章,特别是第35页。
(426) 芬兰:从1918年以后,一直保持议会制政体,1930—1932年为应付法西斯拉普亚运动,对公民自由曾加以一定限制。爱沙尼亚:1934—1940年由派茨总统和莱多纳将军的独裁政权统治。拉脱维亚:1934—1940年,总理厄尔曼尼斯实施独裁统治,他于1936年任总统。立陶宛:1926—1940年实施独裁统治,1926—1929年的独裁者是沃德马拉斯总理,1929—1940年是斯梅托纳总统。波兰:1919—1926年实施议会制政体,维托斯是农民党的领袖。1926—1939年实行独裁制,1926—1935年的独裁者是毕苏斯基,1935—1939年是由若干上校统治(总统莫希齐茨基、总司令西米格莱-雷兹、外交部长贝克三人执政)。捷克斯洛伐克:自1919年到1938年第一次被瓜分以后,议会制政体,农民党在历届联合政府中是主要执政党;1938—1939年是民主专政制。奥地利:1913—1933年为议会制政体(赛佩尔于1922—1924年和1926—1929年两度出任基督教社会党的总理)。1933—1938年实行独裁制,1933—1934年由陶尔斐斯独裁,1934—1938年由许施尼格独裁。匈牙利:1919年是贝拉·库恩领导下的共产党政权,1919—1920年是白色恐怖和复辟时期。1919—1945年由霍尔蒂任摄政,名义上是议会制政体,实际上是独裁,历任总理是:拜特伦,1921—1931年;贡伯士,1932—1936年;达兰伊,1936—1938年;伊姆雷迪,1938—1939年;捷列基,1939—1941年。罗马尼亚:1919—1937年为议会制政体,1922—1928年是布拉蒂亚努领导下的自由党人执政,1929—1931年和1932—1933年是马钮领导下的民族农民党人执政。国王卡罗尔二世(1930—1940年)自1930年起取得了个人占优势的地位。1937年是戈加的反犹太主义政府执政;1937—1940年是君主独裁制。南斯拉夫:1921—1928年是议会制政体,有帕西奇领导的塞尔维亚激进党,拉迪奇领导的克罗地亚农民党;拉迪奇于1928年被暗杀。1929—1934年是国王亚历山大的君主独裁制,1934—1941年由摄政王保罗继续实行君主独裁制(1935—1939年由斯托亚迪诺维奇任首相)。保加利亚:1919—1923年为议会制政体,由农民党领袖斯坦博利斯基任首相,斯坦博利斯基于1923年被杀害。1923—1924年的历届政府都被恐怖主义的马其顿革命组织控制。1934—1935年在维尔切夫和格奥尔基耶夫领导下实行军事独裁。1935—1943年是国王博里斯二世(1918—1943年)的君主独裁制。阿尔巴尼亚:1920—1924年是摄政会议制;阿赫梅特·索古于1925年叛乱,1925—1928年他作为共和国的总统执政,1928—1939年他又作为索古国王执政。希腊:1917—1920年由维尼齐罗斯任首相。1920—1922年国王康斯坦丁复辟;1922—1923年国王乔治二世在军队统治下执政,1924—1935年为共和国,1928—1932年由维尼齐罗斯任总理。1935年发生军事政变,国王乔治二世(1935—1947年)复辟,1935—1936年为君主立宪制,1936—1941年由梅塔克萨斯将军实行独裁。土耳其:由1923年后即由人民共和党一党专政,1923—1938年基马尔·阿塔图克任总统,1938年后由伊诺努任总统。
(427) 见下文,原著第248页和注③。
(428) 主要见《曼彻斯特卫报》,1930年10月14日、22日、24日和25日,11月17日,12月29日;H·塞顿-沃森:《东欧》,第335页。《概览,1932年》,第368页注①曾表示要全面论述乌克兰问题,但这一意图未能实现。
(429) H·塞顿-沃森:《东欧》,第148—149页,第336—338页。
(430) 同上书,第149—150页;参阅第153页,第241页,第262—263页,第317页,第337页,以及威斯克曼:《不宣而战》,第98页,第107—108页。
(431) 以下是1939年农业人口占职业人口的大致百分比:芬兰,60%;爱沙尼亚,60%;拉脱维亚,66%;立陶宛,77%;波兰,63%;捷克斯洛伐克,34%;匈牙利,55%;罗马尼亚,73%;南斯拉夫,75%;保加利亚,80%;希腊,61%;土耳其(全国),82%。在最原始的阿尔巴尼亚,几乎全部人口都从事畜牧业。
(432) 哈布斯堡帝国的经济统一体的情况是不明确的,大体上它所起的经济作用是落后的,帝国的居民生活水平是低标准的。“所听到的关于1918年以后这一君主国的自然经济统一体的情况比以前的多得多。”〔C·A·麦卡特尼:《多瑙河流域的问题》(Problems of the Danube Basin),剑桥大学出版社,1942年版,第78页〕经济上民族主义的弊病导致为过去哈布斯堡帝国辩护的争论。弗雷德里克·赫茨〔见《多瑙河国家的经济问题》(The Economic Problem of the Danubian States),伦敦,高兰兹,1947年版〕说继承国的国民收入减少了。而科林·克拉克的见解则与此相反〔见《经济进展的条件》(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伦敦,麦克米伦,1940年版,第127—136页〕。
(433) 严格说来,“凡尔赛解决方案”一词用之于东欧是不合适的,因为1919年6月28日的凡尔赛和约只限于德国,只是在限定德国的东部边界时才影响东欧。协约国给东欧新体制以法律形式所根据的条约是:1919年9月10日与奥地利签订的圣日耳曼昂莱条约,1919年11月27日与保加利亚签订的塞纳河畔纳伊条约,1920年6月4日与匈牙利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以及1923年7月24日与土耳其签订的洛桑条约(取代1920年8月10日的塞夫勒条约)。
凡尔赛和约刊载于《和会史》,iii.100以下。奥地利和匈牙利签订的条约刊载于同上书,v.170以下。保加利亚的条约刊载于同上书,v.305以下。同土耳其签订的两个条约并未载入《和会史》,分别见《条约汇编》第11号(1920年),《1920年8月10日在塞夫勒与土耳其签订的和平条约》,敕令第964号,以及《条约汇编》第16号(1923年),《1923年7月24日在洛桑与土耳其签订的和平条约及其他文件》,敕令第1929号。
(434) L·B·纳米埃尔:“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和会史》,第4卷,第1章,第3编)对奥地利的这一过程作了最精辟的简短叙述,尤见第90页,第113页。
(435) “因为昔日的土耳其已不再存在,它的继承者对帝国不感兴趣,俄罗斯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的联盟,哈布斯堡王朝已经覆灭;凡尔赛、特里亚农和圣日耳曼条约使弱小民族获得自由。自由对这些民族来说是令人欣喜若狂的……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都像从长时间沉睡中醒来的年轻人,在清晨敞开的窗前伸展自己的肢体。”(韦斯特:《黑羊和灰鹰》,ii.494)参阅T·E·劳伦斯:“仿佛就在清晨,未来世界的清新感使我们陶醉”〔《智慧的七根支柱》一书被删除的序言中语,转引自戴维·加尼特编:《T·E·劳伦斯书信集》(David Garnett, ed.: The Letters of T.E.Lawrence),伦敦,凯普,1938年版,第262页,以及A·N·劳伦斯编,T·E·劳伦斯后来的改写本:《东方集会》(Oriental Assembly),伦敦,威廉斯和诺盖特,1939年版,第142页〕。
在西伯利亚,春天来临得稍许早一些,大约在1904年:“革命一代的青年和工人运动的青年恰好相合。这是18岁到30岁的年轻人时代。超过那个年龄的革命者是极少的,因为超龄者似乎就是老年人了。革命运动那时还绝不是职业性的,它是凭对未来的信念,凭自我牺牲精神。那时还没有惯例可循,没有规定公式,没有戏剧化姿态,没有现成的演讲诀窍。斗争本是出于万般无奈,出于不好意思而又十分尴尬。‘委员会’、‘政党’等一类词儿都还是新词,带有清新的气息,在年轻人听来就像是又迷人又叫人难以平静的音调。”〔列夫·托洛茨基:《斯大林》(Leon Trotsky:Stalin),查尔斯·马拉默特译自俄文,伦敦,霍利斯和卡特,1947年版,第53—54页〕在德国,春天自然是随着纳粹革命到来的,见希特勒1934年3月19日在慕尼黑的演说〔1922年4月至1939年8月的《阿道夫·希特勒言论集》,编译者N·H·贝恩斯,以下简称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42年版,i.212。
(436) “我们已经看到,在许多地区,就民族领域而论,已逐渐形成一种复杂的等级制度。1919年的解决方案大体上是颠倒了早先的位置,惟一的例外是卢西尼亚人,他们无论在1919年以前或以后,都是处于底层的民族。”(麦卡特尼:《多瑙河流域的问题》,第120页;参阅第151—152页,第108—109页;以及汤因比:《和会后的世界》,第60—61页)
(437) 阿尔巴尼亚不属于任何一类,它并不是战争中的交战国,除作为一种政策的对象外,也无其他作用;它最后划定的边界与1913年划定的并无多大差别。它对南斯拉夫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问题肯定有不满情绪,可是由于自己弱小,它也无法推行要求修改条约的政策。
(438) 土耳其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有1920年的塞夫勒条约记录在案;但它又是1919—1923年希腊—土耳其战争的战胜国,有1923年的洛桑条约记录在案。
(439) 《和会史》,iv.119;博克瑙:《奥地利和以后》,第206页。
(440) 同上书,iv.391—392;i.347;ii.13—14。
(441) 《概览,1920—1923年》,第316页。
(442) 《和会史》,iv.382—383;《概览,1920—1923年》,第304—307页。
(443) 《概览,1920—1923年》,第333—334页。第一次是在1913年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败于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同它们之间的其他差别一样,它们要求修改和约的主张在性质上的不同是与以下事实有关的,即“保加利亚的社会结构在东欧是最平等的,匈牙利的社会结构则最不平等”。H·塞顿-沃森:《东欧》,第130页。
(444) 《概览,1934年》,第524—525页。
(445) 关于“公道”词义的含糊不清,见《和会史》,iv.439—442。“令人吃惊的是,经常可以发现同一个民族主义的德国人一方面声称把东普鲁士从德意志帝国分割出去是根本不行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说谁要是怀疑德意志—波希米亚的可行性简直是荒谬。”伊丽莎白·威斯克曼:《捷克人和德国人:关于历史上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省的斗争之研究》(Elizabeth Wiskermann: Czechs and Germans: A Study of the Struggle in the Historic Provinces of Bohemia and Moravia),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38年版,第86页。
(446) “今天在奥地利帝国的继承国中间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并不少于帝国瓦解之前”(博克瑙:《奥地利和以后》,第83页)。参阅1920年5月6日协约国致匈牙利的复信,见《和会史》,iv.422。
(447) 见“古代自由史”一文,载《自由史和其他论文》(The 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伦敦,麦克米伦,1907年版,第4页。
(448) 见“民族”一文,载《自由史和其他论文》,第297页,第290页。
(449) 1938年9月26日他在柏林体育馆的演说中说:“而且我还向他进一步保证,在捷克斯洛伐克解决它的问题时,也就是说在捷克人同他们的其他少数民族达成协议时,和平地而不使用压迫手段达成协议时,我对捷克国家就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要求了。那便是向他提供的保证!我们不要捷克人!”见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526;《文件,1938年》,ii.259。
(450) 见1939年3月16日规定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为保护国地位的法令绪言〔《帝国法律汇编》,1939年,第一部分,第485页;《阴谋与侵略》,viii.404(051—TC);《文件,1939—1946年》,i.62〕。
“民族”扩张和“领土”扩张的矛盾是1939年1月16日希特勒与恰基谈话的主题。希特勒斥责匈牙利在第一次瓜分捷克斯洛伐克时所提的要求是干蠢事,因为采取的形式是民族要求而不是领土要求。匈牙利的坚持民族原则使德国在外交上很为难,如果它按领土原则而与德国合作,希特勒就可以不理会张伯伦〔关于1939年1月16日希特勒与恰基谈话的报告,载《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2卷(匈牙利),第25号〕。还有类似的情况,希特勒在1939年3月13日会见蒂索时说,“[他]在慕尼黑作出决定时……并不是在玩弄强权政治,而是在为德国人民谋利益”〔德国外交部关于1939年3月13日希特勒会见蒂索的谈话记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152(2802—PS);译载《文件,1939—1946年》,i.48;参阅《阴谋与侵略》,v.445〕。
(451) “在1919年的另一次创造性场合中,一位波兰外交官向我阐述了他的国家的范围极大(而且相互矛盾)的领土要求。我问他这些要求根据什么原则,他以少有的坦率态度答道:‘根据历史的原则,凡属有利于我们的就用语言的原则加以改正。’”〔L·B·纳米埃尔:《1848年:知识分子的革命》(1848:The Revolu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雷利历史讲座,1944年,见《英国学院议事录》,第30卷,伦敦,杰弗里·坎伯利奇,牛津大学出版社,第66页〕参阅《概览,1920—1923年》,第228页注③。
(452) 《和会史》,iv.418—419。
(453) 同上书,第276—277页。
(454) 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作为地理单位的历史和安纳托利亚的历史正好相反。在1919—1923年的安纳托利亚战争中,土耳其人违背协约国的意志胜利地维护了安纳托利亚的民族统一,他们赶走了希腊少数民族,消灭了塞夫勒条约设想的士麦那飞地(《和会史》,vi.53—54,11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仿效这种暴力先例,力图最后解决它的少数民族问题。
(455) 各少数民族在1938年的东欧各国总人口中的大致百分比如下:芬兰,11%;爱沙尼亚,12%;拉脱维亚,23%;立陶宛(梅梅尔除外),16%;波兰,31%;捷克斯洛伐克在第一次被瓜分前(除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外),33%;匈牙利,10%;罗马尼亚,25%;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除外),12%;保加利亚,10%;阿尔巴尼亚,可能为5%;希腊,12%;土耳其的欧洲部分(除有大量希腊少数民族的伊斯坦布尔外),无少数民族。
(456) 将近1/3的匈牙利民族不在特里亚农条约规定的匈牙利国境内,150万人在罗马尼亚,75万人在捷克斯洛伐克,50万人在南斯拉夫,特里亚农条约规定的匈牙利境内只有700万匈牙利人。纳伊条约规定的保加利亚,情形不那么突出,境内有525万保加利亚人,国界以外有50万人,如果把保加利亚-马其顿人包括在内则有100万人;在罗马尼亚有36万人;在南斯拉夫有7万纯保加利亚人和50万保加利亚-马其顿人;在希腊有8.2万马其顿人。1/3的阿尔巴尼亚人生活在国境以外,在南斯拉夫有50万人,在希腊有1.9万人。土耳其人中有1 800万在土耳其,50余万人在保加利亚,19万人在希腊。关于东欧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见下文,原著第332页注②,即本书第469页注①。——译者
(457) 参阅L·B·纳米埃尔:《1938—1939年外交序曲》〔(Diplomatic Prelude,1938—1939),伦敦,麦克米伦,1948年版,第17页注①〕。关于东普鲁士的殖民地性质,见《和会史》,ii.289—290,以及莫罗:《德国—波兰边界的和平解决》,第223—225页。
(458) 见《和会史》,ii.210,vi.255—256。纳粹政府早就准备发展东普鲁士作为军事基地〔见1934年9月29日勃劳希契的备忘录:《阴谋与侵略》,vi.280—281(3585—PS)〕,如果在进攻波兰以前兼并但泽,势必就要从东普鲁士实行兼并〔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v.481—483(137—C);译载《文件,1939—1946年》,i.97;参阅《阴谋与侵略》,vi.945—950〕。
(459) 纳米埃尔:《外交序曲》,第88页;《每日电讯报》,1939年3月24日。希特勒“有一次对雷德尔说:‘在陆地上我是英雄,在海上我是懦夫’”〔安东尼·马丁森:《希特勒及其海军将领》(Anthony Martienssen:Hitler and his Admirals),伦敦,赛克和沃伯格,1948年版,第2页〕。“攫取西普鲁士是柏林所干的掠夺行为中最情有可原的一项……即使拿破仑在大败普鲁士之后也未敢改变这个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必然结果……现在经过一个世纪之后,西普鲁士与它两边的德国土地的联盟比任何时候更为牢固,如果我们不按拿破仑的先例,那是很不明智的……即使欧洲所有的其他问题都得到公正的解决,光是西普鲁士本身就足以使全欧洲陷入另一次大战。”A·J·汤因比:《民族和战争》(Nationality and the War),伦敦,登特,1915年版,第75页。
(460) 但泽在10世纪至12世纪之间从一个渔村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1308年它被条顿骑士团占领,1361年它成为汉萨同盟的成员之一;1466年它被条顿骑士团根据托伦条约割让给波兰。从1466年以后,它是在波兰宗主权下的一个自由城市,直到1793年第二次瓜分波兰后被普鲁士取得为止。在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时,由于普鲁士取得了一个“普鲁士走廊”,即连接勃兰登堡和东普鲁士的西普鲁士,但泽便和波兰分开了,只是由于俄国对普鲁士的猜忌,但泽才能在1793年以前维持它那岌岌可危的分离地位。1807年拿破仑根据提尔西特条约把但泽从普鲁士划分出来。在法国的保护下,恢复它的自由市地位。1814年普鲁士又把但泽夺回。1919年它又一次恢复自由市地位,置于国际联盟的保护下。见《和会史》,ii.291—293,366—367,383,391—392;vi.257—261;莫罗:《德国—波兰边界的和平解决》,第2章。
(461) 梅梅尔是条顿骑士团在1252年建立的,先后是条顿骑士团以及普鲁士历代公国和王国的一部分,直到1919年。当时它被德国割让给协约国,但在1923年它又被立陶宛夺取,主权于1929年转给立陶宛,条件是梅梅尔享有地方自治权。《和会史》,ii.290—291,366—367,391;vi.247—248;《概览,1920—1923年》,第256—261页;莫罗,前引书,第13章。
(462) J·F·C·富勒:《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J.F.C.Fuller:The Second World War,1939—1945),伦敦,艾尔和斯波蒂斯伍德,1948年版,第48页。
(463) “实际上德国总有理由和波兰发生争执的。但是按理有可能,也需要,把这些理由减少到最低限度。在这种情况下,波兰人避免和俄国发生一切可能发生纠纷的原因,那是明智的,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在某些问题上承认俄国人提出来的要求在他们看来是不公正的。尤其是利用俄国暂时的软弱地位,在未经边境民族明确表示其愿望前就兼并这些民族,那是危险的。这种行动在空间上是把俄国和德国分开了,在精神上却是把它们结合起来了,很容易导致一次新的而且是最后的瓜分波兰,这一次任何人间的力量都无法挽救波兰了”(H·J·P·佩顿语,载《和会史》,vi.240。这个预言发表在1924年)。
(464) 见威斯克曼:《捷克人和德国人》,第83页;A·J·P·泰勒:《哈布斯堡王朝,1809—1918年》(A.J.P.Taylor: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第2版,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48年版,第250页。
(465) 《和会史》,iv.356—363。
(466) 参阅希特勒1939年4月28日在帝国议会的演说:“布尔什维克侵略欧洲的桥梁”、“一直延伸到德意志帝国境内的堡垒”〔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612—1613;《文件,1939—1946年》,i.222—223;参阅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第1488页,第1519页,第1597页,以及《概览,1935年》,i.296〕。
(467) 见《和会史》,iv.273—274;T·G·马萨里克1915年4月的机密备忘录“独立的波希米亚”,载R·W·塞顿-沃森写的《马萨里克在英国》(Masaryk in England),剑桥大学出版社,1943年版,第129页;麦卡特尼:《匈牙利和它的继承国》,第51—53页。
(468) 见《和会史》,iv.273;R·W·塞顿-沃森:《马萨里克在英国》,第45页,第23页;参阅《概览,1937年》,i.406。
(469) 《和会史》,i.335—339;iv.104—105,135;vi.266—274,283注;《概览,1920—1923年》,第271—272页。
(470) 1933年12月7日在新扎姆基的演说。麦卡特尼:《匈牙利和它的继承国》,第249页。
(471) 《和会史》,i.356;iv.139,160,489;vi.246。
(472) 哈尔福德·J·麦金德爵士:《民主的理想和现实》(Sir Halford J.Mackinder: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哈蒙斯沃思,企鹅书局,1944年版,第118页。
(473) 参阅马萨里克的战时备忘录,载R·W·塞顿-沃森:《马萨里克在英国》,主要是第130页,第193—196页。
(474) 《和会史》,vi.318。参阅温斯顿·S·丘吉尔:《余波》(Winston S.Churchill,The Aftermath),伦敦,巴特沃思,1929年版,第13章。
(475) 贝奈斯1933年12月7日在新扎姆基的演说。麦卡特尼:《匈牙利和它的继承国》,第249页。
(476) 关于这整个问题,见《和会史》,第5卷,第2章,第4卷,第434—435页;《概览,1920—1923年》,第213—225页;麦卡特尼:《民族国家和少数民族》;雅各布·鲁宾逊等著:《少数民族条约是失败的经验吗?》(Jacob Robinson and others:Were the Minorities Treaties a Failure?),纽约,犹太事务学会,1943年版。如果把土耳其算作东欧国家,那么在少数民族待遇问题上承担相似国际义务的惟一其他国家就是伊拉克,1932年英国的委任统治结束,伊拉克加入国际联盟时承担了此种义务(《概览,1934年》,第208—211页)。
(477) 马萨里克:“独立的波希米亚”,1915年4月的秘密备忘录,载R·W·塞顿-沃森:《马萨里克在英国》,第130页。
(478) 在1939年3月以前的20年间,英国和德国占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出口贸易的一半,进口贸易的3/4。见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波罗的海国家》,第125—127页,第164—1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