śaya
我们首先要声明,这四种形式虽然见于《梵语千字文》、《梵唐消息》和《梵语杂名》,实际上却不是什么“梵语”,是在任何梵文作品里都找不到的。它们都是外来的借字。
但是究竟是从哪种语言里,在什么时候借来的呢?这个问题和中国纸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来研究一下。śaya(舍也)这个字很怪,在我们知道的与中亚细亚有关的语言里找不到类似的字。关于这个字的来源我们目前还不能有什么肯定的意见,现在先不谈。我们在这里先谈其余的三种形式。我们上面已经说到,阿拉伯文纸叫做kāghad,波斯文叫做kāghaz或 kāghiz。只从字形上也可以断定,kākali,kakali和kakari和阿拉伯字和波斯字是一个来源。在印度1395年12月7日的一个马拉提(Marathi)写本里用了kāgad这个字来表示“纸”。在耆那教的著作里也很早就有kāgada和kadgala这两个表示“纸”的字。1396年写成的一个 Ṛṣabhadevacarita 钞本里有kāgad这个字[67] 。在现 代印度语言里,印地文“纸”是patra和kaga  或kāgad[68] 。patra是梵文,就是上面谈过的“贝叶”。乌尔都文是kāgaz,泰米儿文是kāgidam,马拉亚拉文是kāyitam,坎拿大文是kāgada。这些字和kākali,kakali和kakari也都是一个来源,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时间来说,义净和礼言收到他们的著作里的那几个“梵文”的“纸”字比起以后印度方言里的“纸”字至少要早六七百年,是它们的祖宗。就形式来说,义净和礼言的“纸”字最后一个音节是-li或-ri,而不像后来印度方言里的“纸”字以-d或-
或kāgad[68] 。patra是梵文,就是上面谈过的“贝叶”。乌尔都文是kāgaz,泰米儿文是kāgidam,马拉亚拉文是kāyitam,坎拿大文是kāgada。这些字和kākali,kakali和kakari也都是一个来源,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时间来说,义净和礼言收到他们的著作里的那几个“梵文”的“纸”字比起以后印度方言里的“纸”字至少要早六七百年,是它们的祖宗。就形式来说,义净和礼言的“纸”字最后一个音节是-li或-ri,而不像后来印度方言里的“纸”字以-d或-  收声。无论是l或r,d或
收声。无论是l或r,d或  ,大概都代表一个印度语言里不存在的辅音。究竟从哪种语言里借的这个字呢?过去有的学者认为,波斯字是源于中国,阿拉伯字又源于波斯。这一点我们已经谈到过。有的学者认为,这说法不正确,波斯字和阿拉伯字都源于土耳其文,原义是“树皮”。 B. Laufer就这样主张,他从土耳其方言里举出了许多例子[69] 。但是这种说法我们也不能同意。在中亚细亚和新疆新发现的古代土耳 其文(维吾尔文)残卷里我们找到这个字的更古的形式:kägdä[70] ,kagda。这个字可能并不是什么土耳其字,而是从粟特文kāγδi (k'γdyh) 转化成的。我们都知道,粟特文是一 种属于伊朗语系的语言,那么,土耳其文起源说也恐怕就很难成立了[71] 。
,大概都代表一个印度语言里不存在的辅音。究竟从哪种语言里借的这个字呢?过去有的学者认为,波斯字是源于中国,阿拉伯字又源于波斯。这一点我们已经谈到过。有的学者认为,这说法不正确,波斯字和阿拉伯字都源于土耳其文,原义是“树皮”。 B. Laufer就这样主张,他从土耳其方言里举出了许多例子[69] 。但是这种说法我们也不能同意。在中亚细亚和新疆新发现的古代土耳 其文(维吾尔文)残卷里我们找到这个字的更古的形式:kägdä[70] ,kagda。这个字可能并不是什么土耳其字,而是从粟特文kāγδi (k'γdyh) 转化成的。我们都知道,粟特文是一 种属于伊朗语系的语言,那么,土耳其文起源说也恐怕就很难成立了[71] 。
义净于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启程到印度去,于武后证圣元年(695)回国,来去都是海路。他接触到这个“梵文”的“纸”字决不会是在新疆或中亚细亚一带地方,而是在印度。可见在7世纪末叶印度语言里已经有了“纸”字了。过去一般人都以为伊斯兰教徒于8世纪后进入印度,是他们把纸带到印度去的,kāgaz、kāgad、kāga j等字也是在这时候传入印度的。现在看起来,这说法是丝毫也站不住了。
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推测,印度既然至迟在7世纪末叶已经有了“纸”字,那么纸这个东西本身也应该至迟在7世纪末叶就已经到了印度。事实上正是这样。证据也是在义净的书里找到的。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二:
其伞可用竹织之,薄如竹簟一重便得,大小随情宽二三尺,顶中复作,拟施其柄。其柄长短量如盖阔。 或可薄拂以漆,或可织苇为之,或如藤帽之流,夹纸亦成牢矣。[72]
必用故纸,可弃厕中。既洗净了,方以右手牵其下衣。[73]
卷四:
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74]
《南海寄归内法传》这部书主要讲的是南海方面的情形,特别是印度的情形,但是有的地方措辞模糊,不知道他究竟说的是什么地方。上面引的三条不一定全说的是印度。但是最后一条说的是印度却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下文还有“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从这里可以看出,义净到印度以前,换句话说,也就是7世纪末叶以前,纸 已经到了印度。他在印度接触到“梵文”的“纸”字,也就不足怪了[75] 。
以上谈的是中国纸输入印度的问题。造纸法怎样呢?在这方面我们的材料就比较少,很难做出什么结论。上面已经说到,至迟在7世纪末叶印度已经有了纸。这些纸是中国去的呢?还是印度人民制造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当时大部分的纸是从中国去的,即便不是全部都是从中国去的话。至于造纸法是否已经输入,我们目前还不敢说。无论如何,造纸法的输入一定晚于纸。怛逻斯之役是在751年,上距义净回国已57年。在这次战役中有中国造纸工人被俘,造纸法因而传入阿拉伯,又从阿拉伯辗转传入印度也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度以后,虽然还不能一下子就代替了旧日那些贝叶、树皮之类的东西,但自11世纪末叶起,印度纸写本的数目就逐渐多了起来。正如在新疆一带,在印度我们也可以看出纸和那些古旧的书写材料斗争的情形,以及纸逐渐占上风的情形。纸的胜利就表示文化传播的加速和扩展。等到中国发明的印刷术,不管是直接地或是间接地,传入印度以后,那更是锦上添花,纸与印刷术配合起来,对文化传播和推进的作用就更大了。
至迟在15世纪初年印度已经建立起自己的造纸工业。明初马欢随郑和下西洋,于1406年到了印度孟加拉。在他著的《瀛涯胜览》里,他记述榜葛剌(孟加拉)的纸:
一样白纸,亦是树皮所造,光滑细腻,如鹿皮一般。[76]
巩珍也是随郑和下西洋的一个人,在他的《西洋番国志》里,也说 到孟加拉的纸:“一等白纸,光滑细腻如鹿皮,亦有是树皮所造。”[77] 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谈到孟加拉的出产,“有桑皮纸”。我们上面已经说到过在敦煌附近发现的公元前1世纪用桑皮织成的布,蔡伦用来造纸的原料中也有树皮一项。现在印度造纸用桑皮,其一脉相传的痕迹可谓显而易见了。在《瀛涯胜览》的另一个本 子里,记述稍有不同:“布有白者,树皮制成,腻滑光润如鹿皮。”[78] 《皇明世法录》卷八十一也说:“白树皮布,腻润与鹿皮等。”这里说的显然都是一件东西;但是为什么有的书上说是纸,有的又说是布呢?这种用桑树皮制成的纸既然“腻润与鹿皮等”,把它误看成布,也是很可能的。
中国造纸法输入印度以后,就逐渐发展起来。到现在印度造纸工业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规模。除了机器造纸以外,手工造纸业仍占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专门机构来鼓励推动这种手工业。我并不是说,中国造纸法传入印度以后就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中间也有过许多改进与发展;但是无论如何,最 初的方法总是从中国传去的,中国造纸法对于印度总算是源远流长了[79] 。
以上根据现有的材料简略地把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度的经过追寻了一下。将来有了新材料,特别是考古方面的材料,本文里面许多说法说不定都要补充或修正的。我在本文一开头就说到,中国纸和造纸法的传布史是一个极大而又极有意义的题目,同时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题目,连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度的这个小题目也有很多问题。我现在的这个尝试只能算是一个开端。
注释:
[1] 关于中国纸的历史参阅桑原骘藏《东洋文明史论丛》第93—118页,《纸の历史》;内藤虎次郎《东洋文化史研究》第75—84页,《纸の话》;劳幹:《论中国造纸术之原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傅振伦:《中国纸的发明》,《历史教学》1955年8月;袁翰青:《造纸在我国的起源和发展》,《科学通报》,1954年12月号;王明:《蔡伦与中国造纸术的发明》,《考古学报》,第8册。
[2] Th. Lindner,《世界史》,第4册,第8节。
[3] Thomas Francis Carter,《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 New York, 1925,第一章。
[4] 《后汉书》,卷一百八,《蔡伦传》说:“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东观汉纪》卷二十《蔡伦传》注:“案一本作伦典尚方作纸,用故麻名麻纸,木皮名谷纸,鱼网名网纸。”实际上,这种造纸的方法可能已经在民间肇端,蔡伦只是把这方法提高了一步,集其大成。《学斋占毕》卷二,纸笔不始于蔡伦、蒙恬:“又如蔡伦乃后汉时人,而前汉《外戚传》云:赫蹄书,注谓赫蹄乃小纸也,则纸字已见于前汉,恐亦非始于蔡伦。”
[5] 印度学者P. K. Gode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纸输入印度的论文:《中国纸输入印度考》(Migration of Paper from China to India ), 1944,但不详细。
[6] 贝鲁尼:《印度》(Alberuni 's India ), ed. by Dr. Edward G. Sachau, London 1914, p. 171。
[7]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一,页八五九中(下面缩写为  51,859b)。
51,859b)。
[8]  51,865b—c。
51,865b—c。
[9]  50,714c。
50,714c。
[10] 贝鲁尼《印度》,p. 171。
[11]  54,1102a。
54,1102a。
[12] Richard Pischel,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Kalidāsa ’s Śakuntal ā),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Vol. 16, 1922, iii, 18, 3—4。
[13]  51,864b。
51,864b。
[14] 同上。
[15]  54,229b—c。
54,229b—c。
[16]  50,238a。
50,238a。
[17]  50,428c。《佩文韵府》卷一百六:“梵夹,贝叶经也。以板夹之,谓之梵夹。”所以贝叶经都以夹计。“夹”有些本子作“甲”。
50,428c。《佩文韵府》卷一百六:“梵夹,贝叶经也。以板夹之,谓之梵夹。”所以贝叶经都以夹计。“夹”有些本子作“甲”。
[18]  50,430b。
50,430b。
[19]  50,432c。
50,432c。
[20]  50,437c。
50,437c。
[21]  50,456c。
50,456c。
[22]  50,718b。
50,718b。
[23]  50,719a。
50,719a。
[24] 参阅《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列传》,天竺国。
[25]  51,981b。
51,981b。
[26]  50,734b。
50,734b。
[27] 参阅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附录。
[28] Aurel Stein,《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 ), Oxford 1921, p. 650。
[29] Aurel Stein,《西域考古图记》pp. 673—674。参阅A. Hermann,《楼兰》(Loulan ), Leipzig 1931, p. 110;Aurel Stein, 《西域考古记》(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 ), London 1933, p. 188;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33页。
[30] 参阅姚士鳌:《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辅仁学志》第一卷第一期,第75—80页;Aurel Stein,《西域考古图记》,pp. 673—674;A. F. Rudolf Hoernle,《谁是褴褛纸的发明者?》(Who was the Inventor of Ragpaper ), JRAS., 1903。
[31] 关于康居与粟特(Sogdiana)异同的问题,请参阅白鸟库吉《粟特国考》,王古鲁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32] 《北史》卷九七《西域传》,字句几乎完全一样。
[33] 粟特文纸写的残卷在新疆一带发现的很多,但时代都比较晚。参阅《粟特文残卷》(Codices Sogdiani ), Monumenta Linguarum Asiae Maioris, III, par E. Benveniste, Copenhague 1940;《粟特文残卷》(Textes Sogdiens ), Mission Pelliot en Asie Centrale, série in-quarto, III, Paris 1940。其他零星散见各杂志的还不少。
[34] 见Éd. Chavannes,《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发现的中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 ,d 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 Nos 706—708。
[35] 同上,Nos 710—719。
[36] 按咸熙系魏纪元,魏亡于咸熙二年。咸熙三年和咸熙五年之出现,恐系人不知,或有意用之。
[37] 参阅August Conrady,《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中文写本及其他零星物品》(Die chinesischen Handschriften 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s in Lou -lan ), Stockholm 1920。
[38] 参阅同上,p. 33;A. Hermann,《楼兰》,pp. 109—110。
[39] 《中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 ), deuxième section: documents de l'époque des Tsin, No. 896, No. 910, No. 912。
[40] 黄文弼:《高昌》,第一分本,《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二,考古学第一辑,《新疆发现古物概要》。明高濂《遵生八笺》:“高昌国金花笺亦有五色,有描金山水图者。”可见高昌又以金花笺著名了。
[41] 香川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
[42] 《吐火罗文残卷》(Tocharische Sprachreste ), herausg. von E. Sieg und W. Siegling, Berlin und Leipzig 1921。
[43] 黄文弼:《高昌》,第一分本。
[44] 黄文弼:《高昌》,第一分本;《吐火罗文残卷》,I. Band, Die Texte, p. IV。
[45] 《西域考古图谱》。
[46] Gode,《中国纸输入印度考》,pp. 209—210引用Katre, Indian Textual Criticism p. 135, Katre原书未见。
[47] 《和阗文残卷》(Codices Khotanenses ), Monumenta Linguarum Asiae Maioris II, ed. by H. W. Bailey, Copenhagen 1938。
[48] M. Aurel Stein,《沙埋和阗废址记》(Sand -buried Ruins of Khotan ), London 1903, p. 296 sqq, 404,416;《古和阗》(Ancient Khotan), Oxford 1907, p. 135, 247, 269 sq. 369, 426。
[49] 这号码是Chavannes,《中文文书》里面的。
[50] 关于这次战役的考证,参阅姚士鳌:《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辅仁学志》第一卷第一期;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怛逻斯战役和它的影响》。
[51] 贝鲁尼:《印度》,p. 171。
[52] 《两个回教游历家关于古代印度及中国的记述》(Ancient Accounts of India and China by two Mohammedan Travellers ), Transl. by Eusebius Renaudot, London 1733, p. 14。
[53] B. Laufer:《中国伊朗文化交流》(Sino -Iranica ), Chicago 1919, pp. 557—559;Karabacek和Hoernle (JRAS., 1903, p. 671) 都同意这说法;Philip K. Hitti:《阿拉伯民族史》(History of the Arabs ), p. 414也同意。
[54] 《海国图志》,正集,中,卷二十三。
[55] 《伊朗语言学纲要》(Grundriss der iranischen Philologic ), 1. Band, 2. Abteilung, p. 7。
[56] 关于中国纸币,参阅Laufer,《中国伊朗文化交流》,pp. 560—564;Henry Yule:《马可波罗游记》(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 vol. l, pp. 426—430。
[57] Henry Yule:《马可波罗游记》,vol. l, p. 423。
[58] 见Henry Yule:《东域记程录丛》(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 vol. IV, p. 112. 其他中世纪西方旅行家谈到中国钞的还不少,例如13世纪的阿尔明尼亚的海顿(Hayton)(见Yule:《东域记程录丛》vol. I, p. 259);14世纪意大利的裴哥罗梯(Francis Balducci Pegolotti)(见同书,vol. III, pp. 149—151)。
[59] 有的印度学者认为印度在纪元前3世纪已经有了纸;参阅H. R. Kapadia:《古文书学大纲》(Outline of Palaeography ), Bombay University Journal, 1938, May, p. 105。这说法缺少可靠的根据,印度学者也不承认;参阅P. K. Gode:《中国纸输入印度考》,p. 218。
[60]  54,1190a。
54,1190a。
[61]  54,1196b—c。
54,1196b—c。
[62]  54,1191a。
54,1191a。
[63]  54,1195b。
54,1195b。
[64]  54,1201b。
54,1201b。
[65]  54,1213c。
54,1213c。
[66]  54,1233a。另外一个本子作kakali。
54,1233a。另外一个本子作kakali。
[67] P. K. Gode:《中国纸输入印度考》,p. 215,218。
[68] S. H. Kellogg:《印地语法》(A Grammar of the Hindi Language ), London 1938, p. 40。
[69] B. Laufer:《中国伊朗文化交流》,p. 559。
[70] F. W. K. Müller:《古代土耳其文(回鹘文)论丛》(Uigurica II), APAW. 1910, S. 70,《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
[71] A. von Gabain:《古土耳其语法》(Alttürkische Grammatik ), Leipzig 1941, p. 313。
[72]  54,215b。
54,215b。
[73]  54,218b。
54,218b。
[74]  54,226c。
54,226c。
[75]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51,11a):“净于佛逝江口升舶附书,凭信广州,见求墨纸,抄写佛经,并雇手直。”可见义净曾在佛逝江口向中国索要过纸墨。
51,11a):“净于佛逝江口升舶附书,凭信广州,见求墨纸,抄写佛经,并雇手直。”可见义净曾在佛逝江口向中国索要过纸墨。
[76] 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商务印书馆版,第61页。
[77] 此条蒙向达先生抄示,谨此志谢。参阅《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第 52页。
[78] 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六册,第503页。
[79]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许多地方都谈到造纸。在第1卷第4篇第13章VIII《近代手工制造业》里他谈到英国贮藏了无数的褴布用来造纸(郭大力、王亚南译本第1卷,第564—565页)。在第13章I《机器的发展》里,他说,在中国和印度造纸工业还有两种不同的古亚西亚的形态(同书,第459页)。
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
蚕丝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发现之一,在全世界各国中,中国是最先发现蚕丝的国家。正如我国其他伟大的发明或发现一样,它一旦被发现了,就不会停留在本国,而是向外国传布。中国蚕丝的向外传布可能在公元前三四百年以前已经开始了。丝的贸易对古代中西的交通,甚至对古代中西各国的历史有极大的影响。横亘欧亚的“丝道”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中国蚕丝传布的历史一向是东西各国学者一个极其喜爱的研究题目。本文想研究的只是这个大题目中的一个小题目,一个过去还没有任何人系统地深入地研究过的小题目: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问题。中国蚕丝的输入印度在中印两个伟大民族文化交流史上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我们必须研究清楚。
要想谈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就要牵涉到中国蚕丝输入波斯的过程,所以本文就包括以下几个项目:
一、中国古代蚕丝的发现。
二、蚕丝在古代西域的传布。
三、中国蚕丝输入波斯的过程。
四、蚕丝在古代西南的传布。
五、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过程:
南海道。
西域道。
西藏道。
缅甸道。
安南道。
一 中国古代蚕丝的发现
根据中国向来的传说,黄帝的妃子 嫘祖(时间很难确定,但总在公元前两千多年)是首先发现蚕丝的人[1] 。但是这决不会是事实。像蚕丝这样伟大的发现决不会是一个人在短期间就可以完成的。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活动中与大自然有密切的接触,经过长期的细致的观察,逐渐发现某一种虫子结成的茧可以拿来抽成丝,而这丝又可以织成衣料。这就是所谓“野蚕”丝。再进一步才把“野蚕”变为“家蚕”。这经验是劳动人民穷年累月积累成的,把它说成是某一个妃子的功绩是不合客观发展规律的。
但是这传说也有它的意义,它暗示给我们,中国人民一定在极早的时候就发现了蚕丝。因为黄帝相传是汉族的始祖,古代人民把蚕丝的发现权推到始祖的妃子身上,可见他们也认为这发现是由来已久了。而 事实也正是这样。从“卜辞”来看,商代已经有了桑树 ,有了丝和帛[2] 。金文里也有“丝”字,是像成束的丝的形状的[3] 。虽然还没有发现单独用的“丝”字,但是作偏旁用是常见的。所以至迟在商代(公元前1563年 〔?〕—公元前1066年〔?〕)中国已经有了养蚕织帛的手工业[4] 。《晋书》卷一六《食货志》:“〔辛纣〕宫中以锦绮为席,绫纨为荐。”假如这话靠得住的话,在商代的王宫里,丝的应用已经很广了。
中国最古的书里也都有关于丝的记载。《尚书·禹贡》:
兖州: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贡漆丝,厥篚织文。
青州:岱畎丝、枲、铅、松、怪石……厥篚檿丝。
徐州:厥篚玄纤缟。
扬州:厥篚织贝。
荆州:厥篚玄纁、玑、组。
豫州:厥贡漆、枲、、纻。厥篚纤纩。
《禹贡》 不是禹时代的书,这是学者们所公认的。但是至晚也是周代的书[5] 。从这记载里可见周代蚕丝分布之广。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都产丝。当时的天下没有后代这样大,这样多的州都产丝,几乎可以说是遍天下了。
在《诗经》里也有许多地方谈到丝[6] 。有没有染色的“素丝”,也有染过色的丝(《邶风·绿衣》: “绿兮丝兮”)。丝可以制衣服,也可以制带子(《曹风·鸤鸠》:“其带伊丝”),应用很广。而且还可以用来交换其他的物品。《卫风·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可以为证。丝已经织成了锦(《卫风·硕人》:“衣锦褧衣”)[7] ,在纺织技术方面又进了一步。《诗经》里也谈到蚕(《豳风·七月》:“蚕月条桑”;《大雅·瞻卬》:“休其蚕织”)和桑(《鄘风·桑中》:“期我乎桑中”,“定之方中”,“降观于桑”;《卫风·氓》:“桑之未落”)。《礼记》里同样有关于蚕桑的记述:《月令》:“季春之月,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最古的子书里,像《孟子》、《墨子》、《庄子》等,都谈到丝。《 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8] 《墨子 》和《庄子》都是丝麻并举,这两种东西可能就是当时最普通的衣料[9] ,而丝似乎又比较贵重些,因为五十岁以上的老人才能穿丝衣服。《荀子》二十六《赋篇》还专为蚕写了一篇赋:“功被天下,为万世文。礼乐以成,贵贱以分。养老长幼,待之而后存。”对蚕也可以说是推崇备至了。
《周礼·天官冢宰》上:
典丝,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贾四人,徒十有二人。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此外还有“掌染丝帛”的染人。《冬官》:“设色之工五。”可见染丝的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天官·冢宰》下:
仲春,(天官内宰)诏后帅内外命妇始蚕于北郊,以为祭服。
《春秋》桓十四年《谷梁传》也说:“王后亲蚕,以共祭服。”蚕丝一定是在 日常生活中已占很重要的地位,王后才会每年亲自来举行养蚕的仪式[10] 。这种仪式一直 传了下来,汉、魏、晋、宋、北齐、后周、唐等朝代的皇后都举行过[11] 。蚕丝对中国人民生活的重要意义也概可想见了。
《春秋》桓十四年《谷梁传》也说:“王后亲蚕,以共祭服。”蚕丝一定是在日常生活中已占很重要的地位,王后才会每年亲自来举行养蚕的仪式。这种仪式一直传了下来,汉、魏、晋、宋、北齐、后周、唐等朝代的皇后都举行过。蚕丝对中国人民生活的重要意义也概可想见了。
以上列举的中国古书中关于蚕丝的记载在近代考古发现中得到了证明。我们知道,用丝织品或布料包裹铜器,在土里埋得时间久了,丝织品或布料就会凝结在铜器上,形成清晰的花纹。安阳出土的铜器上有的就有这样的花纹。瑞典的学者维维·希尔万(Vivi Sylwan)研究过一只铜斧和另一件铜器上的花纹,她的结论是,中国在殷代不但已经有 了丝,而且织丝的技术已经相当发达,在这以前必已有很长的历史了[12] 。过去有的学者认 为,中国在汉代还没有织斜纹的技术,这种技术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13] 。殷代铜器上的花纹证明这说法是不正确的。此外,中国考古学者在山西西阴村发掘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掘出了一个半割开的丝似的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 是极平直。”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但也没有什么证据断定它不是[14] 。假如立刻就断言,中国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养蚕业,似乎证据还薄弱一些;但是假如把考古学提供的这些证据和中国古代文献里那些记述结合起来看的话,恐怕没有人会否认中国蚕业已经有极长的历史这个事实吧。
二 蚕丝在古代西域的传布
古代西域是没有蚕丝的。《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
但是这只是说,当地不产丝,并不是说,那里根本没有丝。丝是有的,不过都是从中国内地传过去的。有名的横亘欧亚大陆的“丝道”就通过西域。
中国古代史籍里有很多关于丝传布到西域去的记载。中国皇帝最喜欢把丝织品“赐”给西域各国。《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说到,中国皇帝赐给单于“黄金、锦绣,缯布万匹”,又赐“彩缯千匹,锦四端”,“赐单于母及诸阏氏、单于子及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缯彩合万匹”,而且还是“岁以为常”。这种办法一直传下来。《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
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称扬坚之威德,并以彩缯赐诸国王。
《旧唐书》卷一〇四《高仙芝传》:
军到,首领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敕命,赐彩物等。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出诏书召慰,赐缯彩。
《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赐〔护密王〕紫袍金带七事,并杂彩五十匹。
到了明朝,皇帝们一直还是用这种办法,《明史》里有很多记载。为什么总是用这种办法呢?丝织品在西域一定是很贵重的东西,很被重视,中国皇帝才用它来拉拢西域各小国的 君长。《法苑珠林》卷四:“胡人见锦,不信有虫食树吐丝所成。”[15] 也足以证明,丝在西域人眼中是一种很奇妙神秘的东西。
最初丝传到西域,除了经过商人的运输以外,大概就通过这种赐的办法。长途跋涉,运输有困难。赐嘛,也只有君长贵族能够得到。所以传过去的丝一定不会太多,因而价钱也就不会便宜。只有酋长和贵族们能穿得起丝衣,一般老百姓是没有份的。许多旅行中亚的和尚对当地人民的服饰都有精确的记述。《高僧法显传》:
〔鄯善国〕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毡褐为异。[16]
玄奘记载得更详细,他几乎把每个他到过的国家的衣服材料都记下来了。 《大唐西域记》记载:阿耆尼国:“服饰毡褐”[17] ; 屈支国:“服饰锦(似为毡之误)褐”[18] ; 跋禄迦国:“细毡细褐,邻国所重”[19] ; 素叶水城:“人衣毡褐”[20] ; 窣利:“服毡褐衣皮  ”[21] ;睹货逻 国:“多衣
”[21] ;睹货逻 国:“多衣  ,少服褐”[22] ;迦毕试国:“服用毛
,少服褐”[22] ;迦毕试国:“服用毛  ,衣兼皮褐”[23] ; 活国:“衣服毡褐”[24] ; 呬摩咀罗国:“衣毡皮褐”[25] ; 钵铎创那国:“多衣毡褐”[26] ; 屈浪拏国:“多服毡褐”[27] ; 达摩悉铁国:“衣服毡褐”[28] ; 尸弃尼国:“皮褐为服”[29] ; 商弥国:“多衣毡褐”[30] ; 朅盘陀国:“衣服毡褐”[31] ; 乌锻国:“衣服皮褐”[32] ;佉沙国:“出细毡褐,工织 细毡
,衣兼皮褐”[23] ; 活国:“衣服毡褐”[24] ; 呬摩咀罗国:“衣毡皮褐”[25] ; 钵铎创那国:“多衣毡褐”[26] ; 屈浪拏国:“多服毡褐”[27] ; 达摩悉铁国:“衣服毡褐”[28] ; 尸弃尼国:“皮褐为服”[29] ; 商弥国:“多衣毡褐”[30] ; 朅盘陀国:“衣服毡褐”[31] ; 乌锻国:“衣服皮褐”[32] ;佉沙国:“出细毡褐,工织 细毡  毹”[33] ;瞿萨旦那国:“少服毛褐毡裘,多衣絁绸白毡”[34] 。法显和玄奘的记 载完全一致。当地人民的衣服不是毡(毛织品),就是褐(粗麻布)[35] 。
毹”[33] ;瞿萨旦那国:“少服毛褐毡裘,多衣絁绸白毡”[34] 。法显和玄奘的记 载完全一致。当地人民的衣服不是毡(毛织品),就是褐(粗麻布)[35] 。
君长的衣服怎样呢?他们穿的是绫罗锦绣和棉布(白叠)。《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又见《北史》卷九七,《隋书》卷八三):
其王索发,冠七宝金花,衣绫罗锦绣白叠。
《洛阳伽蓝记》卷五:
至于阗国,王头著金冠似鸡,帻头后垂二尺生绢广五寸以为饰。[36]
〔嚈哒国〕王著锦衣……嚈哒国王妃亦著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37]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胡密〕 住居山谷,处所狭小。百姓贫多,衣著皮裘毡衫,王著绫绢叠布。[38]
这里说得最清楚,对比最尖锐。平民中唯一的例外就是音乐家,可能是因为职业的关系,非穿漂亮一点不行。《唐书》卷二九《音乐志》记载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舞人和工人衣服上都有锦,这恐怕也只是为了君长们赏心悦目,不能以常情论了。
君长中也有不知道绢可以制衣服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彼王(箇识匿王)常遣三二百人于大播蜜川劫彼商(?) 胡,及于使命。纵劫得绢,积在库中,听从坏烂,亦不解作衣著也。[39]
这大概是因为他穿惯了“皮裘毡衫”,只能算作例外。
除了做衣料之外,绫、绢和锦等丝织品还可以用作交换货物的媒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记载,高昌王麴文泰赠给玄奘“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五百匹,充法师往还二十年所用之资”。此外还写给屈支等二十四国二十四封信,“每 一封书附大绫一匹为信,又以绫绢五百匹,果味两车, 献叶护可汗”[40] 。叶护可汗“又施 绯绫法服一袭,绢五十匹”[41] 。迦毕试王也赠给法师纯锦五匹[42]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也记载了 :“此胡蜜王兵马少弱,不能自护,见属大所管。每年输绢三千匹”[43] 。绢绫和黄金、银钱并举,绢还可以当作贡物来输送,这就充分证明,在古代西域,也和在中国内地一 样,在极长的时间内,绫和绢都是货物交换的媒介,和金钱同时流通[44] 。
以上谈到的那些绫、绢、锦等大概都是从中国内地运到西域去的,西域本地是不是也出产这些东西呢?中国史书上间或也有西域养蚕的记载。《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焉耆国:
养蚕不以为丝,唯充绵纩。[45]
《隋书》卷八三《西域》说高昌国“宜蚕”[46] 。耶律楚材《西游录》:
〔寻斯干〕有桑不能蚕,皆服屈眴。
有的是养蚕不能缫丝,有的有桑树而不能养蚕,这些国家绝不会织出绫、绢、缎、锦的。养蚕而又能缫丝的恐怕只有和阗一国。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二瞿萨旦那国:
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之,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蚕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诫曰:“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验。遂入瞿萨旦那国,止麻射伽蓝故地。方备仪礼,奉迎入宫。以桑蚕种留于此地。阳春告始,乃植其桑。蚕月既临,复事采养。初至也,尚以杂叶(饲)之。自时厥后,桑树连荫。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杀;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敢有犯违,神明不祐。遂为先蚕建此伽蓝。数株枯桑,云 是本种之树也。故今此国,有蚕不杀,窃有取丝者,来年辄不宜蚕。[47]
西藏也有这个传说,内容差不多:国王毗阇耶阇耶(Vijayajaya)娶中国公主哲捏霞(Pre-nye-shar)。她想把蚕带到于阗(Liyul)去,于是就在玛杂(Ma-dza)这个地方养了一些。中国大臣想从中破坏,告诉国王,蚕会变成毒蛇。国王听信了他的谗言,把蚕室放火烧掉。公主抢出了一些 ,后来缫出丝来,制成衣服,穿在身上,把详情告诉国王。国王大悔[48] 。这是不是只是一个传说呢?恐怕不是,这可能是个历史事实,因为正史里也有记载。《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于阗:
初无桑蚕,丐邻国,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许之。将迎,乃告曰:“国无帛,可持蚕自为衣。”女闻,置蚕帽絮中。关守不敢验。自是始有蚕。女刻石约无杀蚕,蛾飞尽得治茧。
这记载虽简短,但与《大唐西域记》完全相同,可见历史上是有过这样一件事情的。而事实上和阗是古代西 域唯一的养蚕出丝的地方,这传统一直维持下来,到现在还没有中断[49] 。
以上根据中国古代史籍和游记简略地叙述了一下中国蚕丝传布到西域去的情形。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的“探险家”在新疆一带作的考古发掘工作给中国古书里的记载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现在我就在下面按地域来谈一谈。
敦煌、玉门关及甘肃西部
自1900年至1916年英国的斯坦因(M. A. Stein)曾三次到新疆去探险。在这里他掘出了不 少极有价值的古代文物, 其中也有丝和丝织品。在敦煌 他找到丝信封[50] , 兵士的丝衣料[51] , 写在丝上的私人信[52] 。他还找到花锦[53] 和丝绣[54] 。 在敦煌千佛洞里他找 到的丝织品数量更多,其中有 装订书籍用的丝[55] ,作 画用的丝[56] , 捆经卷用的丝 带子[57] 。在这里也找到花缎[58] 和绫[59] ,也有丝绣 。[60] 在长城的极西端玉 门关一带他找到了写在丝上的私人书信[61] ,丝裹的窣利文纸卷[62]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千佛洞发现的丝织品上的花样可以明显地分为两类:绝大多数的花样都是中国风味的,但是其中也有一小部分,图案是波斯萨珊王朝特有的。丝既然是从中国内地传进来的,为什么花样会是波斯的呢?原因是,在中国第7世纪或第8世纪初期的丝织品的花样上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找到波斯萨珊王朝艺术的影响,一方面中国艺术影响了波斯艺术,另一方面我们也接受了波斯 的影响,这在其他方面也可以看到,丝织品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63] 。
斯坦因在玉门关找到一块没有染色的丝,虽然也有损伤,但是原有的两端的边缘都还保留下来。原长19吋半。在一端用早期贵霜王朝的婆罗米字体写着四个字,共11个音节,用的是深黑墨汁:
〔ai〕ṣṭasya paṭa giṣṭi ṣapariśa
第一个字意义不明,第二个字是“丝”,第三个字是“一虎口长”,第四个字是“46”(Lüders读作capariśa“四十”),总起来是“……丝长四十六虎口”。中国古代输出的丝都是卷起来的,假如每到 一处都打开来用尺量,那就未免太麻烦了。所以就在一端标明长度。[64] 但是四十六虎口究竟是多长呢?斯坦因另外在这里还找到一块写着中国字的丝条,上面的字是:
任城国亢 父绸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二十五两,直钱六百一十八。[65]
这丝条也是标明长度的。这里说的四丈又是多长呢?斯 坦因在敦煌找到两个后汉时代的木尺,每尺十寸,每寸二二点九公厘[66] ,那么一丈就是二公尺二公寸九公分,四丈就是九公尺一公寸六公分。估计当时输出的丝,不管是用中文标明长度,或是用印度文标明长度,这长度总应该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印度文标出的四十六虎口 可能就等于中国汉代的四丈,也就是可能等于九公尺一公寸六公分了[67] 。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标明长度的字是印度俗语,而字母又是婆罗米。这最少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贩丝的人可能就是印度人;第二,婆罗米字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想的,是随了佛教才传到西域的,而印度俗语在公元前后几十年内已经成为西域一带的商业通用语言了。
楼 兰
斯坦因在 这里找到了各种颜色的丝的碎片,找到写在丝上的驴 唇体字母的残卷 [68] 。 在第三次探险时他也找到了许多丝的断片[69] 和丝绣[70] 。最有趣的发现是一捆黄色绢,宽十八又四分之三吋,直径二又二分之一吋。这个发现很重要,因为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测出汉代输出的丝织品的形式,它的大小也合乎当时的规格。上面谈到“任城国亢父绸”,宽二尺二寸,每寸二二点九公厘,二尺二寸计五〇点三八公分,相当于一九点八三吋。这一捆丝织品宽度是十八又四分之三吋, 两下里一比较,相差无几,可能因为在地里埋藏过久,因而收缩了[71] 。
斯坦因在这里找到了丝织品, 从织的技巧上来看,有它的特点:都是经纬交错织成的,而不是斜纹[72] 。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却是这些丝织品的图案。正如在敦煌找到的丝织品一样,它的图案有中国的,也有波斯的,交互影响的痕迹灼然可见。
斯文赫定也在这里找到许多丝绸的碎片:有黄色 的,有海绿色的,有深蓝色的,还有棕色的;有的有花纹, 有的没有[73] 。此外他还找到几封写在纸上的信, 都与买绫有关[74] 。还有一个记载着“余彩七匹(?)”的木简[75] 。可 见绫、彩等丝织品在当地人民日常生活中已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了[76] 。
吐 鲁 番
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时,在吐鲁番附近阿思塔那(Astāna)村一个古代墓地里找到的纺织品几乎全是丝。死人全都用丝裹,有没有染色的,也有染过色的。本地或附近地带并不产丝,这些丝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是从中国内地。但是根据当时与内地交通困难的情况来估计,可能有一部分丝来自和阗和粟特。至于作为死人遮面 巾的印花的丝,从花样上来看,是萨珊王朝的,可能是从西方输入的[77] 。
此外,在吐鲁番附 近的吐峪沟(Toyuk),斯坦因也找到了丝织品,是淡蓝色的锦[78] 。
黑城(Khara-khoto)
斯坦因在这里找到许多丝织品的断片,其中有缎子, 有绫,有绢;有蓝色的,有土灰色的,有的还印着图案——龙和火焰[79] 。
高有玛尔(Koyumal)和巴士—高有玛尔(Bāsh-Koyumal)
斯坦因在这里找到了印度Pōthī式的丝的残页,是用印度笈多体婆罗米字母写的梵文佛典 。这是第一个写在丝上的佛典,从书写材料上来看,是有特殊意义的[80] 。
磨朗(Mīrān)
在这里 斯坦因找到的丝比较少,其中有锦,有锻子,有薄纱似的丝,有丝绣[81] 。
和 阗
在古代西域,和阗是以产丝著名的,是最早从中国内地输入养蚕法的。因此,在这里发掘出来的丝的断片也就特别多,在附近地带只要发掘过的 地方都有丝。在安得悦(Endere),斯坦因找到了绢旛和锦缎[82] 。 在神像面前找到许多纺织品,有丝也有棉, 大概是敬神用的[83] 。在尼雅 (Niya)找到很细致的丝织品[84] ,还有穿着丝衣服的木偶[85] 。 在和阗河左岸马扎尔塔格(Mazār-Tāgh)找到锦[86] 。
在丹丹乌里克(Dandān-Uiliq)同样找到丝[87] 。斯坦因在这里发见一块画版,中央画着一个盛装贵妇,头戴高冕,女郎跽于两旁。画版一端有一只篮子,里面装满了果实似的东西。左边的侍女用左手指着贵妇人的冕。这画什么意思呢?这贵妇人 无疑就是我们上面谈到的把蚕种藏在帽子里偷传到和阗去的中国公主[88] 。她对当地人民有大功,他们忘不掉她,奉她为神明,又把她画在画版上。
斯坦因还在和阗北面一座古庙的废址里 发见了一幅壁画,画着一个四臂蚕神,就是中国古书上所谓“先蚕”[89] 。也可以看出,蚕丝在当地人民生活中占多么重要的地位了。
近代考古发掘工作在新疆一带发现丝的地方当然不限于上面说到的这几处,为了叙述简短起见,就不一一列举了。中国古籍里关于蚕丝在西域传布情形的记载与考古发掘的结果可以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我们可以看到,西域最初虽然没有丝,但是由于商人的转运,君王的“赏赐”,蚕丝终于传过去。靠近古代交通大路的地方都传到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蚕丝的输出并不停留在西域,西域只能算是一个过道,通过这个过道,更向西方传去,一直传到波斯、希腊和罗马,一直传到印度。
三 中国蚕丝输入波斯的过程
古代波斯一方面和中国在文化上关系很密切,另一方面又和印度有极频繁的文化交流。所以要想谈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问题,就不能抛开中国蚕丝输入波斯的问题不谈,这两个问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谈到中国蚕丝与波斯的关系,首先,应该从横亘中亚的“丝道”谈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与罗马间通过“丝道”进行的丝的贸易有极重大的意义。但是因为路途遥远,山川阻隔,所以这贸易并不容易。又因为中间国家很多,而且这些国家又忽兴忽灭,忽分忽合,变化非常剧烈,每个国家都想从丝的贸易上捞一把,这就更增加了贸易的困难。波斯就是想从中渔利的许多国家中的一个。“丝道”自木鹿(Merv)至斯宾国(Seleucia)一段自公元前129年至公元后224年为安息所控制,继之而起的是萨珊王朝,一直到7世纪阿拉伯人兴起为止。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其(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又见《文献通考》卷三三九)
《三国志·魏志》卷三〇注引《魏略·西戎传》:
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
这说得非常明白,大秦想和中国直接贸易,但是安息却从中作梗。《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安息国:
永元九年(97)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又见《晋书》卷九七)
从表面上来看,这只是一段简单的叙述,似乎没有什么。但是假如和安息人想垄断丝的贸易这件事实结合起来看,里面就有了文章。焉知不是安息人故意危言耸听吓唬甘英,使他望而却步不能够直接与大秦交通呢?
安息国的这种垄断政策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促使大秦开辟海路直通中国。《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
第二,促成了蚕种的西传。史家柏罗科劈斯(Procopius, 500—565)记载:有印度国的和尚到了君士坦丁堡,见到哲斯丁(Justinian)皇帝,告诉他,他们有办法可以使罗马人不再向波斯或其他国家购买丝货。他们曾在一个叫做赛林达(Serinda)的地方住过很久,他们曾悉心研究,如何使罗马境内也可以产丝。产丝的是一种虫子。假如能把虫卵带至罗马,就可以孵化成虫子。皇帝答应重赏他们,只要他 们把这种虫子运到罗马。他们果然运到了,从此罗马境内也 有了丝业[90] 。索那拉斯(Zonaras)记载了同一个故事[91] 。拜赞 庭的梯俄方内斯(Theophanes)也记叙了一个类似的故事[92] 。所谓赛林达就是指的新疆一带,再缩小一下范围,可能就是和阗,因为和阗是最先从中国内地输入蚕种的。在古代,和阗一带的确住过印度人,那么印度人从这里把蚕种输入罗马也就不足怪了。
波斯既然位于“丝道”之上,中国的丝一方面通过波斯向西传,一方面当然也就传到波斯。传过去的方向,除了商贾转贩以外,还有中国皇帝的赠送。正如对待西域其他国家的君长一样,中国皇帝也喜欢用中国的丝织品赠送波斯国王。自汉代起,波斯与中国交通频繁,中国皇帝“赐”丝织品的记载在正史以及其他书籍里,例如《册府元龟》里面都可以找到。除了陆路通过“丝道”以外,还有海路。《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亦泛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93]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曾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但是这是司马迁时代的情况。以后丝就逐渐从海陆两路传到波斯。当地的人,首先是君长和贵族也就可以穿丝了。《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
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锦袍。
《周书》卷五〇《异域传》下:
王姓波斯氏,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锦袍。
《隋书》卷八三《西域传》也说:“〔王〕衣锦袍。”《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传》也同样说:“〔王〕服锦袍。”“丈夫”(男人)的巾帔,“两边缘以织成锦”(又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以上谈的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丝。养蚕缫丝的方法是不是也传过去了呢?据一些学者的意见,萨珊王朝(226—640 左右)末叶中国养蚕法传入波斯,而且很可能与蚕种的传入和阗有关[94] 。但是事实上可能比这还要早。《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谈到波斯的出产,里面有“绫锦”。《隋书》卷八三《西域传》记载波斯的出产,里面也有“锦”。《南史》卷七九《夷貊传》滑国:
普通元年(520)〔滑国〕遣使献黄师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
可见至迟在公元6世纪初叶以前波斯已经能织绫锦。《白孔六帖》卷八记载吐蕃贡波斯锦。可见在唐代波斯锦又通过吐蕃传入中国。同时玄奘更提供给我们可靠的证据。《大唐西域记》卷一一波剌斯国:
工织大锦、细褐、毹之类。[95]
这传统一直承继下来,地域逐渐扩大,到了明朝,波斯及附近地带有很多地方都能织锦了。
陈诚《使西域记》:
〔哈烈国Herat〕多育蚕,善为纨绮。木有桑、柳、榆、槐、松、桧、白杨。
《明史》卷三三二《哈烈传》:
多育蚕,善为纨绮。
《皇明世法录》卷八一哈烈:
地力宜桑与蚕,为纨绮,细密逾中国。
织纨绮的技术是从中国学去的,而能“细密逾中国”,这真可以说是青出于蓝了。
尽管波斯出产的锦很多又很好,但是中国究竟是出产锦的老地方,所以中国锦在波斯依旧享有盛名。波斯大诗人费尔多锡(Firdausī, 939—1020)在他的诗篇里提到中国锦,称之为dībā-ičīn。 他还提到一种特别细致的印花的中国丝织品,叫做parniyān[96] 。
一直到清代,波斯仍以产绸缎出名。魏源《海国图志》,正集,中,卷二三欧罗巴人原撰,林则徐译的《西印度西巴社国》(波斯国):
产米、麦、盐、丝发、五采地毡、羊毛、绸缎、磁器、纸、皮、宝石、铜、铁。
同书引《地球图说》:
〔白耳西亚国〕土产毡、毯、呢、羊毛、布、绸、缎、葡萄酒、羊、马、枣、铜、油、盐。
到现在,波斯绸缎仍然有名。在中国蚕丝传入波斯后的一千多年中,织丝的技术当然有不少改进与发展,对波斯人民的生活当然有很多的好处,追本溯源,不能不归功于中国人民。
波斯锦大概也传到印度。波斯文里有一个字kimxāw,亦作kamxāb,kamxā或kimxā ,意思是“锦”,可能是从中文借过去的,就是“锦花”两字的转化[97] 。这个字也许就是随了实物到了印度,在印地文里和乌尔都文里都有:kamkhvā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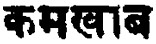 )。虽然只是一个借字,但是也可以透露中国锦在波斯和印度辗转传布的关系。
)。虽然只是一个借字,但是也可以透露中国锦在波斯和印度辗转传布的关系。
四 蚕丝在古代西南的传布
以上谈的是蚕丝在西域一带的传布以及传入波斯的情形。中国蚕丝传入印度是否只限于西域一路呢?当然不是。除海道外,过去也曾有人注意到缅甸道。但是从这一路输入印度的丝的来源问题却似乎还没有人谈到过。我觉得,这在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过程中,在中印交通史上,都是一个重要问题,应该研究一下。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蚕丝在古代西南传布的情况。
中国文化最初繁荣滋长于黄河流域。根据《禹贡》的记载,蚕丝最初也主要是传布在这一带。但是四川古名曰蜀。蜀字在甲骨文里是蚕的象形。扬雄《蜀王本纪》:“蜀王之先名蚕丛。”四川许多地名都有“蚕”字,像蚕崖、蚕陵等。为什么四川和蚕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呢?古代四川大概以产蚕著称,所以才名之曰蜀,而先王和许多地方的名字也都有“蚕”字。《禹贡》:荆州“厥篚玄纁、玑、组”。1949年春天在长沙市陈家大山一座楚墓里发掘出 一幅帛画,在一张长30公分宽20公分的丝织上画着一个古代妇女[98] 。可见至迟在公元前3世纪现在的湖北、湖南一带已经有了丝了。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
〔唐蒙〕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又见《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通志》卷一九七《西南夷序略》)
至迟在汉武帝时中国内地的丝织品(缯帛)已经传到现在的云南、贵州一带地方,为当地人民所喜爱。
到了汉朝末叶,四川丝业已经很发达。当时蜀锦名闻全国。左思《蜀都赋》赞美四川的锦:
贝锦斐成,濯色江波。
《文选》李善注引谯周《益州志》:
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
可见蜀锦之美丽。蜀锦既以美丽著称,当时必定是销行全国。山谦之《丹阳记》:
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布(疑是“市”字之误)于蜀,而吴亦资西道。
环氏《吴记》:
蜀遣使献重锦千端。
《神仙传》: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少有神道。尝在魏武帝坐。帝曰:“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敕使者增市二端。”须臾即得姜还,并获使报。
魏文帝诏:
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比,适可讶。而鲜卑尚复不爱也。自吾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亦有金薄、蜀薄来至洛邑,皆下恶。是为下土之物皆有虚名。
三国时,魏吴都到蜀去买锦,而蜀也用锦来赠送人。虽然曹丕对蜀锦有意见,认为它徒有虚名;但是蜀锦必有许多不可及的地方,否则《丹阳记》也不会说它“独称妙”了。《江表传》:
陆逊攻刘 备于夷陵,备舍舡步走,烧皮铠以断道,使兵以锦挽车,走入白帝。[99]
竟然以锦挽车,可见产量之多。实际上,当时三国鼎立,蜀的经济情况最差,锦几乎就是西蜀的唯一的经济来源。《诸葛亮集》:“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可见锦对西蜀的重要意义了。刘备赏赐群臣也用锦。《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蜀志》:“先主入益州,赐诸葛亮 、法正、张飞、关羽锦各千匹。”也可见锦在蜀国经济中所占的地位[100] 。
晋常璩《华阳国志》里也谈到西南一带蚕丝生产的情况。卷一《巴(今重庆)志》里说这里有“桑、蚕、麻、苎”。汉桓帝时有人倡议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一治安汉,各有桑、麻、丹、漆、布帛、渔池,盐、铁,足相供给”。巴西郡:“土地山原多平,有牛、马、桑、蚕。”卷三《蜀(今成都)志》里说这里有锦绣,有桑、漆、麻、苎。汉安县:“山水特美好,宜蚕桑。”卷四《南中志》里谈到永昌郡“土地沃腴,黄金、光珠、虎魄、翡翠、孔雀、犀、象、蚕、桑、绵、绢、采帛、文绣”。不但说什么地方有蚕桑,连什么地方没有也谈到了。譬如,卷一涪陵郡:“无蚕桑,少文学;惟出丹、漆、蜜、蜡。”卷四牂柯郡:“畲山为田,无蚕桑。”南广郡:“土地无稻田蚕桑。”云南郡:“土地有稻田,但不蚕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郡而没有蚕桑好像是缺点什么,好像是例外,所以才特别加以说明。反过来说,有蚕桑就是正常的情形,也可见西南一带蚕桑的普遍了。
《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蛮列传》:
人水耕,食蚕以柘,蚕生阅二旬而茧,织锦缣精致。
《云仙杂记》卷三:
杜甫寓蜀,每蚕熟,即与儿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悯,惠我一丝两丝。
可见唐代西南一带蚕丝生产的情况。唐樊绰《蛮书》记载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衣著。卷一:“〔乌蛮〕妇人以黑缯为衣,其长曳地。”卷四:“〔施蛮〕男以缯布为缦裆裤。”“〔寻传蛮〕俗无丝绵布帛,披波罗皮。”“〔粟栗两姓蛮〕丈夫妇人以黑缯为衣,其长曳地。又东有白蛮,丈夫妇人以白缯为衣,下不过膝。”卷八:“南诏以红绫,其余向下皆以皂绫绢。”“贵绯紫两色。得紫后,有大功,则得锦。”“妇人一切不施粉黛,贵者以绫锦为裙襦,其上仍披锦方幅为饰。”卷七对养蚕纺织的办法记述得非常详细:
蛮地无桑,悉养柘蚕,绕树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数顷,耸干数丈。三月初,蚕已生。三月中,茧出。抽丝法稍异中土。精者为纺丝绫,亦织为锦及绢。其纺丝入朱紫以为上服,锦文颇有密致奇采。蛮及家口悉不许为衣服。其绢极粗,原细入色,制如衾被,庶贱男女,许以披之。亦有刺绣,蛮王并清平官礼衣,悉服锦绣,皆上缀波罗皮。俗不解织绫罗,自太和三年(829)蛮贼寇西川,虏掠巧儿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织绫罗也。(参阅《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蛮传》)
西南兄弟民族织绫罗的技巧也是从四川一带传过去的。《新唐书》卷三二《地理志》说到成都的贡品,其中有锦和单丝罗。可见在唐代四川的织锦工业依然很兴盛。
到了宋代情况仍然没变。《通志》卷一九七《四夷传》第四《南蛮》上《松外诸蛮》:
自夜郎滇池以西,皆庄之裔。有稻、麦、粟、豆、丝、麻、薤 、蒜、桃、李。以十二月为岁首。布幅广七寸。正月蚕生,二月熟。[101]
《哀牢夷》:
土地沃 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102]
《文献通考》三二九《四裔考》六《南诏》:
自曲靖州至滇池,人水耕,养蚕以柘。
哀牢夷不但知道养蚕缫丝,而且还知道染采。南诏人民养蚕的办法和《蛮书》所记相同,可见这也是一个传统的老办法。宋黄休复《茅亭客话》:“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苏辙《诗序》也谈到眉山的蚕市。赵朴《成都古今记》里说:“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锦市,四月蚕市。”蚕和锦在宋代成都人民生活中所占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元费著《蜀锦谱》里还记载了蜀锦不同的名称。
从上面简短的征引和叙述里可以看到古代西南,特别是成都,丝业的茂盛。这一带与缅甸接壤,一向有交通,中国输入缅甸,通过缅甸又输入印度的丝的来源地不是别的地方,就正是这一带。
五 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过程
以上简略地叙述了中国古代蚕丝的发现,蚕丝在古代西域的传布,中国蚕丝输入波斯的过程,以及蚕丝在古代西南的传布。这些都是中国蚕丝如何输入印度这个问题的前提,应该先加以阐明。现在就来谈中国蚕丝从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输入印度,输入后又发生了什么作用的问题。从时间上来说,不是一时输入的;从地点上来说,也不是一地输入的。上下千余年,绵延数千里,这就是输入的总的情况。把时间和地点分开来叙述,也有困难。所以我在这里先谈一谈时间上的上限,然后再以地域为主、时间为辅来叙述输入的过程。
中国丝究竟从什么时候起就输入印度呢?最早的记录是在印度古书里找到的。在㤭胝厘耶(Kauṭilīya)著的《治国安邦术》(Artha śāstra)里有这样一句话:
kauśeyaṃ cīnapaṭṭāśca cīnabhūmijāḥ(㤭奢耶和产生在脂那的成捆的丝)
cīnapaṭṭā这个字是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cīna,就是“脂那”、“支那”;另一个是paṭṭā,意思是“带”、“条”。两个字合起来意思就是“中国的成捆的丝”。这个字本身已经把丝的产地告诉我们了。㤭胝厘耶据说是生于公元前4世纪,是孔雀王朝月护大王(Candragupta)的侍臣。假如 这部书真是他著的话,那么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丝必已输入印度[103] 。
印度其他古籍里讲到丝的也不少。但是这些书都不太古。吠陀里面没有讲到,足见印度人民知道蚕丝是在吠陀时代以后的事情。但是在另一方面,从梵文“丝”字里可以看出,古代印度人民对蚕丝的认识比希腊人和罗马人高明得多。希腊罗马几乎没有人知道丝是蚕吐的,对于丝他们有的只是一些离奇古怪不着边际的幻想。古代印度则不然。梵文里有许多字都有“丝”的意思:kīṭaja,kṛmija,kītasūtra,kīṭajasūtra,kṛmijasūtra,kīṭatantu,kīṭakosa,kīṭakoṣa,kīṭakoṣaja,kṛmikoṣaja。这些字都是复合字,组成部分都有kīṭa或kṛmi这个字,意思是“虫子”,kīṭaja和kṛmija意思就是“虫子生”。此外还有一个字kauśeya,是从kośa这个字演变来的,kośa的意思是“茧”,茧产生的东西就叫做kauśeya。印度古代知道丝是虫子吐的,知道丝是茧抽成的,这不是比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高明得多吗?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后2世纪这期间纂成的《摩奴法论》(Manusmṛti)里面有好几处讲到丝。一一,一六八说到,谁偷丝,谁就被罚三天内只许喝牛奶。在这里“丝”字是kīṭaja。五,一一九说到,丝要用盐基性的土来刷净。在这里“丝”字是 kauśeya。一二,六四说到,谁要是偷丝就变成一只鹧鸪。这里也是用kauśeya。著名的史诗《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和《罗摩衍那》(Rāmāyaṇa)里面也有好几处讲到丝。《摩诃婆罗多》二,一八四七用的是kīṭaja这个字,一三,四四六七用的是kauśeya。《罗摩衍那》二,三二,一六;三,四九,四四;五,二二,三〇用的都是kauśeya。约生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语法家波你尼(Pāṇini)在他的著作里用了kauśeya这个字。此外,kauśeya还见于印度古代诗圣迦梨陀娑(Kālidāsa)的《鸠摩罗出世》 (Kumārasambhava)和《六季杂咏》(Rtusamhāra)[104] ;以及《五卷书》(Pañcatantra),医典《 素室噜多经》(Suśrutā-Saṃhitā)等印度古代典籍[105] 。cīnapaṭṭa这个字除见于《治国安邦术》之外,还见于《素室噜多经》(一,一八,一一),与kauśeya并列。它又见于《说海》(Kathāsaritsāgara)四三,八九。最初的意思是“从中国输入的成束的丝”,后来逐渐有了“丝衣服”的意思。再经过几度演变,这个字的两个组成部分cīna和paṭṭa都可以独立存在,而仍有“丝”的意思。与这个字有关的cīnāmśuka,原义是“中国衣服”,后来也转成“丝衣服”。从这几个字可以看出,印度人一想到丝就想到中国,一想到中国也就想到丝,在他们心目中丝与中国简直是一而二、二而一了。
cīnapaṭṭa和kauśeya这两个字一般都理解为“丝”,但是其间难道一点区别都没有吗?这问题与中国丝的输入印度有些关联,应该加以研究。cīnapaṭṭa是从中国输入的丝,这个字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动摇的证明。假如kauśeya同cīnapaṭṭa是一种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就是从中国输入的,问题也就比较简单。但是《治国安邦术》里这两个字并列,足见其间还有一些区别。cīn apaṭṭa是从中国输入的,而kauśeya是印度本地出产的[106]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
其所服者,谓㤭奢耶衣及㲲布等。㤭奢耶者,野蚕丝也。[107]
㤭奢耶”就是kauśeya的音译。假如玄奘的解释正确的话,那么kauśeya就是野蚕丝,这种蚕吃的不是桑叶。这不是从中国输入的,从中国输入的只有cīnapaṭṭa。
以上我们初步确定了中国丝输入印度时间方面的上限,我们也简略地谈到印度古代对丝的知识,以及土产野蚕丝存在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就来谈中国丝输入印度的过程和道路。根据目前可能利用的文献记录以及考古发掘的结果,大概有五条道路:南海道,西域道,西藏道,缅甸道,安南道。以下就分别叙述。
南 海 道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
这是一段非常重 要的记载。从雷州半岛发船,到的国家虽然很难说相当于现在什么地[108] ,但是多数学者都 认为黄支国就是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〇达罗毗荼的都城建志补罗[109] 。足见前汉时代中国已经由海路通印度。去的目的是买璧流离、奇石异物。带去的是黄金与中国丝织品。这是中国正史上关于中国丝输入印度的最早的记载。当时中印交通主要是由陆路,海路也利用。《汉书·王莽传》有“东致海外,南怀黄支”之语。王莽奏文里说:“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班固《两都赋》及杜笃《论都赋》都有“黄支”之名。可见黄支和中国的交通是很频繁的。此外《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谈到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象牙、犀角、玳瑁。也可见日南在当时中外海路交通上的重要性。《通典》卷一八八:
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后汉桓帝时大秦天竺皆由此(日南)遣使贡献。(参阅《后汉书》卷八八,《天竺国》条)
更足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在印度古代典籍里也同样可以找到有关中印海路交通的记载。巴利文《那先比丘经》(Milindapañha)是记录弥邻陀王(希腊名Menandros,约在公元前125年至公元前95年)和龙军(Nāgasena)和尚问答的一部书。龙军举的一个例子里面说到运货的船远至支那等地。
在西方的典籍里也有中国丝运到印度去的记载。约生于公元后6世纪的希腊人科斯麻士(Cosmas)写过一部《基督教诸国风土记》(Topographia Christiana),里面说:
从遥远的国度里,我指的是中国和其他的输出地,输入到锡兰岛(Taprobane,巴利文Tambapanni) 的是丝、伽罗木、丁香、檀香,以及其他东西,因各地出产而异。[110]
汉以后中国和印度仍保持海上交通。刘宋时锡兰曾通使中国(见《宋书》卷九七)。吴时,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物使天竺(见《梁书》卷五四)。梁时,锡兰曾派使臣来(见《梁书》卷五四,《南史》卷七八)。唐高宗总章三年(670)以及玄宗天宝初年锡兰都派遣过使者来朝(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天宝五载(746)、天宝九载(750)都来过(见《册府元龟》卷九七一)。锡兰来的使者估计都走海路。
中国和尚到印度去求法,最初多经陆路。唐以前几乎没有走海路的。法显是泛海回国的,当时是很稀见的。到了唐代有了很大的变化。从海路到印度去的多起来了。常慜、明远、义朗、智岸、义玄、会宁、运期、解脱天、智行、慧琰、大乘灯,以及其他和尚都走的是海路。有名的义净来去都是海路。这些和尚到印度去是求法,并没有带了中国丝去贩卖。但是,既然他们能走,就表示这是中印交通重要道路。中国丝从这重要道路运至印度,也总是意中事吧。
自宋代起,中国丝从海路运至印度这事实就又有了文献的记录。宋代来中国贸易的国家主要是大食(阿拉伯),但是印度也是其中之一,而且从中国到阿拉伯,或者从阿拉伯到中国都要经过印度。宋周去非《岭外代答》:
中国舶欲往大食,必自故临(Quilon)易小舟而往。虽以一月南风至之,然往返经二年矣。
大食之来也,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至三佛齐国,乃复如三佛齐之入中国。
一方面印度扼中国与大食交通的咽喉,另一方面,印度也与中国交通。中国丝织品就大量输入印度。宋赵汝适《诸蕃志》细兰国(锡兰):
番商转易用檀香、丁香、脑子、金、银、瓷器、马、象、丝帛等为货。
南毗国:
用荷池、缬绢、瓷器、樟脑、大黄、黄连、丁香、脑子、檀香、豆蔻、沉香为货,商人就博易焉。
故临国:
博易用货亦与南毗同。
到了元朝,中印海上贸易仍然维持。元汪大渊《岛夷志略》有详细的记述。土塔(那迦八丹西北):
贸易之货用糖霜、五色绢、青缎、苏木之属。
挞吉那(?):
贸易之货用沙金、花银、五色缎、铁鼎、铜线、琉黄、水银之属。
小呗喃(Fandaraina):
贸易之货用金、银、青白花器、八丹布、五色缎、铁器之属。
古里佛(Kaulam):
去货与小呗喃国同。
朋加剌(Bangala):
贸易之货用南北丝、五色绢缎、丁香、豆蔻、青白花器、白缨之属。
大乌爹(Udeyapur):
贸易之货用白银、鼓板、五色缎、金、银、铁器之属。
马八儿屿:
贸易之货用沙金、青缎、白矾、红绿烧珠之属。
甘埋里:
来(?)商贩西洋互易。去货丁香、豆蔻、青缎、麝香、红色烧球、苏杭色缎、苏木、青白花器、瓷瓶、铁条。
乌爸(Orissa〔?〕):
贸易之货用金、银、五色缎、丁香、豆蔻、茅香、青白花器、鼓瑟之属。
此外还有几个地名不能断定是否在印度[111] 。从上面的引证里可以看出中国绢缎输入印度的范围。从孟加拉起沿印度东岸一直到印度西岸重要港口都有输入,范围不可谓不广了。
但是到了明代,中印海上贸易才达到最高潮。明初采取了发展生产的政策,扶植工商业。生产迅速提高,到了永乐时代,国内外市场都需要大力开拓。于是就有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随郑和下西洋的人里面有会稽人马欢,太仓人费信和应天人巩珍。回国后,他们各撰一书,马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这些书里都谈到中国丝绸输入印度的情形。现在就在下面分别谈一谈。
《瀛涯胜览》锡兰国:
中国麝香、纻丝、色绢、青磁盘碗、铜钱、樟脑,甚喜,则将宝石珍珠换易。
古里国:
其二大头目受中国朝廷升赏。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主为买卖。王差头目并哲地未讷几计书算于官府。牙人来会,领船大人议择某日打价。至日,先将带去锦绮等物逐一议价已定。随写合同价数,彼此收执。其头目哲地即与内官大人众手相拿。其牙人则言某月某日,于众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 贱,再不悔改。然后哲地富户才将宝石、珍珠、珊瑚等物来看议价。[112] (参阅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古里国第一九最后的附录)
这一段记述绸缎交易的情形非常生动详细。
费信虽然和马欢同时下西洋,但是他俩的记述却不完全一样,详略各异,可以互相补充。《星槎胜览》锡兰山国:
货用金、银、铜钱、青花白磁、色段、色绢之属。
小呗喃国:
货用丁香、豆蔻、苏木、色段、麝香、金、银、铜器、铁线、黑铅之属。
柯枝国(Cochin):
货用色段、白丝、青白花磁器、金、银之属。
古里国(Calicut):
货用金、银、色段、青花白磁器、珍珠、麝香、水银、樟脑之属。
榜葛剌国:
货用金、银、布缎、色绢、青白花磁器、铜钱、麝香、银珠、水银、草席、胡椒之属。
大呗喃国:
货用金钱、青白花磁器、布段之属。
溜洋国(Maldives):
货用金、银、色段、色绢、磁器、米谷之属。[113]
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记述的差不多。锡兰:
甚爱中国麝香、纻丝、色绢、青磁盘碗、铜钱。[114]
马欢、费信、巩珍三个人同时随郑和下西洋,他们三个人的记述可以互相参阅。
以上诸书的记载多据亲闻目见,所以是可靠的。此外,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也记载了明代中印交通的情况。但是这 部书是汇集马欢、费信及他书而成,虽较详尽,然而不是第一手资料[115] 。古里国:“五色丝帨谓之西洋手巾,其广五尺,其长一丈二尺,其价金钱百。”与巩珍所记相同。还有明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八一记榜葛剌“产镔铁、翠羽、琉璃、桑、漆,大广丝绵,兜罗锦”。
综观自汉武帝以来中印海上丝织品贸易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汉代运去的是“杂缯”,其后各代见于文献记录者较少,到了宋代元代,中国海上贸易空前发展,于是“丝帛”、“缬绢”、“五色绢”、“青缎”、“五色缎”,甚至“苏杭色缎”就大量运至印度。金吾古孙仲端《 北使记》里记载“〔印都回纥〕金、银、珠、玉、布帛、丝枲极广”[116] ,可见数量之多了。到了明初可以说是达到中印海上贸易的最高潮,中国的“纺丝”、“色绢”、“色段”、“白丝”源源运至印度。明代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印交通受到阻碍,海上丝绢贸易也就随之中断了。
西 域 道
有名的横亘欧亚大陆的“丝道”就通过西域,所以中国蚕丝通过西域转入印度,实在可以说是近水楼台。但是这还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有比“丝道”更有利的条件。
20世纪初叶,考古学者在新疆和阗一带发掘出许多残卷,是用印度字母写的,却不是印度文。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这个新语言已经读通。有人叫它做北雅利安语(Nordarisch),有人叫它做东伊朗语。因为是在和阗发掘出来的,又有人把它叫做和阗语。这个语言里有一个表示Z 音的特别字母ys。同样一个字母也在印度塞种统治者的名字里发现[117] 。这表示,在印度西北部统治的塞种人和在新疆和阗居住的人说的是同一种或极相近的语言。 这种语言现在就定名为和阗塞种语(Khotansakisch)[118] 。印度西北部的塞种人和住在和阗而说这种语言的人既然语言相同很可能就是同种或者是近支。无论是同种或近支,和阗和印度的交通自公元后一二世纪起长时期内一定非常频繁,这是可以断言的了。
此外考古学者还在和阗附近的尼雅(Niya)和安得悦(Endere)一带发掘出许多用驴唇体字母(Kharosṭhī)写的残卷,这可能是 古代鄯善国政府用的语言。这是一种印度俗语,来源地是印度西北部[119] 。和阗一带曾为说印度俗语的人所统治,这是一个事实。这事实也 告诉我们,在纪元前后几世纪内,和阗和印度的交通一定是很畅达的[120] 。
和阗是新疆产丝最著名的地方,中国蚕种也是最先由内地传到和阗的。这一带既然与印度有那样密切的关系,那么蚕丝从和阗传入印度也就是再方便不过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事实上,在和阗附近发现的驴唇体残卷里我们常看到paṭa这个字,paṭa就是上面说过的paṭṭa,中译“绢匹”。这种paṭa是作为交换媒介而流行当地。买一个女人要用41paṭa,罚款也以paṭa计算。它传入印度也是完全可以想象到的。
在西方古代著作里同样可以找到证据。公元后80年到89年之间埃及的希腊人某著的《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记载着:“过克利斯国(Chryse,今下缅甸及马来半岛)到了中国(Thin)海乃止。有大城曰秦尼(Thinae)在其国内部,处于北方。从这里生丝、丝线及丝织品由大夏经陆路运至巴利柴格(Baryzaga,今印度孟买附近之Broach港),更由恒河经水路而至李米里 斯(Limyrice,Schoff读作Damirike)。”[121] 这里面把运输的路线都清清楚楚地说了出来,是很可宝贵的记录。
要想再征引文献说明中国丝从西域输入印度的情况,文献是征引不完的。上面列举的那几个事实已经够说明这种情况了。中国丝从西域输入印度的问题也就谈到这里为止。
西 藏 道
由于山岭绵亘,交通很不方便,这条道路利用的最少。唐代玄照法师曾从这条路到印度去。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途经速利,过睹货罗,远跨胡疆到吐蕃国,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122]
回来的时候也走的是这条路。“路次泥波罗国,蒙王发遣,送至吐蕃,重见文成公主,深致礼遇,资给归唐。”此外走这条路到印度去的还有道生法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想通过吐蕃的有道希,到过泥波罗的有道方,回国时死于泥波罗的有末底僧呵、玄会法师(皆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在唐初这条路是比较畅通的。
但是,可能还不限于初唐。古代西方地理学家托雷美(Ptolemy, 87—165)在他的《地理书》,一,一七记载着:
他们说,不仅有一条路从这地方(中国)通过石塔(在帕米尔)到大夏,而且还有一条通到印度华氏城(希腊文Palimbothra,梵文Pāṭaliputra,今Patna)。
这条路大概是从甘肃经青海到拉萨,再越喜马拉雅山经锡金到巴特那[123] 。此外道宣《释迦方志》卷一还记载了白河州经吐蕃入印度的道路。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高宗嗣位……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高宗嗣位于650年,蚕种就于此时传入西藏。中国的丝从这条路运到印度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
缅 甸 道
缅甸介于中印两国之间,一方面很早就通中国,另一方面与印度交通也极早,从中国经缅甸道到印度去,应该说是极自然的事情。
在中国历史上首先倡议开辟中印缅道的是汉武帝时张骞。《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参阅《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