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宋代的海上交通
在这一节里,我列举的海外诸国不限于有甘蔗、沙糖或石蜜的,所有在文献中同宋王朝有交通关系的都收在这里。这个工作我实际上在上面已经做了。那些国名我用不着重复抄录,我只把出现的地方写在这里,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参阅:
(1)《文昌杂录》卷一
(2)《玉海》
(3)《文献通考》
此外,《宋史》和《宋会要辑稿》中的有关章节,都可以参考。
3.宋与大食的交通
我深深感觉到,大食这个国家(以后成为一组国家)在把沙糖或制糖术传入中国方面,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宋以前已经如此,在宋以后更为突出。所以我现在把大食同其他国家分离开来,予以特殊地位,专门谈一谈宋与大食的交通,我用列年表的方式来谈。我列表的根据是两部书,一部是《文献通考》,一部是《宋史》。两者基本相同,但也稍有差异。《文献通考》卷三三九之大食与《宋史》卷四九○之大食,使用资料有渊源关系:
乾德四年(966年) 行勤游西域,因赐王书以招怀之。
开宝元年(968年) 遣使来朝(又见《诸蕃志》)。
四年(971年) 又贡方物,是年又致贡物于李煜(又见《诸蕃志》)。
六年(973年) 遣使来贡方物。
七年(974年) 遣使入贡(《宋史》:“国王诃黎佛又遣使不啰海)。
九年(976年) 遣使入贡(《宋史》:又遣使蒲希密,皆以方物来贡)。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 遣使贡方物(《宋史》:遣使蒲思那、副使摩诃末、判官蒲罗等贡方物)。
四年(979年) 复有朝贡使至。
雍熙二年(985年) 国人花茶复来献……白沙糖……(按:《宋史》作元年)
雍熙三年(986年) 同宾瞳龙国来朝(见《诸蕃志》)。
淳化四年(993年) 又遣其副蕃(《宋史》作“酋”)长李亚勿来贡(又见《诸蕃志》)。
至道元年(995年) 其国舶主蒲押陁黎赍蒲希密表,献……白沙糖……
咸平二年(999年) 又遣判官文戍至。
三年(1000年) 舶主陀罗离遣使穆吉鼻来贡。
六年(1003年) 又遣使婆钦罗三摩尼等(《宋史》增“来贡方物”),对于崇政殿(又见《诸蕃志》)。
景德元年(1004年) 又遣使来。其年秋,蕃客蒲加心至(又见《诸蕃志》)。
四年(1007年) 又遣使同占城使来(又见《诸蕃志》)。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 陁婆离随驾东封。又舶主李亚勿遣使麻勿来献玉圭(根据《宋史》。《诸蕃志》载此事,但无年月)。
《文献通考》接着写道:“自国初以来数入贡,路由沙州,涉夏国,抵秦州。乾兴初(1022年,其实乾兴只有一年),赵德明请道其国中,不许。”这一件事情,《宋史》写在天禧三年(1019年),恐怕按年代顺序这更合理一些。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谈。
下面《文献通考》缺两年,《宋史》有: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 祀汾阴,又遣归德将军陀罗离进缶香、象牙……诏令陪位(又见《诸蕃志》)。
五年(1012年) 大食国人无西卢华百三十岁,附古逻国舶船而来(《诸蕃志》载此事,但无年月)。
天禧三年(1019年) 遣使蒲麻勿陁婆离,副使蒲加心等来贡。
下面紧接着《宋史》写了一段话,内容同上面大中祥符元年《文献通考》的那一段话几乎完全相同,只把“自国初以来”改为“先是”。
天圣元年(1023年) 来贡,恐为西人钞略,乃诏自今取海路,由广州至京师。
羡林按:在中国同大食的交通史上,这无疑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由陆路改变为海路。《文献通考》和《宋史》写的地方虽不同,内容却完全是一样的,所谓“恐为西人钞略”,指的就是以赵德明为首的西夏人。他向宋朝廷要求,让大食人走西夏,目的明显是经济效益。朝廷不允许,西夏人恐怕就要钞略了。所以才改走了海路。下面接着再写年表:
至和(1054—1056年)嘉祐(1056—1063年)间 四贡方物。
熙宁(1068—1077年)中 其使辛押陀罗乞统察蕃长司公事。
六年(1073年) 都蕃首保顺郎将蒲陀婆离慈表令男麻勿奉贡物,乞以自代而求为将军。
元祐三年(1088年) 大食、麻啰拔国遣使入贡(此据《岭外代答》)。
政和(1111—1117年)中 横州士曹蔡蒙休押伴其使入都。
建炎三年(1129年) 遣使奉宝玉珠贝入贡。
绍兴元年(1131年)、六年(1136年) 俱以船舶入贡
乾道四年(1168年) 进贡方物。
开禧(1205—1207年)间 遣使入贡。
羡林按:《诸蕃志》:“元祐、开禧间,各遣使入贡。”元祐恐系衍文,因为元祐1086—1094年,相距太远。
年表到此为止。值得注意的是《宋史》只写到绍兴元年。综观全表,从乾德四年(966年)至开禧末年(1207年),几乎与宋代共始终,共有241年,中国同大食来往之频繁,颇堪惊人。大食不是一个国家。《岭外代答》说:“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又说:大食诸国之京师是白达,即今之巴格达。好像大食是一个联合体。中国史籍中有时提“国王”,更多的是“舶主”,看来是官商两面都有,后者或尚更为重要。“商人重利轻别离”,商人在中国与大食间的往还中是重要的角色。
我想在这里补充一点大食与辽的关系:
《辽史》卷二《太祖本纪》:天赞三年(924年),大食国来贡。
《辽史》卷一六《圣宗本纪》:开泰九年(1020年),大食国遣使进象及方物,为子册割请婚。太平元年(1021年),大食国王复遣使请婚。
《辽史》卷三○《天祚本纪》:明年(1123年)二月,甲午,遗书回鹘王毕勒哥曰:“今我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其勿致疑。”
注释:
〔1〕 参阅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二期,拙作《唐代印度眼科医术传入中国考》。
〔2〕 此处疑缺一“酒”字。
〔3〕 这个年份有问题,怎样也解释不通。查《中国人名大辞典》,只有其名,而没有生卒年月。宋赵与 《宾退录》卷三,有一条讲到唐慎微。
《宾退录》卷三,有一条讲到唐慎微。
〔4〕 “飴糖”,一般是指麦芽糖,本来可以不写。但在前一章讲唐代《糖史》时,我却碰到了一个难题。在王焘的《外台秘要》卷八,治疗鱼骨哽在喉或腹中方中有“飴糖”,经我同别的书对勘,“飴糖”即“糖”。所以对于“飴糖”究竟如何区别,还是一个难题。在这里,我暂时写上。下面不一定全写。
〔5〕 《四库全书》本改为“边徼”。清朝统治者不愿见到这些字眼。
〔6〕 《四库》作“就传”。
〔7〕 《四库》作“扬”,正确。
〔8〕 《四库》作“两傍”,误。
〔9〕 《四库》作“阁”,误。
〔10〕 原缺一字,根据《四库》本补。
〔11〕 《苏轼诗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卷二四,第1268—1269页,中华书局。
〔12〕 我所见到的本子都作“餳”,不作“糃”,《四库全书》本亦然。
〔13〕 1982年,中华书局。
〔14〕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作“密”,显然是错误的,下面还有。
〔15〕 《四库全书》本“薦”字有问题。根据前后文,此处应作“蔗”字。
〔16〕 梁代以前的种蔗地区,这里暂不列。
〔17〕 上面地名变化之解释,多根据臧励龢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31年初版,1982年重印。
〔18〕 在前一章讲唐代甘蔗种植地区时,对沙州能否种植甘蔗,我划了一个问号。到了宋代,这问题仍然无法回答。《玉照新志》讲到泽州餳,我不敢说“餳”究竟是不是糖。
〔19〕 唐以前中国甘蔗种植地区和传播情况,李治寰《中国食糖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73—76页,有比较详细的叙述,请参阅,我在这里不再重复。
〔20〕 Deerr,The History of Sugar,p. 17.
〔21〕 李治寰,上引书,第67—73页。
〔22〕 李治寰,上引书,第141页。
〔23〕 李治寰:《从制糖史谈石蜜和冰糖》,《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150页。
〔24〕 只有国名而没有种蔗和制糖的国家,这里一概不提,下同。
第七章 元代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1206—1368年)
同唐宋比较起来,元代享国时期极短,是秦、隋以后第三个年代最短的朝代。这个特点当然会影响我们叙述的内容。因此,本章分为下列三大段:
(一)材料来源。
(二)甘蔗种植和沙糖应用。
(三)外来影响。
在元代以前,所有成为正统的王朝其统治者全是汉族。至于血统是否完全纯粹,那是可以研究的,至少名义上是如此。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创建的朝代。这个特点决定了它文化的构成和统治的方式。蒙古族人数不多,文化水平不高。在建国过程中,它充分利用外族人和北方的汉人。它把人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在宗教信仰方面,它对儒、释、道,甚至医卜都尊重,文化多种多样,既矛盾,又融合。但是元代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却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一,它给中国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一个文化,如果僵硬死板,固步自封,不汲取新的成分,就必然不能持久。第二,元代蒙古人创立了一个囊括欧亚大陆的空前的大帝国。在它统治期间,东西交通畅行无阻,大大地便利了东西文化的交流。这对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当然会产生影响。
(一)材料来源
在这方面,元代同唐宋都稍有不同,可以说是大同而小异吧。现将条目胪列如下:
1.正史
2.本草和医书
3.诗文
4.地理著作与中国人游记
5.外国人游记
6.笔记
7.农书
8.类书
1.正史
所谓“正史”,指的就是《元史》。明代官修,以李善长(1314—1390年)为监修。《四库全书提要》说:“二百一十卷,明宋濂(1310—1381年)等奉敕撰。洪武二年(1369年)诏修《元史》。以濂及王祎(有的书作‘ ’,1322—1373年)为总裁。二月开局天宁寺,八月书成,而顺帝一朝史犹未备。乃命儒士欧阳佑等往北平采其遗事。明年二月诏重开史局。阅六月书成。为‘纪’四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传’一百一十四卷。(羡林按:这些数目与中华书局新版不同)书始颁行,纷纷然已多窃议。迨后来递相考证,纰漏弥彰。”可见此书问题之多。《提要》列举了一些明清学者的意见,指出《元史》疏漏之处甚多,但是,《提要》最后列举了几个此书的优点,说“未尝不可以为考古之证,读者节取其所长可也”。
’,1322—1373年)为总裁。二月开局天宁寺,八月书成,而顺帝一朝史犹未备。乃命儒士欧阳佑等往北平采其遗事。明年二月诏重开史局。阅六月书成。为‘纪’四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传’一百一十四卷。(羡林按:这些数目与中华书局新版不同)书始颁行,纷纷然已多窃议。迨后来递相考证,纰漏弥彰。”可见此书问题之多。《提要》列举了一些明清学者的意见,指出《元史》疏漏之处甚多,但是,《提要》最后列举了几个此书的优点,说“未尝不可以为考古之证,读者节取其所长可也”。
我无法仔细翻检全书,那种大海捞针的做法未必可取。我只重点翻阅了与我的研究有关的《地理志》。但是,《元史·地理志》不像有一些《地理志》那样,每个地方都有“土产”一项,因此产蔗或贡糖的记载一概没有。我又寄希望于《食货志》,结果依然失望。特别让我失望的是《外夷传》。元朝混一欧亚,与外国交通频繁,按理说,《元史》的《外夷传》内容应当十分丰富,篇幅应当十分繁多,换句话说,对我有用的资料应当十分多。然而,事与愿违,《外夷传》内容不丰富,篇幅也不多,我几乎没有找到什么可用的资料。南海许多国家的“传”,主要讲的是蒙古大军征服那个国的过程。这种记载对我的研究毫无用处。
总之,我对于《元史》,从实用主义的角度上来看,是颇为失望的。
但是,《元史》这个大海中毕竟还是有针的。尽管这个针不是我亲自捞出来的,它对我总是有用的。《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第三○一卷“糖部纪事”引了《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中的一段话:
希宪尝有疾,帝遣医三人(《四库全书》本缺)诊视。医言须用沙糖作饮。时最难得,家人求于外。阿哈玛特(《古今图书集成》作“阿哈马”)与之二斤,且致密意,希宪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终不以奸人所与求活也。”帝闻而遣赐之。
从上面这一段简短的记载中,我们至少能够了解以下几点:第一,沙糖能治病。第二,沙糖有时并不容易得到,只有“奸人”和皇家才能有。这对我们研究元代沙糖问题,是有帮助的。
元代正史中的资料,目前我只能搜集这一点。《元史》中估计还会有一些的。限于目前的条件,也就暂时只能这样了。至于那些还没能搜集到的资料是否真有对我的研究有决定性的意义,我是抱怀疑态度的 〔1〕 。
2.本草和医书
中国本草和医书的一般情况,我在前两章唐代和宋代的有关章节中已经介绍过了。元代继承了宋代和宋以前的传统,虽然享国时间不长,但是这两类书的数量也颇可观。从这些书中搜集我所要用的资料,我没有电脑,只有人脑,仍然使用以前使用过的极笨但又是唯一可行的办法:逐本、逐页、逐行地翻检。我所遇到的困难和苦恼,完全同以前一样。这里不再重复叫苦了。
关于元代的《本草》和医书,甄志亚的《中国医学史》 〔2〕 记载了下列诸书:
| 《日用本草》(1329年) | 吴瑞编著 |
| 《饮膳正要》(1330年) | 饮膳太医忽思慧著 |
| 《济生方》(1253年) | 严用和(约1200—1268年)撰 |
| 《活人事证方》(1216年) | 刘信甫撰 |
| 《仁斋直指方》(1264年) | 杨士瀛撰 |
| 《世医得效方》(1337年) | 危亦林著 |
| 《局方发挥》(14世纪中) | 朱震亨著 |
| 《御药院方》(1267年) | 许国祯撰 |
| 《订补风科集验名方》 | 赵大中、赵素著 |
| 《简便方》 | 王幼孙撰 |
| 《岭南卫生方》 | 释继洪著 |
| 《医方集成》(1314—1320年) | 孙允贤撰 |
| 《永类铃方》(1331年) | 李仲南著 |
| 《医方大成》 | 陈子靖撰 |
| 《加减十三方》 | 徐文中著 |
| 《加减方》 | 潘阳坡著 |
在《四库全书》中也有不少元代《本草》和医书。我也抄在下面:
| 《内外伤辨惑论》 | 李杲撰 |
| 《脾胃论》 | 李杲撰 |
| 《兰室秘藏》 | 李杲撰 |
| 《此事难知》 | 王好古撰 |
| 《医垒元戎》 | 王好古撰 |
| 《汤液本草》 | 王好古撰 〔3〕 |
| 《瑞竹堂经验方》 | 沙图穆苏编 |
| 《世医得效方》 | 危亦林撰 |
| 《格致余论》 | 朱震亨撰 |
| 《局方发挥》 | 朱震亨撰 |
| 《金匮钩玄》 | 朱震亨撰 |
| 《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 | 王国瑞撰 |
| 《外科精义》 | 齐德之撰 |
| 《脉诀刊误》 | 戴启宗撰 |
| 《医经溯洄集》 | 王履撰 〔4〕 |
上面这个书目,还不会是十分完备的。元代享国没有唐宋那样长,但已经有了这样多的书,足见它能继承唐宋的传统,对人民的卫生事业是很重视的。我之所以抄这样多的书有什么意义呢?我研究的并不是中国医学史。但是,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甘蔗和沙糖等的主要作用不出两途:一食用,二药用。要想搜集药用方面的资料,离不开上面这一些书。这就是我不厌其烦地抄这个书目的原因。
上面这一些书,我大体上都翻检了一遍。有一些书对我的研究没有什么用处,我就存而不论。对我的研究有用的书,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来是有用的,我就像在前一章宋代那样,把书的情况简略地介绍一下,这对读者会有帮助的。我的介绍主要是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正如一般的评价那样,《提要》是写得很有水平很有见地的。
我翻检这些书的结果,确实找到了一些蔗和糖等药用的例子。这当然很使我高兴,力量没有白费。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些出乎意料的情况。这些情况我在前一章已经略有申述,现在再集中地比较具体地谈一下。归纳起来共有两点:第一,唐代《本草》和医书中,蔗和糖等药用例子最多,宋代次之,元又次之。第二,在唐代,甚至在宋代,一些用蔗和糖等来治的病,到了元代,蔗和糖都不见了。金代医书也有这种情况,为了让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情况,我也附在这里一谈。
我现在就以书为单位,把其中有关蔗和糖等的药用情况抄录出来,同时也把上面提到的两种情况中的第二种情况指了出来,供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1)金张元素《病机气宜保命集》
《四库全书提要》说:“《保命集》三卷,金张元素撰……凡分三十二门,首‘原道’、‘原脉’、‘摄生’、‘阴阳’诸论,次及处方、用药、次第加减、君臣佐使之法,于医理精蕴,阐发极为深至。”
下面是资料:
〔5〕第一个数字指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册数,第二个数字指页数。
羡林按:根据唐代医书,治这样的病都应该有沙糖之类的东西,这里没有。
(2)金张从正《儒门事亲》
《提要》说:“十五卷,金张从正撰……名目颇烦碎,而大旨主于用攻。”
资料如下:
羡林按:这里情况与(1)相同。
(3)金李杲《内外伤寒辨惑论》
《提要》说:“三卷……是编发明内伤之症有类外感,辨别阴阳寒热有余不足,而大旨以脾胃为主。”
(4)金李杲《脾胃论》
《提要》:“《脾胃论》三卷,金李杲撰。杲既著《辨惑论》,恐世俗不悟,复为此书。”
(5)金李杲《兰室秘藏》
《提要》说:“其治病分二十一门,以饮食劳倦居首……惟杲此书载所自制诸方,动至一二十位(味?),而君臣佐使,相制相用,条理井然,他人罕能效之者。斯则事由神解,不涉言诠。读是书者能喻法外之意,则善矣。”
资料如下:
羡林按:情况与(1)相同。有一件事情必须说明。著者李杲,《四库全书》书内作“金”,但目次都作“元”。原因何在呢?745—363说:“(李杲)金亡时,年五十五,入元十七年乃终。”这就是亦“金”亦“元”的原因。
(6)元王好古《此事难知》
《提要》说:“(王好古)李杲之高弟也。是编专述杲之绪论。”
(7)元王好古《医垒元戎》
共十二卷。《提要》说:“其书以十二经为纲,皆以伤寒附以杂证,大旨祖长沙绪论,而参以东垣易水之法。”
下面是资料:
(8)元王好古《汤液本草》
三卷。《提要》说:“曰汤液者,取《汉志》汤液经秘也。”
资料如下:
(9)元沙图穆苏编《瑞竹堂经验方》
五卷。《提要》说:“明中叶以前,原帙尚存。其后遂尠传本。今据《永乐大典》所载搜采编辑。计亡缺已十之五六,而所存者尚多……殊病其过于峻利。盖金元方剂,往往如斯,由北人气禀壮实与南人异治故也。”
下面是资料:
羡林按:《提要》提出了用药峻利的原因,合情合理,十分值得重视。下面还要谈这个问题。至于“糖毬子”,下面还有解释。
羡林按:治这种病,唐代用沙糖。
(10)元危亦林撰《世医得效方》
《提要》说:“二十卷,元危亦林撰。……是编积其高祖以下五世所集医方,合成而成。……序中称其高祖遇仙人董奉二十五世孙,传其秘方。虽技术家依托之言,不足深诘,而所载古方至多,皆可以资考据,未可以罕所发明废之也。”
资料如下:
羡林按:用沙糖来解砒及巴豆毒,恐怕是一个新发展,唐宋药方中不记得有这个办法。
(11)元朱震亨撰《格致余论》
(12)元朱震亨撰《局方发挥》
羡林按:以上两书中没有与我的研究有关的资料,因此只列书名,不作介绍。
(13)元朱震亨撰《金匮钩玄》
《提要》说:“三卷,元朱震亨撰,明戴原礼校补。中称戴云者,原礼说也。……是书词旨简明,不愧钩玄之目。原礼所补,亦多精确。”
资料如下:
羡林按:上面(2)已经介绍过的金张从正《儒门事亲》,《四库全书》745—281有“茶癖”一项,但没有“砂糖水调服”这个规定。
(14)元王国瑞撰《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
(15)元齐德之撰《外科精义》
(16)元戴启宗撰《脉诀刊误》
(17)元王履撰《医经溯洄集》
羡林按:以上四种书,经我粗略翻检,没有对我有用的资料,故介绍从略。
(18)元吴瑞撰《日用本草》
此书《四库全书》未收。现根据《中国医学史》(第222页)介绍如下:
《日用本草》(1329年):吴瑞编著。全书共八卷,分为米、壳、菜、果、禽、兽、鱼、虫等八门,载药540余种。着重论述了常用食物中的性味功用,以便从饮食中研究治病的规律和方法。
李汎为该书作序称:“夫本草曰日用者,摘其切于饮食者耳。盖饮食所以养人,不可一日无,然有害人者存,智者察之,众人昧焉。故往往以千金之躯,捐于一箸之顷而不知。瑞卿悯之……然非上考神农疗疾本草,及历代名贤所著,与夫道藏诸方书……瑞卿可谓善学,继其先志,修复先世遗文,俾二百余年残仁断惠,续行于世如一日。……事虽近,而利则远。文虽浅,而意则深。不但泛泛误于饮食者可免而已。为人臣子,而欲尽忠爱于日膳者,皆不可以不知也。”
此书的性质可见一斑。
我目前还没能借到此书,内容不详。我只能暂时从《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第三○一卷,“糖部”“沙糖”“集解”中抄一段:
吴瑞曰:稀者为蔗糖,干者为沙糖,毬者为毬糖,饼者为饼糖。沙糖中凝如石,破之如沙,透明白者,为糖霜。
这里解决了一个问题:什么叫“毬糖”?上面(9)《瑞竹堂经验方》中有一味药“糖毬子”(746—12);(13)《金匮钩玄》中有“糖毬”(746—729);下面(19)《寿亲养老新书》中有:“毬糖”。我原来不知道是什么药品。现在看了吴瑞的解释,豁然开朗了。
(19)宋陈直《寿亲养老新书》,元邹铉续编
《四库全书提要》说:“四卷。第一卷为宋陈直撰,本名《养老奉亲书》,第二卷以后则元大德中泰宁邹铉所续增,与直书合为一编,更题今名。……然征引方药,颇多奇秘,于高年颐养之法,不无小补,因为人子者所宜究心也。”
下面这几条资料出自本书第三卷和第四卷,出自元代邹铉之手:
关于“毬糖”,上面已经谈到。蔗糖和毬糖都是糖,只不过外形不同,所以“亦好”。
(20)元忽思慧《饮膳正要》
《四库全书》缺。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藏明景泰七年(1456年)刻本,另藏有日本迻录明成化刻本。前有虞集元天历三年(1330年)五月朔日序和同年三月三日忽思慧序。二序对本书的撰写宗旨说得一清二楚。虞集说:“昔世祖皇帝食饮必稽于《本草》,动静必准乎法度,是以身跻上寿,贻子孙无彊(应作‘疆’)之福焉。是书也,当时尚医之论著者云:噫!进书者可谓能执其艺事,又以致其忠爱者矣。”忽思慧说:“伏睹国朝奄有四海,遐迩罔不宾贡。珍味奇品,咸萃内府,或风土有所未宜,成(应作“或”)燥湿不能相济。倘司庖厨者不能察其性味,而概于进献,则食之恐不免于致疾。……将累朝亲侍进用奇珍异馔汤膏煎造及诸家《本草》名医方术,并日所必用谷肉果菜,取其性味补益者,集成一书,名曰《饮膳正要》,分为三卷。”从两序中可见,本书的目的性是非常鲜明的。
现将有用资料摘抄如下:
第一卷
木瓜汤 补中顺气,治腰膝疼痛,脚气不仁
羊肉 草果 回回豆子
右件一同熬成汤,滤净,下香粳米一升,回回豆子二合,肉弹儿木瓜二斤,取汁,沙糖四两,盐少许,调和或下事件肉。
第二卷 诸般汤煎
桂沉浆 去湿,逐饮生津止渴,顺气
紫苏叶(一两剉) 沉香(二钱剉) 乌梅(一两取肉) 沙糖(六两)
荔枝膏 生津,止渴,去烦
乌梅(半斤取肉) 桂(一十两去皮剉) 沙糖(二十六两)
麝香(半钱研) 生姜汁(五两) 熟蜜(一十四两) 梅子丸(药名略)
右为末,入麝香,和匀沙糖,为丸,如弹大,每服一丸,噙化。
五味子汤
北五味(一斤净肉) 紫苏叶(六两) 人参(四两去芦剉) 沙糖(二斤)
人参汤
新罗参(四两去芦剉) 橘皮(一两去白) 紫苏叶(三两) 沙糖(一斤)
木瓜煎
木瓜(十个去皮穰取汁熬水尽) 白沙糖(十斤炼净)
香圆煎
香圆(二十个去皮取肉) 白沙糖(十斤炼净)
株子煎
株子(一百个取净肉) 白砂糖(五斤炼净)
紫苏煎
紫苏叶(五斤) 干木瓜(五斤) 白沙糖(十斤炼净)
金橘煎
金橘(五十个去子取皮) 白沙糖(三斤)
樱桃煎
樱桃(五十个取汁) 白沙糖(二十五斤) 同熬成煎
石榴浆
石榴子(十个取汁) 白沙糖(十斤炼净)
五味子舍儿别
新北五味(十斤去子水浸取汁) 白沙糖(八斤炼净)
生地黄鸡
飴糖(五两)
羡林按:飴糖显然不是白糖,在这里泾渭分明。写在这里,以资同其他书比较。
此外,还有一个项目,叫“食物相反”,中有:
鲫鱼不可与糖同食;
虾不可与糖同食;
葵菜不可与糖同食;
竹笋不可与糖同食。
第三卷
沙糖 味甘寒,无毒,主心腹热胀,止渴,明目(即甘蔗汁熬成沙糖)
资料抄完了。我还想提出两点,供学者们参考。第一,食品和药品中,都有不少非汉语的词儿,比如“马思荅吉汤”、“沙吉某儿汤”等等,其中一定有蒙古语和西域民族语。这说明饮食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下面还要谈到这个问题。第二,元朝统治者出身于游牧民族,吃的东西花样繁多,其勇气决不低于后来的广东人。我只举一个例子,在“兽品”中有牛、羊、黄羊、
 、马、野马、象、驼、野驼、熊、驴、麋、鹿、獐、犬、猪、野猪、獭、虎、豹、狍、麂、麝、狐、犀牛、狼、兔、狸、塔剌不花、黄鼠、猴。四条腿的几乎无不可吃。元朝皇帝吃东西的勇气,仅从“兽品”这一项就充分显示了出来。他们能征服世界,良有以也。
、马、野马、象、驼、野驼、熊、驴、麋、鹿、獐、犬、猪、野猪、獭、虎、豹、狍、麂、麝、狐、犀牛、狼、兔、狸、塔剌不花、黄鼠、猴。四条腿的几乎无不可吃。元朝皇帝吃东西的勇气,仅从“兽品”这一项就充分显示了出来。他们能征服世界,良有以也。
(21)《饮食须知》
《学海类编》一○五
卷四 果类 甘蔗
卷五 味 黑沙糖 白沙糖
3.诗文
元代享国虽短,但是诗文的数量依然很可观。我仍然遵照以前的办法,不去翻检全部诗文。那样做,一定要付出极大的劳动,而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即使找到一些可用的资料,也不见得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我仅仅利用一些其他的书,其中也包括类书,抄出一些有关蔗和糖的资料,聊备一格。
(1)顾瑛
蔗浆玉碗冰泠泠。
见《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甘蔗部·选句》。
(2)洪希文《糖霜》
春余甘蔗榨为浆,色美鹅儿浅浅黄。
金掌飞仙承瑞露,板桥行客履新霜。
携来已见坚冰渐,嚼过谁传餐玉方。
输与雪堂老居士,牙盘玛瑙妙称扬。
见《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糖部·艺文二诗》。
(3)耶律楚材(1190—1244年)《湛然居士集》
卷六《西域河中十咏》,其十
原诗在前一章宋代(二)“甘蔗种植”3.“疏勒问题”已经抄出,请参阅,这里不再重复。
4.地理著作与中国人游记
元代版图扩大,亘古所未有。这给中外旅行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中外旅行家的游记都有一批。国外旅行家的著作,下一节来谈,这里只谈中国旅行家的游记和有关的地理著作。
(1)元孛兰肹等撰《元一统志》
本书《四库全书》未收。原称《大元大一统志》或《大元一统志》,元扎马剌丁、虞应龙和孛兰肹、岳铉先后主编。一千三百卷。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初编为七百五十卷。大德七年(1303年),全书始成定编,并有彩画地图。沿唐宋旧志成例,按中书省、行中书省和所辖各路的现行政区划分篇,以府、州为记叙单位,分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胜、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目。全书后佚,明中叶后尚存残篇。后来收入一些丛书中。1966年中华书局出版赵万里校辑本,为迄今收录最全的本子。我就根据赵本抄录一些有关资料,主要来自“土产”一项。在本书中,“土产”一项详略差异极大,有的地方一件没有,有的地方则列上了十种二十种。有的地方我本来期望会有的,结果是没有。我现在把资料介绍如下,顺序根据原书:
卷五 潼川府 遂宁州
根据唐宋的记载,遂宁应该有糖霜或者沙糖。但是,在这里连“土产”这个项目都没有。
卷九 广州路
在这里,“土产”这一项竟列有95种动植物,真可谓洋洋大观了。其中第17项是:
蔗 番禺、南海、东莞有。乡村人煎汁为沙糖,工制虽不逮蜀汉川为狮子形,而味亦过柳城也。
羡林按:这一段记载非常重要,下面(二)“甘蔗种植和沙糖应用”中将详加讨论。
卷九 潮州路
“土产”中有“蔗”。
材料就这样多。我再补上几句:在卷三扬州路;卷七福州路、泉州路;卷九赣州路等处,都没有甘蔗和沙糖的记载。
(2)元刘郁《西使记》
《四库全书提要》说:“《西使记》一卷,元刘郁撰。郁,真定人。是书记常德西使皇弟锡里库军中往返道途之所见。”刘郁曾官监察御史。宪宗九年(1259年)奉命随转运使常德自和林去西亚(波斯)觐见旭烈兀大王,中统四年(1263年)回国,写成此书。初载于元王恽《玉堂嘉话》(见下面6.笔记),并收入《学津讨原》,近人丁谦和、王国维都有校刊本,王著见于上海古籍书店《王国维遗书》第13册。《元史》卷一四九,《传》三十六《郭侃传》记载郭侃统兵到过的地方,有与《西使记》相同者。
有关资料条列如下:
羡林按:足证这里吃糖是比较多的。
下面还有关于密实勒国(今埃及)的记载。《玉堂嘉话》(《四库》866—455):“即唐拂菻地也。”这对于探讨“拂菻问题”,是有帮助的。
(3)元耶律楚材《西游录》
此书最初见于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上中。关于《庶斋老学丛谈》,《四库全书提要》有如下的介绍:“三卷。元盛如梓撰。……其书多辨论经史、评骘诗文之语,而朝野逸事亦间及之。分为三卷,而第二卷别析一子卷,实四卷也。”在本书卷上有下面一段话:
下面是《西游录》中的一些有用的材料:
羡林按:此诗上面已引。请参阅本书第六章(二)“甘蔗种植”3.“疏勒问题”;及本章(一)3.“诗文”(3)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六。
除了以上几种书以外,元人还写了几本游记,比如《长春真人西游记》等。我翻检了一遍《西游记》(见《王国维遗书》第13册),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资料,对此书不再介绍。此外,元周致中有《异域志》。仅在“大食无斯离国”有几句话:“出甘露,秋露降,暴之成糖霜,食之甘美。”也许对我的研究有点用处 〔6〕 。
上面我讲的几本书是中国人游历西域的记录。下面再讲几本中国人游历南海和西洋的书。
(4)元汪大渊《岛夷志略》
《四库全书提要》说:“一卷,元汪大渊撰。大渊,字焕章。至正中(1341—1368年),尝附贾舶浮海,越数十国,纪所闻见,成此书。”《提要》中提出了一个颇有意义的问题:“至云爪哇即古阇婆。考《明史》,太祖时,爪哇、阇婆二国并来贡,其二国国王之名亦不同。大渊并而为一,则传闻之误矣。”这个问题,这里先不讨论,以后有机会再谈。
在胪列资料之前,我先说明几句。看来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做生意提供情报,汪大渊的主要兴趣也完全在商品上。因此,几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都有“地产”和“贸易之货”两项的记载。汪大渊对于酒似乎特感兴趣,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酿酒的记载。关于种植甘蔗,直接讲到的地方极少;但是,如果有“酿蔗浆为酒”的记载,则此地必然产蔗,几乎可以断言。
下面是资料。我把酿酒的记载也都附上。我用的本子是中华书局1981年苏继庼校释本:
第16页 琉球 酿蔗浆为酒
第23页 三岛 酿蔗浆为酒
第33页 麻逸 煮糖水为酒
第38页 无枝拔 酿椰浆蕨粉为酒
第50页 交趾 酿秫为酒
第56页 占城 酿小米为酒
第69页 真腊 酿小米为酒
第79页 丹马令 酿小米为酒
第86页 日丽 酿浆为酒
第89页 麻里鲁 酿蔗浆为酒
第93页 遐来勿 酿椰浆为酒
第96页 彭坑 酿椰浆为酒
第106页 戎 以椰水浸秫米为酒,复酿榴实酒
第109页 罗卫 以葛根浸水酿酒
第114页 罗斛 酿秫米为酒
第120页 东冲古剌 酿蔗浆为酒
第136页 尖山 酿蔗浆水米为酒
第141页 三佛齐 酿秫为酒
第148页 浡泥 酿秫为酒
第168页 重迦罗 酿秫为酒
第173页 都督岸 酿蜜水为酒
第175页 文诞 酿椰浆为酒
第178页 苏禄 酿蔗浆为酒
第181页 龙牙犀角 酿秫为酒……地产蜜糖……
第184页 苏门傍 贸易之货,用白糖……
请注意:这里出现了“白糖”。
第187页 旧港 酿椰浆为酒
第190页 龙牙菩提 浸葛汁以酿酒
第196页 班卒 酿米为酒
第227页 东西竺 酿椰浆为酒
第234页 花面 地产……甘蔗……
请注意:这里明确提出了“甘蔗”。
第250页 特番里 酿荖叶为酒
第257页 曼陀郎 以木犀花酿酒
第270页 高郎步 酿蔗浆为酒
第277页 东淡邈 酿椰浆为酒
第280页 大八丹 贸易之货,用……白糖……
请注意:这里又出现了“白糖”。
第282页 加里那 酿椰浆为酒
第285页 土塔 贸易之货,用糖霜……
请注意:这里有“糖霜”,是唯一的一次。
第297页 加将门 酿蔗浆为酒
第305页 挞吉那 酿安石榴为酒
第308页 千里马 酿桂屑为酒
第339页 大乌爹 以逡巡法酿酒
第342页 万年港 酿蔗浆为酒
第344页 马八儿屿 酿椰浆为酒
第349页 哩伽塔 酿黍为酒
第358页 层摇罗 酿蔗浆为酒
第369页 麻呵斯离 酿荖叶为酒。
下面有一段话很重要:
甘露每岁八九月下,民间筑净池以盛之,旭日曝则融结如冰,味甚糖霜。
羡林按:这一段话颇有意思。请参阅上面引用的元周致中《异域志》中的一段话。明陈诚《西域番国志》“沙鹿海牙”条说:“又有小草,高三尺,枝干丛生,遍生棘刺,叶细如蓝,清秋露降,凝结成珠,缀枝干,甘如餳,可熬为达郎古宾,即甘露也。”指的可能是一件事。
我在这里想附带讲两件事:第一,我们根据过去的记载,本来期望有蔗或糖记载的地方,却没有这类记载,值得注意。第二,本书20—21页“琉球”条注⑦中讲到中国历史上的蔗和糖,没有新材料,不具引。只有几句话值得注意,“汉语蔗之复名,当由方言读成二字音,不能因此即视其为外来语之对音也。”下面在第二编还将谈到这个问题。
(5)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
《四库全书提要》说:“真腊本南海中小国,为扶南之属,其后渐以强盛。自《隋书》始见于外国传,唐宋二史并皆纪录。……元成宗元贞元年乙未(1295年),遣使招谕其国,达观随行,至大德元年丁酉(1297年)乃归,首尾三年,谙悉其俗,因记所闻见为此书,凡四十则,文义颇为赅赡。”此书最佳版本为夏鼐校注本,中华书局,1981年。现根据此书将有用资料抄录如下:
第151页(二十二)草木
惟石榴、甘蔗、荷花、莲藕、羊桃、蕉芎与中国同。
第158页(二十七)醖
酒有四等:第一等唐人呼为蜜糖酒,用药曲,以蜜及水中半为之。其次者,土人呼为朋牙四,以树叶为之。朋牙四者,乃一等树叶之名也。又其次,以米或剩饭为之,名曰包棱角。盖包棱角者米也。其下有糖鉴酒,以糖为之。又入港滨水,又有茭浆酒;盖有一等茭叶生于水滨,其浆可以釀酒。 〔7〕
5.外国人游记
正如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样,蒙古大帝国地跨欧亚大陆,驿站林立,畅通无阻,旅行之便利为亘古所未曾有。因此西方和阿拉伯国家来华的旅行家,为数颇多,其中著名的有穆斯林伊本·白图泰(Ibn Batuta)、天主教徒鄂多瑞克(Odoric,方豪《中西交通史》译为和德理)等,最著名的应当是众所周知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
在这些旅行家中,有一些人有自己撰写的或由别人记述的“游记”。游记虽然颇多,但是有关甘蔗和沙糖的记述却不是很多,而我最关心的正是这一部分。因此,我在这里不谈他们的旅行情况,我只在众多的记录中把有关蔗和糖种植和生产的资料抄录下来。
我根据的书籍主要有下面几种:
(1)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直译:亨利·玉尔,《中国与通往那里的道路》;1949年北京影印本译为《东域记程录丛》;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译为《古代中国闻见录》),共五册,1913—1916年,Hakluyt Society。
(2)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1930年,辅仁大学图书馆,共六册。
(3)方豪:《中西交通史》,台湾《华冈丛书》,共五册,1977年,台湾华冈出版有限公司。
以上三部巨著中,涉及到元代(还有别的朝代)外国旅行家的游记的地方颇多,但是与甘蔗和沙糖有关的记载,却不是太多。我在下面仅仅把与蔗和糖有关的资料抄录下来。至于元代同欧洲以及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国家的一般交通情况,留待下面(三)“外来影响”中去谈。对所抄录资料的分析与研究,也将在那里去完成。
抄录资料根据年代顺序:
(1)《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1254—1324年)
(2)《鄂多瑞克游记》(鄂多瑞克:1265—1331年)
(3)《索尔塔尼亚(Soltania)大主教游记》(约1330年)
(4)《伊本·白图泰游记》(伊本·白图泰:1304—1377年)
(1)《马可波罗游记》
在上列的游记中,这是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一部。版本极多,译本不少。中国也有几种译本,其中最好的是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1936年初版,1937年再版,商务印书馆 〔8〕 。我抄录资料就是根据这个译本。
我先想根据方豪《中西交通史》(三)第74—75页介绍一下马可波罗一家的情况,这对了解他的《游记》会有帮助的 〔9〕 。波罗一家为意大利威尼斯人,是巨商。蒙古军西征后,威尼斯更加繁华,可能也给波罗一家带来了好处。马可波罗之祖父曰安德勒·波罗(Andrea Polo),有三子:长曰马可(Marco,与我们的马可波罗同名——羡林按),次曰马飞奥(Mafio),幼曰尼古拉(Nicolo),是马可波罗的父亲。大哥老马可波罗卒于1260年(元世祖中统元年)。这一年,两个弟弟到了克里米亚;三年后,到了布哈拉,遇到元帝遣来的使臣,坚请波罗兄弟同行。忽必烈厚遇之,并请二人充其使臣,前往天主教廷。至元六年(1269年)回到欧洲。新当选的教皇派他们二人回访中国,尼古拉之子马可波罗随行,至元十二年(1275年)抵上都,见世祖。马可即习汉语,兼及蒙古、回鹘、西夏、西藏等文字,得到了世祖的宠爱,任官十七年。二十七年末或二十八年初(即1291年初),乃得西返,1295年(元贞元年)始回抵故乡,离家已二十三年了。马可波罗于1324年(泰定元年)去世。
下面抄录资料,章、页码都照冯译本:
125章,第496页 班加剌州 〔10〕 (孟加拉)
班加剌(Bangala)者,向南之一州也。基督诞生后之1290年,马可波罗阁下在大汗朝廷时,尚未征服,然已遣军在道。应知此州自有一种语言,居民是极恶偶像教徒,与印度(小印度)为近邻。其地颇多阉人,诸男爵所有之阉人,皆得之于此州。
其地有牛,身高如象,然不及象大。居民以肉乳米为粮,种植棉花,而棉之贸易颇盛,香料如莎草(Souchet)姜糖之属甚众。印度人来此求阉人及男女奴婢,诸奴婢盖在战争中得之于他州者也,售之印度商贾,转贩之于世界。
上面这一段记载,各种文字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里都有。平常容易见到的本子我不具引。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图书室中有一部英译本,颇为少见,这就是William Marsden从意大利文直接译成英文的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1818年出版于伦敦。上面这一段记载见于此书的卷二,第45章,第451—452页。
152章,第592页 大汗每年取诸行在及其辖境之巨额赋税
行在城及其辖境构成蛮子地方九部之一。兹请言大年每年在此部中所征之巨额课税。第一为盐课,收入甚巨。每年收入总数合金八十秃满(Toman) 〔11〕 ,每秃满值金色干(sequin)七万,则八十秃满共合金色干五百六十万,每金色干值一佛罗铃(Florin)有奇,其合银之巨可知也。
述盐课毕,请言其他物品货物之课,应知此城及其辖境制糖甚多,蛮子地方其他八部,亦有制者,世界其他诸地制糖总额不及蛮子地方制糖之多,人言且不及其半。所纳糖课值百取三,对于其他商货以及一切制品亦然。木炭甚多,产丝奇饶,此种出产之课,值百取十。此种收入,合计之多,竟使人不能信此蛮子第九部之地,每年纳课如是之巨。
上面这一段记载见于Marsden译本卷二,第49章,第544—545页。译文与冯译本稍有不同。“蛮子”,Marsden本作Manji,“色干”作saggi。Marsden本对于产糖数量之巨,只字未提。冯本“值百取三”,Marsden本作three and one-third percent(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
154章,第599—604页 福州国
从行在国最后之信州(Cinguy)城发足,则入福州(Fuguy)国境。由是骑行六日,经行美丽城村……上述之六日程行三日毕,则见有城名格里府(Quelifu),城甚广大,居民臣属大汗,使用纸币,并是偶像教徒。……再行三日又十五哩,抵一别城,名称武干(Vuguen),制糖甚多。居民是偶像教徒而使用纸币。
冯本引剌木学本之异文如下:
(注甲)离行在国最后一城名称吉匝(Gieza-Cinguy)之城后,入崇迦(Concha)国境,其主要之城名曰福州。……(第75章)
(注乙)行此国六日至格陵府(Quelinfu),城甚广大。……(第76章)
(注丙)自建宁府出发,行三日,沿途常见有环墙之城村,居民是偶像教徒,饶有丝,商业贸盛,抵温敢(Unguen)城。此城制糖甚多,运至汗八里城,以充上供。温敢城未降顺大汗前,其居民不知制糖,仅知煮浆,冷后成黑渣。降顺大汗以后,时朝中有巴比伦(Babylonie,指埃及)地方之人,大汗遣之至此城,授民以制糖术,用一种树灰制造。(第77章)
冯本还有一些注,现节引如下:
(注七)武干一地,似即尤溪。此城在延平府南直径48公里。菲力卜思(《通报》1890年刊224至225页)曾云:“自延平循闽江下行85里,至尤溪水汇流处,溯尤溪上行80里,抵尤溪县城。行人至此,舍舟从陆,而赴永春州及泉州府,是为自尤溪赴海岸常循之道。我以为剌木学本之温敢,应是今之永春,土语称此名与《波罗书》之温干(Unguen)颇相近也。”
余以为如谓其可对永春,亦可以对漳州北150公里之永安。但此二城距建宁皆远,而永安相距有87公里也。菲力卜思虽谓永春有一传说,昔有西方人至此,授以制糖术,然不能因此遽谓制糖之所,仅限于一地也。——参看《通报》1896年刊226页。
这一段记载,Marsden本与冯本颇有不同。冯本只说“制糖甚多”,而Marsden本则增添了不少的描述,几乎完全同上面征引的冯本(注丙)相同,这里不再抄录。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巴比伦”一词的解释。冯本说“指埃及”,而Marsden本则说:“‘巴比伦’应理解为巴格达城,这里技艺繁荣,虽然是处在蒙古鞑靼人统治之下。”(第557页,注1104)。
此外,关于Un-guen或U-gueu 〔12〕 (早期威尼斯节录本是这样写的),Marsden说,不管怎样,这是一座二等或三等城市,在福州府辖境内。(第556页,注1101)
第556页,注1102,Marsden引P. Martini的话说:On fait dans son territoire une trés-grande quantité de sucre fort blanc.“在(福州)境内,人们制造极大量的非常白的糖。”在这个注内,Marsden又引Martini的话说,这里讲的“制造”,仅仅是指“精炼”,因为制糖术最早见于四川,是由一个印度人引进的。羡林按:Martini在这里是把唐太宗派人到摩揭陀(印度)去学习制糖术同邹和尚在四川遂宁制造糖霜的故事混淆起来了。
第557页,注1103,Marsden说,这种湿软的未完成的糖,在东印度群岛许多地方被称为jaggri。
同页,注1105,Marsden解释上面引用的冯本(注丙)“用一种树灰制造”说,在使糖变成颗粒状的过程中,投入碱性物,是大家都知道的一种方法。
155章,第605页 福州之名贵
应知此福州(Fuguy)城,是楚伽(Chouka)国之都城,而此国亦为蛮子境九部之一部也。此城为工商辐辏之所。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臣属大汗。大汗军戍此者甚众,缘此城习于叛变,故以重兵守之。
有一大河宽一哩,穿行此城。此城制糖甚多,而珍珠宝石之交易甚大,盖有印度船舶数艘,常载不少贵重货物而来也。此城附近有刺桐(Zayton)港在海上,该河流至此港。
这里出了一个极大的问题。根据Marsden本第76章,不是福州,而是Kan-jiu也就是广州。冯本第606页(注一)说:“仅有剌木学本写此地名作漳州(Cangiu),不作福州。”羡林按:Kanjiu与Canjiu恐系一字,冯译为“漳州”,疑有问题。Marsden对这个问题写了一段相当长的注释。大意是,说此地是广州有困难。从行程上来看,从地理环境上来看,都讲不通;马可波罗讲的恐怕还是福州(第558页,注1106)。
我现在再介绍一部有关《马可波罗游记》的书,这就是A. C. Moule和Paul Pelliot(伯希和)的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George Routledge,London 1938。共两册,第一册是英译文,第二册是在Toledo发现的拉丁文本。世界学术界公认,这是有关《马可波罗游记》的最详备最有权威的本子。
我现将有关资料介绍如下。
上面介绍过的冯译本125章,第496页关于孟加拉情况的一段,在这个版本里是126,p. 295,全文翻译如下:
他们是非常坏的偶像崇拜者——要了解这些偶像崇拜者。他们处在印度边界上。有很多阉人,他们被阉割。在这个省里的所有的贵族们和所有的老爷们,都从这里获得许多阉人,用来保卫他们的太太们。这里也有牛,高如大象,但不像大象那样粗壮。省里的人大都食肉,喝奶,吃大米,这些东西这里很多。他们有足够的棉花,他们用棉花大做生意。他们是巨商大贾,因为他们有甘松和高莎草,产量极大,而胡椒、姜和糖也大量生产,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香料。
冯译本152章,第592页,在本版本里与之相应的是153,p. 341。有关段落翻译如下:
我告诉你,糖付税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甘蔗)长于此城及其所属地区,糖也在这里制造,此地为蛮子九部之一;糖也制于所说的蛮子国其他八部所有地区。此国产糖极多,较世界其余地区所制之糖多出一倍还多,许多人说的是真话;这是税收的极大的来源。
冯译本154章,第599—604页福州国,在本版本中与之相应的是155,p. 347。下面我只翻译与武干有关的一段:
在三日行程之后,又走了15哩,来到一座城镇,名字叫Vuguen(武干),这里制造极大量的糖。大汗宫廷中所食的糖皆取给于此城;糖极多,所值的钱财是没法说的。但是,你应当知道,在被大汗征服以前,这里的人不知道怎样把糖整治精炼得像巴比伦(Babilonie)各部所炼的那样既精且美。他们不惯于使糖凝固粘连在一起,形成面包状的糖块,他们是把它来煮,撇去浮沫,然后,在它冷却以后,成为糊状,颜色是黑的。但是,当它臣属于大汗之后,巴比伦地区的人来到了朝廷上,这些人来到这些地方,教给他们用某一些树的灰来炼精糖。
《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资料就介绍到这里 〔13〕 。
(2)《鄂多瑞克游记》
这一部游记中关于糖的资料见于Henry Yule上引书Ⅱp. 183—190。在抄译资料之前,先简略介绍一下鄂多瑞克(和德理)的生平,材料根据方豪上引书,第三册,第六节,第84—86页“和德理之东游及其贡献”。
鄂多瑞克,意大利弗黎乌里(Friuli)省乌地纳(Udine)人,1265年(世祖至元二年)生,是方济各会会士。1316年(仁宗延祐三年),起程来华,途经波斯、印度、锡兰、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占婆等地,在广州登陆。然后经泉州、金华等地抵杭州,后又至南京、扬州,由运河从临津、济宁而抵北京,居三年。后由陕西、四川入中亚,经波斯、亚美尼亚返抵故乡意大利,于1331年(至顺元年)在故乡逝世。
资料翻译如下:
离开了那个县,经过了许多城镇,我来到了一座华贵的城市,名字叫做Zayton(刺桐)) 〔14〕 ;在这里,我们低级圣职人员的修士有两座房子,我将为了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而以身殉道者的遗骨安置于此。
在这座城中有大量的人类生存所需要的各种物品。比如,你能够用比一groat(旧日英国四便士的银币——羡林注)一半还要少的钱买到三磅八两糖。
(3)《索尔塔尼亚大主教游记》
波斯索尔塔尼亚大主教有几个留传下来的名字。据此书内容所述,此书可能撰于1330年前后。此时的大主教是约翰·柯拉(John de Cora),他是意大利人,为多密尼根派僧人。他著有《大可汗国记》一书,原文为拉丁文,后译为法文。Henry Yule书中所收者为英文译本。这位大主教是否真正到过中国,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15〕 。
有关糖的资料,抄录如下:
Henry Yule译本:但是,他们有大量的糖,因此在那里糖非常便宜。(上引书,,p. 96)
张星烺译文:产糖甚丰,故价亦至廉。
(4)《伊本·白图泰游记》
伊本·白图泰的全名是Abu Abdu Llah Mahomed Ibn Batuta。他于公元1304年(回历703年,元成宗大德八年)2月24日,回历7月17日,中国农历正月十九日生于摩洛哥之丹吉尔港(Tangier)。22岁时即开始旅行,初游北非,后漫游巴勒斯坦、叙利亚等地,朝拜麦加二次。卒至印度,始见中国船,对此他有比较翔实细致的描述。在印度漫游后,经爪哇来到中国。所记有关中国之事物和城镇等,多出悬揣,有些地方他并没有到过。最后由泉州泛海,于1349年(至正九年)返回祖国。摩洛哥苏丹命白图泰口述,由苏丹秘书穆罕默德·伊本·玉萨(Mahomed Ibn Yuzai)笔录。著书时间前后仅三月,杀青于回历757年2月(公元1356年2月4日至3月3日,即至正十六年农历正月三日至二月二日之间)。同年伊本·玉萨卒,白图泰则卒于公元1377年5月10日起至次年4月30日(回历779年,明洪武十年农历四月三日至次年四月二日之间) 〔16〕 。
《伊本·白图泰游记》是中非或中阿关系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译本甚多,影响广被。现根据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5页,将有关蔗糖的一段抄在下面:
中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各种水果、五谷、黄金、白银,皆是世界各地无法与之比拟的。中国境内有一大河横贯其间,叫做阿布哈亚,意思是生命之水。发源于所谓库赫·布兹奈特丛山中,意思是猴山。这条河在中国中部的流程长达六个月,终点至隋尼隋尼。沿河都是村舍、田禾、花园和市场,较埃及之尼罗河,则人烟更加稠密。沿岸水车林立。中国出产大量蔗糖,其质量较之埃及蔗糖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葡萄和梨,我原以为大马士革的欧斯曼梨是举世无匹的唯一好梨,但看到中国梨后才改变了这种想法。中国出产的珍贵西瓜,很像花剌子模、伊斯法罕的西瓜。我国出产的水果,中国不但应有尽有,而且还更加香甜。小麦在中国也很多,是我所见到的最好品种。黄扁豆、豌豆亦皆如此。
与中国译文相应的英译文,见Henry Yule上引书Ⅳ,pp. 108—109。
6.笔记
同宋代相较,元代的笔记要少得多。这与朝代的久暂有关,是在意料之中的。但是,我在上面曾说到过,笔记这种体裁是中国文人所喜爱的。因此,元代也还是有一些笔记的。
同前面一样,我无法把元代所有的笔记都翻检一遍。我仅能从我翻检过的笔记中抄录一些有用的资料。
(1)《湛渊静语》
《四库全书提要》说:“《湛渊静语》二卷,元白挺撰。……元兵破临安时,(挺)年二十七矣。故其书于宋多内词……则食元之禄久矣,而犹作宋遗民之词,迨所谓进退无据者也。……然其他辨析考证,可取者多。其记汴京故宫尤为详备,在元人说部之中,固不失为佳本矣。”
资料如下:
866—290 采石蜜
羡林按:这里的“石蜜”,显然指的是岩石上所采之野蜂蜜,与以蔗糖制成者无关;但是,在上面的叙述中,“石蜜”一词常有混淆。所以在这里我也把它记了下来。以供参考,对比。
866—314 卷二 舟之最大者莫若木兰皮国。
羡林按:木兰皮,即今之北非摩洛哥一带,所谓马格里布。参阅《诸蕃志》卷上。
(2)《玉堂嘉话》
此书收录了元刘郁的《西使记》,上面4.“地理著作与中国人游记”中已介绍,兹不赘 〔17〕 。
(3)《庶斋老学丛谈》
此书收录了耶律楚材《西游录》,上面4.“地理著作与中国人游记”中已介绍,兹不赘。
(4)《东南纪闻》
《四库全书提要》说:“三卷,不著撰人名氏。”中间列举了许多缺点,然后说:“然大旨记述近实,持论近正,在说部之中,犹为善本。”
资料如下:
1040—218 卷三 九江岳肃之负山立屋,在湓城之中……
庆元初年五月,大雨,其巅,古冢出焉。……居数日,山
,圹周半堕,骨、发、棺、椁皆无存。两傍列瓦碗二十余……碗中有甘蔗节,有铜盆,类今厮罗。
1040—218 卷三 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本占城之贵人也。
7.农书
同唐宋相比,农书之多是元代的一个特点。从全部中国历史来看,绝大多数的统治者都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元代这样重农,并不奇怪。但是元代蒙古人本是游牧民族,本不知农业为何物。大概入居中原以后,也感到非重农不行。所以,元世祖于至元七年(1270年)即设司农司,掌管农桑水利,推广当时先进的耕作技术,并编写成书 〔18〕 。
《农桑辑要》
元司农司撰。七卷,包括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岁用杂事等内容。同《齐民要术》相比,桑、蚕增添了大量材料,又新添了许多作物种类和栽培法。对木棉的输入和栽培,有较详细论述,这一点颇值得注意。本书主要目的是为黄河流域农业服务的。但书中也记述了原在长江流域或长江以南的植物,如苎麻、茶、橙、橘、甘蔗等逐渐向华北平原扩展的情况。本书为元代三大农书之一,不但在国内影响广被,而且还流传国外,首先是朝鲜。
资料如下:
730—278至279 卷六
甘蔗
新添栽种法:用肥壮粪地,每岁春间耕转四遍,耕多更好。摆去柴草,使地净熟,盖下土头。如大都天气,宜三月内下种。迤南暄热,二月内亦得。每栽子一个,截长五寸许。有节者中须带三两节,发芽于节上。畦宽一尺,下种处微壅土高,两边低下,相离五寸,卧栽一根,覆土厚二寸,栽毕,用水绕浇,止令湿润,根脉无致淹没栽封。旱则三二日浇一遍。如雨水调匀,每一十日浇一遍。其苗高二尺余,频用水广浇之。荒则锄耘。并不开花结子。直至九月霜后,品尝秸秆,酸甜者成熟,味苦者未成熟。将成熟者附根刈倒,依法即便煎熬外,将所留栽子秸秆斩去虚梢,深撅窖坑,窖底用草衬藉,将秸秆竖立收藏,于上用板盖土覆之,毋令透风及冻损,直至来春,依时出窖,截栽如前法。大抵栽种者多用上半截,尽堪作种。其下截肥好者,留熬沙糖。若用肥好者作种,尤佳。煎熬法:若刈倒放十许日,即不中煎熬。将初刈倒秸秆,去梢叶,截长二寸,碓捣碎,用密筐或布袋盛顿,压挤取汁,即用铜锅内,斟酌多寡,以文武火煎熬。其锅隔墙安置,墙外烧火,无令烟火近锅,专一令人看视。熬至稠粘似黑枣合色,用瓦盆一只,底上钻箸头大窍眼一个,盆下用瓮承接。将熬成汁用瓢盛,倾于盆内。极好者澄于盆流于瓮内者,止可调水饮用。将好者即用有窍眼盆盛顿,或倒在瓦罂内亦可,以物覆盖之,食则从便。慎勿置于热炕上,恐热开化。大抵煎熬者止取下截肥好者,有力糖多。若连上截用之,亦得。
730—391 卷九
荔枝
取其肉,生以蜜熬作煎,嚼之如糖霜。然名为荔煎。
元代三大农书的其他二种:王祯《农书》和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中,没有找到与蔗和糖有关的资料。
8.类书
同唐宋比较起来,元代类书较少,有影响者更少。
(1)《韵府群玉》
《四库全书提要》说:“二十卷,元阴劲弦(时夫)撰。……然元代押韵之书,今皆不传,传者以此书为最古。又今韵称刘渊所并,而渊书亦不传。世所通行之韵,亦即从此书录出。是韵府诗韵皆以为大辂之椎轮,将有其末,必举其本。此书亦曷可竟斥欤!”
此书按韵部排列,每一字下有解释。我找的资料就在这些解释中,我依次抄录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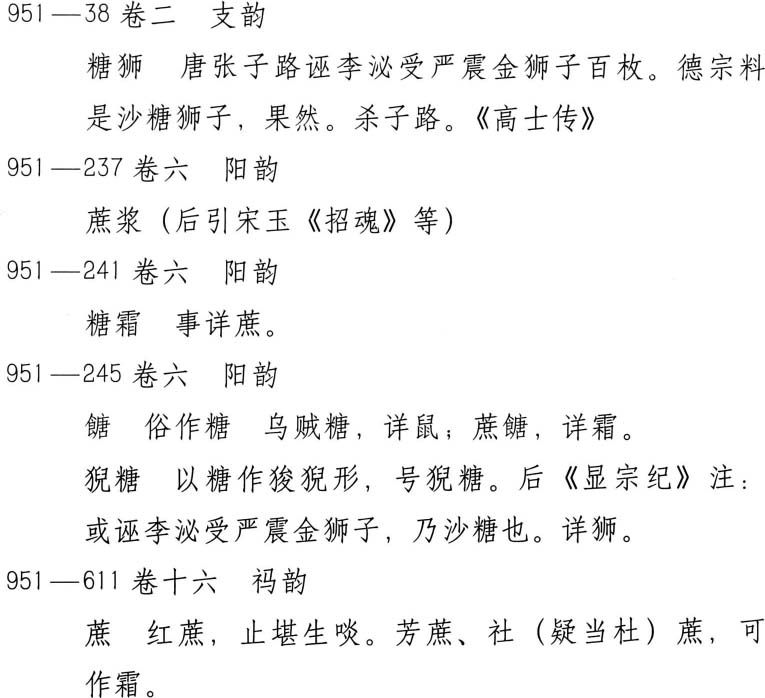
《本草》崑赤蔗。蔗白者曰荻蔗。《世说》扶风(疑当作南)蔗,一丈三节,见日即消,见风即折。唐僧邹和尚跨白驴登伞山。盐、菜、薪、米书于纸,系钱缗,遣驴负至市。人知为邹也,取平值,挂物于鞍,纵驴归。一日,驴犯黄氏蔗苗,请偿于邹。邹曰:“汝未知因蔗糖为霜,利十倍。”自是其法流行。宋野史:神宗问吕惠卿曰:“何草不庶出,独于蔗庶,何也?”曰:“凡草种之则正生耳。蔗,庶出也。”
蔗餳、鼠屎,详梅。吟咏:冰盘善(疑为荐)琥珀,何似糖霜美。——坡“远寄糖霜知有味。”——谷 遂宁糖霜见之文字者,始二公,盖遂宁蔗为最。
啖蔗 初味犹啖蔗。——韩 老境清闲犹啖蔗。——坡
压蔗 溜滴小漕如压蔗。——坡
射蔗 齐宜都王钟取甘蔗插地,目(百?)步蔗射之,十发十中。——史
倒餐蔗 顾恺之每食蔗,自尾至本,曰:渐入佳境。——《世说》
百挺蔗 宋孝武答魏主曰:知行路多乏,今付酒二器,其蔗百挺。——沈约《宋书》
写到这里,本章(一)“材料来源”本来已经可以算是写完了。但是,有一个问题还有待于解决。《永乐大典》是明朝的规模空前的类书;但是,在有关甘蔗和糖这个问题上,却讲的是元代的情况。是放在这里叙述呢?还是留待下一章明代?在反复思考之余,我决心在这里叙述,因此就拖了这个尾巴。
《永乐大典》,第一一九○七卷,引《广州府图经》 〔19〕 在“课利”一章中,讲到香山县“糖榨课钞二百九十四定一贯二百五十文”,下面还有。可见元代榨糖是要收税的,也可见糖的产量是相当大的,否则政府不会定为收税的对象。
在“土产”一章内有如下的记载:
大德三年(1299年),泉州路煎糖官呈,用里木榨水,煎造舍里别。
夹注说:
《南海志》云:“舍里别,蒙古语曰解渴水也。凡草木之汁,皆可为之。独里木子香酸,经久不变。里木,即宜母子。今本路番禹县城东厢地名莲塘,南海县地名荔枝湾创置。” 〔20〕
果部列举诸果中有“蔗” 〔21〕 。下面还有关于“甘蔗”的记述,今暂从略 〔22〕 。
(二)甘蔗种植和沙糖应用
元代的沙糖制造技术几乎没有什么记载,因此,我无法立专章来谈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只谈甘蔗种植和沙糖应用,想谈下列四个问题:
1.甘蔗种植的地域。
2.甘蔗种植的技术。
3.沙糖的药用。
4.沙糖的食用。
1.甘蔗种植的地域
我在这里只谈国内的情况,国外情况下面“外来影响”一段中再谈。
要谈元代甘蔗种植的地域,最可靠的依据当然是《元一统志》,其中有关资料已在上一段“材料来源”4.“地理著作与中国人游记”(1)中抄录了,请参阅。令人失望的是,《元一统志》这一部书似乎颇不完备。根据唐宋资料,本来应该有关于蔗和糖记载的地方,此书却付阙如。例子很多,其中最突出的应该是四川遂宁。本书卷五潼川府遂宁州,连“土产”这个项目都没有,更谈不到什么糖霜了。难道到了元代,此处的糖霜或者沙糖就突然停止了生产吗?这似乎不大可能。其他一些唐宋时代种蔗产糖的地域,可以依此类推。原因我想很可能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校辑本不完整,原书在明代就已成残篇。
在甘蔗种植地域问题上,最值得重视的一点是,甘蔗等原生长在长江流域或长江流域以南的农作物,逐渐向华北平原扩展。上引的《农桑辑要》中确能看到这种迹象,比如卷六“甘蔗”一条中说:“如大都天气,宜三月内下种。迤南暄热,二月内亦得。”好像是说,在大都能种植甘蔗。这情况是符合发展规律的。热带,特别是亚热带的植物,在中国来说,就是南方的植物,渐渐向北扩展,颇不稀见。甘蔗也属于这个范畴。我认为,这决不是由于气候的变化。气候是会变化的,但是所需时间极长,短期是不行的。这只能是由于人工的栽培。
再回头来谈《元一统志》。上面已经谈到,此书对唐宋以来著名的蔗和糖的产地没有有关蔗和糖的记载。可是此书卷九对广州路和潮州路的土产记载极为详尽。在几十种上百种的土产中,甘蔗占有一个地位。番禺、南海、东莞都产蔗,而且“乡村人煎汁为沙糖”,虽然不能像蜀汉川那样把沙糖制成狮子形,可是味道却远过柳城。柳城在什么地方呢?根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共有五个地方叫“柳城”,按照能否种蔗这个标准来衡量,只有广东的柳城墟合乎条件。此地位于广东河源县东北东江右岸,北接龙川县界。这里的地理方位是能够产蔗的。
总之,在元代,广东一些地方种甘蔗,而且能熬制沙糖。
2.甘蔗种植的技术
关于这个问题,上面“材料来源”7.农书《农桑辑要》有极为详尽细致的描述,请参阅,这里不再重复。
3.沙糖的药用
沙糖,还有甘蔗汁,在元代的药用范围,不算太大。我在上面(一)“材料来源”2.“本草和医书”这一节中引用了一些例子,有的例子说明,沙糖在元代被认为能治什么病;有的例子则说明,同唐宋相比,有一些病,例如目疾、咳嗽、误吞麦芒和鱼刺等等,唐宋使用沙糖和甘蔗汁,元代则否。请读者参考,这里不重复细说。
值得指出的是糖霜入药,治疗癣疮。在元代,糖霜同宋代颜色差不多,不是纯白,而是淡黄,有如琥珀。苏轼和黄山谷的诗可以证明这一点。元代洪希文的《糖霜》诗“色美鹅儿浅浅黄”,说得更加鲜明、具体。
还有糖毬子或糖毬或毬糖入药,好像是自元代开始。顾名思义,不管是哪一个名字,其中都有“糖”字,可见是由糖做成的,在药用中起作用的是糖。但是糖毬子等与蔗糖似乎又不尽相同。上引宋陈直《寿亲养老新书》,元邹铉续编,干荔枝汤药品中有蔗糖一味,夹注:“毬糖亦好”,可见二者不完全相同。什么叫“毬糖”?上引吴瑞的话:“稀者为蔗糖,干者为沙糖,毬者为毬糖,饼者为饼糖。”似乎只是形状的不同。
上引《元史·廉希宪传》告诉我们,希宪得了病,医生说要“用沙糖作饮”。那时候,糖极难得,皇帝只好御赐。可见在元代糖并不是随时随地可以得到的。
现在再来谈沙糖药用由唐至元范围越来越小的问题。十分合理的解释,目前我还不能够完全说明。我引《四库全书提要》对《汤液本草》说的一段话:“考本草药味不过三品,三百六十五名。陶弘景《别录》以下递有增加,往往有名未用。即本经所云主治,亦或古今性异,不尽可从。如黄连今惟用以清火解毒,而经云能厚肠胃,医家有敢遵之者哉!”(745—909)沙糖能否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呢?
4.沙糖的食用
沙糖的食用范围在宋代已经相当大了。到了元代,似乎更大了。宋代在这方面的资料,基本上都是民间的。在元代,民间的资料不多,我所依据的一本书《饮膳正要》,主要是讲宫廷中的饮膳。这似乎不够全面,但目前也只能如此。仅从这一本书就可以看到蔗和糖食用范围之广。读者请参阅上面从这一本书中抄录的资料,这里不重复。
特别要提出的是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饮食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虞集在给本书写的序中说:“噫!进书者可谓能执其艺事,又以致其忠爱者矣。”在这里,饮食已经被提高到忠君爱国的水平上,也就是伦理道德的水平上。这是以前没有见到过的。
(三)外来影响
在上面唐、宋两章里,我都提到了外来影响。到了元代,从我上面抄录的资料来看,由于政治环境的巨大变化,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中国文化沿着欧亚交通大道(不完全是丝绸之路),逐渐传入阿拉伯国家,传入欧洲。唐杜环《经行记》已经讲到了中国工匠到了阿拉伯。元代蒙古大军驰骋欧亚大陆,无远弗届。随军的一些能工巧匠,到了中亚、西亚一带,有的就留在了那里。结果是中国科技传入阿拉伯国家和欧洲。这种情况,透过中外一些历史资料,可以看到。
在另一方面,外国文化,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也传入中国。专就制糖术而言,中国在唐代以前已经能熬制沙糖。但是,唐太宗仍然派人到印度去学习制糖术。结果是中国制糖术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到了元代,阿拉伯国家的制糖术又传入中国。这与蒙古大军西征有密切的关系。结果是中国制糖术又大大地提高了一步。这一次提高的意义,较之唐代,更为重要。我甚至想称之为有划时代的意义。
下面分三项来探讨外来影响:
1.中阿关系。
2.白沙糖的炼制。
3.南洋一带的情况。
1.中阿关系
阿拉伯,中国古籍上往往称之为大食。在古代,中国同这一地区,一定就有交通往来。到了唐代,中国与大食的关系,豁然开朗。伊斯兰教也就是在唐代开始传入中国的。
中国同大食的外交和贸易关系,上面第五章唐代和第六章宋代已经谈了一些。这里只谈元代情况 〔23〕 。
元代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是多方面的。有军事政治方面的,有贸易方面的,也有科技文化方面的,以及民族方面的。
元代诸帝统率大军西征。战场之广阔,战线之漫长,都是空前的。蒙古大军一直打到今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古代译为报达。元军大将郭侃就曾攻占此城。大食帝国阿拔斯(Abbas)王朝覆灭。旭烈兀本来还想进军埃及,会蒙哥死,乃命怯的不花镇守叙利亚,率军回国。
在贸易方面,中阿之间有悠久的互相贸迁有无的历史。唐代已有大批的阿拉伯人到中国来做生意,有的久留不归。宋代继之,贸易兴隆,有增无衰。到了元代,虽因元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曾一度影响了对外贸易。但是,总起来看,中阿贸易仍然繁荣。元代有许多对外贸易港口,比如泉州、广州、杭州、宁波、扬州、澉浦、温州等等,在这些贸易港中,都有阿拉伯商人。
在科技文化方面,我想先引方豪先生的几句话:
元以前,传入中国之西域文化,皆属于波斯系即伊兰系者;元以后则阿拉伯色彩之回教文化,代表所谓西域文化。回教人挟其学艺以俱来,在“色目”人中特受蒙古人之重视。京师建立回回国子学,以专授阿拉伯语文,实为阿拉伯文化在中国发扬之最好说明。而最可注意者则为天文、历法、地理及炮术等。[上引书(三),第141页]
这一段话很有见地,事实正是这个样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看出中阿文化交流之硕果,这就是中国和阿拉伯地区动、植、矿物之交流。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张星烺,上引书第三册,第101—111页,我不再详谈。
所谓民族方面,我主要指的是民族同化。阿拉伯人同化于中国,不自元始,唐宋已然。到了元代,人数更多了,不但华化,而且入仕,陈援庵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论之极详,可参考。张星烺先生,上引书、册,第297—303页“元时阿拉伯人受华化及入仕中国者”,从《元史》中举出了一些例子,也可参阅。这里不再列举 〔24〕 。
综上所述,元代中阿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下面专门谈一个与糖有关的鲜明具体的问题,以证实中阿关系之重要。
2.白沙糖的炼制
从中国制糖史上来看,技术的进步集中表现在糖的颜色上:技术越精,颜色越白。中国古代《本草》和医书中有时候也有“白糖”一类的字眼。实际上那决不会是纯白的糖,不过颜色较之红黑色的糖略显淡黄而已。在唐代,中国糖和印度糖相比,有“色味逾西域远甚”的说法,味当然指的是甜,而色我认为指的就是白。《马可波罗游记》记载着,在福州境内,人们能炼制“非常白的糖”,不但“白”(blanc),而且还“非常”(fort),可见洁白的程度。
在上面引用的《饮膳正要》中,元宫廷中食用的有“沙糖”,还有“白沙糖”,说明二者之间还是有点区别的。
制造这种“白沙糖”的技术是从哪里来的呢?《马可波罗游记》中讲得非常清楚。在“福州国”一段里讲到一个叫做Vuguen(武干)的地方,大汗宫廷中所食之糖皆取给于此城。下面一段话十分值得重视:
但是,你应当知道,在被大汗征服以前,这里的人不知道怎样把糖整治精炼得像巴比伦各部所炼的那样既精且美。
这一下子就把制糖术与大汗的征服联在一起了。一方面,大汗征服了阿拉伯一些国家,从那里把制糖工匠带回中国;然后把这种技术传授给有制糖传统的福州地区的糖工。于是在被大汗征服前和后,此地的制糖术有显著的不同,水平大大地提高。过去此地只能熬制黑色的糖块。巴比伦地区的人来到此地以后,教本地人用一些树的灰来炼精糖,于是黑一变而为白了。树灰中含有一些化学成分,有利于使糖变白。这是合乎科学原理的。
现在要问:巴比伦是什么地方呢?我在上面已经谈了这个问题。学者们的意见不一致,不外两种意见:一个说巴比伦是埃及,一个说是伊拉克。我现在不想来费大力量解决这个问题。反正是不出阿拉伯的范围,这对我们来说就已经够了。
3.南洋一带的情况
我在上面(一)“材料来源”一段里,抄录了一些有关南洋一带产蔗用糖的情况。这个问题我想留待本书第二编第八章,“南洋一带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中去详细讨论,这里暂且不谈了。我只想提请读者注意《岛夷志略》中使用的“白糖”这个字眼,不叫“沙糖”,而称“白糖”,这也是颜色方面的问题。南洋一带制造“白糖”同阿拉伯国家有什么关系吗?值得进一步思考与探讨。
注释:
〔1〕 写到这里,我才听说,台湾已把全部二十五史输入电脑。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消息,十分值得我们重视。我临时想到了两点:第一,将来利用中国古籍研究学问,过去认为是最繁重最困难的搜集资料的工作,已经迎刃而解,可以大大地节省我们的力量了。这是一个福音,是社会前进的必然的结果,不足为奇。第二,我们的研究方法和精力分配的重点,必须相应地改变。资料固然重要,但是资料还不就是研究工作的一切。不管多完备的资料,其中必然有矛盾,有抵触。这就需要我们来解决,电脑是代替不了的。否则,今后就用不着什么学者,只要会操纵电脑,则学问之事毕矣。这哪是可能的呢?
〔2〕 《中国医学史》,主编甄志亚、副主编傅维康,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第219—223页、227—228。
〔3〕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湾版,745册。
〔4〕 同上,746册。
〔6〕 《异域志》,中华书局,1981年有陆峻岭点校本。第25页,“爪哇国”说:“古阇婆国也。”这对我下面提到的爪哇和阇婆问题的解决会有帮助,特记于此。
〔7〕 此外,元代还有几次赴南海招谕和出征的活动,一次是杨庭璧之出使,一次是史弼之远征爪哇。因为没有留下什么书,所以略而不谈。请参阅方豪《中西交通史》(三),第25—27页。
〔8〕 另一个译本是《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曼纽尔·科姆罗夫英译,陈开俊等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第二次印刷。
〔9〕 我同时也参考了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59—60页。
〔10〕 冯承钧原译,下同。
〔11〕 原书作Joman,误。
〔12〕 最后的字母u,恐怕n之误。
〔13〕 《马可波罗游记》版本极多,流传极广,影响极大。参阅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三册第四节“《马可波罗游记》及其流传”。
〔14〕 关于这个名字,参阅Henry Yule上引书Ⅱ,p. 183,注2。
〔15〕 这位大主教和这一部书的详细情况,参阅Henry Yule上引书Ⅲ,p. 36—37;张星烺,上引书,第二册,第234—250页。
〔16〕 关于伊本·白图泰及其《游记》,请参阅Henry Yule上引书Ⅳ,p. 1—79;张星烺,上引书,第三册,“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第108—219页;方豪,上引书(三),第90—93页。
〔17〕 本书卷二有一段话:“鹿庵先生曰:‘作文之体,其轻重先后,犹好事者以画娱客,必先示其寻常,而使精妙者出其后。予偶悟曰:此倒食甘蔗之意也。’”录之以供参考。
〔18〕 参阅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下册,第372—380页。
〔19〕 这一部书似已佚,看样子应该是元代著作,待查。
〔20〕 此书即系《大德南海志》。北京图书馆藏有此书,系海内孤本,仅存六—十卷。
〔21〕 在我的笔记本中,有一张自《永乐大典》第一一九○七卷抄出的资料。我现在想核对一下,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和教员阅览室中华版《永乐大典》,遍查无着,后来到北京图书馆觅得此卷。
〔22〕 韩儒林,上引书,下册,第372页。
〔23〕 一般的中阿关系,参阅张星烺,上引书,第三册,“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还有方豪,上引书(三)。
〔24〕 华化最著名的人物无过于蒲氏一家,请参阅方豪,上引书(三),第38—42页。
第八章 明代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1368—1644年)
这一章的写法仍然同唐、宋、元代一样。全章分为五大段:
(一)材料来源。
(二)甘蔗种植。
(三)沙糖制造和应用。
(四)白沙糖的出现(另列一章)。
(五)外来影响和对外影响。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它通过农民起义建立了汉族的政权,在国内实行残酷的高压政策,其残酷程度,较之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对外方面,同以前所有的朝代一样,始终有外患侵扰。我认为,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中国爱国主义之所以始终受到人民的高度重视与赞扬,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未有,其根源就在这里。这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解释,是完全实事求是的。外敌侵扰,同以前一样,主要来自北方。元代的后裔,虽被逐出中原,然而野心不死,仍然是虎视眈眈。但也有新情况,那就是,北方之敌之外,又增加了倭寇这个东方之敌。到了后期,欧洲的新兴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二者是密切联系的)国家侵入中国。这个侵入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给中国制造了麻烦,另一方面也给中国带来了西方文化。在整个明代,在对外关系方面有两件大事可提,一件事是郑和下西洋,一件事是上面刚才说到的欧风东渐。这两件事都是世界史上的大事,影响深远,一直到今天仍在发挥作用。这是世界学术界的共识,决不能等闲视之。
讲“糖史”我为什么这样在每一个朝代都刺刺不休地讲对外关系和外来影响呢?我几次强调过,我讲制糖历史,这方面的史实当然要讲;但是,我的重点是讲文化交流。既然讲文化交流,就不能不讲对外关系和外来影响,道理非常明白。
(一)材料来源
内容同唐、宋、元基本相同;但是时代毕竟变了,因此又稍有所不同。共分下列几项:
1.正史和杂史
2.本草和医书
3.诗文
4.地理著作和中国人游记
5.外国人游记和著作
6.笔记
7.科技专著
8.类书
1.正史和杂史
就明代来说,所谓“正史”,只有一种,就是《明史》。此书由清明史馆纂修,由张廷玉(1672—1755年)领衔。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此书凡四修,始自顺治二年(1645年),终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前后历时90年。是中国正史上量比较大的一种。
在其他方面,本书的得失我不必去评断。对于糖史的研究,材料却是惊人地少。按理说,这本是正常现象。一部主要是讲政治等国家大事的书,你哪能期望它会有多少关于甘蔗和糖这种微末不足道(我说的是那些纂修者大官们,对我这样专钻牛角的书呆子来说,则正相反)的东西的记载呢?
现在我把在翻检中沙里淘金似的找到的一点资料条列如下,为了使读者能够迅速方便地核对引文,我仍然用《四库全书》作为底本,册、卷、页都依文渊阁《四库全书》来注明。此书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册数号码悉按商务原装。《明史》是从297册至302册,共六大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