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史》(国内编)自序 *
这是拙著《糖史》的第一编——国内编。可以独立成书,因名之曰《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收入《东方文化集成·中华文化编》。
我对科技所知不多,但是我为什么又穷数年之力写成这样一部《糖史》呢?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意在写文化交流史,适逢糖这种人人日常食用实为微不足道,但又为文化交流提供具体生动的例证的东西,因此就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跑了几年图书馆,兀兀穷年,写成了一部长达七八十万字“巨著”。分为两编,一国内,二国际。西方研究糖史的学者已经写过的,我基本上不再重复。我用的都是我自己从浩如烟海的群籍中爬罗剔抉,挖掘出来的。
现在为什么把第一编称为《中华蔗糖史》呢?糖有广狭二义,广义的糖泛指蔗糖、甜萝卜糖,还有麦芽糖等等。我仅取其前者,以蔗糖为主,间亦涉及甜萝卜糖,因为这两种糖与文化交流密切相联,而后一种则无此作用,所以我略而不取。
书中有几章已在一些杂志上发表过。已经发表过的那一些章,我虽还没来得及同我的原稿细细校对;但是,根据我和别人的经验,在个别地方,难免为所谓“责任编辑”所改动过。如果改得对,我当然十分感激。可情况往往不是这个样子。在我的一篇文章中,我使用了“窸窣”二字,这并不是什么稀见的怪字,连小学生用的小词典中都有。可是我们的“责任编辑”却大笔一挥改为“蟋蟀”二字,真令我啼笑皆非。别的作者也有同样的不愉快的经验。兹事体大,这里先不谈。总之,本书中不管已经发表过或者尚未发表的章节,现在出版时,一律根据我的原稿。这决非我狂妄自大,吾不得已也。
但是,阅读一部长达三十五六万字的书稿,确是一件苦事。我现在年迈昏聩,“老年花似雾中看”,字比花更难看,我已无此能力。只好请我的学生王邦维教授担任这一件苦差事。他精通汉语古典文字,又通多种外语,他是完全能胜任的。对我来说,在垂暮之年,这是一件难得令人愉快的事情。
现在采用这种分开来出书的办法,是应急之举,不得已而为之的。将来两编合为一书,仍称《糖史》,加入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文集》中。
1996年6月5日
注释:
* 此序原是作者为《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一书所写的序,此次收入《全集》,改为现题。序文内的书名仍保持1996年写序时的原貌。
引 言
缘 起
我不是自然科学家。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等重要的自然科学分支,我最多也不过是中学水平。为什么竟忽发奇想写起什么《糖史》来了呢?
这有一个颇长的过程,我先谈上一谈。
人们大概都认为,糖是一种十分微末不足道的东西。虽然我们日常生活几乎是离不开糖的,吃起甜甜的,很有滋味——我们不能够想象,如果没有糖的话,我们的生活将是什么样子;但是,恐怕很少有人注意到,考虑到,猜想到,人类许多极不显眼的日用生活品和极常见的动、植、矿物的背后竟隐藏着一部十分复杂的,十分具体生动的文化交流的历史。糖是其中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
我是从什么地方,从什么时候起,注意到“糖”这种东西背后隐藏着一段不寻常的历史呢?只要看一看现代西方最流行的语言中表示“糖”这种东西的单词儿,就可以一目了然:
| 英文 | sugar |
| 德文 | zucker |
| 法文 | sucre |
| 俄文 | caxap |
| 意大利文 | zucchero |
| 西班牙文 | azúcar |
另外表示“冰糖”的单词儿:
| 英文 | candy |
| 德文 | kandis-zucker 此外还有一个动词 |
| kandieren | |
| 法文 | candi,sucre candi |
| 俄文 | κандированный caxap |
| 意大利文 | candito |
| 西班牙文 | candi |
我举的例子不要求全面,那是没有必要的。只从几个主要语言中就可以看出,表示“糖”和“冰糖”这两种东西的单词儿,在这些语言中同一个来源,都是外来语。既然是外来语,就说明,“糖”和“冰糖”这两种东西不是在这些国家中产生的。
这些外来语都来自印度吠陀语和古典梵文的śarkarā,还有kha
 aka,巴利文sakkharā。这说明,欧洲的“糖”和“冰糖”是从印度来的。这两种东西从印度传入欧洲不是直接的,而是经过波斯和阿拉伯的媒介。这个问题在下面本文中还要谈到,这里不过提纲挈领地提上一句而已。
aka,巴利文sakkharā。这说明,欧洲的“糖”和“冰糖”是从印度来的。这两种东西从印度传入欧洲不是直接的,而是经过波斯和阿拉伯的媒介。这个问题在下面本文中还要谈到,这里不过提纲挈领地提上一句而已。
中国怎样呢?中国同欧洲不同,我们很早就知道了甘蔗,后来又能从蔗浆炼糖。这些都是欧洲没有的。但是,中国在制糖的过程中,也向印度以及阿拉伯国家和波斯学习了一些东西。《新唐书》二二一上:
贞观二十一年,(摩揭陀)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拃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
《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
并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东夏。寻敕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
两部书讲的应该是一件事。这说明,中国确实从印度学习过制糖术。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写经残卷中,有一页的背面上用非常拙劣的笔法写着有关制造煞割令(śarkarā的音译,汉文是“石蜜”)的一段话,从字体上来看,不是出自文人学士、有道高僧之手。在根本不产甘蔗的临近沙漠的敦煌地区,似乎是一个工匠的人竟然写了这样一段话。可见制石蜜术已经深入老百姓中。既然用了一个从梵文借来的外来语“煞割令”,其来自印度,当已不成问题。
然而,在另一方面,印地文中有一个单词儿cīnī(中国的),意思是“白糖”。这又肯定说明了印度从中国学习炼制白糖的方法,或者从中国输入白糖。
中印两国在制糖方面互相学习,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这个事实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在印度学范围内,我在德国时专治佛典混合梵语。回国初期,我缺少这方面最起码的图书报刊,不得已而暂时来了一个小改行,转而治中印文化关系史。我对上述互相学习的事实感到兴趣,是非常自然的。我于是就开始留意这方面的著作。在欧洲方面,我读过两部巨著:
Lippmann:Geschichte des Zuckers(《糖史》)
Noel Deerr:The History of Sugar(《糖史》)
还有一些论文。在印度方面,迄今还没有见到类似《糖史》的著作。但在古代文献里,包括佛教和婆罗门教(印度教)等教派,有大量关于甘蔗和糖的记述,有极大的史料价值。此外,还有两部非常重要的书:
Suśruta Sa hitā 《妙闻本集》
hitā 《妙闻本集》
Caraka Sa hitā 《羯罗伽本集》
hitā 《羯罗伽本集》
以及一些书中有关的记载。所有这一些书都大大地扩大了我对于甘蔗和糖的知识,提高了我对于这个问题的兴趣。
在中国当代学人中,颇有一些人注意到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的问题。我读到下列诸文:
吉敦谕:《糖和蔗糖的制造在中国起于何时》,《江汉学报》,1962年第9期,第48—49页。
同上:《糖辨》,《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第181—186页。
吴德铎:《关于〈蔗糖的制造在中国起于何时〉》,《江汉学报》,1962年第11期,第42—44页。
同上:《答〈糖辨〉》,《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第150—154页。
袁翰青:《中国制糖的历史》,见《中国化学史论文集》。
于介:《中国经济史考疑二则,白糖是何时发明的?》,《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第82—84页。
李治寰:《从制糖史谈石蜜与沙糖》,《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146—154页。
同上:《中国食糖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
周可涌:《中国蔗糖简史·兼论甘蔗的起源》,《福建农学院学报》,第13卷,第1期,1984年。
此外还有一些篇幅比较短的文章,不一一列举。在这些学者中,李治寰先生是专门研究中国制糖史的。他既懂科技,又通历史,因而创获独多,成就最大。
除了上面列举的这些书和文章以外,中国古典文献中有大量关于甘蔗种植和蔗糖制造的书,我也一一读过了,详情下面再谈。
读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书以后,我不但了解了有关甘蔗和糖的一些情况,而且也了解了在这方面中国与印度、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交流的事实。我觉得后者更为重要。我一向认为,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研究人类历史,不能不研究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可以见到,在科技方面也能找到。甘蔗种植和蔗糖制造属于后者。因此,即使我不通科技,也想在这方面做些探索工作,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上来探索。
这就是我写《糖史》的最根本的缘起。
资 料
研究任何一门学问,都离不开文献资料,不需要科学实验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更是如此。
我在上面列举的我读过的专著和论文,都属于资料的范畴。下面在我的叙述中,在适当的地方将要加以引用,这里不再谈。我现在想集中谈一谈中国古典文献中的资料,因为这些资料有一些特殊性。对于这些文献典籍我在这里也只做一般的介绍,详细内容都将见于下面的论述中。对于这些资料的介绍,我也不求全。我只举出几个著名的例子。我的目的只在说明,研究糖史这一门学问,同一些别的学问一样,中国人有得天独厚的地方。中华民族是一个异常爱好历史的民族,在全世界民族之林中,实无其匹。中国的历史著作,是中国人对整个人类文化的一大贡献。其意义决不能低估。
我在下面基本上按历史顺序介绍一些与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有关的中国古典文献。
《异物志》
自后汉一直到魏晋南北朝,中国人对所谓“异物”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异物”就是“奇异之物”,多半产生于中国边疆地区和外国。当时出现了很多《异物志》,头绪纷繁,互相抄袭;有时候作者和产生时代都很难弄清楚。为了说明情况,我现在把清张澍的《凉州异物志·序》抄在下面,这篇序对这个十分纷乱的问题做了言简意赅的叙述:
澍按:王伯厚《玉海》云:《隋志》:后汉议郎杨孚纂《异物志》一卷。一云《交州异物志》。《水经注》引作《南裔异物志》。吴丹阳太守万震《南州异物志》一卷,朱应《扶南异物志》一卷。《唐志》: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陈祈畅《异物志》各一卷。房千里《南方异物志》、孟琯《岭南异物志》各一卷。又《文选·注》引谯周《异物志》,即《史记正义》所引《巴蜀异物志》也。《文选·注》又引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一切经音义》引薛珝《异物志》。《隋志》作薛翊。《晋书》续咸著《异物志》十卷。《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引曹叔雅《异物志》。《太平寰宇记》引作《叔雅庐陵异物志》。苏颂《本草》引徐衷《南州异物志》。《史记正义》引宋膺《异物志》。是异物有志,在昔繁矣。而《凉州异物志》著于隋唐志,隋一卷,唐二卷。《博物志》、《水经注》均引作《凉土异物志》。惜不传作者姓字。观其写致敷词,颇谐声律,采藻精华,方诸万氏,又未尝不叹其散佚也。宋膺《异物志》,隐匿鲜章,史注所引,多说西方。且月氏羊尾,文与《凉州异物志》全同。《太平广记》引《凉州异物志》羊子生土中,文亦与宋膺《异物志》同。疑《凉州异物志》即宋膺所纂。汉晋之时,敦煌宋氏俊才如林,文采多丽,亶其然乎。以无左证,未能质言耳。
张澍把《异物志》的问题说得很清楚。虽《异物志》中所言,与我要研究的问题有关者,仅限于甘蔗。但却能启发我想到许多问题,是非常有用的资料。
晋嵇含(262—306年)撰的《南方草木状》三卷,应该归入此类。
《齐民要术》
北魏贾思勰撰。成书于公元533—544年间。此书引用先秦至魏晋古籍一百余种,农谚二十余条,还有探询老农的资料。全书十一万多字,共九十二篇,较系统地总结了6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经验,是我国现存的最早最有系统的农业科学著作,也是世界科技史上最可宝贵的农学文献之一,被中国和世界的农学家视为瑰宝。
《糖霜谱》
宋王灼撰,一卷。约成书于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全书共七篇:“原委第一”,述唐大历(766—780年)中始创糖霜之事。其后六篇,皆无篇名。第二篇讲制蔗糖始末。第三篇讲种甘蔗方法。第四篇讲选糖之器。第五篇讲制糖之法。第六篇讲制糖结霜与否的原因。第七篇讲糖霜之性味和制食诸法。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讲制糖霜方法的书,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的第一部。因此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王灼,四川遂宁人。遂宁自唐代起即以制糖术名闻全国。王灼之所以写这一部书,之所以能写这一部书,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与王灼同时而稍后的著名学者洪迈(1123—1202年),对王灼的著作非常感兴趣。他把王灼七篇的内容压缩了一下,写成一篇不太长的文章。他写道:
宣和(1119—1126年)初,王黼创应奉司。遂宁常贡外,岁别进数千斤。是时所产益奇,墙壁或方寸。应奉司罢,乃不再见。当时因之大扰,败本业者居半。久而未复。遂宁王灼作《糖霜谱》七篇,具载其说。予采取之,以广闻见。(见《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
王灼原书,版本颇多。李治寰:《中国食糖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收入“附录”。
《本草纲目》
明李时珍(1518—1593年)撰,五十二卷。中国古代以《本草》名书者,颇有几本。最古的当推《神农本草》。北宋唐慎微(1056—1063年)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共三十一卷。到了李时珍,以《证类本草》为底本,结合自身经验,遍访名医宿儒,广搜民间验方,亲自观察收集药物标本,深山旷野,无所不至,参阅八百余古代文献,历时二十七年,三易其稿,撰成此书,完成于万历六年(1578年),约一百九十万字,可谓集《本草》之大成者。本书总结了我国16世纪以前的药学理论,对研究生物、化学、地质、地理、采矿等等方面,都有参考价值。不但在中国有广泛的影响,在世界上也被誉为“东方医学巨典”,有多种外国文字的译本。
《天工开物》
明宋应星(1587—1666年)撰,三卷。宋应星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至十一年(1638年)任江西省分宜县(今宜春地区分宜县)儒学教谕。在此期间,他撰成此书。卷上分为“乃粒第一”,讲谷物;“粹精第二”,讲谷物加工;“作咸第三”,讲制盐;“甘嗜第四”,讲制糖、养蜂;“膏液第五”,讲食油;“乃服第六”,讲纺织;“彰施第七”,讲染色。卷中分为“五金第八”;“冶铸第九”;“锤锻第十”;“陶埏第十一”;“燔石第十二”。卷下分为“杀青第十三”,讲造纸;“丹青第十四”;“舟车第十五”;“佳兵第十六”,讲兵器和火药;“曲蘖第十七”,讲造酒;“珠玉第十八”。
从这个简略的内容介绍中就可以看出本书内容之丰富,几乎涉及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各个方面。它确实是中国明代生产知识和工艺技术的总结,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代表作,在世界科技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它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的影响至深且广。在中国有很多刊本,在国外有很多译本。中国迄今最好的版本是潘吉星著《〈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巴蜀书社,1989年。此书上篇是“《天工开物》研究”,下篇是“校注”。在“研究”中,著者首先论述了《天工开物》产生的时代背景,然后谈宋应星的事迹,接着讲此书的科学技术成就和它在科学史上的地位,讲它的国际影响,讲它的版本,最后讲本书所引文献探原。
潘著是一本非常优秀的著作。
我现在不再列举单本的书,而是综合地按照类别介绍一些有关的著作。
第一类是正史。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中华民族是最爱历史的民族。每一个朝代都有一部叙述这个朝代全部历史的书,几乎都是官修的,几千年来没有间断。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隋书》卷三三《经籍志》说:“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意思是“正史”自司马迁和班固算起,一般的说法是“二十四史”,也有“二十五史”之说。二十四史的内容和体例,由于有因袭的关系,所以大同小异。书中不但叙述各有关朝代的历史,也涉及外国情况。研究中外文化交流,是不可或缺的典籍。中国同印度的关系,其中颇多记述。关于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情况,就见于《新唐书》二二一上《西域列传·摩揭陀》。
正史之外,还有所谓“杂史”等,也有与我的研究有关的资料,这里不谈了。
第二类是地志。
所谓舆地之书,亦曰地方志。这一类书籍在中国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省有省志,比如《云南通志》之类;府有府志,县有县志,比如《遂宁县志》之类。里面详细地记录了本省、本府、本县各方面的详细情况,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在有关的省、府、县志中,往往可以找到有关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的记述,是研究中国糖史重要的资料。
第三类是笔记。
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著述体裁。“笔记”,就是随笔记录。这种书籍的量异常大,从古代就有。尽管不一定用“笔记”这个名称,内容则是一样的。一个读书人有所感,有所见,读书有点心得,皆随笔记下。不一定按内容分类。看起来十分庞杂,实则资料对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都非常有用。精金美玉,随处可见,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各取所需。对于中国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在许多笔记中可以找到许多别的地方找不到的资料。这一类书多得无法一一列举,我在这里只举几个例子:明刘献廷的《广阳杂记》,明王世懋的《闽部疏》,明高濂的《遵生八笺》,明陈懋仁的《泉南杂志》,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等等。
上面介绍了我使用资料的特点,换句话说,我把重点放在使用中国古典文献中的资料上。这决非是我的偏见,我只是面对事实,面对现实,离开了中国资料,我的《糖史》是没有法子写的。这是我们中国研究这一门学问的学者得天独厚之处,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者便是。外国学者在这方面是相形见绌的。
我决无意贬低外国的历史资料,古代特别是中世纪外国许多国家也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著作,特别是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一些学者和旅行家的著作,其中有很多涉及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的资料,都是非常珍贵的。治此学者决不能轻视或忽视。
做 法
我这一部书,虽然也名之为《糖史》,但是同Lippmann和Deerr的同名著作却有一些显著不同之处。第一,我的书中,虽然也难免涉及一些科技问题;但是,我的重点却不在这方面。我不想写一部科学技术史,而是想写一部文化交流史。第二,根据上面这个想法,我把重点放在中国。我只用一章来讲欧、非、美三大洲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在这方面我不求全面。Lippmann和Deerr讲过的我基本上不再重复。我只是利用我自己找到的材料,独立地写我自己探索的结果,至多也不过是这些学者的著作的一个补充。我把本书第一编的篇幅全部用来写中国,而把第二编——国际编绝大多数的篇幅用到叙述中国在种蔗制糖方面与印度、南洋、伊朗和埃及的交流情况。
目 的
最后,我想讲一讲本书的目的。
我希望,我这一本书能成为一本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讲的科学著作。删除废话,少说空话,不说谎话。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因此,在很多地方,都必须使用严格的考据方法。为了求真,流于烦琐,在所难免。即使受到某一些反考据斗士的讥诮,也在所不辞。
但是,我决不会为考据而考据。在很多地方我都说过为考据辩护的话。原因就是,我认为考据是有用处的,写科学著作必不可少的。没有清代那一些考据大师的工作,我们的古代典籍能读得懂吗?即使是为考据而考据,也是未可厚非的。可是我仍然不想那样做。我希望能够做到于考据中见义理。换句话说,我希望把自己的一些想法通过考据工作弄清事实的真相然后表达出来。先师陈寅恪先生为国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他于考据最擅胜场,因此颇招来一些非议。但是,我窃以为寅恪先生实不同于清代许多考据大师。在极其严格的甚至貌似流于烦琐的考据的后面,实在隐藏着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一种义理,一种“道”。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寅恪先生颇乏解人。他曾多次赞美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对“天水一朝”的文化颇为推崇。从表面上看起来,颇难理解。深入思考,就不难理解他的用意之所在。这一点,现在理解的人越来越多了。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以予驽钝,焉敢望先师项背!但是,在过去颇长的时间以内,我通过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些想法。这些想法,由支离到完整,由模糊到清晰,由抽象到具体,终于颇有了一点体系。我想通过现在这一本书,把这些想法表达出来。我的想法是什么呢?简短点说,就是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进步,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尽管需要的时间会很长很长,道路会非常坎坷弯曲,这个目标必然要达到,这是我深信不疑的。
当前,由于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发达,地球实际上变得越来越小了,不同的人民和民族靠得越来越近了。然而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能够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也越来越暴露出来了。如果人类还想顺利地在这个地球上共同生活下去的话,人类应该彻底改弦更张,丢掉一直到现在的想法和做法,化干戈为玉帛,化仇恨为友爱,共同纠正人类在过去所犯下的错误,同心戮力,同自然搏斗。我个人认为,今天的人类应当有这个共识。
但是,可惜得很,居今之世,懵懵懂懂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大有人在。我个人人微言轻,我所能做到的事情是很有限的。即使是力量很有限吧,我也不甘心沉默。我的一个小小的希望就是通过我这一本《糖史》,把一个视而不见的历史事实揭露给大家,让大家清醒地意识到,在像糖这样一个微末不足道的日用食品的背后,居然还隐藏着一部生动的人类文化交流史。从这一件小事情上,让人们感觉到实在应该有更多的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有更多的互相帮助互相依存的意识,从而能够联合起来共同解决一些威胁着人类全体的问题,比如人口问题、环保问题、资源问题、粮食问题、自然界生态平衡的问题,甚至还有淡水问题、空气问题,等等,等等。人类再也不应当鼠目寸光,只看到鼻子底下那一点小小的利益了。这样下去,有朝一日,整个人类会面临着威胁自身生存的困难。
如果我这样一个素来不重视义理,不重视道的人,今天也想宣传一点义理,宣传一点道的话,就让这一点想法成为我的义理,成为我的道吧。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应该大力提倡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不能算是一门新兴学科;但又似乎是一门新兴学科。因为,尽管中国从20年代起就有了这方面的著作,可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很多颇有水平的著作,许多大学的历史系不见得都能开出这样一门课,社会上的重视也很不够。这方面的学会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已经做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工作;可是我总觉得,中外文化交流史还没有成为一门有理论、有纲领的独立的学科。我诚恳地希望,我们国家,甚至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志同道合、有志有识之士,能够多方协作,共同努力,写出一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也可以就某一事件或某一事物,比如说类似糖这一类的事物,经过认真探讨,不尚空论,写出一些比较让人满意的专著;在这些专著的基础上,到了适当的时候,写成一部或多部世界文化交流史。到了那时候,我们人类的共识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人类的前途看起来就会比现在更光明。跂予望之!
第一章 飴 餳餹
餳餹
现在要写《糖史》,无法像写其他一些事物的历史那样,能够追溯到渺茫的远古去。因为糖或其他糖的变种是很容易消失的东西,不能在地下保留很长的时间。考古工作对我们的这项研究不能提供任何帮助。因此我现在唯一依靠的就是古代文献记载。
按时代顺序,这一章应该放在第二章的位置上,因为它涉及先秦,又深入汉代。但是,我觉得,如果我选出的飴、 、餳、餹四个字其确切含义得不到界定,研究先秦和汉代的糖的问题,都会有极大的困难。所以我就决心先解决这四个字的问题,然后再按时代顺序继续写下去。
、餳、餹四个字其确切含义得不到界定,研究先秦和汉代的糖的问题,都会有极大的困难。所以我就决心先解决这四个字的问题,然后再按时代顺序继续写下去。
在这四个字中,正式见于先秦古籍的只有一个飴字,比如《诗·大雅·緜》:“周原
 ,堇荼如飴。”《礼记·内则》:“子事父母,枣栗飴蜜以甘之。”《山海经·南山经》有“其味如飴”的话。tang这个音也已出现,比如《楚辞·招魂》:“粔籹、蜜饵,有
,堇荼如飴。”《礼记·内则》:“子事父母,枣栗飴蜜以甘之。”《山海经·南山经》有“其味如飴”的话。tang这个音也已出现,比如《楚辞·招魂》:“粔籹、蜜饵,有
 些。”据学者们的意见,“
些。”据学者们的意见,“ ”字取其双声,“
”字取其双声,“ ”字取其叠韵,合起来就成为“tang”,至于用哪个字来表示,则我们现在还无法确知。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讨论。
”字取其叠韵,合起来就成为“tang”,至于用哪个字来表示,则我们现在还无法确知。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讨论。
到了汉代,陆续出现了 、餳、餹等字。这些字决不仅仅是单个的字,它们背后隐藏着一部制糖史,对我们很有启发。我现在就对这几个字进行一些分析。
、餳、餹等字。这些字决不仅仅是单个的字,它们背后隐藏着一部制糖史,对我们很有启发。我现在就对这几个字进行一些分析。
研究古文字离不开《说文》,而要研究《说文》,又离不开清代几个朴学大师的有关著作。其中最著名、创获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推段玉裁(1735—1815年)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异常推崇这一部书,说“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我的分析主要依靠这一部书,旁及桂馥(1736—1805年)、朱骏声(1788—1858年)等人的有关著作。
我首先把段书中的有关资料抄在下面。段书中引证多,提出的问题多,解决的问题也多,所以我抄得比较详尽。这样一来,实际上是避免了我再加以引证,节约了篇幅。
飴(《说文解字注》五篇下)
正文:米糱煎者也。
注:者字今补。米部曰:糱,芽米也。火部曰:煎,熬也。以芽米熬之为飴。今俗用大麦。《释名》曰:餳,洋也。煮米消烂,洋洋然也。飴,小弱于餳,形怡怡也。《内则》曰:飴蜜以甘之。
正文:从食,台声。
注:与之切,一部。
下面是一个籀文飴字,正文:从異省。
餳
正文:飴和馓者也。
注:不和馓谓之飴,和馓谓之餳。故成国云:飴弱于餳也。《方言》曰:凡飴谓之餳,自关而东,陈楚宋卫之间通语也。”杨子浑言之,许析言之。《周礼·小师》注:管,如今卖飴餳所吹者。《周颂》笺亦云。
正文:从食,昜声。
注:各本篆作 ,云易声,今正。按餳从昜声,故音阳,亦音唐,在十部。《释名》曰:餳,洋也。李轨:《周礼》音唐是也。其陆氏音义,《周礼》辞盈反,《毛诗》夕清反。因之《唐韵》徐盈切。此十部音转入于十一部,如行庚觥等字之入庚韵。郭璞《三仓解诂》曰:杨,音盈协韵。晋灼《汉书音义》反杨恽为由婴,其理正同耳。浅人乃易其谐声之偏旁。《玉篇》、《广韵》皆误从易。然《玉篇》曰:
,云易声,今正。按餳从昜声,故音阳,亦音唐,在十部。《释名》曰:餳,洋也。李轨:《周礼》音唐是也。其陆氏音义,《周礼》辞盈反,《毛诗》夕清反。因之《唐韵》徐盈切。此十部音转入于十一部,如行庚觥等字之入庚韵。郭璞《三仓解诂》曰:杨,音盈协韵。晋灼《汉书音义》反杨恽为由婴,其理正同耳。浅人乃易其谐声之偏旁。《玉篇》、《广韵》皆误从易。然《玉篇》曰: ,徒当切。《广韵》十一唐曰:糖,飴也。十四清曰:
,徒当切。《广韵》十一唐曰:糖,飴也。十四清曰: ,飴也。皆可使学者知餳糖一字,不当从易。至于《集韵》始以餳入唐韵、
,飴也。皆可使学者知餳糖一字,不当从易。至于《集韵》始以餳入唐韵、 入清韵,画分二字,使人真雁(
入清韵,画分二字,使人真雁( )不分,其误更甚。犹赖《类篇》正之。餳,古音如洋,语之转如唐,故《方言》曰:餳谓之餹。郭云:江东皆言餹,音唐。
)不分,其误更甚。犹赖《类篇》正之。餳,古音如洋,语之转如唐,故《方言》曰:餳谓之餹。郭云:江东皆言餹,音唐。
段注关于 和餳,就抄这样多。
和餳,就抄这样多。
段玉裁在这里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最主要的是改 为餳。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均未改。《四部丛刊》景宋本《说文》和《方言》,均作
为餳。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均未改。《四部丛刊》景宋本《说文》和《方言》,均作 ,而不作餳。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谈。其次,段注把飴和餳的区别说得非常清楚。《说文解字》本已交待清楚:餳,飴和馓者也。但是段玉裁在注中又着重加以区分。他对馓字也作了详细注解,里面有几个地方很重要,我也抄在下面。
,而不作餳。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谈。其次,段注把飴和餳的区别说得非常清楚。《说文解字》本已交待清楚:餳,飴和馓者也。但是段玉裁在注中又着重加以区分。他对馓字也作了详细注解,里面有几个地方很重要,我也抄在下面。
馓
正文:熬稻
 也。
也。
注: ,依《韵会》从食。各本作
,依《韵会》从食。各本作 。盖因许书无
。盖因许书无 改之耳。《楚辞》、《方言》皆作
改之耳。《楚辞》、《方言》皆作
 。古字盖当作张皇。《招魂》:有
。古字盖当作张皇。《招魂》:有
 些。王曰:
些。王曰:
 ,餳也。《方言》曰:餳谓之
,餳也。《方言》曰:餳谓之
 。郭云:即干飴也。诸家浑言之,许析言之。熬,干煎也。稻,稌也。稌者,今之稬米,米之黏者。煮稬米为张皇。张皇者,肥美之意也。既又干煎之,若今煎粢饭然,是曰馓。飴者,熬米成液为之。米谓禾黍之米也。馓者,谓干熬稻米之张皇为之。两者一濡一小干,相盉合则曰餳。此许意也。杨、王、郭以餳飴释
。郭云:即干飴也。诸家浑言之,许析言之。熬,干煎也。稻,稌也。稌者,今之稬米,米之黏者。煮稬米为张皇。张皇者,肥美之意也。既又干煎之,若今煎粢饭然,是曰馓。飴者,熬米成液为之。米谓禾黍之米也。馓者,谓干熬稻米之张皇为之。两者一濡一小干,相盉合则曰餳。此许意也。杨、王、郭以餳飴释
 ,浑言之也。豆飴谓之
,浑言之也。豆飴谓之 ,见豆部。
,见豆部。
正文:从食,散声。
注:苏旱切,十四部。
在这里,段玉裁对飴和餳与馓的关系说得更清楚了。原注具在,不再重复。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卷一四,保留了飴和 ,
, 没有改作餳。对飴字的注,有的与段玉裁相同,有的不同。相同的我不再重抄。不同之处在于,桂馥引用了一些古籍,比如《楚策》、《吕氏春秋·异用篇》、《淮南·说林训》。他还引用《急就篇》颜注,区别飴和餳。又引《齐民要术》作糵法,以小麦和大麦为糵。又引《本草》,说明飴即软糖,北人谓之餳。对于餳字,桂馥注引用了《方言》、《楚辞·招魂》,卢谌《祭法》、《齐民要术》、《宋书·颜竣传》、《幽明录》、《白帖》、《十道志》、《南齐书·周颙传》、《隋书·梁彦先传》、《傅芳略记》等书。
没有改作餳。对飴字的注,有的与段玉裁相同,有的不同。相同的我不再重抄。不同之处在于,桂馥引用了一些古籍,比如《楚策》、《吕氏春秋·异用篇》、《淮南·说林训》。他还引用《急就篇》颜注,区别飴和餳。又引《齐民要术》作糵法,以小麦和大麦为糵。又引《本草》,说明飴即软糖,北人谓之餳。对于餳字,桂馥注引用了《方言》、《楚辞·招魂》,卢谌《祭法》、《齐民要术》、《宋书·颜竣传》、《幽明录》、《白帖》、《十道志》、《南齐书·周颙传》、《隋书·梁彦先传》、《傅芳略记》等书。
桂馥又在注中引赵宧光曰:“南方之胶餳,一曰牛皮糖,香稻粉熬成者。”他接着说:
馥案:今以蔗作者,沙餳也。《江表传》:“孙亮使黄门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献甘蔗餳。”《广志》:甘蔗,其餳为石蜜。《一切经音义》十一:蔗餹,以甘蔗为餳餹也。今沙糖是也。《北堂书钞》有沙餳,引张衡《七辩》:沙餳石蜜,远国贡储。盛翁子《与刘颂书》:沙餳,西垂之产。馥谓:此皆非飴和馓之餳也。
羡林按:桂馥的意见是正确的。上面列举的这一些都是甘蔗制成的,而飴和馓之餳则是米或麦制成,当时还不知道用甘蔗制糖。
下面一段是讨论发音问题的,很重要。我照抄在下面:
易声者,当为昜声。《六书故》:餳,徒郎切。《方言》:餳谓之糖。昜与唐同音。孙氏徐盈切。昜非徐盈之音。《六经正误》,诗有瞽笺,卖餳作,误。《荆楚岁时记》,元日进胶牙餳。《御览》引《风俗通》,作胶牙糖,卢君文弨曰:《说文》
,从食,易声,徐盈切。案:易声殊不相近,自当从昜。刘熙《释名》云:餳,洋也。谐声取义。《周礼·小师》注:管,如今卖飴餳所吹者。《释文》音辞盈反。又云:李音唐。徐盈,辞盈,其音近精,与唐实一声之转。又曰:餳,从昜,古音唐,亦或读为辞精、辞盈、夕清等切者,以阳、唐、庚、耕、清本相通也。李善注《文选·王僧达祭颜光禄文》引郭璞《三仓解诂》曰:杨(楊),音盈,与上声下英协韵。《玉篇》:瑒,雉杏切,又音暢。可知凡字从昜者,皆有两音。《说文》从易,偶脱中间一画耳。不可执是过生分别。馥案:哀十二年《左传》:郑人为之城喦、戈、鍚。《释文》:鍚,音羊,一音星历反。《容斋三笔》:天台士人左君,颇有才,最善谑。杨和王之子除权工部侍郎,张循王之子带集英修撰。左用歇后语作绝句云:木易已为工部侍(郎),弓长肯作集英修(撰)。此皆昜易混淆。《广雅》:

飴
餹餳也。曹宪音辞精反。宪岂不知餳从昜者,盖转音也,音转而字体因之以讹。
桂馥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他的话“凡字从昜者,皆有两音”,值得重视。但是,我认为,问题可能比这还要更复杂。这同我要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我不再细究了。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由于“定声”,所以打乱了原有的顺序,把飴字归入颐部第五。对于这个字他的注较以上二者为少。他说:
古以芽米熬之成液,今或用大麦为之,再和之以馓,则曰餳。
简短扼要,说明了原料的转变。他把餳字归入壮部第十八,注也极为简单。他说:“
 合音为餳。”也简短准确。他说餳字亦作餹,作糖。他没有分清餳、餹与糖的极其重要的区别,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谈到。
合音为餳。”也简短准确。他说餳字亦作餹,作糖。他没有分清餳、餹与糖的极其重要的区别,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谈到。
此处还有一个 字。《说文解字》:申时食也。与飴餳无关。但是《释名》却有:“哺,
字。《说文解字》:申时食也。与飴餳无关。但是《释名》却有:“哺, 也。如餳而浊可
也。如餳而浊可 也。”我抄在这里,以供参考。
也。”我抄在这里,以供参考。
上面我引证了段玉裁、桂馥和朱骏声三本关于《说文解字》的书,抄了他们引用的一些资料。问题看起来比较复杂,甚至有点混乱。经过深思熟虑,我现在提出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一定很成熟,但是我觉得是能够成立的。我认为,在先秦时代,人民喜欢吃甜的东西,除了天然产生的蜜以外,人工制造的主要有两种:一种叫yi,一种叫tang。人民群众的方言最初是只有音的。两者都是开头用米,特别是糯米来制作的,后来(其中也可能包括一些地域的原因),也用小麦和大麦。这样制作出来的东西,清者也就是软一点、湿一点、稀一点的叫yi。yi这个音写法有分歧,有的写作飴,有的写作 。稠者也就是硬一点、干一点的叫tang。tang这个音写法也有分歧,有的写作餳,有的写作餹,有的干脆用拼音(反切)的方法来表示,这就是
。稠者也就是硬一点、干一点的叫tang。tang这个音写法也有分歧,有的写作餳,有的写作餹,有的干脆用拼音(反切)的方法来表示,这就是
 、张皇、
、张皇、
 、
、
 〔1〕 ,前者取其双声,后者取其叠韵,拼起来就是tang。至于
〔1〕 ,前者取其双声,后者取其叠韵,拼起来就是tang。至于 和餳之间的关系,用桂馥的“凡字从昜者皆有两音,《说文》从易,偶脱中间一画耳”的说法,解释不通这个问题。
和餳之间的关系,用桂馥的“凡字从昜者皆有两音,《说文》从易,偶脱中间一画耳”的说法,解释不通这个问题。 和餳二字不是一个意思。《方言》有一段话:
和餳二字不是一个意思。《方言》有一段话:
谓之

(即干飴也),飴谓之
(音该),
谓之
(以豆屑杂
也音髓),
谓之餹(江东皆言餹,音唐),凡飴谓之
,自关而东,陈楚宋卫之通语也。
这里的“ ”都应写作餳。这一段值得思考。但是方言以音为主,不以字为转移。
”都应写作餳。这一段值得思考。但是方言以音为主,不以字为转移。
我对飴、 、餳、餹四个字的意见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
、餳、餹四个字的意见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
我在《引言》中谈到的李治寰《中国食糖史稿》也谈到了类似的问题。他在这本书的论述中发表了很多很精彩的意见。有的问题我不想也没有能力来谈论,比如“糖和人类的关系”等等,我从中都学习了很多有用的东西。我们的书,正如我在《引言》提到的那样,目的是不相同的,重点也因之不能相同;但是,正因为如此,两本书是可以互相补充的。这一点读者自会明了,用不着我再来啰嗦。可是李著中仍然有一些地方是有商榷的余地的。我在这里首先谈一下与我讨论的四个字有关的问题。
李治寰先生在他的书中在几个地方,比如第35页、第40页,都引用了《说文解字》:
糖 飴也,从米,唐声。
这似乎就有问题。《四部丛刊》景宋本《说文解字》,确实有李治寰的上列引文。但是,李先生却似乎忽略了其中的几个字:“文六,新附”。所谓“新附”,意思就是新附加上的,原来并非如此。事实上,我检查了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等书,都没有“糖”字。足征“糖”字的晚出。徐锴《说文解字通释(系传)》卷一三,米部也没有“糖”字,更证明了此字的晚出。在中国古代韵书中,确有此字的,比如《广韵》就有“糖”字。但是这一部书的出现也不太早,最早只能追溯到隋代的陆法言。原为梁顾野王撰的《玉篇》中,也有“糖”字。此书虽较《广韵》为早,也还连汉代都够不上,无论如何也证明不了“糖”的早出。因此,李治寰先生引用《说文解字》中“新附”的东西,把“糖”字与“飴”、“ ”、“餳”等字并列,给人造成了一个印象,好像先秦时代“糖”字已经出现了,似乎不妥。也许有人要问:为了一个字出现的早晚,你竟费了这么多的笔墨来讨论,岂非小题大做?答曰:否,否!这决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大题大做。究竟底细如何?以后还要谈到。这里先就此打住了。
”、“餳”等字并列,给人造成了一个印象,好像先秦时代“糖”字已经出现了,似乎不妥。也许有人要问:为了一个字出现的早晚,你竟费了这么多的笔墨来讨论,岂非小题大做?答曰:否,否!这决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大题大做。究竟底细如何?以后还要谈到。这里先就此打住了。
其次,我想谈一谈“ ”字的问题。李著第40页引《释名》:“如餳而浊者曰
”字的问题。李著第40页引《释名》:“如餳而浊者曰 。”原文是“哺,
。”原文是“哺, 也,如餳而浊可
也,如餳而浊可 也”。但是,在《说文解字》中,“
也”。但是,在《说文解字》中,“ ”字只有“申时食也”一义。因此,在先秦时代,“
”字只有“申时食也”一义。因此,在先秦时代,“ ”字是否有“餳而浊者”的含义,是值得考虑的。
”字是否有“餳而浊者”的含义,是值得考虑的。
最后,我还再谈一下“餹”字。这个字我在上文中已经谈到过,我把它同“飴”“ ”“餳”并列。从发音上来看,道理是有的。但是“餹”字并不见于《说文解字》。《方言》里有这个字,足征这个字是比较晚出的 〔2〕 。
”“餳”并列。从发音上来看,道理是有的。但是“餹”字并不见于《说文解字》。《方言》里有这个字,足征这个字是比较晚出的 〔2〕 。
注释:
〔1〕 参阅姜亮夫《楚辞通故》,1985年,齐鲁书社,第三辑,第195—197页,“
 ”条。
”条。
〔2〕 我在这里再补充一点资料。李治寰《中国食糖史稿》,第39至40页说:“西汉启蒙识字课本《急就章》‘枣、杏、瓜、棣、馓、飴、 ’,高二适引前人注谓颜师古本作昜。其字从昜不从易。‘居
’,高二适引前人注谓颜师古本作昜。其字从昜不从易。‘居 ’金文
’金文 ,高明同志释为餳字(《古文字研究》、《古文字类编》)。秦篆餳作
,高明同志释为餳字(《古文字研究》、《古文字类编》)。秦篆餳作 。两字都从昜不从易。”羡林按:高二适原著《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上,第136—137页,高手书作餳,不作
。两字都从昜不从易。”羡林按:高二适原著《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上,第136—137页,高手书作餳,不作 。高二适说:“又餳作
。高二适说:“又餳作 ,云颜本作枣作餳是也……如
,云颜本作枣作餳是也……如 ,章草易旁与昜旁无别。”我在上面讲到段玉裁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高的意见可以参考。
,章草易旁与昜旁无别。”我在上面讲到段玉裁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高的意见可以参考。
第二章 周秦至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飴 餳餹以及甘蔗和蔗浆
餳餹以及甘蔗和蔗浆
上面第一章的重点是界定飴、 、餳、餹四个字的确切含义。因为,如果这四个字的确切含义不能界定,以后按时代顺序进行叙述时就容易造成概念混乱。界定时,我基本上没有考虑时代问题,笼统地讲就是古代,这样也就够了,它并不影响本书基本上按时代顺序叙述的结构框架。
、餳、餹四个字的确切含义。因为,如果这四个字的确切含义不能界定,以后按时代顺序进行叙述时就容易造成概念混乱。界定时,我基本上没有考虑时代问题,笼统地讲就是古代,这样也就够了,它并不影响本书基本上按时代顺序叙述的结构框架。
本章的重点是叙述从秦汉以至南北朝时期这四个字在文献中出现的情况,以及这四个字所代表的实物演变的情况。还有一个重点是讨论甘蔗和蔗浆的问题。在叙述这两个重点以前,我想说得再远一点,讲一讲最古时代的甜东西以及甜这个味觉的原始含义。因此,本章就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一)古代的甜东西。
(二)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飴 餳餹。
餳餹。
(三)这一时期的甘蔗和蔗浆。
下面分别依次加以叙述。
(一)古代的甜东西
几乎所有的人(甚至一些动物)都喜欢吃甜东西。这是一个生理问题,与我们研究糖的历史关系不大,我在这里不讨论。我只讲最古的人吃的甜东西。
这个问题,李治寰在他的《中国食糖史稿》 〔1〕 中,已经做了很细致周到的阐述,我没有必要再重复论述,请读者自行参考。我只想做一点补充。第一点补充是讲一讲中国古代文献中对“甜”这一味觉的理解或者解释。第二点补充是再讲一讲蜜。李治寰在该书第二章中谈到自然糖的食用史,第三讲的是蜜,第一是乳糖,第二是果实。
古代对甜这一味觉的理解或者解释,我只能通过语言文字来探讨。最古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蒙昧渺茫,邈乎远矣。我不想去谈它。我想从《说文》谈起。《说文解字》的注本很多,我使用的是最有权威的清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 〔2〕 。在《说文解字》中,表示“甜”的含义的字有几个,最重要的是甘、甜、旨、美四个字。
甘 五篇上,甘部,第202页上。“甘,美也。”《注》:“羊部曰:美,甘也。甘为五味之一,而五味之可口者,皆曰甘。”“从口含一,一,道也。”《注》:“食物不一,而道则一。所谓味道之腴也。”“凡甘之属,皆从甘。”
甜 同上篇、部、页。“甛,美也。”《注》:“周礼注恬酒,恬即甛字。”
旨 五篇上,旨部,第202页下。“旨,美也。”《注》:“叠韵,今字以为意恉字。”“从甘,匕声。”《注》:“职雉切,十五部。”“凡旨之属,皆从旨。”
美 四篇上,羊部,第146页下。“美,甘也。”《注》:“甘部曰:美也。甘者,五味之一,而五味之美皆曰甘。引伸之,凡好皆谓之美。”“从羊大。”《注》:“羊大则肥美。”“羊在六畜主给膳也。”《注》:“周礼,膳用六牲,始养之曰六畜。将用之曰六牲。马、牛、羊、豕、犬、鸡也。膳之言善也。羊者,祥也。故美从羊。此说从羊之意。”“美与善同意。”《注》:“美譱義羑皆同意。”
《说文解字》就引这样多。引文本身已经把事情说得非常清楚,我再加解释反而会成为多余的了。《说文解字》一说:“甘,美也。”又说:“美,甘也。”这几个字的相互关系,实际上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用不着再细说。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美”字的来源和最基本的含义以及美与善的关系。这虽然似乎像是题外的话;但是,我认为,讲上一讲,会对研究中国美学、伦理学等等的学者有很大的启发。
人类,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爱美都可以说是天性。自古以来,中西各国都形成了一门专门研究“美”的学科:美学。研究美学的书籍,汗牛充栋;对美的本质的争论也是剑拔弩张。我对这些书籍颇多涉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最近读到了周来祥、陈炎合著的《中西比较美学大纲》 〔3〕 。我觉得这是一部十分精彩的书,立论有据,逻辑清晰,把这一个异常抽象的美的概念讲得生动具体。他们讲的“美”,同我上面引用《说文解字》讲的“美”有密切联系。所以我就抑制不住自己,来谈上一谈。先引一段原书:
动物性的快感是与其个体和族类的生存欲望密切相关的,前者表现为“食”,后者表现为“性”。在原始人那里,最初的食、性活动还只是为了满足肉体的生物本能,然而随着劳动生产和社会实践的出现,这些生物性本能渐渐演化为精神享受:食不仅仅是为了果腹,而且是一种美味;性也不单单是为了交配,而且是一种爱情。这就是动物性快感向人类美感进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尽相同的侧重点和倾向性。从现在的资料看,中国古代的审美活动最初显然与“食”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西方古代的审美活动最初或许与“性”更加相关。这大概也就是人们将中国文化称为“食文化”,将西方文化称为“性文化”的原因之一吧。 〔4〕
我在上面的引文中的“美,甘也”,“美”这个字来源于肥美的羊,充分证明周、陈的书中论断的准确性。谈糖而谈到甘,谈甘而谈到美,谈美而谈到美的起源,谈美的起源而谈到中西美的起源之不同,虽然似乎扯得远了一点,却还没有到“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程度。
从《说文解字》中“美与善同意”这一句话中,从“善”这个字也来源于羊这个事实中,我还想再扯远一点,讲一讲东西哲学家和其他一些什么家都常谈到的“真善美”这三个概念的相互关系。至少是在中国,美与善是“同意”的。关于这一点,我不想进一步去阐述。我只在这里点出这个问题,供有关学者思考。
话还是扯得远了一点。闲言少叙,书归正传。现在我来对李治寰讲的自然糖的第三种:蜂蜜做一点补充。
蜂蜜大概是人类食用的自然糖中最甜的、最普通的一种。世界上各民族几乎都有吃蜜的习惯。这从语言上就可以得到佐证,比如印欧语系各语言表示“蜜”的字是:
梵文 madhu
古希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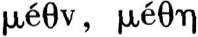
斯拉夫系 medǔ
立陶宛文 midùs,medùs
日耳曼系 meth
英文 mead
这只是例子,是有代表性的,其余的用不着多举了。这些字显然源于一个共同的原始印欧语。先有事物,然后才能有表示这个事物的字。“蜜”这一种东西大概在原始印欧人中是普遍食用的。
在中国,“蜜”字出现得很早。我仍然从《说文解字》谈起。《说文》,蜜,十三篇下,虫部,第675页上: “蜂甘飴也。”《注》:“飴者,米蘖煎也。蜂作食,甘如之。凡蜂皆有
“蜂甘飴也。”《注》:“飴者,米蘖煎也。蜂作食,甘如之。凡蜂皆有 。《方言》:蜂,大而蜜者,谓之壶蜂。郭云:今黑蜂穿竹木作孔,亦有有蜜者。是则蜂飴名
。《方言》:蜂,大而蜜者,谓之壶蜂。郭云:今黑蜂穿竹木作孔,亦有有蜜者。是则蜂飴名 ,不主谓今之蜜蜂也。”
,不主谓今之蜜蜂也。”
“蜜”字还见于其他一些先秦古籍中,不具引。我只想讲一讲楚辞的情况。《楚辞·招魂》:“粔籹蜜饵,有
 些。”“
些。”“
 ”就是tang(餹、餳),我在第一章中已经谈过,请参阅。对《招魂》中的这一句话,王逸注:“言以蜜和米面,熬煎作粔籹,捣黍作饵。” 〔5〕
”就是tang(餹、餳),我在第一章中已经谈过,请参阅。对《招魂》中的这一句话,王逸注:“言以蜜和米面,熬煎作粔籹,捣黍作饵。” 〔5〕
我顺便讲一讲楚辞里面的“甘”字。在楚辞中,“甘”字凡四见,其中为木名“甘棠”,与我所要谈的问题无关,不具引。其他三处皆“味美”一义之引申。《招魂》:“此皆甘人,归来恐有遗灾些。”王注:“甘,美也。”《招魂》又曰:“辛甘行些。”王注:“辛,谓椒姜也。甘,谓飴蜜也。”《大招》:“有鲜蠵甘鸡和楚酪些。”王注:“言取鲜洁大龟,烹之作羹,调以飴蜜;用肥鸡之肉,和以酢酪,其味清烈也。” 〔6〕
对李治寰《中国食糖史稿》第二章的补充就到这里为止 〔7〕 。
(二)秦汉到南北朝时期的飴、 、餳、餹
、餳、餹
飴、 、餳、餹等四个字的确切含义,第一章已经作了界定,目的是给人一个全方面的概念。在现在这一段里,我想按照历史顺序,讲一讲这几个名词出现的情况,目的是给人一个历史概念。从时间顺序上来讲,先秦时代出现的只有一个“飴”字,“餹”字最晚出。根据我在第一章中的意见,这四个名词实际上只代表两种东西:飴和
、餳、餹等四个字的确切含义,第一章已经作了界定,目的是给人一个全方面的概念。在现在这一段里,我想按照历史顺序,讲一讲这几个名词出现的情况,目的是给人一个历史概念。从时间顺序上来讲,先秦时代出现的只有一个“飴”字,“餹”字最晚出。根据我在第一章中的意见,这四个名词实际上只代表两种东西:飴和 同读为yi,指软一点、湿一点、稀一点的用糯米或小麦、大麦制成的甜东西。餳和餹同读为tang,指稠一点、硬一点的 〔8〕 。除了这四个字以外,我在第一章里还谈到“馓”、“
同读为yi,指软一点、湿一点、稀一点的用糯米或小麦、大麦制成的甜东西。餳和餹同读为tang,指稠一点、硬一点的 〔8〕 。除了这四个字以外,我在第一章里还谈到“馓”、“ ”等字,含义已阐述过,今后就不再谈了。
”等字,含义已阐述过,今后就不再谈了。
下面按照顺序谈这四个字。
飴 
我想先条列引文,然后再加以分析,从中得出可能得到的一些结论。引文不求完备无遗,那是很难做到的,重要的决不会遗漏。上面已经引过的,除了极其重要的非引不行的以外,不再重复 〔9〕 。
《诗·大雅》参阅上面页28。
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前476年)青铜器“居 ”上有
”上有 字 〔10〕 。
字 〔10〕 。
《礼记·内则》参阅上面页28。
《山海经·南山经》:
又东三百七里曰仑者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有木焉。其状如谷而赤理。其汁如漆,其味如飴,食者不饥,可以释劳。其名曰白
,可以血玉。
《吕氏春秋·审时》:
得时之黍,芒茎而徼下,穗芒以长,抟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如此者不飴。
史游《急就篇》:
馓(生侃反)、飴、餳。
《方言》:
餳,谓之
。飴,谓之
。
,谓之
。餳,谓之餹。凡飴谓之餳 〔11〕 ,自关而东,陈楚宋卫之通语也。
注:
,即干飴也。
,以豆屑杂餳也。餹,江东皆言餹。
《释名》卷四《释饮食》第十三:
餳,洋也。煮米消烂,洋洋然也。
飴,小弱于餳,形怡怡然也。
哺,也。如餳而浊可
也。
《说文》上面第一章已讲过,请参阅。
《淮南子·说林训》第十七:
柳下惠见飴曰:“可以养老。”盗跖见飴曰:“可以黏牡。”见物同而用之异。
注:牡,门户籥牡也。
张衡《七辩》:
沙餳石蜜,远国贡储。
崔寔《四民月令》:
十月洗水冻作煮(京),煮暴飴。
《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引。“水”《集成》作“冰”。
卢谌《祭法》:
冬祠用荆。
《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引。“ ”《集成》作“餳”。
”《集成》作“餳”。
《后汉书·后纪》:
明德马皇后报章帝曰:“吾但当含飴弄孙,不能复关政矣。”
《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引。
《晋书·石崇传》:
(崇)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恺以澳釜,崇以蜡代薪。
《世说新语·汰侈》第三十:
王君夫以
澳釜。石季伦用蜡烛作炊。君夫作紫丝巾步障碧绫裹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以椒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羡林按:“ ”即“飴”字。《说文》无“
”即“飴”字。《说文》无“ ”字。
”字。
《幽明录》:
王允祖安国张显等,以太元中乘船,见仙人赐糖飴三饼,大如比轮钱厚二分。
《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引。
关于“飴”字的引文就引这样多。有一个小问题想在这里说明一下。李治寰上引书,第40页说:“糖:《说文解字》谓:‘糖 飴也。’”我在上面第19页已经谈过这个问题,在这里再交代一句。“糖”字并不见于《说文》,只见于“新附”。
把上面的引文归纳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只有“飴”字见于先秦典籍,后来“飴”“ ”混用,见于多种汉至南北朝典籍中。制造“飴”的原料是大米和麦,尚无用甘蔗者。至于“飴”的价值,大概是非常高的,否则南北朝时期的石崇和王恺斗富炫侈,决不会用
”混用,见于多种汉至南北朝典籍中。制造“飴”的原料是大米和麦,尚无用甘蔗者。至于“飴”的价值,大概是非常高的,否则南北朝时期的石崇和王恺斗富炫侈,决不会用 (飴)的。
(飴)的。
餳 餹
我仍然先条列引文:
《方言》 上面已引过。
《释名》 上面已引过。
《说文》 上面已讨论过。
崔寔《四民月令》上面已引过。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御览》作“ ”,《古今图书集成》作“餳”。
”,《古今图书集成》作“餳”。
《盐铁论》:
洗爵以盛水,升降而进餳,礼虽备,然非其实也。
卢谌《祭法》:
冬祠用荆。
《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引。
值得注意的是:前者引作“ ”,后者引作“餳”。
”,后者引作“餳”。
《三国志·吴志·孙亮传》注《江表传》:
亮使黄门以银碗并盖,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献甘蔗餳。黄门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餳中,启言:藏吏不谨。亮呼吏持餳器入。问曰:“此器既盖之,且有掩覆,无缘有此。黄门将有恨于汝邪?”吏叩头曰:“尝从某求宫中莞席。宫席有数,不敢与。”亮曰:“必是此也。”复问黄门,具首伏。即于目前加髠鞭,斥付外署。
《古今图书集成》引。
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九,“餳 ”第八十九:
”第八十九:
这里主要讲的是“餳”的制作方法。有“煮白餳法”、“黑餳法”、“琥珀餳法”、“煮 法”、“食经作飴法”、“食次曰白茧糖法”、“黄茧糖”等。值得注意的是:《齐民要术》似乎把“飴”与“餳”混为一谈,不加区分。第二,餳是用大麦、小麦制成的。“煮白餳法”中说:“用白牙散糵佳,其成饼者则不中用。”“黑餳法”中说:“用青牙成饼糵。”详细制作过程,请参阅李治寰书第42—43页。
法”、“食经作飴法”、“食次曰白茧糖法”、“黄茧糖”等。值得注意的是:《齐民要术》似乎把“飴”与“餳”混为一谈,不加区分。第二,餳是用大麦、小麦制成的。“煮白餳法”中说:“用白牙散糵佳,其成饼者则不中用。”“黑餳法”中说:“用青牙成饼糵。”详细制作过程,请参阅李治寰书第42—43页。
《宋书·颜竣传》:
竣为丹阳尹,加散骑常侍。时岁旱,民饥。竣上言,禁餳一月,息米近万斛。
《古今图书集成》引。这里明确说明,餳是米作的。
《王大令集》:
餳大佳。柳下惠言餳可常饵,亦觉有益耳。
《古今图书集成》引。
把上面引文归纳一下,我觉得,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餳”“ ”二字经常混淆,上面举的只是两个例子,类似的情形还多得很。第二,“餹”字只见于《方言》。实际上,“餹”“餳”二字,实即一字,都代表的tang音。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壮部第十八”说:“餳,从食,昜声。字亦作‘餹’,作‘糖’。”说“作糖”,是不知道“糖”字晚出。第三,把“餳”与“
”二字经常混淆,上面举的只是两个例子,类似的情形还多得很。第二,“餹”字只见于《方言》。实际上,“餹”“餳”二字,实即一字,都代表的tang音。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壮部第十八”说:“餳,从食,昜声。字亦作‘餹’,作‘糖’。”说“作糖”,是不知道“糖”字晚出。第三,把“餳”与“ ”“飴”混淆起来,是没有分清二者的区别。我在上面几次谈到,yi音代表的是软的东西,tang音代表的是较硬一点、较干一点的飴。第四,《江表传》中使用了“甘蔗餳”三字。这非常值得重视。自周秦起,制作“飴”或“餳”用的原料都是米或麦。这里第一次见到用甘蔗作的餳,时间是三国时代(220—280年)。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谈到。《江表传》用的是“餳”字,按照我上面的说法,是比较硬的,比较干的。但是,从《江表传》的上下文来看,“餳”要用银碗来盛,而且里面还能搀上老鼠矢,足见它还没有凝结成块,仍然是比较稀的。
”“飴”混淆起来,是没有分清二者的区别。我在上面几次谈到,yi音代表的是软的东西,tang音代表的是较硬一点、较干一点的飴。第四,《江表传》中使用了“甘蔗餳”三字。这非常值得重视。自周秦起,制作“飴”或“餳”用的原料都是米或麦。这里第一次见到用甘蔗作的餳,时间是三国时代(220—280年)。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谈到。《江表传》用的是“餳”字,按照我上面的说法,是比较硬的,比较干的。但是,从《江表传》的上下文来看,“餳”要用银碗来盛,而且里面还能搀上老鼠矢,足见它还没有凝结成块,仍然是比较稀的。
(三)这一时期的甘蔗和蔗浆
甘蔗,原生地大概不在中国。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谈到,请参阅本书第二编第二章:“甘蔗的原生地问题”。
在中国先秦时代,只有“柘”字,没有“蔗”字。到了汉代“蔗”字才出现。这是两个同音字。因此,我猜想,这两个字同是zhe音的音译,至于zhe究竟是什么语言,目前还说不清楚。它很可能是印度支那半岛某一个古国的某一种文字 〔12〕 。
在汉文中,“甘蔗”的写法很多。《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第一一三卷,归纳出来了一些写法:

《神异经》 亦作

甘蔗 《草木状》
《说文》
竹蔗 陶弘景
荻蔗 陶弘景
崑蔗 孟诜
杜蔗 《糖霜谱》
西蔗 《糖霜谱》
蔗 《糖霜谱》
蜡蔗 《糖霜谱》
红蔗 《糖霜谱》
紫蔗 《糖霜谱》
这个归纳很混乱,又很不全,聊备一格而已。
对于“甘蔗”的名称,我也有一个归纳,请参阅本书附录《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这里不重复。
同一个或两个音竟然有这样多的写法,可见这些都只能是音译,连“甘”字也只能是一个注音符号,与“甘甜”的“甘”无关。
现在来谈秦汉至南北朝时的甘蔗与蔗浆问题。因为先秦已经出现了“柘”字,所以要把时间上限往上挪一点,挪到周代。
我仍然按照上面的办法,先条列引文,然后再加以论述:
《楚辞·招魂》:
胹鳖炮羔,有柘浆些。
王逸注:“柘,蔗也。言复以飴蜜,胹鳖炮羔,令之烂熟,取
蔗之汁,为浆饮也。”“柘,一作蔗。一注云:胹鳖炮羔,和牛五藏臛为羹者也。”洪补:“相如赋云:‘诸柘巴苴’,注云:‘柘,甘柘也。’”朱熹注:“柘,一作蔗。柘,
蔗也。
言取蔗之汁为浆饮也。” 〔13〕
这是先秦时期“柘”(蔗)字唯一的一次出现。
汉刘向《杖铭》:
都蔗虽甘,殆不可杖。佞人悦己,亦不可相。
《古今图书集成》引。
《说文》:
三个注本不尽相同。我现依次抄在下面: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柘,柘桑也。三字句。各本无柘字,今补……从木,石声……”没有谈到假借为“蔗”。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在注中也只讲到“柘”即是桑。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到,“假借为蔗,《楚辞·招魂》‘有柘浆些’,《汉书·礼乐志》,‘泰尊柘浆析朝酲’”。
至于“蔗”字,段书是:“ ,
, 蔗也。”注是:“三字句。或作诸蔗,或都蔗。
蔗也。”注是:“三字句。或作诸蔗,或都蔗。 蔗二字,叠韵也。或作竿蔗,或干蔗,象其形也。或作甘蔗,谓其味也。或作邯
蔗二字,叠韵也。或作竿蔗,或干蔗,象其形也。或作甘蔗,谓其味也。或作邯 。服虔《通俗文》曰:荆州竿蔗。”羡林按:段注“谓其味也”,恐有问题。把全部蔗名归纳起来,“甘”只能是译音。
。服虔《通俗文》曰:荆州竿蔗。”羡林按:段注“谓其味也”,恐有问题。把全部蔗名归纳起来,“甘”只能是译音。
桂书的注比较长,他引用了很多书,比如《广雅》、《子虚赋》、《古文苑·蜀都赋》、《南齐书·扶南国传》、《西京杂记》、《本草》陶弘景注、《蜀本图经》、《通俗文》、《荆州图》、《永嘉郡记》、《寰宇记》、《南州异物志》、《异物志》、《吴录·地理志》、《南方草木状》、司马相如《乐歌》、《容斋四笔》、张协《 蔗赋》、李伯仁《七欸》、《唐书·摩揭陀传》、卢谌《祭法》、范汪《祠制》、曹植《矫志诗》、冯衍《竹杖铭》,等等。提供的资料很有用,我现在抄一部分在下面:
蔗赋》、李伯仁《七欸》、《唐书·摩揭陀传》、卢谌《祭法》、范汪《祠制》、曹植《矫志诗》、冯衍《竹杖铭》,等等。提供的资料很有用,我现在抄一部分在下面:
“,蔗也。从草,诸声”。《南都赋》“
蔗姜
”。注:“甘蔗也。”按
蔗叠韵连语,与《尔雅·释草》“菋荎著之草五味”。《释木》“味荎著之木五味”。《广雅·释草》“

,署预也”。《北山经·景山》“其中多草

”即今山药同音。单言曰蔗,累言曰
蔗耳。《南都赋》四物并言,疑
当为

本字。《汉书音义》训甘蔗,则四字为三物,恐非。《山海经》郭注,草

,今江南单呼为
,语有轻重耳。又按苏颂《本草图经》闽中出一种薯蓣,根如姜芋而皮紫,极有大者。土人单呼为
。此疑即苏俗所云山芋,形短而椭圆,与山药不同。
羡林按: 蔗之“
蔗之“ ”,与山药之“
”,与山药之“ ”恐系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恐系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曹丕《典论》:
(邓展)求与余对。酒酣耳热,方食干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
《艺文类聚》引。《太平御览》引。
魏文帝《感物赋》并序:
南征荆州,还过乡里,舍焉,乃种诸蔗于中庭,涉夏历秋,先盛后衰。悟兴废之无常,慨然永叹,乃作斯赋,云:伊阳春之散节,悟乾坤之交灵。瞻玄云之蓊翳,仰沉阴之杳冥。降甘雨之丰霈,垂长溜之泠泠。掘中堂而为圃,植诸蔗于前庭。涉炎夏而既盛,迄凛秋而将衰。岂在斯之独然,信人物其有之。(《四库全书》,846,761上)
曹植《矫志诗》:
都蔗虽甘,杖之必折。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引。《艺文类聚》引。《三国志·吴志·孙亮传》注《江表传》,上面已抄。
司马相如《子虚赋》:
诸柘巴苴。
张衡《南都赋》:
其园则有蓼、蕺、蘘荷、蔗、姜、
、菥蓂、芋、瓜。
《汉书·礼乐志》:
上引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已抄录。
《吴录·地理志》:
交阯句(音漏)县,干蔗大数寸,其味醇美,异于他处。笮以为餳,曝之,凝如冰,破如博棋,入口消释。
《太平御览》引。参阅上引《江表传》中的“甘蔗餳”。
《南中八郡志》:
交阯有甘蔗,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断而食之,甚甘。笮取汁,曝数时,成飴,入口消释。彼人谓之石蜜。
《艺文类聚》引。请与上引《地理志》文参照。这里使用的字是“飴”,而不是“餳”。
虞翻《与弟书》:
去日南远,恐如甘蔗,近抄即薄。
《太平御览》引。
应璩《与尚书诸郎书》:
檀氏园,葵菜繁茂,诸蔗瓜芋亦离尚萌。未知三生复何种植。
《太平御览》引。
冯衍《杖铭》:
杖必取材,不必用味。相必取贤,不必所爱。都蔗虽甘,犹不可杖。佞人悦己,亦不可相。
《太平御览》引。
左思《蜀都赋》:
其园则有蒟蒻茱萸,瓜畴芋区。甘蔗辛姜,阳阴敷。
张协《都蔗赋》:
若乃九秋良朝,元酎初出。黄华浮觞,酣饮累日。挫斯柘而疗渴,若漱醴而含蜜。清滋津于枣梨,流液丰于朱橘。
《太平御览》引。
李伯仁《七欸》:
副以甘柘,丰弘诞节。纤液玉津,旨于飴蜜。
《太平御览》引。
范汪《祠制》:
孟春祠用甘蔗。
《太平御览》引。
张载诗:
江南都蔗,酿液沣沛。三巴黄甘,瓜州素。凡此数品,殊美绝快。渴者所思,铭之裳带。
《太平御览》引。
《晋书·顾恺之传》:
(顾恺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渐入佳境。”
《太平御览》引文稍异。《艺文类聚》卷八七引文稍异,注明引《世说》。又引《世说》:“扶南蔗一丈三节,见日即消,风吹即折。”
《宋书》:
庾仲文好货。刘雍自谓得其助力,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
又:
元嘉末,魏太武征彭城,遣使至小市门,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人送酒二器、甘蔗百挺。
以上二则《太平御览》引。
《齐书》:
宜都王铿善射。常以堋的太阔,曰:“终日射侯,何难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发十中。
《太平御览》引。
又:
范云永明十年使魏。魏人李彪宣命至云所,甚见称美。彪为设甘蔗黄粽。随尽复益。彪笑谓曰:“范散骑小验之!一尽不能复得。”
《太平御览》引。
《梁书》:
庾沙弥性至孝。母刘亡,好啖甘蔗。沙弥遂不食焉。
《太平御览》引。
《三国典略》:
陆纳反湘州,分其众二千人,夜袭巴陵。晨至城下。宜丰侯修出垒门,座胡床以望之。纳众乘水来攻,矢下如雨。修方食甘蔗,曾无惧色。
又:
侯景至朱雀街。南建康令庾信守朱雀门。信众撤桁,始除一舶,见景军皆着铁面,退隐于门,自言口燥,屡求甘蔗。俄而飞箭中其门柱。信手中甘蔗应弦而落。
《太平御览》引。
《隋书》:
赤土国物产,多同于交阯,以甘蔗作酒,杂以紫瓜根。酒色黄赤,味亦香美。
《永嘉郡记》:
乐城县三州府,江有三洲,因以为名。对岸有浦,名为菰子,出好甘蔗。
《太平御览》引。
《扶南传》:
安息国出好甘蔗。
《太平御览》引。
《广志》:
甘蔗,其餳为石蜜。
《太平御览》引。
《云南记》:
唐韦齐休聘云南。会川都督刘宽使使致甘蔗。蔗节希似竹许。削去后,亦有甜味。
《太平御览》引。
《神异经》:
南方荒内
林,其高百丈,围三丈,促节多汁,甜如蜜(
音干
音柘)。
请注意“
 ”这个写法。
”这个写法。
《异物志》:
甘蔗,远近皆有。交阯所产特醇好。本末无薄厚,其味甘。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断而食之,既甘。生取汁为飴餳,益珍。煎而曝之,凝如冰。
《甄异传》:
隆安中,吴县张牧字君林。忽有鬼来,无他。须臾,唯欲啖甘蔗。自称高楬。主人因呼“阿楬”。牧母见之,是小女,面青黑色,通身青衣。
《太平御览》引。
《袁子正书》:
岁比不登。凡不给之物,若干蔗之属,皆可权禁。
《太平御览》引。
《齐民要术》 〔14〕 这一部非常重要的书,在前面几章讲种植五谷(卷一、卷二)、菜蔬(卷三)、果(卷四)、树木(卷五)等的时候,没有提到甘蔗。本书最后一章,第十章,标题是“五 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后面还加了一个小注:“聊以存其名目,记其怪异耳。爰及山泽草木任食非人力所种者,悉附于此。”在这一章里出现了“甘蔗”。我现在把原文引在下面,以供参考:
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后面还加了一个小注:“聊以存其名目,记其怪异耳。爰及山泽草木任食非人力所种者,悉附于此。”在这一章里出现了“甘蔗”。我现在把原文引在下面,以供参考:
《说文》曰:“蔗也。”案书传曰:或为芋(羡林按:或当作“芉”)蔗,或干蔗,或

,或甘蔗,或都蔗,所在不同。
都县,土壤肥沃,偏宜甘蔗,味及采色,余县所无,一节数寸长。郡以献御。
(《异物志》,上面已引,不重引。)
《家政法》曰:“三月可种甘蔗。”
羡林按:甘蔗在这里所处的地位很奇特,下面再谈。
引文就到此为止。引文多了一点,目的是为了论证方便,而且也便于读者。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引文不求全;有的引文只根据类书引用,没有核对原文,其原因我在本章注〔9〕 中已经详尽阐述,这里不再重复。我只想再补充说明一点,就是我引书基本上没有按照时代顺序,只是大体上按照而已。因为有一些书出现的时间很难确定,特别是所谓“伪书”,学者间意见极为分歧。在这方面费很多精力,问题不见得能得到解决,仍然得不偿失。
统观上述引文,我想着重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从先秦一直到六朝的典籍中讲到甘蔗的地方,颇为不少,“柘”字只不过是“蔗”字另一个拼法。甘蔗种植的地方也不算少。但是,从许多例子都可以看出来,甘蔗还是相当名贵,还没有能走入寻常百姓家。
第二,关于甘蔗产地的问题。在国内,基本上都在南方,引文中提到或暗示的地方有楚国、安徽亳县、南都(今河南南阳)、檀氏园、吴国、蜀都(四川成都)、江南、南方、巴陵、永嘉、云南等地。在国外,则有安息(波斯,伊朗)、赤土(泰国或苏门答腊)、扶南(柬埔寨一带)、交阯(越南一带)等地。比较详细的情况,请参阅李治寰上引书有关章节。
第三,种植问题。左思《蜀都赋》有“其园”这样的字样,可见当时甘蔗是种植在“园”中的,与一些瓜果并列,并不像后代在郊外大面积地像种粮食谷物那样种植的。
第四,引文中讲到甘蔗,不是生吃,就是饮蔗浆,没有讲到用甘蔗制糖的。罗颀:《物原·食原》卷一○说:“孙权始效交趾作蔗糖。”我觉得其中似有问题。因此,在上面引文中我没有引用。请参阅本书第一编,第四章,“蔗糖的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
第五,吴、蜀问题。在上面引文中讲到甘蔗产地的时候,有两个地方引起了我的注意和联想:一个是长江上游的蜀,一个是长江下游的吴。如果不去联想,决不会发现什么问题:两地都有生产甘蔗的权力,何必硬往一处扯呢?但是,在中国与佛教有关的典籍上,吴、蜀总是连在一起出现,比如唐礼言的《梵语杂名》,中国地名只有三个:京师 矩畝娜曩,kumudana;吴 播啰缚娜paravada;蜀 阿弭里努Am du 〔15〕 。《大宝积经》卷一○,《密迹金刚力士会》第三之三:“其十六大国……释种、安息、月支、大秦、剑浮、扰动、丘慈、于阗、沙勒、禅善、乌(焉)耆前后诸国、匈奴、鲜卑、吴、蜀、秦地……” 〔16〕 以上两例可以证明,吴、蜀两地是常常连在一起的。这个现象怎样解释呢?吴、蜀都濒临长江,交通方便,二者关系密切,可以理解。但是,愚见所及,可能还有一个同国外交通的问题,具体地讲,就是从蜀起经过滇、缅甸,一直到印度和波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参阅本书下面第二编第六章,“邹和尚与波斯”。
du 〔15〕 。《大宝积经》卷一○,《密迹金刚力士会》第三之三:“其十六大国……释种、安息、月支、大秦、剑浮、扰动、丘慈、于阗、沙勒、禅善、乌(焉)耆前后诸国、匈奴、鲜卑、吴、蜀、秦地……” 〔16〕 以上两例可以证明,吴、蜀两地是常常连在一起的。这个现象怎样解释呢?吴、蜀都濒临长江,交通方便,二者关系密切,可以理解。但是,愚见所及,可能还有一个同国外交通的问题,具体地讲,就是从蜀起经过滇、缅甸,一直到印度和波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参阅本书下面第二编第六章,“邹和尚与波斯”。
第六,疏勒种植甘蔗的问题。甘蔗是热带或半热带的产物。上面的引文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引文中提到的产地,在国外是印度支那半岛和南洋群岛;在国内是多在南方。这是完全合理的。但是有个别的书上竟把甘蔗的产地放在新疆一带,比如《太平寰宇记》,卷一八一说:
(疏勒)土多稻、粟、甘蔗、麦、铜、铁、绵、雌黄……
疏勒在中国新疆,毗邻沙漠地带,怎么能种植热带或半热带植物甘蔗呢?然而白纸黑字,不容怀疑。这个问题同在敦煌卷子中发现有关制糖的记载,同样难解。参阅本书附录《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 〔17〕 。
第七,《齐民要术》第十章那个小注的问题。原文上面已引过,请参看。我认为,这里暗示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到了南北朝贾思勰的时代,甘蔗在中国早已成为习见之物。为什么贾思勰竟在书中给它安排了这样一个位置?这是否意味着贾思勰认为甘蔗非中国所产呢?这个问题我还不敢回答。
第二章就写这样多 〔18〕 。
注释:
〔1〕 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一、二、三章。参阅本书第一编第一章注〔2〕。
〔2〕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8年。
〔3〕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
〔4〕 上引书,第27页。
〔5〕 参阅姜亮夫:《楚辞通故》,齐鲁书社,1985年,第三辑,第197—198页。关于“
 ”,参阅同书、辑,第195—197页。
”,参阅同书、辑,第195—197页。
〔6〕 同上书,第四辑,第70—71页。
〔7〕 本段写完,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上面列举的印欧语系众语言表示“蜜”这个概念的字,都以m音起首而以齿音t,th,d,dh为尾音。汉文的“蜜”字以m音起首,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整个字今天北方话读作mi。古音不是这样子的。根据高本汉(Karlgren)的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蜜”字古音是m êt。这还可以从汉字音译梵字中得到证明。比如梵文Praj
êt。这还可以从汉字音译梵字中得到证明。比如梵文Praj āpāra-mitā汉字音译为“般若波罗蜜多”,mi(蜜)后面有tā(多),才是齿音。又如常见的梵文人名中有mitra,音译为“蜜多罗”,mi(蜜)后面也有t。也许有人认为,tā自成一个音节,与上文mi无涉。实际上这只是皮相之谈。后面的字,即使自成音节,也影响前面的字。最著名的例子是“南无”,梵文、巴利文是namo(a
āpāra-mitā汉字音译为“般若波罗蜜多”,mi(蜜)后面有tā(多),才是齿音。又如常见的梵文人名中有mitra,音译为“蜜多罗”,mi(蜜)后面也有t。也许有人认为,tā自成一个音节,与上文mi无涉。实际上这只是皮相之谈。后面的字,即使自成音节,也影响前面的字。最著名的例子是“南无”,梵文、巴利文是namo(a )和namo。“南”字的古音是nam,不是今天的nan。上面的例子都说明“蜜”字的古音是m起首t结尾,与印欧语系众语言中表示“蜜”字概念的字完全相当。我这样说,并不想证明汉印欧同源。印度学者师觉月(P. C. Bagchi)曾有过这种想法,德国有一位华裔的汉学家也有这种主张。但我认为,下这种结论还为时过早。不过,无论如何,中国的“蜜”字与印欧语系既然如此相近,其中不可能没有原因的。
)和namo。“南”字的古音是nam,不是今天的nan。上面的例子都说明“蜜”字的古音是m起首t结尾,与印欧语系众语言中表示“蜜”字概念的字完全相当。我这样说,并不想证明汉印欧同源。印度学者师觉月(P. C. Bagchi)曾有过这种想法,德国有一位华裔的汉学家也有这种主张。但我认为,下这种结论还为时过早。不过,无论如何,中国的“蜜”字与印欧语系既然如此相近,其中不可能没有原因的。
〔8〕 参阅上面33—34页。飴 为一物,餳餹为一物。
为一物,餳餹为一物。
〔9〕 关于引文,有一个重要问题,必须交代一下。作文章难免引用古书原文,而引文又难免间接引用,比如利用唐《艺文类聚》、宋《太平御览》等古代所谓类书。这些类书引文,大概是为了尽量压缩,往往改写原文。我曾想把这些类书引用的文字,源源本本地、一字不易地查出来。这当然很好,我也努力做过;但是,古代类书引用古书,往往只写书名,比如《诗经》、《汉书》等等,这样的古书有的几十万字,有的上百万字,没有章节,查找起来,宛如大海捞针,艰苦异常。就以《太平御览》为例,我在本章中引用了其中的一些材料,也按照我的想法,同原书进行核对。然而只有书名,没有章节,我尝尽了苦头,有的仍然查不到。我于是就下决心,改弦更张,只引其引文,不再进行核对。如果是搞校勘学的话,这样做是绝对不行的。但我只是利用资料,只要出现的时间与地点基本清楚,就决无损于我的探讨工作,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因此,今后我不再核对原文。偶尔遇到原文,我就写在注中,供读者对比。
还有一点,我也想在这里说明一下。我的探讨目标是“飴”等字所代表的东西出现的时间和地点。至于制造工序和使用材料,李治寰的书中有详尽的叙述,我不再重复,请读者自行参阅。
〔10〕 李治寰上引书,第39、41页。
〔11〕 疑当作“ ”。这两个字在古书中经常相混。
”。这两个字在古书中经常相混。
〔12〕 参阅B. Laufer:Sino-Iranica,Chicago,1919,376页。Laufer认为甘蔗可能原生于印度或东南亚国家。
〔13〕 参阅姜亮夫:《楚辞通故》,齐鲁书社,1985年,第三辑,第187—188页。
〔14〕 我用的是《四部丛刊》上海涵芬楼借江宁邓氏群碧楼藏明钞本影印。
〔15〕 《大正新修大藏经》54,1236上。
〔16〕 同上书,11,59上。参阅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上册,第108—114页《蜀吴之梵名》。岑先生学问广博,甚多建树。但是对中外地名人名的对音问题,却确是一个门外汉,梵文字母看来他都不懂。然而却乐此不疲,说了许多极其离奇荒诞的话,请读者千万要注意。
〔17〕 B. Laufer:Sino-Iranica,p. 376,注2。
〔18〕 《文选》里面还有一些地方提到甘蔗,没有必要再加以征引了。
第三章 石蜜
“石蜜”一词儿最早出现于后汉时期。李治寰说:“石蜜最初是进口商品。” 〔1〕 这是非常可能的。“石蜜”有时被称作“西极石蜜”,或“西国石蜜”,“石蜜”简直就等于“西极(国)石蜜”。这两个词儿有时候难解难分,不辨彼此。
中国古代典籍中使用“石蜜”的地方不少。这个词儿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把多种含义集中到了自己身上。有的同我现在讲的“石蜜”,除了名称相同外,毫无共同之处。这样的例子我也引在这里,目的是让读者对这个名词儿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此外,其中当然也有中国自己制造的“石蜜”,与从外国进口的石蜜并列。在这样的情况下,本书既然分为“国内”和“国外”两编,我就不得不把石蜜也分别在两编中加以讨论。我尽力把在国内制造的石蜜与从外国进口的区分开来。二者的关系既然是难解难分,所以我的区分有时候也难以十分准确,甚至劳而无功。但是我仍要努力去做。
我在本章里主要讲汉魏两晋南北朝的石蜜,隋唐以后的则分别在有关的章中论述。但是,为了让读者能够对“石蜜”这个词儿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隋唐以后的文献也不得不征引一些,免得支离破碎,过分分散。这只限于名词解释,与制造有关的问题,仍在有关章节中加以论述。
根据我的统计,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石蜜”这个词儿共有以下含义:
(一)糖浆
(二)固体石蜜
(三)糖水、牛乳、米粉合成的乳糖
(四)片糖、捻糖
(五)享糖、飨糖、响糖 * 、兽糖
(六)白沙糖
(七)糖霜
(八)冰糖
(九)飴
(十)崖蜜、岩蜜
(十一)樱桃
我在下面分别加以论述。仍然按照上面的老办法,先征引原文,然后加以阐释分析。至于与“石蜜”一词儿相对应的印度梵文原文,则留待下面第二编第三章“西极(国)石蜜”中去探讨。
(一)糖浆
《南中八郡志》:
甘蔗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断而食之,甚甘。榨取汁,曝数时成飴,入口消释,彼人谓之石蜜。 〔2〕
晋郭义恭《广志》:
蔗餳为石蜜。
“蔗餳”就是浓缩糖浆。
(二)固体石蜜
《凉州异物志》:
石蜜非石类,假石之名也。实乃甘蔗汁煎而曝之,则凝如石而体甚轻,故谓之石蜜也。 〔3〕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凉州接近丝绸之路,从西域进口东西是很容易的。其次,“异物”二字也有特殊含义,说明这种“固体石蜜”很可能不是国货,而是域外进口的。第三,这种“石蜜”来自蔗浆,是把蔗浆熬了以后又在太阳中曝晒,终于成为固体的东西。总之,这种石蜜似乎就是“西极石蜜”了。在下面第二编中还要谈。
我在这里还必须谈一谈“煎而曝之”的问题,因为这牵涉到石蜜制造的过程。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上,“甘蔗”条说:
交趾有甘蔗,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断而食之甚甘。笮取汁,曝数时成飴,入口消释,彼人谓之石蜜。
《齐民要术》卷一○,“甘蔗”条引:
《异物志》曰: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甘蔗特醇好。本末无薄厚,其味至均。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斩而食之既甘。迮取汁如飴餳,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如冰,破如砖其(?)。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
“砖其”二字,颇怪。《太平御览》卷八五七,引《异物志》作“破如博棋”,疑“砖其”二字即“博棋”之讹。
李时珍《本草纲目》引用了万震《凉州异物志》中的那一段话,见上面所引。
类似的资料还有一些,我不再引用了。从这条引文中就可以看出,正如我在上面“引言”中“资料”一节中所说的,当时出现了不少的《异物志》,头绪纷乱,互相抄袭。我不想,也没有能力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看来也无此必要。因为我探讨的重点不是这个问题。
我想探讨的是“煎”与“曝”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这种固体石蜜是熬成的呢?还是晒成的?或者先熬后晒成的?《南方草木状》只讲到“曝”,《异物志》则是“煎而曝之”。孰是孰非,我目前还无法判断 〔4〕 。
(三)糖水、牛乳、米粉合成的乳糖
唐苏恭《新修本草》(《唐本草》):
石蜜用水(羡林按:李治寰《从制糖史谈石蜜和冰糖》〔《历史研究》1981年第二期〕说:此处脱一“糖”字,应为“糖水”。我看是正确的)、牛乳、米粉和煎成块,作饼坚重。西域来者佳。江左亦有,殆胜于蜀。
请注意:这里用的是“煎”字。
和苏恭一起修《唐本草》的孔志约 〔5〕 说:
石蜜出益州、西域,煎沙糖为之,可作饼块,黄白色。
这里用的也是“煎”字。
唐孟诜《食疗本草》:
石蜜自蜀中、波斯来者良。东吴亦有,不及两处者。皆煎蔗汁、牛乳,则易细白耳。
这里同样用的是“煎”字。
以上引用的都是唐人的说法。但是,我怀疑,这种制造法也许唐代以前就有,所以我在这里论述。至于宋代以后的说法,这里就暂且不谈了。
(四)片糖、捻糖
宋寇宗奭《本草衍义》卷一七:
石蜜,川浙者最佳。其味厚,他处皆次之。煎炼以铜象物,达京师。至夏月及久阴雨多,自消化。土人先以竹叶及纸裹包,外用石夹埋之,不得见风,遂可免。今人谓之乳糖。其作饼黄白色者,谓之捻糖,易消化,入药至少。
李治寰,上引文,第148页说:
石蜜制成饼状或块状是为了便于包装运输,制成人物鸟兽状是作为馈赠礼品。前者如宋寇宗奭所说的捻糖及以后演变为我国民族性的传统产品的片糖。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所说的“兽糖”就属于这一类。
(五)享糖、飨糖、响糖、兽糖
这一些糖名同上面(四)片糖、捻糖有时难以区分。为了全面起见,姑分为两类。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造兽糖》:
凡造兽糖者,每巨釜一口,受糖五十斤。其下发火慢煎。火从一角烧灼,则糖头滚旋而起。若釜心烧火,则尽沸溢于地。每釜用鸡子三个,去黄取青,入冷水五升化解。逐匙滴下用火糖头之上,则浮沤黑滓尽起水面,以笊篱捞去。其糖青白之至。然后打入铜铫,下用自风慢火温之。看定火色,然后入模。凡狮象糖模,两合瓦为之。勺泻糖入模,随手覆转倾下。模冷糖烧,自有糖一膜靠模凝结,名曰享糖,华筵用之。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
以白沙糖煎化,模印成人物狮象之形者,为饗糖,《后汉书》所谓猊糖是也。
李治寰,上引文,第149页说:“这些享糖、飨糖、响糖、兽糖等,也是唐宋时的石蜜。”
(六)白沙糖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第三十三章,“石蜜”条:
石蜜,即白沙糖也。凝结作饼块如石者为石蜜。轻白如霜者为糖霜。坚白如冰者为冰糖。皆一物有精粗之异也。
李治寰,上引文,第151—153页认为:李时珍的石蜜即白沙糖的说法有点误解,请参阅原文。我在下面第八章讲到明代制糖术的时候,还要讨论这个问题。
(七)糖霜
(八)冰糖
我把糖霜和冰糖结合在一起来讨论,因为没有法子分得清楚。石蜜、糖霜和冰糖,似是一物,但有时又有区别,其间关系错综复杂。
上面(六)中引用了李时珍的说法,他把石蜜、糖霜和冰糖都说成是来自白沙糖,只是制成的形式有点差别,“皆一物有精粗之异也”。在中国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赋和文中,以及这一时期的正史中,只有“石蜜”一个词儿,没有“糖霜”和“冰糖”的名称。“石蜜”把这些东西都代表了。引文见下面第二编国际编第三章,“西极(国)石蜜”,这里不引。
至于“糖霜”与“冰糖”的关系,也是混淆不清的。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和李调元(《粤东笔记》卷一四),都说糖霜就是冰糖。丁国钧《荷香馆琐言》说:“糖霜当是冰糖。”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也认为糖霜应是冰糖 〔6〕 。
(九)飴
宋洪迈《糖霜谱》:
《南中八郡志》云:笮甘蔗汁,曝成飴,谓之石蜜。
《太平御览》八五七,饮食部:
《本草经》曰:石蜜,一名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