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人类的性选择及本书的结论
·Sexual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Man,and Conclusion·
这里所得到的主要结论是,人类起源于某种体制较低的类型,这一结论现在已得到了许多有正确判断能力的博物学者们的支持。这一结论的根据决不会动摇,因为人类和较低等动物之间在胚胎发育方面的密切相似,以及它们在构造和体质——无论是高度重要的,还是最不重要的——的无数之点上的密切相似,还有,人类所保持的残迹(退化)器官,他们不时发生畸形返祖的倾向,都是一些无可争辩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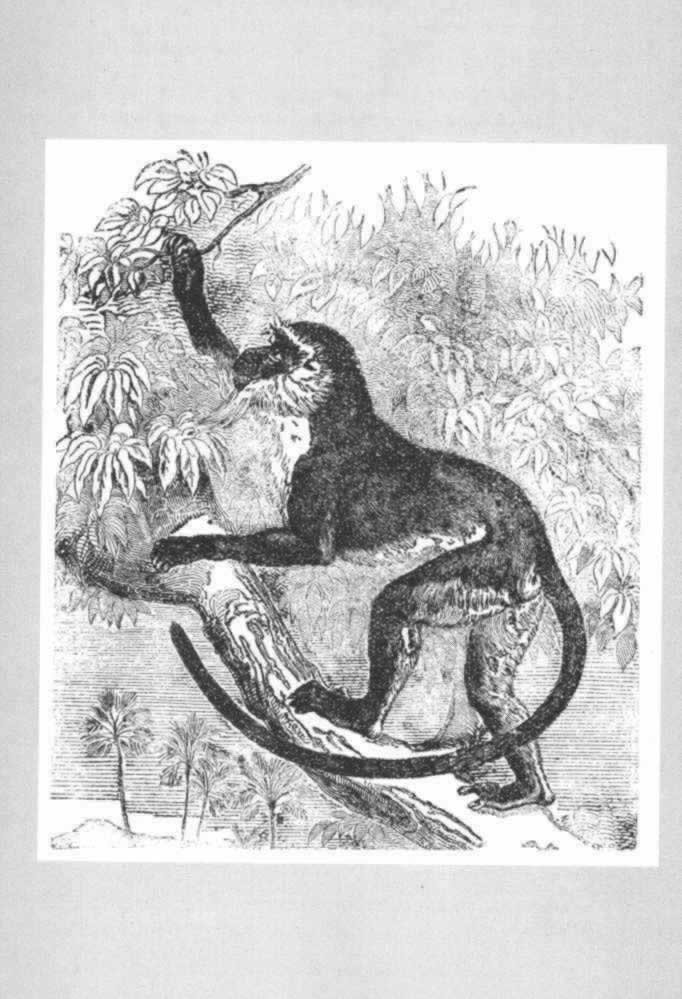
▲在动物学会的动物园里,我常常无意中听到游客们赞美另一种猴,它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为白须长尾猴。
在这等猴以及许多其他猴中,其颜色之美及其奇特的排列,尤其是头部冠毛以及簇毛的各式各样的优雅排列,迫使我不得不相信这等性状完全是作为装饰物,通过性选择而获得的。
第十九章 人类的第二性征
男女之间的差异——这等差异以及男女双方所共有的某种性状的起因——战斗的法则——心理能力以及声音的差异——美貌对决定人类婚姻的影响——未开化人对装饰品的注重——未开化人对女性美的概念——对各个先天特性夸张的倾向
人类男女之间的差异大于大多数四手类的性差异,但不及某些四手类,如西非山魈的性差异那么大。男人平均比女人高得多、重得多、而且力量大得多,前者的双肩较宽阔,肌肉也显著地更发达。由于肌肉的发达同眉部的向前突出存在着关联 (1) ,所以男人的眉脊一般高于女人的。男人的体部,尤其是面部具有更多的毛,而且他的音调不同,更加强有力。在某些种族中,据说女人的肤色同男人的稍有差异。例如,施魏因富特(Schweinfurth)当谈到居住在北纬数度的非洲腹地的蒙博托族(Monbuttoos)黑人妇女时说道:“她的皮肤比她丈夫的要淡几个色调,有点呈半炒咖啡色,所有她这个种族都是如此。” (2) 由于妇女在大田里劳动,而且不穿衣服,所以她们在肤色上同男人的差异不见得是由于暴露在日光中较少的缘故。欧洲妇女的肤色恐怕比男人的较鲜明,当男女双方同等地暴露在日光中时即可明了这一点。
男人比女人勇敢、好战、精力强,而且富有较高的发明禀赋。男人的脑绝对地大于女人的脑,但这是否同其较大的身体成比例,我相信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女人的面部较圆;两颚和头骨基部较小;体部轮廓较圆,有些部位较突出;而且女人的骨盆比男人的宽阔 (3) ;但是,与其把后述这一性状视为初级性征,莫如把它视为次级性征。她达到成熟的年龄比男人更早。
在所有各纲的动物中,雄性不到接近成熟时,其显著不同的性状不会充分发展,而且施行去势之后,这等性状即永不出现;在人类中亦复如此。例如,胡须是一种次级性征,男孩没有胡须,虽然在其幼小时头发很多。这大概由于在男人方面所发生的连续变异是在生命的很晚时期出现的,男人通过这等变异获得了男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只向男性传递。男孩和女孩彼此密切相似,就像如此众多的其他动物的雌雄幼仔彼此相似一样,在这些动物中其成年的雌雄二者却大有差别;同样地,男孩和女孩同成熟女人的相似远比同成熟男人的相似为甚。然而,女人最终总要呈现某种明确不同的性状,而且在其头骨的构造上据说是介于儿童和男人之间的。 (4) 再者,亲缘密切近似,但有所不同的物种,其幼仔之间的差异并不像成年动物之间的差异那样大,人类不同种族的儿童也是如此。有些人甚至主张从婴儿的头骨不能找出种族的差异。 (5) 关于肤色,新降生的黑人婴儿呈微红的栗色,很快就变为蓝灰色;在苏丹,婴儿到一岁时其皮肤黑色才充分发达,在埃及,不到三岁这种黑色不会充分发达。黑人的眼睛在最初呈蓝色,毛发最初为栗褐色,而不是黑色,只在发端是卷曲的。澳大利亚人的儿童刚降生时呈黄褐色,但在以后的年龄中其肤色就变深了。巴拉圭的瓜拉尼族(Guaranys)婴儿呈白黄色,但在几个星期后便获得了其双亲的黄褐色。在美洲的其他部分所作的观察也相似。 (6)
我之所以列举上述人类男女之间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同四手类的情况异常相似。在四手类中,雌者的成熟年龄早于雄者的,至少巴拉圭卷尾猴(Cebus azarae)肯定如此。 (7) 大多数四手类物种的雄者比雌者身大力强,在这方面,大猩猩提供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例。甚至像非常微小的一种性状,如眉脊的突出,某些猿猴类的雄者也不同于雌者, (8) 这与人类的情况相符。在大猩猩以及某些其他猿猴类中,成年雄者的颅骨具有强烈显著的矢形突起(sagittal crest),而雌者却没有这种突起;埃克尔发现澳洲人男女间也有与此相似的差异残迹。 (9) 在猿猴类中,如果在叫声方面存在任何差异,总是雄者的叫声更加强有力。我们已经看到,某些雄猴具有十分发达的胡须,而雌者却完全没有胡须,或者其胡须发育差得多。据知还没有一个事例表明雌猴的胡须、颊须和髭长于雄者的。甚至在胡须的颜色方面,人类和四手类之间也异常相似,人类的胡须如果同头发的颜色有所差异,正如通常所见到的那样,几乎总是胡须的颜色较淡,而且常常呈现微红色。我在英格兰曾反复对此做过观察;但有两位先生最近给我写信说,他们是例外。其中一位先生说,其原因在于他家庭中父系和母系的发色迥然不同。此二人早已觉察到这一特点(其中一人常被指责把胡须染了),因而被引导去观察别人,他们终于相信这等例外是很罕见的。胡克博士在俄国为我注意观察过这个问题,发现没有一个例外。在加尔各答,植物园的斯考特先生非常热心地为我观察了当地以及印度一些其他地方的许多种族,即:锡金的两个种族、波达人(Bhoteas)、印度人、缅甸人和中国人,大多数这些种族的面毛都很稀少;他总是发现,如果头发和胡须在颜色方面有任何差异的话,一定是胡须的颜色较淡。那么,关于猿猴类,如上所述,它们的胡须和头发在颜色上往往差异显著,在这等场合中,总是胡须的颜色较淡,常呈纯白色,有时呈黄色或微红色。 (10)
就一般体毛而言,都是女人的毛比男人的毛较少;在少数某些四手类中,雌猴身体底面的毛比雄猴这一部分的毛为少。 (11) 最后,雄猴就像男人那样,比雌猴更勇敢而且更凶猛。它们领导猴群,遇有危险,则勇往直前。由此我们便可知道,人类和四手类的性差异是何等密切相似。然而,少数某些物种,如某些狒狒、猩猩以及大猩猩的性差异要比人类的大得多,犬齿的大小、毛的发达及其颜色,尤其是裸皮的颜色,都是如此。
人类的一切次级性征都是高度容易变异的,甚至在同一种族的范围内也是如此;而若干种族的次级性征则差别很大。这两条规律一般在整个动物界中都是适用的。在诺瓦拉(Novara)船上所做的精密观察表明, (12) 澳大利亚人的男子仅高于女子65毫米,而爪哇人的男子却高于女子218毫米;因此,后一种族的男女身高之差高出澳大利亚人3倍以上。关于身长、颈围、胸围、脊骨长度以及双臂长度,在各个不同种族中进行了大量的精细测量;几乎所有这些测量结果都表明,男人彼此的差异要比女人的大得多。这一事实示明,仅就这等性状而言,自若干种族从其共同祖先分歧以来,主要发生变异的正是雄者。
不同种族的、甚至同一种族不同部落或家族的男人,在胡须以及体毛的发育方面均有显著差异。我们欧洲人看看自己就可知道这一点了。按照马丁的材料 (13) ,在圣基尔达岛(St.Kilda),男人不到30岁或30岁以上不长胡须,甚至在这时候他们的胡须也很稀疏。在欧亚大陆,直到越过印度以西,各个种族男人的胡须都很旺盛;但锡兰土人却往往不长胡须,第奥多拉斯(Diodorus)在古代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14) 印度以东的各个种族,如暹罗人、马来人、蒙古人(Kalmucks)、中国人以及日本人则胡须稀疏,尽管如此,在日本列岛最北方居住的虾夷人(Ainos) (15) 却是世界上最多毛的人。非洲黑人甚少胡须或无胡须,而且具有颊须者也很少;男女双方的体部几乎连细毛也没有。 (16) 相反,马来群岛的巴布亚人虽和黑人差不多一样黑,却有十分发达的胡须。 (17) 太平洋上斐济群岛(Fiji Archipelago)的居民都有浓厚的大胡须,但其附近汤加(Tonga)群岛和萨摩亚(Samoa)群岛的居民就不长胡须;不过他们属于不同的种族。在埃利斯(Ellice)群岛,所有居民都属于同一种族,然而只有一个岛,即努内玛亚岛(Nunemaya)的“男人生有漂亮的胡须,而其余各岛男人的胡须照例也不过是十几根零乱的毛而已”。 (18)
在整个美洲大陆上居住的土人可说都不长胡须,但几乎所有部落的男人都有在面部生长少数几根短毛的倾向,特别是老年人尤其如此。在北美的诸部落中,卡特林(Catlin)估计20个男人中就有18个生来就完全不长胡须;间或可以看到一个男人,如果在青春期忘拔胡须的话,也会有1~2英寸长的柔软胡须。巴拉圭的格拉尼族和所有周围的部落不同,具有短胡须,甚至在体部也长些毛,但没有颊须。 (19) 福布斯先生特别注意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说,科迪耶拉(Cordillera)的亚马拉人和基切亚人都是显著无毛的,但到了老年偶尔也会在下巴上长出少数几根零乱的毛。这两个部落的人在欧洲人茂密长毛的那些身体部位,却只长很少的毛,而女人在相应的部位则无毛。而他们男女的头发却特别长,往往几乎触及地面;有些北美部落的人也是如此。就毛的数量和身体的一般形状而言,美洲土人男女之间的差异并不像大多数其他种族那样大。 (20) 这一事实同亲缘密切近似的猴类之间的情况是相似的;例如黑猩猩雌雄二者之间的差异就不像猩猩或大猩猩雌雄二者之间的差异那样大。 (21)
在以上数章里我们已经看到,有各种理由可以相信哺乳类、鸟类、鱼类、昆虫类等等的许多性状最初是由某一性通过性选择而被获得的,然后又传递给另一性。由于这种同样的传递形式显然也非常通用于人类,所以当我们讨论为雄者所特有的性状以及为雌雄二者所共有的某些其他性状之起源时,将会省去无用的重复。
战斗的法则
关于未开化人,例如澳洲土人,妇女是同一部落诸成员之间以及不同部落之间进行战斗的一个经常原因。在古代无疑也是如此;“希腊以前,战争的原因就是为可憎的女子”。关于某些北美印第安人,他们的这种争斗已成为一种制度。优秀的观察家赫恩(Hearne)说 (22) :“男人强夺他们所爱慕的女人,已成为这等民族的风俗;当然,总是最强的一伙得胜。一个软弱的男人除非是一个良好的猎手而且十分可爱,很少能保住自己的妻子而不被较强者夺去。这种风俗通行于所有部落,并且鼓舞着青年们的竞争精神,他们从小就利用一切机会参加抢婚,练武习艺。”阿扎拉说,南美瓜纳人(Guanas)的男子不到20岁以上很少娶妻,因为在20岁以前他们不能战胜其对手。
还可以举出其他相似的例子;但是,即使没有关于这一问题的证据,根据高等四手类的情况来类推 (23) ,我们差不多也可以肯定战斗的法则在人类的早期发展阶段是通行的。人类今天还偶尔生长犬齿,超出其他诸齿之上,下颚也偶尔会出现容纳上颚犬齿的虚位痕迹,这种情况完全可能是返归往昔状态的一个例子,那时人类的祖先还具有这等武器,就像如此众多的现存雄性四手类那样。在前一章已经提到,当人类逐渐变得直立并且不断地使用手和臂拿木棍和石头来进行战斗以及从事其他生活活动时,他们使用颚和齿就会越来越少。于是上下颚及其肌肉通过不使用大概就要缩减,而牙齿通过尚未十分理解的生长相关原理和生长经济原理大概也要缩减;因为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凡是不起作用的部分都要缩小。通过这样的步骤,人类男女的颚和齿的原始不相等性,最终就会消除。这一情况同许多雄性反刍动物的情况差不多是相似的,反刍动物的犬齿已缩小成仅仅是一种残迹,或竟消失,这显然是角的发达的结果。由于猩猩和大猩猩雌雄二者在头骨方面的重大差异同其雄者巨大犬齿的发达存在着密切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推论,人类早期祖先的颚和齿的缩小一定会引起他们的面貌发生最显著而有利的变化。
同女人比较起来,男人的体格较大、体力较强,而且双肩较阔,肌肉较发达,身体轮廓较粗壮,更为勇敢,更为好斗,所有这些主要都是来自其半人男性祖先的遗传。然而,在人类长期的未开化期间,由于最强壮而且最勇敢的男人无论在一般生存斗争还是在夺妻斗争中均获得成功,上述性状大概会被保存下来,甚至会被增大;这种成功大概还会保证他们比其较劣的同伴留下大量的后代。男人最初获得较强的体力大概不会是由于下述的遗传效果所致,即男人为了自己和家庭的生计要比女人付出更强的劳动;因为,在所有未开化的民族中女人也要被迫劳动,其强度至少和男人的一样。凭战争来占有妇女,在文明人中早已停止了;另一方面,按照一般规律,男人势必比女人付出更强的劳动来维持其共同的生活,这样,他们的较强体力大概会保持下来。
男女心理能力的差异
关于男女之间这种性质的差异,性选择大概起了高度重要的作用。我知道有些作者怀疑任何这等差异是否经过遗传而来的;但是,根据具有其他第二性征的低于人类的动物来类推,上述情况至少是可能的。没有人会争论,公牛和母牛、公野猪和母野猪、公马和母马,在性情方面彼此之间都不相同,而且正如动物园管理员所熟知的那样,大型猿类雌雄二者的性情也彼此不同。女人和男人的气质似乎也不相同,这主要表现在她们较多的温柔和较少的自私;甚至未开化人也是如此,在芒戈·帕克所写的《旅行记》的著名一节中以及在许多其他旅行者的叙事中均有这样记载。女人由于她的母性本能,对其婴儿把这等属性发扬到极端的程度,所以她们把这等属性扩展到同群之人是很可能的。男人是另外男人的竞争对手;喜欢争胜,这就会引起野心,而野心非常容易发展成利己主义。后面这等属性似乎是他所具有的天然的而且不幸是生来就有的权利。一般承认,女人所具有的直觉能力、迅速知觉的能力、恐怕还有模仿的能力,都比男人强得多;但是,至少有些这等官能乃是较低种族的特征,因而也是过去文化较低状态的特征。
男女智力的主要差别在于男子无论干什么事,都比女人干得好——无论需要深思、理性的,还是需要想象的,或者仅仅使用感觉和双手的,都是如此。如果列出两张表,载入在诗歌、绘画、雕塑、音乐(包括作曲和演奏)、历史、科学以及哲学诸方面的成就最杰出的男人和女人,每一门为10名,即可看这两个表将无法进行比较。高尔顿先生在其《遗传的天才》那一著作中,对“平均离差法则”(1aw of the deviation from average)做过充分的说明,我们根据这一法则可以推论,如果男人在许多智力活动方面都优于女子,则男子的心理能力一定高于女子。
在人类的半人祖先中,以及在未开化人中,男人之间为了占有女人进行了许多世代的斗争。但是仅恃体大力强,很少能取胜,除非同勇敢、坚忍以及不挠的精力结合起来,才能奏效。关于社会性的动物,幼小的雄者在赢得一个雌者之前,势必通过多次争斗,而且较老的雄者也势必重新进行战斗才能保持住它所占有的雌者。在人类的场合中,男人还势必保卫其占有的女人及其子女不受所有种类的敌者为害,同时还得为大家的共同生存去狩猎。但是,为了成功地避免敌害或向它们进攻,为了捕获野生动物,为了制造武器,就需要较高的心理官能、即观察、理解、发明或想象的帮助。这种种官能在男子成年期间不断受到检验和淘汰;在这同一期间,这等智力通过使用进而得到加强。因此,按照常常提到的那一原理,我们可以预期这等智力至少倾向于在相应的男子成年期间主要向男性后代传递。
那么,如果两个男人进行竞争,或者一个男人同一个女人进行竞争,而且双方所具有的每一种心理属性都是同等完善的,那么倘一方具有较高的精力、坚持力和勇气,则这一方一般就会在各种事务中领先并占有优势。 (24) 所以说他有天才——因为一位大权威曾经宣称,天才就是耐力;从这种意义来说,耐力就意味着不屈不挠的坚持。但这种对天才的见解恐怕还有不足之处;因为,如果没有想象和理解的较高能力,就不能在许多问题上得到卓越的成功。后面所说的这等官能以及前面所说的那些官能在人类中是通过性选择——即通过敌对的雄者之间的斗争、而且部分地通过自然选择——即通过在一般生存斗争中获得成功而发达起来的;由于这两种争斗都是在成熟期间进行的,所以,这一时期所获的性状传递给雄性后代的比传递雌性后代的更加充分。
这同下述观点显著符合,即,人类许多心理官能的变异和加强都是通过性选择来完成的,第一,这等心理官能的大量变化显然发生于青春期, (25) 第二,阉人的这等心理官能终生处于劣势。这样,男人终于要变得优于女人。幸而性状向雌雄双方同等传递的法则通行于哺乳类;否则男人的心理禀赋可能远远高出女人之上,就像雄孔雀的装饰性羽衣优于雌孔雀的那样。
必须记住,雌雄任何一方在生命晚期获得的性状,都有在那一时期传递给同一性别的倾向,而在生命早期获得的性状则有传递给雌雄双方的倾向,这虽然是一般规律,但并非永远都能适用。如果这一规律永远适用,我们便可断言(但我已超出了我的讨论范围),男孩和女孩的早期教育的遗传效果大概会同等地向男女双方传递;所以男女双方心理能力现今这样的不相等并不会由于早期教育的相似过程而被抹去;而且这种不相等也不是由于早期的不相似教育而形成的。因此,要使女人达到男人同样的标准,就应该在她们接近成年时锻炼其精力和坚忍精神,而且运用其理解力和想象力以达到最高水平;于是,她大概可以把这等属性主要传递给其成年的女儿。然而,不是所有女人都能提高到这样的水平,除非具有上述健全美德的女人在许多代中都能婚嫁,而且比其他女人生下数量较多子女。至于上面所说的体力,现今已用不到它去进行夺妻斗争了,这种选择方式已成过去,但是,在男子成年期,他们一般还要进行剧烈的争斗以维持其本身和家族的生存;这就倾向于把他们的心理能力保持下来,甚至增强,其结局便形成了男女之间现今这样的不相等性。 (26)
声音和音乐能力
在四手类的某些物种中,成年的雌雄二者之间在发音能力方面以及在发音器官的发达程度方面都有重大差异;人类似乎也从其早期祖先遗传了这种差异。成年男人的声带约比女人和小孩的长三分之一,去势对人类发生的效果和对低于人类的动物发生的效果一样,因为这种效果“抑制了甲状腺的显著生长,等等,而‘声带’的延伸正与甲状腺的生长相伴随”。 (27) 关于男女之间这种差异的原因,我在前一章曾谈到雄者在爱情、愤怒和嫉妒的激动下长期连续使用发音器官的可能效果,此外我还无可补充。按照邓肯·吉布(Duncan Gibb)的说法, (28) 声音和喉头的形状在人类的不同种族中是不同的;但是,据说鞑靼人、中国人等,其男人的声音同女人的声音不像大多数其他种族男女之间的这种差别那样大。
歌唱和演奏音乐的能力及其爱好,虽然不是人类的一种性征,却不可置之不论。所有种类的动物发出的声音虽有许多用途,但有一个强有力的事例可以说明,发音器官的最初使用及其完善化是同物种的繁殖有关联的。昆虫类以及某些少数蜘蛛类是最低等的动物,它们故意地发出声音;这种发音一般是借助于构造美丽的摩擦发音器官来完成的,而这种器官往往只限于雄者所有。这样发出的声音是由有节奏地反复同一音调构成的 (29) ,我相信在所有场合中都是如此;这种音调有时甚至使人类感到悦耳。其主要的、在某些场合中唯一的目的在于召唤或魅惑异性。
据说在某些场合中只有雄鱼在繁殖季节才发出声音。一切呼吸空气的脊椎动物均须具有一种吸入和呼出空气的器官,同时还需具有一根在一端可以关闭的气管。因此,当这一纲的原始成员强烈激动时,它们的肌肉就要剧烈收缩,毫无目的的声音几乎肯定会由此发生;这等声音如果被证明在任何方面有所作用,由于完全适应的变异得到保存,它们大概就会容易地被改变或加强。呼吸空气的最低等动物为两栖类;在这类动物中,蛙类和蟾蜍类都有发音器官,在繁殖季节它们不断地使用这等器官,而雄者的发音器官往往比雌者的更加高度发达。在龟类中只有雄者才能发音,而且仅在求偶季节如此。雄鳄鱼在求偶季节也吼叫。众所周知,鸟类把它们的发音器官用做求偶手段的是何等之多;而且有些物种还会演奏所谓的器乐。
在这里我们特别关心的是哺乳类,在这一类动物中,几乎所有物种的雄者在繁殖季节比在任何其他时期更加常常使用它们的声音;有些物种除在这一季节外绝不发音。另外有些物种,其雌雄二者或只是雌者使用它们的声音作为求偶的召唤。鉴于这等事实,以及某些雄性四足兽的发音器官在繁殖季中永久地或暂时地比雌者的发音器官更加发达得多;同时鉴于在大多数较低等的动物纲中,雄者的发音不仅用来召唤雌者而且用来刺激或魅惑雌者,那么,要说我们至今还没有掌握任何良好的证据来阐明雄性哺乳动物使用这等器官来魅惑雌者,那就真是一件怪事了。美洲卡拉亚吼猴恐怕是一个例外,同人类近似的敏长臂猿也是如此。这种长臂猿的声音极高,不过好听。沃特豪斯(Waterhouse)说 (30) ,“其音阶的上下之差永远正好是半音;我确信其最高音至最低音恰为八音度。音调非常悦耳;除了它的声音过高外,我不怀疑一位好提琴家大概能够正确地奏出长臂猿所作的曲调。”然后沃特豪斯记出其音符。欧文教授是一位音乐家,他证实了以上的叙述,并且说道,“在野生的哺乳动物中只有长臂猿可称为能歌唱”,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它们在歌唱之后,似乎非常激动。不幸的是,在自然状况下从来没有对它的习性进行过观察,但从其他动物来类推,它在求偶季节格外运用其音乐能力。
在能歌会唱的属中,这种长臂猿不是唯一的物种,因为我的儿子弗朗西斯·达尔文(Francis Darwin)在伦敦动物园中用心地听过银灰长臂猿(H.leuciscus)的歌唱,这个乐章由三种音调组成,其音程真正是音乐的,而且具有清楚的音乐调子。还有更为奇怪的事情,某些啮齿类会发出音乐的声音。常常提到有能歌唱的鼠,而且被展览过,不过一般猜测这是欺骗。然而,我们终于得到了著名观察家洛克伍德(Lockwood)牧师 (31) 对一个美洲物种的音乐能力所作的清楚记载,这个物种就是西洋鼠(Hesperomys cognatus),属于和英国鼠不同的一个属。这个小动物养于拘禁之中,反复地听到它的演奏。它演奏的有两支主要歌子,在其中的一支歌子中,“最后一小节屡屡延长为两三个小节;它有时把C高音和D音变为C本位音和D音,然后用柔和的颤音唱出这两个音调,片刻之后,以快速的C高音和D音来作结束。其半音之间的界限有时是很明显的,而且善听之耳容易加以区别。”洛克伍德先生把这两支歌子记入乐谱,而且补充说道,这种小鼠“虽无节奏感,却能保持B调(降两个半音),而且严守主调”。……“其柔和清脆的声音非常正确地降下一音阶;然后在结束时再度抬高转为C高音和D音的急速颤声。”
一位批评家问道,人类之耳(他还应加入动物之耳)何以能够通过选择而适应去辨别音乐的声调。但是,这一发问表明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有某种混淆不清之处,所谓噪音乃是对各个不同乐段的若干空气“单振动”同时存在所产生出来的感觉,各个单振动的中断如此屡屡发生,以致无法觉察到它的分别存在。噪音和音乐声调的差别仅仅在于噪音的振动缺少连续性,且各个振动之间缺少和谐性。这样,耳就能够辨认噪音——每一个人都承认这种能力对一切动物的高度重要性,因此耳对音乐声调也一定能够有所感觉。甚至在等级很低的动物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关这种能力的证据:例如,甲壳类具有不同长度的听毛(auditory hairs),如果奏出适当的音乐声调,可以看到听毛就会振动。 (32) 在前一章已经提到,关于蚊类触角上的毛,也做过同样的观察。优秀的观察家们曾经断定,音乐对蜘蛛有吸引力。有些狗听到特殊的音调就要吠叫, (33) 这也是众所熟知的。海豹显然欣赏音乐,“古人对海豹的这种爱好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在今天猎人还常常利用这一点”。 (34)
因此,仅就对音乐声调的感觉而言,无论在人类的场合中,还是在其他动物的场合中,似乎都不存在特殊的难题。海伦赫支根据生理学的原理来说明和谐音为什么是悦耳的,而不和谐音为什么是不悦耳的;但这同我们的讨论关系不大,因为和谐的音乐乃是晚近的发明。同我们的讨论关系较多的乃是悦耳的音调,按照海伦赫支的说法,为什么要使用音阶的音符也是可以理解的。耳可以把所有声音分析为合成这等声音的单振动,虽然我们对于这种分析并不自觉。在一种音乐声调中最低的音一般占主位,其他较不显著的音为第八音,第十二音,第十六音,等等,所有这等音都是同基础主音相和谐的;音阶中的任何两个音共同都有许多这等和谐的陪音。于是,情况就似乎相当清楚了:如果一个动物总是准确地唱同一支歌,那么它就要接连地使用那些共同具有许多陪音的音调——这就是说,这个动物为它的歌唱大概会选用属于人类所使用的音阶的那些音调。
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具有一定顺序和节奏的音乐调子为什么能使人和其他动物感到愉快,我们所能举出的理由不会超出为什么一定的味道可以悦口而且一定的气味可以悦鼻。根据这等声音是由许多昆虫类、蜘蛛类、鱼类、两栖类以及鸟类在求偶季节发出的,我们可以推论这等声音确能使动物感到某种愉快;因为,除非雌者能够欣赏这等声音,而且受到它的刺激或魅惑,否则雄者不屈不挠的努力以及往往只是雄者才具有的这种复杂构造大概就是无用的了;但这是不可相信的事。
一般认为,人类的歌唱乃是器乐的基础或起源。由于欣赏音乐以及产生音乐调子的能力就人类的日常生活习性而言都是一点也没有用处的才能,所以必须把它们列为人类禀赋中最神秘的一种。人类的所有种族、甚至未开化人都有这等才能,虽然是处于很原始的状态;若干种族爱好什么样的音乐却如此不同,以致我们的音乐不会使未开化人感到有趣,而他们的音乐大多数则使我们感到讨厌和索然寡味。西曼(Seemann)在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有趣评论中 (35) 怀疑到,“甚至在西欧诸民族中,某一个民族的音乐是否会按照同样的意义被其他民族所理解,虽然它们交通紧接,来往频繁,关系密切。愈向东行,我们便会发现那里肯定有不同的音乐语言。欢乐的歌唱以及舞蹈的伴奏已不像我们那样地使用大调(major keys),而总是使用小调。”无论人类的半动物祖先是否像能够献唱的长臂猿那样地具有产生音乐调子、因而无疑具有欣赏音乐调子的能力,我们知道人类在非常远古的时期就有这等才能了。拉脱特描述两支由骨和驯鹿角制成的长笛,这是在洞穴中发现的,其中还有燧石具以及绝灭动物的遗骸。唱歌和跳舞的艺术也是很古老的,现在所有或几乎所有人类最低等的种族都会唱歌和跳舞。诗可以视为由歌产生的,它也是非常古老的,许多人对于诗发生在有史可稽的最古时代都感到惊讶。
我们知道,完全缺少音乐才能的种族是没有的,这种才能可以迅速地而且高度地得到发展,例如霍屯都人和黑人都可以成为最优秀的音乐家,虽然他们在其家乡所演奏的没有一种可以称为音乐的。然而,施魏因富特却喜欢他在非洲腹地所听到的一些简单的曲调。不过人类的音乐才能处于潜伏状态一点才不奇怪:有些鸟类的物种生来就不鸣唱,但把它们教会并不十分困难;例如,有一只家麻雀学会了红雀的鸣唱。由于这两个物种的亲缘是密切接近的,都属于燕雀目,这个目包括了世界上几乎所有能鸣唱的鸟,所以麻雀的某一个祖先可能就是能鸣唱的。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鹦鹉所属的类群不同于燕雀类,且其发音器官具有不同的构造,它不仅可以学会说话,而且可以学会吹奏人类所制的曲调,所以它一定有某种音乐才能。尽管如此,倘假定鹦鹉来源于某一个能鸣唱的祖代类型,未免还是过于轻率了。可以举出许多事例来表明,原本适于某一目的的器官和本能竟用于另一截然不同的目的。 (36) 因此,人类未开化种族所具有的高度发达的音乐能力,或是由于人类半动物祖先演奏某种粗略形式的音乐,或是单纯地由于它们获得了适于不同目的的适当的发音器官。但是,在后一场合中我们必须假定他们已经具有对音调的一定感觉,上述鹦鹉的情况就是这样,恐怕还有许多动物也是如此。
音乐可以激发人类的各式各样的情绪,但不是恐怖、畏惧、愤怒等那样激烈的情绪。它能唤醒温柔而怜爱的优雅感情,由此很容易变为虔诚。在中国的编年史中写道,“闻乐如置于天上。”它还能激起我们的胜利感以及光荣地进行战争的热情。这等强有力的和交集的感情可以充分地引起崇高感。正如西曼博士所观察的,一曲音乐比若干页文章更能把我们的强烈感情凝聚起来。当雄鸟倾吐其全部歌唱,与其他雄鸟竞争,以吸引雌鸟时,其感情同人类所表现的大概差不多是相同的,不过远远不及人类情感那样强烈,那样复杂而已。在我们的歌曲中爱情依然是最普通的主题。赫伯特·斯宾塞说:“音乐可以激发潜伏的情感,我们既不能想象其存在,又不知其意义;或者,如里克特(Richter)所说的,音乐告诉我们的事情是未曾见到的,而且今后也不会见到。”相反,当演说家感到并表达强烈的情绪时,甚至在普通谈话中,也会本能地使用音乐的调子和节奏。非洲黑人当激动时会突然大声歌唱;“另外的人则以歌作答,于是大家用低沉的声音齐声合唱,好像受到音乐之波的触击一般”。 (37) 即使猴类也会用不同的音调来表达强烈的感情——用低音来表达愤怒和急躁——用高音来表达恐惧和痛苦。 (38) 由音乐所激发的或由演说的抑扬声调所表达的情感和观念,从其模糊不清、但深远的性质来考虑,颇似在心理上返归悠久过去时代的情绪和思想。
如果我们可以假设人类的半动物祖先在求偶季节会使用音乐的声调和旋律,那么,有关音乐以及热情讲话的所有上述事实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可以理解的了;其实,所有种类的动物在这个季节不仅会由于爱情而激动,也会由于嫉妒、竞争以及胜利的感情而激动。根据基础深厚的遗传的联想原理,音乐的调子大概会模糊不定地唤起悠久过去时代的强烈情绪。由于我们有各种理由可以设想,有音节的语言是人类所获得的最晚的、肯定也是最高的一种艺术,同时由于产生音乐声调和音乐旋律的本能力量在低等动物的系列中已经得到了发展,所以,如果我们还承认人类的音乐能力是从热情洋溢的讲话发展起来的,那就完全同进化原理背道而驰了。我们必须假定演说的韵律和抑扬声调是来源于以前发展起来的音乐能力。 (39) 这样,我们便能理解音乐、舞蹈、歌唱以及诗歌怎么会是从如此古老时代发展而来的艺术。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如前章所述,我们相信音乐的声调是语言发展的基础之一。 (40)
由于几种四手类动物雄者的发音器官比雌者的发达得多,而且由于一种长臂猿——类人猿的一种——可以发出全部八音度的音调,或者可以说他们会歌唱,所以,人类的祖先,或男或女,或男女双方,在获得用有音节的语言来表达彼此爱慕之情的能力以前,大概会用音乐的声调和韵律来彼此献媚的。关于四手类动物在求偶季节使用声音的情况,我们所知者如此之少,以致没有方法去判断最初获得歌唱习性的,究竟是人类的男性祖先,还是女性祖先。一般都认为妇女的声音比男子的更甜蜜,仅用这一点作为判断的依据,我们可以推论妇女最先获得了音乐的能力,以便吸引男性 (41)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也是发生在很久以前,那时我们的祖先还没有十足地变成人类,而且也没有把妇女仅仅当做有用的奴隶来对待。热情洋溢的演说家、诗人以及音乐家用其变化多端的乐音以及抑扬的声调激起了听众的最强烈情绪,那么,毫无疑问,他所使用的方法同其半动物祖先很久以前在求偶和竞争期间用以激发彼此热情的方法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美对决定人类婚姻的影响
在文明生活中,男人在选择妻子时大部分要受到对方外貌的影响,但决非全部都如此;不过我们所讨论的主要是原始时代,而我们判断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只能去研究现存的半文明民族和未开化民族。如果这样能够阐明,不同种族的男人喜爱具有种种特点的女人,或者不同种族的女人喜爱具有种种特点的男人,那么我们势必去研究这种选择实行许多代以后,按照通行的遗传方式,是否会对这个种族的男女任何一方或双方产生任何可以觉察的效果。
最好先稍微详细地说明一下未开化人对其个人的容貌是非常注意的。 (42) 众所周知,他们热心于装饰;一位英国哲学家甚至主张,衣服最初的制作乃是为了装饰,而不是为了取暖。正如魏采教授所说的,“无论多么贫穷和悲惨的人,都以装饰自己为乐”。下述情况足以表明南美的裸体印第安人在装饰自己方面是很奢侈的:“一个高个子的男人艰苦地工作两周所得才能换得用来涂身的红色‘奇卡’(chica)颜料”。 (43) 驯鹿时期(Reindeer period) (44) 的欧洲古代野蛮人把他们碰巧找到的任何发亮的或特别的物品都带回洞中。今天各地的未开化人还用羽毛、项圈、臂钏、耳环等物来打扮自己。他们用最多种多样的方式来涂饰自己。正如洪堡(Humboldt)所观察的,“如果对涂身的民族就像对着衣的民族那样,进行相同的考察,大概可以发觉最丰富的想象力和最多变的趣味创造了涂饰的流行样式,就像创造了服装的流行样式那样”。
在非洲有一个地方的人把眼睑涂成黑色;另一个地方的人把指甲染为黄色或紫色。还有许多地方的人把头发染上各种颜色。不同地方的人把牙齿染成黑的、红的、蓝的,等等,在马来群岛,人们认为牙齿“如果白的像狗牙那样”简直是可耻。北自北极地区,南至新西兰,没有一处大地方的土人不文身的。古代的犹太人和布立吞人都实行文身。在非洲也有些土人文身,但那里最普通的风俗却是,在身体各部割一些伤口,然后在伤口上擦盐,使成疣状物;苏丹的科尔多凡人(Kordofan)和达尔福尔人(Darfur)把这种疣状物视为“最富魅力的容姿”。在阿拉伯各国,凡双颊“或鬓角没有伤疤的” (45) 不能叫做完全的美人。在南美,正如洪堡所说的,“如果母亲没有使用人工的方法把孩子的小腿按照该地的流行样式改变形状,她就要受到对孩子不关心的责备”。在新世界和旧世界,往昔于婴儿时期就把头骨弄成奇形怪状,现在还有许多地方依然如此,而这种毁形却被视为一种装饰。例如,哥伦比亚(Colombia)的未开化人 (46) 把非常扁平的头视为“美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在各个地方,对头发的梳理都特别注意;有的任其充分生长,以至触及地面,有的梳成“紧密而卷曲的拖巴头,巴布亚人把这种发式视为骄傲和光荣”。 (47) 在北非,“一个男子完成其发式的时间需要8~10年”。另外一些民族却实行剃光头,南美和非洲一些地方的人,甚至把眉毛和睫毛都拔掉。上尼罗河地方的土人把四个门牙敲掉,说,他们不愿同野兽相像。更向南行,巴托卡人(Batokas)只敲掉上边的两个门牙,正如利文斯通所说的 (48) ,这使其面貌可憎,由于其下颚突出之故;但这些人却认为门牙最不雅观,当看到一些欧洲人时,便会喊出,“瞧大牙呀!”酋长塞比图尼(Sebituani)曾试图改变这种风气,但失败了。非洲和马来群岛各地的土人把门牙锉尖,就像锯齿那样,或者在门牙上穿孔,把大头针插入。
在我们来说,赞人之美,首在面貌,未开化人亦复如此,他们的面部首先是毁形的所在。世界所有地方的人都有把鼻隔穿孔的,也有把鼻翼穿孔的,但比较少见;在孔中插入环、棒、羽毛或其他装饰品。各地都有穿耳朵眼的,而且带上相似的装饰品,南美的博托克多人(Botocudos)和伦瓜亚人(Lenguas)的耳朵眼弄得如此之大,以致下耳唇会触及肩部。在北美、南美以及非洲,不是在上嘴唇就是在下嘴唇穿眼,博托克多人在下嘴唇穿的眼如此之大,以致可以容纳一个直径4英寸的木盘。曼特加沙写过一项令人惊奇的记载说:一位南美土人因卖掉他的“特姆比塔”(Tembeta)——一块插入唇孔的着色大木片——而感到羞愧,并且因此引起了对他的嘲笑。中非妇女在下嘴唇穿孔,还要安上一块晶体,在说话时由于舌的转动,这块晶体“也随着颤动,其可笑之状简直无法形容”。拉图卡族(Latooka)的酋长夫人告诉贝克爵士说,“如果贝克夫人把下颚的四个门牙拔掉,并且在下嘴唇装上一个尖而长的发亮晶体,就可大增其美”。 (49) 更向南行,玛卡洛洛族(Makalolo)在上嘴唇穿孔,并且在孔中插入一个大型的金属环和竹环,这种环叫做“陪尔雷”(pelelé)。“这使一位妇女的嘴唇突出于鼻尖以外达2英寸,当这位妇人发笑时,由于肌肉的收缩,竟把上嘴唇抬高到双眼之上。有人问年高德劭的酋长秦苏尔第(Chinsurdi),妇女们为什么戴这些东西?他对这样愚蠢的问题显然感到惊异,答道:那是她唯一所有的美丽东西;男人有胡须,女人却没有。如果不戴上“陪尔雷”,她将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她的嘴像男人,却又没有胡须,她大概完全不是一个女人了。” (50)
身体的任何部分,凡是能够人工变形的,几乎无一幸免。其痛苦程度一定达到顶点,因为有许多这样的手术需费时数年才能完成,所以需要变形的观念一定是迫切的。其动机是各式各样的;男人用颜色涂身恐怕是为了在战斗中令人生畏;某些毁形,或同宗教仪式有关,或作为发育期的标志,或表示男子的地位,或用来区别所属的部落。在未开化人中,相同的毁形样式流行既久 (51) ,因此,无论毁形的最初原因为何,很快它就会作为截然不同的标志而被重视起来。但是,自我欣赏、虚荣心以及企图博得赞美似乎是最普通的动机。关于文身,新西兰的传教士告诉我说,他们曾试图劝说一些少女戒绝此事,她们答道,“我们必须在嘴唇上稍微划上几条线,否则在我们长大以后就会变得十分丑陋”。关于新西兰的男子,一位最有才华的判断者说道,“在脸部刺上优美的花纹,乃表示青年们的大野心,这使他们对妇女有吸引力,还使他们在战斗中显得威风”。 (52) 在前额刺上一颗星,在颊部刺上一个斑点,都被非洲一个地方的妇女视为不可抗拒的魅力。 (53) 在世界大部分地方,但非全部地方,男人的装饰都过于女人,而其装饰方式也往往不同;有时女人几乎一点也不装饰,但这种情形并不多见。由于未开化人的妇女必须从事最大部分的劳动,而且由于不允许她们吃最好的食物,所以不允许她们得到或使用最优良的装饰品,是同人类所特有的自私性相一致的。最后,正如上述所证明的,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在改变头部形状方面,在头发的装饰方面,在用颜色涂身方面,在文身方面,在鼻、唇或耳的穿眼方面,以及在拔除或锉磨牙齿方面等等,世界上相距辽远的地方现在都通行着或长久以来就通行着相同的样式。要说如此众多民族所实行的这等风俗应该是由于来自任何共同起源的传统,都是极其不可能的。这表明人类心理是密切相似的,无论他们属于什么种族都是如此,正如舞蹈、化装跳舞以及绘制粗糙的画是最普遍的习俗一样。
关于未开化人赞赏各式各样的装饰品以及我们视为最难看的毁形,即如上述,现在我们再看一看女人的外貌对男人究竟可以吸引到怎样程度,还有,他们的审美观念是什么。我曾听到有人主张未开化人对他们的妇女的美漠不关心,而仅把她们当做奴隶来评价;因此,最好注意到这一结论同妇女喜欢装饰自己和妇女具有虚荣心是完全不相符的。伯切尔(Burchell) (54) 做过一项有趣的记载:布西(Bush)部落 (55) 的妇女大量使用油脂、红赭石以及闪闪发光的粉,“如果她的丈夫不很富有,将会因此而破产”。她“还表现有很大的虚荣心,而且她的优越意识也是非常明显的”。温伍德·里德先生告诉我说,非洲西海岸的黑人常常讨论他们的妇女的美。有些优秀的观察家们认为可怕的杀婴恶习的部分原因在于妇女期望保持其美貌。 (56) 若干地区的妇女戴咒符或用迷药以博取男子的爱情;布朗先生举出4种植物,是美洲西北部的妇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使用的 (57) 。
一位最优秀的观察家赫尔恩 (58) 多年同美洲的印第安人生活在一起,当他谈到他们的妇女时说道,“如果问北部印第安人何为美女时,他的回答将是:宽而平的脸,小眼,高颊骨,双颊各有3或4条宽阔的黑线,低额,大而宽的下巴,隆大的钩鼻,黄褐色皮肤,而且乳房下垂及腹”。帕拉斯曾经访问过中华帝国的北部,他说,“在那里满洲式的女人是为人所爱好的,这就是说,要有宽脸、高颧骨、很宽的鼻子以及大耳朵”; (59) 沃格特说,“作为中国人和日本人特征的斜眼在画上未免夸大了,其用意似乎在于“同红毛野蛮人的眼睛相比,以表示这种斜眼的美。”正如胡克(Huc)反复提到的,中国内地的人认为欧洲人很丑,因为他们的皮肤是白的,鼻子是高的。按照我们的看法,锡兰土人的鼻子远远不算太高;但“7世纪的中国人已经看惯了蒙古族的扁平面貌,对于锡兰人的高鼻子还是感到惊奇;张把他们描写为鸟喙人身之人。”
芬利森(Finlayson)在详细地描述了交趾支那(Cochin China)人之后说道,他们的圆头和圆脸为其主要特征;接着他说:“女人整个面部的圆形更为显著,她们的脸越圆被认为越美。”暹罗人的鼻子小,鼻孔远离,阔口,厚唇,面庞甚大,颧骨高而阔。所以“我们认为是美人的,在他们看来却是异乡人,这一点也不奇怪。但他们以为他们自己的妇女要比欧洲妇女漂亮得多。” (60)
众所周知,许多霍屯都人(Hottentot)妇女的臀部异常突出;这叫做臀脂过肥(steatopygous);安德鲁·史密斯爵士肯定这一特点必为那里的男子大加赞赏。 (61) 有一次他看到一位被视为美人的妇女,其臀部如此发达,以致坐在平地上而无法起立,她势必拖着自己前进,直至达到一个斜坡时,才能站起。在各个不同的黑人部落中,有些妇女也具有同样特点;按照伯顿(Burton)的说法,索马里男人“选择妻子的方法是,把她们排成一线,挑出其臀部最为突出者”。与此相反的形态乃是黑人最厌恶不过的。 (62)
就肤色来说,芒戈·帕克的白皮肤和高鼻子受到了黑人的嘲笑,他们认为此二者皆不堪入目,而且形态奇异。反之,帕克却称赞他们的皮肤黑得光泽夺目,鼻子扁得秀丽美观,他们说这是“甜言蜜语”,尽管如此,还是给他东西吃。非洲的摩尔族(Moors) (63) 看到帕克的白皮肤,“便皱起眉来,好像不寒而栗。”在非洲东海岸,黑人小孩们看到伯顿(Burton)时便大声喊叫,“看这个白人呀,他难道不像白猿吗?”温伍德·里德先生告诉我说,在非洲西海岸,黑人称赞皮肤越黑越美。按照这位旅行家的意见,他们对白皮肤感到恐怖,这可能部分地由于大多数黑人相信魔鬼和灵魂都是白色的,部分地由于他们认为白皮肤是健康恶劣的标志。
非洲大陆较南部分的班埃族(Banyai)也是黑人,但“大多数这种人的皮肤都是浅咖啡牛奶色的,在那整个区域,的确都把这种肤色视为漂亮美观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种不同的审美标准。卡菲尔人(Kafirs)同黑人大不相同,“除了靠近迪拉果阿湾(Delagoa Bay)的部落以外,他们的皮肤通常都不是黑色的,主要的肤色为黑与红的混合色,最普通的色调为巧克利色。暗色的皮肤由于最普遍,自然得到最高的评价。如果告诉一位卡菲尔人说,他的皮肤是浅色的,或与白人相像,这会被认为大不敬。我听说有一个不幸的男子,由于他的皮肤白皙,以致没有一个女子愿意嫁给他。”祖鲁族(Zulu) (64) 的王有一徽号为“汝乃黑色者”。 (65) 高尔顿先生当同我谈到南非土人时说道,“他们的审美观念和我们的似乎很不相同;因为在某一个部落中,有两位窈窕淑女竟得不到土人的赞美”。
再来看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按照普法伊费尔夫人(Madame Pfeiffer)的材料,在爪哇,黄皮肤的、而不是白皮肤的女子被视为美人。一位男子“以轻蔑的语调谈到英国大使夫人的牙白得像狗牙一样,红润的肤色就像马铃薯花的颜色那样。”我们知道,中国人讨厌我们的白皮肤,北美土人赞美“黄褐色的皮肤”。南美的余拉卡拉族(Yuracaras)居住在东部科迪耶拉山潮湿的、森林茂密的斜坡上,皮肤色甚淡,正如他们语言所表示的其名称那样;尽管如此,他们还认为欧洲妇女远在其本族妇女之下。 (66)
在北美的若干部落中,头发极长;卡特林提出一个奇妙的证据来证明在那里长头发受到何等重视,因为,乌鸦族(Crows)的酋长之所以能够被选举担任此职,是因为在该部落的男子中他的头发最长,即达10英尺7英寸。南美的亚马拉人和基切人同样也有很长的头发;福勃斯告诉我说,长头发之美受到如此高度的评价,以致把它割掉乃是所能给予他的最严厉的惩罚。无论南美或北美的土人有时为了增加头发的长度,要把纤维物质编进去。虽然头发受到这样的珍视,但北美印第安人却把脸上的毛视为“丑陋不堪”,所以每一根脸毛都被仔细地拔掉。整个美洲大陆,北从温哥华岛起,南至火地,都盛行此事。当贝格尔号舰上的火地人约克·明斯特尔(York Minster)被带回他的家乡时,那里的土人告诉他应该把脸上的那几根毛拔掉才好。有一位青年传教士同他们相处不久,他们威胁他,要把他的衣服剥光,拔掉他脸上和身上的毛,然而他的毛决不是很多。这种风气在巴拉圭的印第安人中达到了极端,以致他们把眉毛和睫毛统统拔掉,说,他们不愿同马相似。 (67)
值得注意的是,全世界的种族凡是几乎完全不具有胡须的,都讨厌脸上的和身上的毛,而且尽力把它们拔光。外蒙古人是无发的,众所熟知,他们把所有散生于身体各处的毛都拔掉,波利尼西亚人、某些马来人以及暹罗人都是如此。维奇(Veitch)先生说,所有日本妇女“都对我们的连鬓胡子有反感,认为它很丑,并且叫我们把它刮掉,像日本男子那样。”新西兰人生有卷而短的胡须;然而他们以往都把脸上的毛拔掉。他们有一句谚语:“没有一个女子愿意嫁给多毛的男子”;不过新西兰人的这种风气大概已经改变了,这恐怕是由于欧洲人来到那里之故,有人向我确言,毛利人现在已对胡须加以赞美了。 (68)
相反,胡须长的种族却赞美他们的胡须并对其评价很高;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中,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一个公认的价值;“失去胡须者估价为20先令,而大腿折断者仅定为20先令”。 (69) 在东方,男子用他们的胡须庄严地发誓。我们已经看到,非洲玛卡洛洛(Makalolo)族的酋长秦塞第(Chinsurdi)认为胡须是一种重大的装饰。太平洋的斐济人的胡须“十分茂密,这是他们最大的骄傲”,但邻近的汤加群岛(Tonga Is.)和萨摩亚群岛(Samoa Is.)的居民“却是无须的,并且厌恶毛糙的下巴”。在埃利斯群岛中,只有一个岛上的男人多须,“但对此毫不感到骄傲”。 (70)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类不同种族的审美感是何等广泛地不同。每一个民族如果达到充分进步的程度,都要雕刻他们的神像以及他们的奉若神明的统治者像,毫无疑问,雕刻师们都会尽力表达其美丽与庄严的最高理想。 (71) 根据这一观点,我们最好把希腊的朱庇特(Jupiter)像或阿波罗(Apollo)像同埃及或亚述的雕像加以比较;再把这些雕像同中美败壁残垣上的丑陋浮雕加以比较。
我所遇到的反对这一结论的叙述还不多。温伍德·里德先生有丰富的机会不仅对非洲西海岸的黑人进行过观察,而且对从来没有同欧洲人接触过的非洲腹地的黑人也进行过观察,然而他却相信他们的审美观念同我们的完全一样;罗尔夫斯(Rohlfs)博士写信告诉我说,泡尔奴族(Bornu)以及普洛(Pullo)部落所在地方的情况也是如此。里德先生发现他和黑人对评价当地女子的美有一致的看法,而且他们对欧洲妇女美的欣赏,同我们也是一致的。他们赞美长发,并且用人工方法使其显得茂盛;他们还赞美胡须,虽然自己胡须稀疏。什么样的鼻子最受称赞,里德先生还感到怀疑:他曾听见一个女子说,“我才不要嫁他呢,他没有生鼻子”;这表明很扁平的鼻子是不受欢迎的。然而,我们应该记住,西海岸黑人的平阔的鼻子及其突出的颚部,乃是非洲居民的例外类型。里德先生尽管有以上叙述,他还是承认黑人“不喜欢我们皮肤的颜色;他们以厌恶的神情来看我们的蓝眼睛,他们以为我们的鼻子太长,我们的嘴唇太薄。”仅仅根据对身体美的鉴赏,里德先生并不以为黑人喜欢最美丽的欧洲妇女胜过喜欢一个面貌好看的黑人女子。 (72)
很久以前洪堡 (73) 所主张的原理说,人类赞美而且常常夸大自然给予他的任何特征,这一原理的一般正确性已从许多方面得到阐明。少须的种族把每一根胡须都拔光,而且常常把所有身体上的毛都拔掉,这一情况为上述提供了例证。在古代和近代,许多民族大大改变了其头骨形状;毫无疑问,这种习俗的风行乃是由于要夸大某种自然的和受到赞美的特点。据知,许多美洲印第安人赞美极扁的头,它们扁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在我们看来好像是白痴的头。非洲西北海岸的土人把头部压成尖圆锥形;而且经常把头发束弄在头顶,打成一个结,正如威尔逊(Wilson)博士所说的,这是为了“增加他们所爱好的圆锥形的明显高度”。若开(Arakhan)的居民赞美宽而平的前额,为了“弄成这种形状,他们在新降生的婴儿头上捆扎一块铝板。”相反,斐济群岛的土人却把“宽而十分圆的后头视为至美”。 (74)
对鼻子也像对头骨一样;阿替拉(Attila)时代的古匈奴人惯于用绷带把婴儿的鼻子捆平,“为了夸大一种自然的形态”。塔希提人 (75) 把“高鼻子”视为侮辱的字眼,为了美观,他们把小孩的鼻子和前额压平。苏门答腊的马来人、霍屯都人、某些黑人以及巴西土人也是如此。 (76) 中国人的脚本来异常之小; (77) 众所熟知,中国上层阶级的妇女还要把脚缠得更小。最后,洪堡以为美洲印第安人喜欢用红色涂身是为了夸大其自然的色调;直到最近,欧洲妇女还用胭脂和白色化妆品来增添其自然的鲜艳肤色;不过野蛮民族在涂饰自己时一般是否有这种意图,还是一个疑问。
就我们的服装流行式样而言,我们看到了把每一点弄到极端的完全一样的原理和完全一样的愿望;我们还表现了一样的竞争精神。但未开化人的流行式样远比我们的流行式样持久得多;当他们的身体人工地被改变之后,情况必然如此。上尼罗河的阿拉伯妇女要用三天左右的时间去整理头发;她们决不模仿其他部落,“只是彼此竞争,以求得最新颖的式样。”威尔逊博士在谈到各个美洲种族压平其头骨时,接着说道,“在革命的冲击下,可以改朝换代,消灭更为重要的民族特点,但这种习惯最难除尽而且会长久保存下去。” (78) 同样的原理在育种技术上也会发生作用;于是我们便能理解那些仅仅作为观赏之用的动物和植物的种族为什么会那样异常发达,我在他处已经说明过这一点。 (79) 动物和植物的爱好者永远要求各种性状仅仅稍为增大而已;他们并不赞美中间的标准,他们肯定不希望他们的品种性状发生重大而突然的变化;他们所赞美的仅仅是他们所习见的那些性状,但他们热烈地希望看到各个特征稍微有一点发展。
人类和较低等动物的感觉似乎是这样构成的:它们都适于欣赏鲜艳的颜色和某些形态以及和谐的、有节奏的声音,并把这些称之为美;但为什么会如此,我们还不知道。要说在人类思想中有任何关于人体美的普遍标准,肯定是不正确的。无论如何,某些爱好经过一定时间可能是遗传的,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这种信念;果真如此,各个种族大概都会有自己先天的审美理想标准。有人主张 (80) ,丑恶同低等动物的构造接近,对比较文明的民族来说无疑这是部分正确的,这些民族对理智有高度评价;但这种解释不能完全应用于所有的丑恶形态。各个种族的人都爱好他们所习见的东西;他们不能忍受任何重大的变化;但他们喜欢多样化,而且赞美各个特征不趋于极端, (81) 只有适度的改变。习惯于接近椭圆形脸庞、端庄容貌、鲜艳肤色的男人们,正如我们欧洲人所知道的,称赞非常发达的这些特征。另一方面,习惯于宽脸、高颧骨、矮鼻子、黑皮肤的男人们却称赞强烈显著这等特点。毫无疑问,所有种类的性状都可能过于发达而超出美的范围之外。因此,完全的美意味着许多性状都以一种特殊方式发生改变,这在每一个种族中大概都是奇迹。正如大解剖学家比夏(Bichat)很久以前所说的,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在同一个模型里铸造出来的,大概就没有美人可言了。如果所有妇女都变得像维纳斯(Venus de'Medici)那样美丽,我们将会暂时感到陶醉;但很快我们就要希求变异;一旦我们得到了变异,我们则希求看到某些性状稍微超过现在的普通标准就可以了。
第二十章 人类的第二性征(续)
各个种族的妇女按照不同审美标准连续选择对象的效果——干涉文明民族和野蛮民族进行性选择的诸原因——原始时代有利于性选择的诸条件——人类性选择的作用方式——未开化部落的妇女有选择丈夫的某种权利——体毛的缺如以及胡须的发育——肤色——提要。
我们在前章已经看到,所有野蛮种族都高度重视装饰品、衣服以及外表;并且男子以迥然不同的标准来评定其妇女的美。其次,我们必须研究,那些对各个种族的男子最有魅力的妇女许多世代以来受到这样偏爱、因而受到选择,是否会仅仅改变妇女一方的性状,或改变男女双方的性状。对哺乳动物来说,一般的规律似乎是,所有种类的性状都同等地遗传给雌雄二者;因此,对人类来说,我们可以期待女方或男方通过性选择所获得的任何性状普通都会传递给女性后代和男性后代。如果这样引起了任何变化,几乎肯定的是,不同种族将会有不同的改变,正如各个种族有它自己的审美标准一样。
关于人类,尤其是关于未开化人,仅就身体构造而言,有许多干涉性选择作用的原因。文明人大部分受到妇女精神魅力以及她们的财富所吸引,尤其受到她们社会地位的吸引;因为男子很少同比自己等级低得多的妇女结婚。能够成功地得到比较美丽妇女的男子,并不见得比那些娶平凡妇女为妻的男子有更好的机会留下悠长系列的后裔,但按照长子继承权留下遗产的少数人则除外。关于选择的相反方式,即妇女选择比较富有魅力的男子,虽然文明民族的妇女有选择对象的自由,或者差不多有这种自由(野蛮种族没有这种自由),但她们的选择大部分要受男子的社会地位及其财富的影响;而男子在其生涯中获得这种成功主要决定于他们的智力及其精力,或者依靠其祖先由这等能力所获得的成果。比较详细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正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所说的,“一切私通的最终目的,不论是喜剧的还是悲剧的,都比人类生活的其他目的更为重要。它所实现的就是下一代的构成……这不是任何个人的幸与不幸,而是同未来人类的存亡攸关”。 (82)
然而,有理由可以相信,在文明民族和半文明民族中,性选择对改变某些人的身体构造曾发生过一些影响。许多人相信,我们的贵族(在这个名词下包括长期实行长子继承权的一切富有家庭)许多代以来从所有阶级中选择比较美丽的妇女为妻,按照欧洲人的标准,他们已经变得比中等阶级更为漂亮,我也认为这种说法是合理的;不过就身体的完全发育来说,中等阶级所处的生活条件同贵族是相等的。库克(Cook)说,“在太平洋所有其他岛屿上所看到的贵族那样端正的容貌,在桑威奇群岛上则到处可见”;但这种情形可能主要是由于他们的食物以及生活方式较好的缘故。
古时的旅行家查丁(Chardin)在描写波斯人时说道,“他们的血液由于同格鲁吉亚人(Georgians)和塞卡斯人(Circassians) (83) 不断地通婚,现在已高度改良了,这两个民族的容貌之美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波斯上等人的母亲大都是格鲁吉亚人或塞卡斯人。”接着他又说,他们的美貌“不是从其祖先那里遗传的,因为如果没有上述通婚,作为鞑靼族后裔的上等波斯人大概是极其丑陋的”。 (84) 这里还有一个更为奇妙的例子;在西西里岛的圣朱利亚诺(San-Giuliano)有一座维纳斯·爱里西纳(Venus Erycina)庙,这个庙的尼姑都是从全希腊选出来的美女;但她们并不是纯贞的处女,这个事实是考垂费什 (85) 讲的,他说,圣朱利亚诺的妇女现在以其最美的容貌而驰名该岛,美术家们常求之为模特儿。但是,所有上述事例的证据显然都是可疑的。
下述事例虽然是关于未开化人的,由于它的奇特性也值得在此一提。温伍德·里德先生告诉我说,在非洲西海岸有一个黑人部落叫做乔洛夫(Jollofs),他们“以其一致的美好容貌而闻名”。他的一个朋友问到其中一人:“为什么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这样好看?不仅男子而且妇女都是这样?”乔洛夫部落的人答道,“这很容易解释:长久以来我们有一种风俗,就是把最难看的奴隶挑出来,卖掉他们。”所有未开化人都以女奴为妾,这就无须多说了。这个部落的黑人之所以有如此美好的容貌,应归功于长期不断地汰去那些丑陋的妇女,至于这种做法是对还是错当做别论;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像最初听到时那样令人感到奇怪;因为,我在别处已经阐明 (86) ,黑人对其家养动物选育的重要性是有充分认识的,我根据里德先生的材料不过补充一个有关这个问题的证据而已。
在未开化人中阻止或抑制性选择作用的诸原因
其主要的原因是,第一,实行所谓杂婚(communal marriage),即乱交;第二,实行杀害女婴的后果;第三,早婚;第四,贱视妇女,待之如奴隶。对这四点必须稍作详论。
显然,只要人类或其他任何动物的交配只要完全靠着机会,任何一性都不实行选择,那么就不会有性选择;也不会有某些个体由于在求偶时比其他个体占有优势而对其后代发生作用。现在有人断言,今天还有一些部落实行卢伯克爵士用有礼的言辞所谓的杂婚;这就是说,一个部落的男女彼此相互为夫妻。许多未开化人的混乱生活确是令人吃惊的,但是,在我看来,在我们充分承认他们在任何场合中都实行乱交之前,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尽管如此,所有最密切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 (87) ,而且他们的判断远比我的判断更有价值,都相信杂婚(对这个名词有各种不同解释)乃是全世界所通行的普通而原始的形式,其中包括兄弟姐妹的通婚。已故史密斯爵士曾广泛地在南非各地游历,他通晓那里的以及别处的未开化人的风习,他以最强烈的看法向我表示,没有一个种族把妇女视为公共财产的。我相信他的判断大部分是由婚姻这个名词的含义所决定的。在以下整个讨论中,我是按照博物学者们所说的动物一雌一雄相配的同样意义来使用这个名词的,因此其意义乃是雄者只选一个雌者或为一个雌者所接受,同雌者在繁殖期间或全年生活在一起,并且依照强权律把她据为己有;或者,我是按照博物学者们所说的一雄多雌的物种那样意义来使用这个名词的,其意义乃是一个雄者同若干雌者生活在一起。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就是这种婚姻,因为对性选择的作用来说,这就足够了。但是,我知道上述作者中有些人认为婚姻这一名词意味着受到部落所保护的公认权利。
支持往昔曾经盛行杂婚的间接证据是强有力的,其主要依据为,在同一部落中诸成员之间所使用的亲属关系这一名词意味着和部落的关系,而不是和任何一亲的关系。但是,即使在这里对这个问题扼要地谈一谈,也是范围太大而且太复杂,所以我只能稍微说上几句。在这种婚姻的场合中,或者说在婚姻结合很放纵的场合中,孩子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无法知道的。但如果说孩子同母亲的关系也完全受到忽视,则似乎是难以令人相信的,特别是因为大多数未开化人部落的妇女哺育婴儿的时间要很久。因此,在许多场合中只能通过母系而不是通过父系去追查谱系。但在其他场合中,所使用的名词仅表示和部落的一种关系,甚至不表示和母系的关系。同一部落的具有亲族关系的诸成员共同暴露在所有种类的危险中,由于需要相互的保护和帮助,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可能远比母与子之间的关系更加重要得多,因此就会导致专门使用表示上述那种关系的名词;但莫尔根先生相信这种观点决不够充分。
世界各地所用的亲属关系这一名词,按照莫尔根的意见,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分类的(classificatory)和描述的(descriptive)——我们所使用的为后一种。分类的体系强烈地导致了如下的信念,即杂婚以及其他极端放纵形式的婚姻最初是普遍实行的。但是,就我所能了解的来说,即使以此为根据,也没有必要去相信绝对乱交的实行;我高兴地得知卢伯克爵士也持有这一观点。男和女就像低于人类的许多动物那样,以往在每次生产时都要实行严格的、虽然是暂时的结合,这种场合就像乱交场合那样,在亲属关系这一名词方面会发生差不多一样大的混乱。仅就性选择来说,全部所需要的就是在双亲结合之前实行选择,至于这种结合是终生的或者仅是一个季节的,并无关紧要。
除了由亲属关系这一名词所得到的证据以外,其他方面的推论也可示明以前曾广泛实行过杂婚。卢伯克爵士用共妻曾为原始交配形式这一点,来说明 (88) 异系婚姻(exogamy)这一奇特而广泛实行的习俗——即某一部落的男子从另一不同部落夺取妻子;所以,一个男子除非从一个邻近的敌对部落俘虏到一个妻子外,他决不会得到自己专有的妻子,俘虏到一个妇女后,她自然就会变为他专有的宝贵财产。这样,抢妻之风就兴起了,由于因此可以获得荣誉,这种习俗最终就会普遍实行。按照卢伯克爵士的意见 (89) ,我们由此还能理解“根据古老的观念,一个人没有权利占有属于全部落的东西,由于结婚破坏了部落的习俗,所以有赎罪的必要”。卢伯克爵士进一步列举了大量事实来阐明,在古代极端放荡的妇女非常受到尊敬;正如他说明的,如果我们承认乱交曾是原始的,因而长期受到尊重的部落习俗,上述情况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摩尔根先生、伦南先生以及卢伯克爵士曾对此事进行过最严密的研究,根据这三位作者的几点分歧意见,我们可以推论婚姻约束的发达方式还是一个没有弄清楚的问题,虽然如此,但根据上述证据以及若干其他方面的证据 (90) ,可知婚姻习俗按其字面的任何严格意义来说,似乎可能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且接近乱交的结合,即很放纵的结合在全世界一度是极其普遍的。尽管如此,根据动物界普遍具有的强烈嫉妒感,根据低于人类的动物来类推,特别是根据与人类最接近的动物来类推,我无法相信在人类达到动物界现今等级的不久之前曾经盛行过绝对的乱交。正如我试图阐明的,人类肯定是从某一类猿动物传下来的。关于现存的四手类,仅就所知道的其习性而言,某些物种是一夫一妻的,但每年只有一部分时间同雌者生活在一起:猩猩在这方面似乎提供了一个例子。有几个种类的猿猴,例如某些印度猴和美洲猴都是严格一夫一妻的,而且全年都同妻子生活在一起。另外有些种类是一夫多妻的,例如大猩猩和几个美洲物种就是如此,而且各个家族是彼此单独生活的。即便是这种情形,居住在同一地区的诸家族大概多少还是社会性的;例如,黑猩猩偶尔会合成一大群。再者,还有些物种也是一夫多妻的,不过各有其自己雌者的若干雄者共同生活在一起,例如狒狒的几个物种就是如此。 (91) 我们知道所有雄性四足兽都是嫉妒的,它们许多都有特殊的武器同其竞争对手进行战斗,我们的确可以据此断言,在自然状况下,乱交是极端不可能的。配偶可能并非终生,但可限于每一次生产;然而,如果雄者是最强壮的而且最能保卫或帮助其雌者和幼者,那么它们就能选择更富魅力的雌者,只此一点就足可以进行性选择了。
因此,回顾远古,且由人类现今的社会性习俗来判断,最合理的观点似乎是,人类在原始时期系以小群生活在一起,每个男人只有一个妻子,如果男人是强者,就有几个妻子,于是他要嫉妒地防备所有其他男人来侵犯他的妻子们。或者,他还没有成为社会性动物,就像大猩猩那样,同几个妻子在一起生活;因为所有土人“都承认在一群大猩猩中只能看到一只成年的雄者;当幼小的雄者长大之后,就会发生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最强的雄者把其他雄者杀死或赶跑之后,他就成为这一群的首领”。 (92) 这样被赶跑的幼小雄者便到处漫游,如果最后能够找到一个伴侣,大概就可以防止在同一家族的范围内进行过于密切的近亲交配。
虽然未开化人的生活现在是极端放荡的,虽然杂婚在往昔可能盛行过,但许多部落还是实行某种形式的婚姻,但其性质远比文明民族的婚姻松弛得多。正如刚才所说的,每个部落的首领几乎普遍实行一夫多妻。尽管如此,还是有些部落,虽然位于差不多最低的等级,却实行一夫一妻。锡兰的维达人(Veddahs) (93) 就是如此:据卢伯克爵士说 (94) ,他们有一句谚语:“夫妻不死不分离。”康提人(Kandyan)的一位酋长自然是一夫多妻的,他对只有一个妻子而且不死彼此不分离的极端野蛮风俗非常抱有反感。他说:“这恰好同乌绵猴(Wanderoo monkeys)相似。”现在实行某种婚姻形式(不论是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的未开化人是否从原始时代起就保有这种习俗,还是通过乱交的阶段而又返回某种婚姻形式,我不敢妄自猜测。
杀婴(Infanticide)
实行杀婴现今在全世界很普通,有理由相信在古时实行得更为广泛。 (95) 野蛮人发现同时养活他们自己和儿童是困难的,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的婴儿杀掉。按照阿扎拉的材料,南美的某些部落以前杀死了如此之多的男女婴儿,以致濒于绝灭的境地。据知,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妇女要杀掉四至五个、甚至十个自己的孩儿;埃利斯在那里未曾发现一个妇女没有杀死过自己孩儿的。麦克洛克(MacCulloch)在印度东部边境的一个村庄竟连一个女孩也未曾发现过。凡是盛行杀婴的地方,生存斗争的剧烈程度就要差得多 (96) ,而且部落的所有成员都会有差不多同等良好的机会来养育其幸存下来的少数儿童。在大多数场合中,女婴被杀害的要比男婴为多,因为,对部落来说,男婴显然有较高的价值,在他们长大之后,可以协助保卫部落,而且能够养活自己。但是,正如妇女们自己以及各观察家所列举的,妇女养育小孩的麻烦,由此而失去她们的美貌,以及妇女数量越少越受到重视而且命运越佳,都是杀婴的另外动机。
当妇女由于杀害女婴而少起来的时候,从邻近部落抢妻的风习自然就会兴起。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卢伯克爵士把抢妻的主要原因归于往昔的杂婚,因此男子就会从其他部落抢妻作为他们自己的私有财产。还可以举出另外的原因,如群体很小,在这样场合中可婚嫁的妇女往往是缺乏的。抢妻的习俗在古代最盛行,甚至文明民族的祖先也实行过抢妻,保存下来的许多奇特风俗和仪式明确地阐明了这一点,关于这等风俗和仪式,伦南先生做过有趣的记载。英国举行婚礼时的“伴郎”最初似乎就是新郎抢妻时的主要帮手。现在只要男子还习惯地通过暴力和诡计来获得他们的妻子,他们大概就乐于占有任何妇女,而不去选择那些比较更有魅力的。但是,如果和一个不同部落用物物交换(barter)的办法来获得妻子,就像现今在许多地方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被购买的大概一般就会是比较更有魅力的妇女。然而,任何这种形式的习俗必然要引起部落与部落之间的不断杂交,这就有使同一地方的所有居民保持差不多一致性状的倾向;而且这还会干涉性选择对分化诸部落的力量。
杀害女婴引起妇女的缺少,妇女的缺少又引起一妻多夫的实行,现今在世界的若干地方实行一妻多夫的还很普通,伦南先生相信在往昔几乎全世界都盛行过这种习俗:不过摩尔根先生和卢伯克爵士却对这个结论有所怀疑。 (97) 只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男子被迫娶一个女人,这个部落的所有女人肯定都可以结婚,这样就不会有男子选择魅力较大的女人的事情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妇女无疑会有选择的权力,她们将挑选魅力较大的男子。例如,阿扎拉描述一个瓜纳人(Guana)的妇女在接受一个或更多的丈夫之前多么细心地要求各种特权;因而那里的男子非常注意他们自己的容貌。印度的托达人(Todas)也是如此,他们也实行一妻多夫,女子可以接受或拒绝任何男人。 (98) 在这等场合中,很丑的男子恐怕完全不能得到一个妻子,或者只能在晚年得到一个妻子;不过,比较漂亮的男子虽然能够更成功地得到妻子,但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他们大概不会比同一个妇女的较不漂亮的丈夫们留下更多的后代以遗传他们的美貌。
早期订婚以及奴役妇女
许多未开化人有一种风俗,当女子还在婴儿的时候就实行订婚;这会有效地阻止男女双方按照容貌去实行选择对象。但是,这不能阻止更强有力的男子在以后把魅力较大的妇女从其丈夫那里把她们偷走或抢走;在澳大利亚、美洲以及其他地方都常常发生这种情形。当妇女几乎完全被视为奴隶或牛马时,就像许多未开化人的情形那样,性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产生同样效果。男子在无论什么时候大概都会按照他们的审美标准去挑选最漂亮的奴隶。
由此我们看到了未开化人所盛行的几种风俗,这一定会大大地干涉或完全停止性选择的作用。另一方面,未开化人所处在的生活条件以及他们的某些习俗则有利于自然选择;这同时对性选择也会起作用。据知,未开化人由于反复出现的饥馑而受害严重;他们不会用人为的方法去增加食物;他们对婚姻很少限制 (99) ,一般在幼小时就结婚了。结果他们一定要不时陷入剧烈的生存斗争,只有占有优势的个体才能生存下来。
在很古时期,人类还未达到现在这样阶段以前,他们同现今未开化人所处的许多生活条件都不相同。从低于人类的动物来类推,那时他们实行的不是一夫一妻,就是一夫多妻。最强有力而且最能干的男子最能成功地得到富有魅力的妇女。他们在一般生存斗争中,以及在保卫其妻子儿女不受一切种类的敌害侵袭方面最能获得成功。在这样古远的时期,人类祖先的智力还没有充分进步到可以看到遥远未来的意外事故;他们也不会预见到养育他们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将会使其部落陷入更加剧烈的生存斗争中。他们比今天的未开化人更多地受到其本能、更少地受到其理性的支配。他们在那一时期不会失去所有本能中最强烈的一种,这是一切低于人类的动物所共有的,即,对他们幼儿的爱;因此,他们不会实行杀害女婴。这样,妇女就不至于缺少,一妻多夫就不至于实行;因为,除了妇女的缺少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原因似乎足以打倒天然的和广泛占有优势的嫉妒感以及每个男子各自占有一个女人的欲望。杂婚或接近乱交的习俗大概是自然由一妻多夫发展而来的;虽然最优秀的权威们都相信乱交的习俗在一妻多夫之前。在原始时代不会有早期订婚,因为这含有预见的意思。那时也不会把妇女仅仅视为有用的奴隶或牛马。如果允许男人和女人实行任何选择的话,男女双方差不多都要完全根据外貌而不是根据精神的美或财产,也不是根据社会地位去选择其配偶。所有成年人都会结婚或找到配偶,所有子女只要可能都会受到养育;所以生存斗争就要周期地异常剧烈起来。于是,在这样时期比在较晚时期——人类在智力上进步、但在本能上退步的时期,所有条件更有利于性选择。因此,在产生人类种族之间的差异以及人类和高等四手类之间的差异方面,无论性选择的影响如何,这种影响大概在远古时期比在今天更为强有力,虽然这种影响在今并未完全消失。
人类性选择的作用方式
关于刚才所说的生活在有利条件之下的原始人类,关于那些在今天实行任何婚姻约束的未开化人,性选择或多或少地受到杀害女婴、早期订婚等等干涉,它大概以下述方式发生作用。最强壮的和精力最充沛的男子——那些最能保卫其家族并为其狩猎的男子,那些拥有最好武器和最大产业(如大量的狗或其他动物)的男子——比同一部落中较弱而且较穷的成员,大概会在平均数量上养育更多的儿女。毫无疑问,这样的男子一般还会选择魅力较强的妇女。现今世界上几乎每一个部落的酋长都能得到一个以上的妻子。我听曼特尔(Mantell)先生说,在新西兰,直到最近,几乎每一个漂亮的女子或者将来可成为漂亮的女子,都是某一酋长的“塔布”(tapu) (100) ,汉密尔顿(Hamilton)先生说,卡菲尔人的“酋长一般在许多英里范围内挑选妇女,而且不屈不挠地确立或巩固他们的特权”。 (101) 我们已经看到各个种族都有它自己的美的风格,并且我们知道,如果家养动物、服装、装饰品以及个人容貌稍微超出平均之上,就会受到人们的称赞,这乃是人类的本性。于是,如果上述几项主张得到承认(我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可疑之处),那么,魅力较大的妇女被力量较强的男子所选择,并且平均养育了较多数量的儿童,要说这样经过许多世代之后还没有使这个部落的特性有所改变,大概是费解的事情。
如果家养动物的一个外国品种被输入一处新地方,或者,如果一个本地品种作为实用品种或鉴赏品种而长期受到细心的养育,只要采用比较的方法,就可发现经过数代之后就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发生是由于在一长系列的世代中进行了无意识选择的缘故——这就是最受称赞的个体被保存下来了——饲养者并没有要求或预期这种结果的发生。再者,如果有两位细心的饲养者多年以来都养育同一家族的动物,而且不使它们相互比较或同一个共同标准比较,那么就会出乎饲养者的意外,他们的动物会出现轻微的差异。 (102) 正如冯·纳修西亚斯所恰当表达的那样,每位饲养者已把他自己的心理特性——他自己的爱好和判断刻印在他的动物之上。那么,如果说每一部落中能够养育最多小孩的男子连续选择最受赞美的妇女,而不会产生与上述同样的结果,实无理由可举。这大概就是无意识选择,因为无意识选择会产生一种效果,而同偏爱某些妇女的男子的任何要求或期望无关。
假定有一个部落的成员实行某种形式的婚姻,散布于无人居住的大陆上,他们很快就会分裂成不同的群,彼此被各种壁垒所隔离,由于所有野蛮民族之间的不断战争,这种隔离就更加有效。这些群将处于稍微不同的生活条件和生活习俗之下,他们迟早会在某种微小程度上出现差异。一旦这种情形发生,各个隔离的部落就会形成它自己的稍微不同的审美标准 (103) ;于是,通过比较强有力且居于领导地位的男子挑选他所喜爱的妇女,无意识选择就要发生作用。这样,部落之间的差异在最初虽很轻微,但会逐渐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有所增大。
关于在自然状况下的动物,雄者所固有的许多特性,如力气、特殊武器、勇敢以及好斗性,是依照斗争法则而获得的。人类的半人祖先,就像其亲缘关系相近的动物——四手类那样,几乎肯定也是这样变异的;由于未开化人现在依然为了占有妇女而进行争斗,一种相似的选择过程大概或多或少地一直延续到今天。低等动物雄者所固有的其他特性,如鲜明的体色以及各种装饰物,乃是由于雌者挑选她们所喜爱的魅力较大的雄者而获得的。然而也有例外的情形,即雄者选择雌者,而不是被雌者所选择。根据雌者比雄者的装饰更为高度——她们的装饰特性完全地或者主要地传递给雌性后代,我们便可认识上述那种情形。在人类所属的灵长目中有一个这样的例子,那就是恒河猴。
男人在肉体和精神方面都比女人更加强有力,而且在未开化状态下男人对女人的束缚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动物的雄者;所以他应该得到选择的权力,就不足为奇了。各地的妇女都会意识到其美貌的价值,当有办法的时候,她们比男人更喜欢用所有种类的装饰物来打扮自己。她们借用雄鸟的羽毛来打扮自己,这是大自然给予雄者的装饰,以便用来取悦于雌者。由于妇女因其美貌而长期受到选择,因此她们的某些连续变异应该完全传递给同一性别,就没有什么奇怪了;结果是,她们把美貌传递给女性后代的,在程度上应稍高于传递给男性后代的,按照一般的意见,她们这样就会变得比男子更美。然而,妇女肯定要把大多数特性传递给男女后代,其中包括某种美貌在内;所以各个种族的男子按照他们的审美标准,挑选他们所喜爱的魅力较大的妇女,将有助于按照同样方式来改变这个种族的男女。
关于性选择的另一种方式(低等动物实行这种方式的要多得多),即,雌者选择雄者,而且只接受那些最能使她们激动或魅力最强的雄者,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性选择的方式以前曾对我们的祖先发生过作用。人类的胡须恐怕还有某些其他性状,多半是从一个古代祖先那里遗传来的,这个祖先由此得到了装饰。但是,这种选择方式可能是在较晚时期偶尔实行的;因为在极端野蛮的部落中,妇女在选择、拒绝和引诱其情人方面,以及此后在更换其丈夫方面,所拥有的权利之大可能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之外。这一点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所以我将详细地举出我所能搜集到的这类证据。
赫恩描述过美洲近北极地方有一个部落的妇女,如何屡屡从她的丈夫那里跑掉去同情人相聚;按照阿扎拉的材料,南美的卡鲁阿人(Charruas) (104) 可以完全自由地离婚。阿比朋人(Abipones) (105) 的男子当选中一个妻子时要同她的父母商定她的身价。但是,“屡屡发生的是,这个女子会取消双亲和新郎达成的协议,顽固地拒绝这个婚事”。她常常跑走,隐匿起来,以逃避新郎。马斯特斯(Musters)上尉曾同巴塔戈尼亚人一齐生活过,他说,他们的婚姻永远是根据个人意愿来决定的;“如果双亲所许的婚事同女儿的意愿相违背,她就会加以拒绝,决不被迫去服从”。在火地岛,一个青年男子先要给女方的父母做些事情以求得他们的同意,这时他就试着把女子带走;“但如果她不愿意,她就躲藏在森林之中,直至求婚者倦于寻找而后已;不过这种情形很少发生”。在斐济群岛,男子真正地或假装地用武力去占有他要使其作为妻子的妇女;但是“当到达这位劫持者的家中时,如果她不赞同结婚,她即跑到能够保护她的某位人士那里;如果她满意了,就可立刻成婚”。关于蒙古人,新娘和新郎按照规定要进行一场竞跑,而且新娘公平地先起跑;“克拉克肯定地说道,除非她对追逐者有所爱好,就不会发生女子被捉到的情况”。在马来群岛的野蛮部落中,也有竞跑求婚的;卢伯克爵士说,根据包林(Bourien)的记载,“‘竞跑并非迅速者获胜,战斗也并非强者获胜’,胜利归于能够取悦新娘的运气好的青年”。亚洲东北部的高拉克人(Koraks)盛行一种相似的风俗,其结果亦相同。
再来看看非洲:卡菲尔人有买妻的习俗,如果女子不愿接受父亲为其择定的丈夫,就要受到父亲的毒打;但是,根据斯库特尔牧师所举出的许多事实来看,那里的女子显然还有相当的选择权利。这样,很丑的男人,虽然富有,据知也找不到妻子。当女子同意订婚之前,她要迫使男子先从前方、然后从后方来显示自己,而且还要他们“表演步态”。据知她们也向男子求婚,而且同心爱的情人一齐逃走的并不罕见。再者,莱斯利先生非常了解卡菲尔人的情况,他说:“如果想象那里的父亲在出卖女儿时,其方式就像处理一头母牛那样,而且拥有同样的权威,那将是一个错误。”
在衰退的南非布西门人(Bushman)中,“当一个女子达到成年而尚未订婚时(这并不常见),她的情人必须取得她的同意,也要取得她父母的同意,才能成婚。” (106) 温伍德·里德先生为我做过有关西非黑人的调查,他告诉我说:“那里的妇女得到她们所愿嫁给的丈夫并不困难,至少比较聪明的沛根部落(Pagan tribes)是如此,但向男子求婚被看做是不符合女人身份的。她们完全能够恋爱,显示温柔、热烈而忠实情感。”关于这种情形,还可举出另外一些例子。
由此可以看出,并非像常常设想的那样,未开化人的妇女在婚姻方面是完全处于屈从地位的。无论在婚前或婚后,她们可以诱惑所喜爱的男人,而且有时可以拒绝她们讨厌的男人。妇女的这种选择如果稳定地朝着任何一个方向发生作用,最终就会影响这个部落的特征;因为妇女不仅按照她们的审美标准一般选择漂亮的男人,而且选择那些同时最能保卫和养活她们的男人。这样禀赋良好的配偶比禀赋较差的,通常能养育较多数量的后代。如果男女双方都实行这种选择,显然会以更加显著的方式产生同样结果;这就是说,魅力较大的而且力量较强的男人喜爱魅力较大的女人,而且被后者所喜爱。这种双重的选择方式似乎实际发生过,尤其是在我们悠久历史的最古时期更加如此。
现在我们稍微仔细地考察一下区分若干人类种族以及区分人类种族和较低等动物的某些特性,即:体毛的多少缺如以及皮肤的颜色。
关于不同种族在面貌和头骨形状方面的巨大多样性,我们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因为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看到对这些方面的审美标准是何等不同。因此,这等特性大概会受到性选择的作用;但我们无法判断这种作用主要来自男方,抑或来自女方。人类的音乐才能也同样被讨论过了。
体毛的缺如以及面毛和头发的发育
根据人类胎儿的柔毛、即胎毛,并且根据在成熟期散布于身体各部的残迹毛,我们可以推论人类是从生下来就有毛而且终生如是的某种动物传下来的。毛的消失对人类来说是不方便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甚至在炎热气候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因为人类这样就会暴露在太阳的灼热以及骤然寒冷之中,在多雨的天气里更加如此。正如华莱士先生所提出的,所有地方的土人都喜欢用某种轻的覆盖物把裸露的背部和肩部保护起来。没有人设想皮肤的无毛对人类有任何直接的利益;因此,人类体毛的消失不会是通过自然选择而实现的。 (107) 正如以前一章所阐明的,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阐明这是由于气候的直接作用而发生的,而且这也不是相关发育的结果。
体毛的缺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第二性征;因为世界一切地方的妇女都比男子少毛。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性状乃是通过性选择获得的。我们知道有几个猴的物种,其面部无毛,另有几个物种的臀部的大片表面无毛;我们可以稳妥地把这一点归因于性选择,因为这等表面不仅颜色鲜明,而且像雄西非山魈和雌恒河猴那样,某一性别的这种颜色比另一性别的要鲜明得多,特别在繁殖期间尤其如此。巴特利特先生告诉我说,当这等动物逐渐到达成熟时,这等无毛表面在同身体大小的相比下要变得大些。然而,毛的消除似乎并非为了裸的缘故,而是为了可以更加充分地显示那一块皮肤的颜色。再者,有许多鸟类,其头部和颈部的羽毛好像通过性选择被拔掉了,借以表现其颜色鲜明的皮肤。
由于妇女的体毛比男子的为少,而且由于这一性状是一切种族所共有的,我们可以断言,最初失去毛的乃是我们半人的女祖先,并且这在若干种族从一个共同祖先分歧出来之前的极其遥远的古代就发生了。当我们女祖先逐渐获得这种新的无毛性状时,她们一定把这种性状几乎同等地传递给幼小的男女后代,所以这种性状的传递,就像许多哺乳类和鸟类的装饰物那样,既不受性别的限制,也不受年龄的限制。我们类猿的祖先把毛的局部消失视为一种装饰,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所有种类的动物把大量的奇异性状视为装饰,而且结果是通过性选择得到了这等性状。同时这样会获得稍微有害的性状也不奇怪;因为我们知道某些鸟类的羽饰以及某些公鹿的角就是如此。
在以前一章中曾提到,有些类人猿的雌者,其体部底面的毛比雄者的略少;这或是毛的消失过程的开始。关于通过性选择来完成这一过程,我们最好记住新西兰的一句谚语,“妇女不嫁多毛的男子”。凡是看过暹罗多毛家庭相片的人,都会承认妇女的异常多毛真是丑得滑稽。暹罗皇帝势必用钱来利诱一个男子去娶一个家族的多毛长女;而且她把这一性状传递给了其男女双方的幼年后代。 (108)
有些种族远比其他种族的毛多,尤其男人更加如此;但千万不要假设,比较毛多的种族如欧洲人比毛较少的种族如外蒙古人或美洲印第安人更加完全地保持了他们的原始状态。更加可能的是,前者的多毛乃是由于局部的返祖;因为在某一既往时期长久遗传的性状永远是容易返祖的。我们已经看到,白痴常常是多毛的,而且它们在其他性状上总是容易返归低等动物的模式。容冷的气候在导致这种返祖方面好像没有什么影响;但在美国生活了几代的黑人 (109) 以及在日本列岛的北部诸岛居住的虾夷人可能是例外。不过遗传法则是如此复杂,以致我们很少能理解其作用。如果某些种族的较强多毛性是返祖的结果,不受任何选择形式的抑制,那么它的极端变异性即使在同一种族的范围内也就不值得加以注意了。 (110)
关于人类的胡须,如果求助于我们的最好向导——四手类,我们就可看到许多物种雌雄二者的胡须是同等发达的,但有些物种仅限于雄者有胡须,或者其胡须比雌者的更为发达。根据这一事实,并且根据许多猴类头毛的奇特排列及其鲜明颜色,正如以前所解释的,非常可能是雄者最先通过性选择获得了它们的胡须作为装饰,并在大多数场合中把胡须同等地或差不多同等地传递给男女后代。根据埃舍里希特(Eschricht)的材料 (111) ,我们知道人类的男女胎儿在面部、特别在嘴的周围生有很多毛;这暗示着我们是从雌雄双方均有胡须的祖先传下来的。因此,最初看来,男人可能从很古时期以来就有胡须,而且女人在其体毛差不多完全失去的同时也失去了其胡须。甚至我们胡须的颜色似乎也是由类猿祖先遗传下来的;因为,如果头须和胡须的色调有任何差异的话,在所有猴类以及人类中总是胡须的颜色较淡。在四手类中,如果雄者的胡须大于雌者的,前者的胡须只是在成熟期才充分发育,恰好人类亦复如此;人类所保持的可能只是较晚的发育阶段。与人类从古代就保持胡须这一观点相反的是在不同种族、甚至在同一种族中胡须巨大变异性的事实;因为这暗示着返祖——长久亡失的性状在重现时很容易变异。
我们千万不要忽视性选择在较晚时期所起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关于未开化人,无须种族的男子把胡须视为可憎,煞费苦心地把脸上每一根毛都拔掉,而有须种族的男子对他的胡须则感到最大骄傲。毫无疑问,妇女也有这种感情,倘如此,则性选择在较晚时期几乎不会不发生一些作用的。长期不断的拔毛习惯可能产生遗传的效果。布朗-塞奎(Brown-Séquard)博士已经阐明,以一种特殊方法对某些动物实行手术,它们的后代会受到影响。还可举出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切断手术的遗传效果;不过沙尔文(Salvin)先生 (112) 最近确定的一个事实同现在这个问题有更直接的关系;因为他曾阐明,摩特鸟习惯地把两支中央尾羽的羽支咬掉,于是这两支尾羽的羽支天然地缩小了。 (113) 至于许多种族的头发怎样发达到现在这样的巨大长度,还难以形成任何判断。埃舍里希特说 (114) ,人类胎儿的面毛在第五个月的时候比头发长;这表明我们的半人祖先不具长发,所以长发一定是后来获得的。不同种族的头发长度有巨大差异,这同样也表明了上述情况;黑人的头发犹如卷毛的绒毯;欧洲人的头发很长,而美洲土人的头发触及地面者并不罕见。瘦猴属一些物种的头发长度中等,这大概作为装饰之用,而且是通过性选择获得的。同样的观点恐怕可以引申到人类,因为我们知道,无论现在和以往,长发都受到特别赞美,在几乎每一位诗人的作品中都可能看到这一点,圣保罗说:“妇人有长发,乃彼之荣耀”;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在北美,一个人被选为酋长完全是因为他有长发的缘故。
皮肤的颜色
关于人类的皮肤颜色通过性选择发生变异的最好证据尚不多见;因为在大多数种族中男女在这方面没有差异,在另外一些种族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仅有轻微的差异。然而,我们根据已经举出的许多事实得知,所有种族的男子都把皮肤的颜色视为美的高度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它很可能是一种通过性选择而发生变异的性状,许多低于人类的动物所发生的大量事例正是如此。如果说黑人的乌黑发亮的肤色大概是通过性选择获得的,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奇怪的设想;但这一观点得到了各种类似情况的支持,而且我们知道黑人赞美他们自己的肤色。关于哺乳动物,如果雌雄在颜色方面有所差别的话,往往雄者是黑的,或者比雌者的颜色暗得多;这种颜色或任何其他颜色究竟向雌雄双方传递或只向一方传递,仅仅决定于遗传形式。僧面猴(Pithecia Satanas)具有乌黑发亮的皮肤、滚滚转动的白色眼球以及头顶的分开的头发,俨然是黑人的雏形,其状显得滑稽。
各种猴的面部颜色的差别比人类各个种族的这种差别大得多;我们有某种理由可以相信,它们皮肤的红色、青色、橙色、接近白色和黑色,甚至雌雄二者都呈现这等颜色,都是通过性选择获得的,此外,皮毛的鲜明颜色以及头部的装饰性簇毛也是如此。由于生长期间的发育顺序一般表明一个物种的诸性状在以前各代中发育和变异的顺序;而且由于人类各个种族新生婴儿虽然完全无毛,他们的肤色差别并不像成年人那样大,所以我们还有某种微小的证据可以证明不同种族的肤色是在毛的消失之后获得的,而毛的消失一定是在人类历史的很古时期。
提要
我们可以断言,同女人相比,男人的体格、力气、勇气、好斗性以及精力均较大,这些都是在原始时代获得的,而且此后主要通过男人为了占有女人所进行的斗争而增大了。男子较强的智力和发明力大概是由于自然选择的作用,而且结合着习性的遗传效果,因为最有才干的男子们将会最成功地保卫自己以及妻子儿女。就我们对这个极其错综复杂问题所能作出的判断来说,看来人类的男性似猿祖先获得他们的胡须似乎是作为一种装饰以魅惑或刺激女人,而且这种性状只向男性后代传递。女人最初失去她们的体毛显然也是作为一种性的装饰;不过她们把这种性状几乎同等地传递给男女双方。女人在其他方面为了同一目的和按照同一方式发生变异并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女人获得了比较甜蜜的声音,而且比男人漂亮。
值得注意的是,就人类来说,在许多方面适于性选择的条件,在很古时期——当人类刚刚达到人的状态时——比在较晚时期更加有利得多。正如我们可以稳妥地作出的结论,这是因为那时的人类更多受到本能的情欲所支配,较少受到预见或理智所指引。他将以嫉妒之心去监视他的妻子或妻子们。他不实行杀婴;不把他的妻子们看做有用的奴隶;也不在婴儿时期就实行订婚。因此,我们可以推论,仅就性选择来说,人类种族的分化主要是在远古时代;这个结论对下述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提供了说明,即:在有史的极古时代人类种族之间的差异已经差不多或者完全和今天一样了。
关于性选择在人类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已在这里摆出了一些观点,不过这些观点还缺少科学的精确性。凡不承认在低于人类的动物场合中也有这种作用的人将会无视我在本书第三部分中所写的有关人类的一切。我们无法肯定地说,这一性状如此变异了,而那一性状并未如此变异;然而已经阐明,人类种族彼此之间以及和其亲缘关系最近的动物之间在某些性状上有所差别,而这些性状就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性来说并无用处,而且极其可能是通过性选择发生变异的。我们已经看到,各个未开化部落的人们都赞美其自己的特征——头和脸的形状,颧骨的方形,鼻的隆起或低平,皮肤的颜色,头发的长度,面毛和体毛的缺如,以及大胡子等等。因此,这等性状以及其他这样的性状都是缓慢而逐渐扩大的,它们的扩大乃是由于各个部落中比较强有力而且比较有才干的男子成功地养育了最大数量的这等后代,并且选择了特征最强烈的,因而魅力最大的妇女作为他们的妻子。在我来说,我可断言,导致人类种族之间在外貌上有所差别的所有原因,以及人类和低于人类的动物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差别的所有原因,其中最有效的乃是性选择。
第二十一章 全书提要和结论
人类起源于某一较低类型的主要结论——发展的方式——人类的系谱——智能和道德官能——性选择——结束语
简短的提要足可以引起读者们对本书一些比较突出之点进行回忆。在已经提出的诸观点中,有许多是高度推测的,无疑还有些将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我在每一个场合中都举出了导致我为什么主张这一观点而不主张另一观点的理由。关于进化原理对人类自然史中的一些比较复杂问题究竟能解释到怎样程度,似乎值得试着在这里讨论一下。虚假的事实对科学进步的危害极大,因为它们往往持续长久;但受到某种证据支持的虚假观点则为害很小,因为每一个人都乐于证明它的虚假性,这是有益的:当这样做之后,则通向错误的那一条路被关闭了,而通向真理的那一条路便往往同时敞开了。
这里所得到的主要结论是,人类起源于某种体制较低的类型,这一结论现在已得到了许多有正确判断能力的博物学者们的支持。这一结论的根据决不会动摇,因为人类和较低等动物之间在胚胎发育方面的密切相似,以及它们在构造和体质——无论是高度重要的,还是最不重要的——的无数之点上的密切相似,还有,人类所保持的残迹(退化)器官,他们不时发生畸形返祖的倾向,都是一些无可争辩的事实。这等事实久已为人所知,但直到最近,它们对人类的起源并没有提供什么说明。现在当使用我们对整个生物界的知识来进行观察的时候,这等事实的意义就清清楚楚了。如果把这等事实同其他事实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例如,同一类群的诸成员之间的相互亲缘关系,他们在过去和现在的地理分布,以及他们在地质上的演替,那么,伟大的进化原理就可以明确而坚定地站得住了。如果以为所有这等事实都被说错了,那是不可令人相信的。一个人如果不像未开化人那样满足于把自然现象看做是不相联系的,他就不会再相信人类是分别创造作用的产物。他将被迫承认,人的胚胎同狗的胚胎密切相似——人的头骨、四肢以及整个构造同其他哺乳动物这等部分的设计是相同的,不管这等部分的用途如何,都是如此——不时重现各种构造,例如人类不正常具有的、而为四手类所共有的几块肌肉的重现——所有这些点都以最明确的方式引出了下述结论,即: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乃是一个共同祖先的同系后裔。
我们已经看到,人类在身体的一切部分以及在心理官能上不断地表现个体差异。这等差异或变异就像在低于人类的动物场合中那样,似乎都是从相同的一般原因诱发的,而且都是服从相同的法则。相似的遗传法则适用于上述双方。人类增加速度有大于食物增加速度的倾向;结果他们就要不时地陷入剧烈生存斗争之中,而自然选择就会在它所及的范围内发生作用。对自然选择的工作来说,连续而强烈显著的相似变异决不是必需的;个体中轻微而彷徨的变异就足够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设想同一物种体制的一切部分有同样程度地发生变异的倾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身体各部分长期连续的使用或不使用的遗传效果将会按照自然选择的同一方向发挥重大作用。已往具有重要性的变异,现在虽然没有任何特殊用途,还是长久遗传的。当某一部分发生变异时,其他一些部分就会按照相关原理发生变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奇妙的相关畸形来说明。多少可以归因于周围生活条件如丰富食物、炎热或潮湿的直接而一定的作用;最后,生理上不很重要的许多性状,以及生理上确很重要的一些性状,都是通过性选择获得的。
毫无疑问,人类以及其他各种动物还具有这样一些构造,按照我们有限的知识来看,它们无论现在或以往对一般的生活条件或两性关系都没有任何用处。这等构造都不能由任何形式的选择或身体各部分使用和不使用的遗传效果得到解释。我们知道,家养的动物和植物偶然在构造上出现许多奇异而强烈显著的特性,如果它们的未知原因更加一致地发生作用,这等特性大概会为这个物种的一切个体所共有。关于这等偶然变异的原因,我们可以希望今后会多少有所理解,尤其是通过对畸形的研究,更可以如此:因此,实验工作者们的劳动,如卡米尔·达列斯特(M.Camille Dareste)的,将来都大有希望。总之,我们所能说的仅是,导致各个轻微变异和各个畸形的原因,由于生物体质的要远远超过由于周围条件的性质;虽然变化了的新条件在激发许多种类的生物变化上肯定会起重要的作用。
通过上述方法,恐怕还要借助于其他未发现的原因,人类才会上升到今天这样的地位。但是,自从人类达到人的等级以后,人类就分歧为不同的种族(races),更适当地可以称为“亚种”(sub species)。有些种族,如黑人和欧洲人,如此截然不同,以致如果把他们的标本带给一个博物学者去看而不进一步给予说明,毫无疑问这位博物学者将把他们视为十全十美的真正物种。尽管如此,所有种族在非常多的不重要细微构造上以及在非常多的心理特性上还是彼此一致的,以致只有根据从一个共同祖先遗传的道理,这等构造和特性才能得到解释;而一个具有这样特征的祖先大概值得列入人的等级的。
千万不要设想,每一种族同其他种族的歧异,以及所有种族同一个共同祖先的歧异,都可以向后追溯到任何一对祖先配偶。反之,在变异过程的每一阶段,无论在什么方面能够更好地适应它们生活条件的所有个体,虽然其程度有所不同,都比适应较差的个体能够存活下来的数量较大。人类并非有意识地选择家畜的特殊个体,而是用所有优秀的个体进行繁育,遗弃那些低劣者,人类的变异过程也与此相像。这样,人类就会缓慢而稳定地改变其种族,并且无意识地形成一个新族系。至于不是由于选择获得的变异,而是由于有机体性质和周围条件作用或生活习性变化获得的变异,没有任何一对配偶的改变大于在同一地方居住的其他配偶的改变,因为所有个体通过自由杂交将不断地混合在一起。
根据人类的胚胎构造——人类和低于人类的动物的同源器官——人类所保留的残迹(退化)器官——返祖的倾向,我们便能想象到我们早期祖先的往昔状态;并且能够大致地把他们放在动物系列中的适当地位。于是,我们可以知道人类起源于一个身体多毛的、有尾的四足兽,大概具有树栖的习性,是居住在旧世界中的。如果一位博物学者对这种动物加以检查,大概会把它分类在四手目中,其确切程度正如把旧世界和新世界猴类的更古祖先分类在这一目中一样。四手目和所有其他高等哺乳动物大概来自一种古代的有袋动物,有袋动物经过一长系列的形态分歧,来自某一与两栖类相似的动物,而这种动物又来自某一与鱼类相似的动物。我们可以看到,在朦胧的过去,所有脊椎动物的早期祖先一定是一种水生动物,有鳃,雌雄同体,而且其身体的最重要器官(如脑和心脏)是不完全的或是完全不发达的。这种动物同现存海鞘类(Ascidians)的相像,似乎胜于同任何其他已知类型的相像。
当我们作出有关人类起源的这样结论之后,最大的难题便是人类的智力和道德倾向何以达到如此高的标准。不过,凡是承认进化原理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看到,高等动物同人类的心理能力,虽然程度非常不同,但性质无异,是能够进步的。例如,在某一高等猿类和某一鱼类之间或一种蚂蚁和介壳虫(Scale-insect)之间心理能力的间隔是巨大的;然而它们的发展并没有任何特别困难;因为,就我们的家养动物来说,心理官能肯定是可变异的,而且这种变异是遗传的。谁也不会怀疑心理能力对自然状况下的动物具有极度重要性。因此,外界条件对心理能力通过自然选择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的。同样的结论可以引申到人类;智力对人类一定是高度重要的,甚至在很古时代也是如此,它能使人类发明和使用语言,制造武器、器具、陷阱等等,在其社会的习性帮助下,人类很久以前就成为一切生物的最高支配者。
一旦半技术和半本能的语言被运用之后,智力的发展紧跟着就阔步前进了;因为,语言的连续使用将对脑发生作用,并产生一种遗传效果;反过来这又会对语言的进步发生作用。昌西·赖特(Chauncey Wright)说得好, (115) 同低于人类的动物相比,人脑按其身体的比例来说是大的,这种情形主要应归因于某种简单形式的语言之早期使用——语言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机器,它能给各种物体和各种性质做上记号,并引起思想的连锁;单凭感觉的印象,思想连锁决不能发生,即使发生也不能进行到底。人类的较高智力,如推理(ratiocination)、抽象作用(abstraction)、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等等,大概都是因其他心理官能的不断改进和运用而产生的。
道德属性(moral qualities)的发展是一个更加有趣的问题。其基础建筑在社会本能之上,在社会的本能这一名词中含有家庭纽带的意义。这等本能是高度复杂的,在低于人类的动物场合中,有进行某些一定活动的特别倾向;但其更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是爱,以及明确的同情感。赋有社会本能的动物乐于彼此合群,彼此警告危险,以及用许多方法彼此互保和互助。这等本能并不扩展到同一物种的一切个体,而只扩展到同一群落的那些个体。由于这等本能对物种高度有利,所以它们完全可能是通过自然选择而被获得的。
有道德的生物能够反省其过去的行为和动机——能够赞同这个、反对那个;人之所以值得称为人者,即在于人类和低于人类的动物之间的这种最大区别。但是,我曾在第四章试图阐明,道德观念(moral sense)起源于:第一,社会本能的持续和恒久存在;第二,人类懂得同群诸人的称赞和非难;第三,人类心理官能的高度活动以及对过去的印象鲜明,而且人类同低于人类的动物的区别即在于后面这几点。由于这种精神状态,人类不可避免地要瞻前顾后,并把过去的印象加以比较。因此,当某种暂时的欲望和激情抑制了其社会本能之后,一个人就要反省对这种过去冲动的现已减弱的印象,并把这等印象同恒久存在的社会本能加以比较;于是他感到不满,这是所有不满的本能留给他的,所以他决定将来不再有这样行为——这就叫做良知。任何一种本能如果永久地强于另一种本能,而且持续较长,这种本能就会引起我们用语言来表达的“应该遵从它”的那种感情。一只向导狗如果能够反省其过去行为,它大概会对自己说,我应该(恰如我们说给它的那样)示明那只山兔的所在,而不应屈从于一时的诱惑去猎捕它。
社会性的动物局部地受到一种愿望所驱使,这就是以一般方式对其同群成员进行帮助的愿望,但更为普通的是履行某些一定的行为。人类同样也被帮助其同伙的一般愿望所驱使;但只有很少特别为此的本能,或者根本没有这种本能。人类和低于人类的动物之间的区别还在于前者有用语言表达自己愿望的能力,这就成为需要帮助和给予帮助的引导。人类给予帮助的动机同样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它已不再单纯是盲目的本能冲动了,而是大大地受到其同伙的称赞或谴责的影响。对称赞和谴责的鉴别以及称赞和谴责的给予都是建立在同情之上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情绪是社会本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同情虽然是作为一种本能被获得的,还是由于使用或习性而大大被加强了。由于所有的人都希望有自己的幸福,所以对行为和动机所给予的称赞或谴责都是以它们能否导致幸福这一目的来决定的,由于幸福是公共利益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最大幸福原理就会作为是非的基本稳妥标准而间接地发生作用。由于推理能力的进展以及经验的获得,就会察觉到某种一系列行为对个人性格以及公共利益所发生的更为遥远的作用;于是自尊的美德就会放在舆论范围之中而受到称赞,反是者就要受到谴责。但就文明较低的诸民族来说,理性常常出现错误,许多坏风俗和愚蠢的迷信也会放在同样的舆论范围之中,于是这等风俗和迷信就作为高度的美德而受到尊重,违反它们就罪莫大焉。
一般认为道德官能比智力具有更高的价值,这种看法是正当的。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在鲜明地回忆过去的印象时,心理活动乃是良知的根本的、虽是第二性的基础。这就提供了一个最强有力的论据,表明每一个人的智能都是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受到教育和激发的。毫无疑问,一个心理迟钝的人,如果他的社会感情和同情心十分发达的话,也会被引导有良好的行为,而且可以有相当敏锐的良知。但是,无论什么情况,只要能使想象更为鲜明并使回忆和比较过去印象的习性加强,就会使良知更加敏锐,甚至多少可以对衰弱的社会感情和同情心有所补偿。
人类的道德本性之所以能够达到今天这样的标准,部分是由于推理能力的进步,因而引起公正舆论的进步,特别是由于通过习性、范例、教育以及反省,他的同情心变得更加敏感而且广泛普及。美德的倾向经过长期实践之后并不是不可能遗传的。就文明较高的种族来说,笃信一位无所不察的神的存在,对道德的向上具有重大影响。虽然很少人能够逃脱同伙褒贬的影响,但最后人类还是不会以褒贬作为他的唯一指针,而是受到理性支配的习惯信仰为他提供了最稳妥的准则。于是他的良知便成为最高的判断者和告诫者。尽管如此,道德观念的最初基础或起源还是在于包括同情心在内的社会本能;这等本能就像在低于人类的动物场合中那样,最初无疑是通过自然选择而被获得的。
常常有人提出,信仰上帝不仅是人类和低于人类的动物之间的最大区别,而且是最完全的区别。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不可能主张人类的这种信仰是天生的或本能的。另一方面,对无所不在的精灵力量的信仰似乎是普遍的;显然这是来自人类理性的相当进步,而且是来自人类想象、好奇和惊异的官能的更大进步。我知道这种假定的对上帝的本能信仰曾被许多人用做一个论据来表明上帝的存在。但以此作为论据未免轻率,倘如此,我们就要被迫去相信许多仅仅比人类力量稍大的残忍而恶毒的精灵的存在;因为对精灵的信仰远比对慈悲的神的信仰更为普遍。直到人类经过长期不断的文化陶冶而被提高其地位之后,人类的思想中似乎才发生了一个万能而慈悲的造物主的观念。
一个人如果相信人类是从某一低等生物类型发展而来的,他自然要问这种信念同灵魂不灭的信念何以相容。正如卢伯克爵士已经阐明的,人类的野蛮种族并不具有明显的这种信念;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从未开化人原始信仰得出的那些论据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或者根本没有用处。在从一个微小胚泡(germinal vesicle)的痕迹开始的个体发展过程中,不可能决定在什么确定的时期人类才变为一种不朽的生物,对此很少人感到不安;而在逐渐上升的生物等级中、即在系统发展的过程中也不可能决定这样的时期,对此就更没有感到不安的理由了。 (116)
我知道,本书所得出的结论将会被某些人斥为非常反对宗教的;但斥责者不得不阐明,以人类作为一个独特物种通过变异和自然选择的法则发生于某一较低类型来解释人类的起源,为什么比按照普通的繁殖法则来解释个体的产生更为反对宗教呢。物种的产生和个体的产生,都是伟大生命事件发生次序中的相等部分,我们的头脑拒绝承认这是盲目的偶然结果。无论我们能否相信构造的每一个轻微变异——每一对配偶的婚姻结合——每一粒种子的散布——以及其他这等事件全是由神来决定去服从于某一特殊目的的,但理智同这种结论是不相容的。
本书对性选择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因为,正如我试图阐明的,性选择在生物界的历史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我知道还有许多情形存在着疑问,但我已就全部情况尽力提出一个公平的观点。在动物界的较低部门中,性选择似乎没有什么作用:这等动物往往终生固定于同一个地点或是雌雄同体,更加重要的是,它们知觉力和智力还没有足够的进步,以表现爱和嫉妒的感情,或实行选择对象。然而,当进至节肢动物和脊椎动物这二个大“门”时,甚至在它们最低等的纲中,性选择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动物界几个大的纲中——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昆虫类,甚至甲壳类——雌雄之间基本按照同样的规律而有所差异。雄者几乎永远是求偶者;唯独它们具有特殊的武器,用来同其竞争对手进行战斗。它们一般比雌者更加强有力而且更加体大,并且赋有勇气和好斗这等必需的品质。声乐器官或器乐器官以及散发气味的腺体,不是为它们所专有就是比雌者的更加高度发达。它们具有各式各样的附器以及最鲜艳的或惹起注目的颜色,这等颜色往往是以优雅的样式来排列的,而雌者却无所装饰。当雌雄二者在更重要的构造上有所差异时,正是雄者具有特殊的感觉器官以发现雌者,具有运动器官以达到雌者的所在,而且常常具有抱握器官以抓住雌者。雄者的这种种媚惑或招致雌者的构造常常只在每年的某一时期、即在繁殖季节才发达。在许多场合中,这等构造或多或少地传给了雌者;倘如此,它们在雌者身上仅表现为残迹。当雄者被去势之后,这等构造即行消失或决不出现。一般的,它们在雄者的幼小时期不发达,而是在达到生殖年龄之前不久才出现。因此,在大多数场合中,幼小的雌雄二者彼此相像;而且雌者终生同其幼小后代多少相像。几乎在每一个大“纲”中都有少数反常现象发生,这时雌雄二者所固有的性状差不多完全互换位置;雌者呈现雄者所固有的性状。在如此众多的和远隔的诸纲中,雌雄二者之间的差异受到了异常一致的法则所支配,如果我们承认一个共同的原因、即性选择在起作用,这种情形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性选择决定于同一性别的某些个体胜过其他个体,这与物种繁殖有关;而自然选择决定于雌雄双方的成功,不问其年龄如何,这与一般的生活条件有关。性的争斗有两种;一是同一性别(一般为雄者)的个体之间的斗争,以便赶走或弄死其竞争对手,而雌者则处于被动地位;另一种斗争同样也是在同一性别的个体之间进行的,以便刺激或媚惑异性(一般是雌者),这时雌者不再处于被动地位,而是选择更合意的配偶。后面这种选择同人类对家养生物的选择密切相似,人类进行这种选择是无意识的,却是有效的,他在悠久的期间内保存了最合意的或最有用的个体,而没有改变这个品种的任何要求。
任何一种性别通过性选择所获得的性状究竟传递给同一性别还是传递给雌雄双方,以及这等性状在什么年龄才发育,均由遗传法则决定之。在生命晚期发生的变异似乎普通只向同一性别传递。变异性是选择作用所必需的基础,变异性同选择完全没有关系。由此而来的是,具有同样一般性质的变异,与物种繁殖有关者,常常通过性选择而被利用和被积累;与一般生活目的有关者,则通过自然选择而被利用和被积累。因此,次级性征当同等地传递给雌雄双方时,只依据类推方法就能够把它们同物种的普通性状区别开来。通过性选择所获得的变异往往是如此强烈显著,以致雌雄二者屡屡被分类为不同的物种、甚至不同的属。这等强烈显著的差异在某种方式上一定是高度重要的;我们知道,在某些事例中它们的获得不仅招致了不方便,而且还要处于实际的危险之中。
对性选择力量的信念主要是以下述考虑为依据的。一定的性状限于某一性别所专有;仅仅这一事实就很可能说明,在大多数场合中这等性状是同繁殖行为相关联的。大量事例表明,这等性状只在成熟时而且常常只在每年的一部分时期——永远是繁殖季节,才充分发达。雄者在求偶时是比较积极的(除少数例外);它们具有较好的武器,而且在各个方面更富有魅力。特别应该注意的是,雄者在雌者面前精心展示其魅力;除了在求爱季节,它们很少或者决不这样展示。要说这一切都没有目的,乃是不可令人相信的。最后,就某些四足兽和鸟类来说,我们有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某一性别的诸个体对另一性别的一定个体抱有厌恶或偏爱的强烈感情。
如果记住这等事实以及人类对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所实行无意识选择的显著结果,在我看来,几乎肯定的是,如果某一性别的诸个体在一长系列的世代中乐于同另一性别的一定个体相交配——后面这些个体系以某种特殊方式构成其特征的,那么,它们的后代大概会缓慢而肯定地按照这种同样的方式发生变异。我并不试图讳言除非雄者的数量多于雌者或盛行一夫多妻,魅力较强的雄者是否比魅力较弱的雄者能够成功地留下数量较多的后代以承继它们在装饰方面或其他魅力方面的优越性,尚属疑问;但我已经阐明,这大概是由雌者——特别是那些精力较旺盛而且最先繁育的雌者——不仅喜爱魅力较强的、而且同时喜爱精力较旺盛的和获得胜利的雄者所产生的结果。
尽管我们有某种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鸟类欣赏鲜明的和美丽的物体,就像澳大利亚的造亭鸟那样,尽管它们肯定欣赏鸣唱的能力,但我对许多鸟类以及某些哺乳动物的雌者赋有足够的审美力以欣赏那些通过性选择所获得的装饰物,还是充分认为令人感到惊讶;在爬行类、鱼类和昆虫类的场合中这种情形尤其令人感到惊讶。但关于低等动物的心理,我们确是一无所知。例如,不能设想雄极乐鸟或雄孔雀在雌者面前如此尽力地竖起、展开以及摆动其美丽羽毛而全无目的。我们应该记住在前一章根据优秀权威所举出的事实:当禁止几只雌孔雀进入一只受到赞美的雄孔雀所在时,她们宁愿全季寡居,而不与另一只雄孔雀配合。
尽管如此,我所知道的博物学中的事实还没有比雌锦雉欣赏雄者翅羽上“球与穴”装饰物的绝妙色调以及优雅的样式更为不可思议的。谁要是认为雄鸟最初就是像现在这样的形态被创造出来的,那么他必须承认它的巨大羽毛是作为一种装饰物赋予它的,这些巨大羽毛阻碍了双翅用于飞行,而且这些巨大羽毛只在求偶期间而不在其他期间以这个物种所完全特有的一种方式进行展示。倘如此,他还要必须承认雌鸟最初被创造时就被赋予了欣赏这等装饰物的能力。我的看法所不同于此者,在于我相信雄锦雉是通过雌者历代以来对比较具有高度装饰的雄者的爱好而逐渐获得了他的美貌;雌者的审美能力是通过实用或习性而提高的,正如我们自己的趣味是逐渐改进的一样。有的雄者由于侥幸的机会保持了少数未变的羽毛,我们在这等羽毛上可以清楚地找到非常简单的斑点,在其一边稍微呈黄褐色调,这等斑点只要跨几小步就可发展成不可思议的“球与穴,,装饰物;实际上它们大概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有的人承认进化原理,但对雌性哺乳类、鸟类、爬行类和鱼类能够获得鉴赏雄者美貌的高度能力,而且这种鉴赏能力一般符合于人类的标准,却感到非常难以承认,这些人应该思考一下以下情况,即:一系列脊椎动物的最高等成员以及最低等成员的脑神经细胞都是起源于这一大界(kingdom)的一个共同祖先的脑神经细胞。这样我们就能知道何以会发生这样情形:在各种大不相同的动物类群中某些心理官能系按照差不多同样的方式和差不多同样的程度而发展的。
读者读过讨论性选择的这几章之后,将能判断我所达到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充分证据的支持。如果他接受这些结论,我以为他就可以稳妥地把它们扩大应用于人类;不过关于我刚刚谈过的有关性选择显然作用于人类男女的方式就无须在此重复赘述了,性选择引起了男女在身体和心理上的差别,引起了若干种族彼此在各种不同性状上的差别以及同其古老的、体制低等的祖先的差别。
凡是承认性选择原理的人将被引到一个明显的结论:神经系统不仅支配着身体的大多数现有机能,而且间接地影响某些心理属性以及各种身体构造的向前发展。勇气、好斗性、坚忍性、体力强弱和身体大小,一切种类的武器、音乐器官——无论声乐的或器乐的,鲜明的颜色以及装饰性的附器,所有这些都是由某一性别或另一性别通过选择的实行,通过爱情和嫉妒的影响,通过对声音、颜色或形态之美的欣赏,而间接获得的;这等心理的能力显然决定于脑的发达。
人在使其饲养的马、牛和狗进行交配之前,总要细心地检查这些动物的性状及其谱系;但当他自己结婚时,却很少或根本不注意这些。人类高度重视精神魅力和美德,在这方面他虽然远远高出低于人类的动物之上,但人类还是被动物选择对象时的那种同样动机所推动。另一方面,人类会单纯地被对象的财富或地位所吸引。然而人类通过选择不仅对其后代的身体构造和体质会发生一些作用,而且对其智力和道德属性也会发生一些作用。如果男或女的身心在任何显著程度上都是低劣的,他们就应控制自己不结婚;不过这种希望乃是空想,除非遗传法则彻底得到了解之后,甚至局部实现这种希望也是决不会办到的。凡是帮助实现这个目的的人,都有很大贡献。当繁殖和遗传原理得到更好理解时,我们将不会听到我们立法机关的无知人员以轻蔑的态度来否决一个确定血族婚姻是否有害于人类的方案了。
人类福利的增进是一个最错综复杂的问题:凡是生下子女而不能避免陷于赤贫的人,都应控制自己不结婚;因为贫穷不仅是一种巨大弊害,如果结婚不顾后果,而且还有使这种弊害增大的倾向。另一方面,正如古尔顿先生所说的,如果轻率者结婚,而谨慎者避免结婚,则社会的低劣成员就会有取代较优成员的倾向。就像每一种其他动物那样,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到这样高的地步,无疑是通过迅速增殖所引起的生存斗争而完成的;如果人类更向高处进步,恐怕一定还要继续进行剧烈的斗争。否则人类就要堕入懒惰之中,天赋较高的人在生活斗争中将不会比天赋较低的人获得更大的成功。因此,人类的自然增加率虽可导致许多明显的弊害,但也不会有任何方法把它大大降低。所有的人均应参加公平竞争;不应以法律或习惯来阻止最有才能的人获得最大的成功并养育最大数量的后代。生存斗争过去是、现在依然是重要的,然而仅就人类本性的最高部分而言,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力量。这是因为道德品质的进步直接或间接通过习性、推理能力、教育、宗教等效果来完成的,远比通过自然选择来完成的为大;虽然为道德观念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的社会本能可以稳妥地归因于自然选择的力量。
我遗憾地认为,本书得出的主要结论,即:人类起源于某种低等体制的类型,将会使许多人感到非常厌恶。但几乎无可怀疑的是,我们乃是未开化人的后裔。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看到荒凉而起伏的海岸上的一群火地人时所感到的惊讶,因为我立即想到,这就是我们的祖先。这些人是完全裸体的,周身涂色,长发乱成一团,因激动而口吐白沫,他的表情粗野、惊恐而多疑。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技艺,就像野兽那样地生活,捉到什么吃什么;他们没有政府,对不属于自己小部落的每一个人都冷酷无情。当一个人在本地看到一个未开化人时,如果被迫承认在其血管中流有某一更为低等动物的血,将不会引为奇耻大辱。至于我自己,我宁愿是那只有英雄气概的小猴的后裔,它敢于抗拒可怕之敌以保卫其管理人的性命,我也宁愿是那只老狒狒的后裔,它从山上跑下来,从惊慌的群犬中把一只小狒狒胜利地救走,但我不愿是一个未开化人的后裔,他以虐待其敌人为乐趣,他以鲜血淋漓的牺牲来献祭,他实行杀婴而不愧悔,他待妻子如奴隶,他不懂礼仪,而且被粗野的迷信所纠缠。
人类达到生物等级的顶峰虽不是由于自己的力量,但对此感到骄傲还是可以原谅的;人类最初并不据有现在这样的地位,而是后来升上去的,这一事实对人类在遥远的未来注定还可以登上更高的地位给予了希望。但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并不是对未来的希望或恐惧,我们所关注的只是理性允许我们所能发现的真理;我已经尽我的最大力量提出了有关的证据。然而在我看来,我们必须承认,人类虽然具有一切高尚的品质,对最卑劣者寄予同情,其仁慈不仅及于他人而且及于最低等的生物,其神一般的智慧可以洞察太阳系的运动及其构成——虽然他具有一切这样高贵的能力——但在人类的身体构造上依然打上了永远擦不掉的起源于低等生物的标记。
附录 关于猴类的性选择
(原载《自然杂志》,1876年11月2日出版,第18页)
我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讨论性选择时,使我最感兴趣而且最感困惑的事例莫过于某些猴类的臀部及其毗连部分的鲜明颜色了。由于这等部分的颜色在某一性别比在另一性别更为鲜明,而且由于它们在求爱季节变得更加灿烂,所以我断言这种颜色是作为性的吸引力而获得的。我十分清楚,这种说法将使我自己成为笑柄;虽然一只猴子展示其鲜红的臀部,事实上并不比一只孔雀展示其华丽的尾羽更为令人惊奇。可是,关于猴类在求偶期间显示其身体的这一部分,在那时我并没有掌握什么证据;而在鸟类的场合中,这种展示却提供了最好的证据来说明,雄者的这种装饰物对吸引或刺激雌者是有用处的。最近我读过哥达(Gotha)的约翰·冯·菲舍尔(Joh.von Fischer)写的一篇论文,载于《动物园杂志》(1876年4月),其中讨论了猴类在各种不同情绪中的表现,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人读一读这篇文章是十分值得的,它示明作者是一位细心的、敏锐的观察家。在这篇论文中记载了一只幼小的雄西非山魈,最初站在镜前注视自己的举动,接着他写道,过了一会儿,它转过身去把它的红屁股展示于镜前。为此,我写信给冯菲舍尔先生,询问他对这种奇怪动作的意义有什么设想,他回我两封长信,详细地叙述了新奇的情节,我希望以后予以发表。他说,他最初对上述动作也感到困惑,因此引导他对另外几种猴的若干个体进行了细致观察,这些猴都是长期养在他家中的。他发现,不仅西非山魈(Cynocephalus mormon),而且鬼狒(C.leucophaeus)、其他三种狒狒(C.hamadryas,sphinx,babouin),还有黑犬面狒狒(C.hamadryas),以及恒河猴(Macacus rhesus)和豚尾猴(M.nemestrinus),当高兴时都把身体的这一部分转向他,而且也转向别的人作为一种敬意,所有这些物种的臀部多少都呈现鲜明的颜色。他曾尽力矫正一只恒河猴的这种不雅的习惯,最后还是成功了,这只猴他养过五年。当这些猴遇到一只新来的猴时,特别容易做这种动作,而且同时龇牙咧嘴地嘶叫,不过对它们的老猴友也常常如此;在这种相互展示之后,它们就开始一齐玩耍起来了。那只小西非狒狒向着它的主人冯菲舍尔作了一会儿这种动作之后,就自发地停了下来,不过对那些陌生人和新来的猴还继续照样做。除了一次例外,一只幼小的黑犬面狒狒从来不向他的主人做这样的动作,不过对陌生人则屡屡这样做,直到现在还继续如此。根据这几项事实,冯菲舍尔断言,那些猴(即西非山魈、鬼狒、黑犬面狒狒、恒河猴、豚尾猴等)在镜前做这种动作时,好像以为镜中的映像是新相识似的。西非山魈和鬼狒的臀部装饰得特别厉害,它们甚至在幼小的时候就行展示了,而且比其他种类更加常常如此、更加卖弄这一部分。其次就属黑犬面狒狒了,而其他物种做这种动作的则比较少见。然而,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有差异,有些个体很羞怯,从来不展示它们的臀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冯菲舍尔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物种有目的地展示其臀部,如果其臀部完全没有颜色。这一看法也可应用于爪哇猴(Macacus cynomolgus)和白眉猴(Cercocebus radiatus,同恒河猴的亲缘关系密切)的许多个体,还可应用于长尾猴属(Cercopithecus)的三个物种以及几种美洲猴。把臀部转向老朋友或新相识作为一种敬意,这种习性在我们看来似乎很古怪,其实这并不比许多未开化人的一些习性更古怪,例如未开化人用手摩擦自己的肚皮,或者彼此摩擦鼻子。西非狒狒和鬼狒的这种习性似乎是本能的或遗传的,因为很幼小的这等动物就这样干了;不过,它像许多其他本能那样,由于观察而有所改变,或者被观察所支配,因为冯菲舍尔说,它们尽力地把这种展示做得充分;如果在两位观察者面前做这种动作,它们就会把臀部转向那位似乎最给予注意的人。
关于这种习性的起源,冯菲舍尔说,他养的那些猴喜欢轻拍或敲打它们无毛的臀部,这样做之后,它们就感到高兴并从喉部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它们还常常把臀部转向给它们除掉污物的其他猴子,对于那些给它们剔去棘刺的猴子无疑也会如此。不过成年猿猴的这种习性在一定程度上却与两性情感有关联,因为冯菲舍尔曾透过玻璃门去注视一只雌性黑犬面狒狒的活动,它在几天内,“把它的很红臀部转向一只喉部咕噜作响的雄者,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只动物这样做过。显然这只雄者看到雌者的红色臀部后便激动起来了,因为即使用手杖敲地砰砰作响,它的喉部还是突然一阵一阵地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按照冯菲舍尔的说法,凡是臀部多少呈现鲜明颜色的猴类都生活在开阔的多岩石地方,所以他以为这种颜色是为了使某一性别在远处容易看到另一性别;但是,由于猴类是群居的动物,我想没有必要使雌雄双方在远处彼此辨认。在我看来更加可能的似乎是,无论面部或臀部的鲜明颜色,或像西非山魈那样,面部和臀部均呈鲜明颜色,都是用做一种性的装饰和魅力。无论如何,由于现在我们知道猴类有把其臀部转向其他猴的习性,所以身体的这一部分得到装饰就完全不足为奇了。就现在所知道的来说,只有猴类具有这种特征,而且以这种方式向其他猴表示敬意,这一事实使人对下述情况产生了疑问:这种习性最初是否由于某种独立的原因而被获得的,此后这等议论中的部分作为一种性的装饰而着上了颜色;或者,这种颜色以及转动臀部的习性最初是否通过变异和性选择而被获得的,此后通过遗传原理的联合作用,作为高兴或致敬的一种标志而被保存下来了。这一原理显然在许多情况下都发生作用:例如,一般承认鸟类在求爱季节的鸣唱主要是用来吸引异性的,黑松鸡的盛大集会是同它们的求偶有关系的;但有些鸟,例如欧鸲,保持了在快乐时鸣叫的习性,而黑松鸡也保持了在每年其他季节举行集会的习性。
请允许我再讨论一下同性选择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有人反对性选择说,仅就雄者的装饰物而言,这种选择的方式意味着同一地区的所有雌者一定都具有和行使完全一样的审美力。然而应该注意到,第一,一个物种的变异范围虽然很大,但绝不是无限的。关于这一事实,我在别处举出过一个有关鸽的良好事例,鸽至少有一百个变种,它们的羽色大不相同,鸡至少有二十个变种,它们的羽色也大有差别;但这两个物种的变动范围却极端不同。所以,自然物种的雌者在审美方面不会有毫无限制的范围。第二,我以为没有一个支持性选择原理的人相信雌者所选择的,是雄者特有的美的部分;而只是某一雄者比另一雄者对它们刺激或吸引的程度较大而已,这一点往往决定于灿烂的颜色,鸟类尤其如此。甚至一个男人对他所赞美的女人面貌上的轻微差异也不加分析,而她的美恰恰决定于这等轻微差异。雄西非山魈不仅臀部而且面部均呈灿烂的颜色,此外,面部还有隆起的斜条纹、黄胡须以及其他装饰物。根据我们所看到的家养动物的变异,可以推论西非狒狒获得上述几种装饰物,乃是由于某一个体在某一方面发生了一点变异而另一个体在另一方面发生了一点变异所致。雄者如果任何方面在雌者看来都是最漂亮而且最有吸引力的,雄者大概就会最常常交配,并且会比其他雄者留下更多的后代。其雄性后代虽然多方面地进行杂交,但还是承继了其父本的特性,或者向下传递一种增大的倾向而按照同样方式进行变异。因此,居住在同一地区的雄者,其整个身体由于不断杂交的作用大概有发生差不多同样变异的倾向,不过有时这一种性状变异得大些,有时那一种性状变异得大些,尽管这等变异的速度是极端缓慢的;这样,最终所有个体都变得更能吸引雌者。其过程正如人类所实行的被我称为无意识的选择那样,关于这一点我已经举出过若干事例了。某一地方的居民重视快速的、即轻型的狗或马,另一地方的居民却重视比较重型的和比较强有力的狗或马;但在这两处地方都不选择身体或四肢比较轻型的或比较强有力的个体动物;尽管如此,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还可发现诸个体都按照所要求的方式发生了几乎一样的改变,虽然在每一处它们的改变是不同的。如果在两处界限绝对分明的地方居住着同一个物种,其个体在悠久的期间内决不互相迁移和互相杂交,而且在这两处地方发生的变异大概不会完全相同,于是性选择就可能致使这两处地方的雄者有所差别。在我看来,下述信念完全不见得是空想,即:处于很不相同环境中的两组雌者大概会获得对形态、声音或颜色的多少不同的爱好。不管怎样,我还是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举出了一些事例表明在不同地方居住的亲缘密切的鸟类,其幼鸟和雌鸟没有区别,而成年的雄鸟都彼此差别很大,这非常可能是由性选择作用所引起的。
————————————————————
(1) 沙夫豪森,译文见《人类学评论》,1868年10月,419,420,427页。
(2) 《非洲中心地带》(The Heart of Africa),英译本,第1卷,1873年,544页。
(3) 埃克(Ecker)译文见《人类学评论》,1868年10月,351—356页。男女头骨形状的比较,是由韦尔克(Welcker)非常仔细地作出的。
(4) 埃克和韦尔克,同前杂志,352,355页;沃格特(Vogt),《人类讲义》,英译本,81页。
(5) 沙夫豪森,《人类学评论》,1868年10月,429页。
(6) 普鲁纳-拜(Pruner-Bey)论黑人的婴儿,沃格特引用,《人类讲义》,1864年,189页;关于黑人婴儿的另外事实,引自温特-博顿和坎普尔的著述,参阅劳伦斯的《生理学讲义》,1822年,451页。关于格拉尼族的婴儿,参阅伦格尔的《哺乳动物志》,3页。再参阅戈德隆的《物种》,第2卷,1859年,253页。关于澳大利亚土人,参阅魏茨的《人类学概论》,英译本,1863年,99页。
(7) 伦格尔,《哺乳动物志》,1830年,49页。
(8) 关于爪哇猴(Macacus cynomolgus),见德马雷的《哺乳动物学》,65页;关于长臂猿,见小圣·伊莱尔和居维叶的《哺乳动物志》,第1卷,1824年,2页。
(9) 《人类学评论》,1868年10月,353页。
(10) 布莱思告诉我说,关于猴子的胡须和颊须在年老时变白,他只见过一个事例,但人类通常皆如是。在槛中饲养的一只老年爪哇猴的胡须变白,它的唇须“非常之长,同人类的相似”。这只老猴同欧洲的一个在位君主非常相似,普通竟以这个君主的名称作为这只猴子的绰号。人类某些种族的头发从不变成灰白色,例如福布斯告诉我说,他从未看见过南美的亚马拉人(Aymaras)和基切人(Quichuas)的头发变成灰色的。
(11) 这是关于长臂猿几个物种的雌者的例子,参阅小圣伊莱尔和居维叶的《哺乳动物志》,第1卷。关于白手长臂猿(H.lar.),再参阅《佩尼百科词典》(Penny Cyclopedia),第2卷,149,150页。
(12) 这个结果是由魏斯巴赫(Weisback)教授根据舍策尔(Scherzer)和施瓦茨(Schwartz)两位教授所作的测计推算出来的,参阅《诺瓦拉旅行记》;《人类学评论》,1867年,216,231,234,236,239,269页。
(13) 《圣基尔塔航行记》(Voyage to st.kilda),第3版,1753年,37页。
(14) 坦南特爵士,《锡兰》(Ceylon)。
(15) 考垂费什,《科学报告评论》,1868年8月29日,630页。沃格特;《人类讲义》,英译本,127页。
(16) 关于黑人的胡须,沃格特,《人类讲义》,127页;魏茨,《人类学概论》,英译本,第1卷,1863年,96页。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纯种黑人及其混血儿后代的体毛之多似乎同欧洲人差不多一样(见《关于美国士的军事学和人类学的统计之研究》,1869年,569页)。
(17) 华莱士,《马来群岛》,第2卷,1869年,178页。
(18) 巴纳德·戴维斯论大洋洲的种族,《人类学评论》,1870年4月,185,191页。
(19) 卡特林,《北美的印第安人》(North American Indians),第2卷,第3版,1842年,227页。关于格拉尼族,阿扎拉(Azara)《南美游记》,第2卷,1809年,58页;还有,伦格尔,《巴拉圭的哺乳动物》(S ugethiere von Paraguay),3页。
ugethiere von Paraguay),3页。
(20) 阿加西斯教授说美洲男女之间的差别小于黑人之间的以及高等种族之间的差别,见《巴西游记》(Journey in Brazil),530页;关于格拉尼族,再参阅伦格尔的上述著作,3页。
(21) 吕蒂迈尔(Rütimeyer)《动物界的边际;用达尔文学说进行的观察》(Die Grenzen der Thierwelt;eine Betrachtung zu Darwin's Lehre),1868年,54页。
(22) 《从威尔士亲王要塞出发的旅行记》(A Journey from Prince of Wales)第八版,都柏林(Dublin),1796年,104页。卢伯克爵士提供一些北美的相似事例,见《文化的起源》,1870年,69页。关于南美的瓜纳族(Guanas),参阅阿扎拉的《航海记》,第2卷,94页。
(23) 关于雄大猩猩的争斗,参阅萨维奇的文章,见《波士顿博物学杂志》,第5卷,1847年,423页。关于长尾叶猴(Presbytis entellus),参阅《印度大地》(Indian Field),1859年,146页。
(24) 米尔(Mill)说,“男人最胜过女人的,在于那些需要以独立思考进行和若干千锤百炼的事情”《女子的隶属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1869年,122页,此非精力和坚忍为何?
(25) 莫兹利(Maudsley),《精神和身体》(Mind and Body),31页。
(26) 沃格特做的一项观察同这个问题有关,他说:“值得注意的一个情况是,男女之间关于脑壳的差异,随着种族的发展而增加,所以欧洲男女在这方面的差异远比黑人男女为甚。韦尔克尔根据胡希克(Huschke)对黑人和德国人头骨所做的测计,证实了他的上述说法。”但是,沃尔特认为对这个问题还需要进行更多的观察(《人类讲义》,英译本,1864年,81页)。
(27) 欧文,《脊椎动物解剖学》,第3卷,608页。
(28) 《人类学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Soc.),1869年4月,57,58页。
(29) 斯卡德尔(Scudder),《关于摩擦发音的记录》(Notes on Stridulation),见《波士顿博物学会会报》,第11卷,1868年,4月。
(30) 见马丁的《哺乳动物志大纲》,1841年,432页;欧文,《脊椎动物解剖学》,第3卷,600页。
(31) 《美国博物学者》,1871年,761页。
(32) 赫姆霍尔兹(Helmholtz)《音乐的生理学理论》(Théorie Phys.de la Musique),1868年,187页。
(33) 关于这种效果曾发表过几篇文献。皮奇(Peach)先生写信告诉我说,他反复看到,当长笛发出B降半音时,他的那条老狗就吠叫,而它听到其他音调就不吠叫。我还可以补充一个事例:有一只狗当听到演奏六角手风琴走调时,它就哀哀吠叫。
(34) 布朗先生,《动物学会会报》,1868年,410页。
(35) 《人类学学会会报》,1870年10月,155页。再参阅卢伯克爵士的《史前时代》一书的后面几章,第2版,1869年,其中有关于未开化人的令人钦佩的记载。
(36) 当本章付印之后,我曾看到乔塞·赖特所写的一篇有价值的文章(见《北美评论》,1870年10月,293页),当他讨论上述问题时说道:“终极法则、即自然界的一致性产生许多结果,于是某一种有用能力的获得将会引出许多利益以及有限度的不利(实际的和可能的),这可能是功利原理在其作用中所不曾包括的。”正如我在以前一章所试图阐明的,这一原理同人类获得某些心理特征有重要关系。
(37) 温伍德·里德,《人类的折磨》,1872年,441页;《非洲随笔》,第2卷,1873年,313页。
(38) 伦格尔,《巴拉圭的哺乳动物》,49页。
(39) 赫伯特·斯宾塞先生所写的《关于音乐的起源及其功能》(Origin and Function of Music)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有趣的讨论,载于他的《论文集》,1858年,359页。斯宾塞所做的结论同我的结论正相反。他的结论正如戴德罗特(Diderot)以前所做的那样,认为激情言语所使用的抑扬顿挫的声调提供了音乐所赖以发达的基础;而我的结论则是,音乐的调子和节奏是由人类男女为了取悦异性而最初得到的。这样,音乐的调子同一种动物所能感到的最强烈激情是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结果就会本能地使用音乐调子,或在言辞中表达强烈情绪时通过联想也会使用音乐调子。为什么高亢的和深沉的音调会表达人类和低于人类的动物的某些情绪,斯宾塞先生没有提供任何令人满意的解说,我也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斯宾塞先生对诗歌、朗诵和歌唱之间的关系也进行过有趣的讨论。
(40) 我在蒙包多(Monboddo)勋爵的《语言的起源》(Origin of Language)一书(第1卷,1774年)中发现布莱克洛克(Blacklock)同样认为,“人类最初的语言为音乐,在用有音节的声音来表达我们的思想之前,则赖不同程度的高低的音调来互通思想。”
(41) 参阅赫克尔(H ckel)对这个问题的有趣讨论,《普通形态学》,第2卷,1866年,246页。
ckel)对这个问题的有趣讨论,《普通形态学》,第2卷,1866年,246页。
(42) 关于世界各地未开化人装饰自己的方法,意大利旅行家曼特加沙教授做过最优秀的详细记载,见《拉普拉塔旅行记及其研究》(Rio de la Plata Viaggi e Studi),1867年,525—545页;所有以下叙述,凡未记明其他参考书者,均引自此书。再参阅魏采的《人类学概论》,英译本,第1卷,1863年,275页及以下诸页。劳伦斯也做过很详细的记载,见他的《生理学讲义》,1822年。本章写成之后,卢伯克爵士发表了他的《文化的起源》(1870年),该书的有趣一章对现在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关于未开化人染牙、染发以及穿齿孔,我从那一章引用了一些事实(42,48页)
(43) 洪堡,《个人记事》,英译本,第4卷,515页;关于涂身所表明的想象,522页;关于改变小腿的形状,466页。
(44) 古石器时代的后半期。——译者注
(45) 《尼罗河支流》(The Nile Tributaries),1867年;《阿尔贝·尼安萨》(The Albert N'yanza),第1卷,1866年,218页。
(46) 皮卡得(Pichard),《人类体格史》,第1卷,第4版,1851年,321页。
(47) 关于巴布亚人,参阅华莱士的《马来群岛》,第2卷,445页。关于非洲人的头发式样,参阅贝克爵士的《阿尔贝·尼安萨》,第1卷,210页。
(48) 《旅行记》,533页。
(49) 《阿尔贝·尼安萨》,第1卷,1866年,217页。
(50) 利文斯通,《英国科学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1860年;《科学协会会刊》所刊登的一篇报告,7月1日,1860年,29页。
(51) 贝克爵士当谈到中非土人时说道(同前书,第1卷,210页)“每一个部落都有一种固定的特殊发式”。阿加西斯记载过亚马孙河流域印第安人固定的文身式样,见《巴西游记》,1868年,318页。
(52) 泰勒(R.Taylor)牧师,《新西兰及其居民》(New Zealand and its Inhabitants),1855年,152页。
(53) 芒特热沙(Mantegezza)《拉普拉他旅行记及其研究》(Viaggi e Studi),542页。
(54) 《非洲游记》,第l卷,1824年,414页。
(55) 南非卡拉哈里沙漠地区的一个游牧部落。——译者注
(56) 参阅格兰德(Gerland)的《原始民族的消亡》(Ueber das Aussterben der Naturv lker),1868年,51,53,55页;再参阅阿扎拉的《航行记》,第2卷,116页。
lker),1868年,51,53,55页;再参阅阿扎拉的《航行记》,第2卷,116页。
(57) 关于美洲西北部分印第安人所使用的植物,参阅《药学杂志》(Pharmaceutical Journal),第10卷。
(58) 《从威尔士亲王要塞出发的旅行记》,第8卷,1796年,89页。
(59) 普里查德(Prichard)在其著作《人类体格史》中引用,第4卷,第3版,1844年,519页;沃格特,《人类讲义》,英译本,129页。关于中国人对僧伽罗人(Cingalese)的看法,参阅坦南特的《锡兰》,第2卷,1859年,107页。
(60) 普里查德引用克劳弗德(Crawfurd)和芬利森的意见,见《人类体格史》,第4卷,534,535页。
(61) 这位声名赫赫的旅行家告诉我说,我们最嫌恶的妇女月经带,以前却最受这个种族的重视,但这种风气现在已有改变,其重视程度已经远不及以前了。
(62) 《人类学评论》,1864年11月,237页。再参阅魏茨的《人类学概论》,英译本,第1卷,1863年,105页。
(63) ⑻指非洲西北部柏柏尔人的后裔。——译者注
(64) 在非洲东南部,班图族的一支。——译者注
(65) 芒戈·帕克的《非洲游记》,1816年,53,131页。沙夫豪森引用伯顿的叙述,见《人类学文献集》(Archiv für Anthropolog),1866年,163页。关于班埃人,利文斯通,《游记》,64页。关于卡菲尔人,斯库特尔(Schooter)牧师,《纳塔尔和祖鲁地方的卡菲尔人》(The Kafirs of Natal and the Zulu Country),1857年,1页。
(66) 关于爪哇人和交趾支那人,参阅魏茨的《人类学概论》,英译本,第1卷,305页。关于余拉卡拉族,皮卡得在《人类体格史》中引用杜比尼的材料,第5卷,第3版,476页。
(67) 卡特林著,《北美的印第安人》,第1卷,第3版,1842年,49页;第2卷,227页。关于温哥华岛的土人,参阅斯普罗特(Sproat)的《未开化人生活的景象及其研究》,1868年,25页。关于巴拉圭的印第安人,参阅阿扎拉的《航行记》,第2卷,105页。
(68) 关于暹罗人,普里查德,同前书,第4卷,533页。关于日本人,雏奇,《艺园者纪录》(Gardener's Chronicle),1860年,1104页。关于新西兰人,曼特加沙,《拉普拉他旅行记及其研究》,1867年,526页。关于上述其他民族,劳伦斯,《生理学讲义》,1822年,272页。
(69) 卢伯克,《文化的起源》,1870年,321页。
(70) 巴纳德·戴维斯引用皮卡得先生以及其他人士关于波利尼西亚人这等事实的述说,见《人类学评论》,1870年4月,185,191页。
(71) 孔德(Ch.Comte)在其《法律专著》[(Traité de Législation),第3版,1837年,136页]中曾谈到此事。
(72) 《非洲随笔》,第2卷,1873年,253,394,521页。有一位传教士曾同火地人长久在一起住过,他告诉我说,火地人以为欧洲妇女非常美丽,但是,根据我们看到的其他美洲土人的判断,我不得不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除非少数火地人曾同欧洲人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而且他们把我们看做优等的人。我应该补充一点:最有经验的观察家伯尔登船长相信我们认为美丽的妇女在全世界都会受到称赞,《人类学评论》,1864年3月,245页。
(73) 《个人记事》,英译本,第4卷,518页及其他诸页。曼特加沙在其《拉普拉他旅行记及其研究》中强烈主张这同一原理。
(74) 关于美洲部落的头骨,参阅诺特(Nott)和格利敦(Gliddon)的《人类的模式》,1854年,440页;普里查德,《人类体格史》第1卷,第3版,321页;关于若开土人,同前书,第4卷,537页;威尔逊,《自然人种学》(Physical Ethnology),史密森协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1863年,288页;关于火地人,290页。卢伯克爵士关于这个问题写过一篇优秀的摘要,见《史前时代》,第2版,1869年,506页。
(75) 居住在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译者注
(76) 关于匈奴人,戈德隆,《论物种》,第2卷,1859年,300页。关于塔希提人魏采,《人类学概论》,英译本,第1卷,305页。皮卡得在其《人类体格史》中引用马斯登(Marsden)的材料,见该书,第5卷,第3版,67页。劳伦斯,《生理学讲义》,337页。
(77) 此事见《诺瓦拉旅行记》(Reise der Novara):《人类学评论》,威斯巴哈博士1867年,265页(这是臆造的情况——译者注)。
(78) 《史密斯协会》,1863年,289页。关于阿拉伯妇女的发式,贝克爵士,《尼罗河支流》,1867年,121页。
(79)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1卷,214页;第2卷,240页。
(80) 沙夫豪森,《人类学文献》,1866年,164页。
(81) 关于美的观念,贝恩先生搜集了约12个多少不同的学说(见《心理学和道德学》,1868年,30—314页);但是没有一个学说同这里所说的相同。
(82) 《叔本华和达尔文主义》(Schopenhauer and Darwinism),见《人类学杂志》(Journal of Anthropology),1871年1月,323页。
(83) 高加索人的一个部落。——译者注
(84) 这些话引自劳伦斯的《生理学讲义》(Lectures on Physiology),1822年,393页,他把英国上等阶级的美貌归因于这个阶级的男子长期选择比较美丽的妇女。
(85) 《人类学》,见《科学报告评论》,1868年10月,721页。
(86)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1卷,207页。
(87) 卢伯克爵士,《文化的起源》,1870年,第三章,特别是60—67页。伦南先生在其极有价值的著作《原始婚姻》(1865年,163页)中谈到,男女的结合“在最古时代是散漫的、暂时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混乱的”。伦南先生和卢伯克爵士就现今未开化人的极其混乱生活搜集了大量证据。莫尔根先生在一篇有关亲属关系分类体系的有趣报告中断言[见《美国科学院院报》(Proc.American Acad.of Sciences),第7卷,1868年2月,475页],一夫多妻以及所有婚娴形式在原始时代基本上都是不存在的。根据卢伯克爵士的著作,巴霍芬(Bachofen)似乎也相信原始时代曾盛行过群交。
(88) 《在英国学术协会上关于人类低等种族社会状况和宗教状况的讲话》(Address to British Association on the Social and Religious Condition of the Lower Races of Man),1870年,20页。
(89) 《文化的起源》,1870年,86页。在以上引用的几种著作中可以发现关于单独通过母系的亲属关系以及单独通过部落的亲属关系的丰富证据。
(90) 韦克强烈反对这三位作者所持的观点——认为往昔曾盛行过接近群交的结合方式,他以为亲属关系的分类体系可用他法来解释(《人类学》,1874年3月,197页)。
(91) 布雷姆说(《动物生活图解》,第1卷,77页),埃塞俄比亚鼯猴(Cynocephalus hamadryas)营大群生活,其中成年雌者为雄者的两倍。参阅伦格尔关于美洲一夫多妻物种的叙述,以及欧文(《脊椎动物解剖学》,第3卷,746页)关于美洲一夫一妻物种的叙述。此外还有其他参考材料。
(92) 萨维奇,《波士顿博物学杂志》,第5卷,1845—1847年,423页。
(93) 锡兰(现名斯里兰卡)最古老的土著。——译者注
(94) 《史前时代》,1869年,424页。
(95) 伦南,《原始婚姻》,1865年。特别参阅有关族外婚姻和杀婴部分,130,138,165页。
(96) 格兰德博士(《原始民族的消亡》,1868年)搜集了很多有关杀婴的材料,特别参阅27,51,54页。阿扎拉(《游记》,第2卷,94,116页)详细地讨论了其动机。再参阅伦南(同前书,139页)所举出的有关印度的例子。本书第2版在上述一节中不恰当地举出了格雷(Grey)爵士错误的引证,现已删去。
(97) 《原始婚姻》,208页;卢伯克爵士,《文化的起源》,100页,再参阅摩尔根上述著作中有关古时盛行一妻多夫的部分。
(98) 阿扎拉,《游记》,第2卷,92—95页,马歇尔上校,《在托达人中间》(Amongst the Todas),212页。
(99) 伯切尔说(《南非游记》,第2卷,1824年,58页),在南非各野蛮民族中无论男人或女人没有过独身生活的。阿扎拉(《南美游记》,第2卷,1809年,21页)对南美野蛮印第安人提出了恰好一样的看法。
(100) 即tabbo,系宗教迷信或社会习俗的禁忌。——译者注
(101) 《人类学评论》,1870年1月,16页。
(102)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210—217页。
(103) 一位富有才华的作者主张,从意大利画家拉斐尔(Raphael),荷兰画家鲁宾斯(Rubens)以及近代法国画家们的绘画来看,美的概念即使在欧洲也绝对不同,参阅旁贝特(Bombet)著,《海登和莫扎特的生平》(Lives of Haydn and Mozart),英译本,278页。
(104) 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在哥伦布以前的时代,他们分布在乌拉圭一带。——译者注
(105) 居住在巴拉圭平原上的一个部落,现已成为说西班牙语的混血儿。——译者注
(106) 阿扎拉,《游记》,第2卷,23页。多布瑞热弗尔(Dobrizhoffer),《关于阿比朋人的记载》(An Account of the Abipones),第2卷,1822年,207页。玛司特斯船长,《皇家地理学会会报》(Proc.R.Geograph.Soc.),第15卷,47页。威廉斯(Williams)关于斐济岛民的叙述,卢伯克引用,见《文化的起源》,1870年,79页。关于火地人,金和菲茨罗伊(King and Fitzroy),《探险号和贝格尔号航行记》(Voyages of the Adventure and Beagle),第2卷,1839年,182页。关于蒙古人,伦南在《原始婚姻》中的引文,1865年,32页。关于马来人,卢伯克,同前书,76页。舒特(Shooter)牧师,《关于卡菲尔人和纳塔尔人》(On the Kafirs and Natals),1857年,52—60页。莱斯利先生,《卡菲尔人的特性和风俗》(Kafir Character and Customs),1871年4月。关于布西门人,伯切尔,《南非游记》,第2卷,1824年,59页。关于高拉克人,韦克先生在《人类学》(1873年10月,75页)中引用麦克肯南(McKenan)之说。
(107) 《对自然选择学说的贡献》,1870年,346页。华莱士先生相信(350页),“某种智力支配了或决定了人类的发展”;他认为皮肤的无毛状态应归属于这个问题之下。斯特宾(Stebbing)在评论这一观点时说道(《德文郡科学协会会报》,1870年),如果华莱士先生“没有用其敏锐的眼光来观察人类无毛皮肤这一问题,那么他大概会看到对无毛皮肤的选择可能是通过这种至美或健康所必需的非常清洁”。
(108)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1868年,327页。
(109) 《关于美国士兵的军事学和人类学的统计之研究》,古尔德著,1869年,568页:——当2129名黑人以及有色人种士兵入浴时,曾对他们体毛的多少进行过细致的观察;粗略地看一下已发表的表格,就可知道“白人和黑人在这方面如果有任何差异的话,显然也是微乎其微的”。然而,黑人在其非洲本土热得多的地方,他们的体部是显著无毛的。应该特别注意到纯种黑人和黑白混血儿均列入上述数字之中;这是一件不适当的事情,因为,根据一项原理——我在他处已经证实了它的正确性,人类的杂交种族显著容易返归其早期类猿祖先的原始多毛性状。
(110) 本书中受到最大反对的观点即为,关于人类毛的消失乃是通过性选择的上述说明[例如,参阅施彭格尔(Spengel),《达尔文主义的发展》(Die Fortschritte des Darminismus),1874年,80页];但是,同一些事实相比,没有一个反对的论点在我看来是有很大分量的,这些事实表明在人类以及某些四手类中皮肤无毛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第二性征。
(111) 《论人类体部的无毛》(Ueber die Richtung der Haare am Menschlichen K rper),见米勒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文献集》(Archiv für Anat.und Phys.),1837年,40页。
rper),见米勒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文献集》(Archiv für Anat.und Phys.),1837年,40页。
(112) 关于翠鴗(Momotus)的尾羽,见《动物学会会报》,1873年,429页。
(113) 斯普罗特(Sproat)先生提出过同样的观点,见《未开化人生活的景象及其研究》(Scenes and Studies of Savage Life),1868年,25页。有些人种学者相信头骨的人工改变倾向于遗传,日内瓦的戈斯即为其中的一人。
(114) 《论人类身体的无毛》,40页。
(115) 《论自然选择的范围》(On the Limits of Natural Selection),见《北美评论》,1870年10月,295页。
(116) 皮克顿(J.A.Picton)对这个效果给予他的见解:《新理论和旧信仰》(New Theories and the Old Faith),18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