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的化学家》导读
袁江洋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010)
Chinese Version Introduction
在当代研究中,波义耳也不再只是作为一名杰出的化学家而受人关注,他更是作为17世纪英国实验哲学的设计者、倡导者、组织者与实践者而出现的。波义耳除了是当时一流的化学家、物理学家之外,也是热心的医学研究者,是虔诚的宗教家、神学学者,是英国皇家的重要组织者,是当时实验哲学的杰出辩护人。一句话,波义耳是现代科学道路的一位探索者与开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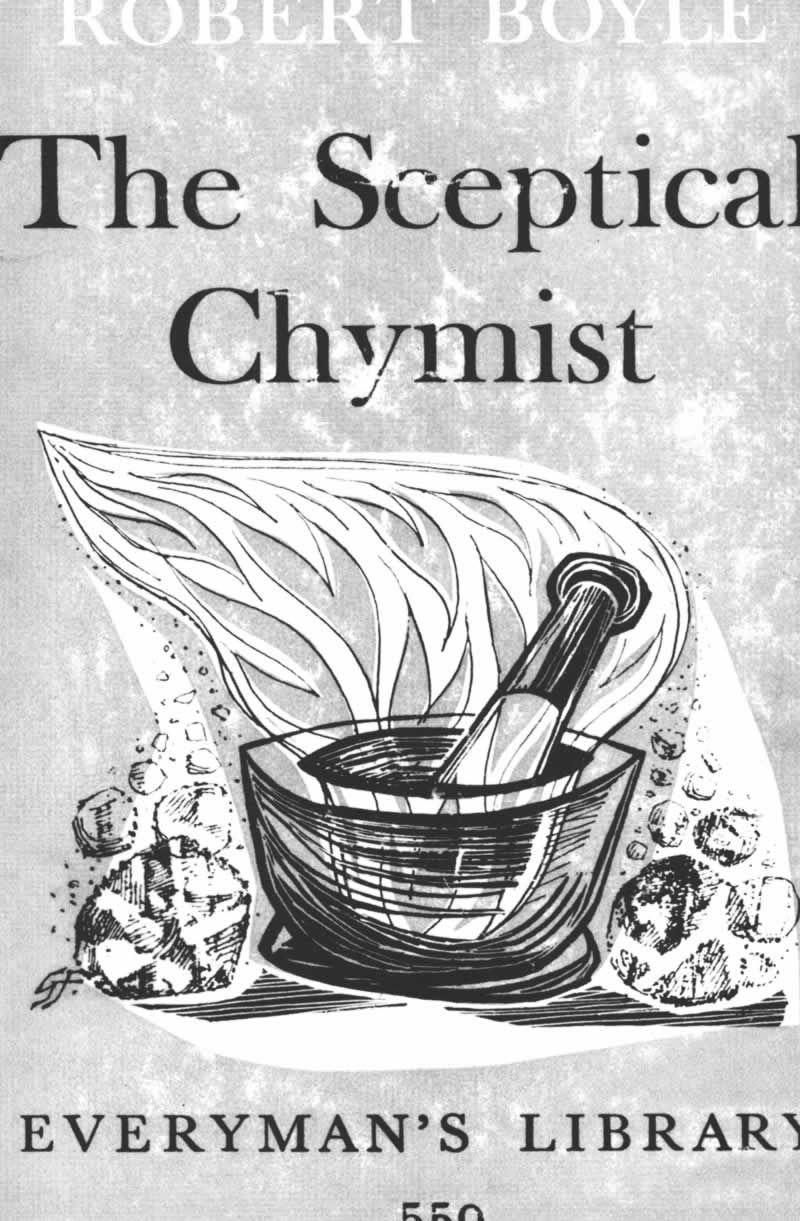
1911年出版的《怀疑的化学家》封面。
一、《怀疑的化学家》版本介绍和主要内容
怀疑精神是科学永恒的魅力的显现。“摧毁古人的全部自然哲学,并创立自然哲学学派的新学说”[范·赫尔孟特(van Helmont)语],恰恰是17世纪前后数代自然哲学家内心追求的真实写照。《怀疑的化学家》是被称为“近代化学的奠基者”的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 1627-1691)的一部代表作,它旨在以实验为基础摧毁一切旧自然哲学的物质学说(包括其同时代的化学家们所奉行的各种元素说、要素论以及元素—要素说)的不可靠的实验基础,其中也夹杂有他对物质之谜的构想,一种不同于以前的任何一种原子论或微粒论的构想——这种构想贯穿于其全部自然哲学(包括物理、化学、炼金术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之中。
本书英文第一版出版于1661年,但其部分内容早在1648-1649年间就写成了;1680年再版时波义耳作了一些增补,如书中“对后一文的序文”这一部分;拉丁文版始见于1677年。1744年,柏奇(T. Birch)将其收入他所编辑的《罗伯特·波义耳著作集》(The Works of the Honorable Robert Boyle );1911年,登特父子公司将其收入《人人文库》(Everyman's Library ),作为第559卷,并将其原有的冗长的书名The Sceptical Chymist or Chymico-Physical Doubts and Paradoxes,Touching the Spagyrist's Principles Commonly call'd Hypostatical; As they are wont to be Propos'd and Defended by the Generality of Alchymists. Whereunto is Premis'd Part of another Discourse relating to the same Subject 简作The Sceptical Chymist ,这是现在最常见的版本,本汉译本即是据此译出的。
《怀疑的化学家》是对话体的论战著作,是化学史上的一本“奇书”。在这本书中,“只有绅士才可被推荐为发言人”(见“对后一文的序文”);其行文方式委婉而繁复,超长的语句比比皆是,文章结构犹如现代计算机程序,“主程序”中有许多“子程序”。英国著名的化学史家柏廷顿(J. R. Partington, 1886-1965)曾说《怀疑的化学家》虽相当冗长,但是好读。
《怀疑的化学家》全书共分六部分,外加“序言”和“结论”等,所展现的是波义耳对当时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元素理论或化学家们的要素学说的质疑与批判。尽管它在表述微粒哲学见解时,在“用理智来衡度真理”时,显得十分犹疑,但它的批判,基于实验的批判,却是至为清晰的、锐利的。它虽没有促使17世纪的化学家们从整体上接受微粒哲学的思维模式,但却使他们感到了震撼。
二、波义耳生平简述
1627年1月25日,波义耳(Robert Boyle, 1627-1691)生于爱尔兰的利斯莫尔(Lismore),他父亲科克伯爵一世(Richard Boyle)在英格兰及苏格兰均拥有大量财产,是一个通过自己的奋斗而受封为伯爵的新兴贵族。1635年,波义耳进入伊顿公学学习。1639年,波义耳和他的一位哥哥在家庭老师的陪同下开始游历、求学于欧洲各国,并被欧洲大陆的自然哲学、数学、医学、人文艺术与宗教传统深深吸引。1641年,他们来到意大利,在那里,波义耳读到了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于1638年出版的《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一书。这种以对话形式写成的著作,给波义耳留下了深刻的影响,20年后,《怀疑的化学家》就是模仿这本书的形式而写成的。
他曾打算学习医学,这或许是因为自幼身体羸弱;后又打算钻研他眼中的“最精密的科学”(the best science)——数学,但一次特殊的经历使他的注意力发生了转变。波义耳在一次出行中遭遇雷击而幸免于难,这促使他从此对宗教、道德生活产生高度关注。因此,在他的青年时代,在波义耳成为一名自然哲学家之前,他先成为了一名严于律己的道德家与虔诚而执著的宗教家。他探讨绅士的美德与操守,他思考个人的获救之路,并将他的想法写成论文公开发表。
1645年,波义耳居住在继承的祖传领地多塞特(Dorset)郡的斯托尔布里奇(Stalbridge)庄园。斯托尔布里奇庄园位于伦敦西南约百英里处,在这里,波义耳度过了随后10年里的大部分时间。波义耳阅读了大量哲学、自然科学和神学的书籍,并建立了实验室,牛津和伦敦两地的学者经常来这里聚会,探讨物理、化学方面的学术问题。也正是在这10年里,波义耳接触到后来他将之称为“无形学院”的学术圈。他最初是以道德家的身份介入此一学术圈的,他的一生从未放弃对道德问题的关注,然而在与著名的教育科学家哈特利伯(Samuel Hartlib, 1600-1662)等人交往的过程中,他对自然哲学(科学)再次发生浓厚兴趣。(医药)炼金术开始成为他关注的研究领域,这固然与哈特利伯等人关心炼金术有关,与波义耳本人历来体弱多病有关,更与他确立自己微粒哲学并力图揭开物质之谜有关。1650年秋,美国炼金家斯塔克(George Starkey, 1628-1665)抵达伦敦,并迅速与喜爱炼金术的哈特利伯及波义耳等人建立起联系。波义耳宴请斯塔克到家中工作,并跟随他学习赫尔孟特派炼金术及化学,还建起化学炉,进行有关实验。此后,他再未终止炼金术实验。
1654年,波义耳患上重疾,后虽得治愈,但视力严重受损。随后波义耳迁居牛津。正是在牛津,作为一名年青、富有而慷慨、聪颖而有学识的绅士,他更加积极地投入了无形学院的学术生活,并开始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自然哲学方面。从一开始,波义耳就不但是学术探讨的参与者,而且是学术研究的赞助者与支持者。他经常在寓所里举行学术聚会。他拿出资金添置设备、聘请实验助手,进行各种实验。1659年,波义耳等人开始用胡克(Robert Hooke, 1635-1703)为他制造的空气泵做自然哲学实验。空气泵实验得出诸多重要科学成果,其中最著名的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波义耳定律”。1662年,经国王查理二世批准,无形学院正式成为“以促进自然科学知识”为宗旨的皇家学会。波义耳成为第一批最有影响的会员之一。
1668年,波义耳迁居伦敦,与他刚刚失去丈夫的姐姐莱尼拉(Lady Ranelagh)一起生活,直到1691年12月31日去世。
波义耳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大约一半论述神学,另一半论述自然哲学。后者主要涉及化学、炼金术、光学、空气泵实验、微粒哲学、医学以及自然哲学基础与方法论。1661年出版的《怀疑的化学家》是波义耳的主要著作。
三、波义耳的自然哲学蓝图:实验哲学
波义耳留给后人一条著名的“波义耳定律”,此外,他还被当做是现代化学的奠基者而加以颂扬。人们时常误将17世纪化学家所理解的、类似于今天的单质概念的元素概念归结为波义耳的建树,并以此为主要论据之一来论证“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这一命题,但实际上,波义耳只是为了提出对此类元素概念的批判,才特意先行予以归纳,使之明确化。那么,何以使他在化学史乃至于科学史上享有不朽的声望?
在当代研究中,波义耳也不再只是作为一名杰出的化学家而受人关注,他更是作为17世纪英国实验哲学的设计者、倡导者、组织者与实践者而出现的。波义耳除了是当时一流的化学家、物理学家之外,也是热心的医学研究者,是虔诚的宗教家、神学学者,是英国皇家学会的重要组织者,是当时实验哲学的杰出辩护人。一句话,波义耳是现代科学道路的一位探索者与开创者。
17世纪的英国是欧洲大陆自然哲学家心目中的有着“思想自由”的国度,尽管这里也并不是没有(宗教)狂热、偏执与压迫的一片净土。当时,摆在自然哲学新道路的探索者面前的两大问题是:如何在基督教社会、文化中为自然哲学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这首先意味着要处理好科学与宗教之关系),使之进入合法的知识体系,拥有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如何确立自然哲学的基本目标、方法与研究进路?
当波义耳开始走向自然哲学,他便开始了对科学与宗教之关系的思考,开始了对自然哲学的基础与方法论的思考。实际上,那个时代欧洲大陆及英国的科学先驱均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中世纪末以后,科学、神学双重真理论——两者均发诸于上帝,同为上帝的真理,因而应该是一致的,这种观点在欧洲大陆颇为流行;然而,当科学取得一定发展,它必定会与神学迎头相撞,此时,双重真理论式的科学辩护即会失效。法国的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在看清这种情形后决定放弃科学研究,专心致力于神学工作。意大利的伽利略则试图探寻将科学与宗教分开处理乃至于另解《圣经》的可能性,终而招致亚里士多德哲学及宗教卫道士们的攻击,遭受宗教法庭的审判。
在英国,在波义耳之先,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曾在其《新工具》中号召人们扬帆驶向知识的海洋,发展不受数学和神学点染、败坏的自然哲学,并认为这种自然哲学本身即是领悟上帝的一种方式;他还在其《新大西岛》中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科学王国的蓝图。17世纪早期及晚期的英国自然神论者提出了上帝在创世之后即不再干预世界的看法。剑桥柏拉图派的思想家们则发展了一种唯理智论神学,宣称上帝的理智而非上帝意志是世界的根源。相反,波义耳及皇家学会的创建者们则选择了以正宗的唯意志论神学世界图景为基础发展自然哲学的途径。
在此,我们可以用以下方式描述波义耳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他试图以自然神学为中介,在自然哲学与神学之间建立起桥梁,以期在基督教神学唯意志论的世界图景上建立起有坚实基础的、真正的自然哲学。若不能理解他的这种信念,则不可能真正理解他的全部工作的价值与意义,不可能理解波义耳其人及其思想。
波义耳说,“我将世界视为一所教堂,并据此陈述自然哲学”。在他看来,自然哲学家是这所大教堂里的牧师,他必须同时阅读自然与《圣经》这两本大书,他的责任是运用上帝赋予自己的智慧去了解上帝的创世意图及行为,并以此膜拜上帝。在方法论上,波义耳以下述方式赋予实验以崇高的地位:自然哲学家通过实验与观察来阅读自然之书,由此了解上帝深置于自然过程中的确凿信息——上帝的暗示;而在一时找不到明确的上帝启示及暗示之处(实际上,前沿的科学探索之处大都缺乏这类启示与暗示),则要“用理智来衡度真理”,并用实验来校准人类易谬的理智。
早期皇家学会接受这样的实验自然哲学,并通过推行这种哲学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这种自然哲学高度关注实验过程,但它也并不排斥理智的运用;它寻求科学与宗教乃至于与政治权力的和解,但从其基本特征来看,它毕竟是一种“实验”哲学,并非“协商”的哲学。
四、波义耳的化学/炼金术与他的微粒哲学
波义耳最终选择化学(chemistry)作为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在他已完成了他的空气泵系列实验研究之后。他的这种选择曾令他的一些从事自然哲学研究的朋友感到疑惑,因为在他们看来,化学还算不上(精密)科学,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技艺(art)而已。当时,Chemist一词既可理解为化学家,也可理解为炼金术士。但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炼金术,或者说化学,开始在波义耳这样的自然哲学家那里被纳入自然哲学的框架。波义耳宣称他要从哲学的角度理解化学,并要为之作终生的努力。
波义耳通过阅读机械论者、原子论者以及赫尔孟特派的炼金术哲学著作,早早地发展出了自己的物质理论——微粒哲学。这种微粒哲学的核心内容如下:一切物体乃由同一种粒子凝结而成;这种粒子由上帝所创造,它们是实心的,有大小和形状。它们本身没有运动能力,但上帝在造物时已将它们置于运动之中。这种同质粒子可凝结为“第一凝结物”(第一级微粒),继之,又可由“第一凝结物”凝结成“第二凝结物”,并通过进一步的凝结形成更复杂的微粒乃至于物体。因此,这种凝结过程的逆操作——炼金术操作,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用活性作用剂促使物体腐败、发酵,还原为最小的粒子,再植入“种子”使之按照新的形式凝结,即可使任何物质发生炼金术嬗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化学/炼金术作为实验性的探索与其微粒哲学发生密切关联,并被波义耳视为其自然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在波义耳眼里,化学与炼金术之间只存在着事后的区分:他的大部分实验是围绕炼金术的目的设计的,但如果确认这些实验失败,则这些实验就转化为化学实验,只具有化学实验的意义。
波义耳的微粒哲学并非是纯机械论式的物质理论,因为它不能脱离活性要素。波义耳时常被人们视为“17世纪机械论哲学的重建者”,但是,从一开始,波义耳就对机械论哲学持有明显的保留态度。在波义耳的许多著作中(包括在《怀疑的化学家》中),他多次指出世界上有许多现象是不能单用机械论来解释的。他认为,物质本身不具有任何活性与运动能力,活性与真正的运动必然发诸于上帝。因此,在设想完整的宇宙论时,必须考虑活性原则,必须考虑上帝的作用。波义耳在《怀疑的化学家》一书中也谈到“坦白地说,我完全不能想象,从质料出发,仅仅令其运动而不再管它,怎么能够出现像人体和完善的动物体这样巧妙的构造物,又怎么能够出现像生物的种子那样构造更为巧妙的物质系统。”
以往,时常有人根据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现代划分,将波义耳的微粒哲学说成是脱离科学实验的、纯粹的形而上学,不具备任何科学意义。他们认为在波义耳那里,成功地将其微粒哲学与科学实验(包括炼金术/化学实验以及空气泵实验)完美结合起来建立适当的科学解释的范例是并不多见的。譬如,波义耳在描述空气弹性时虽然提出空气的微粒类似于微小弹簧,但他并没有进一步阐述空气微粒的内部构造及其与空气弹性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在空气弹性与他所说的最小粒子之间建立起合理的联系。但是,17世纪时,并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科学与形而上学之划分。那时的科学(自然哲学)也不等同于今天的科学,它们在其内部学科构造上、在方法论上乃至于在研究对象上均存在着差别。波义耳的微粒哲学,与其炼金术(化学)、光学、空气性质研究及其他空气泵实验,均同属于一个完整的自然哲学思想体系,而且这些思想又与其自然神学以及神学思想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
五、波义耳是否把化学确立为科学?
我们常常见到这样的评价:“波义耳确立了化学元素概念,因此他把化学确立为科学”。然而,如前所述,通常所说的“单质”元素定义并非波义耳的创造,或者说,他非但不是此概念的始创者,而且是其怀疑者与批判者,此点已在数十年前为科学史家澄清。这样,我们就需要作以下追问:在波义耳那里,到底有没有他自己的元素概念?
我们必须看到:
(1)是波义耳将“单质”元素概念从当时专心于“结合物的火分析”的化学家们的工作中抽提出来,并在《怀疑的化学家》一书中予以概念化,尽管他是为着怀疑与批判的目的而将之概念化的。
(2)波义耳在论证他对此概念的怀疑的过程中,在列举许多结合物(在概念上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化合物与复合物)分析实验(这种实验是要将种种结合物分解成亚里士多德派的水、土、火、气四元素或当时化学家们所说的盐、硫、汞三要素,其中所说的元素或要素均是指物质类别而言的。基于这类分析,化学家们又在盐、硫、汞之外增加了精、油两个概念(请读者不要将这里所说的硫、汞与现代元素表上的元素硫、汞混同)。譬如,当分析矾矿得到某种油状物,他们就说该油为矾的油,简称矾油,即现在所说的硫酸。后来,波义耳最终将视线转向了黄金(在当时化学家眼中,黄金是一种结合物)。而且,波义耳充分认识到,黄金在许多通常的化学过程中保持稳定,从这些化学分析中既分不出金的盐,也很难分出它的硫与汞。因此,他以让步的语气说,金是最合乎化学家们所说的、由他本人所概括的“要素”概念的物质(尽管当时人们认为金是一种结合物)。但是,波义耳始终趋向于相信,在真正的炼金术操作中,金可以被成功嬗变。因此,他趋向于认为金也不是不可嬗变的“简单物质”,故不能说是“元素”。反过来说,倘若他对炼金术嬗变失去信心,那么,金就将被认为符合这种元素概念的一种元素。
(3)波义耳的微粒哲学不同于伽桑狄(P. Gassendi, 1592-1655)或查尔莱顿(W. Charleton, 1622-1689)的原子论。原子论将物质的化学性质直接与物质的基本组成部分(即原子)关联起来,而波义耳的微粒哲学则不同意此种做法。波义耳认为,物质的基本组分只有一种,即他所说的“同质粒子”(这与炼金术里“万物同根生”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些粒子有大小、形状,并且上帝已经将它们置于运动之中(运动与活性只能来自上帝)。后来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7)进一步发展了波义耳的微粒哲学,他补充说,这些粒子有质量,它们之间有力在起作用。波义耳以及牛顿的物质理论均是某种物质层系理论,有别于将化学性质与原子直接挂钩的原子论。波义耳在《怀疑的化学家》中没有就其微粒哲学作完整而规范的叙述,但他曾在其他多处解说并运用这种思想。
(4)波义耳和牛顿均在理论上清楚地知道化学操作与炼金术操作之间的界线。按照波义耳的微粒哲学,炼金术操作是指破坏最大的微粒的结构并使之还原为最初的组成粒子的操作,而化学操作则是指最大微粒的直接组成微粒之间的破裂与重组过程。
(5)在《怀疑的化学家》一书中,波义耳甚至曾从其微粒哲学的角度考虑过元素问题,并且以某种方式考虑过“元素性的微粒”的概念。说得更清晰些:假设组成结合物的微粒是由“元素性的微粒”组成,但这种所谓的“元素微粒”仍有其自身的组成与结构(它们是由最基本的同质粒子凝结而成的第一凝结物),并且它们的结构相当稳定,可以在化学过程中保持不变。说它们像是“元素”,是因为它们具有一定稳定性,是用于构成复合物之微粒的材料;而且,如果是这样,它们的数目就绝非像当时的逍遥学派人士或化学家所说的那样只有三五种,而一定会有很多种。但是,它们又称不上“不可嬗变的”元素,它们由最基本的同质粒子构成,其结构虽然相当稳定,但在真正的炼金术操作中其结构仍可被破坏,从而还原为基本的同质粒子,继而能以其他形式逐级凝结,成为其他物体。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波义耳和牛顿思想的深度与创造力,他们的微粒哲学在今天看来可大致算做是一种物理式的基本粒子论,化学性质只是与“最大的粒子”相关;而且,这种学说在理论上承认原始粒子组成的各级微粒(第一凝结物及以下)具有不同程度的稳定性。他们的微粒哲学思想随着他们的著作(如《怀疑的化学家》与《光学》)而传承于世,因此,这些思想也穿透了时间的阻隔,对现代原子论与现代元素嬗变研究,对结构化学的兴起,乃至于对基本粒子物理学与原子核化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事实上,在16、17世纪的那些杰出的自然哲学家中,也不乏否认原子论者,如培根、伽利略均不认同原子论。波义耳所提倡的以微粒哲学为背景的化学研究,并没有在当时以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化学家们当中得到拥护并由此成为化学研究的主流传统。他的化学著作,包括《怀疑的化学家》在内,并没有得到那一时期化学家们的充分解读与利用;相反,成为化学教科书的倒是要素论化学家们的著作。
综上所述,波义耳的确要求要将化学/炼金术作为哲学来看待、来发展,但他所提出的化学研究纲领并不像他所提出的自然哲学总纲领那样有效地为其同时代人所接受。在这种意义上,还不能说波义耳将化学确立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尽管他在思想上远远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化学家们。
六、关于波义耳的著作风格
波义耳的大部分著作都不易解读,原因是多方面的。波义耳是一位绅士型的写作者,他的著述保持着17世纪英国绅士作家的言谈风格,并体现着近代早期英语著作的某些典型特征。这样一种写作风格是由曲折的超长文句、精心选择的隐喻以及其他各种修辞手法复合而成,它可以用极为详尽的方式表达繁复纷纭的思想或重峦叠嶂的文意,但在一般读者的眼中,由此写成的整个著述却显得难以解读。波义耳的那位最为杰出的同时代人,那位“来自林肯郡格兰瑟姆镇伍尔索普村的少年”,后来的“艾萨克·牛顿爵士”,就不曾以这样的方式写作。在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和《光学》中,人们找到了现代科技论文的最早的文体模本,找到了精确的概念、严密的逻辑、简练的论证以及被动语态句子——所有这些,在波义耳的著述中却并不多见。
波义耳自1654年起患有严重眼疾,这使他不得不采用口述加秘书笔录的形式进行写作。在口述过程中,他会不断地插入或增加从句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说明文字以说明他想要述说的思想、概念。而且,波义耳著作的写作周期往往很长,最后出版的著作大多是在初稿完成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在著作初稿完成之后,波义耳会按照他的习惯不断地进行修改或重写,直到著作正式开印为止。这便使他的著作更显得歧途密布,思维若断若续;同时,也使其著作的前后不同版本在文字乃至于思想上出现一些差异。
波义耳素以“实验哲学家”自称,然而,他的许多实验是由他与他的实验助手共同设计并完成的。在他的实验生涯里,他通常都雇用数名助手进行各种实验。早期英国皇家学会的两位秘书,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 1635-1703)与亨利·奥尔登伯格(Henry Oldenburg, 1618-1677),早年都曾协助波义耳进行科学实验研究。由于波义耳所依赖的大量的、直接的实验记录也并非出自他本人,因而在科学写作中,他必须对实验进行系统的重新陈述。这样,波义耳与他的实验助手观察、理解实验的角度之间的细微差异,也可能导致最后的科学论述在写作思路与文字表达上出现涩滞。
波义耳的思想既宽阔、深邃,又时常变动不居。作为人类思想的勤奋的思索者与探索者,波义耳在他所涉足的各个领域,必然面临着形形色色的不确定性与疑惑。因此,他通常以相当谨慎、犹疑而委婉的方式表述自己的见解,一般不肯以确切无疑、不留余地的口吻将他的思想以及他所形成的最后判断(即使有的话)公之于众。在《怀疑的化学家》这样的对话体著作中,波义耳式的犹疑表现得更加明显。卡尼阿德斯也并不等于波义耳本人,尽管在许多场合下,他的确扮演了波义耳的代言人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