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Ⅲ 笛卡儿的方法论和Regulæ
管震湖
Appendix Ⅲ
我可以大胆地说,我真有很大的幸福,自我幼年以来,我已寻到几条道路,领我到学问与公理的研究,由此我形成一种方法,借这种方法的帮助,渐渐增加我的知识,日积月累,此种知识竟达到最高点,几为我孱弱的能力与短短的生命所难于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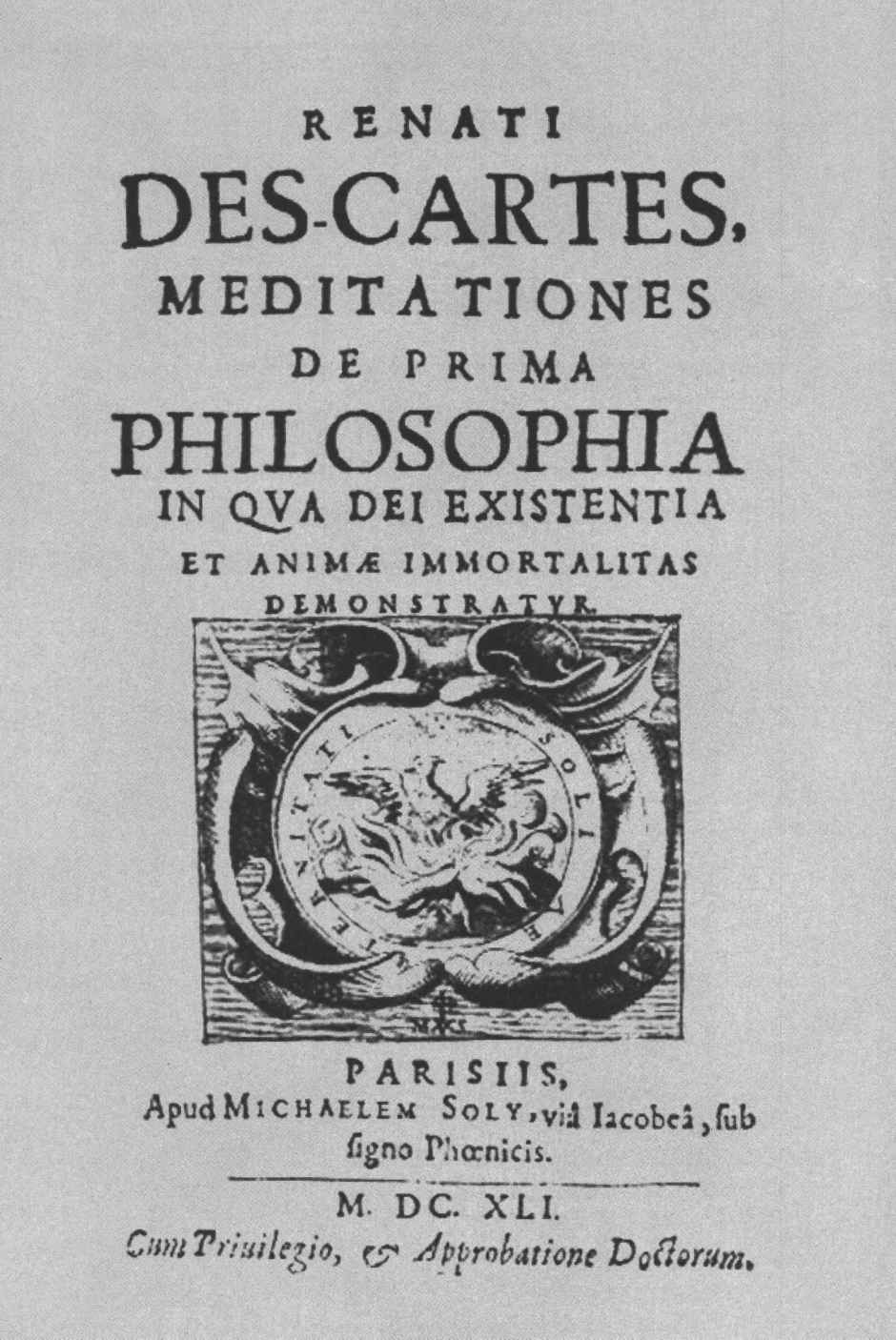 1641年出版的笛卡儿《第一哲学沉思集》的扉页
1641年出版的笛卡儿《第一哲学沉思集》的扉页
任何方法都是为体系服务的,虽然屡见不鲜:体系是荒谬的,方法却是卓越的或颇有可取之处。这就是说,方法既依存于体系而又有其独立性。
“Naturæ mysteria componens cum legibus Matheseos,utriusque arcanaeadem clavi reperari posse aussus est sperare”(“他比较了自然奥秘和数学法则,大胆希望两者的秘密可以用同一把钥匙解开”)——《笛卡儿墓志铭》。既是哲学家,又是自然科学家、数学家,笛卡儿力求以他的体系把自然科学和数学这两个互相依存而又互相有别的领域结合起来,用玄学思辨把二者统一为一个模式。这是一把钥匙,他的方法论探求的就是怎样才能掌握这把钥匙,意图教给世人的也是如何运用他所认为的这把万能钥匙。事实上,假如我们识破了并且把握住这个特异之处,也就是掌握了笛卡儿方法论的奥秘。
笛卡儿坚持人类知识统一性的观点,在《哲学原理》 (1) 的序言 (2) 中指出:“亚里士多德派经院学者认为,数学来源于其纯形式的确定性,在以具体广延为依据的[其他]学科中是不可达到的,所以每一学科的方法必须适应该学科所研究的题材之不同而且随之变化”,而他反对这种看法,于是提出了他对知识谱系的见解:“整个哲学好比一棵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形而下学,树干上长出的树枝可分三大类,即,医学、力学和伦理学——我说的是最高级最完美的伦理学,它以充分掌握其他科学为前提,构成最高智慧。”他解释说,这种普遍的科学一致性将显示出来,那就是,“把单一的同一方法不断运用于种种不同的学科,因为这种共同适用的可能性和实践性,意指:整体的科学无非是人的理性本身的统一性”。这个理性,既不言而喻地支配着他比做树根的形而上学,也理所当然地支配着由这个树根上生长出来的树干——形而下学;这个思维着的实质、这个独一无二的认识力、主宰着人这个复合体的心灵,就是笛卡儿体系的依据和实质内容,因而也是笛卡儿方法服务的对象。
但是,方法一经确立,它自身的发展——只要它不是胡拼乱凑,欺世盗名,只要它确实遵循严谨的确定的逻辑推演系列,堪称一种方法论而无愧,那么,往往不一定始终准确依据体系为它规定的轨道,它甚至可以与它原来的出发点背道而驰。雅典娜一旦从她父亲宙斯头脑中全副武装蹦了出来,她的生命归她自己所有,证实她的力量的是她自己的行为。
唯心主义体系需要的方法,理应适合保卫体系的根本要义,即,精神、思想、观念是第一性的。但是,正如恩格斯在体系和方法的关系问题上,关于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所说的:“在这里问题决不在保卫黑格尔的出发点:精神、思想、观念是本原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自然辩证法》,《马恩选集》第三卷第469页)。为什么呢?恩格斯解释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同上,第469—470页)。
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笛卡儿在他的形而下学领域和他所认为的普遍科学——数学,更确切说,马特席斯领域内,正是从既有的事实出发,根据当时已有的条件,按照“存在于事物本身的秩序”,或者按照“我们凭借思维巧妙铸造的秩序” (3) ,通过奋勉努力,探求得知某些真理,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作为严肃的思辨家、深刻的思想家,笛卡儿也尝试在哲学领域内以同样的方式,作出同样的努力,探求不仅仅是个别真理,而是达到真正符合上述两种秩序的普遍真理。但是,我们看见,他是如何削足适履,强要自然万物秩序顺从他作为玄学家的专断安排,不仅在体系上造成无法弥补的缺陷,而且在方法上不时陷入形而上学(不是他所使用的那个意义)的泥淖。
尽管如此,笛卡儿仍然不失为近代哲学中(就是说,在许多方面继承了古代哲学思想的中世纪以后西方哲学中)“辩证法的卓越代表”(《反杜林论》,《马恩选集》第三卷第59页)。这样说,当然不单单指他在自然科学领域内不可避免地使用了辩证法而且卓有成效。
笛卡儿和培根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一致宣布:我们自己就是古人!他们与当时的以及以后的一切哲学革新家一样,要求砸烂已经陈腐的使人窒息的法则桎梏,使我们的睿智从任何成见定规中解放出来,只依从理性光芒的指引,去探求事物的真理。理性的现实光芒不是指向早已作古的先哲,而是指向现时的权威,首先指向那些发展古人遗训中反动方面并且使之成为僵死教条、甚至成为可以使人肉体消灭的刑律的经院哲学。是从十六、七世纪开始显露光芒的理性主义敲响了僧侣思想体系的丧钟!再以后,经过十八世纪狄德罗等伟大唯物主义者的努力,终于埋葬了这种“枯燥的、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恩格斯)。
就我们涉及的范围而言,我们特别要注意他在认识论和方法论 (4) 方面辩证法运用的实例。
那么,笛卡儿这两方面的特征是什么呢?它们在哪些地方表明:笛卡儿论自觉与否,也出色地运用了辩证法?又在什么地方表明:他在哲学体系上坚持的反科学立场和观点阻碍着他的方法,使其终于不能形成完善的科学方法?
一、笛卡儿在晚年的一封信中,回顾他二十三、四岁学习和研究人生时说:“几何学家达到最困难证明时使用那些简单容易的推理系列,当时已使我想象:人类认识的一切对象都是这样互相依存的(《方法谈》中重复了这几句,此处作‘互相联系’),只要我们力求避免作出错误的推断(作:‘只要我们拒绝接受任何不真实物为真实’),遵守一事物至另一事物前后相继的秩序(作:‘坚持由一真理至另一真理演绎所需的秩序’),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远不可及,也没有什么东西隐而不露不为我们发现”。他在其他地方还提出,是人的bona mentis(良知)在一切科学之间确立完美交流的;又说是,各门科学好似同一物的各个多变的面貌,彼此却相似,因为它们都首先依存于单一人类心灵。
Connexio scientiarum(科学之间密切联系),是笛卡儿一贯的思想。笛卡儿幼年和少年时期在耶稣会神甫督导下广泛涉猎各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其中尤其是逻辑、哲学和数学的研究,以及以后他深入“研读世界”和展开自然科学众多学科的研究,使他不断发现这些学科之间的联系,得出了科学之间密切联系的结论。为求他哲学体系的完整,他进一步认为,人类认识的一切领域构成的一个整体,统统受唯一认识力(vis cognoscens)即理性的支配。
开宗明义,他在Regulæ中首先指明:“研究的目的,应该是指导我们的心灵,使它得以对于[世上]呈现的一切事物,形成确凿的、真实的判断”(原则一的命题全文)。根据他在下文中对这个头道命题的阐述,这就是说,不可以把我们考察的对象,包括自然科学各门对象,割裂开来逐一研究,而应该看到一切科学彼此密切联系,“把它们统统完整地学到手,比把它们互相割裂开来,更为方便得多”。“因此,谁要是决心认真探求事物真理,他就必须不选择某一特殊科学:因为事物都是互相联系、彼此依存的”。正是如此!只要我们不为形而上学的“迷人障碍所困扰”,我们在科学研究中,在对一切事物观察和认识中,“从了解部分到了解整体、到普遍联系的道路”就不会堵塞 (5) 。
笛卡儿从直观察知:一切事物自有一种安排,他称之为秩序或度量。据他在《方法谈》中解释,这种ordo naturalis(天然秩序)就是一切客体彼此之间自然互相联结的秩序;探求事物真理,也就是按照这种秩序,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性。这说得多么好呀!
然而,为维护他的唯心主义体系,这个天然秩序变成了他那个上帝安排的结果。无论他怎样对他的上帝给予理性的解释,他心中构想的世界仍然是本末倒置的世界。他从神学词汇中借来的ordo vel mensura(秩序或度量),恰恰适用于他的体系:事物的天然秩序成了先验的观念,这个观念反过来又产生万物秩序。辩证法的光辉锋芒就此消钝,形而上学倒显示出它禁锢人的力量。
卓越的自然科学家笛卡儿不能不察知:“我们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借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说法),但是,由于当时自然科学尚处于不发达状态,也由于笛卡儿自己的形而上学推演和列举(即归纳),他接受了自从古希腊以来科学家和哲学家(这两者往往是一身而兼之,与我们现代不同)的一种错误的见解,即,存在着一种科学之科学,“某种普遍科学,可以解释关于秩序和度量所想知道的一切”,它不是研究某一学科的专门对象,而是“凡其他科学涉及的范围,它都涉及了,而且只有过之”(原则四);我们知道:笛卡儿这里所说的“其他科学”不单单是当时几乎无所不包的数学项下各学科,而且实质上就是心灵探求的一切对象。这个东西,就是既为普遍科学、又为普遍方法的Vera Mathesis(真正马特席斯)或名Mathesis Universalis(普遍马特席斯)。然而,这种科学之科学是不存在的;在笛卡儿而言,它被构想出来,只是为了使他在本论文开宗明义提出的探求一切事物真理成为确凿有据的体系。
是的,必须看到“事物都是互相联系、彼此依存的”(原则一),也必须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去认识各事物之间真实发现的秩序、或者我们依据正确判断而获知的秩序,从而尽可能全面地从整体上掌握事物的普遍内在规律。但是,无比丰富的客观辩证法绝不是任何马特席斯所能概括的。即使仅就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而言,哪怕我们承认马特席斯具有普遍指导原则的总和的价值,它也不能代替对于特殊事物的具体研究。笛卡儿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原则八中假设有一人仅仅研究数学,此人“试作一直线:屈光学上称为光折线的直线……”,他会发现“该直线的确定取决于反射角和入射角的比例;但是,他没有能力继续探讨下去了,因为继续下去就超出了马特席斯的范围,而涉及物理学了,他不得不就此却步,停留在门槛上,而无可奈何……”原来,马特席斯甚至不能适用于也存在着秩序或度量的物理学。于是,笛卡儿只好回过头去,重新提出作为认识过程的起始的悟性,重申“只有悟性才有真知能力”,“先于悟性而认识是绝不可能的”(原则八)。那么,结论是什么呢?仍然是维护他的体系,指出问题在于“我们心灵的限度”,告诉我们说:在充分掌握了他的整个方法之后,“运用心灵去认识某一事物的时候”,会遇到两种情况:或者是我们认识了它,或者是我们还是不能认识它,而后一种情况或是由于尚未有必需的经验,那就不是自己心灵的过错,或是由于“所求之物超过了人类心灵所及”(原则八),那也不是人类心灵的过错。这样,笛卡儿也就否认了他自己实际上主张过的我们的认识不断加深,在无限时间系列中不断接近绝对真理的可能性。
笛卡儿自己举出的这个例子还说明普遍与个别、一般和特殊之间另一个辩证关系。那就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明白指出的:“只有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了解现实的因果关系。为了了解单个的现实,我们就必须把它们从普遍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且在这里不断更替的运动就显现出来,一个为原因,另一个为结果”(《马恩选集》第三卷第552页)。这就是说,第一,原因和结果这一对对应项之相互作用是一个普遍的一般的概念,我们据以了解现实中呈现的一切因果关系:平行光线经折射(因),交叉于一点而为光折线(果),正是应该从普遍的相互作用(联系)出发去考察,所以,笛卡儿发现:入射角和反射角之间的比例还取决于其他若干因素,进而他认为:“必须知道一般自然力是什么”;第二,要了解单个现象中的原因和结果,虽然要放在普遍联系中去考察,但确切地解决问题(笛卡儿称之为“困难”),仍须“把它们从普遍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笛卡儿对该比例,进入其特殊领域即物理学中去考察,正是这样做的;因此,第三,我们的认识既是从个别和特殊归纳为普遍和一般,又是从普遍和一般演绎到个别和特殊,这里也是不断更替、交互作用的;原因和结果上是如此,其他事物(或者使用笛卡儿所称的“项”这个词)也是如此。那就不能如笛卡儿那样,虽然认为原因和结果是对应项,也说“它们的性质确实是相对的”,却从只承认原因在二者中是绝对项出发,进而否认它在普遍联系、相互作用之中也是其他原因的结果;也不能像他那样,虽然把他所说的列举,即归纳,提出作为演绎的对应项,作为与演绎同等重要使真理臻于完善的方法,实际上却告诉我们:二者相较,绝对的是演绎,相对的是归纳,根本的手段是演绎,归纳只是辅助的手段 (6) 。由此可见,笛卡儿所说原因、独立、简单、普遍、单一、相等、相似、正直等诸如此类之物作为他所谓的绝对项,结果、依附、复合、特殊、繁多、不等、不相似、歪斜等诸如此类之物作为他所谓的相对项 (7) ,不是现实的生动的辩证法的概念,而是虚幻的死滞的形而上学的概念;而演绎和归纳被排除在他的互相联系、相互作用之处,也就丧失了它们在即使笛卡儿体系中也可以起到的“使真知臻于完善”的作用,尽管它们分别地孤立地运用——他主要还是运用演绎——可以发现某些片面的真理。归根到底,这是因为笛卡儿念念不忘他的体系中的最绝对项,即某种或某些从真实逻辑系列中脱离(他又称之为“抽象”)出来的先验观念,恰恰扔掉了或者说忘掉了他探求的宗旨:依据事物的实在秩序去找到事物真理。
就他的自然科学研究而言,情况也是这样。这里面既有笛卡儿本人坚持体系、因而蓄意为之的原因,也有当时整个水平使然的原因。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关于古希腊人的辩证思维发表的一段评论是颇有意义的。他说:“在这里辩证的思维还以天然的淳朴的形式出现……在希腊人那里——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还被当做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这种联系对希腊人来说是直接的直观的结果”(《马恩选集》第三卷第468页)。在笛卡儿,他的天然淳朴形式(固然比他的前辈古人还要高级一些的形式)的辩证思维,更多的是一个严谨自然科学家不得不然的思维,而且时常受到形而上学的困扰以至破坏,同时,他也没有进步到足以深入自然界细节的程度,即使在他所擅长的几门学科中限于当时一般水平,他也没有达到足够解剖、分析的程度,只能从总的联系上去予以理解,于是总的联系也就难免笼统含糊,甚至脱离了考察对象的实际而成为仅仅产生于哲学家头脑中的玄学思辨的概括。
二、笛卡儿说,在一个“完满的宇宙”(Universum plenus,意即为理性所支配的宇宙)中,运动可以无须通过星体的物质移动而直接扩散直至我们,犹如在一根盲人拐杖之中;光,是从构成太阳和恒星的初质(elementum primus)发射的运动,更恰当地说,是发射的“运动倾向”(《折光》);这种“火质”,世上最精致、最活跃、最有穿透力的质,同天和地的区别(天和地是第二质和第三质)只在于“运动、厚度、形象以及‘火质’各部分的排列”(《论世界》);火质,由于“自身运动的不可阻挡性”,可以辐射至一切地点,沐浴一切物体(同上);它的作用(actio)以一种无限的、瞬间的、直线的运动,透过天的物质“一阵又一阵地”传导(同上);它的射线可以合、分、交、阻、屈、缩、增、减;这些射线触及物体,其运动就机械地迟缓或加速,屈曲或收缩,就像玩球的人扔掷的球一样(同上以及《折光》);它们到达我们的眼球时,就在我们的身体器官中延续为一种神经网运动。
这大致上就是笛卡儿精细缜密观察自然现象为人们感知这一过程而获致的结论,也是他从他所重视的实验以及经验中形成的宇宙观的一个方面的简单陈述。这里涉及的是我们认为存在于我们心外、他认为物归于心 (8) 的客观世界。那么,这个客观世界是怎样作用于我们的主观世界呢?
原则七的命题是:“要完成真知(又义:要使真知臻于完善——引者),必须以毫无间断的连续的思维运动,逐一全部审视我们要探求的一切事物,把它们包括在有秩序的充足列举之中”。这种“连续的思维运动”(他又称之为“频繁重复的思维运动”)之所以必要,笛卡儿在该原则和原则十一中解释说,是为了把所研究的对象通观始终,极为迅速地从始项看到末项,几乎不留任何一项在记忆里,而是仿佛整个一下子察看全事物。
笛卡儿确实不是把我们的认识过程看做一次完成的、固定不变的静止现象,而是看做连续不断、反复加深的运动过程。在本论文中未及充分阐述,但在其他著作中多有涉及,尤其在研究人的生理心理活动的各专著中更有详尽的描述。这些无疑也是卓越的思想和运用。
我们知道,笛卡儿正确地认为人的认识过程开始于感觉。他尤其重视其中的视觉(他表述为“直观”的感觉起点,直观与视觉的关系,可以参阅《附录一:关于直观》)。这是因为他所理解的物质运动只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局部运动,即位移)。唯有一种运动不受此限,那就是光的运动。这当然是超出了当时的自然科学水平,是一种卓越的猜想;但是,如果我们说他把物质运动实质上等同于光的运动,那也不为过分。这就无怪乎他那样重视视觉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了。
(局部运动,即位移)。唯有一种运动不受此限,那就是光的运动。这当然是超出了当时的自然科学水平,是一种卓越的猜想;但是,如果我们说他把物质运动实质上等同于光的运动,那也不为过分。这就无怪乎他那样重视视觉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了。
他在《论人》、《折光》、《激情论》中是这样说的:光的运动作用于我们的眼球之后,引起视肌肉的活动,使眼球按照景象的距离、亮度、方向等等自动调节;物体发出的光线从瞳孔进入,穿透三种透明的体液,集结于视网膜,机械地作用于视觉神经;物体各不同点发出不同光线以不同方式作用于不同神经,就形成视网膜上的“画”,按照反射光的方式不同的颜色;最后达至大脑,使我们的灵魂得以构成种种不同的视概念。他着重指出,视像就是[客观]世界对于“思维着的实质”连续不断的“袭击”,造成扩散的震撼,在我们的心灵中“显示出宇宙机械运用,促请我们的心灵作出反应”。
笛卡儿认为,其他感觉不如视觉有用,也不及它那样为我们所知悉,但是,它们同样也是由于物体以不同方式作用于不同神经,在大脑内部由灵魂表达为感性认识。
经过这种种外在感觉,我们的肉体产生饥、渴、痛、痒等等,我们的灵魂产生喜、怒、哀、乐、爱等等,这些统统是由心灵的运动促成、维持和加强的。最后,他得出结论说,在变易不已的世界中,“种种运动就这样通过神经达至我们的灵魂,与之结合而成为一体的大脑的某个地点,使这个地点产生种种不同的思维,皆随各该思维的不同而异;就是通过大脑神经刺激而成的运动所直接产生的我们灵魂这种种不同的思维,我们恰当地称之为我们的感性认识,或者说,我们感官的认识”(《原理》四)。
正是如此,运动是“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移起直到思维”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恩选集》第三卷第491页)。不仅如此,笛卡儿还十分先进,甚至先于任何人(虽然不是以完善的形式)表达了宇宙中运动量守恒的见解(笛卡儿原理)。但是,第一,我们认为运动仅仅依附于物质,不是他所认为的依附于广延;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方式、物质的固有属性,不是他所认为的广延的方式、而从广延中却不能演绎出运动;没有运动就没有物质,没有物质也就没有运动(包括思维运动在内),也不是他所认为的没有广延就没有运动、而广延却是一个先验的绝对项。第二,宇宙万物的运动形式千变万化,虽然都与某种位移相联系,但是不能归结为简单位移,位移绝不能把有关的运动的性质和形式囊括无遗。第三,关于一切运动中最高级最复杂的思维运动,既然思维被他认为是一种没有广延的存在,那么,思维的运动与他认为的物质固有属性广延也就并无逻辑必然的联系(connexio)。那么,他所认为的实质即广延,要与他认为的方式即运动(这里是指他所描绘的思维运动)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实际上也就是要谈什么思维运动的话,就只有乞灵于上帝了,因为尘世间的任何联系都是不可能的。笛卡儿正是这样做的,用《原理》中的话来说,这个“上帝就是一切运动的初因(causa prima)”,“他”(上帝)不仅像牛顿所祭起的“第一次冲动”那样启动了客观世界,而且成为我们主观世界中一切运动(包括上述客观反映于主观的过程:作为切实探究人的生理心理过程的自然科学家,对这个过程笛卡儿无疑是相当正确地描述了的)的根本动力。
从辩证思辨最后总是归至玄学思辨,说明的是唯心主义体系的流产。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马恩选集》第三卷第421页)。我们可以说,早在黑格尔以前,另一大系即笛卡儿体系就已经流产了,无论他也曾像黑格尔一样“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同上),甚至在体系运用于自然科学方面做了更多的事情。
星移斗转,岁月流逝,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免除了当时出自蒙昧和迷信的私利纷争,更重要的是有了“极其彻底而且严整”(列宁)的马克思的观点,即辩证唯物主义为锐利武器,可以恰如其分地评价笛卡儿的体系和方法了。
笛卡儿仍然是伟大的思想家,尽管他的体系是彻底唯心主义的,他的方法每每最终陷入形而上学。他留下的相当完整的学说,构成人类知识、精神文明、心智成就的宝库的一部分,而且是特殊重要的一部分,固然我们必须从中剔除其糟粕,尤其要把他那个本末倒置的世界再颠倒过来。
勒内·笛卡儿差不多与弗兰西斯·培根同时,奋力挣脱仍然束缚着人们心灵的中世纪愚昧桎梏,他高举起理性主义大纛,向神学和宗教统治发出了严重挑战。虽然小心翼翼,向经院哲学和前此一切权威宣战的吼声仍然清晰可闻。他们既是第二代文艺复兴巨人,又是开创了远非古希腊罗马一切成就可以比拟的崭新时代的先锋战士。
Cogito,ergo sum!那就是说,不思,人则丧失其存在价值。如果是格言,这个格言要求的是:把一切拿来放在理性光芒的照耀下,重新审视、推敲、明辨并作出判决。即使在今天,在许多场合,理性反省和裁决仍然不失其现实意义。
勒内·笛卡儿像其他若干卓越自然科学家和严谨思辨家一样,在认识和总结客观世界运动及其主观反映的过程中,势所必然在这里或那里运用了唯一科学的方法,即辩证法,留下的大量个别范例今日看来仍然是光辉的。
一代宗师笛卡儿在哲学上的不朽贡献,不仅在于主要由他起始的理性主义敲响了黑暗统治的丧钟,而且由于历史辩证的发展,违反他的意愿,也违反他的哲学要义,源出了整整一派的法国唯物主义,仅就自然科学而言,也“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富”,“在机械的自然科学方面获得了卓越的成就”(马克思:《神圣家族》,《马恩全集》第二卷第160、161页)。
笛卡儿在自然科学若干领域达到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时代的限制:他关于血液循环的学说,人体生理心理的研究,以及差不多在伽利略同时大胆倡言地动说,都不是可以用任何理由加以忽视的;尤其应该提到他比康德还要早数十年蔑视创世说权威,勇敢地提出了关于宇宙形成的旋涡说。
笛卡儿尤其是极其出色的数学家。也可以说,正是他在几何学和算术方面有出众的造诣,他才与众不同地设想以数学方式解释和构想世界。固然这样做也是方法论上的一种流产,但数学大师的光辉仍不稍掩,例如,正是他把代数引入几何,进而“主要由笛卡儿制定解析几何”(恩格斯)。
顺带,我们要特别谈一谈笛卡儿作为数学家的贡献。
《方法谈》所附第三篇科学论文《几何》极有独创见地。他首先给予算术四则和求开方号为今日代数所大体上沿用。在该论文中他广泛使用了解析方法,用语虽然不像今天这样准确,但为公元1800年以后人们所称解析几何奠定了基础。
也是在那篇论文中,笛卡儿以代数方法解决了著名的帕普斯问题。他所使用的符号为今日代数大体上沿用。
笛卡儿创制了后世所称的笛卡儿坐标轴。
他关于他所称的几何曲线(今称代数曲线)的推断之准确,迟至1876年才由英国数学家阿尔弗雷德·B·坎普予以确证。
他巧妙地解决了他的一个学生提出的问题:“求一曲线含其正切某一属性”。这个问题属于积分而且导致一个对数。
他正确地区分了代数数和超越数,而且大致上看出不可能以根号解决大部分代数方程式。
作为数学家,笛卡儿的影响不仅及于当时,对于后世的莱布尼茨和牛顿也有重大影响。
我们不能不说,他在数学领域达到的空前成就表明:他把Regalæ以及《方法谈》等等中倡导的“技艺”运用到了极为“灵巧”(sagacitas)的程度。
此外,他在美学、诗学、语言学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在他身后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也都与他的方法论有关。
Regulæ是笛卡儿方法论三大著作之一:其他两部是《方法谈》和《凭借自然光芒探求真理》。他的传记作者巴伊叶认为,Regulæ比《方法谈》阐述笛卡儿方法更为充分、更为详尽,而后者只是方法论主要原则的概述;又说是笛卡儿自己就多次谈过这一点。不过,也有人认为主要由于Regulæ遗稿不全,比起《方法谈》来就较为逊色。笛卡儿的学生、好友克莱尔色列就不太重视Regulæ,甚至不愿把自己手中保管的手书遗稿拿去出版。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上述三部著作合在一起,再加上散见于他书信中有关方法论的议论,大致上可以得识笛卡儿生前关于他的方法所作文字表述的概貌。
Regulæ写作时间大约在笛卡儿离开法国最终前往荷兰 (9) 之前,一般把下限定为1628年,非常可能就是在那一年的冬季。其酝酿当在他1619年发生精神危机的时候。
据他后来在《方法谈》中说:“我花了几年时间研读世界这本大书(与学者的书相对照),这样获取一些经验,在这以后,有一天,我决定也要研究我自己,尽我心智的全力选择我应该遵循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想,我取得的成就是超过了假如我不离开故国、丢下书本的。这时我正在德国打仗……”
他经过苦思冥想,发现无论作为社会法则或者科学法则,单独一个思想家总比许多思想家构造出来的人类思想体系更好、更有系统,因此,从别人的书中构造真知不是最好的方法(这里我们不妨参阅Regulæ中相似的话)。这个独立创造者后来在一篇拉丁论文中说:“就像那些住在旧房子里的人,非至已经形成建造新房子去代替旧房子的计划的时候,是不会拆掉旧房子的,我也像这样首先考虑怎样才能够找到什么确定无疑的东西,于是花了很多时间寻找有什么真正方法达到我的心灵所能达到的一切事物的真理。”他回顾年轻时学过的学科,认为只有逻辑、数学以及几何学分析稍稍有用,然而,逻辑只能传导,不能发现真理,而且其中真伪杂陈、有用与可疑混淆,至于古人的几何分析和今人的代数,“姑且不谈它们只能用于似乎没有什么用处的抽象题材,前者过于局限于考察图形,后者受到某些规则和图形的奴役,变成了一种混乱而暧昧的技艺,只能困惑心灵,不成其为培育心灵的科学。所以,我想我们必须找出来某种其他方法,包括三者的长处,没有它们的缺点。”我们看见,在Regulæ中这个东西第一次被提出来,定名为“马特席斯”。
于是,他选择了四条逻辑原则(也就是所谓的Regulæ):第一,只承认完全明晰清楚、不容怀疑的[事物]为真实;第二,把一切困难都分割为若干因素(或若干组成部分);第三,从较容易的推至(或叫演绎)较困难的;第四,进行列举,寻求中项,同时考察困难问题各因素,以至任何东西都不遗漏。这些,我们看见,在Regulæ中做了进一步发挥。
这位探求真理者(或者说,探求达到真理的方法者)构造了许多原则,当时就加以运用,获得圆满结果,日后又把它们阐述在关于方法论的著作中。他特别满意的是:他觉得他的方法的原则不仅适用于数学,而且适用于一切事物。这时笛卡儿才二十三岁,但是,他以后学识增长,尤其是哲学思辨日趋成熟,研读世界所获经验更加广泛而深入,使他终于有资格提出了他的独特的方法论。正如他的密友夏努为他身后写的墓志铭中所说:“就是在那个休假的冬天,他比较了自然奥秘和数学法则,大胆希望两者的秘密可以用同一把钥匙解开。”他在方法论方面,决定今后尽毕生之力,努力掌握并教人掌握这把钥匙。1619年的精神危机是有积极成果的。
从1625年开始,笛卡儿在巴黎居住了三年 (10) 。与他交往的大多是科学家和数学家,他们之间的交谈和争论,对于“而立”之年的笛卡儿既是学习的机会,也促使他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思想,同时进一步坚定了信心:确信自己即将创立的方法是唯一正确的。
在与巴黎学术界人士的交往中,有一次,他驳斥了一个物理学家兼炼金术士提出的所谓理论体系,他当即说明还不能仅仅否定,而应该提供区分真理与谬误的标准,而且他还提出他自己就可以运用当时流行的论证方法证实任何谬误的任何真理。在场的人都大为赞赏,一致敦促他把这样敏锐观察、渊博学识的推理向公众贡献出来。这次的成功以及以后不断在交往圈子里获得的成功鼓舞了他,使他决心实现久已考虑的使用自己的方法建立一个新的哲学体系,积极的成果之一就是遗稿Regulæ。实际上,他想做的就是用积极的建树(而不是单单否定)去代替经院哲学。弗兰西斯·培根这个名字,对于笛卡儿而言,仍然只是意指否定,只是表明旧有的体系已经土崩瓦解,必须有某个新体系建立起来代替它。笛卡儿还认为,培根的实证主义实验过于松弛,也过于含糊,也就是说没有绳之以数学方法。培根的逝世中断了深入一步研究的工作。这个未竟任务必须由笛卡儿自己去完成,当然是以不同于培根的方法,也就是以见诸Regulæ和其他著作的方法。
他受到学术界朋友的怂恿,把种种想法写成一条条的Regulæ的同时,还在构思另一部著作(是论证上帝的存在的,大概是一种自然神学理论),而且忙于准备迁居国外,也许集中精力不够,致使本论文中留下了一些不很完善的地方,例如原则和原则之间繁简不一,或不够衔接,也有互相矛盾的,还有些陈述失之含混,有时又显得重复,有些文句表达不确切,留下费解的难点,原文为拉丁文,有人说有些拉丁词句语法不通,等等。不过,这些似乎都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作者想说的意思还是看得清楚的,况且,作者自己在原则四末尾也告诉了我们:“这本小册子”原本不是准备出版的,只是为了他自己日后备忘的,同时也是为了记录下来之后便于自己“转入其他题材的研究”。
Regulæ第一次出版是1701年,已在作者逝世半个世纪又一年之后。遗稿原在克莱尔色列手中,巴伊叶写《传记》时还查看过,以后却遗失了。幸亏,存下了两份抄本:一份原为莱布尼茨所有,现存汉诺威图书馆,世称汉稿或汉本(H);另一份在1701年曾被《遗著》编者使用为印行所据的蓝本,由于《遗著》出版于阿姆斯特丹,世称阿稿或阿本(A)。阿本比汉本完善得多。1897—1909年Adam和Tannery所编《笛卡儿著作》十一卷,采用的就是A本,被称为AT本。1977年法国学者Marion据AT本,参照以往几种法译本和荷兰译本,重新译为法文,这就是我们汉译文的依据。在汉译的过程中有些不明白的地方,对照过AT本拉丁原文;如有必要,日后当按照拉丁原文整个核校一遍。
AT本和法译本都只有二十一条原则,但莱布尼茨看过克莱尔色列手中保存的原稿之后说看了“二十二条有解释、有阐述的原则”。而笛卡儿本来的打算是写三部分,每部分各有十二条,那么合计为三十六条原则。大概是作者没有完成写作计划,现在我们见到的只有二十一条,而且最后三条只有命题而没有阐述。
原来计划的三十六条分为三部分,各占一册。第一部分从原则一至原则十二,要旨是准备我们的心智,训练我们的理性,使之可以进而研究简单命题;第二部分从原则十三至原则二十四,研究的是所谓完全问题,即各项已充分知悉、只是答案尚未揭晓的问题;第三部分从原则二十五至原则三十六,探讨不完全问题,并研究如何归结为完全问题。
笛卡儿写作这些原则本不是为了出版,所以并没有加上任何篇名或题目。是巴伊叶在他写的《传记》中使用了《指导心灵探求真理的原则》。A本作Regulæ ad directionem ingenii,H本作Regulæ de inguirenda veritate。法译者加上“有用的”、“清晰的”两个形容词,根据的是笛卡儿逝世后在斯德哥尔摩进行遗物登记中使用的名称,这个名称用的是法语。我们的汉译本为求书名的汉语、拉丁语、法语一致起见,合并了A本和H本的拉丁语,加上了两个形容词utiles和clari;法语书名书写当然是Marion给予的全称。这些称呼都很啰唆,也不符合现代人的习惯,同时鉴于笛卡儿自己并没有给原稿定个名字,所有名目均为后人所加(除上述四种书名以外,还可以举出十来种),所以汉译者斗胆予以简化,在封面上仅称《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这似乎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有点像巴伊叶初定的书名。至于简称,有时称Regulæ,有时称本论文,两者均从其他研究者的习惯。
————————————————————
(1) 这是一部专为女弟子波希米亚王室伊丽莎白公主撰写的教科书(讲义),1644年出版于海牙。
(2) 从拉丁原文第一个译为法文的是皮科神甫,笛卡儿的《作者致译者信》就是该著作的序言。
(3) 原则十。后者是指凭借笛卡儿所提供的正确方法推演而知的秩序,说的是事物秩序本身不能自行呈现的时候。
(4) 对笛卡儿本体论的剖析在这一长篇论文的前一部分,从略。
(5)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6) 参阅原则五、六、七关于列举,以及头几个原则中关于演绎的论述。
(7) 原则六。
(8) 译者认为笛卡儿不是二元论者,而是唯心主义一元论者,他的唯心主义而且是彻底的,这个见解已经口头表达和文字发表,这里不再赘述。
(9) 1621年冬笛卡儿浪游至荷兰海牙,对以后他将长期寓居的低地之国有了良好的印象。1629年春他又由法国北部抵达阿姆斯特丹,从此以后,除了短暂离开以外,在那里寄寓至1637年,以后选定了更为幽静的乡村——荷兰北部的比嫩的埃格蒙德为退隐归居之地。逝世前数月应瑞典女王之请前往斯德哥尔摩向她讲授哲学,1650年在那里病故。
(10) 其间,他第二次去当志愿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