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科学与道德
(1886年)
· Science and Morals ·
(灰姑娘)发现,这个貌似混乱的世界渗透着秩序;进化这部宏大戏剧,既充满遗憾和惊惧,又充满善良和美丽,一幕一幕在她眼前铺开。她在内心深处记下这一教训:道德的基础在于坚决不说谎,不假装相信没有证据的东西,也不转述那些对不可知的事物提出莫名其妙的命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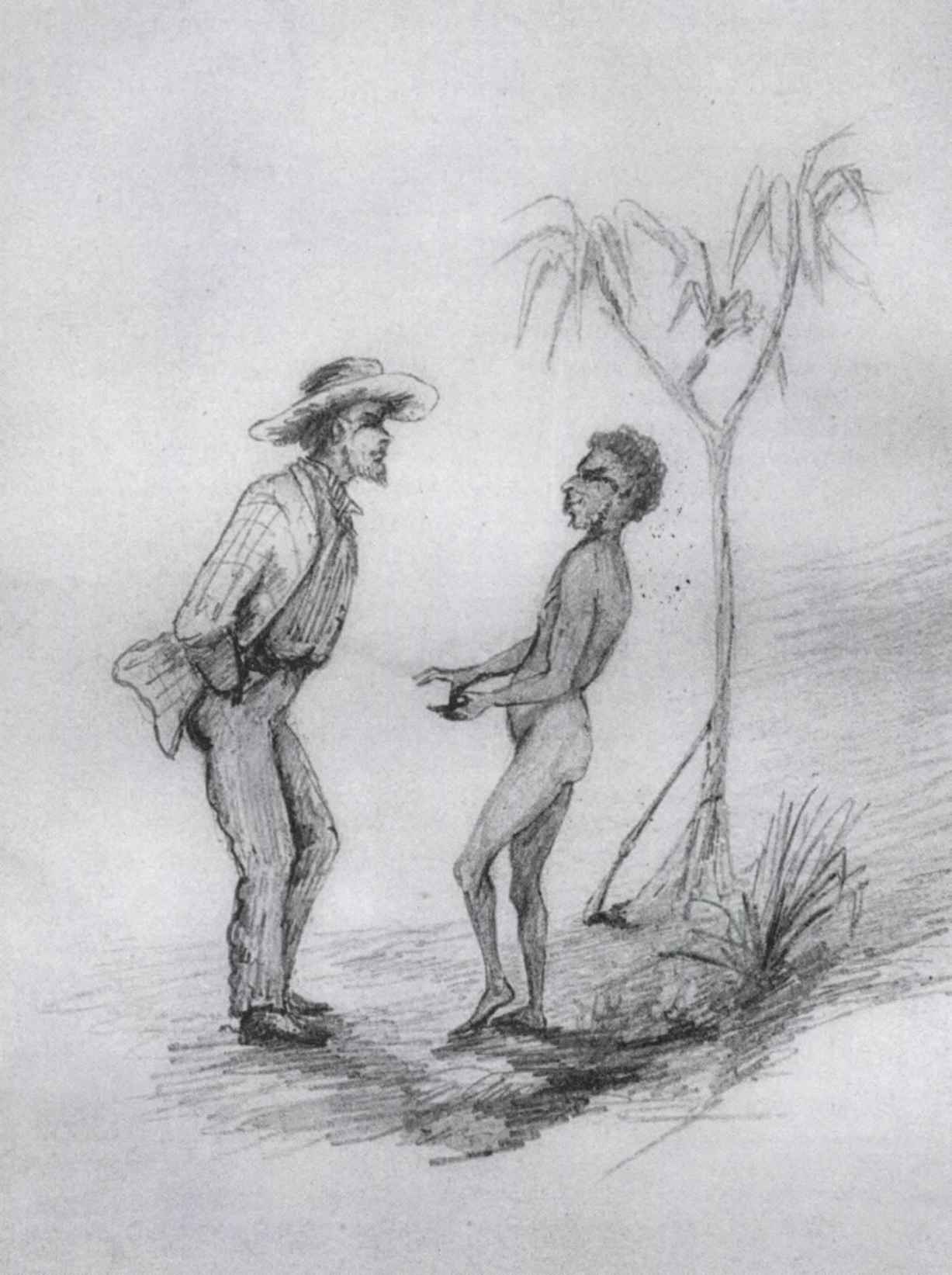
这张素描表现了赫胥黎正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交谈。
长期以来,我对心灵感应一直抱有疑虑,虽然这种疑虑并非全无根据,但我现在开始觉得,它一定有些道理。因为,最新一期的《双周评论》提供的证据,让我不能漠视。它说:在至今尚未发现的人类天赋中,也许存在着一种比“生活于中国最高峰”的佛教圣徒的神秘能力还要奇妙的一种力量。秘传的佛教圣徒有一种神秘能力,他能够辨识伦敦邮区某条普通街道上居民的内心世界。这种先知的洞察力的确了不起,但更了不起的是,有人不仅能洞察到思考者意识到的想法,而且还能觉察连思考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想法——他能觉察思考者如何无意识地得出其原本反对的结论,无意识地支持其原本憎恨的学说。能够洞穿旁人内心世界的这种混乱——这种能力若是起效,则有可能深入某人对于人格和责任感的看法之中——是危险的,疯子才表现出这种行径。但真理就是真理,而且当仅有的选择就是支持刊登在1886年《双周评论》第六期上的那篇《唯物主义与道德》的文章的作者的时候,我几乎要勉强相信这种对乌有之物的神奇的洞察力。就我所知,尽管作者的能力和诚实,正如他信誓旦旦所保证的那样,但如果我了解自己的想法,那么,文中之言就是诸多一流错误的堆砌。
我非常钦佩利利先生的坦率,对他正直的用心也是心悦诚服,因而我不愿与他发生争执。此外,他大胆鄙视时下那些卑劣的冒牌著作,对此我也是深表赞同,所以在他的理论没有对我的信条做任何不当的阐述之前,我心甘情愿保持缄默,只要我觉得这种克制对于我们双方心中的理想有利的话。但是,我没法这样想。我的信条也许不讨人喜欢,但它是我自己的信条,就像试金石 (1) 看待他的心上人一样。我对心仪的对象身上固有的美德评价很高,所以不可能平心静气地看着她被说成是一个丑陋不堪、一无是处的荡妇。我相信,如果我曾追随过某一理想,那么即便它行将末路,我也会坚持到底,但是,为了一个行将末路而且你曾竭尽全力去埋葬的理想而受苦,这种极端的折磨我还没有体验过。利利先生强加在我名下的那种哲学理论,我曾再三否认与我有关。在我看来,那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是必将走向绝境的。我反对他把我视为这种理论的捍卫者,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利利先生模仿中世纪的辩论家,推出三大命题,因为在他看来,这三大命题代表了赫伯特·斯宾塞先生、已故的克利福德 (2) 教授以及我本人所宣扬的最主要的异端思想。他说,我们三人一致同意“(1)感官不能证实的事物视为无法证实,要放在一边;(2)自然科学范围以外的事物视为无法证实,要放在一边;(3)不能进行实验和化学处理的事物视为无法证实,要放在一边”。
我的已故的年轻朋友克利福德,虽然天性柔和但却是一个最锐利的辩论者。虽然他不能亲自参加我们这场小小的论辩,但他的著作可以为他说话,而且凡是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他对利利先生的主张的驳斥。赫伯特·斯宾塞先生目前已表明,他既不缺乏为自己辩护的能力,也不缺乏为自己辩护的意愿。如果我替他拿起棍棒,不仅多此一举而且显得鲁莽无礼。但是,对我本人来说,如果假定我对我自己的意识有足够了解的话(而且我绝对不会自命不凡地去了解我的“无意识”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请允许我说,在我看来,第一个命题是不正确的,第二个命题同样不正确,假如可以为不正确评级,那么第三个命题则不正确得骇人听闻,即使它还没有在逻辑地狱的附近踉跄挣扎,也已经在荒谬透顶的边缘逗留盘旋。因此,对这三大命题,我的回答十分恰当:Nego——我说“不”。接下来我会陈述否定的理由,然而礼节不允许我采用如我所愿的那种断然语气。
让我从第一个命题开始,即我认为“感官不能证实的事物视为无法证实,要放在一边”。像这类关于人类的命题,怎么可能是严肃地提出来的呢?然而,我不是被委派来为整个人类辩护,我只为我自己辩护。请允许我说,此刻我坚信,利利先生完全被一种明显而严重的误解所误导。尽管(在没有任何心灵感应能力的情况下)我不能通过触摸也不能通过尝、嗅、听、看等所有的感官能力,来对我的坚信进行“证实”,但我绝不想把它放在一边。
再者,也许我可以冒昧地赞美一下,利利先生表达观点的文字既清晰又生动,但是,这种赞美之情,不是源于我的五种感官能力在他文章的字里行间所发现的东西,因为如果是这样,猩猩靠着和人类一样敏锐的感官也可能发现。不!这种赞美之情源于审美能力对文艺形式的鉴赏,源于知性能力对逻辑结构的评价,而它们都不是感官能力,而且常常在感官精力充沛时,令人沮丧地消失。在感官能力方面,我可能还不如我那浅薄的亲戚 (3) ,但我肯定,当谈到文艺风格和三段论时,它就得甘拜下风了。
如果这个世界上还存在什么让我坚信不疑的事情,那就是因果律的普遍适用性,但这种普遍性是不能靠经验的多少来证明的,更甭说靠感官来证明了。当意志活动改变了我思想的倾向时,或者当一个念头招来另一个相关的念头时,我一点也不怀疑,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中,引起第一个现象的过程,和第二个现象存在着因果关系。然而,企图通过感官来证实这种信念,纯粹是精神错乱。我相信,利利先生不会怀疑我的心智健全,因此目前看来,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承认他的第一个命题是错误的。
利利先生指控我的第二个命题是“在自然科学范围以外的事物视为无法证实,要放在一边”。我再说一遍:不!我想,没有谁会认为我希望限制自然科学的范围,但是,我确实觉得必须承认,大量非常熟悉而又极为重要的现象,的确处于自然科学的合理界限之外。我不能相信,诸如意识之类的现象,以及其他由自然过程而来但又非自然的现象,为何会划归到自然科学的范围。拿一个可能是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如对红色的感觉。自然科学告诉我们,当具有某种特征的光以太振动刺激视网膜时,分子的变化就从眼球传送到大脑物质的特定部分,结果就出现通常所看到的红色。让我们假定,物理学分析方法进展极快,能使人们看到分子链上的最后一环,观察分子运动犹如观察打台球用的球,称一称重量,量一量大小,从而掌握物理学上能了解的一切信息。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也仍然无法将意识所产生的现象即对红色的感觉,包含在自然科学的范围之内。意识现象就像现在一样,仍然是与我们称之为物质和运动的现象不同的东西。假如存在我竭力加以完善并一再坚持的明显真理,那就是我上面主张的观点——而且,不论它是不是真理,我都坚持认为,它没有为利利先生的主张留下任何辩护的余地。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要问:怎么能够想象,一个心智完全健全的人竟然会抱有这样的观念?我不认为我具有什么特别的天赋,因为我一生都在享用自然和艺术所提供的对美的敏锐感受。也许是现在,也可能是将来某一天,自然科学能够使我们的后代详尽地解释,对美的极度着迷所带来的生理反应和生理状态。但是,即使那一天真的到来,对美的着迷也仍然像现在一样,处于自然世界的外部,超出自然世界之外——甚至在精神世界,也有一些东西添加到纯粹的感觉中去。我不愿意在我卑微的堂兄——猩猩——面前,太过自鸣得意,不过在审美领域,犹如在知性领域一样,恐怕没有他的容身之地。我不怀疑,他能在一片我什么也看不清的浓密树叶中找到果实,但我尚能自信的是,他永远不会像我带着灰暗的宗教忧郁,敬畏供奉大地之神的教堂那样,敬畏他所栖身的热带雨林。然而,我也不怀疑,当我那可怜的长臂短腿的朋友,坐在那儿,若有所思地咀嚼榴莲果时,在它那张忧郁的斯多葛派面孔后面,有些东西绝对是“在自然科学范围之外”的。自然科学也许知道它在采摘、咀嚼、消化果实方面的一切事情,而且知道它的上颚在受到刺激后,快感是如何传输到他的大脑灰质的某些微小细胞的。但是,就有那么一会儿,他那忧郁的眼神闪现出一丝甜蜜感和满足感,酷似人类的游吟诗人那“如痴如醉”的样子——这也是绝对处于物理学范围之外的。
就算把我放在一边,难道利利先生真的相信,世上会有这样的人:一个有音乐感的人,他明明从音乐中得到了快乐,就因为这种快乐处于自然科学范围之外,至少是处于纯粹的听觉范围之外,就不相信这种快乐的真实性?但是,也许是这样,他把音乐、绘画、建筑等艺术全都放在自然科学的名头之下——如果真是如此,我只能遗憾地说,他这样抬高我的那些至爱的身价,我实在不能苟同。
利利先生第三个命题是这样的,我把“不能进行实验和化学处理的事物,视为无法证实”放在一边。我要再一次说:不!这种奇异的主张并不新奇,我常常从那种地方听到——在此,体面(或不体面的)愚钝常常无所顾忌地占据支配地位,它就是教堂。但是,我惊异地发现,一个具有利利先生那样的智慧和真诚的作者,竟也愿意领养这个废物。因此,如果我要严肃地对待此事,就发现自己真是左右为难。要么把词典中没有的一些含义加到“试验”和“化学”的头上,要么这个命题就是(我绞尽脑汁想说得委婉而又贴切,应该怎么说呢?)——完全——非历史性的。
难道利利先生认为,我会把一切数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真理都视为“无法证实”而放在一边吗?假如我不这样做,那么他会大发慈悲地告诉我们,如何在设备最好的“实验室”里,对二项定理进行“化学”处理?或者告诉我们,哪里有天平和熔炉,可以检验关于巴斯克语 (4) 属性的各种学说?再或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试剂可以从已有的罗马历史中提炼出真理,然后将错误如同灰烬那样抛弃吗?
我的确无法回答这些问题;除非利利先生能够回答,否则我想,从今以后,在把这些荒谬的观念强加给他的同道之前,他会三思而后行——因为,正如一位博学的律师所言,他们毕竟是有脊梁的动物。
整个事情让我困惑良多。我相信,一定存在着某种解释,能够保住利利先生在判断力和公平处事方面的声誉。有没有可能是这样——我只是试探性地这么说——很多粗心大意的人会把事情弄混,是不是利利先生一不留神也给弄混了?显然,说自然科学的逻辑方法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是一回事,而断定所有思考的对象都在自然科学的范围之内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经常断言,我确信只存在一种能够获得知识之真理的方法,无论研究的内容是属于自然领域还是意识领域。支持将我最常用的自然科学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的唯一理由是:在我看来,与其他学习相比,自然科学能更好地锻炼年轻人在评判归纳证据方面的心智。我反复强调,自然科学有可能通过理性的运用,对于知识以及阐述真理不可分割的模式,提供了最适合也是最易于理解的说明,但我要补充的是,我从不认为,其他学科的知识不能提供同样的训练。而且确凿无疑的是,面对别人强加给我的“在自然科学范围之外,没有任何东西真正存在”这一荒谬论点,我从未有过丝毫的让步。毫无疑问,一个想说别人坏话的人,根本不会在意话的真假,因此常常歪曲我的明确含义。但利利先生不是那种可以让人不屑一顾的家伙,他居然混迹于这群人中间,我只能是既伤心又疑惑。
利利先生在评论专栏上抛出的三个命题就说到这里。我认为,我已经说明,第一个命题是不正确的,第二个命题也是不正确的,第三个命题还是不正确的。这三个不正确加在一起,就构成一种巨大的歪曲,尽管我不怀疑它是无心之作。假如利利先生和我都是雄辩家,在主编的眼皮下,为了娱乐公众,在《双周评论》这个竞技场上进行角逐,那么我最好的策略就是马上离开这个战场。因为,问题在于,我是否持有某些看法,是一个事实问题。有鉴于此,至少在无意识的心灵感应的证据得到更普遍的认同以前,我的证据可能被视为是结论性的。
然而,利利先生对那些多多少少有争议的问题所作的其他一些论断,其对错却不是那么容易澄清的,但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他犯的错误似乎不亚于我们刚刚讨论过的那些命题。由于这些问题太重要了,我不得不斗胆说上几句,即使我会为此被迫离开我所熟悉的知识领域。
就在利利先生发射上述三枚鱼雷且已经可悲地在自己船上爆炸之前,他说:不论“我用多么华丽的修辞来给我的学说镀金”,它仍然是“唯物主义”。在此,我要顺便说一句,这种华丽的装饰品并没有对我构成什么妨碍,而且依我看,给纯金镀金,总不及用花言巧语给真理的美丽面孔涂上厚厚的脂粉那样令人讨厌。如果我认为我有资格获得“唯物主义者”这顶头衔——在这儿是把它作为一个哲学术语而不是骂人的词来讨论——那么,我就不应该设法用镀金之类的手法将它包装起来。在过去的30年里,我找不出什么理由要去在意什么不好的名头,现在我老了,更不会变得敏感起来。但在这儿,我只是要重复一下我曾不止一次费尽苦心地用最朴实的日常用语讲过的东西。我认为,我所理解的唯物主义学说是一种哲学上的错误思想,我拒绝接受;同样,我也不接受利利先生提出的唯心主义学说。我拒绝接受这两种学说的理由是相同的,即不论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有什么不同,但他们都对一些问题——我可以肯定我对这些问题是一无所知的,而且我也相信他们对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很无知的——做出了绝对的断言。进而言之,即使他们所断言的东西在我的知识能力范围之内,但在我看来也常常是错误的。此外还有一个原因,让我不愿意加入他们两派中的任何一派。他们每一派都特别喜欢把对方并不持有的结论强归于对方,并加以非难,尽管这些结论都是两者的基本原理经逻辑推导后的必然结果。一个做事谨慎的人,尽量避开这些哲学上的黑白之争,不与任何一派发生纠葛,理应是不会受到非难的吧?
我是这样理解唯物主义的主要原则的:宇宙中只存在物质和力,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解释为这两种本源的产物。唯物主义的伟大捍卫者,利利先生眼中的自然科学权威布希纳 (5) 博士,将上述信念写在他的著作《力和物质》的扉页上。这本著作把力和物质标榜为“存在”的阿尔法和奥米伽 (6) 。据我理解,这是唯物主义这种信念的基本内容,而且凡是不坚持这种信念的人,那些更为热忱的信仰者(正如我理应知道的)就将他们打入专为白痴或伪君子预备的地狱。但是,我打心底里不相信这一切。虽然可能被视为老调重弹,但我仍将简要地陈述我坚持不信唯物主义的理由。首先,正如我前面所暗示的,在我看来极为明显的是,宇宙中存在着第三种东西,那就是意识。无论意识现象的表现形式与被视为物质和力的现象有多么密切的关系,我固执的心灵和倔强的头脑,都无法将意识视为物质、力或任何可以想象出来的物质或力的变体。第二,笛卡儿和贝克莱曾论证过,我们获得的知识不可能超出我们的意识之外。大约在半个世纪前我第一次接触这些论证时,就觉得他们是无法驳倒的,现在看来依然如此。所有我知道的唯物主义者都想啃一啃这一铁证,其结果无非是把牙齿给咬崩了。不过,如果这一论证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一方面可以肯定精神世界的存在,另一方面还可以肯定,力和物质的存在将沦为一种假设,至多是可能性很高的假设。
再者,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本该嬉戏玩耍,却反常地乐于思考。我总是在想,如果事物失去了它们的性质,会变成什么呢?我的心智因为思考这道难题而得到了极大的锻炼。由于性质并不是客观存在,而没有性质的事物就什么也不是,于是坚固的世界似乎被一片片地削掉了,这让我大为惊骇。当我长大一些,学会使用“物质和力”这两个术语,那个孩子气的问题换个名称后再度出现了。一方面,不承认力只承认物质的论调,似乎把世界变成了一组几何学幽灵,毫无生气;另一方面,博斯科维奇 (7) 的假设倒是挺诱人的,即物质被分解为力的中心。但如细究一下,当力被视为一种客观实在时,力又到哪里去了呢?关于力的问题,即便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会同意最坚定的唯心主义者的看法,力不过是引起运动的原因的代名词。如果同意博斯科维奇的假设,把物质分解为力的中心,那么物质就会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非物质的实体。这样一来,人们倒不如坦率地接受唯心主义,也就完事了。
尽管很丢脸,但我必须坦承,我没有形成一丝唯物主义者所谈论的那些“力”的概念,倒是他们多年来似乎就拥有装在瓶子里的那些“力”的样品。他们告诉我,物质是由原子构成的,而原子散布在虚无一物的真空里——而且在这个虚空中,原子发出吸引力和排斥力,并且相互影响。如果谁能够清晰地构想出那些不但存在于虚无之中而且还具有强劲引力和斥力的事物,我会羡慕他拥有一种不仅高于我而且高于莱布尼兹或牛顿的理解力 (8) 。在我看来,经院哲学家所说的“在虚空中嗡嗡直叫、吞噬第二种思想的凯米拉 (9) ”,同这类“力”比起来,还算是一种熟悉的家养动物。此外,根据上面提到的假设,可以推出:力不是物质。这样一来,在一定相互作用下产生的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属于唯物主义者所说的物质。不要误认为我在怀疑使用“原子”和“力”这两个术语是否恰当。它们是自然科学的初步假设,作为公式,它们在解释自然方面十分精确且简便易行,因而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但是,如果把原子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真正实体,是一种占据空间且又不可分割的粒子,的确让人难以想象。至于那种无处藏身的原子,其运动是靠寄身于虚无中的“力”,也实在让我无法想象,我想其他人也会有同感。
在没有人为我消除所有这些怀疑和困难之前,我认为我有权对唯物主义敬而远之。至于唯心主义,当我想用现实中实实在在的硬币来兑换唯心主义的本票时,难度就更大了。因为那个假定的物质实体,精神,被认为属于意识现象,就如物质属于物理性质的现象一样,当这些现象被抽离的时候,连几何学的幽灵也不存在了。而且,即使我们假定,存在着这样一种没有任何特性的实体——也就是说,一种空洞的存在——那么,对心灵而言,有谁知道这种实体与同样不具备任何特性的构成物质基础的另一实体有何不同呢?总之,唯心主义与倒置的唯物主义好不到哪儿去。如果我试图将那个“精神”,即根据这种假说,人将它藏在脑子里的那种东西,看作是即使在思维中也与空间没有任何关系、不可分的,与此同时,又假定它就在空间之中而且具有六种不同的本领,那么我坦言,我实在是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以前就说过,如果我不得已要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做出选择,我应该会选择后者,但我的的确确与软弱无力的唯心主义神话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我觉得现在没有人逼迫我进行选择。有先哲说,人类是宇宙的尺度。对此,我总是抱有强烈的怀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而且这种信念并没有因为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有所削弱。论及上述这些猜想,让我回忆起了年轻时做船员的经历。在接受训练时,只要特别小心且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你就可以十分安全地把罗盘转动一圈。如果你心猿意马,忘记了这些限制,假如不是太糟的话,等着你的是气急败坏的几声责骂。我守在甲板边,不时将救生圈丢给因走到船的边缘而落水、在海中挣扎的同伴,而我的善行所得到的回报是,只要他们之间相互停止咒骂,他们就一起骂我。
我年纪尚小的时候,就发现一种为多数人所不容的罪过:一个人竟敢不给自己贴标签。这种人在世人眼里,就像警察带着没有戴嘴套的狗,缺乏有效的控制。我发现没有适合自己的标签,而我又渴望给自己排队,以获得人们的尊重,于是我自己就发明了一个。由于我最确信的一点是,我对周围公认熟悉的各种“主义”和“分子”知之甚少,故而我把自己称为不可知论者。确实,再没有比这更稳妥、更恰当的名称了。然而,我不明白,为何我还是时常被赶出避难所,有时被称为唯物主义者,有时是无神论者、实证主义者,呜呼哀哉,有时还被称为是胆小怕事或保守反动的反启蒙主义者。
我相信,现在我终于澄清了自己的问题;我相信,从此以后,我便可以落个清静了。不过,我还得再做一番解释——因为利利先生的看法说明,我还是有必要再解释一下的。可以看出,关于“实验室”和“化学”的含义,我的这位出色的批评家有一些独创性的观点,而且不管在我还是在他自己看来,他对“唯物主义者”的定义尤为不同寻常。尽管我已尽力避免对他的误解,但他还是把我放在唯物主义者的名下(这种推断建立在我已表明没有任何基础的基础之上)。他的理由如下:第一,我曾经说过,意识是大脑的功能;第二,我坚持决定论。至于第一点,我不知道有谁会怀疑,在“功能”这个词的恰当的生理学意义上,意识至少在某些形式上是大脑的功能。在生理学上,我们把功能称为由器官活动所引起的结果或一系列结果。因此,它是引起动作的肌肉的功能——当神经受到刺激并传导到肌肉时,肌肉就产生动作。如果将人的手臂的某一神经束暴露在外面,刺激其中某些神经纤维时,那只手臂就开始动起来。如果刺激其他的神经纤维,结果就产生“疼痛”这种意识状态。现在,如果我追踪神经纤维后面提到的那些,会发现它们最终与大脑的部分物质相连,就像前面那种神经纤维与肌肉物质连在一起一样。如果在第一种情形中产生的动作,可以称为肌肉物质的功能的话,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把在第二种情形下产生的意识状态称为大脑物质的功能呢?从前,确实存在一种假定,认为一种特定的“动物精神”栖身在肌肉之中,是真正的能动者。既然我们已经不再提这种虚构的纯粹多余的肌肉器官名称,为什么还要保留一个相对应的虚构的神经器官名称呢?
如果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没有一个生理学家,不管他多么偏爱心灵,会去设想简单的感觉需要一种产生它们的“精神”,那么我必须指出:这就是说,我们一致同意,意识是物质的一种功能,而且不能把这一特殊原则作为唯物主义的标志。任何进一步的讨论取决于下列问题,即不仅要弄清楚意识是否是大脑的一种功能,而且要弄清楚所有意识形式是否都是如此。再者,即便唯心主义假设有什么根据,但我还是认为,说物质变化是引起精神现象的原因(而且作为一个结果,在器官中发生的这些变化,就产生了这种对应于器官功能的现象),还是十分正确的。人人都会毫不犹疑地说,事件A是事件Z产生的原因,即使在这一因果链条中,存在许多已知和未知的中间事项,就像在A和Z之间还存在许多字母一样。一个人将子弹上膛,把手枪对准另一个人的头颅并扣动扳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引起后者死亡的原因。尽管严格地说,那个人除了手指在扳机上动了一下,没有“引起”其他任何事情发生。同样,我们说,通过刺激人体某个很远的部分,引起大脑物质的某个特定部分发生分子变化,就产生感觉这一结果,也是恰当的。就这一过程而言,不论在生理作用和实际的心理产物之间,还可加入什么尚不知名的术语,把分子变化称作感觉产生的原因,都是恰如其分的。因此,除非唯物主义拥有正确使用语言的专利权,否则我看不出,我所使用的语词有什么唯物主义的特征。
在利利先生为授予我唯物主义者称号而提供的理由中,就剩下一条了,那就是他引用我说过的一段话。在这段话里,我说,科学的进步意味着我们称之为物质和力的范围的扩展,与此相伴的是,人类思维中所有被称作精神和自发行为的领域逐渐缩小。如果说我现在的立场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我比20年前发表上述看法时,立场更为坚定,因为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是,我并未发现,这种看法与唯物主义有什么关联。依我看来,这种看法与最彻底的唯心主义倒是一致的,而且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实在是一目了然的。
科学的发展,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是所有科学的发展,都意味着用以前未曾有过的概念,来揭示现象之中的秩序和自然的因果联系。凡是对200年来科学思想在人类知识的每个领域取得的进步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科学王国的版图获得了巨大的增长;没有人会怀疑,未来两百年人们将目睹科学王国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扩张。特别是在神经系统生理学领域,从目前分析生理和心理现象之间的联系所取得的成就来看,有理由相信未来会取得更为巨大的进步——迟早会准确地揭示出,一切所谓的心灵的自发活动,彼此之间相互联系,而且与生理现象相关联,将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自然因果系列。换句话说:我们现在仅仅知道因果链条的较近部分,即所谓的物质现象经过因果变化产生所谓的精神现象;接下来,我们会知道因果链条的较远部分。
以我的无知之见,我已经习惯于认为,我上面说的不过是对事实的陈述。如果好心的贝克莱大主教还活着,他会认为,这些事实轻而易举就能应用到他的体系中去。由于利利先生宣称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对他的对手们有利,因而有可能落入他们的圈套——在我看来,他的这种做法,在他诸多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的手法中,可谓一个典范。的确,利利先生不会认为,不相信自发行为——这个术语,如果非要赋予其内涵的话,那就是指非外因引起的行为——是难以驯服的“唯物主义”的标志吧?如果是这样,那他就得准备对付众多的笛卡儿信徒(如果不是笛卡儿本人的话)、哲学家中的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以及神学家中的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加尔文及其同道等唯物主义者了。显然,这为其分类方法提供了充分的反证。
真实的情况是,当利利先生狂热地在任何他讨厌的东西上涂上“唯物主义”几个大字时,他忘记了一个极为重要且是每一个关注人类思想史的人都明了的事实,即困扰康德的三个理论难题——上帝的存在、自由意志和不朽。在所谓的自然科学诞生之前,这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而且即使将现代自然科学予以消灭,这些问题仍将继续存在。自然科学所做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使一些以前难以理解的难题看得见、摸得着了。这些难题不仅在唯物主义的假说中存在,而且同样在唯心主义的假设中存在。
研究自然的人,如果从因果律的普遍公理着手,那他就不会拒绝承认有一种永恒的存在;如果承认能量守恒,就不会否认有可能存在一种永恒的能量;如果承认以意识形态出现的非物质现象的存在,就无论如何必须承认可能存在这种现象的永恒连续;如果他的研究结出了探究自然的最好果实,他就会彻底明白斯宾诺莎所说的:“神,我理解为绝对无限的存在,亦即具有无限‘多’属性的实体。” (10) 这样设想出来的上帝,只有超级白痴才会否认它的存在,确实他也只敢在心里否认。自然科学不是无神论,也不是唯物主义。
至于不朽的存在,自然科学在陈述这个问题时似乎是这样说的:“把意识状态的连续与无数相连的不同物质分子的排列和运动偶然地联系起来,已有70年了。有什么方法让我们知道,这种意识状态的连续,能否与不具有物质和力的特性的某些实体发生类似的联系而继续下去?”正如康德所说,在类似的情况下,如果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他正是我想拜访的那个人。如果他说,意识除非与某些有机分子发生因果联系,否则就不能存在,那么我就得问他是如何知道的;如果他说能存在,我还会问同样的问题。就像诙谐的彼拉多 (11) 一样,我恐怕会想,(我的时日已不多了)等待回答是不值得的。
最后,说一说自由意志这个古老的谜。在我看来,“自由”这个词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是可以理解的——所谓自由,就是在一定限度内不对一个人想做什么予以限制——对此,自然科学确实提不出比人类常识更多的理由来加以质疑。自然科学一方面不断强化我们对因果关系的普遍性的信念,另一方面又将偶然性视为荒谬而予以排除,由此得出决定论的结论。其实在自然科学产生或被思考之前,哲学和神学中那些始终遵循逻辑的思想家早就有此结论,自然科学不过是顺其道而行之。不论是谁,只要他把因果律的普遍性视为一种哲学信条,他就会否认无因现象的存在。被不恰当地称为自由意志的学说的实质,是认为人的意志总是偶然地由自身(self)而引起的,也就是说,根本不是被引起的,但要引出自身,个体必须先于自身而产生——退而言之,这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谁把无所不知的神的存在视为一种神学信条,他就得肯定事物的秩序是只能从不朽走向不朽,因为对事件的先知先觉意味着这一事件一定会发生,而一个事件发生的确定性则意味着:它是注定或命定要发生的。 (12)
谁声称存在着无所不知的神,这个神创造万物、养育万物,那么如果不自相矛盾的话,他就不能声称存在着神以外的原因。而且如果他声称万物的原因会“允许”万物中的一个事物成为一个独立因,那就纯粹是一种狡猾的托词。
谁声称神是一种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于一身的存在,他就得默认命运的存在。因为如果他有意创造一个东西并把它放在一定的境遇之中,而他又完全知道这种境遇会对这个东西产生什么影响,那么实际上他就已经预定了何种命运会降临到那个东西的头上。
这样一来,我们终于接近整个讨论真正重要的部分。如果相信上帝对道德是必要的,那么自然科学没有对此造成障碍;如果相信不朽对道德是必要的,那么自然科学反对这种学说的可能性不会超过最平凡的日常经验,而且自然科学还有效地封住了某些人的嘴——他们自称,仅凭从自然数据得出的反对理由就可以驳倒它;最后,如果相信意志的自因性对道德是必要的,那么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只会跟逻辑哲学家或神学家一样,反对这一谬论。我再说一遍,自然科学并没有发明决定论,即使没有自然科学,决定论也会像现在一样立于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请那些怀疑这一点的人读一读乔纳森·爱德华兹 (13) 的作品,他的论证全部源于哲学和神学。
利利先生像所罗门的鹰那样,到处宣告“悲哀将降临到这个邪恶的城市”,抨击自然科学是当代社会中邪恶的天才——即唯物主义、宿命论和其他该受谴责的各种主义——的根源。我斗胆请他去指责当受指责的人,或者至少把自然科学那些罪孽深重的姊妹们——哲学和神学——一同推上被告席,因为她们更为年长,长期统治各种学院和大学,应该比可怜的灰姑娘懂得更多。无人怀疑,当代社会已疾病缠身,而且与那些古老的文明社会没有什么不同。人类社会如同正在发酵的一团物体,就像德国人称为“奥佰赫夫”(Oberhefe)和“安特赫夫”(Unterhefe)的啤酒一样;与此同理,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每个社会,上部都会冒泡沫,底部都会沉渣滓。但我怀疑,是否任何“信仰时代”都极少泡沫或渣滓,或者相应的,啤酒桶里完全有益于健康的东西格外多。我想,会让利利先生或其他人迷惑不解的是,可以列举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世界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比我们当今英国社会更具有责任感、正义感和互助意识。呀!不过,利利先生说,这些全都是我们基督教传承的产物,如果基督教义不存,美德必将随之绝迹,到时唯有从祖先猿和虎那里遗传的兽性横行。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显而易见,基督教也从异教和犹太教那里继承了很多东西——如果斯多葛派和犹太人收回他们的遗产,那么基督教可变卖的道德财产就很少了。如果发现道德被数次扒掉特别不合身的几套外衣之后尚能存活,那它为什么就不能穿上自然科学所提供的亮丽轻巧的衣服阔步前进呢?
但这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如果社会的病因在于弱化了对神学家所说的上帝存在的信仰,对未来状态的信仰,对无因直觉的信仰,那就得像医生们所说的那样,禁止神学和哲学,因为神学家和哲学家对他们一无所知的事情争吵不休,正是罪恶的怀疑主义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和赖于生存的不竭动力,而怀疑主义则是乱闯不可知的领域应得的报应。
灰姑娘谦卑地意识到她对这些高深问题的无知。她点起火炉,打扫房子,准备饭菜,而这一切的回报是,别人说她是只关心低级物质利益的下贱东西。然而,在她的阁楼里,她能看到童话般的世界,而楼下吵架的两个泼妇则根本无从想象。她发现,这个貌似混乱的世界渗透着秩序——进化这部宏大戏剧,既充满遗憾和惊惧,又充满善良和美丽,一幕一幕在她眼前铺开。她在内心深处记下这一教训:道德的基础在于坚决不说谎,不假装相信没有证据的东西,也不转述那些对不可知的事物提出的莫名其妙的命题。
她知道,保证道德安全既不在于采纳这种或那种哲学思想,也不在于采纳这种或那种神学教义,而是在于切实、强烈地相信自然固有的秩序,这种秩序把瓦解社会的行为视为罪恶行径,就像坚定地把身体上的疾病归因于身体受到侵害一样。正是出于这种坚定而真实的信仰,成为女祭司是她的天职所在。
————————————————————
(1) 莎士比亚剧作《皆大欢喜》中的人物。他爱上了乡村姑娘奥德蕾。他有句台词说:“她是个寒伧的姑娘,殿下,样子又难看;可是,殿下,她是我自个儿的:我有一个坏脾气,殿下,人家不要的我偏要。”——译者注
(2) William Kingdon Clifford,1845—1879年,英国数学家,在非欧几里得几何与射影几何方面有许多建树。——译者注
(3) 指猩猩。——译者注
(4) 巴斯克语是一种非印欧语系的语言,使用于巴斯克地区,即西班牙东北部的巴斯克和纳瓦拉两个自治区以及法国西南部。巴斯克语又称欧斯卡拉语,语系归属未定。——译者注
(5) Ludwig Büchner,1824—1899年,德国哲学家、生理学家,19世纪科学唯物主义的倡导者。在《力和物质》(1852年)一书中,他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源,一切自然力和精神力量都来源于物质。这本书在当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译者注
(6) Alpha and Omega,其小写为α 和ω ,分别是希腊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α 和ω 引申指事情的“始终”,“来龙去脉”或“全部”。——译者注
(7) Roger Joseph Boscovich,1711年—1787年,德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外交家和诗人。他是近代原子论的代表人物;博斯科维奇月溪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译者注
(8) 参阅克拉克1717年发表的著名的《论文集》。莱布尼兹说:“不相邻的两个物体不借助任何中介而相互吸引,这也是超自然的。”克拉克代表牛顿给这段话作了一个注解:“一物体不借助任何中介吸引另一物体,的确,这不是奇迹,是自相矛盾,因为这是在假定事物在它根本不在的地方活动。”
(9) “chimæra, bombinans in vacuo quia comedit secundas intentiones”,为拉丁文,源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1494—1553)的《巨人传》第二部分的第七章。secundas intentiones,第二种思想,在神学上是指思想的思想。参阅成钰亭的译作《巨人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259页。Chimera,古希腊神话中的妖怪,拥有羊身、狮头和蛇尾,会喷火;希腊语的意思是“山羊”,英语中还有“妄想,奇想”的意思。赫胥黎在这里是一语双关。——译者注
(10) 原文为拉丁文。出自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论神”定义6。——译者注
(11) Pilate,曾任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巡抚。根据圣经《新约·马太福音》所述,耶稣基督在他的任内被判钉十字架。——译者注
(12) 我可以引用两位肯定不会被利利先生藐视的权威的看法,来支持上述经合理推论得出的明显结论。他们是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前者声称,“命定”不过是神意(Providence)张冠李戴的说法。(奥古斯丁的原话为:“Prorsus divina providentia regna constituuntur humana. Quæsi propterea quisquam fato tribuit, quia ipsam Dei voluntatem vel potestatern fati nomine appellat, sententiam teneat, linguam corrigat.”引自《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V. c. i)
另一位著名的天主教权威神学家,即苏亚雷斯所说的“神圣的托马斯”,在我看来,他非凡的领悟力和敏锐的理解力几乎无人匹敌。当他说,行为者行为的基础不过是已经完成的事情的前身,可谓言简意赅。(托马斯·阿奎那的原话为:“Ratio autem alicujus fiendi in mente actoris existens est quædam præ-existentia rei fiendæ in eo.”引自《大全》问题二十三,第十一条)
如果还嫌不够,我再问一句:唯物主义者对决定论的理论曾经所作的说明,难道比托马斯·阿奎那在《大全》问题十四,第十三条里所说的那段话更透彻吗?(托马斯·阿奎那的原话为:“Omnia quæsunt in tempore,sent Deo abæterno præsentia, non solum ea ex ratione quæhabet rationes rerum apud se presentes, ut quidam dicunt, sed quia ejus intuitus fertur abæterno supra omnia, prout sunt in sua præsentialitate. Unde manifestum est quod contingentia infallibiliter a Deo cognoscuntur, in quantum subduntur divino conspectui secundum suam præsentialitatem;et tamen sunt futura contingentia, suis causis proximis comparata.”)
(正如我曾经说过的,托马斯·阿奎那显然是一个决定论者。我不明白,从他的著作中所引述的内容怎么与前面的内容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一致。)
(13) Jonathan Edwards,1703—1758年,美国神学家和哲学家,著有《自由意志论》、《宗教情操论》等著作。——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