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者前言
Chinese Version Preface
本书是第一次译成汉文出版。本汉译本译自罗伯特·克尔的英译本。克尔的译本在上个世纪中被多次重版和重印,也是专家们进行研究引用频率最高的版本。

拉瓦锡(Antoine-Laurent Lavoisier, 1743—1794),法国化学家。
本书作者安托万-洛朗·拉瓦锡(Antoine-Laurent Lavoisier,1743—1794)对生理学、地质学、经济学和社会改革均作出过贡献,但主要因在化学科学中的划时代成就而受到后世的景仰。
拉瓦锡是近代化学的奠基者。他创立了在化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氧理论,这一理论战胜燃素理论被认为是一切科学革命中最急剧、最自觉的革命。对这场化学革命的研究,早已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在国际上已形成多个研究中心,因拉瓦锡研究方面的成就而获德克斯特奖(the Dexter Award)者就有5人之多。据I. 伯纳德·科恩(I. Bernard Cohn)考证 (1) ,拉瓦锡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了衡量卡尔·马克思的伟大而借以与之比较的仅有的两位伟人之一(另一位是查尔斯·达尔文)。托马斯·S. 库恩(Thomas S. Kuhn)在他系统论述他的科学发现的历史结构的第一篇论文 (2) 中,篇幅最大的一节便是分析氧的发现。保罗·撒加德(Paul Thagard)甚至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这场革命的概念结构和机制进行探索 (3) 。由此可见拉瓦锡研究之深入。实际上,这个领域的文献已经如此之多,以致如果我们不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爱德华·格里莫克斯(Edouard Grimaux)、埃莱娜·梅斯热(Hélène Metzger)、丹尼斯·I. 杜维恩(Denis I. Duveen)、道格拉斯·麦凯(Douglas McKie)、亨利·格拉克(Henry Guerlac)、莫里斯·多马斯(Maurice Daumas),W. A. 斯米顿(W. A. Smeaton)、罗伯特·西格弗里德(Robert Siegfried)和卡尔·E. 佩林(Carl E. Perrin)等人的工作上的话,我们就把握不住拉瓦锡研究的学术走向。
本书是拉瓦锡的代表作。科学史学家认为,“它就像牛顿的《自然科学之数学原理》在一个世纪前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一样,奠定了现代化学的基础” (4) ,它“在化学史上的重要性怎样强调也不过分” (5) 。作者在1778至1780年间写出了书的提纲,法文书稿于1789年3月在巴黎面世,13年之内在法国出了8版,即1789年巴黎2版,1793、1801、1805年巴黎各1版,1793年被人盗印2版,1804年在阿维尼翁出1版。法文版初版不久,很快就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其他国家出版。罗伯特·克尔(Robert Kerr)的英译本于1790、1793、1796、1799和1802年在英国爱丁堡5次出版(其中1802年版为2卷本),1799年在美国费拉德尔菲亚、1801和1806年在美国纽约共3次出版;温琴佐·丹多洛(Vincenzo Dandolo)的意大利译本于1791、1792和1796年在威尼斯3次出版;S. F. 赫尔姆布施泰特(S. F. Hermbstadt)的德译本于1792和1803年在柏林2次出版;曼努埃尔·穆纳里斯(Manuel Munarriz)的西班牙译本于1798年在马德里出版;N. C. 德·弗雷里(N. C. de Fremery)的荷兰译本于1800年在乌得勒支出版;此外,1791年在阿姆斯特丹、1794年在格赖夫斯瓦尔德、1797年在墨西哥还分别出版过荷兰、德文和西班牙文节译本。这部科学经典巨著在17年的时间内,就在8个国家以6种文字出版了26次,足见其在当时的影响之广泛。
克尔的英译本在最近半个世纪中还被多次重版和重印,如1952年收入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主编、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c.)出版的《西方世界名著》(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第45卷(删去了副书名、附录和大部分英译者注)已印刷20余次,1965年多佛出版公司(Dover Publication,Inc.)按1790年版原貌重印,等等。而且,我们在《爱西斯》(Isis )、《英国科学史学报》(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 ),《科学史年刊》(AnnaIs of Science )《奇米亚》(Chymia ),《安比克斯》(Ambix )等权威刊上看到,克尔译本也是专家们进行研究引用频率最高的版本。因此可以说,这个译本是国际上最通行的版本。
本书是第一次译成汉文出版。本汉译本译自克尔的英译本。英译本出版于200多年前,其中所用的一些现已废弃了的古异拼词甚至在《牛津英语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secon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中都查不到,加上拉瓦锡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化学语言改革,这就给本书的翻译工作带来许多困难。译者在译述过程中力图谨慎地(但不一定是高水准地)按英译本原貌用汉语再现这座历史丰碑。有些物质名词,如compound和bond,在拉瓦锡著作中的意义与在现代化学文献中的意义相差甚远,我们必须按拉瓦锡的用法而不是现代用法去翻译。同一种物质往往有不同名称,如quicksilver(水银)与mercury(汞),muriatic acid(盐酸)与marine acid(海酸),hepatic air(肝空气)、sulphurated hydrogen gas(硫化氢气)与foetid air from sulphur(来自硫的臭空气),base(基)与radical(根),等等,汉译本中尽量采用不同的对应名称分别表示之。有些在今天看来是完全相同的物质,而在拉瓦锡看来却是不同的物质,如acetic acid与acetous acid,我们均按拉瓦锡的本意将它们译成不同的汉语术语。有些物质名词原本是俗名,在今天的英汉词典中却被“现代化”了,译者遇到这类名词时注意还其历史原貌,比如butter of arsenic和butter of antimony在各种现代英汉词典中分别被译为三氯化砷和三氯化锑,其实拉瓦锡时代根本就不知道氯元素的存在,因此我们只能将它们分别译作砒霜酪和锑酪。有些物质名称由于其历史源衍关系和化学源衍关系的不同而在译述时必须特别注意,如potash和potassium,在化学上是先有后者、后有前者,但在历史上则是先有前者、后有后者,而且拉瓦锡时代还不知道后者的存在,这样,本书中只能把前者译为草碱而不是钾碱。
为保证译文的准确性,我们除了根据汉语表达习惯对逗号作了必要的增删处理(少数地方还转换成为顿号)之外,对其他标点符号都维持原有用法。英文本中的数字并没有全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汉译本中也相应的将英文数字译为汉文数字,而阿拉伯数字则一仍旧贯。英文本中,第一、三部分有章有节而第二部分却有节无章,第一部分的表格在目录中均未列出而在正文中还有编号,第二部分的表格统统列于目录之中而又皆无编号,译者在汉译本中完全保留了这些特点。原书目录和正文中的标题并不精确一致,如第一部分第九章之中的各个小标题前,目录中标有节数而正文中未标节数,再如第一部分第十六章目录和正文中标题的文字略有不同、节数的表示也不完全一样,等等,我们在翻译中有意保持了诸如此类的不一致,以使汉译文与英译文更加一致。译者冒昧改动的只是第二部分正文中的一些节的序数。这一部分正文中的标题与目录中的标题文字上基本一致,只有详略区分,未作改动;但正文中有些节的序数重复,有些序数又没有,故译述中按目录节序将正文中的一些混乱节序纠正过来。
英译者在他的“告白”中谈到他的一个疏忽,即在第一部分没有把炭和碳区别开来(作者本来是加以区分了的)。实际上,英译者在全书中都没有区分。汉译本中,保留了英译本中的这种疏忽。英译者对附录所作的改动,“告白”中已有交代,不赘述。作者注和英译者注均按英译本分别以字母A和E标明,汉译者注以C标明。
汉译本所依据的爱丁堡1790年版中的图安排得较松散:图版VIII和XI的版心分别为33厘米宽、21厘米长和28厘米宽、24厘米长,两个图版各占1页;其他11个图版都各占1页以上,每页的版心约为11厘米宽、16厘米长;全部13个图版共27页。《西方世界名著》第45卷中将每个图版中的图作了密集重拼处理,在保持每个图版中各图图序不变的情况下,使13个图版只占17页,同时将每页版心安排得大小相同(约13厘米宽、29厘米长),并删去了图版V、VI、VII、VIII、IX和XI中标出的比例尺。汉译本中采用了后一版本中的图,只是相应地略有缩小。
本书法文版绪论(Discours préliminaire )即英文版的序(Preface ),是作者的一篇较著名的作品,金吾伦教授首先将其译成汉文发表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4年第4期第23~28页。译者不仅在翻译序文的过程中参考了金先生的这篇译文,而且还采纳了他通过法英文比较而琢磨出的对于本书主书名的译法。刘兵教授、李先锋博士为译者复制了有关资料。天主教中南神哲学院陈定国先生在拉丁文的翻译方面提供了帮助。辛凌教授和王丹华博士在语言理解方面提供了帮助。此译本于15年前纳入我主编的《科学名著文库》,由武汉出版社出了第一版。当初这部译著的面世,得益于彭小华先生的策划、李兵先生的组织、吴涛先生的装帧。此次再版,金吾伦老师撰写了导读,陈静小姐选配了辅助性的图片并撰写了相应的文字说明。译者谨向他(她)们致以谢意!
任定成
2008年6月21日
于承泽园

拉瓦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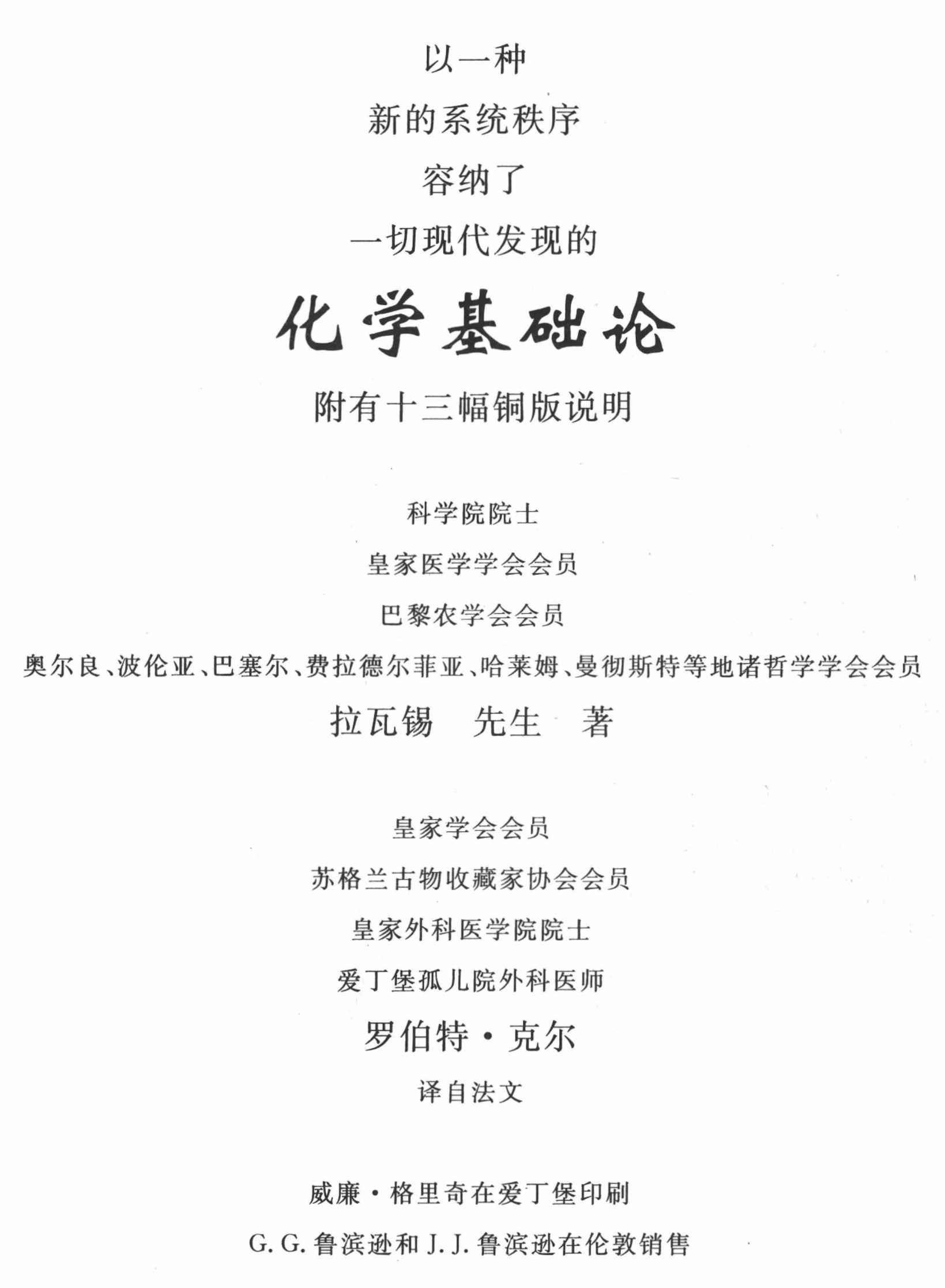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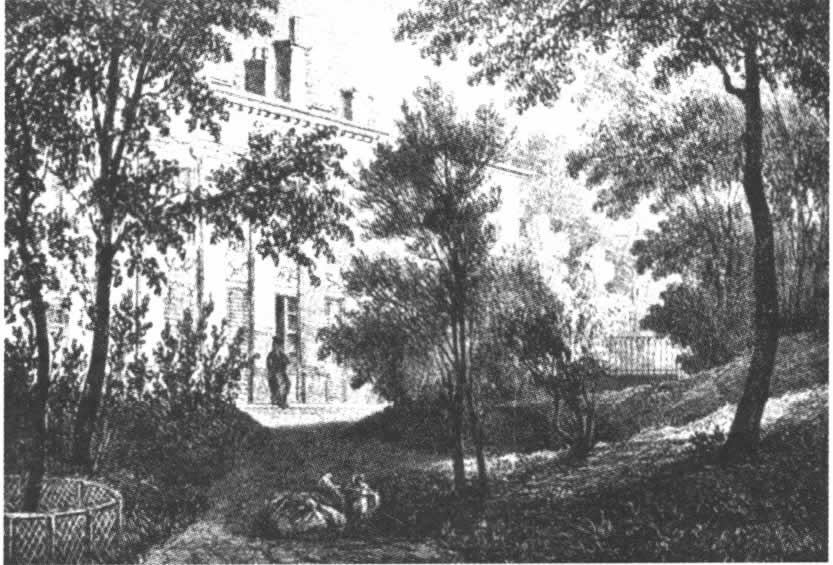
拉瓦锡1792年位于马德琳(de la Madeleine)的住所。
————————————————————
(1) 见Revolution in Science , The Belkan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514—515.
(2) 见Science , Vol. 136(1962), No. 3518, pp. 760—764.
(3) 见Philosophy of Science , Vol. 57(1990), No. 2, pp. 183—209.
(4) Douglas McKie, Antoine Lavoisier : Scientist , Economist , Socical Reformaer , Da Capo Press, Inc., 1980, pp. 274—276.
(5) H. M. Lecicest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hemistry , John Wiley & Sons, Inc. 1956, p. 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