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Postscript of Chinese Version
本书对耗散结构理论作了一个简明、扼要而又比较系统的介绍,为具有一定物理学、化学和热力学知识的读者说明了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怎样从混沌无序演化为复杂的结构,本书还着重讨论了时间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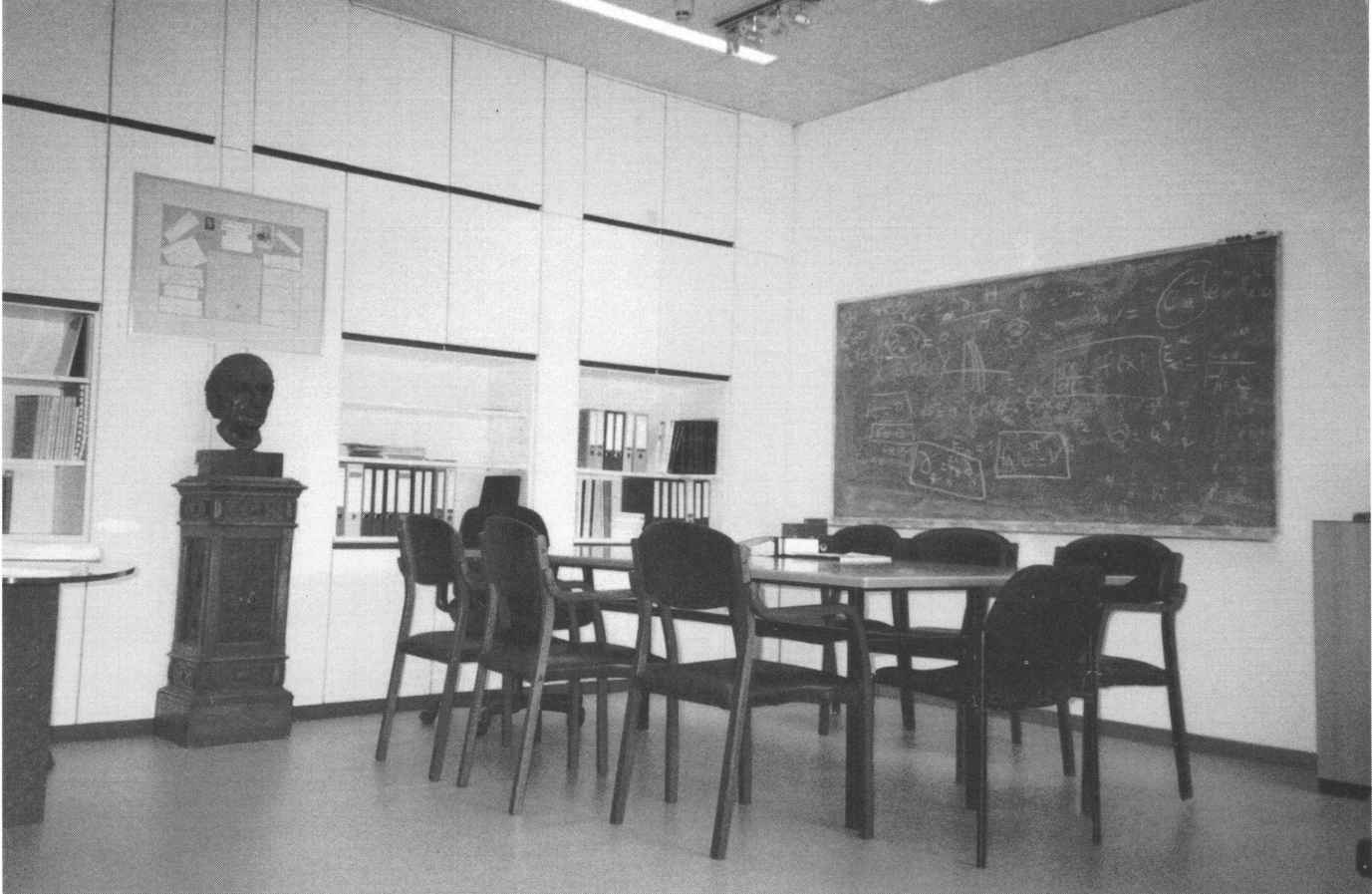
普里戈金生前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办公桌(彭丹歌摄)。
(一)
本书的作者伊利亚·普里戈金教授是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索尔维国际物理学和化学研究所所长兼美国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统计力学和复杂系统研究中心主任。他的原籍是俄罗斯,1917年1月25日生于莫斯科,父亲罗曼·普里戈金(Roman Prigogine)是化学工程师。1921年随其家庭移栖国外,经过几年漂泊不定的生活之后,于1929年定居比利时,1949年取得了比利时国籍。
普里戈金在布鲁塞尔上小学和中学,青年时代的兴趣集中在历史学、考古学和哲学方面,对音乐特别是钢琴也很爱好。后来他转攻物理学和化学,1941年在比利时自由大学获博士学位,1951年起任该校理学院教授,曾任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长,后被选为美国全国科学院外籍通讯院士,不久前又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他还做过不少国家的客座教授,获得过多种奖金和奖章。
普里戈金长期从事化学热力学方面的研究。早期他研究的问题有溶液理论、对应状态理论以及处于凝结阶段的同位素作用理论,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他对历史和哲学的爱好激发了他探讨时间单向性的兴趣,他在物理化学领域中进行的大量工作使他从感性和理性上丰富了对不可逆过程的理解。普里戈金在回顾他的科学生涯时曾经写道:“热力学为我们提供的这许许多多的观点和各种各样的前景中,使我感受强烈,并抓住了我的注意力的是这样一点:一切都明显地表现出‘时间的单向性’这个不可逆现象。从这点出发,我总是把任何一项富有建设性的作用都归功于某种‘过程’,而不是采取传统的‘静止’的态度对待”。 (1) 当人们还将不可逆现象当做令人讨厌的因素而极力回避的时候,他却敏感地意识到对不可逆过程的研究可能会带来重大的成果。此后,他集中精力研究不可逆过程热力学,于1945年得出了最小熵产生原理,这一原理和翁萨格倒易关系一起为近平衡态线性区热力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普里戈金早期对热力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最小熵产生原理在近平衡态线性区取得的成功促使他试图将这一原理延拓到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去,但是,经过多年努力,这种尝试以失败告终。普里戈金从挫折中吸取了有益的启示,认识到系统在远离平衡态时,其热力学性质可能与平衡态、近平衡态有重大原则差别。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系统的状态出现了多种可能性,表现出更加复杂的性质,因此研究工作应当另辟蹊径。以普里戈金为首的布鲁塞尔学派在这一新认识的指导下重新进行了探索。经过多年努力,他们终于建立起一种新的关于非平衡系统自组织的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普里戈金在回顾他们这一段科学历程时曾经说,当他了解到翁萨格倒易关系和最小熵产生原理一般说来只是在不可逆现象的线性范围内有价值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翁萨格倒易原理之外,但仍在宏观描述的范围之内,远离平衡的稳定状态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些问题使我们耗费了近20年心血,即从1947年到1967年,最后终于得到了‘耗散结构’的概念。” (2)
1969年,普里戈金在一次“理论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国际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这一理论指出: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不管是力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乃至社会的、经济的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经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乱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这种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形成的新的稳定的宏观有序结构,由于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或能量才能维持,因此称之为“耗散结构”。普里戈金在谈到宏观现象中存在的两种结构——耗散结构与平衡结构之间的区别时曾经指出:“平衡结构不进行任何能量或物质的交换就能维持。晶体是平衡结构的典型。”“反之,‘耗散结构’只有通过与外界交换能量(在某些情况也交换物质)才能维持。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是热扩散电池,其浓度梯度由能量流维持着” (3) 这就表明,是否耗散能量是两类结构的根本区别。
耗散结构理论研究一个开放系统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从混沌向有序转化的共同机制和规律。这一理论不仅可以应用于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领域,而且还成为描述社会系统的方法。因而受到了不同学科的学者的广泛重视。普里戈金由于对非平衡热力学特别是建立耗散结构理论方面的贡献,荣获了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
(二)
本书对耗散结构理论作了一个简明、扼要而又比较系统的介绍,为具有一定物理学、化学和热力学知识的读者说明了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怎样从混沌无序演化为复杂的结构,例如大气的循环花纹、化学波的形成和传播、单细胞生物的聚集等。本书还着重讨论了时间问题。我们知道,在经典力学中以及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力学中,时间仅仅是描述运动的一个几何参量。力学问题可以放在四维时空中研究,它们的基本方程,无论是牛顿运动方程,还是薛定谔方程,对于时间来说都是可逆的、对称的。在这些方程中,过去和未来没有区别,因而它们所描述的是一个静止的世界。在物理学中第一个描述了时间的不可逆性的是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定律用熵增加原理第一次把进化的观念、历史的因素引入到物理学中。在本书中,普里戈金对研究时间的不可逆性,即过去和未来的不对称性,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他描述了一个进化着的而不是静止的世界。本书的主题是讨论不可逆过程,讨论时间在描述物质世界演化过程中的作用。在普里戈金看来,不可逆性可能是有序的源泉、相干的源泉和组织的源泉。为此,他曾打算将本书取名为“时间——被遗忘的维数”,以说明他对时间问题的重视。
《从存在到演化》一书共分三篇十章,前面有一个序言,后面有四个附录。在第1章中作者着重讨论了物理学中的时间问题,说明了有不同层次的时间概念。然后,他将物理学按对时间的观念不同分为存在的物理学和演化的物理学两大部分。上篇讲存在的物理学,包括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两章,存在的物理学对时间是可逆的,即过去和未来是对称的。中篇讲演化的物理学,包括热力学、自组织和非平衡涨落等三章。演化的物理学对时间是不可逆的,即过去和未来是不对称的。下篇讲从存在到演化的桥梁,其中的动力论、不可逆过程的微观理论和变化的规律等三章,主要讲从存在的物理学到演化的物理学的过渡。在第二版中增加的第10章“不可逆性与时空结构”通过构造对称破缺变换使不可逆性和不允许时间反演的半群联系起来,从而把热力学第二定律概括为一个动力学基本原理,在我们关于空间、时间和动力学的概念上导出了深远的后果,并在存在和演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样,本书就比较全面而扼要地勾画了耗散结构理论的轮廓,叙述了普里戈金自己的科学观点,并阐发了其工作的哲学意义。
与普里戈金和尼科利斯合著的另一本专门的学术著作《非平衡系统的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 in non-equilibrium systems,New York,Wiley,1977)一书不同,本书对耗散结构理论的数学部分作了较多的删减,突出了它的物理内容和科学意义,是一本具有导论性质的入门书。正如普里戈金本人在为本书所作的序中所说的:“本书在一个中等水平上写成,因此要求读者熟悉理论物理学和化学的基本工具,不过,我希望,通过采用这种中等水平,我可以为大量的读者提供一个简捷的介绍。”因此,本书可供各个领域中具有一定物理学和化学知识的读者学习、研究和应用耗散结构理论时参考。
(三)
普里戈金教授对中国十分友好。1978年6月,钱三强副院长率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比利时等西欧各国时,开始与以普里戈金为首的布鲁塞尔学派有了直接联系。1978年11月,郝柏林等同志应邀到布鲁塞尔参加了普里戈金主持的第十七届索尔维国际物理学会议。1979年8月,普里戈金教授应钱三强副院长邀请来华讲学,到西安参加了我国“第一届全国非平衡统计物理学术会议”并在会上作学术报告。1980年7月,布鲁塞尔学派另一位主要成员尼科利斯教授应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邀请来华讲学,出席了在大连召开的“第二届全国非平衡统计物理学术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近几年来,普里戈金曾多次邀请我国学者到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索尔维国际物理学和化学研究所和美国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统计力学和热力学研究中心去工作、进修、访问,并经常与我国有关单位交换学术资料,交流彼此的研究成果,这对我国在非平衡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方面的研究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普里戈金非常关心本书在中国的出版。1979年他来华访问前,就向译者赠送了此书的英文打字稿,此书正式出版后又向我们赠送了本书的德文版(1979)和英文版(1980)。1980年,他亲自为本书的中文版写了序言。1984年本书出了第二版,他不仅立即寄来了修改稿,并且又给中文译本写了一个序言,说明了修改的原因和增加的主要内容。在前后两个序言中他热情洋溢地表达了他对中国学者的友好感情和对中国哲学的浓厚兴趣,并希望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能对中国广大青年学者研究耗散结构理论提供一定的帮助。
本书的译文初稿是根据1979年的英文打字稿翻译的,以后又根据1980年和1984年的英文版并参照1979年的德文版作了增补校订。
在书中人名的译法上,凡在历史上较为著名、已为各界公认的人名,一般采用习惯译名,并以国内主要辞书上的译名为准。但本书所涉及的人名国籍较多,而英文版中所列的人名均为英文译音,因而给中文译法带来一定困难。我们在翻译时力求准确,但也难免有误。
由于本书涉及的知识领域很广,新的科学名词较多,译者的科学知识和外文水平有限,因而译文肯定有不少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在翻译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郝柏林、漆安慎、陈浩元、安文铸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谨记
1984年12月
————————————————————
(1) 普里戈金,《我的科学生活》,参见《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2) 普里戈金,《我的科学生活》,参见《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3) 普里戈金,《结构,耗散和生命》,参见《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