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Postscript of Chinese Version
哈维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他的工作标志着新的生命科学的开始,属于发端于16世纪科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维也因为他对心血系统的出色研究,使得他成为与哥白尼、伽俐略、牛顿等人齐名的科学革命的巨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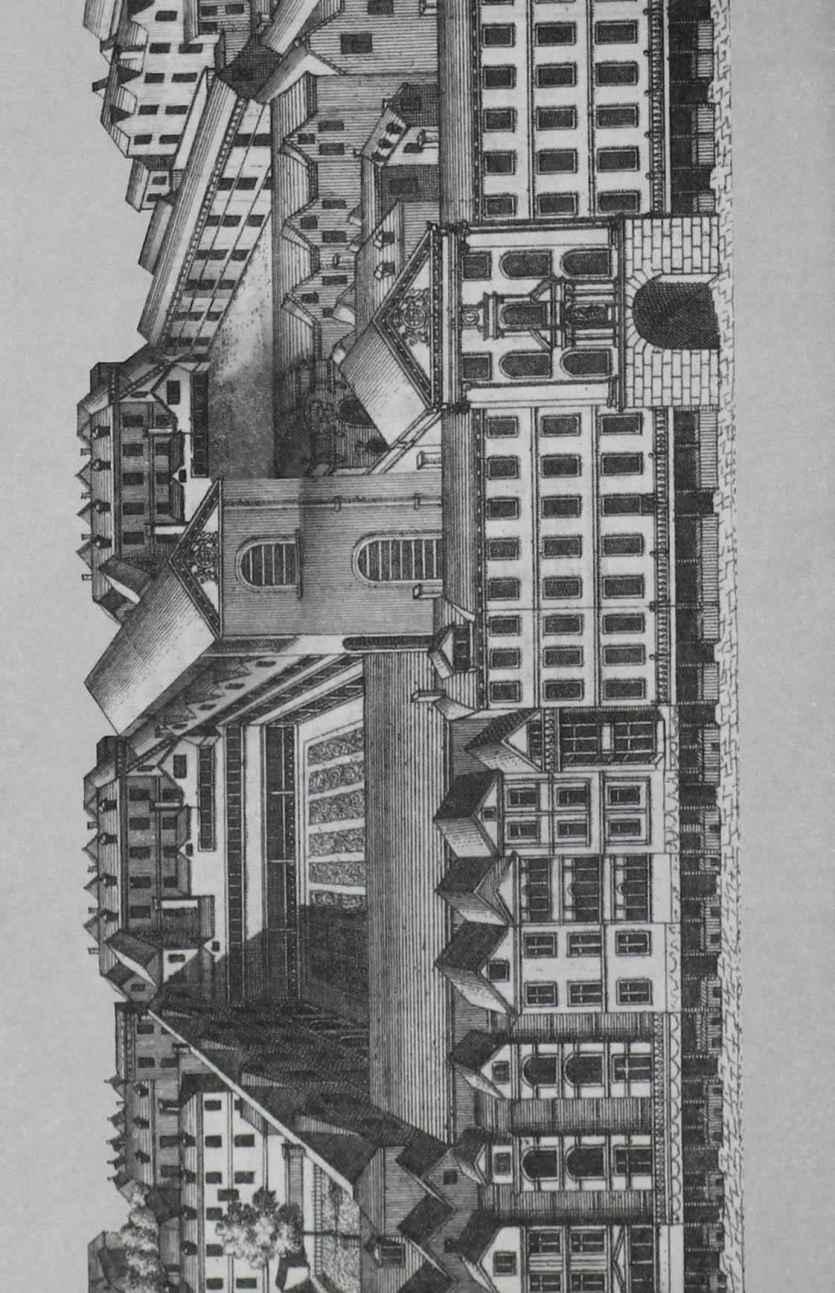
1723年的伦敦圣巴塞洛缪医院
1628年,英国医生、生理学家、胚胎学家威廉·哈维发表了他的划时代著作《关于动物心脏与血液运动的解剖研究》(Exercitatio Anatomica de Motu Cordis et Sanguinis in Animalibus)(中译名称以《心血运动论》驰名)。这部书的问世标志着近代生理学的诞生,同时也奠定了哈维在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哈维出生于英国肯特郡福克斯通镇,排行老大。他的父亲托马斯·哈维是当地一位富裕的地主,曾做过福克斯通镇的镇长。哈维在坎特伯雷的著名私立学校金学院(King's School)受过严格的初、中等教育,15岁时进入剑桥大学学习人文学科,1597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继续在剑桥学习了两年与医学有关的一些学科。为了深入学习医学,哈维来到意大利帕多瓦大学专门学习医学。帕多瓦大学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高级科学学府,科学革命时期的巨匠伽利略当时就在这所大学执教。哈维的老师当中不乏大科学家,如著名生理学家、解剖学家法布里修斯。1602年哈维在帕多瓦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证书。
自1603年起,哈维开始在伦敦行医,不久他与伊丽莎白女王的御医朗斯洛·布朗的女儿结婚。哈维无儿无女。这桩婚姻对于哈维的事业大有帮助。1607年哈维被接受为皇家医学院成员,1615年他被任命为卢姆莱(Lumleian)讲座的讲师,1616年被任命为圣巴塞洛缪医院的医生。
在哈维的职业生涯中,他与皇室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主要靠他的岳父的关系,哈维先后做过国王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御医。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都曾经观看过哈维的科学实验;尤其是查理一世,不仅与哈维的私人友情甚笃,而且对哈维的科学工作很感兴趣。查理一世经常与哈维一起从事一些科学实验,其中就包括有关心血运动的实验。查理一世还将皇家公园的鹿提供给哈维研究动物的生殖。哈维一直效忠查理一世国王,即使在英国国内战争期间也是一样。1649年查理一世被绞死后,哈维便失去他的事业上的最重要的支持者。自此以后,哈维的科学活动逐渐衰微。
英国国内战争结束后,哈维因为忠于查理一世而被克以罚金2000英镑,并被禁止进入伦敦城。1657年,79岁的哈维死在伦敦郊外他弟弟家。
哈维一生中写过大量的科学论著,但是只发表了《心血运动论》和《论动物的生殖》(心血运动与动物的生殖是哈维毕生研究的两个主要领域)以及几封为《心血运动论》辩护的公开信。在哈维晚年时,他在伦敦的寓所遭到抢劫,后又被大火焚烧,留下的手稿仅有两部,一部是论述感觉的,一部是论述动物运动的。
哈维生于文艺复兴的后期、宗教改革的中期,正是社会剧烈变革和学术蓬勃发展的时期,中世纪的神权统治以及思想的禁锢受到动摇。在英国,国王享利八世(1491—1547)于1534年与教皇决裂,实行宗教改革。享利八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继任王位以后,继续宗教改革,加强英国国教的地位,促进工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确立了英国的海上优势。在以后的詹姆斯一世(1566—1625)和查理一世(1600—1649)时期,虽然英国的经济发展很快,文学、艺术和哲学有很大的进展,涌现了像莎士比亚(1564—1616)这样的文学泰斗和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这样的哲学大师(哈维与培根交往甚密),但是国内的矛盾也愈发尖锐,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保皇派与新兴的资产阶级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以至在1642年爆发了国内战争,战争到1646年才结束。
哈维生活的时代正是科学革命时期。早他一世纪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1543)提出日心说,揭开了科学革命的序幕,开普勒(1571—1630)从数学角度增加了哥白尼体系的精确性,并且提出了行星运行三定律,伽利略(1564—1642)利用望远镜对天体的观测,为哥白尼和开普勒的学说提供了确切的依据。哈维在帕多瓦大学攻读医学课程时,伽利略在那里教授数学。我们不清楚哈维是否与伽利略有过直接的接触。但是帕多瓦大学的新的科学思想氛围对哈维的思想无疑有很大的影响。
哥白尼的日心说动摇了影响西方人上千年的、被教会推崇的托勒密地心说。在科学革命时期,另一被教会视为权威的盖仑的心血运行观点也遇到了挑战。
盖仑(Claudius Galenus或Galen,约129—200)是古罗马时期的医学家,他是继希波克拉底之后最著名的医学理论大师,他把古希腊医学与生理学、解剖学加以系统化,并且在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和医疗学等方面都有许多重要的发现。他一生著述甚丰,约有400种,留下来的著作有50本左右。他的解剖学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论解剖标本》和《论静脉和动脉之解剖》等。盖仑解剖学方法包括躯体解剖和脉管解剖,但是他的一些观点是想象的产物。他提出“元气”是生命的要素,“动物元气”位于脑,脑是感觉和活动的中心,“生命元气”在心脏中与血液混合,心脏是血液运动的中心,并且是调节体热的中心,“自然元气”从肝到血液中,肝是营养和新陈代谢的中心。他认为从食物中摄取的有用部分以“乳糜”的形式进入肝脏,再变成血液,在肝脏调制成的血液由静脉运送到右心室。他发现心房瓣膜的作用是阻止血液倒流,但他认为并不能完全阻止。盖仑认为血液可以透过心室间的隔膜从右心室流到左心室,在左心室,静脉血中的烟气与废物被分离出来,通过肺静脉排到肺里;空气从肺进入左心室,在左心室空气和元气与血液混合成鲜红的动脉血流到躯体的各个部分。在盖仑看来,血液在体内并不是循环的,而是在心脏和肝脏产生,通过动脉和静脉向身体各部分输送。盖仑还提出心脏也负责呼吸,心脏舒张时吸进空气,收缩时排出空气。
盖仑的学说基本上与基督教的教义相符合,例如他认为身体是灵魂的外壳,人是神造的等。所以他的权威性受到教会的长期支持。直到文艺复兴时为止,盖仑的解剖学观点曾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不允许批判或用实验去验证。提出质疑的人,常被视为异端。
尽管直到哈维时代还没有多少人(包括哈维本人)公开指责盖仑的观点,但是自从16世纪初期开始,一些学者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开始动摇盖仑的权威性。
1543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发表的同一年,时任帕多瓦大学医学教授的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发表了《人体的构造》一书。维萨里在书中虽然表达了对盖仑的崇敬,但还是对盖仑的一些观点提出怀疑。例如,维萨里指出,心室之间的心肌比较坚韧,血液不可能透过。此外,维萨里强调了解人体结构的最好方法是通过直接解剖人体,而不是通过阅读书本,或只是通过解剖动物。西班牙哲学家、医学家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 1511—1553)在他1553年发表的《基督教的复兴》一书中,提出心室不存在隔膜,血液只有通过进出肺的血管从右心室到达左心室和主动脉。塞尔维特的这部书主要是一部宗教、哲学书籍,出版后大部分书很快便被卡尔文教派的人焚烧了,他本人也很快被施以火刑。意大利人哥伦坡(Realdus Columbus, 1516—1559)在16世纪中期也提出心室间的隔膜无法透过血液,右心室的血液是通过肺循环到达左心室的。哥伦坡的学生及后来的同事切萨尔皮诺(Andreas Caesalpinus, 1524—1603)广泛传播了哥伦坡的思想。哈维在帕多瓦大学的老师、维萨里的学生、著名解剖学家和胚胎学家法布里修斯(Girolamo Fabricius, 1537—1619)积极倡导维萨里的观点,并且发现了静脉瓣,但他当时还不清楚静脉瓣的作用。
尽管有一些解剖学家和医学家的出色工作,但是直到哈维,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心血观点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在广大医学工作者以及普通人的心目中,盖仑的观点依然是不能更改、绝对正确的。哈维的工作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
1616年,哈维在开设卢姆莱讲座时,就开始向听众传播他的心血运动观点,这些观点收在他1628年出版的《心血运动论》一书中。
哈维的工作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和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并没有明显直接地批驳盖仑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而且在《心血运动论》一书中尽量用他们的话作依据。他的哲学框架仍然是传统的,很少当时流行的机械、化学哲学的成分,他所使用的方法主要还是解剖与观察,而且他似乎比同时代的其他解剖学家更重视功能的研究。
然而,哈维的观点之所以能够彻底改变人们的思想,主要在于他在一本书中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其中包括人的临床观察、尸体解剖、许多种类动物的解剖与观察,而且利用定量思想、逻辑分析和生理测试,从各个方面证明心脏是一个可以泵出血液的肌肉实体,血液以循环的方式在血管系统中不断流动。
哈维彻底否定了心脏的心室之间可以透过血液,指出右心室的血液通过肺循环流到左心室。他证实了心脏瓣膜的作用是防止血液倒流,证实了静脉瓣的作用是防止静脉中的血液以离心脏的方向流动。他通过定量计算和逻辑分析,证明人体及一些动物体内的血量是有限的,血液只能以循环的方式在体内流动,而并非像盖仑所说的血液可以通过食物的消化不断地直接提供到心脏和血管系统。他证明动脉是将血液从心脏输出的血管,静脉是将血液输回心脏的血管,这两个血管系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当剖开静脉,不仅静脉中的血液,而且动脉中的血液都会流空,反之亦然。他说明左右心房和左右心室之间的联系途径,以及它们各自不同的作用。他利用比较解剖的方法,说明了高等动物以及人与低等动物的心血系统的差别,说明了胚儿与成年人心血系统的差别。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哈维从各种角度,利用大量证据证明血液在体内以循环方式流动。
哈维的方法是很精巧的。他反复利用定量方法,这在他以前以及同代人的生命科学研究中是不多见的。在说明心脏泵出的血量和证明血液循环时他都利用了这种方法。哈维清楚地认识到活体解剖方法在了解人体心血系统方面的局限性,他便利用临床观察、大型哺乳动物的观察,以及通过解剖活的低等动物,来作弥补。例如,利用人以及高等动物,很难清楚地观察心脏的搏动,哈维便通过对心跳较慢的冷血动物的观察来研究心脏的搏动;再比如,哈维还利用放大镜研究身体透明的河虾的心脏搏动。哈维尽可能地利用当时可以利用的技术和技巧来掌握更多支持他的观点的证据,这样使他的心血运动观点显得相当有说服力。
哈维心血运动体系当中,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体循环当中,动脉与静脉之间的联系,但他已经设想到类似毛细血管结构的存在。在哈维去世后的第六年,即1661年,意大利人马尔比基(Marcello Malpighi, 1628—1694)利用显微镜证明了毛细血管的存在,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哈维的心血运动观点。
尽管哈维没有证明毛细血管的存在,尽管不是哈维首次提出血液循环观点——除了维萨里、哥伦坡、切萨尔比诺外,还有一些人在哈维之前提出过这种观点,实际上早在古希腊时期,希波克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提出过血液在体内循环流动的观点,尽管不是哈维,而是法布里修斯首先发现了静脉瓣,但是哈维在一本小册子当中,利用充分的证据和缜密的推理,使得血液循环流动的观点显得十分牢固、透彻、无可辩驳、令人信服。哈维虽然不是出于本意,但却彻底推翻了盖仑的心血运行体系,开创了生理学、解剖学的新时代。
哈维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他的工作标志着新的生命科学的开始,属于发端于16世纪的科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维因为他的出色的心血系统的研究(以及他的动物生殖的研究),使得他成为与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齐名的科学革命的巨匠。他的《心血运动论》一书也像《天体运行论》、《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体系的对话》、《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等著作一样,成为科学革命时期以及整个科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文献。
为便于中文表达,我在有些句子中加进了少量的短语或语词,皆以方括号标出。在翻译过程中,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潘承湘先生曾审校过部分章节,并对全书的翻译工作提出过一些意见。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刘兵先生多次督促,不断鼓励笔者的工作。在此我愿向他们表示我的诚挚谢意。笔者的中外文知识以及专业学术水平有限,翻译这样的著作实为一件诚惶诚恐之事,译文中的错误之处,还望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
于北京玉泉路
